美国的“大棒”曾挥向哪里
李俊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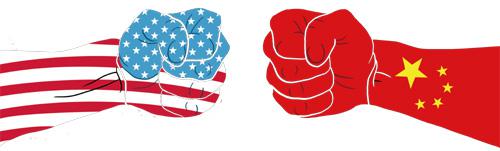
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新钢铝关税方案,决定对输入美国的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此举迅速引起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也受到了美国国内一些行业的批评。3月22日,特朗普于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在现场宣布“可能对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商务部、外交部与驻美使馆先后展示了坚定的报复能力与决心。一时间,“贸易战”言论甚嚣尘上,媒体、学者纷纷探讨中美貿易战的可能性与对策。揆诸历史,不难发现美国仰仗经济实力与市场优势是历次贸易战的主要挑起者。审视这些经典案例与各方的应对,或许对认识当前中美贸易有所裨益。
以邻为壑:斯穆特-霍利关税贸易战
南北战争后,在北方制造业集团及共和党代表的主导下,美国凭借贸易保护政策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和对发达工业国家的赶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受增加税收、保护战时工业与经济民族主义的驱使,建立高关税壁垒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美国也不例外:一方面通过高关税政策限制进口,另一方面凭借最惠国待遇原则获得进入他国市场的机会。
然而,此时从低强度、小规模的贸易保护到高强度、大规模且以相互报复为特征的贸易战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1930年,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美国总统胡佛签署了著名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扩大关税保护的范围并且将关税从39%提高到53%,迅速引发全球性的贸易战争。在这场贸易战中,东欧、北欧等小国不愿直接对美国进行经济制裁,它们或寻求其他大国的庇护,或与其他小国组成贸易区;而日本、法国、德国等大国则采取提高关税或控制配额等措施直接进行报复。英国在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的鼓动下也重回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列,建立起排他性的帝国特惠制。
关于此次多边贸易战的结果,经济学家至今未有笃定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衰退掩盖了贸易战的影响。然而可以肯定,它没有帮助各国挣脱大萧条的泥潭,世界贸易因此受到重创。美国投资与金融理论家威廉·伯恩斯坦写道:“西班牙的水果、加拿大的木材、阿根廷的牛肉、瑞士的手表以及美国的汽车从全世界的码头上消失了……所有国家都要做到自我供应充足,而不管这些行为有多么荒谬。”
贸易战的另一影响是美国国内的反思,罗斯福在“新政”中任命信奉自由贸易的赫尔为国务卿。在他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确立了美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并将制定关税的权力从国会让渡给总统,使其不再受保护主义利益集团之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便是拆除贸易壁垒,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遵循着自由贸易的信条,这也为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基础。
“公平贸易”对抗“自由贸易”:美日贸易战
战后,日本在查默斯·约翰逊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模式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其核心在于依托强大政府制定特定产业政策,不断增强纤维产业、科技产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成为美日贸易中的逆差国,日益面临日本商品的进口压力,同时难以打开日本国内农产品、公共采购等市场。不过由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过一系列贸易协议的形式“自愿限制出口”,美日摩擦没有升级为贸易战。

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的议题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半导体、芯片与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挤占美国市场,争端领域也从贸易延伸到金融货币领域。1985年,美、日、德、法、英五国签署《广场协议》以引导美元贬值,提升美国商品竞争力,但这一举措未能改善美日贸易逆差。此后,在里根、布什、克林顿三任总统时期,两国先后启动了“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与“日美经济框架对话”机制,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强。
追求“公平贸易”的克林顿政府不满“自由贸易”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主张对主要贸易顺差伙伴采取强硬措施,美日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日本被塑造为一个经济封闭、采取进攻性贸易战略以及无能且无意愿解决贸易不均衡问题的“异质国家”。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桥本内阁最终推行了“向国际社会完全开放、责任制与市场原则”导向的自由化改革。
多边贸易战中可能没有赢家,但双边贸易战中美国的优势终究会体现出来。《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应对乏术,经历了日元被迫升值而引发泡沫经济以及长期经济低迷的痛苦。但是美国强烈的外在压力也成为倒逼日本政府推进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动力。日美通过事务级官员对话、规制改革和竞争政策对话、财政金融对话等机制就改革议程进行持续沟通。在贸易争端中,日本充分利用WTO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诉讼,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改革进程,不仅在钢铁、汽车、胶片等竞争力较强的领域胜诉,还推动产品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等规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
上兵伐谋:美欧农产品贸易战
欧共体(欧盟)与美国同为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不存在经济、政治体制的相互指责,但由于欧共体在一体化过程中的共同经济政策表现出强烈的贸易保护倾向,美欧之间在农产品、工业产品及公共采购上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并且围绕相关领域展开了艰难谈判。不过欧共体灵活的应对策略与谈判技巧也最大限度地规避了损失,在历次贸易战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以农产品领域为例,欧共体所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要求成员国统一政策、取消内部关税与统一进口关税、提供高额补贴并建立农业基金,它不仅使欧共体农产品从进口转变为出口,而且日益侵蚀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尤其是随着欧共体成员增加,美欧之间围绕市场进入、农业补贴、农业产量等议题的冲突更加激烈。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后,欧共体将西班牙饲料谷物关税从20%升到100%,控制大豆与豆油的进口配额,规定葡萄牙谷物市场的15%保留给欧共体成员。此举迅速引起大豆出口国美国的威胁与报复,二者围绕配额控制进行的制裁直到1991年才结束。
贸易战本质上是国家决心与意志的较量,在谈判过程中需要巧妙适时地向对方展现制裁或报复的决心、谈判的底线以及妥协的意愿,协议通常在谈判即将结束前几个小时才能达成。在历时8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欧就农产品问题进行激烈争吵,但是双方运用丰富的贸易威胁与妥协策略最终避免了双输的结果。
1992年10月,在面临谈判无果的可能时,美国威胁即将发动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声称如果欧共体不降低油籽产量,美国将对3亿美元粮食加征200%的惩罚性关税,并于当年12月5日开始生效。美国的强硬最终促成11月美欧“布莱尔协议”的达成。欧共体则在谈判前就形成统一的政策立场,利用法国等农业大国的坚定立场“束缚双手”以提高谈判时的要价,此后法国以谈判破裂相要挟,坚决拒绝批准对自己不利的“布莱尔协议”,最终迫使美国让步,修改协议内容。
某种程度上,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与美日、美欧贸易战均有相似之处。美国指责中国利用非市场手段进行不公平贸易与声称日本是“异质国家”的论调相差无几,中美关于“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争论也与美日、美欧的争吵颇为相似,日本与欧共体的经历为中国这个在贸易战上不太“成熟”的国家提供教训与经验。
从美国发动历次贸易战的经验来看,一方面中国需要避免美国联合欧盟及其他国家对中国形成包围,防止将多边贸易争端转变为双边贸易战;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制定切实、灵活的谈判策略,针对性地做好反制美国农产品、电影、汽车或飞机等产业的准备,以增加谈判筹码,同时需要利用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作为解决争端的途径。
从长远来看,完善贸易保护相关立法应作为今后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一项主要任务,例如欧盟就针对美国的“301条款”制定了《贸易壁垒规则》,最大限度地增加反击与谈判的空间,避免完全屈服在美国的“大棒”之下。最后,中美贸易争端也应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以及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向国际开放的动力。
“301条款”
“301条款”源于美国《1974年贸易法》,该法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标志。其核心是授权总统采取单边措施迫使对方改变不公正、不合理、歧视性或限制美国商业的贸易行为。《1988年贸易法》进一步增强了美国进行单边报复的合法性,提出“特别301条款”与“超级301条款”,分别针对没有充分知识产权保障的国家与对美设置贸易壁垒的国家。
美國以上述法令为依据多次对欧盟、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等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但大多以签署贸易备忘录、在WTO机制下达成谅解等和平方式规避了报复升级。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贸易行为展开调查。今年3月22日,最终调查报告称中国利用外国所有权限制与行政审批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指责中国进行不合理的对外投资以及利用网络入侵窃取知识产权与敏感商业信息,以此作为挑起贸易争端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