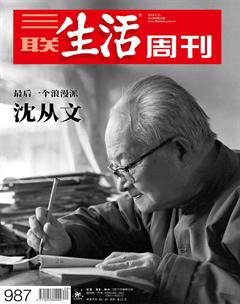丁玲的选择
傅婷婷

作家丁玲(摄于1980年12月)
当时他们都住在北京香山一带,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的图书馆工作,丁玲和胡也频住在香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中的房租相对便宜。三人都喜欢文学,住得又近,在穷困的日子里,有很多共同语言。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曾回忆,丁玲和胡也频二人有时绝了粮,也和他吃过几次“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
虽然穷困,这段时光却是三个人友谊最单纯的时期。后来,胡也频就义,丁玲和沈从文选择的道路不同,沈从文对丁玲在患难时帮助,1949年后丁玲也曾在自身难保的时候帮助过沈从文。然而,直到两人在80年代去世,沈从文和丁玲,在各自的危难中帮助彼此,却再也没有回到这简单的时光里了。
从相识到《红黑》杂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艺青年们扎堆的地方。报纸杂志、出版社很多,也有很多发表文章的机会。
王增如在丁玲晚年曾担任丁玲的秘书,她和她的爱人李向东合著了《丁玲传》。李向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们三人在艰难日子里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那时,沈从文对丁玲和胡也频他们一直是很好的。”
1928年7月,经沈从文介绍,胡也频到当年年初创刊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工作,编辑《红与黑》副刊,胡也频、沈从文和丁玲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歌。当时,胡也频已经成为丁玲的爱人,在杂志社工作后,胡也频和丁玲的穷困的生活好转了很多。《丁玲传》记载:“他们有了点钱,搬到了地处法国租界的萨坡赛路196号,住三层后楼,每月30元房租,另花10元钱把饭食也包在房东家。住在附近的沈从文也把伙食包在这里,每天过来吃饭。”
三个月后,三人想创办《红黑》月刊,在湘西土话里,“红黑”即“横直”“无论怎样都得”的意思。他们选中了萨坡赛路204号,合租了一幢三层楼的一楼一底房子,丁玲和胡也频住在二楼,沈从文住在三楼。三人筹备了两个月,1929年初办了起来。然而,这本杂志只办了半年就停刊了。后来,根据丁玲的回忆,停刊的原因一方面是资金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胡也频读了俄国左翼文学家的作品开始左倾,沈从文和他们“在思想上碰不拢来”,在那样的时代,三个人选择的路也开始有了分歧。丁玲曾说,沈从文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但是选择的不同,还是让三个人渐行渐远了。丁玲曾在80年代说过:“我们同沈从文,是既有共同语言,又没有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我们都穷愁潦倒,没有出路。但我们的理想前途不一样,又没有共同语言。”
和丁玲不同,沈从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被认为是“现代评论派”,对革命一直保持距离。丁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受到了亲戚的冷落。她的母亲有民主思想,丁玲小时候就认识了母亲的结拜姐妹,她称为“九姨”的向警予,后又认识了瞿秋白、王剑虹。
在1950年11月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丁玲写了三个人当时思想的差别:“那时我们三个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李向东分析道:“沈从文在北平经常投稿的《现代评论》,主要是留洋回来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来看,是生活比较优裕的阶层,《现代评论》把沈从文当成一个骨干的作者。这批人跟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是不同的人。革命者日子往往过得很苦,对社会不满,要改变和推翻现实。”
王增如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丁玲的经历,也是她和沈从文选择不同的重要原因:“1922年,她在平民女校的时候,就接触到革命了。认识了王剑虹、李达、王会悟。当时她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又不系统。她和王剑虹才跑到南京,见到了瞿秋白,瞿秋白又介绍她们俩到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比平民女校正规一点,然后又学了一些东西,这时候她接触的共产党就更多了。但是那时候她不入党,不愿意受约束。胡也频牺牲之后,她觉着凭着自己东闯西闯的不行,要加入到组织中去。胡也频牺牲一年后,丁玲入了党。《北斗》是她参加的第一份革命工作。当时,胡也频如果不牺牲,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开会。丁玲要求去苏区,跟张闻天沟通后,张闻天建议她留在上海办杂志,1931年,她主编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丁玲与胡也频的合影(摄于1926年6月)
营救:胡也频和丁玲被捕
1931年,沈从文和丁玲一起经历了的一个艰难时刻,是胡也频被捕。
1931年初,元旦过后,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去看望丁玲和胡也频,看到当时胡也频还穿着短衣,二人生活窘困,便把一件新的海虎绒袍子借给了胡也频。时隔半月,胡也频被捕,成为历史上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胡也频被捕時,胡也频和丁玲的孩子蒋祖林只有两个月大。丁玲到处奔走。《丁玲传》记载:“沈从文十分着急,找了徐志摩、胡适,又专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接到沈从文救助后,蔡元培曾给当时上海市市长张群写信,托他设法。后来郑振铎和陈望道介绍丁玲去找邵力子,于是沈从文又陪丁玲第二次去南京。邵力子给张群写了信,蔡元培又给张群写信,回到上海后,沈从文拿信去见张群,被告知,胡也频和其他人已被转移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了。
“1931年1月下旬的一天,天很冷,飘着雪花,沈从文陪着丁玲去龙华探监,送被子和换洗衣服,但因胡也频属要犯,等了一上午也不让见。丁玲和沈从文想了半天,请求送十元钱进去,要求得到一张收条。”
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回忆:“一会儿,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丁玲大声喊了起来,胡也频却来不及回应,就被推走了。
沈从文陪丁玲去了南京,继续设法营救胡也频。后二人辗转乘火车回到上海。丁玲回忆:“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一个相片册子,里面有也频。”“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相。”“这天夜晚12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2月7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3月21日,沈从文陪丁玲把孩子蒋祖林送回了湖南老家,路上走了10天。
1933年,丁玲被捕。沈从文立即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两篇文章,对当局提出抗议。后写信给胡适求助,希望胡适“说几句话,提醒一下政府”,不要一捉到左翼作家就杀,“其实是用不着这样严厉的”。又写了10余万字的《记丁玲女士》。
“丁玲对于沈从文产生一点芥蒂,缘于有人告诉她两件事。一个是,上海左联为营救丁玲,给沈从文写信,被复信冷淡拒绝。另一件是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路过常德,有师生建议他去看丁玲的母亲,他没去,并且在丁玲的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
事实上,胡适让沈从文对丁玲被捕事件后来安下心来。胡适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写道:“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
丁玲当时是一个中国最当红的女作家,她的被捕马上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李向东分析:
因为当时他们住的是由外国人管的租界,法租界是法国人管的,国民党不经过法国领事馆同意和批准,就到租界来抓人,是不行的。声援活动以来,开始不承认抓,又不能放,又不敢杀,就把丁玲在南京软禁起来了。
丁玲失踪后,左联还有许多国际友人都掀起了营救丁玲的舆论。沈从文也写了文章营救,但是他可能不愿意跟左联这边一起行动,所以左翼的人找他,他是拒绝了。沈从文又信任胡适,相信了国民党的解释,也没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让她到上海来打官司。也许跟丁玲传话的人,也有一定的倾向性。1936年的时候,他们中间就已经有了一些误会,只是80年代丁玲复出后,才看到沈从文的《记丁玲》,当时的特殊环境让丁玲说了一些火气很大的话。
丁玲1933年被捕之后,没有被关押在监狱,也没有坐牢,没有受刑。国民党每个月给她100元生活费,所以1955年,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她的这段历史就被说成是一个污点,说成是被捕期间有变节行为。
误解
解放初期,沈从文被排除在新中国的文艺圈子之外,去了故宫博物院搞文物研究。其间,遇到了几次困难,找丁玲帮忙。
沈从文的老乡、曾任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曾在1991年《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中,把1949年3月沈从文的自杀,归结为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斥反动文艺〉对他的评价与丁玲的态度》,“丁玲的态度”是指在这段时间沈从文曾经找过丁玲,但是丁玲态度十分冷淡。
据王增如和李向东二人考证,这个记载是有误的。当时丁玲其实并不在北京。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分析沈从文的自杀:“政治的压力确实存在,但‘未必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认为其中还有沈从文当时面临的感情危机问题。
1949年6月8日,丁玲到了北京,6月10日就去看望了沈从文。王增如和李向东认为,以沈从文的性格,后来他去找丁玲,还是把丁玲当成可以信任的朋友:“丁玲两次探视,沈从文并未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对丁玲的印象也绝非‘大失所望。”“他实际上是把丁玲视为新政权文化界领导层里,能说得上话的第一人选。”
1955年11月,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遇到难处,写信给丁玲:“丁玲: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感谢党对我的一切的宽待和照顾,我正因为这样,在体力极坏时还是努力做事。可是怎么做,才满意?来帮助我,指点我吧!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当时,中国作协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党组扩大会已开完,丁玲正在听从发落,不便会见沈从文。第二天给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秘书长严文井写信,提到“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如果文井同志能够同我一道见他则更好”。
在动荡的年代,丁玲和沈从文在文学和政治上都选择了不同的路,丁玲认为文学是实现政治的途径。王增如分析了丁玲为何如此选择:“现在是左翼革命文学受冷落的时候,有些年轻人不大喜欢革命作家、革命文学。但是,文学根本就没法脱离政治,喜欢革命文学也好,不喜欢革命文学也好,这里面本身就有政治倾向。原来我曾经听丁老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话有道理。丁玲出生于一个有钱的大家族,但是这个家族里的许多人好吃懒做,躺在床上抽大烟。她从小看见他们那样的堕落,特别是她父亲死以后,寄人篱下的生活对她的影响非常大。丁玲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的性格,也感觉到这个社会不合理,后来又接触了一些进步的共产党人,比如向警予。丁玲也觉得女性要自强,所以走上了革命道路。到了延安以后,她觉得女人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到压制和不公平待遇,就写了《三八节有感》。”
“文革”结束以后,沈从文和丁玲,都各自经受了很多,到了晚年才都过上稳定一些的日子。
在1980年,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中驳斥沈从文《记丁玲》,成为人们热炒的话题。虽然《记丁玲》写于30年代,但丁玲却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在王增如看来,两个人真正矛盾爆发还是由于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引起的,当时丁玲刚刚复出,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的理由就是丁玲被捕后还和冯达一起生活,他们又认为冯达是叛徒,所以,丁玲历史上是有污点的。而沈从文的《记丁玲》中,又讲到了冯达。丁玲感到,这会给她的平反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王增如说:“不管如何,丁玲和沈从文纵然在政治和文艺观点上不一样,但一直都有朋友的感情,曾经在30年代和50年代对彼此伸出援手。”她回忆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细节:“一个杂志社的编辑看了丁玲的文章,就写了批判沈从文的文章,重新批判《记丁玲》,厚厚的一沓子。丁玲很平和地说,算了,他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别发了。”
在王增如的印象里,晚年的丁玲,想要的就是安心地写作。她回忆道:“晚年我来到她身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給她找房子。她复出后,好多人非常想见她。在木樨地,来找她的记者和熟人很多,她觉得不能安心写作,我到处给她找房子,颐和园、党校……最后本来想回到桑干河附近的一个小院,她想离开纷杂的行政事务去写作。她想要通过写作表达她想要表达的东西。她当年写小说,办杂志,办《红黑》,办《北斗》,都是希望能够写出自己想说的话。”
(参考资料:《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记丁玲 记丁玲续集》,沈从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丁玲散文选集》,武在平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