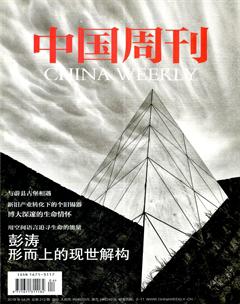栖息地共管
在现实里,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应运而生的。就是说,我们身边的环境是因为我们的意识、习惯和目标而建构起来的。其实人类是环境最大的危急因素。如果我们依然以这个环境内的思维来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恶化依然会延续。
靠山吃山的彝族、傣族村民也要致富。在国家水电站、野生动物保护法、当地发展利益等因素相交替的情况下,在偏远地区如何做好保護?国有林、生态林、公益林大部分都被划为保护区,但在西南山地还存在绿孔雀这样普遍的保护空缺。保护绿孔雀需要有突破。我们需要科学的认知、乡村老百姓参与、民间机构推动,需要政府的牵头,需要公众支持。
重新认识眼前的环境
专家建议,“要跳出水电站影响,跳出绿孔雀濒危的思路”来设计方案。在大部分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域,虽然已明确为国家保护动物,但缺乏具体的保护条例和管理办法、措施,公众的保护意识也亟待加强。做公共事件与公共政策影响力评估的林杨建议,要对当地的社会形态做描述性调查,以“绿孔雀生存繁育需求与当地群众在种植、畜牧、采集等方面的生活、生产方式有一定的冲突”为主题,整合信息作为形成方案的基础。
西南林业大学的李永杰高级工程师向大家介绍了南滚河佤族公众亚洲象传统知识调查的方法用参与式访谈、关键人物访谈和三角核实方法。南滚河流域的佤族村寨的经验是,以见过亚洲象的老人和猎人为访谈对象,结合保护的话题,鼓励被访者谈出对亚洲象的传统知识,和亚洲象保护措施等等。经过参与式的分析发现,保护区里没有了以前的刀耕火种,缺乏了大象吃的食物,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适当轮耕种植大象喜欢吃的食物,砍去部分竹林,促进森林绿草更新。他建议利用乡村的乡土知识和经验来重新形成保护意识和村规民约,建立绿孔雀和人一村的友善关系。韩联宪也说,响鼓箐的滇金丝猴得了绦虫病,根据本地傈僳族村民的经验,喂槭树籽和南瓜子发现效果很好。要挖掘一些在保护上面有用的东西,不能直接否定老百姓不懂科学,他们的一些经验也会对保护产生作用。
绿孔雀栖息地共管保护小区项目由阿拉善SEE基金会一诺亚方舟出资金,合作项目团队由来自多方成员一起探索保护方案,有政府行业部门代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发展政策评估专家、地方县乡村林业官员、村民代表、林业巡护员、玉溪观鸟会、山水代表、阿拉善SEE项目中心执行团队等等,四次到实地考察、多次座谈磋商提出方案,三次论证和修改,2017年10月确定了绿孔雀栖息地的共管保护小区的方案,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
绿孔雀为什么濒危了
首先了解绿孔雀濒危的真实的历史。绿孔雀栖息于海拔2000米以下的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混交林,尤其喜欢在疏林草地、河岸、农田边和林中空旷开阔的地带活动。韩联宪告诉我们,云南的绿孔雀主要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三条江流域:怒江中下游、澜沧江中下游、红河石羊江中下游。绿孔雀过去在滇中不仅仅是中下游河谷地区,那些云南松林都是它的分布地。在20世纪80年代,在滇中一带像禄丰一平浪樟木箐、紫溪山那些地方都有。他在做论文是,双柏几乎每一个乡镇都有,包括大麦地镇都有。绿孔雀种群下降,最大的问题还是栖息地消失。
韩联宪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政策调整初期,滇西南地区发展经济,绿孔雀栖息地的低山灌丛林全都砍了种上甘蔗,叫“甘蔗上山”。在困难的年代,糖是国家直接调拨的重要奇缺食品。龙陵乡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曾经是荷兰和云南的合作项目,划出6000多公顷一大片山成立保护区,包括怒江的江中山,怒江大拐弯是有绿孔雀的。但有4000多公顷是保护区建立之前,就被政府租给糖厂种甘蔗。保护区就只剩下2000多亩,江边比较好的林子,但还是遭到残蚀。如今租期到了,而依靠于甘蔗地赚取现金的村民不愿意归还土地。保护与生计成为一对难以调解的矛盾。
绿孔雀与其它鸡禽雉类动物相似,与村落、民居有高度的相依性,喜欢在村庄的豌豆、养麦和稻田里觅食,造成了农户庄稼一定程度减产。大约是2002年,那个区域一年毒死了18只绿孔雀。那个年代,粮食是很精贵的,在产量极低的山区,粮食是养家糊口的保障。江中山的绿孔雀飞到了对面镇康县农田里吃百姓的庄稼,稍后有人举报,绿孔雀被毒死了。保护区管理局也不是说不想抓,也想去查案办案,去蹲了两个星期没有找到人,也就不了了之。在龙陵与德宏州芒市交界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调查时就说瑞丽有孔雀,但最近几年村民说,多年没听见叫声了。根据现在的调查,那个地方可能也就剩下微乎其微的那么两三只吧。
云南是鸟的天堂,高黎贡山和哀牢山沿线区域都是候鸟和留鸟的迁徙和栖息地。山区一个青年朋友其父辈是猎人,自己也跟着打过猎。云南西南部靠近边境,曾经枪支泛滥,好多鸟被人吃绝了。即使10年多次执行收缴枪支的行动后,民间还是有自制的猎枪。不过,老百姓现在抓鸟根本不用枪。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旅游和观鸟点很多,现在捕鸟厉害得很,用粘鸟的竹签布到鸟经常出没的地方,一天能粘上百只。而当高速路和村村通乡间路硬化后,外来的游客多了,城市来的游客是不拒绝山珍野味的,包括麂子、锦雉各种鸟,还有高原湖畔河流里的珍稀土著鱼类,都吃得濒危了。卖到游客多的街市餐馆能为家里赚到不少的收入。
想到北美的旅鸽,尽管它曾经有多达50亿只,但它最终灭绝,最主要的原因是无序的商业捕获。欧洲拓荒者占据北美后,砍伐森林造成旅鸽失去栖息地,又建立大规模的农场种植棉花和小麦,加上旅鸽肉味鲜美而被大量猎杀,成为农贸市场上抢手的商品。旅鸽数量逐步减少,直至1914年9月1日彻底灭绝。
绿孔雀之乡老百姓的声音
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是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一部分,包含了国际鸟盟的两个重点鸟区。高海拔的原始林对于山区鸟类多样性具有维持的重要作用,中低海拔的次生林、薪材林和人工松林也部分缓解原始林消失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今我们走近哀牢山东缘,绵延上百公里的外围中低海拔林地都被开垦为规模化的橙子种植园,绿孔雀栖息地被毁灭。当全球化的超市里提供了大量统一标准化的橙子、香蕉、玉米、咖啡、可可等产品,其生产链上是规模化、统一性的化肥和农药,橙子树下一棵草都不剩。这些产品的原始地都是热带雨林、季雨林,是绿孔雀、亚洲象、犀鸟、长臂猿、印支虎曾经生活的地方
者奄乡的村民大部分是彝族和傣族,30~40岁以上的老乡,20年前都看到了孔雀,1987年绿孔雀数量大约30~40只。但2006年附近發生森林大火,绿孔雀被逼到坡脚豌豆地,有23只,同时还看见60多只猴子。2005年的七八月,老百姓去林子里采甜菜——一种云南箐沟里长的乔木类枝叶做蔬菜的特色民间食品,还发生了绿孔雀抓人脸的事情。现在绿孔雀能看见的只有六七只了,2016年5月份在山谷养羊处山箐有水处还看见3只绿孔雀来喝水。
有老乡采甜菜时见过绿孔雀蛋,如鹅蛋大小,有一点点黄色,数量好几个,小时候父亲告诉过:这就是孔雀蛋。他还曾经见过绿孔雀打架,公的会撵其他公的,要赶出它的地盘才行。另外一位50多岁的老乡回忆,小时候地里以种植旱稻、豌豆、养麦为主,绿孔雀都会来家门和村里,一只公孔雀应该带着三四只母孔雀。在河边,绿孔雀会吃爬虫水蜈蚣,也吃麻雀。现在种植玉米、香蕉、核桃、冰糖橙,再加上为了村村通修路,孔雀就都在河边生活。种这些作物,一家5口人30亩地每年有4~5万元收入。
10多年前村民猎捕绿孔雀,后来枪被收了才没有打猎事件了。自两三年前村民陆续认识到绿孔雀是濒危保护动物,2017年林业厅到村里普及宣传,大家才知道绿孔雀是国家保护动物,捕捉是犯法会坐牢的。村民将牛羊散放在绿孔雀栖息的山林中,傍晚大声吆喝牛羊回家,对绿孔雀造成很大的惊扰。
县乡政府、村委会等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栖息地周边村民都对绿孔雀保护有基本认识。全村妇女认为,有绿孔雀在,是大家的荣幸,大家有保护好绿孔雀的意愿。村民讨论了绿孔雀保护和让其数量增长的措施:在乡林业站的指导下建立巡护队,严禁外来人进入林子,严格控制人为干扰;杜绝打猎行为,严禁开荒、砍伐,做好防火;在专家的指导下适当增加补充食源地,种植传统的豌豆和荞麦;地里农作物不需要打农药;在绿孔雀繁育严禁进入林子采甜树叶,防止人为惊扰导致其弃巢;帮助专家和林业部门做好监测工作。乡村两级干部们提出,加强绿孔雀科普知识宣传工作,法律责任宣传要跟进。
老乡的迷惑与失落
云南山高水远,上千年来农耕文化开发缓慢。在20世纪中期,山区民众多少还是典型的采集和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以物易物商贸形式普遍存在。而过去60年,国家投资集中到东部和大城市,云南这个高山占94%的省份,由于“发展落后”才依然保持了中国和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独特性。
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部和大城市急需大量电力,西部开发直入山区深部。高山林立和水力资源丰富的云南,成为国家以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战略能源基地,云南成为国家电力调配枢纽的能源强省,“西电东送”为东部和城市配送清洁能源基地,可当地农村用电费用高于对外输出的电力。
云南省2006年的装机容量为1813.00万千瓦,2015年已达到7671.07万千瓦,发电量从2006年的692.01亿千瓦时增加到2015年的2352.45亿千瓦时,水电的电力比例也从42.51%增加到84.12%。除了澜沧江、金沙江和怒江三大水系作为国家优先和重点开发的对象,引发了云南省各州县也为自身的经济用电、农业水利调配的小水利工程的建设。随高速公路、高铁和村村通道路而来的生态旅游出现了商机,更将生物多样性核心区碎片化,物种濒危程度加速,保护工作危急。而常规性政府对保护区的财政拨款甚少,难以维持物种监测和保护区的巡护和管理的需求,造成诸如云南巍山青华绿孔雀自然保护区内没有绿孔雀的情况。
“自然之友”向楚雄州人民法院提出公益诉讼,要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消除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嘎洒江水电站建设停工。这一下子打破了彝族村寨的平静。为了保护“最后一片绿孔雀栖息地”,本来修建电站乡财政可以获得的1600万的补偿费落空了。对于深山里的村民来说,来到眼前的“现代化的机会”被“夺走了”。电站停工,几百上千农民工一下失去了就业的机会。他们还得回家在山林里开垦30多亩耕地,赚取养家糊口和送儿女上学的费用。而大片土地的规模化种植,正是绿孔雀失去栖息地的主要原因。
无奈的老乡不知道何处诉说“当外界像洪水猛兽一样地发展,我们的资源被贱卖,我们的山林被破坏,千年的大树倒下,只能换来孩子的一个书包和妻子的一件过冬衣服。”
绿孔雀栖息地共管保护
阿拉善SEE基金会一诺亚方舟项目,在云南省林业厅牵头下,由专家指导,整合在地鸟协和公益组织、村民与林业站等资源,2017年9月正式启动新平绿孔雀栖息地共管保护小区项目,探索在政府保护区以外的濒危物种绿孔雀栖息地的有效保护。项目由阿拉善SEE基金会一诺亚方舟出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雉类专家杨晓君教授、云南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韩联宪教授、云南林业科学院李永杰工程师、公共政策影响力评估专家林杨先生、生态地理专家闻丞博士、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的专家与地方的基础林业部门、村民共同制定方案,并形成一个委员会,计划用五年时间每年投入50万,实施绿孔雀栖息地保护和自然繁育监测。项目的特点是,执行的机构是乡林业站与村巡护队和村民,推动机构是在地的玉溪观鸟协会。
诺亚方舟项目的总目标是:在农林山地区域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立绿孔雀栖息地共管保护小区,为西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一个政府一科研机构一社区一公益机构合作和资源整合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保护模式。项目的措施和目标任务首先是,在专家指导下。当地居民、政府林业部门、公益机构为周边林区残存的绿孔雀确定自然栖息地以及实施保护管理边界,再由村民和基层林业站组成巡护队并实施日常管理,减少人为干扰。
第二,监测绿孔雀种群数量稳定和复壮的条件,由专家指导,设置科学监测,定期收集绿孔雀栖息地保护的信息。除了原来的半湿润的季雨林,云南松林也是雉类生境可替代的树林,是否需要修复也要做监测和实验;定期确定保护小区内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和自然复壮的情况,判断其他影响因素,再确定是否需要人工改善绿孔雀食源地、栖息地的生境状况。
第三,提升当地政府、社区与公益机构共同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重建社区与自然友善依存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将乡村收集的民间的传统经验提供给专家和有关部门与公众,并用于社区保护教育、科研和政策使用;提高当地村代表、巡护员和基层政府部门的能力,使他们具备绿孔雀保护必要的基本知识和保护的行动,并具有(在村、乡镇两级)参与讨论和评估巡护制度和保护小区管理制度的能力。
专家认为“水电建设对绿孔雀的栖息地肯定是有比较负面的、严重的影响。但“停建水电站”对促进保护绿孔雀还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老百姓的行为非常关键,他们祖祖辈辈从采集时代就是打猎、砍树、采山珍,需要现金就毁林开荒种地。需要在实施项目中用参与式评估,确定生态友好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推动向生态友好生产和生活目标而努力,探索解决村民可持续生计的生产方式。
2017年“9·9”公益筹款日,由阿拉善SEE基金会一诺亚方舟资金支持,云南自然与文化遗产促进会在腾讯筹款平台上发起为“绿孔雀保护音乐会”项目筹款,获得3000人次支持共筹得28.8万元。同时,由阿拉善SEE基金会一诺亚方舟资助玉溪市红塔区观鸟协会发起的“我为绿孔雀请保安项目”,获得近1000人次5.5万元公众筹款支持。2017年11月18日,云南自然与文化遗产促进会与阿拉善SEE基金会成功举行公益“绿孔雀保护音乐会”,与公众以歌声援助绿孔雀保护,呼吁公众参与绿孔雀保护。
我们希望看到,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友善依存,用我们的智慧,为后代保留着活体诺亚方舟,让西南山地永远是天上有鸟、林中有兽、水中有鱼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