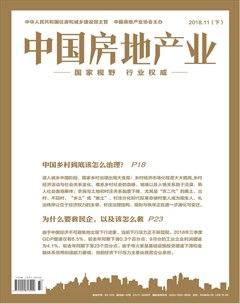中国乡村到底该怎么治理?
刘守英
2003年是中国城乡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中央从战略上明确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国家解除对农业的直接贡赋、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解决农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此带来国家与农民及乡村关系的根本变化;随着国家能力的提升,国家着手解决乡镇和村级代理人的财政保障、减少制度性寻租造成的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紧张。但是,乡镇和村级组织财政自主性的下降也带来基层治理动力的衰竭和国家直接抵达乡村治理成本的上升和绩效下降。
乡镇政权在乡村治理中的自主性下降
一是乡镇财权上收。税费改革之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从财政权力、人事编制和行政权等方面被不断削弱,乡镇政府实际上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农村税费改革减免了1250亿元农民负担,属于原乡村两级“三提五统”和其他税费的资金达850亿元,导致乡村两级收入减少和财政困难。农业税费取消以后,2006年实施“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的乡财县管制度,县级财政部门直接监管乡镇财政收支,同时撤销乡镇财政国库,明确乡镇财政支出范围、顺序和标准,统一县乡工资福利政策和标准,控制和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等。乡财县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保证了乡镇人员的工资发放和机构运行,但也减低了乡镇政府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激励。
二是乡镇人事权弱化。在弱化乡镇财税自主性的同时,也通过乡镇机构改革削弱乡镇政府权力,包括乡镇撤并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从2005年开始,乡镇机构改革旨在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但核心还是调整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精简富余人员。从2001年初到2016年,全国乡镇数量从45667个减少到31813个,共减少13854个,撤并率超过30%。同时通过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在体制内合并、综合设站,在县域内设置跨乡镇的综合性服务站所,体制外将乡镇事业单位整体改制成企业、人员买断退出财政供养序列,原来由这些单位提供的公共服务采取“政府购买,市场招标”的方式进行。
三是事权不断向县级部门集中。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编制设置和机构框架进行规定,按照县级政府部门设置实施垂直管理,乡镇政府实际上是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执行县级政府的行政指令。乡镇政府的职能不断弱化,诸如农业补贴发放、投资项目和征地拆迁审核等均由县级部门直接负责,乡镇政府只是作为一个下属机构配合县级部门开展工作。
村庄治理正式化
一是村庄选举的规范化和正规化。为了加强选举的民主性、程序性,提出“村支部书记人选,先参加村委会选举,获得群众承认以后,再推荐为党支部人选;如果选不上村委会主任,就不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村委会选举成为常态、选举的程序不断规范,农民参选率提高。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07年的选举中,设立秘密划票间的村比例达95.85%;一次选举成功率约占参选村的85.35%,2005—2007年农民参选率约为90.7%。
二是村级财务权力上收。2006年以来,国务院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加强村级财务管理,规范村级会计代理制等管理办法,促进村级财务监管工作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引入社会中介机构为村级财务管理服务”。2008年,“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发展为“村级财务和村级资金的‘双托管”,“即各代理服务机构在接受委托后,各行政村不再设会计和出纳,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报账员,其资金……进行统一管理,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实现‘五个统一,即统一资金账户、统一报账时间(段)、统一报账程序、统一会计核算、统一档案管理。”2010年2月8日,中央纪委、财政部、农业部、民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是农村基层实践工作的创新,是管理农村财务、强化会计监督的有效模式”。
三是村级组织正式化。随着民生建设和维稳工作量的增大以及村级财务支付由财政支出负责,村级干部不断正规化和岗位化。村级干部中非村民干部越来越多,包括各级政府委派的大学生村官或者下派的政府工作人员;税费改革后,村干部工资主要由财政直接负担,村级组织主要干部的工资实行由乡镇核定年薪制,其他干部实行补贴制,村级组织干部工资补贴不得低于当地农民收入平均水平。除工资外,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也由财政给付。村级组织的正式化,导致国家负担村级组织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由此加剧大规模拆村并组,村委会个数及其职工数从1990年的1001272个、409.4万人减少的2015年的580856个、229.71万人,年均分别减少2.2%和2.34%。
城乡统筹格局下的乡村治理秩序与挑战
一是国家直接抵达农民的绩效不高。一方面,城乡统筹以来,国家绕过乡镇等基层政权直接同农民打交道,国家对乡村从间接治理转为直接治理。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降低了由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治理乡村的代理成本,但是,国家整体治理乡村的成本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原因是尽管国家并不能直接处理农民现实中面临的各种矛盾与不公平。但是,农民的预期是只有国家才是满足各种诉求和矛盾的理想解决方案的最终裁决者,这导致上访和维稳的成本不断上升,一旦他们的预期未得到实现,就会“反噬”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国家直接治理造成财政投入越来越大,绩效不佳。各种补贴的增加和乡村投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乡投入不平衡以及公共服务的分享不公平等问题。但是,大量旨在增加粮食产量与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和惠农资金与预期目标并不一致,一些补贴项目甚至造成寻租和腐败,巨额的农业投资由于缺乏监督和评估被用作非生产性或非农用途,由此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和惠农政策的绩效。
二是乡镇基础能力下降导致乡村治理悬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机构改革不断弱化乡镇财权、事权和人事权,导致乡镇行政功能和乡村控制能力不断下降,乡镇政府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出现缺位:一是“服务”缺位。乡镇政府在上级考核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困难的经济压力之下,忙于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没有动力和财力进行乡村社会的治理和提供乡村社会公共服務。二是“治理”缺位。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权的财权、事权和人事权利都由县级政府控制,农业补贴等财政转移支付的涉农资金项目和殡葬费等涉农费用都逐渐上移至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因其“日益匮乏的资源约束”越来越丧失与农民打交道和控制乡村社会的能力,在客观上造成乡镇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正式权威和正规权力的缺失,使得乡村社会处于“治理”缺位的危机中。
三是村治越来越远离自治初衷。村级组织从财务、人事和事权等方面被乡镇政权“接管”,村级组织的行政性倾向增强,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减弱,村级组织的内生性权威不断退化,村庄自治演变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威权性自治,成为贯彻行政命令的工具,丧失其村民主体性。行政村范围的扩大、大量“大学生村官”进村以及下派驻村干部导致村干部陌生化,消解了村民自治的“内生性”。国家对村级组织行政治理正式化要求越来越高,在乡村社会行之有效的利用习俗和传统协调村民生活的治理传统逐渐失去效力。
要强调的是,尽管国家在制度化基层资金来源和使用上投入高昂的成本,对基层对农民的摊派施加了种种制约,但各种名目的负担仍然存在。2011至2016年农民总负担从654.87亿元下降到407.55亿元,其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从1.43%下降为0.56%。农民负担中,占比比较大的几项为上交给集体的土地承包金、一事一议筹资和以资代劳、行政事业收费和农业生产性收费,这说明一些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仍然需要农民自己投入。
是非正式规则在乡村秩序中的主导性增强。城乡统筹以来,随着微观基础上家庭本位的回归,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一,宗族势力在选举中复苏甚至左右民主进程,村庄内的主要宗族通过选举控制村庄的正式权力,有的以此获取村两委的主要位置,村委会和村支部等组织的干部来自于大姓和大族的比例远远大于来自于小姓和小族的比例;其二,新乡贤、新乡绅或者村庄体制外精英出现并发挥作用。由于村两委无法有效提供村庄相关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对于自身利益保护、乡村状况改善和纠纷调解等需求,一些具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新乡贤、新乡绅或者村庄体制外精英”开始在乡村社会中扮演“权威代言人”的作用,他们获得主导村庄治理的支配性地位,形成基层政治中的“能人治村”现象。其三,乡村帮派势力死灰复燃。传统乡土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主的非正式制度的崩溃和改革以来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真空,给了乡村帮派势力以复活的机会。无论是单个的地痞流氓,还是同正式组织相关联的黑恶势力,抑或是同地方宗族势力相关联的“村霸”,不仅造成乡村社会秩序的动荡,而且导致党和政府执政根基的松動。其四,宗教势力乘虚而入,一些宗教的教会会长成为地方精英支配着村庄。村干部不得不借助于在“红白喜事”等礼俗活动中扮演组织者角色,来拉近同村民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认同。
结论性评论
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乡土社会时期县政村治——土改到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改变都是为了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
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乡村经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乡村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变化,维系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趋于淡漠,熟人社会面临解体;农民与土地和村庄关系黏度下降,尤其是“农二代”的离土、出村、不回村,“乡土”成“故土”,村庄分化和代际革命使村里人成为陌生人,礼治秩序让位于经济权力的主宰,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秩序正在和进一步演化与变迁。人地、人村关系变化也带来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变化,城乡统筹格局下对农业进行的大量补贴以及乡村投入,由于大量人口的入城脱村,出现投入错配和绩效不佳。国家必须在新的发展阶段找寻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进行适合乡村治理半径的委托代理设计与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以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订阅号“野三坡经济论坛”2018年11月9日(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