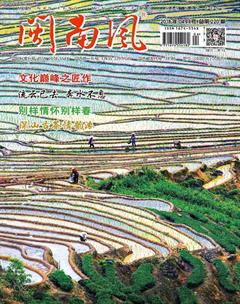缺陷
于燕青
一
我曾一个人在动车站看书,在一群看手机的人群中看书,有点外星人的味道。那是从长汀采风带回的杂志《古韵汀州》,一本县级刊物,封面上是路易·艾黎年轻时的照片,背景是长汀古城楼。这背景与艾黎多么融洽,血与肉的融洽。路易·艾黎,这个尽其一生在帮助中国抗日的外国人,这个跑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新西兰人说:“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福建的长汀,一个是湖南的凤凰”。于是长汀人感激他。我的眼睛湿润了。不过我即使失态流出眼泪也不打紧,我的周围乌泱乌泱一群人低着头看手机,没人注意我。这也是我的背景,这背景与我是不融洽的,这背景是时代的,洪流般强大,我是不入流的,是被出局的。
因為不看微信,常常受到朋友的指责,说加你微信你都不理,波浪没有,涟漪也没有!我说我不会上微信。微信横空出世,大火特火,而我却不会使用,不会用微信发文字,不会发图片发心情,不会视频聊天,不会查看附近的人、不会嘀嘀打车、不会定位导航、不会摇一摇抢红包。微信能干的事我全不会,错过了骂凤凰男骂孔雀女骂熊孩子,辜负了这个时代。因为不上微信,没有赶上朋友的聚会;因为不上微信,诗歌研讨会没有研讨我的诗;因为不上微信,没有及时收到稿费;因为不上微信,朋友手机换号我不知道。大到不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小到不能对朋友的近况了如指掌。这个时代不上微信就好像骑着毛驴与动车赛跑,落伍到可笑的地步。
痛定思痛,终于补上微信这一课。晨起第一件事,打开手机上微信。上下一大溜的圆头红点,是有人发了新信息。红色是警示的颜色,警示我有N多的信息没看,有的都堆积了一百多条。有好友张三李四王五麻六等个体的,也有市作协、市诗歌协会、省散文高研班、众望书店、高中同学、卫校同学等群体的,这些个人或一群的人日夜不停地发送信息,蜜蜂般殷勤。“年度前十名段子”看不看?看!机智狠准的搞笑,一笑能解压,现代人压力山大。“吃了这个会阳痿、绝经、患癌”看不看?看!关乎生命,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再不看又会被屏蔽”看不看?看!太诱惑,况且机会稍纵即逝。“紧急提醒大家当心,骗子新骗局” 看不看?看!这年头骗子太多,隔壁女研究生刚被骗去3万元呢。滴答一声响,文友圈的老黄瓜刚传上来一首诗,从诗歌网站转帖来以飨众文友。来的早不如来得巧,那就先看诗吧,都说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文学的皇冠,还有人说诗歌是从语言困境中拯救语言的救生衣,我很喜欢这句话的。一直以来,当我写作散文语感不好的时候就会去读诗。那首诗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诗人写的,看了两行有点感觉,可时间来不及了,手机玩得不好,不会微信收藏,但会转发,于是先转发到儿子的微信里存起来,等空闲下来再打开细看。就这样,早晨黄金的一个多小时大风般呼呼地刮走了。
迷迷糊糊下楼去买早点,路上看见家住一楼的张大爷,看见他身边另一个还是张大爷;再看卖早点的美女小安,另一个还是美女小安。我知道我的眼睛又重影了,即使重影还是坚持看微信,轻伤不下火线,又一条朋友微博横空出世:“真不能再玩手机了!最近视力下降的厉害,早上远远看见大横幅‘李宇春装B拉!走近一看,原来是‘李宁春装8折!去饭馆吃饭,夹起一块红烧肉发现好多毛,很认真的一根一根拔,等拔干净放进嘴里,是块姜!最丢人的是昨天,老远看见邻居二哥牵了条藏獒在门口,于是客气的打招呼说二哥,啥时候买的藏獒啊? 二哥没答应,走近一看,天啊!是二嫂穿着貂皮大衣蹲下系鞋带呢!”看来都是微信惹的祸,虚拟的世界很真实,真实的世界很虚拟。
吃过早点,打开手机找回发给儿子的那首诗,慢慢品读:“喜欢一座城/喜欢一座城的城南/喜欢一座城的城南空地/喜欢一座城的城南空地上白色时光/现在,我只需要/一间不大的房子,够放一张床/做爱时可以穿越/那片白色的时光那个空地那个城南那座城……”,读着读着忽然冷汗淋漓,这是什么事呀,写点什么不好,非得写做爱,我怎么就把这样的诗发给儿子了?多叫人尴尬,多叫人难堪。建议这一类诗都要标上“母子同读不宜”。想跟儿子解释一下,说什么好呢?说我不知道里面的内容?说我不是故意的?哎呀这只会更尴尬。哎,还是学会收藏吧,捣鼓了一会儿,就发现了路径,从“我”进入,就能看到那个“收藏”的标志,唏嘘不止,早知这么简单,就不会那么尴尬了,都怪我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二
儿子在离我好几十公里的另一个城市上班,当初他在那里读大学,当初我就想他要是毕业了就留在那里上班好了,反正也不太远,可以经常回来,我也不用天天给他煮饭,多好的事呀。那时候我还没老,心还很浮躁。果然是心想事成,儿子毕业后就留在那里了。现在我老了,我空巢了,才知道我为我的不爱煮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我老了,已经从被称为“女人”的阶段步入“人类保姆”的阶段。若还想与“女人”一词沾边,就必须冠以“老”字,谓之“老女人”,那还是不要的好。当我竭力去适应,努力使自己慈祥起来,并准备迎接我写作的敌人——孙子的诞生,儿子却说他不生孩子!声音不高,语气决绝,并微信转来他朋友圈老K的言论,老K还在当他的金牌王老五呢,他自然要说不生孩子好,说当下生存环境如此恶劣,避得了三聚氰胺毒牛奶、苏丹红咸鸭蛋、膨化粉面包、硫磺熏馒头,瘦肉精猪肉火腿、地沟油炸油条,也避不了恶浊的空气。我被五雷轰顶,许久才缓过神来,找不到反击的理由,遂恨恨地骂句:“不孝的东西,想让我这一脉成为终端?”
说句实话,当初我是多么感谢计划生育呀。若是能够选择,我也不想生孩子的,可我的脆弱无以抵抗庸常生活对一个人的要求。老了才知道庸常生活里有真理,才知道有孩子真好。人生的许多彻悟皆在自身的体验之后,别人的经验永远只是别人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历史的经验不断有人总结,却还是不断有人重蹈覆辙。有个时候我总是电话遥控儿子,我让他在单位要低调、让他凡事躲在后面,不要出风头。我知道我在扼杀个性,有点像一个必须锯掉肢体的一部分才能保全生命的病人那样,我心痛,而且那是我自己都做不到的。我自己做不到的却希望儿子能做到,这有点蛮横,有点天方夜谭,但我真是希望他能做到,希望他在这世上少受些伤害,不要像我。向来,一个人担忧另一个人,最是精神负重,是最重的担子。一旦做了父母的人,便也是加入这劳苦担重担之人的行列。
年轻时,我总是急于到达某个地方。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浑身湿漉,喘着粗气,像一个刚被救上岸来的溺水者,我忽然相信,他是从另一个世界涉水而来的。他让我感觉,要闯过生之门,非用大力气不可。抱着这粉嫩的肉团我总想什么时候才满月呀,满月了我又盼百日、周歲、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我被岁月追赶着,赶着赶着就老了。现在我恍然,儿子已经远离我了,我又想着假如时光能倒流该多好。我似乎找不到那个最好的时间段,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有缺陷的。是的,一定是有缺陷的。在我还不老的时候,也许这种缺陷对我的生活并无大碍,没有造成威胁。在我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的过程中,这种缺陷就越来越凸显出来了。
我刚搬来这个小区,就很幸运地认识了几个同龄人,她们基本上不会用电脑,不会QQ不会网购,但她们都擅长广场舞,“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华灯初上,她们就组成大妈的行列,那样的自在如同鱼游入大海。她们在小区的广场上伸臂扭腰,没有几个人的舞姿有美感,却整齐划一,那是一种集体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被她们用来对抗孤独的。
我还是有点舞蹈天赋的,但我就是没法融入这个“广场大妈”的队列,有一种东西在阻碍我,这东西就藏在我的身体里,我身上和她们有着不一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像电流,我看不见,但它是存在的,这东西暗流汹涌,我被挟裹而去,不由自主远离了她们,我就一个人,一个人在家里在书房里在电脑前,我像是被广场大妈空出来的一个人。小区里N的儿子也在外地,儿子在网上帮她买家具,需要N把身份证拍照传过去,N不会,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到处找人帮助,可那天她认识的几个会上网的都不在,半路上遇见了我,问我会不?我说会一点,于是就帮她传了过去。于是N几次热情似火地拉我去跳广场舞,碰了几次壁就不再来了。
三
腿伤住院,两人一间的病房。同房病友是山区农民,乡亲们常来探病,一来就是一屋子人,大把大把地抽烟,且能灵巧躲过医护人员的眼目,只苦了我的眼睛,呛得直流泪。我想制止他们的行为,却没好意思开口。第二年又住院,我不敢再住两人间的了,就住三人间,心想总不至于都抽烟吧?或许还能多一个监督的。那时正值初秋,隔壁床是只火鸟,一晚上开足风扇,且是最强档的风力。我是冷血动物,一晚上紧裹床单像个粽子,还是被吹得晕头涨脑。她还嫌不够,叫嚣着要开冷气,吓得我差点哭起来。另一床界于我俩温差之间,也反对开冷气,她才没开成。一天,与人谈话谈到将来老了怎么办?都是独生子女。有人说,就住到养老院去,两人一间或三人一间。我咬牙切齿地说:“决不决不!”想必我老了是去不成养老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