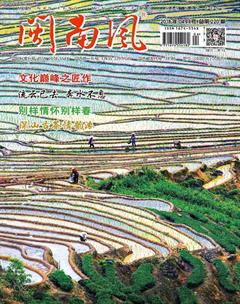遭遇花生
文雨
花生于我的家乡来说不是特产而是土产,许多地方的农作物都有花生,所以这一产物虽然好却并不稀贵。在市场上花生往往以几块钱的价格贩卖,而且个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粒大饱满。自小在花生味里长大,家乡的花生让我觉得像一位年老的长者,我们洞悉彼此;倘若是在异乡看到花生,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兴奋,熟悉又亲切的感觉像流水一样滔滔入心。
在城里遭遇花生是常事,上周五路过罗锦桥的大榕树下,一辆24寸的大自行车驮着两个竹篓筐,筐面搁着两个装满水煮花生的簸箕,我几乎能闻到水煮时花生蒸发出来的香气。靠近摊位,我的车都还没停稳,摊主就开始招买了,她说:“这是今天才摘的,绝对新鲜”。本来无心在意这些花生的季节、来历,被摊主这么一说我反倒心起警觉——刚摘的,怎么可能,现在可是十二月,在闽南花生不是都在农历的六、七月份才有吗?这个时候还有新鲜的花生,该不会又用什么药水培植出来的变异果吧,不是当季的还是少吃为妙。摊主见我踌躇,抓了一把往我手上塞,要我先尝,我推辞,她叫得更勤了,几次三番的招呼,她甚至把壳剥了递到我面前。不打算买,我无心尝试,她的过度盛情让我逃也似地离开。这让摊主很是不解,她不知道是她的一句:“今天摘的,绝对新鲜”把我吓成落跑顾客。我更不知道六、七月的花生是当季的,而十二月份的花生是反季的,產量虽然低了些,但是可以有的。这是回家母亲听了我的唠叨告诉我的,听完后我有种无知自大被贬的傀怍。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农家子女,自小就与花生结下渊缘,自以为对花生有知节解末的了解,没想到不当农夫的人论起农业知识再熟悉也是门外汉。
在我那个如今人见人赞的老家,三十年前可谓是偏而远的乡村,沿海风大,黑土地缺水,农业主打产品除了水稻、番薯、花生,再插种一些红高粱和旱麻,除此以外再无其它了。水稻的生长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天不下雨乡亲们就得筹款上交给水库,求人放水灌溉,而种花生就相对比较省事了。
花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不仅仅像许地山笔下的象征处事为人的那么一点点价值,它还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经济来源。希望大,种植量也大,为此在我那充满劳作记忆的童年里,花生是我非常排斥的作物,因为农忙时节实在太累了,偏偏它的收获季节总在一年之中最炎热的六、七月份,这期间全家人都忙于下地根本没空煮一顿像样的饭,而且老人、小孩皆没能逃过忙碌的派遣。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得跟着双亲下地,到中午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回家,还得随行挑一担花生回来。山高路陡,且都是羊肠小道,两旁又有农作物缠绊,空手走都很不方便更何况要挑担子。挑回到家的花生还得一颗一颗地摘下来,晒干,择净。摘花生是一个叫我痛苦的差事儿,之前拔花生就已经让手密布水泡了,这会儿我还得用这只累累伤痕的手去碰那外壳坚硬的果实,简直要人命。我于是经常找各种借口溜出家门,农忙时节还这么不懂事是最容易触怒母亲的,从地里回来,一看我不在家,母亲必扯开嗓门喊,把我喊回来棍子伺候,后来我学聪明了,夏天也穿长裤,防备母亲的棍子。不耐烦的时候我问母亲:“今年花生收完,明年还种吗?”母亲吼道:“不种,我们吃什么?”这是要人崩溃的回答。不过在一次打过我之后母亲偷偷地抹泪,我怯着胆告诉她我手疼,并且把双手摊在她面前,过后我便被允许不用下地,还可以带着手套摘花生,虽然笨拙了些,但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双手。
晒干后的花生能在院场上打滚,像活泼乱跳的小人儿,发出呵啦啦的声响,一个个都黄灿灿,要是堆成堆看着像一堆黄金小山。可惜这些“黄金”并不归农户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政策里还要农民交三金农业税,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秋收后的日子是农民交税正当时。收获完毕的花生要经过一番优劣筛选,小部分的优质花生要留着明年当种子, 其余的都被送往粮站进行统购,售出后所得的钱基本都上交农业三金,多还少补。要是遇上好年头,大丰收,统购完还能余一点留着自家打油,花生油可不像现在的菜仔油、玉米油纯粹烹调作用,在皮外伤方面花生油有很好的去瘀消肿、消炎作用,对于极个别的皮肤炎症,用花生油调药粉涂抹能根除。打油后花生渣会形成一圈一圈类似糯米糕的圆形固体花生箍,农民用它来喂猪营养很丰富。倘若遇上糟糕的干旱年景,收成少,农业三金得想办法筹去上交,更别想打油了。
后来体制改革,村里按人口分土地,缴纳三金的政策也取消,少了缴税的压力,父亲还是坚持种花生,卖给贩子换取生活费,收获越多,卖得越多,我们那一年就能过得越滋润,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生活,父亲那些年像打了鸡血一样铆足了劲,一口气承包别人家十几亩地,全种花生。也多亏了那十几亩地和花生,我们家庭经济的最大转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花生在我们那儿多得泛滥,如闰土说的:“过路人采个瓜吃,在我们这里不算偷”。在我们村里,过路人随便在哪个院子里抓一把花生吃,都不会有人说你偷,人们总是在拿到它换来的钱时,心里才觉得花生要越多越好,收获的过程中它不过是一种农作物罢。
花生有许多种食用方法,最常见的是生吃和今天我在摊贩上看到的水煮花生。花生生吃很养胃,老家的人要是胃犯上个喛气,反胃酸,抓把花生吃准能缓解。那时候,我们要上学或外出,口袋里都必须装上花生,或生或熟都行,肚子饿时用来充饥,即使不饿,当零食一路咀嚼也相当有趣。把花生煮熟再晒干味道可不一样了,因为煮的时候要加入盐巴和蒜蓉,晒干后吃起来有淡淡的咸味和蒜蓉香,这样的熟花生在若干年前是我们农民最拿得出手的伴手礼。连壳干炒,焗油,酥盐炒,油炸都是花生极妙的食用方法。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除了能用以上的方法将花生变成一道菜以外,她还有更好的方法为来年青黄不接的梅雨季节储上一瓮下饭菜,那就是腌制花生,这个过程不简单。
在腌制之前,准备工作不少,母亲会在提前十来天就清洗出一个瓮,洗完倒扣着风干。再准备一些黄豆,姜,酱油,红糖,叫我剥一大盆花生。
黄豆是用来做豆腐的,浸泡过的黄豆膨胀起来,在石磨上能快速磨出浆,这些豆浆磨出后倒在粿巾里过滤,滤出来的纯豆浆倒入锅里煮沸,撇净一些浮沫,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冷却,然后缓缓加入按比例调配好的盐卤水,在加的过程中必须得有一个人用饭勺不停在锅里搅拌到两者完全融合,豆浆出现豆花样的时候才能盖上锅盖,添把小火,待火完全熄灭,锅里的豆花结成块,再倒入铺着湿粿巾的豆腐模里,四个角落理均匀后盖上粿巾,放上压盖,还要在压盖上压一块石头,有时候这样一压就要一整晚,第二天才拿出来切,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如果马上食用不仅营养丰富,还新鲜嫩滑,可是这是要放到瓮里腌制的,必须再经过盐水煮,煮过后风干到微硬才能放进瓮里。
要腌制的花生也必须用盐水煮,煮完晾到没水份才能用。为确保出味,姜得切成丝,卤盐水,把卤出的汁倒掉,只利用姜丝。
一系列材料准备就绪就可以入瓮了,先在瓮底铺一层盐,在盐上铺一层豆腐,豆腐上铺一层花生和姜,撒上薄薄的红糖,再一层盐,一层豆腐,一层花生和姜,循环着铺上来,直到瓮满放不下为止,再缓缓地灌入酱油,酱油要分几次灌,确保渗透到瓮底,最后一次往往要在相距二至三天以后,灌完才把瓮口封住,封口以后要一段时间不能打开,避免空气进入瓮内干扰发酵。这样的一瓮腌制品在我们家能管大半年的稀饭,美味又实惠。
在我还没外出求学之前,要制豆腐磨黄豆一直是我的美差,我很乐意在那两片小小的磨盘上看完整的豆粒如何身不由己默默地粉身碎骨,尔后幻想浓白的豆浆是它的泪。
由于瓮口小,母亲手大伸不进去,装料入瓮也都是我帮忙的,母亲在一旁监督,就因为参与了整个过程,所以我对腌制花生的步骤记得特别清楚,对家乡的石磨情感特殊。
花生几乎占据了我大半的记忆,现在经常是一闭眼,全是城门外无边无际的绿叶,和大汗淋漓挑着花生的父老乡亲。前些年去郭坑镇采风,我负责鼎寨山采风写作,亲临鼎寨山后,站在山顶居高临下,有坡有坑的鼎寨山多像家乡东门外那一片农田,那些矮植株的茶树远看像极了记忆中的花生枞,在那么一瞬间,扛着尖担,一头绑着草绳的乡亲们都在我眼前走动,他们你来我往地走在通往坑底的羊肠小道上,他们挑花生,挑高梁,挑旱麻,他们披星帶月,挥汗如雨,气喘如牛,恨不得把山也挑回家。记忆让我激动,青草绿叶于我是最普通也是最特别的煽情物,下山时我狂奔在鼎寨山的山路上。如今家乡的农业已经荒远,田地杂草众生,藤蔓攀爬,菅芒长出一人高,许多小树现在参天生长,站在水门城门口已经无法望见坑底,无法望见牛头山,无法望见远处的流会灯塔,记忆成了怀念的全部,只是再也回不去。
那一夜,我因为商贩的水煮花生而回忆了整个童年,灵魂重绕了一趟崎岖的山路,看到许多深深浅浅的脚印,最终还是定格在花生的味道里,我决定去找摊贩买花生。
次日晌午,我特意再路过罗锦桥,远远就看到昨天那个摊贩把自行车停在大榕树底下,我往她的方向靠,她老远就看见我了,扯开嗓门冲我大喊:“昨天的花生是新鲜的,你怕,今天的花生还是新鲜的,你肯定又怕……”这么奇特的招客方式,不得不佩服她的大嗓门,我瞬间有种被路人的眼光灼伤的尴尬,我赶紧调转方向离开。
有心插花尽夭折,该不会是我无缘吃她的水煮花生吧,但我总相信我与花生是有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