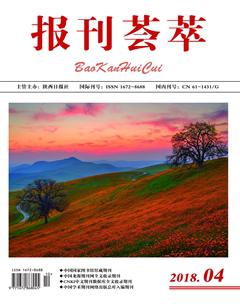西欧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的比较研究
摘 要:在历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西欧中心观”一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随着鸦片战争过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输出,中国愈发受到西方中心观的影响。但是这一趋势却在之后受到中国中心观的反弹,之后柯文提倡在中國发现历史以及巴勒克拉夫提倡的“全球史观”进一步改变着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西欧中心观;中国中心观;历史想象力
一、以自我为中心认识世界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以自我为中心来认识世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几乎每个文明都存在着以自己聚居地为基础的中心观。但随着文明发展,地理条件的限制逐渐被克服,各个文明之间的战争以及贸易交流甚至体育竞技的出现都或多或少改变了自我中心意识。但是在近代之前,中国仍然具有相当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孟子·滕文公》中提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宋代也有石介专门论证“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①。这些观念能够使我们看到古代人们具有的自我中心倾向。
但这样的情况在十九世纪迎来了巨大的变革。随着轻工业技术的改造,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之前无法开采的煤炭资源被有效利用起来,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转变。当古老的中国还在历史的辉煌下安然沉睡的时候,工业国家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已经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对其他国家输出他们的影响了。
二、西欧中心论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国篇中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止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地进步。”②从这样的描述当中,已经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到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无疑是将中国印度等地区排除在外的,因为这些地区在他看来是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而这种观点虽然与后来兰克关于停滞的原因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最终导致除西欧外大部分地区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结果却是一致的。而学生对于这种观点的看法与之前学者的看法也并没有多少分歧,“早在19世纪的时候,黑格尔就提出了‘西欧中心论。并且将‘西欧中心论理论化。他在《历史哲学》中,用地理条件、精神、种族气质来证明他的理论。在黑格尔看来,非洲是‘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亚洲人从来没有加入过世界历史的进程;东欧斯拉夫人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因素,而唯有日耳曼人本性优越。”③
黑格尔认为在中国普遍的原则就是“家庭的精神”,而中国也找不到“主观性”的因素,这种主观性就是个人意志的自我反省和“实体”成为对峙,而它们恰恰被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而消灭了,中国人在家庭之内是缺乏人格的,他们生活在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之上,而在国家的层面上,皇帝作为整个国家的大家长统治着臣民,即使是皇帝也不是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管理国家,而是靠社会流传下来的古训,他的职权虽然大,但是仍然没有行使他个人意志的余地。而正是缺乏这样一种对峙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脱离在世界历史之外。
从客观层面上,受当时时代的限制,西方还并没有多少系统性介绍中国的书籍,黑格尔对于中国的了解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何况除了材料本身具有的问题以外,黑格尔生活的意识环境与中国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带来的认识也会相差很远。比如伏尔泰在黑格尔之前也提到了“历史哲学”,他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史实的记载与罗列,更应该对历史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等作出考察。黑格尔也同样认为这样,并说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过是“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而已。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合乎人类自由的,是辩证的,是发展的。但是两人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就有了相当的差距,在黑格尔的描绘中,伏尔泰在《风俗论》里对于中国的向往和赞美变得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一个早已经不再发展的国度。
兰克在讨论到罗马帝国的基础的时候提到“我们研究罗马帝国的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有关看待罗马帝国的立场。可以说,整个以往的历史都汇入了罗马史,如同汇入了一条奔腾入海的历史长河。整个近代史是以罗马史为起点的。我敢说,假如没有罗马人的存在,整个历史就都没有了价值。”④从这样一段简单的陈述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兰克在看待世界史时所持的基本观点了,在西欧中心论上比起黑格尔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兰克之后,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冲击——反应”模式在大部分学者看来就是西欧中心论的一种具体体现,柯文将其归纳为三种西方中心模式⑤的第一种,此外还有“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而其中的“传统——近代”模式其实类似于“冲击——反应”模式,两者的理论体系似乎不同但是都贯穿着同样的关于西方与中国的前提假设,“冲击——反应”模式假设中国自身是消极的,而“传统——近代”模式假设中国自身是停滞不前的,都是等待西方文明的改变。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的第二部分讨论中国近代的革命史,开篇第一章就是“西方的侵入”,“一个在4000年期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始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名族,不能承认西方的这种主张。然而,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侵略别国的英国人奋力在全世界现实他们的优越地位。进步事业的一切形式,看来都在英国人这一边。随着积累起来的经历始终不利于中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感到异常沮丧。”⑥在这部分的字里行间中能够看到的不只是进步的表象是来自于西方的,甚至进步的原因也是来自于西方的,所谓“进步事业的一切形式,看来都在英国人这一边”。如果这里只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或者人民心态的一种分析的话无疑是中肯的,因为在中国近代确实有很多人存在“西方的都是好的”的这种思想,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却不应该先入为主的代入这种观念,而费正清则的确是这样的。在这一段之后继续写到,“然而,一件基本事实仍然存在:‘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世界的技术进步,和其他种种进步的策源地和发明者都在西方,因此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同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也是一件大事,其中掺杂着许多复杂而互相影响的过程。”⑦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也具体体现在《剑桥中国晚清史》内,他对于当时中国的整体印象恰恰是引用了中国学人梁启超的一句话来概括的,“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⑧结合他认为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上的劣势主要是因为“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是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应” ⑨也就不难理解在《美国与中国》的结构安排中用了大部分的篇幅去讨论在军事、经济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以及随着这种冲击所做出的反应。
不过“冲击——反应”模式这种显然基于西方独特性甚至优越性的说法受到了后来很多学人的异议,杰克·古迪在其比较性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西方并不具备某种朝着资本主义或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潜质⑩……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所提出的停滞僵化的东方社会的观念,实际上乃是西方的一个神话。”?学生对于这一段话有自己的解释,在朝资本主义或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需要某种特殊的潜质,而是很多潜质也许都可以促成这样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并不是需要所有的潜质都具备才会发生的,本文并不是想分析哪些潜质是特殊的或者哪些潜质更重要,而是想像杰克·古迪说的那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随着政治上的革新、工业上的进步,西方也许会是拥有更多优势或者说更多潜质的那一个,但是却并不能说西方就是特殊的那一个。就像成绩相对更好的学生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相对于一般学生而言,他也一样不能被称作特殊的一个。
三、中国中心观
而继流行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以费正清、李文森等人影响的强调外来文化对于中国冲击的历史观逐渐受到反驳,提倡一种从中国自身来解释近代中国变化的方法,这一史学变化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或者译为中国中心取向)。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对这些看法做了一定的汇总。在其前言中称之为“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几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在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向知识分子攻击传统最多的,不外小脚、小老婆、鸦片和人力车,其中后两样便是西人带来的。鸦片是不用说了。人力车本由日本人创造,不能算纯西洋货,但其流入中国,却是由先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代入中国;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西洋人。舶来品竟然成了中国传统——即使是坏传统的象征,最能体现此时西潮已渐成”中国“之一部……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且循环往复了好几次了。”?
当然个人认为并不应该以此就将“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内在发展”混为一谈,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也更不能够否认“西方冲击”与“东方反应”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与其巨大作用。认为在近代西方对于中国的冲击只起到了非常微小的作用的观点,学生认为也是有失偏颇的。也就是说最后的问题不在于“冲击——反应”模式能不能解释问题,而在于能解释多少问题,以及在某个方面上能够多大程度地解释问题。
柯文自己也说到“其实,这一方面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就像在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但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晴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像上述诸例设想的那样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不过在强调“中国中心观”的同时似乎又有另外一种错误产生的可能。暂且不论“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内在发展”两者之间在推动中国现代化上的能力是否有优劣之分,而这种讨论是基于讨论两者能不能产生这种推动效果的。而当讨论一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时,比如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原因,则是基于讨论这种效果是否切实产生。而“中国的内在发展”有能力,也就是能够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代表在实际上确实产生了效果。
巴勒克拉夫在对于世界史的把握上也主张跳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在其《当代史导论》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便明显体现出了这种趋势。在《当代史导论》中第一章“当代史的本质”中就写道“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这意味着,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仅仅是通过增加论述欧洲以外地区事务的章节来补救我们关于当代史的传统观点,而是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示?与修正。”?而其在之后的章节,从科学和技术的方面讨论催化整个新世界的转变,从观念上对欧洲霸权主义的反抗,新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兴起,特别是欧洲在人口因素在那个时代与其它地区相比越来越居于劣势,从而很好的证明了其最开始的观点。
不过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也提到了,这样的世界史观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与困难,比如世界史不应该是简单的国别史的拼凑也不能使按照时间顺序一大堆事件的罗列。不过巴勒克拉夫也只是告诉了我们它不能是什么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比如它是否应该是各种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的比例经过相互反应的组合,比如之前所提到的“中国内在的发展”和“西方的冲击”在近代共同所起到的作用。
当两种不同的观点出现对峙时,往往双方都有其合理的方面,而这个方面便是我们历史想象力发挥的基础,而双方的对峙则是激发这种历史想象力的来源。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学生个人自认很难分出哪种观点是错的哪种观点是对的,即使双方结合也很難说谁更主要谁更次要,某一方面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能够保持尽力激发双方的历史想象,当考虑“冲击——反应模式”时尽力发现与分析西方对中国产生的作用,当考虑“中国的内在发展”时尽力分析中国自身的原因,那么这样虽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是却能让人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从而也许可以让人们更深入地挖掘历史所隐藏的信息。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上,虽然现在的学者不能找到前文所提到的那种包罗世界的体系,但是却不能否认后来人有能够掌握这种体系的可能,在这之前能够以历史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之间的对峙激发出的历史想象力,从而为后来能够掌握把世界文明表述为一个整体的体系奠定基础。为后来的学人提供间接的参考以及做好建立体系所需要的各个部分的工作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注释:
①石介:《中国论·徂徕先生文集》,卷10,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②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3月,第110页。
③赵今禹:《从“西欧中心论”到“全球史观”的发展》,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④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3页。
⑤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译者代序)》,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页。
⑥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32頁。
⑦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32-134页。
⑧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第5页。
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页。
⑩在彭慕兰的《大分流》里面也有这样的观点,中西之间在近代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并不在于其他,而是在于煤铁等天然优势,不过学生认为彭慕兰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与本篇读书报告无太大关系,不详细叙述。
?玛利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0页。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序言,第3-4页。”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页。
?原文如此,疑为审视。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页。
参考文献:
[1]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
[2]赵今禹.从“西欧中心论”到“全球史观”的发展[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4.
[3]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M],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M],张广勇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0.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
[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7]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9.
[8]梁启超.变法通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
[9]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6.
作者简介:郑雨萌(1993—),男,汉族,四川自贡人,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