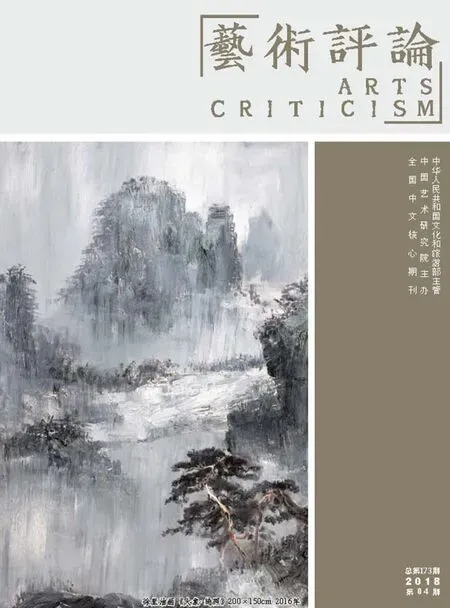《逃出绝命镇》:种族表象下的阶级表达
王 飞
王 飞: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
黑人导演乔丹·皮尔凭借自编自导的处女作《逃出绝命镇》(Get Out,2017)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4项提名,最终成功摘取了“最佳原创剧本奖”。这对于新锐电影导演皮尔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鼓励与肯定。相对于好莱坞大制片,这部仅投资400万美元的小成本制作却在上映后获得了票房和奖项上的双赢,可以说是2017-2018年度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中的一匹“黑马”。
但事实上,整部影片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视觉艺术表达上,都可以说是平淡无奇、老套陈旧。正如戴锦华对2018年奥斯卡的整体评价是“好莱坞正在重新寻找它的政治正确”,该片的获奖仿佛只是奥斯卡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而选择了黑人导演的、以黑人为主角并讲述黑人主体意志的作品。但也正因此,它恰恰可以成为反思“政治正确”的媒介。本文认为该片仍有值得讨论之处,在于它在一种看似完全“政治正确”的表达之下,彰显出在“政治正确”之内已然重构出新的阶级秩序并且阶级与种族关系发生了重新耦合。具体地说,影片中对黑人的颂扬、对黑人自我救赎的认同是建立在一种新的阶级秩序基础上的。所以当奥斯卡出于“政治正确”为目标来选择这样的影片,正是表明其“政治正确”是对一种新阶级秩序的认可。同时,由于这部影片既叫好又叫座,更反映出了这种价值观在当下已经广为接受。所以本文尝试以《逃出绝命镇》为切口,撕破这种“政治正确”的层层包裹,看到其内在重构的阶级秩序,以及这种阶级秩序如何吸收又改造了原本的种族表象,来形成对自身的伪装和保护。
一、《逃出绝命镇》:种族皮相下的阶级
《逃出绝命镇》主要讲述的是黑人男性克里斯(丹尼尔·卡卢亚饰)被白人女友罗斯(艾莉森·威廉姆斯饰)邀请去郊外的本塔科湖附近小镇上的她父母家一起过周末。克里斯听说罗斯尚未告知家里自己是黑人,带着“天生的烦恼”的克里斯因此颇有些忧虑,罗斯告诉他不必担心,她的家族不会在意这件事。他来到罗斯家后受到热情款待,罗斯父母确实不仅没有反感,反而盛赞黑人的种族优势。但克里斯的忧虑感觉始终一样。在经历了种种诡异事件后,克里斯发觉罗斯一家实际上是看上了黑人的身体优势,因此引诱黑人并将他人大脑放入黑人身体中来实现人类改造。他奋起反抗,消灭了罗斯一家,并在黑人同伴的协助下成功地逃出了小镇。
就其故事内容来说,该影片是按照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组合成的一部关于启程——途中——逃出的故事片。按照克里斯蒂安·麦茨的八大组合段加以分析,这部影片从未使用过一次描述性组合段(环境、背景)以及插曲式段落(跟主要情节没有关系)的叙事方式,而是紧紧地围绕着事件本身的发生顺序,采用顺时、线性的叙事结构,环环相扣地推进故事内容的发展。作为主要的叙事动机与线索,每一个麦茨意义上的独立语义段——场景、段落、组合段以及镜头都是围绕着黑人主人公克里斯如何陷入到这场“恋爱”阴谋中,如何得知这个阴谋的真相,以及如何逃出这个阴谋来进行的。
导演皮尔把这种带有“阴谋”的故事片放置在或恐怖、或惊悚、或黑色幽默式的喜剧描写中,辛辣地讽刺了正处身于“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现状。电影通过类型的杂糅与挪用,把或恐怖、或惊悚的剧情与“种族”,把黑色幽默式的喜剧与所谓的“政治正确”有机结合起来,在一部美国B级片中融入了当下对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入思考与批判。如果说“种族”问题始终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痼疾”的话,那么,围绕着“种族”的种种问题便是这种“痼疾”之下不断复现的“幽灵”。正是因为这种杂糅的类型与“幽灵”的结合,才使得这部影片中关于“种族”议题显得颇有深意。
与其他隐喻的、贬损的、刻板印象化的种族歧视的电影不同,《逃出绝命镇》是在一次次白人义正言辞地表示“不”歧视黑人,“夸奖”黑人的言说中展开故事内容的。片中在克里斯到罗斯家时,跟着罗斯父亲参观家宅,父亲指着挂在墙上呈蹲跑状的罗斯爷爷的照片说:“最优秀的雅利安种族狗屁”“黑人的出现,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他们太了不起了”,还表示“如果我还能投第三次票,我一定会投给奥巴马,他是我有生之年最好的总统”。后来罗斯家举行宴会,到场的白人嘉宾们也纷纷对克里斯表达对黑人的赞赏,说道:“过去,大家喜欢白皙的皮肤……现在,黝黑的肤色才最流行”等。然而,影片中的诡异气氛始终让克里斯,也让观众感觉这只是一套表面说辞,猜测这些白人只是挂着“政治正确”的面纱实则还是认为黑人地位的劣等。但随着影片剧情的推进,观众会发现这些言辞并非虚假,他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只是在这么认为之上,他们建立了另一重剥削和侵略之上:他们要占有这种更为优质的身体。
在这种占有和置换中,谁拥有主动权就成为了新一层的问题:具有主导权、代表思想、拥有转换技术的一方,无疑是整个事件的获益方,他们可以攻城略地一般地占有一切,包括占有不具有这些能力的人群的优质身体。因此以智能和技术为媒介,形成了新的阶级/等级压迫。不妨试问一句:谁才是有资格拥有这些优越条件呢?回到影片本身,应该指出的是:克里斯身体的被侵占是在被罗斯父亲拍卖的情况下发生的——无疑表明美国中产阶级(以及比中产阶级拥有更多财富的人)才能拥有或是身体、或是精神上的“重生”。在影片中,罗斯家依靠着拥有现代科学文明的技术来赚取大量的钱财,而前来购买这些的人也都是“美国”(因为影片中出现了亚裔人)上层社会的拥有极大财富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正如影片中罗斯爷爷所说,他们并不是非找黑人不可——种族不是关键,而是拥有了权力的人们主导一切,乃至种族都是在这个等级结构上进行再分配的。
二、种族表象:鹿的隐喻

电影《逃出绝命镇》剧照
但另一方面,就像克里斯提出的问题一样:“为什么是我们黑人?”尽管构成压迫关系的内核是阶级,种族的表象却并非因此而不重要,它正帮助影片表现出了压迫/被压迫的二元对立。正是借由种族,影片可以联系起美国曾经种植园奴隶制度的历史记忆,联系起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中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联系起在“后奥巴马时代”/“后种族社会”中,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种族的困境,也联系起如何利用现代科技的“文明”手段区别阶级差异的事实。也就是说,影片一方面揭示了种族关系之下有着更深层的压迫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更深层的压迫也是借由和种族关系的耦合来表现自身的。
贯穿影片的鹿提供了重要的隐喻意义。鹿在片中扮演重要叙事功能,它首先联系着克里斯的童年创伤记忆。如罗斯开车撞死鹿后,克里斯一直纠结于此,以至于走进树丛中去亲眼看被撞的鹿的状况。其后,睡梦中的克里斯又梦见被撞死的鹿。那么,为什么克里斯会如此纠结于被撞的鹿?是因为被撞的鹿与他母亲的车祸有关。所以,鹿之死唤起了他潜意识中抹除不了的童年记忆,以至于这成为他可以被罗斯母亲催眠的切入口。也就是说,克里斯未能拯救母亲的逝去而给他留下巨大的创伤经验。有趣的是,影片中将克里斯的这种创伤经验被罗斯母亲催眠后呈现为克里斯内心巨大的“暗坑”——无力的、无依无靠的、漂浮在空中的形象。

电影《逃出绝命镇》剧照
另一方面,“鹿”也是黑人的一种自指。当克里斯被制服关押在地下室的屋内时,摄影机从克里斯被捆的椅子后面上升慢摇至克里斯的后脑勺。前景是克里斯的后脑勺,后景是挂在墙上鹿头的装饰品,将克里斯的后脑勺与鹿头的装饰品放置在同一个二维平面中。在这个极端对称的封闭的构图中,鹿头无疑暗示着克里斯=黑人成为了待宰的“羔羊”。随后,在克里斯看完第一段罗斯爷爷录制的电视纪录片后,摄影机先是以侧面特写镜头拍摄克里斯看完这段电视纪录片的面部表情的反应,紧接着,镜头反打至克里斯主观镜头下特写的鹿头装饰品。这一场景无疑指涉着克里斯内心的震惊与绝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联系到罗斯父亲对“鹿”的态度的场景——当罗斯回到家后,告诉其父在路上开车撞死了一只鹿,而她的父亲表明态度说:“我实在不喜欢鹿,我非常讨厌这个物种,它们就像老鼠一样,生态系统都要被破坏掉了,要是我在路边看到一只死鹿,我会在心里说,这只是个开始……我不喜欢鹿”。在这里,笔者认为,在罗斯父亲的内心深处,所谓的“物种”是指“黑人”,“生态系统”无疑是指现今,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社会环境,而黑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像“过街老鼠”一样成为白人“天天喊打”的对象。这表明了鹿=黑人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真实地再现了黑人在白人共同体中生存的困境。然而,有趣的是,影片中,“鹿”同时也成为了白人心目中的“图腾”。比如克里斯被禁闭在地下室之时,有这样一处场景:摄影机(此处摄影机的位置显然是作为白人叙事者的中心位置)从下往上摇移过程中,对于鹿头装饰品的拍摄始终用仰拍镜头。这明显地暗含着白人对鹿=黑人身体的觊觎暗含着一种“图腾崇拜”的意味。在这一点上,也表明了白人对黑人身体所表现的优势的羡慕与觊觎——这也是罗斯不惜以身为饵诱惑克里斯,将他设定为自己的猎物而入局的原因:为了更好完成身体的剥夺与殖民。这同时也解释了影片中白人对黑人的称赞的缘由。
因此“鹿”不仅承担着推动整个电影剧情发展的叙事功能,而且也作为黑人的隐喻而再现了种族的困境。进一步讲,鹿之死与母亲之死的关系,也隐喻着黑人“母”国的沦丧。从影片中,我们得知克里斯从小是一个无父无母而在现代文明的美国社会成长起来的黑人,这正关联着黑人被贩卖到北美这片土地而丧失母国的历史。克里斯可谓美国世界中的“空壳”,他自身不承载文明,而是现代文明要进行发展时所可以征用的“土地”。正如影片中,黑人男佣、女佣与“兄弟”在被手机闪光灯刺激的情况下,唤醒了他们意识中沉睡的自我。在此之前,他们的身体就是被移植者所奴役。只是曾经的种植园制度,在此转变成了个人化、私有制的、为白人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提供的服务。
更进一步说,克里斯乃至黑人都是现代文明为了实现自我扩张而建构出来的异己的存在,这种存在表明世界还有未被现代文明占有的空间,因此现代文明就还有发展的余地。克斯里与罗斯之间的“恋爱”/角逐的关系本身是建立在一种跨肤色、跨种族、跨地域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影片中,这种“恋爱”关系背后隐藏的是夺命的阴谋以及百年殖民历史以个人寓言方式在个体身上的重演。也就是说,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是通过黑人克里斯与白人罗斯的个人情感的欲望力比多的引诱来推动叙事,事实上是为这种多重跨越的种族的不可言说服务。这本身是力比多欲望不可能跨越的“激情的疏离”,或者称为“激情的中断”或“激情的中止”,即以力比多的方式言说了黑人在白人面前的位置,在生理上即便是完整的黑人男性,其引诱也遵循了荷尔蒙的逻辑,但是黑人在美国文化之中并不只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的,在文化精神上是被阉割的,因而只能在个人力比多的激情未发生之前将之束缚住,重新让黑人体验作为被殖民者的痛苦,一如他们的祖辈。因此,当我们看到作为被殖民者的克里斯与殖民者罗斯“恋爱”的个体关系崩溃之时,罗斯的一秒变脸(从楚楚可怜的样子到邪恶女魔),以及在影片结尾处,克里斯也毫不思索地放弃救治昔日所爱恋的女友罗斯。这一场景寓意着这种由荷尔蒙所建立起来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瞬间破碎与土崩瓦解。这本身预示着基于个体的后殖民主义权利之间“碎裂的、矛盾的”关系。同时,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罗斯父亲宛如“纳粹医生”,是一名手持手术刀的刽子手,隐喻着某种纳粹、法西斯、极权的形象将殖民统治直接作用在黑人种族身体(比如男佣、女佣、以及黑人“兄弟”)之上的历史。换句说话,不同于以往,眼下的侵略者是通过现代文明的手段——手术切取黑人身体上他们有用的部分,使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占据了黑人的身体。而他们的身体在这里变成了美国曾经种植园奴隶制度的土地与空间。此时,白人的精神/灵魂侵入进来而黑人们变得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特别应注意的是,其侵入的方法就是现代科技,无疑呼应了现代/传统=殖民/被殖民的关系。
三、逃离异托邦的可能性
为了表明对黑人身体这一独特的“空间”的侵入,影片也为故事的发生设计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在影片中,这一切发生阴谋是在一个名叫“本塔科湖附近小镇”——远离城市的、隐蔽的(周围有树林与湖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夺命空间。事实上,这一空间所呈现的某种异质性在影片开场已经交代清楚了。比如克里斯与罗斯到达她家,其父母走出屋子迎接这两位年轻人,从台词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非常高兴地相互打招呼、介绍与拥抱。然而,此时,摄影机并未使用或是中景、或是近景(甚至是特写镜头)的跟拍镜头来拍摄这一喜悦的场景。相反,摄影机使用固定的远景(甚至可以说是超远景)镜头。在这一极端对称的空间中,加之背景配乐,无疑是把克里斯封闭在一个内部空间中,暗含着异样的惊悚。也只有在这种空间中,白人以及白人社群才能关上大门。也就是说,为了占有“黑人”这一异于白人、异于现代文明的另类空间,影片打造出了一个异于一般现代文明社会的另类所在。在这个看似桃花源般的绝命镇之下,是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
福柯曾界定异托邦的六个基本特征:一是“不真实的空间”;二是“不同的方式存在以及发挥作用”;三是“有权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四是“同时间的片段相结合……为了完全对称,异托邦为把何物称为异托时开辟道路”;五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六是“创造了一个幻想空间的作用……人们以为进入其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其实是被排斥的”。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地指出:“关闭的房屋和殖民地,这些是异托邦的两个极端类型”。按照福柯给出的关于“异托邦”的论述,再借用格雷马斯以两组二元对立为基础所建构的“意义矩形”图,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发掘与理解这部影片中的关于种族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的叙事文本,图解如下:

如上图所示,影片中故事所发生的绝命镇是“异托邦”,在这个空间中,白人实行对黑人身体移植的处决行为,是与克里斯反抗相对立所代表的“反异托邦”。而城市就成为了克里斯所要逃到的、与“异托邦”对立、与“反异托邦”互补的“非异托邦”。在影片中,“非异托邦”所呈现出来的空间是影片开头克里斯可以洗澡、睡觉、工作的地方。“非反异托邦”中,黑人男佣、女佣,以及派对中黑人“兄弟”在精神/灵魂中成为白人中的一员。在两两相对的二元对立中,白人罗斯与黑人克斯里通过个体之间“恋爱”关系使得克里斯从一个城市(非异托邦/想象的乌托邦 )“被迫”来到的一个绝命镇(异托邦)的社会,而这个绝命镇给予了克里斯一个看似“打开的”、完全开放的空间。然而,这种空间是一个易进难出的“关闭的”系统。比如黑人男佣(罗斯爷爷)与黑人女佣(罗斯奶奶)扮演着关门人的角色来协助白人。可以看出,绝命镇上的成员只有在将被排斥在外的、异己的黑人身体经过高科技化的现代化技术移植同化后才能成为这个空间的一员,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有产白人的殖民地空间。
而“逃出”绝命镇,也同时伴随着对这个殖民的异托邦的粉碎。在这个意义上,黑人男主角与异托邦的斗争相对于主流世界来说,成为了一种异己对异己的消耗。终获胜利的克里斯,实际上本就是在现代文明中教养长大的人,他的自我意识恰恰来自于美国教育,他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主体而觉醒了。这让他的反抗反而成为了文明秩序内在的张力。正如《黑客帝国》系列中尼奥等人对矩阵反抗,本质上是矩阵为他们植入了反抗意识,是美国现代文明对危机的自我制造,并通过表现异己的反抗来反身印证关于人性、自由的价值。
而成功出逃的克里斯,也并未真正从等级秩序的结构中逃脱。逃出以及逃出的方式(杀白人)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形式的隔离,白人与黑人之间仍是无法交流的结构。克里斯从绝命镇/异托邦的逃出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的选择。它追求的不是种族平等交流,而只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自卫。这本身与《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中黑人酋长的逃出如出一辙:这“不是一个反叛的故事,而是一个秩序的故事;不是对好莱坞神话的倒置,而是对好莱坞神话一次精妙的改写”。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能够理解在现在白人中心主义的美国社会中,为何克里斯最后杀了白人全家还能在奥斯卡中获奖的原因。如果说这部电影中,鹿的“种族表象”与绝命镇的空间相互耦合,成为一种阶级表达的方式的话,那么基于这种“政治正确”下的口号,同时又预言了另外一种新型阶级的形成。
四、余论:未来阶级的预言
影片借由黑人身体来达到更为完美的智力与肉身的结合,也提示出一个未来乌托邦的探讨,它可以引出对不朽生命的想象。正如戴锦华在数次演讲中,面对今天社会中的数码转型与生物科学技术,提问到:“当人类即将问鼎死亡”的时候,她的回答是:“人类有可能战胜死亡了。生物学遗传工程,预示着我们可以修复细胞衰老,逆转细胞衰老,那我们就可以不死。另外一种不死,是我们可以通过赛伯格化,心脏坏了,换一个心脏……同样战胜了死亡。还有,我们上传下载大脑,做一个合成的数码生命,在我们的肉体后面永生”。虽然这部电影不是在戴锦华所谓的生物学遗传工程,以及赛博格的意义上展开的,但同样给出了我们对于未来的阶级预言启示——当全球上层精英人士拥有更为富裕的财富时,他们/她们面对死亡之时会像影片中通过买卖的行为来换取某一个器官,来换取重生的资格来战胜死亡吗?白人与黑人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到最后谁掌握权力,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下一个“地主”。笔者以为,这才是这部影片给予我们思考的价值所在,也是关于未来阶级议题的一则寓言吧?
注释:
[1] 活字文化.独家︱戴锦华点评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陈旧老套,完全不能打动我[EB/OL]. http://www.sohu.com/a/224870361_268920[2018-4-10].
[2]〔美〕尼古拉斯·韦德.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M].陈华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3]按照影片中罗斯父亲的解说,这张照片是罗斯爷爷曾经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预选赛上输给了一名黑人杰西·欧文斯的照片。
[4]此处的隐喻,请参见索海姆.激情的疏离[M].艾晓明、宋素凤、冯芃芃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
[6]〔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M].王毅、刘伟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7][8]〔法〕米歇尔·福柯.另一个空间[EB/OL].王喆译,http://www.sohu.com/a/130049843_237819[2018-4-1].
[9]戴锦华.经典电影十八讲:镜与世俗神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96.
[10] 戴锦华:当人类即将问鼎死亡[EB/OL].http://www.jiemian.com/article/585670.html[20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