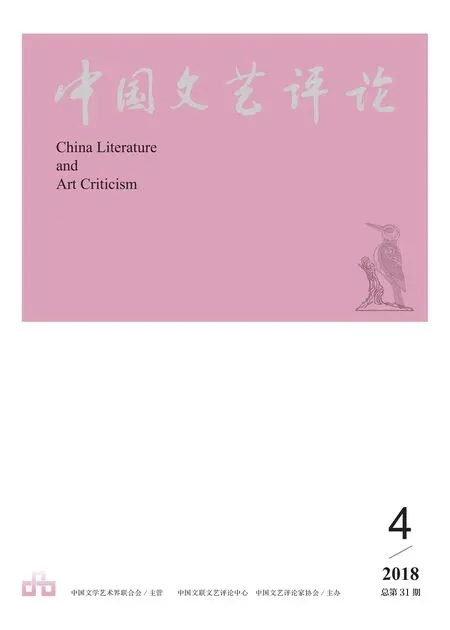当前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访美学家叶朗
采访人:顾春芳

叶朗简介: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座教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6年9月起任教授。曾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三个系的系主任。后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北京市哲学会会长。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美在意象》(《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意象照亮人生》《胸中之竹》《欲罢不能》等。主要编著和合著:《现代美学体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总主编)、《中国美学通史》(主编)、《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主编)、《中国文化读本》(合著)、《文章选读》(选编)。美学和艺术学的核心区域要有中国的东西
顾春芳(以下简称顾):现在学界都关注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美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应该有中国特色,要有中国的立场,要发出中国的声音,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哪里?
叶 朗(以下简称叶):这个问题,是从美学和艺术学的学科性质及学科历史提出来的。美学和艺术学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是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和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中国学者研究美学和艺术学,立足点应该是中国文化。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近代以来,我们的美学理论许多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比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美学理论,概念、范畴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上世纪60年代,周扬曾提出我们的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应该有中国的特色,当时虽然提出了这个要求,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仅仅是在讲到西方某个理论观点的时候,引用几句中国人的话,譬如引用刘勰《文心雕龙》里的话,表明这个观点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理论还不能说它呈现出了真正的中国特色。
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国内出版的美学和艺术学理论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比较多地吸收了西方的东西,但在整体上显得碎片化,缺乏内在的血脉贯通,主要还是它的理论核心依然没有中国的东西。这再一次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美学和艺术学基本理论在吸收和融合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如何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如何体现“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这是美学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的思考是,我们的美学、艺术学基本理论要想体现中国眼光、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在美学、艺术学理论的核心区域要有新的理论创造,要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提炼出具有强大包孕性的概念和命题,形成一个稳定的理论核心。这就是说,仅仅有中国的材料还不是中国色彩、中国精神,仅仅引用中国的例子或中国人的话还不是中国色彩、中国精神,必须理论核心要有中国的东西。这个理论核心是中国精神、中国眼光的结晶。这又要求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据我的体会,中国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学,它们的理论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十分重视精神的层面,十分重视心灵的作用。唐代思想家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宗白华先生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在中国美学中,“心”是照亮美的光之源,就是唐代画家张璪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正是在这个空灵的“心”上,宇宙万化如其本然地得到显现和照亮。中国美学的这个观念,在理论上最大的特点是重视心灵的创造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和精神的追求。这个理论,在历史上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个影响是引导人们特别重视艺术活动与人生的紧密联系,特别重视心灵的创造和精神的内涵。一个影响是引导人们去追求心灵境界的提升,使自己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从而去照亮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认识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学的这种理论品格,对于我们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核心区域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对于我们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中构建带有中国色彩的理论内核,可能有某种指引的作用。
这就是说,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理论核心区要有新的创造,要有中国的东西。这是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也是最前沿的理论问题。所以,我一再说,对美学和艺术学理论来讲,最基础的就是最前沿的。

“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是使美学理论内核带有中国色彩的尝试
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您构建的“美在意象”的框架,是不是在美学基本理论核心区域提炼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范畴的一种尝试?
叶:是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的同时,一直思考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如何体现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美在意象”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我第一次把“意象”作为阐述中国美学史的核心概念,突出了情感与形式的融合:美感和艺术中的情感总是被形式所“照亮”,而美的形式也总是呈现着人的心灵深处的情感。1988年,我带领一批研究生集体撰写了一部《现代美学体系》,这部书立足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吸收20世纪西方美学的成果,初步确立了一个以“意象”和“感兴”为核心概念的美学理论体系。这部书提出了对“现代美学体系”的“现代”的理解,“现代”是一个全球的概念,必须把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融合起来,所以中国学者可以对建设现代美学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在2009年出版的《美在意象》(黑白插图本名为《美学原理》)中,我对“美在意象”的美学理论框架作了比较清晰和比较全面的论述。这个理论框架,有三个核心概念:意象、感兴、人生境界。
第一个概念是“意象”。《美在意象》审视西方20世纪以来以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思维模式与美学研究的转向,从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转向对审美活动的研究,同时,又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反思,特别是审视长期以来美学界主客二分认识论模式所带来的理论缺陷,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范畴提出,将意象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意象”既是美的本体规定,又是对美感活动的本体规定。在审美活动中,美和美感是同一的,它的核心就是意象的生成。由“美在意象”这一核心命题出发,这本书讨论了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诸多问题,认为它们虽分属不同的审美领域,但本体都是意象的生成。许多美学命题与概念都可以在“美在意象”这一观念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与理解。
第二个概念是“感兴”(体验)。我在书中指出,美感不是认识,而是“感兴”(体验)。“感兴”是中国美学的概念,它的内涵相当于西方哲学中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所说的“体验”。我以王夫之的“现量”说来界定“感兴”。“现量”有三层含义:一是“现在”,美感是当下直接的感兴,就是“现在”,“现在”是最真实的。只有超越主客二分,才有“现在”,而只有“现在”,才能照亮本真的存在。二是“现成”。美感就是通过瞬间直觉而生成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三是“显现真实”。美感就是超越自我,照亮一个本真的生活世界。
第三个概念是“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人生境界”的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归结起来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
这三个概念构成了“美在意象”这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在这个理论框架中,美在意象的观点一以贯之:美在意象,美(艺术)是心灵的创造、意象的生成,美育是心灵境界的提升。
顾:您构建的这个“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的核心,很明显是对于您在前面说的中国美学的理论品格的继承。
叶:是的。“美在意象”的核心在理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这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讨论美学的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的新意都根基于此。这里的“心”并非被动的、反映论的“意识”或“主观”,而是具有巨大能动作用的意义生发机制。心的作用,如王阳明论岩中花树所揭示的,就是赋予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以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意义之中也涵盖了“美”的判断,“离开人的意识的生发机制,天地万物就没有意义,就不能成为美”。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张世英先生解释说,人未看深山中的花树时,花虽存在,但它与人“同归于寂”,“寂”就是遮蔽而无意义,谈不上什么颜色美丽。只是在人来看此花时,此花才被人揭示而使得“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哲学关心的也是人与物交融的现实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人与物相互隔绝“同归于寂”的抽象之物。“美在意象”的命题,突出强调了意义的丰富性对于审美活动的价值,其实质是恢复创造性的“心”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提高心灵对于事物意义的承载能力和创造能力。
提出这个理论核心,是出于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生活之间失去平衡。200年前,哲学大师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他的哲学史的讲演的时候,曾经对他那个时代轻视精神生活的社会风气感慨万分。他说:“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种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黑格尔所描绘的19世纪初期的社会风气,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仅重新出现了,而且显得更为严重了,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就是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这样发展下去,人就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当代的美学应该回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问题,而这又正好引导我们回到中国的传统美学,引导我们继承中国美学特殊的精神和特殊的品格。
提出这个理论核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美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突出审美与人生、审美与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价值追求的密切联系。美的本体之所以是“意象”,审美活动之所以是意象创造活动,就是因为它可以照亮人生,照亮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真正的中国美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理论和知识的滋养,培养起纯理论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感受人生、体验人生,获得心灵的喜悦和境界的提升。这样,这个“美在意象”的框架从理论内核上就带有中国的色彩,同时又是对新时代呼唤的一种回应。
人文学科的新的创造要“接着讲”
顾:您经常说,美学要从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接着讲”,为什么必须要“接着讲”?我们要从哪里“接着讲”?如果不“接着讲”会带来哪些问题?请您谈谈。
叶:“接着讲”和“照着讲”,这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两个概念。冯先生说,研究哲学史就是照着讲,康德怎么讲的,我照着他讲,朱熹怎么讲的,我照着讲。但是哲学家呢?要接着讲,就是康德讲到哪儿,我要继续讲下去,不能停留在康德,朱熹讲到哪儿,我也接着往下讲,不能停留在朱熹。冯先生说自然科学不需要接着讲,但是人文学科一定要接着讲,自然科学你可以讲最新的,但是人文学科老的你必须要讲,你永远要讲柏拉图,老子的五千言永远要读,不能抛到一边去,必须要接着讲。冯友兰先生自己对这个很自觉,在抗战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只是照着讲,我要接着讲,他写了《贞元六书》,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所以汪子嵩先生认为冯友兰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哲学家,他把西方的新实在论跟中国的程朱理学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人文学科一定要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照着讲是把原来的东西讲清楚了,接着讲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要往前发展,要有突破,要有飞跃。人文学科要产生新的概念、新的命题、新的思想,必须接着讲。接着讲方能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否则就有可能生造一些“新”概念,胡编一些“新“命题,甚至违反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那不是创新。
顾:我们人文学科,包括美学和哲学,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接着讲,这是什么缘故?
叶:上世纪50年代没有接着讲,这是认识上的原因。因为当时认为,这些老一辈的学者,冯友兰、熊十力、朱光潜等人,他们都是搞唯心论的一套,所以要把他们抛到一边去,一切从头来起。到了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前期,虽然对朱光潜、冯友兰他们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依然没有“接着讲”,为什么?这就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在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两方面有缺陷,所以不可能“接着讲”。当时学术界对西方的东西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对中国的东西也没有很好的研究,怎么能够接着讲?不可能接着讲。很多人读宗白华的文章,就理解不深,因为宗白华继承中国的哲学,如果对中国的哲学根本不了解就读不进去。我自己就有体会,宗先生的书里引了王夫之的一些话,当时我看的时候一晃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对王夫之那些话缺乏认识,所以也就不了解宗先生的深意。同样的道理,他们思想中关于西方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进去,因为我们对西方也不够了解。当时的学者普遍都有这个问题,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足,所以也不可能接着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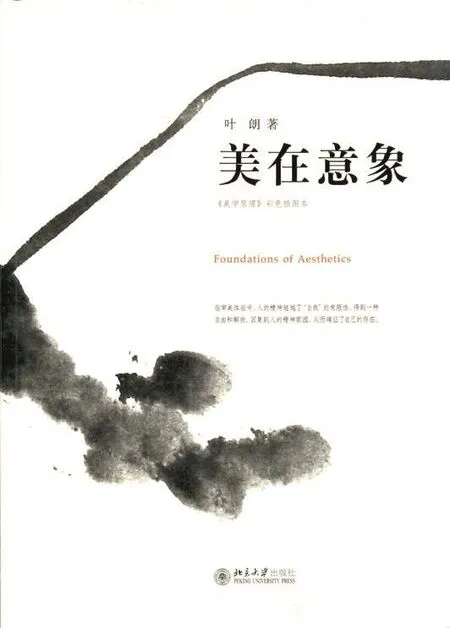
当时没有接着讲,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就是跟中国传统的哲学断了,因为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他们都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你不跟着他们接着讲,就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上停顿下来了。第二,也跟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断了,朱光潜、冯友兰都研究西方近现代哲学,抛开了他们,就等于把西方近现代哲学一些合理的东西也抛弃了。这样我们美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就非常有限。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要重视五四以来的老一辈的学者,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创新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很有启发。我曾经在好几个会上提出,要细读这些前辈学者的书,细读冯友兰、细读张岱年、细读朱光潜、细读宗白华,细读可以读出很多新的东西,细读可以读出很多对我们今天依然很有启示的东西。我自己读宗白华和冯友兰的书,依然不断读出新的东西,过去把这些思想成就完全抛在一边,真是极大的损失。
顾:我们在细读这些前辈的学术著作时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方面呢?为什么?
叶:我觉得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注意老一辈学者的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比如宗白华,他就抓住了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最核心的东西,重视精神的价值、心灵的作用;朱光潜特别强调艺术对于人生的作用;冯友兰强调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于人生境界的思考,这些都是他们各自思想的最有特色的内容。张世英认为哲学是境界之学,哲学就是要提高人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张世英继冯友兰之后接着讲。我们要抓住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接着讲。第二,接着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超越他们。怎么超越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抓住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最核心的地方来超越。譬如说朱光潜重视艺术和人生,那我们接着要讲艺术和人生,而且要抓住这些东西,在艺术和人生的思考上,我们要超越他。宗白华讲心灵的创造,我们要超越宗白华,也要抓住心灵的创造这个问题。
顾:我看到学术界有人说,宗白华先生的影响仅限于对中国古代艺术的解释,而进入不了美学基本理论的领域。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叶:这种说法显然不妥当。这样说的朋友,可能对宗白华先生的著作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宗先生著作对我们的启示,有许多是属于美学基本理论核心区的启示,因而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和美学体系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宗先生在这方面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点:一、美不能离开心灵的创造,因此中国艺术作品乃是呈现一个心灵的境界,我们前面引过他的话;二、中国艺术所呈现的境界,是“物我同一”的境界,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心灵和自然完全合一;三、中国的形而上学是生命的体系,它启示人们体味人生之情趣,因而成就一种审美的人生。这些思想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都有极大的启发。
顾:我想,“接着讲”也要重视张世英先生。张世英先生本来研究的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研究黑格尔。改革开放以后,他从西方古典哲学转过来,注重研究西方现代的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他同时又思考如何把西方这些现代哲学跟中国古典哲学融合起来。比如,他特别强调西方的哲学是主客二分的模式,到了海德格尔就发生了改变,用中国的术语来讲,就是强调天人合一。这对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极有启发。
叶:这个观念对美学来讲太重要了,因为美学在上世纪50年代有过一场讨论,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当时的理论框架就是主客二分,它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的本质,也就是“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美感决定美,还是美决定美感?”这是把哲学里面的物质和精神的问题搬到了美学领域,从哲学讨论的“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转移到讨论“美和美感谁是第一性的?”从理论上说,这种讨论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审美活动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种体验;美感不是认识,不是主客二分的,本来人就在世界里面,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人融身于世界万物之中,所以那个讨论在理论上对美学推动不大。今天我们回到天人合一的思考,所以张世英先生的思想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顾:我读了张世英先生的著作,我感到这些著作对于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也极有启示。

叶:是的,我举一个例子。张世英先生引用禅宗的思想论述中国美学关于消解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的思想,就十分精彩。张先生说,康德已经指出“自我”并不是实体,但他并未完全克服“自我”的二元性和超验性,而中国禅宗的思想就更有启发。大家都知道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慧能的偈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惹尘埃。”(惠昕本《坛经》把慧能的偈子改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明显,在神秀那里,还存在一个实体性的心的本体,要求对它时时拂拭,使之保持寂静,而慧能则要超越这种主客二分关系中的“自我”,要消解神秀这个实体性的心。慧能所说的“心”,是指人们当下念念不断的现实的心。这个现实的心不是实体,不是对象,是“无心”,是“无念”,这种“心”是无从把握的,只有通过在此心此念上显现的宇宙万物而呈现。在这个境界中,人们才能真正见到事物(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万物皆如其本然,这种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在非实体的“心”(“空”、“无”)上面刹那间显现的样子。反过来说,“心”的存在,就在于它显现了万物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心物不二”。所以马祖道一说:“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这就是禅宗的智慧,也是中国美学的智慧。这对我们构建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当然极有启示。
文化的复兴要返回经典
顾:您强调美学和艺术学的研究要重视经典、细读经典,是否请您谈一谈经典的意义。
叶: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凡是文化的复兴都是返回经典,这可能是一个规律。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也要返回经典。我们所要重视的经典,一个是理论经典,理论经典一方面是古代的经典,古代的经典是中国人做学问一个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是现代经典,现代经典是我们直接的资源。我们现在需要在前人开启的重要领域,进一步加以发挥。比如宗白华的很多思想都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发挥。看他的书,有时感到遗憾的就是他没有进一步发挥,而这正是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发挥和创造的理论空间。还有一个就是艺术经典,就是要从抓住中外的艺术经典,通过这些艺术经典来深入探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比如通过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红楼梦》,研究齐白石等人的艺术,在研究艺术大家、艺术经典的基础上展开美学问题的研究,从方法上来讲,这可能是很好的方法。通过这些艺术经典来研究美学,不纯粹是为了解释作品本身,而是要通过对作品的研究,上升为研究中国的美学以及研究一般的美学。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那篇文章中,就提出了一些理论创新的伸展点,他强调把哲学文学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这个思想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中国美学的研究状态,跟今天国际上风行的图像学的这种思想史的研究路数很近似。他特别注意工艺器物、文艺作品的虚灵化的一面,并且把这个方面跟“易”象相联系,他强调器物的非物质化的一面,可以和“道”有契合的一面,这些思想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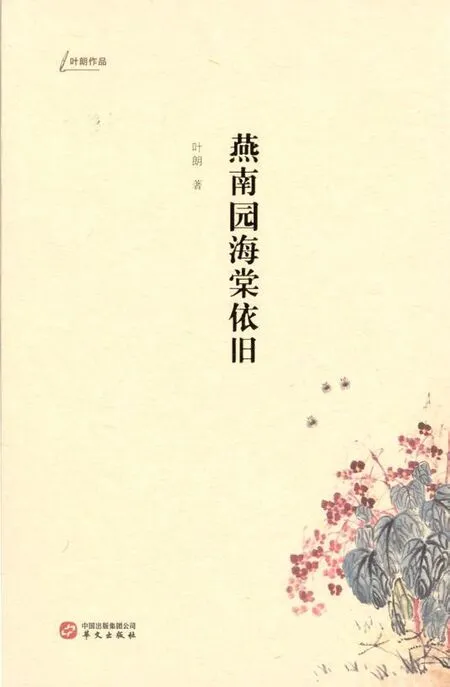
过去有些学者研究美学,因为脱离了艺术,脱离了艺术的实践,所以不可能解释那些造就了经典作品的伟大的心灵。如果脱离活生生现实的生命活动,脱离对于审美意象以及艺术史的具体分析,而去讨论什么美的本身(最早柏拉图提出的),美的根源,往往落到了空洞的概念里面。那种研究不能解释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伟大的心灵,而你看宗先生的著作就没有这个问题。
研究艺术经典是和人类伟大的心灵对话
顾:您认为,推动美学研究当下最需要做些什么?
叶:我们研究美学,需要思考最普遍的理论问题,找到稳定的理论核心,以免随波逐流。现代之后的西方是变来变去的,你也老是跟着它变来变去吗?我们自己要有稳定的理论核心。我们要始终和人类心灵创造的最高成果交流,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借助经典,抓住最普遍的、最稳定的东西做我们的学术研究,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学术不能跟随混乱易变的现象惊魂不定、随波逐流。立足于经典,我们就稳定下来了,这些伟大作品背后是一个个伟大的心灵,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些伟大的心灵的创造。
过去我们跟学生讲,研究美学,你要热爱艺术,你要懂得艺术,不懂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的角度跟过去的角度又有变化,或者说又提升了一步,不仅是你为了要理解美学或者研究美学,要懂得艺术,而且是说我们要通过研究艺术经典来推动美学理论的发展。从研究艺术经典来推动理论的发展,过去好像没有人这么强调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艺术是人类心灵的创造,或者说美是人类心灵的创造,而经典艺术或者艺术经典,历史上的艺术经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心灵的创造。比如《红楼梦》,它就是最伟大的心灵的创造,美的秘密都包含在里面。同样是心灵的创造,一般的心灵创造和伟大心灵创造不一样。从《红楼梦》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审美创造的秘密。又比如贝多芬的音乐,贝多芬从青年到中年、到晚年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到晚年他就进入到一个化境了,也就是天人合一之境,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人生的最高境界。贝多芬是如何到达这个最高的境界的,这对我们研究美学大有启示。再比如毕加索见了张大千说,你怎么还要跑到西方来学艺术?齐白石这个人,他的艺术是纯中国的,他从来没有接受西方的东西,完全在中国这个土壤上土生土长出来的一个画家,却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大师。我们不能拿西方的一个框架来框齐白石,而要从齐白石来研究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美感,这将会给美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我们再回到《红楼梦》,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红楼梦》的意蕴?很多人看到一僧一道带着贾宝玉出走,就认为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所谓“遁入空门”,由此又认为曹雪芹把佛教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其实,贾宝玉并没有出家当和尚。他来自“青埂峰”,又回到“青埂峰”。“青埂”是“情根”,这是说,“情”是生命之根,是天地的本源性存在。这个“青埂峰”就是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有情之天下”的象征。当下的生活世界体现了“有情之天下”的人生理想,就是“青埂峰”。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块石头从“青埂峰”幻形入世,最后又回到“青埂峰”,就是为了显示“有情之天下”不在彼岸,而是在此岸,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尽管受种种限制,尽管时间短暂,有时只是瞬间,但是它是活生生的,而且瞬间就是永恒。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皮埃尔• 阿多说的,当下瞬间的体悟是存在的最为真切的感受,这种有限时刻蕴含有无限价值。“空空道人”看了这部《石头记》,改名为“情僧”,把《石头记》改名为《情僧录》。曹雪芹最终是用“情”充实了“空”,用“情”照亮了“空”,把“情”提升为最高的范畴。对于曹雪芹,“有情之天下”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之所在。这是曹雪芹追求的精神家园。这样我们研究《红楼梦》,就不会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小说研究,而是通过《红楼梦》来研究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研究哲学和美学的问题。
通过研究艺术经典,我们和人类最伟大的心灵对话,通过对话来把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心灵创造的一些秘密,并上升到美学的高度,这样的美学思考,才会有生命力。过去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才是常青的”,但是如果把美学研究和最伟大的艺术经典连在一起,这样的美学理论就是常青的,就会充满了生命力。
顾:我非常赞同您刚才所说的立足于经典研究美学和艺术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样才能寻找到现代性这条流动的河流背后隐藏的那一种不变的本质。卢卡奇认为现代性没有本质可言,为什么没有本质可言呢?因为现代性本来就不是固守传统和现在,而是坚信未来的一种信念,所以由这个未来的诉求催生了一个快速的、易变的时代,从现代到后现代,最突出呈现的特点就是快速和易变,现代人的目标首先是要追寻并拥有一个未来。由这种无止境的速度和变化所带来的正是工具理性的泛滥,而工具理性恰好与人的自由个性相违背,因为它从根本上无视个体生命的差异性,甚至制度性地抑制和抹平个体的差异性,并由此导致了人类群体性的精神危机。而中国哲学的重要核心便是重视心灵、关注当下,和西方现代性的速度与未来的取向不同,中国哲学倡导回归自己的心灵。这种向内的力量和关爱不啻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拯救力量。海德格尔的意义就在于,他指出了生命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指向未来,就是死亡的未来,另一方面是返回本真,体悟当下,这是逆西方的哲学和现代社会的潮流和时间观的一种哲学,而正是这种哲学呈现出和中国哲学的相通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哲学中也包含着现代性的内涵?
叶:是的,中国古人讨论的一些问题,其实很有现代意义,有的超越了现代西方的理论高度,这些问题正是当今时代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对技术的反思,比如美感和宗教感的关系问题,自然和人的关系的问题,生活审美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也许是将来中国美学可以取得突破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去发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有现代意义。尤其是天人合一、拯救心灵的问题,人生情趣、审美情趣的问题,这些理论很宝贵,需要把它提炼出来,提升出来。
艺术家的生存风格和生命华彩
顾:讲审美,我想不仅要追求艺术作品的美,不仅要用艺术的审美体验和心思灌注日常生活,从而获得一种“诗意的栖居”,尤其要追求人格的美。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吧?
叶:当然。中国古人极其重视艺术家的人格,重视艺术家的人生境界。中国美学从来认为,艺术作品的品格和艺术家的品格是统一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嵇康。嵇康这个人长得很美,《世说新语》记载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当时人说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山涛说他“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的书法和他的人一样美,“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 群鸟乍散”。嵇康弹琴,和他的生命追求融为一体。他40岁被司马炎杀害。据记载,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长叹说:“《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的音乐和生命合二为一,升华为崇高的人格境界和审美境界。我们研究中国美学,不仅要关注艺术作品,而且要关注历史上如嵇康这样的艺术家的生存风格和生命华彩,他们用自己的崇高人格和生命创造了诗意的人生境界。
当代艺术大家对美学的启示
顾:刚才讲了借助历史上的艺术经典推升美学研究的重要性,那么美学是不是也要关注有足够历史延伸力的当代艺术经典呢?
叶: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美学当然要研究当代的艺术大家,要照亮当代的艺术大家,这对我们美学研究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研究当代的艺术大家,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我们可以通过当代的艺术大家的研究,去发现中国艺术往前发展,到底碰到什么问题?可能开拓什么新的境界?比如书法,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研究沈鹏这样的书法家,来研究中国的书法现在如何往前发展,如何开拓新的境界?比如潘公凯,他的水墨画有家学渊源,但是他没有限于水墨画,他还想面向当代,面向世界,吸收一些新的东西,把水墨画跟高科技结合在一起,水墨画、动态影像、高科技摄影、装置、建筑合为一体,营造一种动静交融、多种美感交会的环境氛围。这就使我们思考中国水墨画如何向前发展,可能有什么新的境界。从这些艺术家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如何传承和创新。不是像西方后现代,把过去全部推翻,都不要了。我们这些艺术大家是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的大家,我们可能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来发现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些新的方向或者新的境界。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过对当代艺术大家的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东西方艺术的相通之处。我们研究沈鹏,看看他的书法跟西方的艺术是否有些相通的地方?丁方是油画家,他在西北大地上行走,画这崇伟的高原,画七八千米的山峰,他要雕刻出河山的身姿和祖先的面目。他也临摹西方的东西,西方的东西在他的画里怎么体现?可能会给我们启示。
以审美的体验和心思灌注日常生活
顾:除了艺术,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可以从美学的视角出发。 比如近来美学界比较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您可以就此谈谈吗?
叶:日常生活的审美追求,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里的人生情趣,这也很值得研究。过去我们注意不够,现在学术界很多人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一种美的氛围,创造一种快活、热闹、优雅、精致的生活世界。《红楼梦》里就有不少这样的描写,北京的文物学家王世襄,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仅琴棋书画,而且还养老鹰、玩蝈蝈、养鸟、玩鸽哨等等。宋代、明代的那些文人和艺术家在生活美学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宋代的城市有现代气息,不像唐代到了晚上就禁夜了,宋代的城市是彻夜狂欢的,非常有现代味道。这种带有现代味道的城市,就会萌生更多的审美追求,包括人的打扮、装饰,日常生活把玩的事物,都很讲究,富有生活情趣,这应该是审美活动一个重要的方面。
顾:能够有大量属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个生命就显得异常富足,它可以一任心灵做自由松弛的旅行。马克思说过,“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照理说,高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人的自由更多了,但在现代社会结构下,人的时间反而都被绑架了,被一个个所谓的目标给绑架了,所以现代人很少有那种闲情逸致了,生活缺少情趣的直接原因就是人的个性被抹平或者是扭曲了,人没有自由的时间,心灵找不到安顿的方式。所以美是跟自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
叶:是的。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一批文人、艺术家形成了一种优雅、精致的审美情趣,他们弹琴、赏花、品茶、焚香,设计园林,赏玩奇石。据记载,晚明一位品茶专家可以分辨出50种名茶的产地、成色和十多种泉水的滋味,又有一位品鉴香味的专家可以辨别出空气中上百种香气。他们在休闲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生命活动的空间,这是非实用的、审美的空间,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一个张扬“性灵”的空间。在这种非实用的、审美的空间里,他们有了心灵的自由,这是马克思说的自由的王国。
顾:谢谢叶先生。今天您谈了当前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中有观念的层面,也有方法的层面。我想您今天说的最重要的想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现在大家都关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体现中国眼光,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在美学和艺术学的核心区域要有中国的东西,要提炼出具有强大包孕性的概念和命题,形成一个稳定的理论核心。这又要求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学理论,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第二,您提出的“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是构建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的一种尝试。这个理论框架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也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回应。第三,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新的创造,一定要从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张世英等前辈学者“接着讲”。第四,在研究艺术经典的基础上展开美学问题的研究,推动理论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第五,我们也要关注艺术家的崇高人格,关注艺术家的生存风貌和生命华彩,关注当代艺术大家和当代艺术经典,关注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的审美追求。
访后跋语:
我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和叶朗先生经常参加共同的学术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研究项目,有较多的机会求教问学于叶朗先生。美学和艺术学的基本理论建构一直都是叶先生学术思考的重心所在,无论是《美在意象》的撰写,还是由他发起和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都指向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当代中国美学和艺术学如何“接着讲”?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美学和艺术学的特殊品格?此次受《中国文艺评论》的委托,对叶朗先生进行了专访,访问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由于篇幅所限,文章内容聚焦于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艺术思想是各民族思想和文化海拔上的制高点,艺术思想也必将成为历史和时代的精神建筑上凝固的雕塑。每一个时代的特性、思想、文化、气象都会在这个精神建筑中得以彰显。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现实意义和未来空间需要更多的学者加以阐发和推进。这对于重新发现和确立中国美学在当代艺术学理论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于艺术学的研究从中国美学中汲取智慧和方法,从而确立自身的美学立足点,至关重要。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是关于“美”的核心概念,是中国美学一个意味无穷的命题,也是中国美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对美的最高认识。意象世界的把握和创造体现了艺术家对于社会历史和宇宙人生的整体性、本真性的把握,它呈现一个美感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同时也敞开和呈现了一个有别于生活表象的更加深刻和本真的世界。
意象的生成,包含灿烂的感性和深刻的理性。意象的生成不是简单的表现,更非机械的模仿,意象的生成是灵思,是妙悟,是超越表象以契入本真的神思妙造。它需要回归一种内在的、非功利的、虚静空明的心境,从而自由地观照意象之妙,融万趣于神思,艺术的创造、欣赏和领悟,美感的体验皆蕴含其中。对“意象”的研究有助于澄清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上的纠葛,有助于艺术观念的澄澈和提升。
艺术研究不能脱离艺术本身。艺术的研究,艺术学的研究,一定是要立足于艺术本身,不能脱离开艺术来建构所谓的艺术理论。凌空蹈虚的所谓艺术研究,在割裂艺术理论和艺术之时也就宣告研究者退出了艺术研究的核心地带。美国批评家桑塔格曾提出反对过度阐释,过度阐释和根本脱离艺术的阐释使理论变成了自娱自乐,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美学和艺术学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们,必须学会更多地去听,去看,去观察,去体验。艺术理论工作者最根本的一个素质,就是艺术感觉。艺术创造并不是逻辑分析的产物和结果,艺术理论也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逻辑分析的产物和结果,艺术的理论应当包含理论家非常丰富、细腻、精致的艺术感觉,也就是说,理论家也必须具备相当的艺术修养,要有对艺术经典的丰富的直接鉴赏的经验和系统的艺术史的知识。
对于美学和艺术学研究而言,审美意象是在传统和当代、艺术与美学、艺术审美和艺术哲学等多个维度和层面都具备深刻意义的美学范畴。我以为“美在意象”的理论体系建构必将为当代美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建构注入新的活力,也必将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美学和艺术学理论贡献中国智慧。
- 中国文艺评论的其它文章
- 艺术至“真”
——梵高绘画艺术及其内心世界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