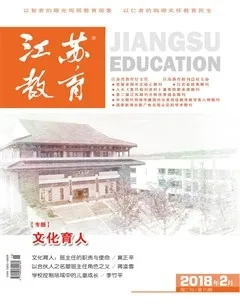学校控制场域中的儿童成长
【摘 要】“自由与枷锁”是理解学校中儿童成长的诸多视角之一,这一视角聚焦儿童成长的真实状态,即儿童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被控制的纪律环境中。理解这一事实,有助于教育者引领、陪伴儿童以主体身份体验自我实现,从而拥有能够自我感知的生命成长。
【关键词】儿童成长;自由与枷锁;空间性和时间性;自我实现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15-0065-03
【作者简介】李竹平,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北京,100176)教师,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
一、枷锁中的儿童选择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适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学校中的儿童。因此,教育语境中的“尊重天性”,也就不是纯粹的诗意情怀,应包含理性思考和判断;尊重的不是简单的“自然属性”或“天然品性”,而是儿童成长的一般规律性。
学校作为一种组织性的存在,从一诞生就拥有了“规则”属性,按照既定目标培养和塑造“人”是其根本职责。进入学校的每一个儿童,无论愿意是否,都被要求学习并内化学校规则,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
讨论学校中的儿童成长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由”和“规则”,卢梭所言之“枷锁”,也可以理解为“规则”。但本文要讨论的与“自由”对举之“枷锁”,还包括其本义。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一个一年级的班主任,新学期一开学就遇上了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刚满6周岁的小男孩死活不肯上学校的厕所,嫌学校厕所脏。不上厕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他在教室里尿裤子了。小男孩第一次尿裤子,班主任与家长沟通后,综合各方面情况,推断原因是孩子贪玩,于是便颁布了一条班级纪律:每节课后必上厕所。但是,小男孩还是尿裤子了。原来,他每节课后虽然都去厕所了,却都是“适可而止”——到了厕所门口就不再向前。班主任再次采取了措施,开了班会,让孩子们认识到憋尿的危害。小男孩几天无事,班主任以为大功告成,没想到真相是他用尽量不喝水或少喝水的对策解决问题,导致口干舌燥,嗓子发炎……
上述案例中,判断学校厕所脏不脏和选择上不上,都是小男孩的自由,从儿童人身权利的角度来考量,学校和班主任应该尊重他的判断和选择。但是,当小男孩连续8个小时都身处学校这一特定空间范围内,却不上厕所解决大小便问题,显然会对其身体造成伤害。这种情况下,班主任颁布了“每节课后必上厕所”的班级规定,明显是为儿童的健康着想的,维护了儿童的健康权。如果小男孩遵守这条规定,就要被迫放弃不上学校厕所的“自由”;如果不遵守这条纪律,就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那么,“每节课后必上厕所”这条纪律,是“规则”还是“枷锁”呢?以小男孩为主体进行考量,这条纪律显然是强加的,他并没有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协商和制订;同样,学校厕所气味难闻,蚊虫飞舞,这样的厕所环境也是小男孩无法选择和改变的。所以,这条纪律对于小男孩而言,不是规则,而是“枷锁”。这是我们将“自由”与“枷锁”对举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在很多情况下,儿童以主体身份参与协商制订的规则也是他们眼中的“枷锁”。有一个哲学命题是“禁止与引诱”,只要是规则,必然包含了“禁止”和“控制”,之所以“禁止”“控制”,从单向度考虑,是为了尊重和保护“他者”的权益,尽管反之亦然,很多人还是觉得“禁止”和“控制”是对自己的约束——儿童更容易有这种感受。“设身处地”是理解规则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应有姿态,儿童往往也能懂得这一点,且大多情况下明白违反规则的不良后果,但在他们的心中,规则本身就是“枷锁”。
面对“规则”或“枷锁”,不同的儿童会有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遵守(屈服),有的选择直接对抗,还有的选择“二次调整”。上面案例中的小男孩面对“每节课后必上厕所”这个规定,就运用了二次调整策略——下课即去往厕所,到厕所门口后返回。他这样做,与一些儿童把玩具藏在口袋或书包里,以应对“不准带玩具到学校”这一规则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属于儿童的“二次调整”。
学校中的儿童,遵守规则是成长,二次调整也是成长,直接挑战规则同样是成长。这是我们理解学校中儿童成长的基调,也是教育者“尊重天性”的理性认同。前者是符合教育目标、合乎教育者期待的成长姿态的,后面两种属于儿童自发的,或者创造性地吸收并整合成人世界解决问题方式的成长选择,教育者需要深入研究其成长价值并做出积极回应。
二、被控制的儿童成长
理解童年离不开两个重要的维度——童年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这两个维度对儿童自身的成长和如何理解儿童的成长,都有重要的意义。“自由”离开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就无从谈起,“规则”亦然。正因如此,时间和空间有时直接成了儿童眼中的“枷锁”。我们讨论学校中儿童的成长自由与否,首先就要承认一个事实:儿童无时无刻不是被“控制”的。
这里要讨论的儿童成长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只限于学校之内——虽然我们很清楚,学校之外的家庭、社会同样在这两个维度上对儿童的成长影响深远,同时,学校还始终与家庭、社会紧密联系,甚至不可分割。
“任何课程的核心组织原则是时间表,而时间表本身是国家意志的高度编码的空间化。”《童年论》中的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学校课程以时间表或课程表的方式,赋予学校内的每一个空间单元以纪律性,使其成为儿童成长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空间,儿童也就自然地被这样的空间所定义、所控制。一间间教室、一座座教学楼、一堵堵围墙,将学校以课程和儿童成长的名义封闭起来,这种空间上的封闭,为的是“塑造”的目的,也是控制的目的。现今,教育研究者越来越强调开放性、综合性或实践性的课程,如最近提出的“研学旅行”,从表面上看,儿童在短时间内摆脱了学校空间结构单元或围墙的控制,置身于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被控制的实际空间发生了转移而已。教育者,尤其是一线班主任,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儿童在学校空间里的真实感受。
关于童年的时间性,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独立的时间段,也可以理解为时间的结构和秩序塑造了童年。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理解时间,它又是儿童以主体身份对童年时间节奏的体验和参与,没有儿童主体的体验和参与,时间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学校中,童年的时间性首先表现为年龄的序列特征,这在现代学校中,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统一年龄入学。这种统一,从制度层面完成了对儿童成长的控制,它简单地将所有儿童同质化,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在制度层面就被忽视——这是标准化对时间的管理加之于儿童的控制。当这种年龄序列成为制度化的一部分,人们就容易忽视其对儿童成长的实际影响。例如,大家在谈论落实教育或教学目标时,往往只谈“课程标准”是怎样规定的,当然也会说到“学段”这类时间概念,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目标所对应的儿童的年龄序列,更没有考虑到这种年龄序列本身对不同儿童差异性的忽视。这些目标将儿童的成长框定在“标准”中,为特定年龄儿童分配了相应楼层的“房间”,而不会关心儿童有没有能力登上那个楼层。我曾遇到一个孩子,在6周岁入学时被测定心智年龄比一般同龄孩子落后了两年,因此要推迟两年入学,但家长必须要提供相关证明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家长觉得这有损自尊,更担心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便放弃申请,让孩子按“规定年龄”入学。现在这个孩子五年级了,学业上始终无法跟上班级同龄儿童的步伐,也无法与同龄儿童正常交流。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空间和时间对儿童的控制?学校中童年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并非完全外在于儿童成长体验的。从课程设计的角度可以肯定,学校中的空间和时间管理立足的是未来导向的视角,指向了儿童未来的样子。这是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儿童习得成人世界规则和节奏的必由之路。在这必由之路上,儿童也并非完全以客体的身份“被控制”和“被建构”,他们会越来越清晰地以主体身份去体验、去参与,并进行创造性的自我建构,逐步发现这种空间性和时间性对自身成长的意义。教育者,尤其是班主任,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与儿童展开理解性的对话,从最大限度上消解这种控制对儿童个体的伤害。
三、自我实现是自由成长的本质
既然童年是整个生命历程中受控制最多的阶段,儿童又如何实现自由成长?
空间和时间在学校环境中限制了儿童的主体性,同时也塑造了儿童的主体性。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他们的自我实现都只能在特定的纪律环境中才具有意义和价值。有人用“农业”来比喻理想的教育和儿童成长,“尊重天性”“顺其自然”成为教育叙事的追求。显然,传统农业只能聊以解决温饱问题,且难以实现置身其中者的精神启蒙。面对一个在课堂上肆意展现“个性”(如随意走动且大声说笑)的儿童,或者一个觉得体育锻炼很累就执意不上体育课的学生,教师是否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学校里的时间和空间(即课程)对这些儿童的控制?问题的源头,要追寻到儿童是如何体验这些控制的,有没有真正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对这些控制的建构当中——缺失了主体身份的建构,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愿望,纪律环境就成了令人恐惧的“枷锁”,而非可以内化为积极体验的规则。因此,教师应该做的,就是引导儿童以主体身份去参与、去体验学校课程。现实教育背景下学校中的儿童被当作了主体,却没有自我感知的主体意识,这才是自由被异化的根源。
儿童是由年龄和身份相互交织的具体形态所定义的。儿童在学校中的体验,是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可能选择一种更加重视当下的世界观,而非如成人所期望的未来导向的世界观。教师读懂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儿童当下的心思和成长的需求,也就拥有了教育意义上的同理心,从而让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建立起沟通的可能。这样,“控制”或“枷锁”就不再是“自由”的对立面,而是“自由”的保障,儿童才能够以主体身份体验到成长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