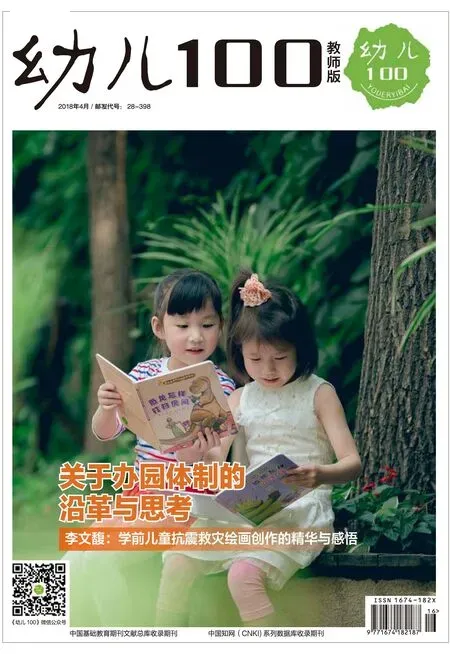从“洋为中用”到“和而不同”
——读《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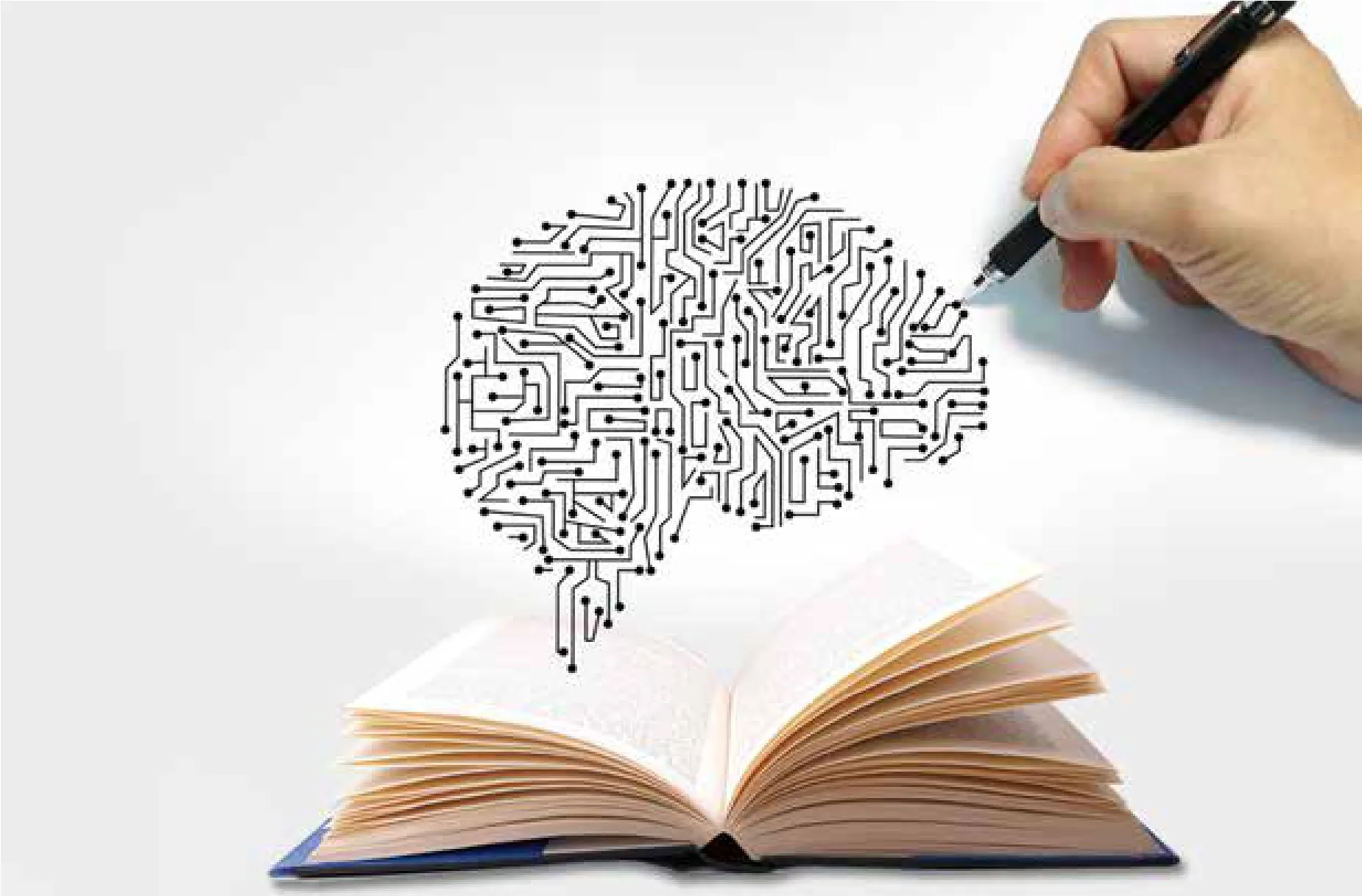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始于“西力”的冲击、“西潮”的启蒙,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学科制度的建立、教育学体系的形成等等,也都不例外。作为教育学科重要的学术分支,比较教育学科百余年来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留下了什么样的学术遗产?《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一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比较教育文库》丛书之一,主编是两位比较教育领域知名的学者王长纯和王建平。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用出版物长时段记录的呈现方式来展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的发展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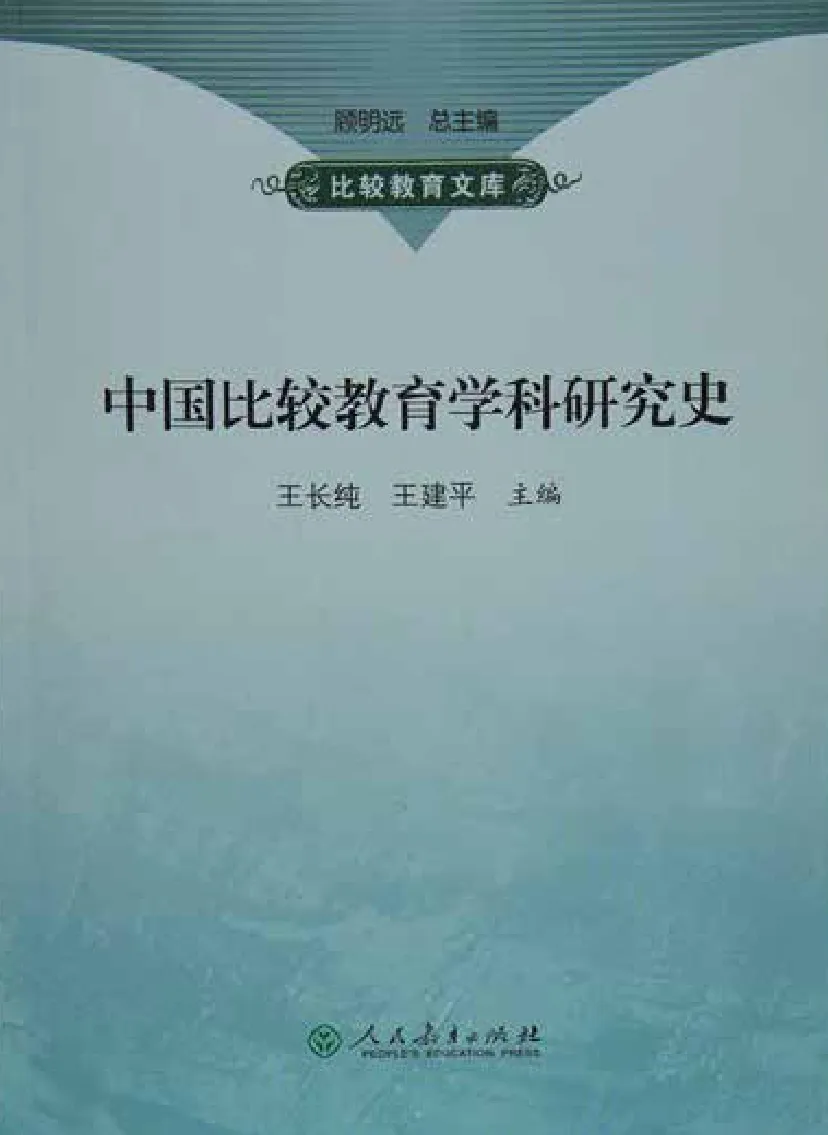
综观全书,其历程可以描述为一幅从“洋为中用”到“和而不同”的漫漫长卷。“洋为中用”是一种借鉴的思想,是中国比较教育起步阶段的特征,也是比较教育在世界诞生之初的特征,其方法是把搜集到的教育资料进行比较,以便把一国“最好”的经验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和而不同”则不再追求“最好”和“借鉴”,而是寻求多元、对话与理解。
在这张铺陈开来的图卷上,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开眼开世界”的中国人奋发图强,忧心国事的志士仁人积极地东学日本、西访欧美,千方百计为衰弱的祖国“输入新知”,以帮助她实现尽快步入现代化之林。在这幅幽深的长卷上,也有着比较教育学科百余年来“探索中的曲折”和“曲折中的探索”。
《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全书内容分为八章,从文字媒体记录的角度来探究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所走过的六个阶段,融实证性、资料性和研究性为一体,初学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一门学科的发展,也可对中国教育百余来汲汲于学的精神有所感悟;研究者更可视此书为一本详实的学术研究资料,分享百余年来每个阶段中向异乡“借镜”的教育学人那迸发的思想,接续他们的曾经的思索。
书中划分的六个阶段分别是酝酿期、初始和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停滞期、重建期和多维探索期,内容分量最多的是第六部分,占到全书三章。
第一个阶段是从1860年到1911年,这是中国比较教育的酝酿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批中国的先觉者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通过翻译西方文献、考察西方实际情况、向中国介绍“西艺”、“西学”、“西政”等方式,推动中国持续卷入现代化浪潮,并促进了中国早期学制的建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书中认为“当推吴汝纶等人”,并提要介绍了吴汝纶的西学观及其在日本所进行的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主编王长纯在后记中动情地谈到“在整理学习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资料时,我曾为《吴汝纶全集》中字里行间洋溢的清末爱国志士拯救国家与民族所表现出的凛然之正气、苦苦追寻之炽烈情感与急切精神所深深撼动,对一百年多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者站在改革前沿为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所做的坚持与奋斗充满由衷的敬意。”
在各类新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出现了《教育世界》等教育专门杂志,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比较教育方面的。另外,这一时期还新建了一些出版机构,并大量引进国外的比较教育研究著作,数量最多的是日本研究外国教育的著述。这一时期尽管“比较教育”这一概念还未曾引入,但先驱者们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体发生了转变。从原来的兼具“官员·学者”身份的人转向专业人士和学者,如庄泽宣、常道直、钟鲁斋、罗廷光等人,不仅在国内外获得教育学专业学位,且在大学中任教,他们开始使用“比较教育”这一概念。这一时期的“著作提要”部分共介绍了四本著作——清华大学教授庄泽宣的《各国教育比较论》以及常道直、陈作栋、钟鲁斋各自的同名书籍《比较教育》。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点是国外的教育制度,目的仍是借鉴国外的经验以改造中国的教育,研究方法则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到国外访问,现场调查,一是进行资料研究。
第三和第四个时期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曲折期和停滞期,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至1976年,比较教育不仅失去了学科地位,甚至这名称也无法保存。深表惋惜之余,书中也关注到了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比较教育研究动态。
第五个时期是从“文革”结束到1992年,称为“重建期”,在老一辈学者带动下,中国第一个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主动与自觉的姿态。在传播上的表现便是各类出版物的涌现。书中分译著、论文、著作及教材四类予以提要介绍。其中译著提要4篇,论文提要50篇,著作提要6篇、教材提要2篇。
第六个时期即“多维探索期”,从1993年至2010年,时间跨度尽管不到二十年,内容分量则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教学活动活跃,且把自身的建设当成了一个专门研究的主题,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多维探索的指的是:一是,对比较教育认识的多元性;二是,在比较教育研究目的上,从“借鉴”转变为“理解”,本书主编王长纯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国际理解是比较教育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总原则应该借用孔子的思想——“和而不同”;三是,研究对象多样性,国际组织、区域等都被纳入比较教育研究的视线;四是,方法论建设上的深刻性。如顾明远运用文化研究方法开拓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关系”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开拓出中国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范式,其代表作为1998年出版的专著《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还有一些学者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迪下,从多的不同的角度聚集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研究上,如冯增俊、项贤明、陈时见、朱旭东等学者都曾撰写过重要的文章。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比较”这个核心关键词,他们指出,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是简单地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加以描述,其任务应该是探寻“关系及关系方式”进行比较而不是对事实进行比较,因此,比较教育的本体不是普通的物质存在,而应是一种“体现学科内在的思维逻辑的一种东西”,可以称之为“比较视野”。在“比较教育学科与教育学科的关系”这一问题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在“研究方法的取向”上,在吸收现代哲学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作用。王长纯提出的将“和而不同”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总原则和总方向。
这样,中国比较教育学科便由开端时期的以国外教育为学习、模仿对象的“洋为中用”阶段,历经探索、劫难,在前进中深化认识,在比较中成长。“和而不同”是对“世界是多元、文明是多元的”这一事实的体认,是对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历史传统、教育文化的尊重与接纳,其路径是:经由“和”,而达到“不同”,其中的关键是“对话”。当然,当今世界的“对话”仍然非常不充分。
这一时期的成果极大丰富。书中仍分译著、论文、著作和教材四类来选择重要作品,编者们精心为每个作品撰写了提要。具体而言,共举出译著6种,期刊论文一共列举了178篇,著作举出了10种,教材5种。这是多么宝贵的资料!只是阅读这些书目的提要,就可以让读者对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园地及其重要景观获得一些清晰的观感。中国自古有重视编写目录书并撰写提要的传统,最著名的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者不从目录入手,就无法快速进入学问的正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目录学的价值。《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做了大量的目录学工作,裒辑的资料弥足珍贵,如果一个人想要快速了解比较教育这门学科,这本书无疑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读完了某个提要而意犹未尽,可以根据书中给出的书目信息按图索骥找到原作详细阅读。一位研究者也可以从阅读中找到可以“接着说”,或者“进行商榷”或者“质疑”的话题。
库森说:“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这句话用在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历程上,也是适合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和”是哲学,是智慧。《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融百余年比较教育学科研究成果之精华于一书,其必将有益于后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