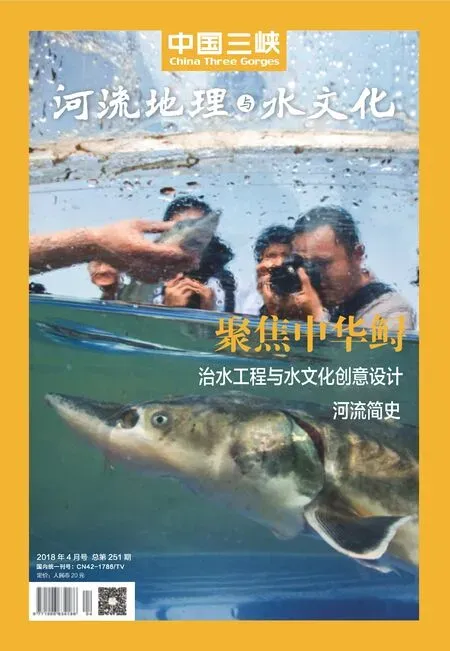剑桥大学的守与变
文 |李海青

《剑桥语丝》(增订本)金耀基 著中华书局2013年9月第1版
《剑桥语丝》以散文形式结集。金耀基先生身在剑桥畅游,从中古世纪一直写到21世纪。剑桥大学扑朔迷离的诞生,名扬海外的学院,令人敬畏的故事,仰观不止的学术自由,在传统时代里的熠熠光景,在科技时代里的转型应对……每一篇章即是剑桥在时间轴上的更迭。
这本书虽是散文集,字里行间却时时荡出学术的思辨。笔底时而沉思,时而浪漫。浓情处以淡笔匀开,思辨处以温情调和,董桥先生敬称之为“金体文”。
金先生本是教育事业中人,接手钱穆先生开创的新亚书院,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施展拳脚。剑桥之游,不是简单的游客观光,而是金先生以内行人之眼捕捉大学精神的机会。如此一来,金先生身处剑大,怎能不联想中国大学?传统与现代在剑桥激荡,又怎能不忧思大学在科技时代的走向?此类问题,《剑桥语丝》一一铺陈,尝试解答。金先生以韦伯所说的“像人一样”去应付时代问题,去思考时代问题,姿态尤低,切点尤深。
剑城是座书城,图书馆、书店像是商品,大街上,琳琅满目。金先生在剑桥有过偶遇,满地的金黄秋叶,华兹华斯描绘的钟声,还有书贾台维爱了剑桥一辈子的故事。英国剑桥大学,一间中古大学,13世纪,神秘浪漫地创立在书城剑城,跌跌撞撞,到了19世纪,她已从传统走向了现代。
剑桥不像一般大学,它是一大群学院的结合,而不是一大群学部的组合。因此,剑大的学院不是研究的场所,而是老少居息一堂的场合。院士终生,以院为家。院士和学生杂处,学人互访。院士言教,也身教,以陶铸学生性情为第一要事。
金先生在文中说:“剑桥把大学教育当做博雅教育,其目的在培养绅士,而不是学者和科学人才。大学的功能在于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创立或推展新知识。”剑桥大学的博雅教育与孔子的言传身教是一致的。言教、身教、心教,是剑桥之特点,也是博雅教育之方式。
19世纪,传统的剑桥是一学问村落,随即规模扩大。许多大学的中心由以人为本,走向以研究为本,到现在的以服务为本。师生之间,人与学术之间,温情痕迹渐淡,陌生之感、像是传染病蔓延扩大。
继而,宗教文化和道德文化在剑桥大学里消隐,人和文的定位驳杂不齐。20世纪的剑桥,也不得不从惰性的人文中,瞧瞧门外的世界。自然科学和人文成为两个文化支柱,对垒的状态僵持不下。但是,金先生漫步剑大之中时,仍旧能感觉到中古时期的博雅传统。剑桥,因着传统的根基,抵挡住了市场经济的淹没势头。正是因为剑桥的保守,而保住了人文的尊严。
然而剑桥并非一成不变,开温第士实验室的成立,科学占据半壁江山。这种变化,不是根除传统的变化,而是移植在传统土壤里的结果。金先生认为:“保守不等于顽固,保守的真义是在其有所保,有所守,保其所应保,守其所应守,并非指一成不变。”剑桥有所变,亦有所保。
中国大学的一系列变化,让金先生对二十一世纪充满忧虑。“21世纪,科学开始要改变我们‘人’本身了,人的定义,人存在的意义都会成为新问题。”人的定位成为问题,文的定位成为问题,大学的定位必然也成为问题。
无论是西方中古的博雅教育,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都是为了陶铸一个完整的人。传统里,有对人的定位,也有对文的定位。天地间的位序,孕育了文明生活。人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文的意义,对生活,对万物,对学术,对历史,也就有了温情和敬意。
守和变,才是一所大学的常态。大学既不应该是隐居的象牙塔,也不应该是卑躬的服务站。金耀基先生认为:“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着,以烛照社会之方向。”在守当中,变才有走向好的可能。没有守,变就没有根基,到最后,可能走向面目全非的境地。
LINKS

《海德堡语丝》(增订本)金耀基 著中华书局2016年1月版
德国海德堡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是一对姊妹城,《剑桥语丝》与《海德堡语丝》便是一对姊妹篇。它们皆以散文的形式结集。《海德堡语丝》延续了《剑桥语丝》的语言风格,亦延续了学术思考与浓郁抒情浃洽的写作风格。金耀基先生说:“这本小书写的不尽是风景,它有对德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所见、所思。”马克斯·韦伯的传说,社会学的发展,歌德的赞誉,皆在海德堡这座历史名城和海德堡大学中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