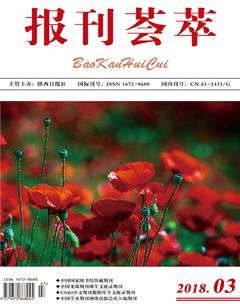抗战时期的师生情感
摘 要:抗战军兴,为保中国高等教育的实力,大批高校陆续西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承继北平师范大学之遗产,定址于甘肃兰州,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在教学和生活的过程中,学院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共同努力,为西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师生情;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民国成立之后,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逐渐传播,亦师亦友的观念更是深入到师生观念之中。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地处西北,抗战建国时期,学生们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始终处于老师、学生构建的社交网络之中。这样的日常生活,既有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师生情感的培养。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家陶行知曾指出:“师生本无一定的高下,教学也无十分的界限;人只知教师教授,学生学习;不晓得有的时候,教师倒从学生那里得好多的教训。”教师要与学生建立平等民主的关系,便要对学生施行“爱的教育”。朱自清在《教育的信仰》中如是写道:“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对学校里的教职员有这样的要求:“学校教职员必须能负责领导学生,举凡思想方面、课业方面、生活方面、精神方面,均能以身作则,以教育家态度教导学生,以最大热忱为学校服务,则学生未有不敦品励行,服膺教诲者。……视学生如子弟,遇有过失,必须负责纠正,绝不可放任纵容,本爱护之热情,立严师之教范,果能如是,则校风自然培植起来。”不仅要老师们对学生的学业负责,还要关注他们的内心思想、日常生活和品格精神。从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对他们有错必纠,身体力行,以教育家的态度来对待学生。
在对待学生的学业上,老师们诲人不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就读的李鼎文先生,在回忆老师的文章中,提及老师对自己学业上的帮助,常常感恩于心:
一天,我读张介侯的《养素堂诗集》,在《忆海藏寺》诗中有“境寂界超心湛冥,木犀香来悟宗旨”两句,不知道出处。后来翻《焦氏类林》,其中有一则说:“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不答。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我以为找到了出处,但这一则却没有注明录自何书。我向丁易先生请教,也不知录自何书。一年以后,丁易先生已到四川,在國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一次给牛维鼎、管家骅几位同学的来信中,提到我曾问过的问题,说是偶阅丁传靖辑的《宋人轶事汇编》,其中有闻木犀香一则,出自宋释晓莹《罗湖野录》。我看信以后,很受感动。先生关心青年、严肃认真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丁易先生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担任讲师,学生在课下向他请教的问题,就算当时不能解答,也依然记在心里。时隔一年,找到答案即为学生答疑解惑,敬业精神令人感动。课余之际,学生也常常写下思念老师的佳句:
送黎师锦熙,调寄破阵子。
山后当堆积雪,门前久赋凋零;夫子文旌西上后,塞外春风蓦地生,木欣欣向荣。有恨频传邮电,催人急切机声! 小子嗷嗷犹待哺,留公无计送公行,惟愿早回程!
师生间的交往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包括课外的情感交流与对话。师生通过共同参与课外活动的形式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情感也在这种对话中自动升温。在国立西北师院教育系学生出外旅行时,鲁岫轩导师提出了自己对师生关系的看法:“导师应具有两种态度,一导师应具有家长态度,训导学生需宽严相济。二导师应具有医生态度,对学生学行须注重诊断与救治。总之,师生彼此应以至诚相待。”鲁岫轩先生身为导师,指出导师应具有家长态度和医生态度。但无论是家长角色,还是医生角色,都流露出对学生的爱与关切。在师生共同参与的外出参观的旅途中,老师与学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1942年春假,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院师生前往宝山参观游览,“见教育系同学,由数学系张主任指导,正作士风舞,笑声四溢,二胡当做乐队,亦一韵事焉。”师生在湑水南岸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勾勒出了一副老师与学生亦师亦友的生动而又温馨的场景。旅游参观是当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经常组织的课外活动,到了假期,学院便派老师带领学生们四处参观,一为陶冶身心,二为了解社会的真实面貌。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师生共赴异地,参观风景,了解风土人情,不进收获了大自然之美,更收获了与老师之间的真挚情感。
为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会自发组织各类游艺会、庆祝会、纪念会等。这些活动从发起到组织,师生们都是踊跃参与。1943年6月20日下午四点钟,学院师生共计五百人,共同参加了“毕业生欢送大会”。下午六点左右,全体师生被安排在教场坝聚餐。“夕阳斜照中”,师生八人一桌共进晚餐,“肆口达嚼,颇饶风趣”,晚餐结束后“尽欢而散”。1940年12月1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体育同乐日的成功举行,也离不开老师与学生的共同参与。体育系主任兼训导主任袁敦礼先生与体育学会的学生们分工合作,终于使“play day”以崭新姿态出现在“抗战时期大西北文化中心的城固”。
在师生交往过程中,彼此感情渐渐加深,更有同学因为由衷敬仰老师的崇高品质,进而产生爱慕之情。老师们传道受业解惑,令学生觉得他们才华横溢,极具人格魅力。不同于青春懵懂期的对异性教师朦胧的崇拜、依恋和爱慕,在感情上,大学生若与老师发生爱恋,则极易“修成正果”。师生恋也是恋爱自由的一种表现,不仅学生们观念大开,很多教职人员的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平等的接纳学生的爱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某一女学生,与体育系教员产生爱情,并最终结成眷侣,得到了全校的祝福与认可。可以看出,当时的婚恋观念是相对开放的,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摒弃了“天地君亲师”的传统师道观念,与老师们建立了平等的恋爱关系,教员们观念也渐渐进步,欣然接受学生们所传达的爱意。
从毕业之际老师为学生写的留念题词、毕业多年后师生间的书信往来,不难见到的,都是浓浓的师生情。毕业时,老师为学生们题字留念,是为了纪念,更是一种关怀与希望。老师对学生之爱,不会因为毕业时的分开而断绝。李鼎文先生在毕业后近三十年,还会与恩师黎锦熙先生来往书信:
1974年夏天,我当时患双眼玻璃体浑浊,心情很坏,曾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先生寄来了一份《八十岁后工作总汇报和展望》的油印本,并对我训勉了一番。先生写道:“盼健康恢复后,工作上少用目力。‘语言,一科,本属‘口耳之学,其‘物质外壳,就是声音,以‘目治者乃其符号(文字)。过去古今考订、方国对应,大都与‘耳治之实际脱离,以致千年以来,漫无定论;八亿民众,尚难统一。目疾虽属病恙,利用有方,‘坏事变成好事,可预料也。”当时先生已臻八十五岁的高龄,用圆珠笔写字已不大方便,但他还没有忘掉我這个多年不见的学生,从万里之外表示关怀,使我深受教育。先生的教育家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在求学时培养出的师生情,并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消失。老师对学生的启发与教诲,并不会停止。真正做到了对学生学业、思想、生活、精神等多方面的关怀,是爱的教育,也是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盼。师生之间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与娱乐,建立了互相信任、尊重、理解的良好师生关系;通过为了国难的东奔西走,共同奋起,组织爱国活动,加深了联系;通过毕业时的留念与毕业后的交流,终成一生挚友,有了无比深厚的情感。师生之间相亲相爱,如兄弟姐妹般亲密无间,学校也就成了学生们无限向往和常常追忆的“极乐之地”。
参考文献:
[1]张新平,陈学军.陶行知的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
[2]浙江省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白马湖文集.上虞:浙江省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第109页.
[3]李蒸.本院的使命与校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创刊号,1942年.
[4]李鼎文.陇上学人文存第3辑李鼎文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5]齐振鹏.词二首.师声,1943年第3期.
[6]孙天泰.教育系二年级旅行霸王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1年第35期.
[7]本院全体师生春假赴宝山旅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2年第41期.
[8]本院师生欢送毕业同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3年第55期.
[9]体育同乐日纪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0年第16期.
[10]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1年第18期.
作者简介:罗瑞琳(1995—),女,汉族,甘肃积石山人,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