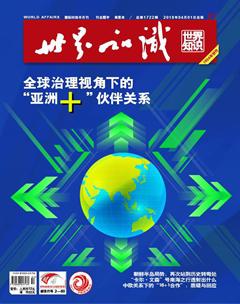“亚洲+”伙伴关系的多维审视
徐秀军

在20世纪末的时候,西方学者就曾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亚洲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的中心逐步向亚洲转移。但更应该注意到的是,21世纪是全球联动发展的世纪。亚洲的发展离不开外部世界,亚洲解决和应对各种问题、矛盾和挑战离不开外部世界的支持和配合。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的,“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在推进亚洲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时,既要强调亚洲的区域属性,更应注重亚洲的开放属性,从而为构建“亚洲+”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伙伴关系
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确实曾多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滑,国际直接投资出现萎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各个地区的外向型经济遭受巨大打击。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质疑。例如,曾任联合国秘书长高级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全球化将可能崩溃,并由此朝着“去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师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认为,过去20年来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开始倒退,随着劳工和资本流动性的下降,未来将出现失落的十年。
但是,经济全球化总体上向前发展的趋势并未发生改变。一方面,国际经贸合作在受到冲击的同时也在孕育新的增长动力。从贸易来看,全球贸易的实际增长率与全球经济增长率之比曾屡创金融危机后的新低。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扣除价格因素后,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较上年仅增长1.3%,并且连续五年低于全球经济的实际增速。进入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全球贸易实际增速有望跃升至3.6%。另一方面,各国政策的传导性和联动性不断加强。相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力要大得多,甚至对一些亚洲国家而言,后者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还要大。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而非相反。目前,一些外部国家内顾倾向严重的经济政策正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同时亚洲各国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也会对相关国家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政策上相互考量的防范与应对,同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突出特征之一。
在全球化时代,对亚洲国家而言,构建“亚洲+”伙伴关系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首先体现在全球经济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更加包容。构建“亚洲+”伙伴关系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从经济上看,“亚洲+”伙伴关系就是秉持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理念,将亚洲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成开放的区域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系。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到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都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亚洲经济发展道路,必须将亚洲与世界对接起来,最大限度地汇聚各国力量和各种资源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并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政治多极化与“亚洲+”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政治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早期多极化格局,主要表现为所谓的“一超多强”的局面。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发展,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符合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基础是多种力量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它有利于遏制美国建立单极世界,并因此大大压缩了全球霸权政治的空间;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弱,以及俄、欧、日实力的变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进程加速推进。一方面,在不考虑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等突发性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将继续发生深刻调整,并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作为全球首要大国,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模式也将发生深刻调整。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无论是现在的“一超”和“多强”,都不可能仅靠自身力量或者联合少数几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好全球面临的经济挑战和此起彼伏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很多领域将更加倚重其他国家的支持。即便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它与亚洲国家的联系也不会因为自身的强大而减少,相反,将与亚洲在世界政治中地位的整体提升紧密相连。同样,亚洲的强大也不可能割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多极化时代,对亚洲国家而言,构建“亚洲+”伙伴关系顺应了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发展推动了国际关系模式的转换,从而为国家之间频繁的互动关系创造了新的机会。倡导和践行“亚洲+”伙伴关系是政治多极化时代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一种尝试。亚洲的崛起意味着亚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更多利益,与外部世界的利益攸关度大幅提升,这就更离不开来自外部世界的支持。在实践上,包含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域外国家在内的东亚峰会等“东盟+”的高层对话模式,为政治领域的“亚洲+”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安全复杂化与“亚洲+”伙伴关系
在国际事务中,安全问题往往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发展等领域的矛盾复杂交织,从而呈现网络化特征。国际安全的复杂化首先体现为安全问题的联动性和扩散性。一方面,个别国家国内社会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以及个别地区的紧张局势往往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形势带來重大影响。一些文化、宗教、民族、性别等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本身就拥有跨国性甚至全球性特征,部分国家和地区因此而产生的动荡往往会激化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相关问题上的矛盾。另一方面,安全威胁的多元化使得国际安全更加综合和多样。除了以军事冲突为代表的传统安全威胁,金融、生态环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与蔓延让全球面临共同的威胁,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不顾外部安全而获得自身的安全。
与此同时,国际安全的复杂化还体现为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让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安全深度融合。网络空间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外空之外的第五空间。当前,全球的数据传播与共享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全球范围内数据和信息的快速流动也为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在网络空间,每一个用户和每一个终端都可以利用网络存在的漏洞和安全缺陷对全球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发起本地和远程攻击。因此,对世界各国来说,维护网络安全需要加强合作,并在相互学习、相互切磋、联合攻关、互利共赢中探索应对之策。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新形势下,对亚洲国家来说,构建“亚洲+”伙伴关系契合安全复杂化的时代需求。当前,亚洲地区在展现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同时,安全风险与挑战也日益增多。例如,亚洲地区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朝核问题、有针对性的军事结盟等传统安全挑战,也存在恐怖主义威胁、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水资源安全等跨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这些安全风险与挑战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通力合作。为此,亚洲国家需要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作为亚洲地区有关安全问题的多边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就安全问题展开对话时,已将乌克兰、美国以及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列为观察员;旨在促进亚洲地区安全与发展的亚洲安全大会(或称“香格里拉对话”)更是以其包容性、灵活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实效性的特征,为亚洲国家与欧美等地区国家对话搭建了平台。
文明多样性与“亚洲+”伙伴关系
当今世界是一个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世界,也是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创造的世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促进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积极因素。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指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尽管这种将文明的冲突作为理解人类社会行为首要因素的论调曾广受追捧,但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并未为其提供有力支持。相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鉴日益频繁,并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为包容才有生命力,文明多样性正在激发亚洲发展新活力。亚洲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地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亚洲地区曾拥有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但是,这些古代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失了,有的融入了其他文明,而中華文明没有中断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包容性。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曾有人将西方文明作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范本,鼓吹全盘西化。但拥有自身文明特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均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印度、印尼等拥有不同文明的亚洲国家也正走在现代化进程之中。
在多样化的世界中,构建“亚洲+”伙伴关系呼应文明多样性的社会现实。亚洲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明存在差异,但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理念和追求,都拥有值得彼此借鉴和吸收之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倡导以文明对话为基础的“亚洲+”伙伴关系,就可以凝聚共识和增进了解、化解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和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