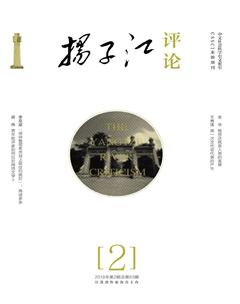论网络文学的两副面孔及内在会通
韩模永
网络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在当下都备受关注,但关于它的概念形态、学理定位甚至命名方式等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甚至说网络文学内部也包含着诸多不同的文学形态,因此,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网络文学将会带来诸多误导性的结论。宏观看来,当下网络文学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网络原创文学”,就是在网络上首发的、原创的、以纯文字为主的作品,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网络文学,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野蛮生长”,极具大众性和商业色彩;二是“数字文学”,或者称之为“ 电子文学”、“数位文学”等,指的是包含“非平面印刷”成分、只可在数字化环境下存在的文学,学界有时所指称的网络文学事实上说的正是数字文学,它与网络原创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类作品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较为常见,富于媒介性和先锋性的特点。因此,要准确地辨析网络文学,一方面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两种形态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它们存在于相同的网络媒介之下,其内在的会通之处。
一、两副面孔
(一)“类型文”
在具体形态上,网络原创文学和数字文学呈现出两副不同的面孔,前者主要表现为“类型文”,后者则为“新文类”。无可置疑,网络原创文学在当下中国是网络文学中的主流,其创作的速度和数量都异常惊人,作品的商业化转换也相当火爆,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因此,网络原创文学本身便携带了商业色彩,具备文学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属性。从商业性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其生产机制正是类型化的,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那种“似曾相识”却又能不断挑起我们某种求知欲的新鲜感,恰好切合了大众的观感和需要,虽充斥着近似的“机械复制”,却又能让人乐此不疲。考察网络原创文学的创作实际,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重要变化,即淡化了传统文学对艺术个性的追求,而走向一种类型化创作,成为一种“类型文”。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十几年以来,产生的‘类型文的丰富性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既有从西方舶来的,如奇幻、侦探、悬疑、言情,又有从中国古典小说继承的,如玄幻、武侠、修仙、官场,还有在‘拿来‘继承后发扬光大的‘耽美‘穿越等,更有网络原创的‘盗墓‘宅斗/宫斗‘练级等”a。与“类型文”一脉相承的是网络原创文学的商业色彩极其浓厚,商业化倾向明显,尤其在当下,网络文学的影视剧改编浪潮正风起云涌,吸引了诸多资本的注意和投入,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热潮,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何不笙箫默》 《花千骨》 《琅琊榜》 《芈月传》 《微微一笑很倾城》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其主要原因正在于“网络文学类型丰富,其新颖独特的叙事形式、贴近现实的叙事内容,庞大的读者群等特点,都是影视剧传播所需要的”b。与此相应,网络文学也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市场格局,囊括了“17K小说网”“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等运营平台的阅文集团是其中的“一超”,“多强”则包括“阿里文学”“百度文学”“掌阅文学”等,其跨界运营模式也日益成熟,产业联动助力网络文学IP变现c。毫无疑问,这种商业化和产业化与“类型文”的生产机制正有着内在的关联。
与这种商业化相呼应,“类型文”还具有突出的通俗性和娱乐色彩。有诸多论者认为网络“类型文”(主要是网络类型小说)正是当下中国通俗文学的代表,“20世纪以来,幻剑书盟、起点、17K、晋江、天涯、红袖添香等网站以青春、都市、武侠、玄幻、军事、历史、同人、耽美、悬疑、职场、盜墓、穿越等类型化的小说形成了火爆的阅读市场,通俗文学的态势开始形成……如果把网络文学放在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上看,可以说,网络小说是中国当代的通俗文学,网络小说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成就,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的前景别有一番天地”d。其通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受众群体的广泛性。据今年8月刚刚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3.53亿,较去年底增加1936万,占网民总体的46.9%,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3.27亿,较去年底增加2291万,占手机网民的45.1%。逐步推进的生态化和崭露头角的国际化是网络文学行业2017年上半年的两大主要发展特征e。可见,网络文学用户的规模是极其巨大和惊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其二是文学表达的口语化。这也是网络“类型文”的突出特点,使用何种文学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文学的存在状态,与经典文学不同,“类型文”抛弃了严肃的雅化传统,走向一种口语化、大众化的表达。其注重日常话语的使用,语言往往简短直白,时尚化、符号化、随意性的现象亦屡见不鲜。网络文学也经常使用对白性的语言来建构情节,显示了一种生活化的特点。“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网络文学语言成了口语词汇占很大比重,速食化特色非常浓厚的语言形式”f。其三是故事讲述的娱乐性。娱乐性是通俗文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特征,尤其在当下随着商业资本的过度介入,网络文学的娱乐色彩成了大多数网络文化娱乐集团追求的主要目标,其背后则是商业利润的追逐和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文学一改传统的精英文学传统,其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网络文学研究专家邵燕君将其精准地概括为“爽文学观”g,这种“爽”就包含了极度的、甚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娱乐特点,当然,如何把娱乐与品质更好地结合起来则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当务之急。
(二)“新文类”
网络文学的另一副面孔即“新文类”,数字文学强调数字媒介的参与和融入,很难在纸质媒介中存在和呈现,这种媒介的特异性导致数字文学发生了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变化,产生了形态多样的“新文类”。当下,学界关于对网络文学的诸多讨论,事实上其对象是“新文类”,而非网络原创“类型文”。从创作的区域来说,这种“新文类”在一些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较为常见,而在中国大陆则以“类型文”为主要形态。“新文类”之“新”倒不是强调其出现时间的先后,而是指相对于传统的纸质文学,“新文类”所发生的新变化。首先,在具体形态上,“新文类”包括诸多新的文学样式,如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动画诗、互动文本、接龙小说、链接体、多媒体文学、机器作品等。其次,在媒介表现上,“新文类”作品不再是纯文字的表现,而是整合了文字、图形、动画、声音、超链接于一体的文本。这种“新文类”的特异性在于数字媒介技术在创作中的真正参与,数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一种表现媒介,它充当了与文字一样的表现功能,此时的媒介是一种作为文字的媒介。从形式创新的角度来看,“新文类”包含三个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核心形式元素,即链接、节点与网络,它们体现出一种媒介的特异性和创新性。这种特异性又不仅仅是单纯的、“物性”的媒介技术论,它与“文学性”紧密相联,携带着强烈的美学意味,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最后,在美学特点上,与这种媒介特异性密切相关,“新文类”也呈现出先锋性和实验性的色彩,这与“类型文”是截然不同的。正如有论者所言,“21世纪的中国网络文学已大体放弃了其实验性、前卫性,而走上商业化、大众化、产业化的道路”h。也就是说,与“类型文”的商业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相比,“新文类”具有先锋性和实验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这种先锋性首先表现在“新文类”对文本结构的变迁,即从传统的线性走向非线性,传统的文本是一种以时间为序的线性结构形式,即为莱辛所言的时间艺术,善于表现在时间中承续的事物。而“新文类”尤其是超文本小说、多向诗、链接体等,由于链接融入到作品之中,文本以一种非线性的形式呈现,成为“无页码的书”,此时的文本成了一种共时的空间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文類”又带有了空间艺术的特点。第二,“新文类”凸显了视觉时代图像与文本的融合关系,具有多媒体性。应该说,传统文本也存在图像与语言互文使用的情况,但图像多为文字的丰富和补充,且由于纸质媒介的限制,只能是静态的,“似动非动”是其极限。同时,传统文本也无法传达声音,只能暗示某种音乐性。而在“新文类”中,一方面,文字本身被图像化,如在文字动画诗中,文字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艺术面貌和动态效果,共同生发作品的主题和意蕴;另一方面,作品中的图像真正成为作品的一个部分。而且“新文类”是真正意义的多媒体,除了图像之外,还有声音、动画、影像等成份的融入,是“文学的演出”。最后,“新文类”的先锋性还表现在作品具有交互性的特点,这也是数字媒介本身的独特性之所在。这种交互性在接龙小说、链接作品等文本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巴特所言的“作者之死”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读者的权力被无限扩张,成为一种新型的读者——“写读者”。当然,无论互动性的程度如何,读者最终还要受制于作者创造的文本,完全抹煞作者的权力既不客观也不可能。
二、内在会通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类型文”和“新文类”虽共属于网络文学这一概念之下,但其现状、面貌及特征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变成了不同的文学形式。但毕竟其承载的媒介具有一致性,因此深度地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在诸多层面上又有着内在的会通之处。具体来说,在深层根源上,“类型文”和“新文类”虽带有后现代的表象,但实则是传统的一种延续;在核心特征上,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网络性;在话语表达上,它们则均表现出反书面语的特点。
(一)深层根源:传统的延续
网络文学“类型文”诞生在网络媒介产生之后,因此,其天然地携带了网络媒介的种种特点,诸如碎片化、平面化、快餐化等等,其语言表达也具有后现代的一些特征,解构和娱乐色彩充斥在作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类型文”具有后现代性也并不为过。但究其本质,事实上“类型文”正是传统通俗文学在新的媒介语境下产生的新形态和新样式,与通俗文学一脉相承,或者说它正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部分和发展阶段。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学正是继中国古代、现当代通俗文学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虽出现的时代不同,但其具备的基本特质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国通俗文学是类型化、模式化的文本,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类型与模式是中国通俗文学在创作流行过程中积淀下来的、被读者大众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美学表现方式,否定了类型和模式也就否定了通俗文学的存在。大众性、商业性和类型模式是中国通俗文学性质的三足鼎,它们构成了中国通俗文学批评标准原则性的基本要素”i。显然,网络文学“类型文”正具备这样的“三足鼎”,因此,“类型文”虽表面上似乎很后现代,而深层根源上仍然是传统的一种延续。
“新文类”与中国传统也不无关联之处,要反对目前研究中那种把其与后现代文学理论过度嫁接的倾向,在本质上说,“新文类”具有内在的自然性,也是传统的一种延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文类”的非线性正是人的非线性思维的一种自然表现,非线性思维是人最本质、最原始的一种思维形式,具有自然性,并不是反叛线性的结果,线性和非线性在思维结构上说是并行不悖的。只不过,在纸质媒体时代,这种非线性难以呈现而已。而到了网络时代,链接的非线性恰巧适应了人的非线性思维模式,从而“新文类”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刻意反叛传统文本线性结构的结果,而是技术变革之后的自然变迁和延续,这与后现代的解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有论者在谈及亚瑟斯超文本美学观念的时候提到,亚瑟斯认为把超文本与后现代文学理论联系起来的策略和方法“对于理解这个领域起了诸多误导的作用”j,考察“新文类”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点确实有其合理性。其次,“新文类”的多媒体性实则是中国传统“出位之思”理论和实践的复现。所谓“出位之思”指的是一种媒体欲超越其本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体的表现状态,钱锺书将其称之为“出位之思”。应该说,这种“出位之思”的观念和实践在中西方均古已有之,如关于诗画统一的讨论等等,“新文类”的多媒体性事实上也正是在新媒介语境下诞生的一种新型的“出位之思”,本质上正是传统的一种延续,当然,这种延续并不是原搬照抄,而是出现了新特点和新变化。
(二)核心特征:网络性
显而易见,无论是“类型文”还是“新文类”都有一个共同的存在前提,即诞生在网络媒介产生之后,网络媒介不仅仅是两者发表的平台,更是生产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介参与了两者的创作过程,成为创作和表达的一个部分,离开网络,网络文学的独特性就无从谈起。因此,作为网络文学的两副面孔,“类型文”和“新文类”虽在呈现面貌、具体特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在核心特征上,它们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网络性。
网络性主要是从媒介的角度来考察和理解的,媒介维度的变化导致文学的相应变化,故而有不少学者倡导“媒介文艺学”的建设并展开讨论k,其要点就是从媒介的角度来研究文艺现象,这种看法应该说切中网络文学的实际。相对于传统的纸质文学,网络性正是“类型文”和“新文类”的独特所在,这种网络性表现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性表现为一种超文本性。“新文类”的超文本性自不待言,尤其是超文本文学,其结构本身就是超文本,这种超文本性是文本观念在媒介革命之后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读者的权力被推向极致,非线性、碎片化更易呈现,读者重组作品的自由无限扩大。当然,这个自由还是要受制于作者的创造和设计。“类型文”同样具有超文本性,只不过,其表现为一种“网站属性”,“每个网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超文本。如果说‘作品意味着一个向往中心的向心力,‘超文本则意味着一种离心的倾向。我们可以说‘作品的时代是一个作者中心、精英统治的时代,‘超文本的时代是一个读者中心、草根狂欢的时代”l。其二,网络性也表现为一种充分的互动性。应该说,互动性是网络媒介不同于传统媒介最为独特的特征所在,传统媒介虽也有互动的一面,但其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是极其有限的,网络媒介的互动性是自然充分的、甚至是即时同步的。“类型文”与“新文类”在这一点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新文类”中的互动文本自然如此,超文本作品的链接选择本身也是一种互动,也就是说,在“新文类”中,读者往往会参与到作品写作和建构的进程之中,作品变成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创造。在“类型文”中,这种读者直接参与写作进程的形式倒并不常见,但作者创造多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在线写作”,读者的跟帖也变成了一种即时的“在线批评”,由于这种跟帖多同步地发生在作品创作的进程之中,因此,很可能及时影响和改变作者对作品的建构和写作,作者的“读者意识”增强了,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变成了一种即时的、双向的对话式交流。显然,这与传统时代那种单向的、作品完成之后的“延时批评”是截然不同的。其三,网络性还表现为一种媒介技术性。技术性是“类型文”和“新文类”的突出特征,如果离开网络这种媒介技术,网络文学“类型文”就不可能产生,它正是在技术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是艺术和技术的融合,“一方面,网络文学需要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正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低成本、无限连接等功能,才使得众多作者能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也得益于移动终端设备的技术发展”m。而“新文类”对技术的依赖则更加紧密,如文本的链接设计、程序控制、动画效果等无一不需要技术的参与,因此“新文类”的创作者往往是“集体作者”,除了文字的表达之外,还需要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设计,是团队集体协作的结果。
(三)话语表达:反书面语
与传统的纸质文学相比,“类型文”和“新文类”也都必不可免地受到网络语言的潜在影响,在话语表达上,均明显地表现出反书面语的特点。只不过,两者反书面语的方式有所不同,在“类型文”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类型文”以娱乐化、草稿化解构书面语的经典化。“类型文”与传统的经典文学相比,不再重视故事背后的理性沉思、艺术追求和经典性建构,其核心追求便是娱乐性的故事,甚至是完全脱离现实和历史真实的构思,是“反重力”的另类表达;与经典文学发表前的反复推敲和打磨不同,“类型文”因日更的现实需求,常常体现出一种草稿化的气质,“由于网络文学特殊的生产机制——文本创作与发表的即时性——使得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网络小说是一部作品的草稿”n。显然,这种草稿化与经典文学的追求是截然不同的。其二,“类型文”以繁琐性、日常性解构书面语的含蓄性。传统的书面语尤其注重语言的简洁性和含蓄性,从道家的“无言之美”开始,这种含蓄性便逐渐演变为中国的艺术精神,追求含蓄、空白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至高追求。而在“类型文”中,这种含蓄性遭到了解构,因日更、“在线写作”的创造形式,网络作家往往重视情节的建构,尤其是故事悬念的设计,如《斗破苍穹》 《回到明朝当王爷》等都有这样的特点,而对写作的语言则不加重视,甚至极其繁琐和粗糙,日常性的对话经常出现在作品之中,这也是网络文学“类型文”多为长篇巨制的主要原因,在篇幅结构上亦表现出与传统文学含蓄性不同的面貌。其三,“类型文”的话语表达也带有视觉化的倾向。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少数先锋性的作品之外,文字表达一统天下,但在“类型文”中也可经常看到各种符号性的文字,如数字、拼音、象形图、脸谱符号、表情符号等,视觉化色彩明显增强。在当下盛行的“类型文”中,其视觉化、画面感则更加突出,诸多网络作家在创作时都有强烈的改编影视的动机,因此他们在创作时便有意识地刻画文字背后的影像,把画面推向文字的前台,虽然这种视觉画面如传统文学一样也是脑海中的想象,但其表现则更加具体和逼真,从文字到画面可以实现自然流畅的转换,视觉化、剧本化倾向明显。
“新文类”在反书面语上则以另外一种姿态来表现,即用视觉语言颠覆传统的文字语言,如果说“类型文”还是一种视觉化倾向的话,那么“新文类”则是标准的视觉语言,这种视觉语言多以三种形式出现在文本之中,其一是文字本身的造景,也就是通过文字的造型设计、色彩处理、动态效果等实现、增强视觉效果,不再是传统的单调的“黑字”。如台湾歧路花网站中的诗作,文字往往是动态的、视觉感强烈的。其二是文字背景的影像化,其背景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白纸”,背景影像化,变成了多媒体的布局,文字在多媒体的影像中展开,如同文字的表演。诗人毛翰的数字诗集《天籁如斯》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文字在美轮美奂的画面和动听的背景声音中呈现,极易将读者拉入诗歌的境界之中,产生沉浸性体验。其三是文本的多媒体性,这是“新文类”话语表达的典型形态。文字不再是文本的唯一表现媒介,图像、声音、动画甚至影像都成了文本的一个部分,与文字一起参与着文本的叙事和讲述。同时,这些视觉语言不同于传统的文本插图,后者往往与文字之间是相互印证、补充的关系,具有独立性,也就是说离开了插图,文字的意义也可独立存在,文本仍保持着完整性。而“新文类”的视觉语言则是作为文字的视觉表达,文字与视觉语言一起共同生发文本的意义,离开了视觉语言,文本将不再完整。这也深层次地改变了传统文学以单一的书面语来表达情感和意义的惯例,变成一种文字和视觉语言相互融合的话语形式。当然,其中的文字仍然是主导的,反之则通向艺术。
【注释】
①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b胡友峰:《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消费”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
c歐阳友权:《多元竞合下的变局与走向: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巡礼》,《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
d周志雄:《通俗文学版图中的网络小说》,《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
e《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708/t20170804_69449.htm
f陈定家:《试论新媒介文化的批评标准与叙事逻辑》,《中州学刊》2017年第3期。
g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h崔宰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年,第13-14页。
i汤哲声:《不变与变: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的原则性和适应性及其思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j聂春华:《艾斯本亚瑟斯超文本美学思想探析》,《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
k详见“专题:媒介文艺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
l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m王传领:《论“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下网络文学的特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n石娟:《草稿化与媒介转移:网络小说性质及经典化路径之探讨》,《小说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