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俨然一块纯美的水晶
姚全兴
俞平伯说它“俨然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就是《浮生六记》。它是清朝苏州人沈复(字三白,1763~1825)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笔记。“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然而,沈复并不将浮生看作一场春梦,放浪形骸、玩物丧志地及时行乐,而是将寻常平民生活过得既有情调又有意味。林语堂在此书汉译英的序中,也指出书中所述夫妇生活的特点是“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这是沈复做人的高明,这本笔记的价值。
童趣解析
《浮生六记》被有心人杨引传从地摊上发现时,已是残本,只存四记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但就是这残本,也足以显示此书不同凡响。
一个人高明不高明,和个性很有关系,和个性中的趣味性更有关系。沈复此人的个性,在于从小就有浓浓的趣味。在封建社会大行科举考试的时代,一个人没有被唯有读书高的风气扼杀,对大千世界事物趣味十足,是很不容易的。沈复童年时期的童趣,使他成为一生趣味性浓郁的人。他在“闲情记趣”说“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这并不是说他果真有明察秋毫的眼睛,而是说他好奇心童趣的流露,使他对藐小之物观察入微。
喜欢沈复文章的人,往往赞赏这样一段话:“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有人不以为然,把令人发怵的“夏蚊成雷”,看作“青云白鹤”,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其实,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即个体依据其需要、情绪的主观指向,将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事物的现象。因此,并不是真的喜欢嗜血成性的蚊子,只是把蚊子想象成自己喜欢的白鹤而已,而这真是童心中趣味性的流露,可以看作化腐朽为神奇的特例。
同样,文章中说“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又说“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也是心理学上的移情作用,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转移到事物上造成的现象。但童年心理的投射效应和移情作用,比成年心理更为突出和强烈,这是它的年龄心理特殊性决定的,值得重视和珍惜,应该尽可能保持下去,可以对儿童的身心发育和人生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世上太多没趣的正人君子,而沈复是一个有趣的人,怪不得有趣的人能够写出有趣的书。
梁启超当年大力提倡趣味教育,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人教版的语文书,曾经将沈复描写的上述童年故事,以《童趣》为题选入,可以说是高度的评价。
散淡的人
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沈复本是清代乾隆至嘉庆期间的小商人,名不见经传,能够写出有趣的书,还在于他将童趣童心日后发酵开来,成为一个审美的智者,有了发现美的眼睛。
当然,这也和他在人格上是一个散淡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散淡的人是潇洒的人,达观的人,优雅的人,因为散淡是一种融合文化底蕴和心胸开阔的人性。一个人散淡了,就能将平淡的生活过得不平淡,在他眼中,天涯何处无芳草?也正是散淡的人,能够将他夫妇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写得清澈而细致。俞平伯说《浮生六记》是一块纯美的水晶,明莹而精微,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散淡的人,心无杂念、襟怀坦白,美的发现必然敏锐、洞察、睿智,应用于实际生活。沈复就是如此。他说,“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虚实相生是古典美学方法,沈复深中肯綮,说明他的散淡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绝不是胸无点墨的凡夫俗子。再加上他在文字方面特有灵性和天分,随心所欲地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淋漓尽致地娓娓道来,一一形诸笔下,难怪是脍炙人口的美文。
一个散淡的人,美的发现必有独特之处。沈复说“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在他看来。扬州园林虽好,但他只看好“九峰园另在南门幽静处,别饶天趣,余以为诸园之冠。”天趣,是他品评园林山水的第一标准。因此,绍兴的吼山为当地名胜,然而“有柱石平其顶而上加大石者,凿痕犹在,一无可取。”同样, 杭州西湖的“湖心亭,六一泉诸景,各有妙处,不能尽述,然皆不脱脂粉气,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雅近天然。”天趣、天然与世俗相悖,从而“黄鹤楼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原来,他之所以尊崇天趣天然,根本原因它们是功名利禄的克星。沈复是苏州人,却对苏州园林山水没有偏爱,而多有微词,说“吾苏虎丘之胜,余取后山之千顷云一处,次则剑池而已,余皆半借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即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桥,不过留雅名耳。其冶坊滨,余戏改为野芳滨,更不过脂乡粉队,徒形其妖冶而已。”而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且石质玲珑,中多古木,然以大势观之,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灾,全无山林气势。以余管窥所及,不知其妙。”至于灵岩山,他也认为“其势散漫,旷无收束,”不及天平山“别饶幽趣”。
是的,散淡的人总是回避庸俗,拒绝庸俗,把天趣天然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
伉俪情深
谈到《浮生六记》,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其中描绘的至诚至爱的伉俪情深。不错,此书正是以和谐的夫妇生活为主线内容的。沈复的妻子芸娘“两齿微露似非佳相”,然而夫妇“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其深层次的原因,芸娘不但有“一种缠绵之态”的女性美,更有非同一般的可贵品性。
其一是志趣相投,芸娘和丈夫有共同的语言。芸娘颇有传统文化知识,对“破书残画反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缺处,倩予全好而卷之,名曰‘弃余集赏’”;“于破笥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她还能够和丈夫评诗论文,说“格律严谨,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故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她对田园生活也很钟情,有一年她与丈夫到苏州郊外菜园避暑,面对一派农家气象,喜不自胜地对丈夫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沈复说当时“余深然之”,又伤感地说“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芸娘喜爱书画诗文,符合丈夫兴趣,夫妇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有利于营造淡泊而雅致的文化氛围,生活艺术化是过好家庭生活的重要因素。芸娘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和丈夫品性相似,内心叛逆礼教,对功名利禄冷淡,丈夫弃儒从商,乐于跟随,还一起种植瓜蔬,表明夫妇都崇尚自然,安于平民生活。而这正契合丈夫的心意,如同林语堂说的那样:“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恬淡自适和知足常乐的天性。”芸娘和丈夫情投意合,彼此欣赏,正如芸娘临终前对丈夫所说“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深情缱绻,莫此为甚!
其二是惺惺相惜,芸娘有丈夫喜欢的个性。芸娘与丈夫同行同坐,卿卿我我,众人面前毫不顾忌,必然遭到家庭上下非议。又如芸娘给丈夫的信中称公公为“老人”,称婆婆为“令堂”,率性随便,有悖礼仪,必然得罪家长。以家长和传统的眼光来看,沈复不思上进,芸娘不守闺训。不仅如此,芸娘女扮男装与沈复同游水仙庙,“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还有一次,沈复夫妇瞒着家长偕游太湖,泊舟于万年桥下,芸娘与船家女素云行酒讴歌,在当时近狭邪之行,无怪乎朋友以为沈复“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夫妇随心所欲,即便后来陷入苦难,芸娘依然拔钗沽酒,不动声色,意趣盎然。林语堂说的“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即此谓也。
这其二值得一议。芸娘为什么有这样的个性,沈复又为什么欣赏她的个性?芸娘看来娴淑,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娴淑,她的言行已有个性解放、反抗礼法的因素。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他又说,“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为什么能够违背“礼法顾忌”而成为“例外创作”?遗憾的是,过去论者没有揭橥其根本缘由。这里只指出一点,“闺房记乐”的人和事,已有不容忽视的世风流变印记。沈复夫妇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江南苏州等地的商业经济文化在欧风东渐的背景下,城市文化生活开始移风易俗,渗透家庭,影响青年男女。尤其沈复夫妇生活在小商人家庭,更对他们的思想感情潜移默化,必然对封建传统文化习俗有所不满,导致他们个性解放、反抗礼法意识的萌芽。芸娘言行举止和传统娴淑有所背离,正合小商人沈复的心意;而小商人沈复的认可和欣赏,又促使芸娘的娴淑走向反传统习俗。而这正是俞平伯、林语堂等新式文人,激赏沈复夫妇带有时代色彩的伉俪情深的原因。林语堂深情地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言辞不免过誉,但对新女性芸娘的敬仰和赞美之心,可以想见。这也是《浮生六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真正发现和风行一时的重要原因。
然而沈复夫妇的日子过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坎坷记愁”一记记录了他们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的忧患岁月,其中经历了家庭不容、寄人篱下、贫病交困等不幸遭际,甚至芸娘至死不肯就医,弥留时惟“愿君另续德容兼备者”。尽管如此,沈复的生动而精致的笔墨,还是将芸芸众生中很多人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滚滚红尘中更多的人认为夫妇生活就是油盐酱醋的看法,彻底的颠覆了。《浮生六记》将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夫妇生活,细腻而率真地和盘托出,怎么不使人看了怦然心动,悠然思绪呢?
当然,《浮生六记》也记录了现实中的丑陋,例如芸娘不顾舆论,想方设法为丈夫纳个美妾,甚至结盟妓女称为姊妹,结果妓女贪财,嫁了富人,为此十分伤心。但这固然反映了时代局限性,却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不仅体现了芸娘在妇女问题上的平等意识,还彰显了笔记反映社会现状的真实性,而真实性正是笔记的重要特征和价值所在。今人不必要求古人尽善尽美,更何况今人的所作所为就尽善尽美了吗?
两个亮点
其一,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得到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赞赏,认为人的生活要有诗意。这实际上是指出过分的物质追求会使人的生活失去诗意,从而陷入苦闷。避免这种苦闷的唯一途径,就是人必须有诗意的人文情怀,必须在生活中诗意地栖居。从美学角度看,审美是生命的载体和流动,做到诗意地栖居,需要有审美的生命的态度。《浮生六记》描绘的生活,之所以值得称道,在于沈复夫妇有审美的生命的态度,真正做到了诗意地栖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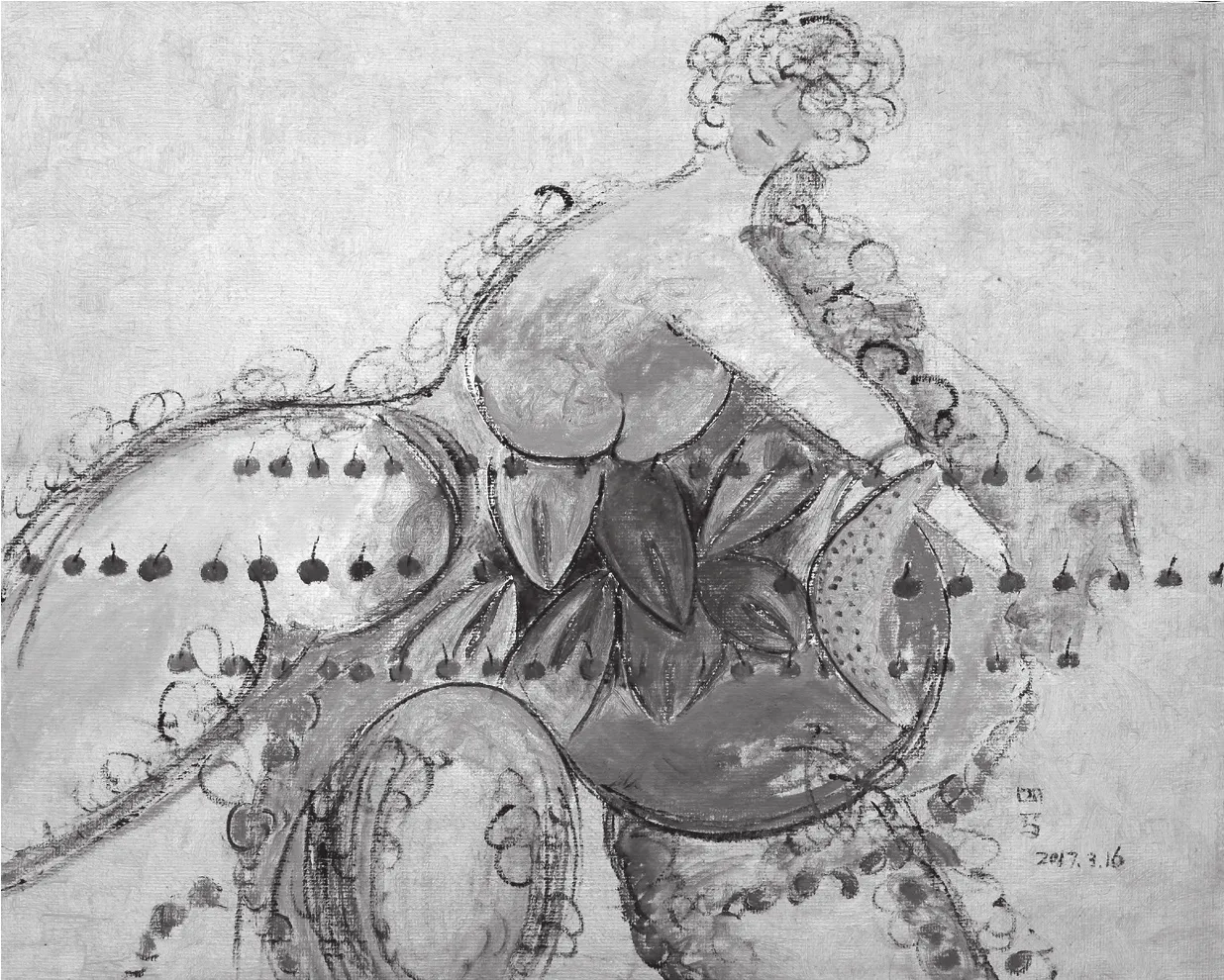
张红兵 布面油画 作品八
其二,《浮生六记》是雅俗共赏的奇葩,奇就奇在它是古代屈指可数的平民生活纪实美文。归有光、张岱、袁枚等明清散文名家也不在少数,但像沈复那样把家常琐事写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多乎哉不多也。有得一比的是同时代的李渔,他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闲情偶寄》也写得颇有趣味,然而此书关于生活方式的笔墨趣则趣矣,但由于涉及面广,文学的艺术含量略逊一筹,终究算不上笔记中的尤物。而薄薄一册的《浮生六记》,名副其实是笔记中的尤物,至今越读越有味道,其中的至情至理,还是令人心旌摇摇,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