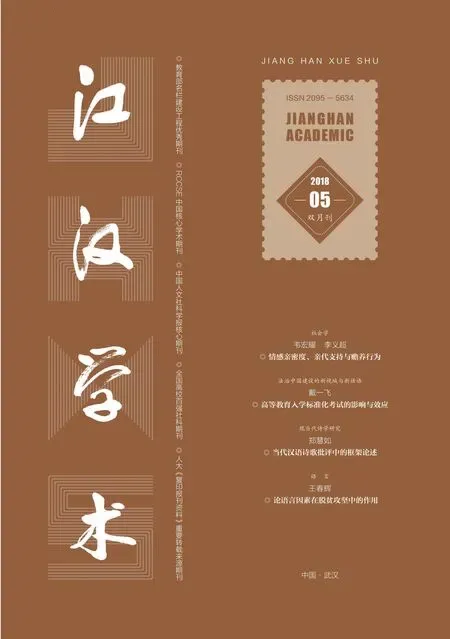纪弦(路易士)与香港诗坛关系考论
刘 奎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1948年底,纪弦从上海赴台,先借《自立晚报》办《新诗》周刊,后创办《现代诗》,组建现代派,发起“新诗再革命”运动,成为台湾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也对现代主义诗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与发扬起到了关键作用,《创世纪》的洛夫也承认,纪弦对于“开一新纪元的中国新诗的大功臣”这一说法“当之无愧”[1]。除了对台湾诗坛的影响外,他在香港现代主义诗歌圈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在1950年代的台、港文坛互动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学界不少论著都已涉及这个问题①。本文将进一步追溯港台现代主义交往的前史,梳理纪弦与香港诗坛的历史渊源,也对他在1950年代台港诗歌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略作回顾。
一、渊源:“我一直到现在都对香港有好感”
纪弦与香港颇有渊源。纪弦原名路逾,1945年前以路易士为笔名;他1913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正值辛亥革命后第二年,袁世凯任大总统之后,宋教仁遇刺,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运动。因其父是军人,这些历史事件与年幼的纪弦也发生了具体关联,尚在襁褓中的他便被带着从天津南下,经上海、香港转海防,到云南。此后,在动荡的时代,年幼的纪弦也常随其父辗转各地,其间就多次驻留香港。他十岁前后在香港和广州生活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还曾在香港的教会学堂读书。这段经历后来被他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对他人生观和诗歌写作也有深远影响,在其1945年出版的《三十前集》中,他曾回味这些经历。不过在他的回忆中,对香港的教会学校印象并不好,认为香港的教会学堂并不适合他,“太不高兴那些宗教上的形式了”,反而是香港周边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海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正如他所回忆的:
只有海,给我以繁多的梦幻的喜悦。在香港,我受的是海的教育,海教育了我。海捏塑了我的性格,海启发了我的智慧。海是我的襁褓时代的保姆,海是我的幼少年时代的先生。我懂得海,海和我有夙缘。我常在九龙半岛的沙滩上掘砂泥,拾贝壳,眺望绿色的海和它的魅人的地平线。我留恋它的明丽,寂寞和神秘。我想我一直到现在都对香港有好感,也许便是为此之故。[2]
与海有夙缘,联系到他后来赴台的经历,这倒似乎有点一语成谶的意味。不过海洋确实成了他此后诗中时见的主题,像《海的意志》《舷边吟》《花莲港狂想曲》等均是,而且他笔下的海洋,呈现出的也多是寂寞与温柔的形象,如《舷边吟》:“说着永远的故事的浪的皓齿。/青青的海的无邪的梦。/遥远的地平线上,/寂寞得没有一个岛屿之漂浮。”[3]与海洋诗歌中习见的狂暴或浩瀚的海洋形象不同,即便是花莲港狂暴的浪涛,在他笔下也似乎变得格外温柔:“而且,我将搂着你底腰肢婆娑起舞,/踏着华尔兹轻快的旋律,波浪似地起伏,/在那微笑着的,辽阔的,青青的大海原”[4];诗人与海洋之间的情感关系较为和谐,诗人甚至是被征服者,如《海的意志》中,诗人面对大海的意志,便自认是“一个浪,不容你多想。/忘了自己”[5],这种臣服于海的姿态,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或许就部分地源自他的幼年经验。
抗战时期,大量文化人南下香港,如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茅盾、戴望舒、杜衡等都曾在香港避难,并在这里创办或主编报刊,如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就成为香港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彼时笔名尚为路易士的纪弦,也从上海经武汉、长沙等地流亡到香港,并与在香港的内地文人圈联系密切:“在香港,和来自上海的老友们重逢,感觉到非常愉快。碰巧的是,大家都住在西环学士台、桃李台一带,朝夕相处,十分热闹。当然,我跑得最勤的,还是杜衡、戴望舒两家。徐迟也常见面。”[6]自1930年代初,路易士便逐渐成为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人组成的现代派文人群的外围成员,与他们有密切联系,抗战初期,因施蛰存在云南,路易士打算去那里谋生,却没寻找到出路,才转而前往香港。在香港避难的文人多从事写作的老本行,除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之外,杜衡主编《国民日报》副刊《新垒》,后来“杜衡有了更好的职务”,就把路易士推荐给该报社长陶百川,让他接任《新垒》主编。路易士接编之后,对《新垒》作了改动,主要是增加了文学内容:“《新垒》是个综合性的副刊,而非纯文艺的,和《星座》不同。后来我向陶公请示,蒙他允许,借《新垒》的篇幅出《文萃》旬刊。我编得很起劲,朋友们也踊跃投稿”[6]。1939年《国民日报》社长更替之后,路易士便辞职回上海,自编自印了三部诗集《爱云的奇人》《烦哀的日子》和《不朽的肖像》。1940年又再度赴港,经杜衡介绍,进入陶希圣主持的“国际通讯社”工作,协助翻译日文资料。直到1941年底香港沦陷之后,路易士才返回上海。
在香港期间,路易士除了与杜衡、戴望舒等之前同在上海的文人来往之外,与岭南诗人李宗大也就是欧外鸥也时常见面。据纪弦回忆:“特别是广东人李宗大,诗人欧外·鸥,在香港教书的,以前时常通信,现在能见到面,又常在一起玩,我最高兴,因为他也抽烟斗,蓄短髭,而且个子不矮,像我一样。”[6]欧外鸥是当时岭南的代表诗人,他出生于广东虎门,少年时曾居香港跑马地,1930年代在香港主编《诗群众》月刊等,有大量关于香港都市的诗作,如“香港的照相册”系列就是其中一部分,据研究者指出,他关于香港的写作超出了都市诗习见的疏离和匮乏主题,而是“把香港的独特地理位置与殖民地的创伤记忆结合起来”“在宏大的背景和视野中演绎一则深刻的身份政治和国族寓言,其中包含的半殖民人民的历史悲情以及对迫在眉睫的战争的隐忧,令人动容,而形式的大胆尝试也令人赞赏”[7],对香港殖民地人民的悲情和精神创伤有深入的体验,应该说欧外·鸥对香港被殖民史与现状不仅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而且也抱着理解与同情的态度。欧外·鸥与纪弦很早就有交往,1936年9月路易士曾在苏州与韩北屏等创办《菜花》诗刊,后改名为《诗志》,《诗志》上每期都有欧外·鸥的诗作。《菜花》上虽然未见欧外·鸥的作品,但他也有关注,如该诗刊之所以改名,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欧外·鸥的来信,据《诗志》创刊号上《编者的话》所说,因为林丁与欧外·鸥两位诗人来信,认为作为刊名的《菜花》“不大好听”“有小家碧玉气”,所以才改名为《诗志》[8]。正因有这个交往前史,路易士在香港期间,才能与欧外·鸥来往如此密切;也正因与欧外·鸥的交往,使路易士不再只是一个游离于香港本土文人圈之外的逃难者。
二、香港诗坛中的路易士/纪弦
纪弦与香港本土诗人的交往,实际上不只欧外·鸥这个中介,在1930年代上半叶,他就曾在香港诗刊《红豆月刊》上发表了大量诗作。1930年代初,路易士逐渐成为施蛰存、戴望舒等现代诗人群的同人,但与此同时,他也经由写作、办诗刊等活动,与全国其他青年诗人群体有较为密切的互动,与他来往较多的诗歌刊物包括北京的《小雅》、武汉的《诗座》、福州的《诗之叶》,以及香港的《红豆月刊》等,用纪弦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来说,这“乃是中国新诗的收获季”[6]106,各地青年诗人和刊物大量涌现,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当时路易士就有大量诗作在香港的《红豆月刊》发表,其数量约在三十首左右,甚至超过在他自己所办刊物《诗志》上发表的数量。
《红豆月刊》是香港1930年代的文学刊物,既有的香港文学史研究较少提及,实际上它是香港1930年代中期最值得重视的文学杂志。陈乔之所主编的《港澳大百科全书》中对该刊有简要介绍:
《红豆》1933年12月创办。月刊。香港梁国英药局主办,药局少东梁之盘主编,该刊主要发表诗歌、小说、散文等创作作品,兼发翻译文章和文艺评论,论文部分则占较大比例。主要作者有李育中、侣伦、陈芦荻、路易士、柳下木、陈江帆、侯汝华、林英强、黎学贤等。曾出版过《英国文坛七杰专号》《诗专号》《世界史诗专号》。1936年8月因故停刊,总共出至第4卷第六期。[7]
该刊第四卷第一期的诗专号几乎全是内地诗人,而且是当时的青年诗人。该专号之后,该刊几乎每期都可见路易士的作品,此外,也有北京《小雅》诗刊编辑吴奔星的诗作。据吴奔星回忆,他主编的诗刊“创刊不久”,“就得到香港梁之盘先生的信,并把他主编的《红豆》文艺月刊寄给我,以示交流。接着,我和李章伯的诗也在《红豆》上发表”[8]。可见梁之盘极为主动地与中国大陆诗人交流。
路易士在《红豆月刊》上发表的诗作,还属于他早期的风格,带着感伤的情调与虚无的色彩,如《虚无人》:“廿世纪的风雨里/他采一朵虚无之花∥他把眼睛闭了——/明天于他是漠然的∥在他心中有一句话/但他悄悄去了”[9]。其他如《秋夜吟》《迟暮小唱》《雨夜》等,也都是这类颇具路易士典型诗风的作品。不过其中还有多首都市诗,如《都市》《在夜的霞飞路上》等,就写出了身居上海都市的独特体验,是路易士此时较为成熟的作品,尤其是在上海租界区的被殖民经验:“在夜的霞飞路上/在我流浪人底心中滋长着一束/做中国人的哀伤/是的,我是一个/黄肤黑发的中国人/而且有着一双/凝滞而多忧的眼睛∥不止那金发的/上帝之骄子/碧眼里投出/电一般的光辉∥而我是疲惫地/曳着自己底/怪凄凉的影子/踅入一条暗黑的小径了”[10]。这种面对殖民者优越性所体现出来的自卑感,是近现代中国所遭遇的心灵创伤的具体投射,这与欧外·鸥对香港殖民地创伤体验的书写是颇为一致的。这种历史经验、现实境遇与诗人体验的相似与同构性,就将上海、香港与台湾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单纯的文人间的来往互动,深入到了精神和心灵层面,也就是说,这些生活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诗人,他们的文化交流,除了常见的诗酒风流一面之外,还带着特定的历史经验与精神烙印。
《红豆月刊》除了发表路易士的诗作外,还多次介绍路易士的诗集《行过之生命》,并且评价颇高:“这是路易士五六年来致力于诗歌写作的心血的结晶,也是1935年中国诗坛上的一大收获。……路先生的作品是具有一种独创的风格的,其表现手法之熟练与多样化,已是远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而他的一种优美的感伤气分,将给你以无穷的喜悦。”[11]虽然带有广告的夸张成分,但对路易士的诗风的把握还是非常到位。
1950年代初,香港文坛也有个路易士,曾在《人人文学》上发表诗作,但此人已是另一个路易士,主要是写言情小说,而上海的路易士已于1945年改笔名为纪弦,并于1940年代末赴台,在台湾继续从事现代诗的创作,并先后主办了多份刊物,提倡“横的移植”的现代诗,让台湾现代诗运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思潮。纪弦在台湾提倡现代主义诗歌的同时,他的作品也时见于同时期香港的报刊,1950年代主要发表于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1960年代为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时报》文艺副刊《浅水湾》,1980年代以后则是《香港文学》。
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创刊于1956年2月18日,为战后香港的文艺复兴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作用。该刊现代主义风格鲜明,除了发表港台诗人的作品外,还译介了大量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该刊发表了纪弦大量的诗作。其诗首见于该刊是第一卷第三期,以《诗十章》总题,包括《山:整体的实感》《火葬》《南部》《金门高粱》《画者的梦》《十一月的新抒情主义》等十首,篇末有后记:“从《火葬》到《十一月的新抒情主义》这八首,作于民国四十四年,和今年的两首放在一起,便可以看出来它们的内容,形式,表现手法之多样性,但风格之统一,却也是不必讳言的。总之,不断地追求,探险和试验,而始终保持个性,这就是我所企图的了”[12]。在《编辑后记》中,纪弦还被夸张地冠之以“台湾诗王”的称号[13]。第二卷第二期又见纪弦的《阿富罗底之死》和《S’EN ALLER》两首诗;第四期的法国文学专号上刊载了纪弦翻译的阿保里奈尔的诗作五首,并附关于阿保里奈尔生平与诗观的介绍;此外,还有叶泥译的保尔·福尔和古尔蒙的作品。《文艺新潮》对法国现代派诗人的重视,部分也源自早期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的译介,这也表明1930年代上海的现代主义诗潮分别在港台分枝与汇流的史实。
纪弦对于1950年代香港文坛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在《文艺新潮》发表了诸多现代主义风格明显的诗作,为香港现代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更在于他在港台文坛互动中所起的连接作用。《文艺新潮》除了登载纪弦的作品外,还曾多次推出台湾诗人专辑。如第九期的“台湾现代派新锐诗人作品辑”,就登载了台湾诗人林泠、黄荷生、薛柏谷、罗行、罗马五位诗人的诗作。在这个特辑之外,也有纪弦的诗作《存在主义》与《ETC》,以及叶泥翻译的日本诗人岩左东一郎的《醒来》与《化妆》两首诗。编者在《编辑后记》中对台湾新锐诗人作了特别强调:“对于我们这个文坛起决定性作用的,照我们看,是一批新朋友的上场。在这一期,我们很骄傲地介绍了台湾的五位新朋友——现代诗派新锐诗人的作品,其中林泠女士和罗行、薛柏谷两先生是台大学生,罗马先生是一位宪兵,黄荷生先生则还穿着中学生制服,但是他们已经具备了阿保连奈尔或高克多年轻时的气质”,“台湾叶泥先生所译介的岩左东一郎,是日本现代名诗人,叶泥先生选择岩佐氏作品曾得其特许”[14]。对台湾诗人和译者都极为推崇,作了隆重的介绍。这个特辑的台湾诗人都是现代派成员,是纪弦所编《现代诗》的常见作者,而代为组稿的也正是纪弦。不久之后,《文艺新潮》又推出“台湾现代派诗人作品第二辑”,刊发了同样属于现代派阵营的林亨泰、于而、季红、秀陶、流沙五位诗人的作品。《编辑后记》对这些诗人也作了相应介绍:“台湾现代派诗人作品第二辑包括了五位比第一辑年长的诗人,林亨泰先生是道地台湾人,原用日文写作,曾被列为台湾现代诗人之一,光复后始学中文并用国文写诗,出有诗集《长的咽喉》,早是一位现代诗的健将了。于而先生系台北工专教授,对爱因斯坦大有研究。流沙先生是宪兵军官,季红先生则系海军军官。秀陶先生为台大学生”,同时也表明,“作为答谢和交流,本刊亦以‘香港现代派诗人作品一辑’之名,推荐了马朗、贝娜苔、李维陵、昆南和卢因五位先生的作品,交由台湾《现代诗》双月刊第十九期发表,尚希注意”[15]。
诚如编者所介绍的,纪弦所主编的《现代诗》紧接着推出“香港现代派诗人作品一辑”,由此,这两份刊物间的互动也成为台港文坛交流的一段佳话,尤其是这三个专辑,常为论者提及。但实际上,在《现代诗》与《文艺新潮》的相互合作下,台湾诗人在《文艺新潮》上发表的作品,远不止学界常提及的两个专辑,这除了常发表诗作的纪弦外,其他现代派成员如黄荷生就在该刊第十一期发表了《贫血》《手术室》等十首诗作;第二卷第一期有台湾诗人方旗的作品;第二卷第三期的台湾作家有高阳、方思和战鸿,尤其是在金门战地的诗人战鸿,编者作了重要介绍:“战鸿先生则是戍守金门的军队诗人,当此炮声响彻金门之际,《失眠夜》是值得特别体味的”[16]。战鸿也是《现代诗》的主要作者。可见《文艺新潮》不仅为纪弦提供了发表园地,让他的诗作得以在香港发表,同时也为以他为首的现代派诸诗人提供了走出去的契机。
《文艺新潮》1950年代末停刊,紧接着《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改为文艺版,是香港1960年代最为重要的文学副刊之一,在编者刘以鬯的主持下,该刊得到了港台诸多作家的支持,据他自己介绍:“《浅水湾》于1960年2月改为文艺副刊后,除香港的文艺工作者之外,还获得不少台湾作家的鼓励和支持,戴天、纪弦、叶泥、魏子云、王敬义、秦松、于还素、宣诚、张健、卢文敏等都有稿子寄来”[17]。纪弦从1961年2月开始在《浅水湾》上发表作品,而且数量不少,除《银桂》《春之什》《榕树》《尤加利》等十数首诗作外,还发表了十二则诗论,这些“袖珍诗论”议题较为广阔,主要是围绕着他的现代诗理论展开,这从论题也可略窥一斑:《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成人的诗与小童的诗》《噪音与乐音》《自由诗的问题》《现代诗的定义》《现代诗的偏差》《现代诗的纯粹性》《作为一个工业社会诗人》《一切文学是人生的批评》《现代诗的批评精神》《诗的本质与特质(上、下)》。对现代诗形式自由的强调、对纯诗的追求,与前后发表于台湾《现代诗》《幼狮文艺》等刊物上的相关诗论《现代诗的偏差》《现代诗的评价》《现代诗之精神》等构成了台港呼应。
1976年底纪弦夫妇移民美国,此后他在香港发表的作品,除了在《大会堂》上的两篇作品外,其他主要刊载于《香港文学》。该刊创始于1985年,发表了纪弦的《怀扬州——呈诗人邵燕祥》《为小婉祝福》《完成篇》《上海上海》《船及其它》《〈纪弦精品〉自序》等诗文;该刊还发表了不少关于纪弦访谈、回忆等文字,是了解纪弦晚期生活、写作与情感状态的重要窗口;此外还有大陆学者蓝棣之、古远清等人的评论文章,从艺术风格和文学史地位等方面对纪弦作了历史评价。这些都是了解纪弦的重要资料。
无论是在香港求学、避难、主编刊物,从1930年代起在香港期刊《红豆月刊》《文艺新潮》《香港文学》等发表作品,还是以他为媒介的两地诗坛的交往,都表明纪弦与香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如果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定义香港文学,那么,纪弦曾在香港生活,在香港创作,并在香港发表作品,那么,他也可部分地归为香港作家②。
三、纪弦对香港诗歌在台湾传播所发挥的作用
台湾《现代诗》与香港《文艺新潮》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纪弦和马朗这两位主编。纪弦在《文艺新潮》发表了大量诗作,并为该刊介绍现代派其他诗人作品,他所主编的《现代诗》也为香港诗人作品进入台湾提供了媒介,甚至连他筹组的现代派诗人群中也不乏香港诗人。
1957年初,纪弦筹组具有社团色彩的现代派,初次加入的诗人达83人,现代派成立之后,后续又有19人加入,这19人中的奎旻与马朗是香港诗人,而且被列为“社务委员”。马朗是《文艺新潮》的主编;奎旻为香港人,时在加拿大留学。据编者介绍:“诗人奎旻现正留学于加拿大,他的家在香港,只身远渡重洋,作客异域,目睹华侨社会现状,感慨万千,于是发为吟咏,以唐人街一诗为代表,一种忧国怀乡之情,跃然纸上,读之发人深省,而其表现手法则又非一般只会喊喊口号者所可企及的,洵佳作也。现在他的诗集《唐人街》业经编就,列入‘现代诗丛’,即将于年内出版”[18]。奎旻在《现代诗》上发表了《唐人街》《奇迹》《没落》等诗作,不过主要是写异国羁旅之思,与香港并无太大关联。
香港诗人在《现代诗》上的集体亮相是第19期的“香港现代派诗人作品一辑”,该辑刊载了五位诗人,包括马朗、贝娜苔、李维陵、昆南和卢因,并对诗人生平作了简要介绍:其中马朗和贝娜苔都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港从事编辑工作;李维陵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写小说和文艺论文;昆南和卢因分别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和英华书院。马朗所选的是《岛居杂咏》系列,包括《北角之夜》《第三个岛屿》《炎夏》和《逝》;贝娜苔选的是《香港浮雕》组诗,李维陵的是《秘密》和《女歌者之爱》,昆南的为《三月的》和《手掌》,卢因的《黑袈裟的一夜》《虽然仍一样沉沦》《追寻》《1956年》和《沉默》。较之《文艺新潮》上所刊登的台湾诗人诗作,这些香港诗人的作品,具有更强的地域色彩和时代气息,这即便置于同时期的《现代诗》诸诗人行列中也是如此。像《北角之夜》,写大都市夜晚的颓唐,《第三个岛屿》有副标题“我的Odyssey”[19],语气却全然是反英雄化的低沉,透露着迷惘色彩,这种现代人的境遇与神话所形成的反讽结构,与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立意类似。昆南的《三月的》也写出了“一九五七春天维多利亚小城”[20]香港的欢笑与阴沉。这些诗作基本上都是对香港历史和地理的书写,虽然还不够成熟,部分地带着感伤的色彩,观察不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层面,个人感悟也缺乏深入的省思,不过它们还是为台湾诗坛注入了鲜明的香港经验,尤其是现代都市的经验,丰富了台湾现代主义的内容和表达形式。
对于《文艺新潮》与《现代诗》之间的交流过程,纪弦在第17期的《编辑后记》中有所说明:
诗人马朗是编者的老友。在香港,他主编的《文艺新潮》已出九期,质精量丰,好评啧啧,为广大读者群所热烈支持。纪弦、叶泥、方思等亦经常为之撰稿:最近由于纪弦的严选与推荐,该刊第九期上又以一个特辑的篇幅发表了林泠、罗行、罗马、薛柏谷及黄荷生五人的作品。至于马朗本人,作为现代派的一员,他也是常有稿子供给本刊的;最近他介绍了香港诗人贝娜苔的译诗,已发表于本期。关于此一台港诗坛交流工作,纪弦马朗二人业经约好,今后仍将继续下去,并将愈益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务使香港诗人佳作经常输入,发表于本刊以与国内读者见面,同时使我自由中国优秀的诗人群都有足以代表的好诗输出,经由该刊以呈献于海外读者之前,彼此观摩,相互勉励,庶几达成吾人所肩负的新诗的再革命这一艰巨的任务,而为现正蓬蓬勃勃展开于台湾及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放一异彩,树一辉煌的里程碑。[21]
马朗原名马博良,1940年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抗战时期曾主编《文潮》月刊,后在上海编辑《自由论坛晚报》副刊,与张爱玲、纪弦(路易士)、邵洵美、吴伯萧等作家相识[22],因而纪弦有“老友”一说。他除了写诗外,也写小说和影评。诗歌则受戴望舒、艾青和纪弦等人影响。在他所主办的《文艺新潮》第一期,登载了他的两首代表作,《焚琴的浪子》和《国殇祭》。《焚琴的浪子》诗为:
烧尽弦琴
古国的水边不再低泣
去了,去了
青铜的额和素白的手
那金属性清朗的声音
骄矜如魔镜似的脸
在凄清的山缘回首
最后看一次藏着美丽旧影的圣城
成千万粗陋而壮大的手所招引
从今他们不用自己的目光
看透世界灿烂的全体
甚么梦甚么理想树上的花
都变成水流过脸上一去不返……
今日的浪子出发了
去火灾里建造他们的城……[23]
有将此诗解为书写香港都市生活体验的,这可能不太准确,因为诗中较少直接涉及香港生活体验,而更像是以象征的手法,写面对时代巨变、大陆易色时,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与不安,并认为大陆民众“褪皮换骨”之后,“只看着红色风信旗的指向”,而“无视自己”,这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统治作了负面的想象和表达。这种态度和处理方式,与彼时香港的“绿背文化”和台湾的“反共文艺”实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该诗后来也被张默、痖弦编入《六十年代诗选》。该诗最后一句“去火灾里建造他们的城”,脱胎于纪弦的诗作《火灾的城》,这重影响业经文学史指出,如刘登翰所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就认为,“‘火灾的城’这一意象可能来自三十年代路易士(纪弦)一首同名的诗”[24]。纪弦对《火灾的城》颇为满意,不仅出版同题诗集,且收入1945年的《三十前集》中,马朗在上海时期既然与纪弦结识,应该读过他这首诗。实际上马朗当时对上海的现代派诗人多有关注,包括他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也受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我老早已看过现代主义,在未曾解放之前,现代主义已是一种impact。当时中国还未曾正式介绍现代主义,但我发现有些杂志上卞之琳已译了好几人的东西,但未曾译到的Andre Breton(布列东),后来我去译。卞之琳译了梵乐希,译了里尔克,西班牙的阿索林,全部都译了”[22]。在上海时期与纪弦有着类似的现代主义知识积累,这类共同的文学经验为他们在港台之间隔海交流提供了历史前提,也在他们此后的编辑生涯和写作翻译中起着持续的影响作用。
马朗作为现代派的成员,确实常有作品发表于《现代诗》,不过主要是翻译作品。《现代诗》先后刊登了他所翻译的史宾德(Stephen Spender)的《命运》《炸后城市的杏树》;H.D.(Hilda Doolittle)的《梨树》《鴗》《花园》;阿茨波麦克列许(Archibald MacLeish)的《征服者》和《遗世书》;奥登(W.H.Auden)的《纪念W.B.叶芝》和《不知名姓的国民》等。较为侧重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这也可看出他与纪弦之间的细微差别,纪弦的翻译对象大多是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而马朗除了关注法国诗人外,对英、美及意象派诗人都较为关注。贝娜苔除了发表诗作,也曾在《现代诗》上发表意大利诗人桑泰耶纳(Santa⁃yana)的诗作《诗人的遗言》,贝娜苔原名杨际光,曾在《香港时报》工作,后有诗集《雨天集》,当时是《文艺新潮》的主要作者。
除了登载马朗、贝纳苔、昆南等香港诗人的诗作外,《现代诗》还特意宣传了《文艺新潮》,不仅整版列出该刊的要目,而且还以现代诗社的名义发表启事:
香港《文艺新潮》创刊以来,深受海内外读者之欢迎,现在第一卷第十二期已出版,封面画是波纳所作《巴黎街头素描》,橙黄、深棕、黑与柠檬黄四色,厚八〇面,每册港币一元。有分量,有立场,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凡看过前几期的,无不誉为东南亚水准最高的读物。
该刊已蒙侨委会批准登记,内销证不日发下,即可大量运台交由本社总经销,诚属高尚的读者们之一大喜讯也。
但在本社尚未正式代理之前,凡欲试阅一两期者,本社现有一、三、四、六、七、八、九、十二各期,每册实价新台币六元,可直接函购。而二、五、十、十一各期缺书,不能预购,这是很抱歉的。③
这则广告透露了很多关键的信息,首先是对《文艺新潮》介绍极为详细,其次是现代诗社是《文艺新潮》“指定台湾总代理”。不过据马朗回忆,台湾当局一开始并未通过该刊的引进,不仅不允许在台湾销售,而且还阻止其在东南亚的销售,因而,《文艺新潮》创办初期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台湾流传,马朗在2002年的一次访谈中曾着意强调这点:
其实左派当时文艺性的刊物有好几份,右派也有好几份。《文艺新潮》就夹在当中。你知道,《文艺新潮》第一期、第二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全部被吊销,说是共产党刊物,国民党告诉他们这是共产党刊物,不要给它们进来。台湾始终不给《文艺新潮》入口,现在就可以看到,后来才给进去的,但他们以前,所有《创世纪》《现代诗》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如纪弦、痖弦、叶维廉等人都可以告诉你,是手抄本的。他们带了一本进去后,就用手抄。是这样的,台湾检查《文艺新潮》也不是太紧,但不准入口。香港的《文艺新潮》对台湾的影响你是知道的,如果是没用的,为甚么要用手抄,而手抄的全是已成名的诗人、艺术家、作家等人。[22]
有手抄本流传,表明台湾文学圈对该刊的重视和认同,马朗就很肯定地说余光中曾看过手抄本,“我知道余光中就看过,余光中能看到,我相信是林以亮,也就是宋淇给他看的”[22]。部分台湾现代派诗人也可能曾受该刊影响,如刘以鬯便指出该刊曾影响台湾的文风,叶维廉则具体指明该刊所推介的西方文学对台湾诗人如痖弦等人的影响:“他在香港办的《文艺新潮》,不只是四十年代现代派一些新思潮新表现的延续(在台湾当时便是纪弦的《现代诗》),而且争先推介了存在主义者沙特和卡缪、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列东、亨利·米修等人及立体主义以还的新艺术,对台湾的诗人曾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即以痖弦的《深渊》为例,便有马朗译的墨西哥现代诗人奥悌维奥·百师(Octavio Paz)诗句的痕迹”[25]。
综合《现代诗》上的信息和马朗的相关回忆,可以发现《文艺新潮》一开始受到台湾当局的抵制,但后来实际上已逐渐方式。当然,台湾当局最初对《文艺新潮》的限制还是部分说明该刊与《现代诗》之间存在差异,较之《现代诗》的右倾色彩,《文艺新潮》立场要更为中立,内容也更为包容,如该刊第三期曾出“三十年来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的特辑,在所选的四篇小说中,就包含了师陀和张天翼这样曾有左翼倾向的作家,同时,在翻译方面,《文艺新潮》所选择的外国作家范围也更广。而反观《现代诗》,一是翻译范围以英法作家为主,其次也缺乏大陆五四以来尤其是左翼文学的信息,而这也不仅限于《现代诗》,整个台湾文坛都是如此,整体屏蔽了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及留在大陆的文人作品,从而造成现代文学的断层。
马朗与纪弦的文学活动和相互交流,为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台港现代诗提供了新的视野。马朗和纪弦早期在上海相识,而且都与现代派之间有较深的关联,1949年之后,二者分别在香港和台湾主持了两地最为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刊物。这表明,就历史渊源而言,港台现代派一定程度上可说是1930年代以来上海现代主义在两地的衍生,是同一枝条上的两支花朵。不过因两地的文化语境不同,现代主义的具体展开也有差异。二者之间的沟通,则可视为新的融合,在此过程中,出身上海现代派、在台湾提倡现代诗运动的纪弦,在港台现代主义的互动中起着桥梁的作用。
注释:
① 杨宗翰:《台湾〈现代诗〉上的香港声音》,《创世纪杂志》第163期,2003年9月;陈国球:《宣言的诗学》,载氏著《情迷家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28-142页;吴佳馨:《1950年代台港现代主义文学系统关系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济安、叶维廉为例》,台湾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第101-120页等。
② 按:对于香港文学定义的标准问题,学界已有较多的讨论,如郑树森就认为“香港文学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是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广义的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参见郑树森:《香港文学的界定》,《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55页)。
③ 见《现代诗》,1957年第19期,第43页(广告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