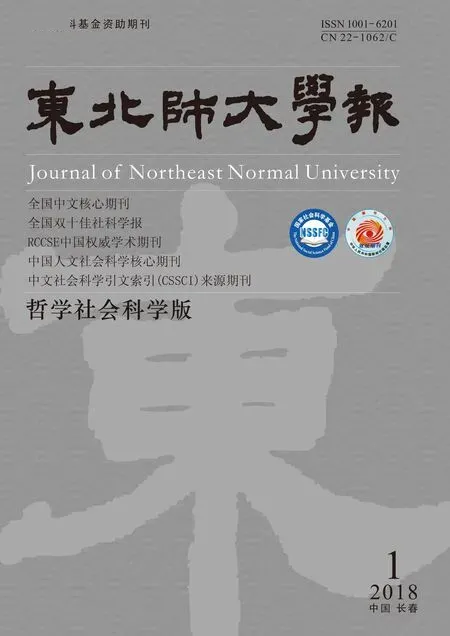好太王碑发现140周年的捶拓与研究
耿铁华
(1.通化师范学院 高句丽研究院,吉林 通化 134001; 2.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19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一直矗立在高句丽故都集安市东郊4公里的大碑街,已经有1603年的历史。清朝初年,为了保护皇族繁兴之地,修筑柳条边将长白山区封禁,高句丽故都便淹没在荒烟蔓草之中。重新被发现是在1877年(光绪三年),至今整好140周年。回顾一下好太王碑发现以来的捶拓与研究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一、好太王碑发现
清同治末年,关内灾荒与兵燹,大批流民闯关东,越过柳条边进入长白山区挖参伐木,开荒种地,清兵多次围剿,流民集结反抗,冲突不断,甚至酿成较大战事。光绪元年(1875年)盛京将军崇实曾派官兵前往通沟一带镇压边民反抗[1]929-930。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朝廷批准盛京将军崇厚奏折,“于六甸之宽甸添设一县,名曰宽甸县;六道河添设一县,名曰怀仁县;头道江添设一县,名曰通化县。分疆划界,委员分署。”[2]1419河南监生章樾,材具明敏,办事安详,“三年任设治委员,四年五月试署,五年二月补,八年正月调署怀德”[3]3177。章樾被委任怀仁县,随行的书启关月山同时到任。关月山其人未见经传,谈国桓《手札》中写到:“奉天怀仁县设治之时,首膺其选者为章君樾,字幼樵。幕中关君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弟髫年犹及见之,字颇精整。当时并未有全拓本,以碑高二丈余,寛六尺强,非筑层台不能从事,而风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收入《辽东文献征略》1925年。后来,他在《跋语》中又提到此事:“章樾字幼樵,河南光州人。光绪十一年,岁在乙酉,先君子宰承德县首邑,晋引入都。章君代理县事。其书启西席关君月山,赠余拓碑字数枚,每纸一字,即此碑也。字甚完整,拓工亦精,惜髫年不知宝贵,随手抛弃。”*文末落款“己巳秋八月二十五日谈国桓”,己巳,1929年。怀仁书启关月山正是好太王碑的发现者。时间在光绪三年秋天,他随章樾到达怀仁不久。好太王碑所在地,设通沟巡检,属怀仁县管辖。谈国桓回忆,髫年曾得到关月山赠送的好太王碑拓字。谈国桓生于1871年(同治十年),髫年为七八岁时,当在1877(光绪三年)—1878年(光绪四年)前后。这与王志修《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中的记载很是相同。
王志修,字竹吾,号少庐,又号梦庐、翛庐,山东诸城人,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王赓言之孙。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顺天举人,曾任奉天府军粮署同知,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金州厅海防同知,调任岫岩知州,著有《翛庐诗草》《奉天全省舆地图说图表》等。王志修工诗善文,尤善书法,惜流传不广。近日于网上得见王志修行书联及旧藏清人册页题跋,惜对联残损,题跋小楷作书工整俊逸,殊为难得*三缄堂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415094937。。题跋署名“东武梦庐主人志修记”,可以证实其籍贯与名号(东武县西汉时设,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诸城县)。
1895年3月,王志修在奉天府军粮署被委托考试奉天府各衙署的青年吏员,他以好太王碑为题做韵文一篇,自己先行写出范文《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同年又写出《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考》合成《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考》由奉天军粮署石印出版[4]48。《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原名《高句丽永乐大王古碑歌试院示诸生》,用七言古风写成。
诗中准确地记载了好太王碑的发现时间,连同后来撰写的《高句丽永乐好太王碑考》,成为清末学者对高句丽研究的最早成果之一。诗中写道:
我皇驭宇之三载,衽席黎首开边疆。
奇文自有鬼神护,逢时不敢名山藏。
伐林架木拓碑出,得者宝之同琳琅。
“我皇驭宇之三载”,非常明确,就是光绪三年——1877年。好太王碑重新发现,迄今为止正好是140年。
经过多年讨论,多数学者都认定了怀仁县书启关月山是好太王碑的发现者,同时注意到怀仁建县的时间1877年(光绪三年),更注意到王志修《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中的“我皇驭宇之三载,衽席黎首开边疆。奇文自有鬼神护,逢时不敢名山藏”,皆可证好太王碑实为光绪三年为怀仁书启关月山发现。
关于好太王碑的发现时间,一直存在着多种说法。多数已被否认。只有部分日本学者还认为好太王碑是光绪六年(1880年)发现。主要依据是叶昌炽《奉天一则》中的记载:“高句丽好太王碑,在奉天怀仁县东三百九十里通沟口。高三丈余,其碑文四面环刻,略如平百济碑。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穷边无纸墨,土人以径尺皮纸捣煤汁拓之。苔藓封蚀,其坳垤之处,拓者又以意描画,往往失真。”*写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收入《语石》,1909年苏州振新书局印刷发行。叶昌炽的这段记载比王志修的《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要晚几年,而且他没有到过通沟,听他人讲述作出的记录。王志修则在好太王碑发现不久就到碑前捶拓过碑文。王健群早已指明“光绪六年”恐系笔误[4]57,231。
反复研读叶昌炽的这段记载,应该包含两方面内容,前一句“高句丽好太王碑,在奉天怀仁县东三百九十里通沟口。高三丈余,其碑文四面环刻,略如平百济碑”,是介绍好太王碑在奉天怀仁县通沟口的距离。有今日公路里程一为144.6公里,一为136.8公里。清末车马路程至多为三百五十里左右,存在几十里的差距。还有好太王碑的高度“三丈余”,其实只有“两丈余”,误差较大,达到30%多。四面环刻碑文倒是不错,可形制“略如平百济碑”则大错特错了。“平百济碑”全称“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或称“苏定方碑”“苏定方塔”“苏定方平百济塔”“苏定方平百济塔碑铭”,是关于唐朝联合新罗灭百济的珍贵文字资料,保存在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的五层石塔底层。每面由4块长方形花岗岩石板镶嵌而成,共16块石板,上面竖刻汉字楷书碑文,右面第一块石板上刻8个篆书大字“大唐平百济碑铭”。整体看就是一座五层石塔,碑铭在下部,造型较为特殊。好太王碑则是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凿而成,为方柱形,无碑首,碑高6.39米,宽1.34—2.0米。四面环刻汉字隶书碑文。无论是形制,还是碑文书体、内容,平百济碑与好太王碑都大不相同。后面一句“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穷边无纸墨,土人以径尺皮纸捣煤汁拓之。苔藓封蚀,其坳垤之处,拓者又以意描画,往往失真。”很明显,不是说碑石发现的时间是“光绪六年”,而是说好太王碑拓本出现在“光绪六年”。怀仁建县之前,通沟一带已经有人居住。初天富、初均德父子就住在好太王碑附近,种地为生。他们看见好太王碑,那不叫“发现”。书启关月山不仅看见,而且知道是高句丽好太王的碑,还“手拓数字,分赠同好”,那才叫“发现”。关月山到通沟发现好太王碑,是没有必要“斩山刊木”的。只有捶拓完整拓本时,才需要“斩山刊木”搭架子,否则是不能“得到”的。下面则进一步说拓本制作的情况:“穷边无纸墨,土人以径尺皮纸捣煤汁拓之。苔藓封蚀,其坳垤之处,拓者又以意描画,往往失真。”仔细读书的人都会明白好太王碑的发现与碑文拓本的出现是两回事。
凡是早期到过好太王碑,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都会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好太王碑发现之初,碑上长满青苔,看不清文字,只有除掉青苔之后,才能得到完整拓本。谈国桓、叶昌炽、杨守敬、顾燮光、张延厚、刘天成,以及后来王健群、方起东的访问记录,都证实了碑上长满青苔和经过火焚除苔的事实。来到碑前的日本人同初天富的谈话记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关野贞记录:初天富“三十年前就住在此地,受当时知县之命,拓制拓本,因碑面有长华(苔藓)以火焚之,致使碑角欠损。”[5]今西龙也记载:“此碑三十年前,碑面长满长华(苔藓)文字遗存与否,无法弄清。他(指初天富)奉知县之命,烧去长华,露出文字。当烧碑之时,使碑一部分毁损。”[6]120在大量的火焚清除苔藓的记载中,只有张延厚的一条《跋语》涉及火焚时间的记录:“又闻寅卯间,碑下截毁于火,为惋惜久之。”[7]70这条《跋语》写在他朋友得到的好太王碑拓本上,对于高句丽建国的时间、邹牟王的神话传说、高句丽的世系、墓碑的主人以及立碑的时间,进行了简单考证,而且是较为准确的。所说“碑下截毁于火”,正是火焚除苔造成的。时间在戊寅年和己卯年之间,即光绪四—五年(1878—1879年),就时间来讲也是对的[4]70。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877年(光绪三年)桓仁设治,书启关月山发现好太王碑,手拓数字,分赠同好;1878—1879年(光绪四—五年)初天富受知县之命火焚除苔,致使碑角伤损;1880年(光绪六年)边民初天富“斩山刊木”搭架子,拓出完整拓本。
二、好太王碑捶拓
怀仁县书启关月山既是好太王碑的发现人,也是第一个拓碑的人。只是由于碑石过高,加之苔藓封蚀,当时不可能得到全拓。正如谈国桓回忆所写:“奉天怀仁县设治之时,首膺其选者为章君樾,字幼樵。幕中关君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弟髫年犹及见之,字颇工整。当时并未有全拓本,以碑高二丈余,宽六尺强,非筑层台不能从事,而风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8]45后来在一份好太王碑拓本上写的《跋语》中也提及此事。之后,关月山向县令章樾报告,命令当地农民初天富清除碑上苔藓,捶制拓本。此后,拓出完整拓本的还有李大龙(李龙、李云从),谈广庆、王少庐、亓丹山,初天富之子初均德。
1963年,经过批准,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明善曾来集安捶拓,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协助进行。1981年周云台为王健群、方起东的研究项目进行捶拓。
目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保存着一批好太王碑不同时期的拓本。在日本、韩国、朝鲜、法国、美国的大学或图书馆也保存着一定数量的好太王碑拓本。
国内外现存的好太王碑拓本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双勾加墨本。开始拓的大部分是这种拓本,方法是将纸贴在碑面上,轻轻捶打之后,出现文字轮廓,再用笔描下来,文字以外的空地用墨廓填。其特点是文字清晰,黑白分明。不足之处是文字容易走形,容易误勾。按照好太王碑的四面,每面有多块纸连接成一幅,共四大张。这是一种完整的本子。还有一种是剪裁本,就是把经过双勾加墨后的本子剪裁成一定规格的小幅,粘贴成字帖。这种剪装本便于收藏和携带,临摹、练习、使用都很方便。不足之处是剪断了碑文原来的排列状态,不利于文字与历史的研究。
双勾加墨本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酒匂景信藏本,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酒匂景信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往中国牛庄的军事间谍。1883年(光绪九年)秋,奉命回国前,在怀仁一带旅游得到了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1884年(光绪十年)将拓本带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进行研究。由于带回去的拓本是由许多小块拓片组成,上面写有编号,需要将其按照编号的顺序粘接成四大幅,才能如好太王碑碑石上文字的样子。经过多方努力,大体可以按照碑文的顺序连接。中国和日本的好太王碑研究著作中都有记载[9]216-223。这种双勾加墨本制作起来较为费力,流行时间不太长,至1890年前后。罗振玉《俑庐日札》记载:“高丽古碑,以好太王陵碑为最先。……盖此碑善拓难得,以前厂肆碑贾李云从拓此碑时,每次上纸二三层。故第一层字迹较明晰。其第二三层模糊不辨之处,辄以墨勾填,不免讹误。”即是说第一层是为拓本,第二三层则作成双勾加墨本。张延厚也证实:吴县潘郑盦尚书“命京师李大龙裹粮往拓,历尽艰险,得五十本,一时贵游,争相购玩。”
第二类,双勾本。1902年,杨守敬从朋友曹廷杰那里得到了好太王碑拓本,感到“明晰清朗,与旧得大异”。出于珍视,杨守敬充分发挥其书法方面的特长,认真摹写出双勾的好太王碑文。这种四面环刻的碑文,文字较多,篇幅较大,摹写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唯一一部好太王碑双勾本。文字清楚,书写精良,排列得体,并在1909年(宣统元年)再版的《寰宇贞石图》中刊出。题签为“高丽好太王”,中缝对折处则是“好太王碑”。每页内有两个字,依照碑文顺次排列,无字或不可辨识处空出相应位置。
第三类,拓本。从广义上讲,双勾本与双勾加墨本也应当属于拓本之列。拓,同搨,古代也包括响搨与摹写。狭义的拓本,是指传统碑刻捶拓方法得到的墨本。先用白芨水浸泡纸张,然后将纸贴在碑石上,用毛刷或鬃刷轻轻捶打显出字形,待阴干以后,选好拓包上墨,最后揭取。由于好太王碑为角砾凝灰岩石质,粗驳不平,最初用较厚的皮纸或毛头纸方可进行捶拓。技术较高的拓碑者也需要二三层宣纸才不致破碎。关月山、李大龙、亓丹山以及谭广庆请来的拓工,技术都较高,初天富、初均德父子技术稍差些,经过多年捶练,技法逐渐成熟。据王健群、方起东调查,1900—1903年期间,初天富父子为了方便捶拓,提高效率,使拓片文字黑白分明,曾用白灰涂抹碑面凸凹不平处[4]33-34。日本学者称之为“石灰涂抹作战”[10]156-157。直至1928—1930年前后,涂抹的石灰开始剥落。
好太王碑拓本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时期。
早期拓本,1900年以前拓得。主要特点是文字间竖行界格清晰,文字笔画真实,无描画痕迹,文字间的石花均匀自然。北京、通化、台湾等地都有这种早期拓本。日本、韩国也有少量这样的拓本。其中以北京大学图书馆A本、日本水谷悌二郎藏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乙本等最具有代表性。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好太王碑拓A上有题签:“晋高丽好太王碑李龙精拓整纸本五分第三。”题签旁有跋文:“右好太王石刻,潘伯寅丈倩工李龙精拓者。题签即丈亲写。其云五分第三者,即所拓五分之第三次拓者。即此四字,已足证为金石家之词。龙号云从,隶古斋所售三阙即李龙手拓,胜王可群手艺多矣。陆和九记。”[11]129可知此本为北京李龙(李大龙、李云从)所拓。据刘承干《海东金石苑补遗》记载:“光绪己丑(1889年)宗室伯羲祭酒(盛昱)始集资令厂肆碑估李云从裹粮往拓,于是流传稍广。”据此可以断定,北大图书馆A本的捶拓时间为1889年(光绪十五年)。
水谷悌二郎藏本是日本保存最为精当的好太王碑拓本。此本所用纸墨俱佳,捶拓技术精良。每一面分成3段保存,共计12段。拓片上文字笔画均匀、清晰完整,竖格连续可见,第一、二面裂痕清楚,这都是早期好太王碑拓本的特点。中学教师水谷悌二郎喜欢收藏碑帖字画,1945年战后在旧物市场购得,水谷根据此本,写出了《好太王碑考》,发表在《书品》1959年100号上,1972年出版单行本。对于好太王碑的文字与拓本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本应该是谈广庆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请良工捶拓,1894年甲午之役被日本掠走。现藏日本国立博物馆。
1983年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对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好太王碑拓本进行著录研究。其中傅斯年图书馆藏好太王碑乙本,品相优良,年代较早[12],发表在《韩国学报》上*2016年11月,笔者和研究院李乐营院长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参加会议,曾与高明士教授联系。经古籍研究所蒋秋华研究员介绍,到傅斯年图书馆看到了好太王碑拓本,管理人员亲自打开拓本,要求我们离开一米远观看,不允许用相机或手机拍照。我们请求,能否距离远些,或用手机记录我们的观察时的工作状态,以好太王碑拓本作远背景,也没有得到允许,多少有点遗憾。。
中期拓本,时间在1900—1949年间。此期间,初天富、初均德父子多次用石灰涂抹碑上不平处,甚至勾描个别文字。1938—1939年前后,初均德七十来岁,拓不动了,搬到上套村居住。由于战乱,后来拓碑的人很少,碑上涂抹的石灰逐渐剥落。石灰涂抹时期的拓本比较多,代表性的拓本有沙畹藏本[13]1-5、内藤湖南藏本[14]569-581、东京大学人文研究所藏本、杨守敬藏本、东北师大藏本、集安博物馆藏吕耀东捐赠本等[15]67-70。这些拓本的特点是,墨色比较浓重,字迹黑白分明,看起来较清晰*2016年4月19日,笔者与研究院李乐营院长飞往济南。20日,在济南开发区报业集团大厦三楼“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见到了徐国卫馆长,他喜欢收藏名人字画、书札、手迹和各种碑帖拓片。手中有两种好太王碑拓本:一种为四大幅,另一种为剪装残本。徐国卫还热情地陪我们参观了他收藏完整的好太王碑拓本。共四大幅,平放在陈列大厅中。据他介绍,拓本是20多年前从上海朵云轩购得。经过允许,我们进行了测量与拍照、现场观察与比较研究。4月22日,我们赶到广州市,在梁英陆老先生家中见到另一种好太王碑拓本。分成四幅折叠收藏,每一幅的碑面都有名家题签。梁英陆先生已经85岁高龄,他详细介绍了拓本的收藏经过,早年由金石学家容庚先生收藏,后来赠送给他的。每面篇幅都很大,室内勉强展开,让我们仔细观察、研究和拍照。此本保存较好,每面都经过装裱,用纸与徐卫国收藏的拓本相同,保存更好些。用墨讲究,内含胶和少许中药,不招虫蛀,文字清晰,没有石花与界格,是典型的石灰涂抹后的拓本。年代在1905—1910年前后。。文字间的竖行界格基本不见,或者只有几处断续可见而不连贯。个别文字经过勾描,与碑上文字不同。如,第一面第1行第26—34字,碑上文字为“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石灰涂抹后的拓片上都是“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德”。很明显,石灰掩盖了原来的文字,勾描致误。类似情况,非只一处。行内之人,一看便知。绝不会因其文字较为清晰明朗、黑白分明而误认为是最早、最好的好太王碑拓本,石灰涂抹后的拓本,年代大约在1905—1913年期间[16]。
现代拓本,具体说来就是1963年和1981年两次捶拓的拓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与文物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先后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公布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文物法规与政策。1961年4月,集安的洞沟古墓群(包括好太王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集安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包括好太王碑)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好太王碑一直受到重点保护。国家文物局曾派专家对碑上的裂痕进行清理加固,重新修建了碑亭,并严格控制捶拓,必要时须经文物局批准。
1963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建立并进行考古调查。期间,曾批准北京故宫博物院拓碑技师张明善到集安捶拓好太王碑,集安博物馆周云台协助工作。先后拓得4套,赠送朝鲜社会科学院一套,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博物馆、集安博物馆各一套。集安博物馆的那套笔者曾多次看过。使用毛头纸拓出,用墨清淡,明丽舒朗,自然流畅,无人为修饰痕迹。捶拓技法精当、科学,文字最接近碑文现存状态。特别是过去的涂抹石灰绝大部分剥落殆尽,只有很少痕迹可见。基本不影响文字,竖行的界格也较为清晰。1985年7月,三上此男先生率日本好太王碑学者访华团在集安访问期间看过张明善拓本,王健群、方起东和日本好太王碑研究学者西嶋定生、李进熙、上田正昭、武田幸男等对这一拓本评价很高。
1981年,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王健群、方起东在集安调查研究好太王碑。经文物局同意,由集安博物馆周云台捶拓好太王碑。周云台是同张明善学到的捶拓碑文技术,使用大张的毛头纸,一得阁的墨汁。墨汁用清水调匀(没有经过蒸煮,这一点与张明善有所不同)。拓包分大小两种,先用大拓包打出轮廓,再用小拓包作深颜色。虽然文字清晰,但是个别文字走形,甚至出现误拓。完整拓本发表在王健群的《好太王碑》一书附录五拓本七,另有部35幅插在122—123页之间。
第四类,摹刻本。好太王碑拓本传入京师以后,金石爱好者与研习书法之人争相购取。由于拓本不多,有人根据拓本用木板刻成,再进行捶拓,形成一种摹刻本。张延厚在跋语中有记载:“胜清光绪初,吴县潘郑盦尚书始访得之,命京师李大龙裹粮往拓,历尽艰险,得五十本,一时贵游,争相购玩。大龙颇欲再往,以道远工巨而止。因是流传日寡。南中好事者,至双勾锓木以传。其墨本之稀可知矣。”此题跋收入《辽东文献征略》,说明至少在1925年之前,就有这种摹刻的拓本流传。
1995年11月,韩国林基中教授作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著录了北大图书馆藏好太王碑“拓片摹刻本”全4幅(编号:拓片室-3021326-M)。只记录了“摹刻本”,无长宽尺寸,亦无其他说明。拓本照片分两页影印[17]225-226。由于是木刻版,文字很清楚,字形与好太王碑上的文字大体相同,只是缺乏石碑上的质感,文字竖行之间亦无界格。个别文字与碑上不同。如第一面第1行第26—34字,碑上文字为“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拓片摹刻本上则是“剖卵降出生子有圣□”,与石灰涂抹后的拓本一样,“生”错刻为“出”,“而”错刻成“子”。还有第3行第41字摹刻成“黄”,第7行第38字摹刻成“當”,第8行第30字摹刻成“王”,第9行第13字摹刻成“皇”,第15字摹刻成“酉”……都是不准确的。类似的木刻版好太王碑拓本也有被剪裁后,装订成字帖的形式,提供给研习书法的人作为参考。
三、好太王碑研究的百年历程
好太王碑研究是从完整拓片出现以后开始的,中国、日本是最先开始研究的国家,后来韩国、朝鲜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
二战以前,好太王碑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和日本学者中间展开的。
中国学者得到好太王碑完整拓本是最早的,开始研究也应该是最早的。如奉天军粮署的王志修,在火焚除苔后不久就来到通沟拓碑。得到拓本之后便开始研究。中国往往不是看学者手稿完成的时间,而是以正式印刷发行为标准。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王志修《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考》刊行,其中包括《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和《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考》。《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原名《高句丽永乐大王古碑歌试院示诸生》,用七言排律写成,共84句,43韵,押下平声七阳韵,有些句子下加小字说明,实际是一篇以诗歌形式写出的考据文章。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荣禧刊印《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谰言》,其中《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是较早的好太王碑释文。中国和日本的一些著作都将其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释文收录。释文中最有特点的是对缺失文字的增补,对后来金毓黻的释文影响很大。
碑文著录较早的还有杨守敬《寰宇贞石图》。1902年 “杨守敬从曹廷杰处获得拓本”。1909年上海重印《寰宇贞石图》时增加了高句丽好太王碑双勾本,较为独特。
好太王碑的著录介绍还有:1909年叶昌炽的《语石》由苏州振新书社印刷发行,《奉天一则》收入其中;1918年顾燮光的《梦碧簃石言》发表,文字数无多,其间加小字注释;1922年,刘承干编成《海东金石苑补遗》其中收录了好太王碑释文,郑文焯著《释文纂考》,罗振玉著《唐风楼碑录》等全文;1923年欧阳辅的《集古求真》刊行;1925年《辽东文献征略》收入谈国桓的《手札》对好太王碑发现与捶拓记录;1928年8月,刘节完成了《好太王碑考释》,发表在《国学论丛》第2卷第1号上;1935年10月,金毓黻同徐景武等人对辑安文物遗迹进行考察,调查记录与草图,收在《静晤室日记》第五卷中;1940年,金毓黻的《中国东北史》上编作为大学教材印行,最先将高句丽史纳入东北史的范畴,对高句丽都城遗迹和好太王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好太王碑的研究较早些。光绪九年(1883年)秋天,日军参谋本部派往中国的间谍酒匂景信得到一份拓本(双勾本),带回日本。日本的好太王碑研究从此开始。
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会余录》第五集刊行,内载《高句丽古碑文》《高句丽碑出土记》,横井忠直的《高句丽古碑考》《高句丽古碑释文》。有人用《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段落牵强解释好太王碑,对好太王碑文中的干支随意改变比定,并对《三国史记》《东国通鉴》等朝鲜史料进行非难和指责,给后来的好太王碑研究和古代日朝关系史研究带来很多不良影响。一些较为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对他们的作法提出批评。
1898年,三宅米吉的《高丽古碑考》《高丽古碑考追加》先后发表在《考古学会杂志》上。他利用小松宫藏本,将好太王碑的文字顺序搞清楚,在解释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为日本好太王碑研究走上正确道路打下了基础。
1900年以后,鸟居龙藏、关野贞、今西龙,黑板胜美等先后到辑安对好太王碑进行调查。规模较大的一次是1935年9月28日至10月5日,池内宏与梅原末治的调查。参加人有:浜田耕作、三上次男、小场恒吉、水野清一、田中丰藏、小泉显夫、泷川政次朗、黑田源次、伊藤伊八、斋藤菊太郎、冈崎信夫。1938—1940年,出版了《通沟》上下卷。
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好太王碑与高句丽历史研究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二战以后,好太王碑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至2000年,整好50年。
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事件有:1955年,韩国学者郑寅普发表《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陵碑文释略》*收入韩国《庸齐白乐濬博士还甲纪念国学论丛》一书。;1959年,日本中学教师水谷悌二郎的《好太王碑考》在《书品》100号上发表。由于他得到了年代早、质量好的拓本,完成了较好的释文与考证,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1966年,朝鲜朴时亨著作《广开土王陵碑》由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1972年,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李进熙的著作《广开土王陵碑研究》,书中第五章提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经三次派人对好太王碑文字进行加工,即所谓“石灰涂抹作战”,篡改文字。这种说法遭到日本一些学者的激烈反对与批评[16];1984年,中国学者王健群的《好太王碑研究》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好太王碑的发现、火焚除苔、石灰涂抹作了大量调查,对碑文进行了考释研究,对李进熙的“石灰涂抹作战”进行了批评,查阅了档案,调查了当地群众,揭示了石灰涂抹的情况;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武田幸男的《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收录了金子鸥亭藏本,傅斯年藏甲、乙本,水谷悌二郎藏本,酒匂景信双勾加墨本;1993年,中国学者朴真奭的《好太王碑与古代日朝关系研究》,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林基中的《广开土王碑原石初期拓本集成》,收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8种好太王碑拓本;1999年,延边大学出版了朴真奭的《高句丽好太王碑研究》;此期间,中国各地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批《好太王碑拓本》字帖。
后一阶段,从2000年至今,只有17年。好太王碑研究进入正常研究状态。其特点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加强。2014年,正值好太王碑建立1 600周年,中国、韩国、日本分别召开了学术会议进行纪念。同时还有不定期的学术交流和会议,促进了学者之间的学术了解与理解。2001年,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朴真奭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王少箴藏本、书通本、吴椒甫藏本;2006年,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在日本东京堂出版;2014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耿铁华、李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藏好太王碑拓本》。
不久前集安高句丽碑的出土,使高句丽碑刻与好太王碑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由于碑文中有“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河伯之孙神灵佑护”“以此河流四时祭祀”及相关法令*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碑》第1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好太王碑密切相关,相互参照,进一步印证了好太王尽为上祖先王墓上立碑历史事实。
[1] 王树楠.奉天通志·大事[M].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2] 柯劭忞.清史稿·崇厚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王树楠.奉天通志·职官[M].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4]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5] 关野贞.满洲辑安和平壤附近的高句丽遗迹[J].考古学杂志,1914(5-3,4).
[6] 今西龙.关于广开土境好太王陵碑[A].久米邦武.日本古代史[C].东京:早稻田大学,1905.
[7] 张延厚.跋语[A].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8] 谈国桓.手札[A].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9] 朴真奭.好太王碑拓本研究[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1.
[10] [日]李进熙.广开土王陵碑研究[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
[11] 徐建新.好太王碑拓本之研究[M].东京:东京堂出版,2006.
[12] 高明士.台湾所藏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J].韩国学报,1983(3)
[13] [日]李进熙.广开土王陵碑研究·附录[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
[14] 谢承仁.杨守敬集·九[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5] 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16] 耿铁华.关于新发现的两种好太王碑拓本[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3).
[17] [韩]林基中.广开土王碑原石初期拓本集成[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