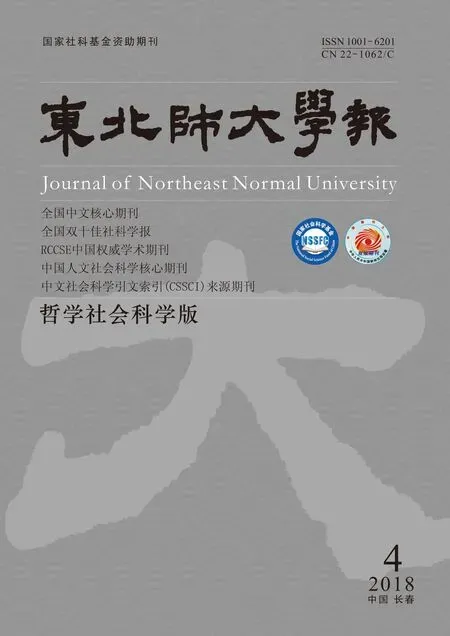婴儿移情的研究综述
刘秀丽,朱宇宁
(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移情是体验一种与他人一致的情感状态的情感反应,它源于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或领悟,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257-267[2]131-149[3]126-136。移情加工过程通常会激发亲社会行为、抑制攻击性,为基于关怀的道德提供基础[4]1-24。目前各个学科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到移情的重要作用。但是,移情能力在人类生命的早期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受哪些因素影响?了解婴儿期移情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机制,对于理解个体早期社会化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现有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对移情这种关键社会能力在个体婴儿期的发展进行总结阐述。
一、婴儿移情概述
从进化的视角,移情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群居动物的一种亲社会能力。这种能力由最初的本能进化而来,随着人类发展不断提高,是社会适应所必需的能力之一。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移情是个体由真实或想象中的他人情绪、情感状态引起,并产生与之相一致的情绪情感体验的能力,还是一种对他人的情绪情感的感受、理解以及产生替代性情绪情感的反应能力[5]557-562。
关于移情的成分结构,不同的研究者拥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移情主要包括情感移情(affective empathy)和认知移情(cognitive empathy)[6]150-165。情感移情是个体能够对他人的情绪情感进行直接反应的能力,婴儿期个体通常表现为被他人的情绪情感所感染,婴儿早期表现出移情悲伤,或相似的面部表情;认知移情是使个体能够对他人的情绪情感进行知觉和理解的认知能力,婴儿期个体通常表现为试图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也即是假设尝试(hypothesis testing)。Decety及其团队成员则认为移情应包含更精细的三种成分:情绪共享(emotional sharing)、情感观点采择(affective perspective-taking)及移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7]525-537[8]337-339。这三成分本质上分别对应情感移情、认知移情和亲社会动机或行为。情感神经科学和发展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同样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移情主要包含三种分离的神经认知成分,也就是情绪成分、认知成分以及动机成分。其中情绪成分类似情感共鸣(affective resonance)或情绪蔓延(emotion contagion);认知成分是一种类似情感观点采择的概念结构;动机成分是一种符合关心他人福利的冲动欲望[9]493,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基础之一。可见,目前研究者对于移情成分的界定表面上看起来虽稍有差异,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移情除了情感移情和认知移情成分,还应有亲社会性成分(动机和行为)。
关于婴儿移情发展的理论,其中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霍夫曼(Hoffman)移情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将移情发展与认知机制的发展相联系,指出个体出现区分自我与他人的认知能力是产生移情的关键因素[10]。霍夫曼提出个体移情发展应包括四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关于婴儿期个体移情发展的描述。第一阶段为自我中心移情阶段(0—1岁):处于该阶段的婴儿由于不能清楚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当看到他人痛苦时,往往不能区分究竟是自己还是他人处于悲伤或痛苦之中,从而使婴儿自身出现综合的痛苦反应。但是,到了6个月时婴儿通常不再自动地对他人的哭泣做出反应,而是首先表现出忧伤的表情,而后哭泣;而9—12个月的婴儿看到其他婴儿受伤并且哭泣,同样也会哭泣,并爬向母亲,向母亲寻求安慰。可见,此时的婴儿虽然能够觉察到其他婴儿发生了悲伤的事情,但仍不能区分谁在真正悲伤,于是自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伤,这也叫移情悲伤。第二阶段为准自我中心移情阶段(1—2岁):此阶段的婴儿开始逐渐学会区分自己与他人的痛苦与悲伤,但是,年幼婴儿仍不能清楚地区分自己与他人的内部状态,仍然经常把自己的痛苦与他人的痛苦相混淆。所以,此时个体的助人行为仍是“自我中心”的,即婴儿表面上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以减轻他人的痛苦情绪,但这或许仅为了减轻婴儿自己的痛苦。第三阶段为认知移情阶段(2—3岁开始):该阶段的婴儿已经具备了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情感和观点的能力。由于随着年龄增长,婴儿学会了理解与搜寻那些和他人痛苦或悲伤相关的信息,并依此形成有效的助人策略[10],所以此阶段的婴儿的助人行为相较于年幼婴儿则更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对他人的情感和需求的恰当理解。
婴儿移情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自然观察法、看护者报告法以及母亲和陌生人假装受伤的情境法(研究者在场进行视频录像)。目前关于婴儿移情的实证研究主要依据Zahn-Waxler等人创设的研究方案:现场设置母亲和陌生人成人悲伤(或痛苦)情境,用视频记录婴儿面对自己的母亲以及陌生人成人悲伤(或痛苦)情境的反应,然后由两名研究者同时对视频进行编码[11]447-458。因许多研究者认为移情是一种旨在减轻他人痛苦的显著的亲社会行为(如帮助、分享以及安慰行为)近端动机[12]1-12,而对于婴儿,测量其亲社会行为也是可行的,所以研究者通常根据以下规则从情感移情、认知移情以及亲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指标对婴儿的移情反应编码:第一,情感移情的指标为情绪感染,是婴儿对受伤者的情绪情感表达,涉及语言表达、面部表情、手势以及身体姿势,分4点评分,从1到4分别表示:没有,轻微的(比如皱眉头但时间比较短暂),中度的(相对长时间),大量的(持续的皱眉、悲伤表情或同情的语气等);第二,认知移情的指标为假设尝试,是指婴儿使用语言或肢体动作等试图探究受伤者,它反映了婴儿试图探测痛苦或尝试从认知上去理解受伤者,也是4点评分,从1到4分别表示:没有,简单的非语言动作(婴儿抚摸与受伤者相似的自己的身体部位或看着受伤者的脸)或者是简单的语言问询,非语言和语言的单一结合(简单的结合),重复的或者相对复杂的尝试;第三,亲社会行为的指标为婴儿试图帮助或者安慰受伤者的行为,该指标也是4点评分:1表示没有,2表示轻度的(比如一次轻拍或抚摸),3表示中度的(帮助或安慰行为持续3—5秒,或者重复的亲社会语言),4表示大量的(帮助或安慰行为超过5秒)。
二、婴儿移情的发展
当前,婴儿移情的发展研究主要是以霍夫曼移情发展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婴儿情感移情、认知移情及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特点进行考察。大量研究都发现,婴儿期个体的移情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年龄发展趋势:随年龄不断增长,婴儿的情感移情、认知移情和亲社会行为能力均逐渐提高,但三成分各自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是因为随年龄增长,婴儿的大脑发育逐渐成熟即移情的神经生理机能不断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婴儿自身的社会互动经验越来越丰富,从而促进婴儿移情的发展。
(一)婴儿情感移情的发展
婴儿情感移情呈现出从自我中心的移情反应到他人中心的移情反应的阶段发展特点。前者主要是指婴儿的移情悲伤,指婴儿在面对他人悲伤的情境中,自己也变得悲伤并沉浸其中,例如新生儿的反应性哭泣;后者则是指婴儿在面对他人悲伤的情境中产生他人定向的反应,主要包括对悲伤他人的直接注视以及简单的安慰。
1.婴儿自我中心的移情反应
霍夫曼认为人类个体拥有天生感受他人痛苦情绪的移情能力,如移情悲伤。即便是新生儿在听到他人哭泣时,自己也会跟着哭泣,这也叫新生儿的反应性哭泣。在有关新生儿听到或观察到其他婴儿哭泣时的反应的相关研究[13]418-426[14]3-9[15]175-176[16]136-150中,研究者普遍发现,婴儿会对同龄人的哭泣表现出反应性哭泣。这些研究直接证明了婴儿期个体普遍存在的移情悲伤。除此之外,许多研究也发现,婴儿早期出现的反应性哭泣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如在听到机器模拟产生的哭声时,出生2到3天的新生儿并不会哭泣;也有学者发现,婴儿能区分自己的哭声与他人的哭声,并出现不同的反应,如当给婴儿呈现预先录制的婴儿自己哭声的录音时,他们不会产生反应性哭泣,即婴儿没有表现出移情悲伤[13]418-426。还有研究发现婴儿对其他婴儿哭声的反应性哭泣也不是快速的自动反应,他们平均是在1.5至3分钟之后才开始出现反应性哭泣[16]136-150[17]279-288。
综合分析上述的研究结果可见,尽管婴儿对他人悲伤同样表现出了移情悲伤,但是并不能认为新生儿的反应性哭泣就是简单的情绪蔓延,婴儿极为有限的情绪调节能力可能也影响着婴儿的移情悲伤。其实已有研究者指出,当他人悲伤比较强烈或持续时间比较长时,婴儿由于无法调节由他人悲伤引起的移情悲伤而出现反应性哭泣[18]126-131。
2.婴儿他人中心的移情反应
霍夫曼移情发展理论第一阶段认为0—1岁的婴儿分不清自我和他人,移情是自我中心的。但后来的许多研究发现,在第一年的中期以后,婴儿面对他人悲伤时,已逐渐出现了他人中心的移情反应,而不再仅仅是反应性哭泣。如Hay等人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面对同伴的哭泣和烦恼时,其移情悲伤很少出现,婴儿会以一种他人中心的方式进行移情反应,比如,对哭泣同伴进行直接地注意,或者对哭泣同伴的一次抚摸等[19]1071-1075。Liddle等人以8个月的婴儿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婴儿看到同龄同伴(有其母亲在场)悲伤时,婴儿首先注视对方,紧接着会表现出一些简单的安慰行为,如用玩具轻触或抚摸一次该同伴,然后注视悲伤同伴的母亲,最后才看向自己的母亲,而且很少出现自我悲伤[20]446-458。可见,霍夫曼移情发展理论低估了婴儿他人中心的移情反应能力的发展,婴儿早在6个月时就开始发展出了此能力。
(二)婴儿认知移情的发展
随着婴儿月龄的增长,婴儿大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婴儿与成人互动经验也增加了,婴儿逐渐表现出认知移情。2011年Roth-Hanania等人以8至16个月婴儿为研究对象进行的一项聚合交叉研究发现,月龄为8至10个月时婴儿表现出中度的情感移情(即婴儿出现相应的悲伤的面部表情)的同时,还能够一定程度地表现出认知移情(婴儿试图探索以理解他人的痛苦)。在此研究中他们还发现,不同移情成分的发展趋势各不一致:随月龄增长,虽然婴儿情感移情能力不断发展,但是月龄差异并不显著,即情感移情能力的发展较为稳定;而认知移情(假设尝试)的发展则存在显著的月龄差异[11]447-458。也就是说,婴儿对他人的情感移情在第一年出现并在第一年基本达到成熟;而婴儿的认知移情虽然也是开始于第一年,但在第二年中仍然不断发展。
(三)婴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根据Roth-Hanania等人的研究结果,婴儿的亲社会行为也是从第一年开始,在第二年逐步增长。虽然亲社会行为与认知移情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轨迹,但与认知移情相比,亲社会行为不但发生频率较低,而且出现的时间也稍晚,亲社会行为在第二年才会增长迅速[11]447-458。之所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会呈现出与情感移情以及认知移情不同的轨迹,是因为亲社会行为需要情感、认知和动作的复杂整合[3]126-136[18]126-131。如相关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婴儿的亲社会行为(帮助,安慰等)在14个月到36个月期间迅速增加[21]737-752[3]126-136。早在1992年相关的研究也发现,个体稳定的移情反应出现在儿童2岁时[22]126-136,而且在第一年观察到的婴儿情感移情和认知移情能够对第二年婴儿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做出系统地预测。
综合上述众多的研究可见,婴儿移情各成分的发展趋势以及发展特点各不一样,情感移情始于新生儿,在生命第一年发展迅速并达到稳定;认知移情发展始于第一年,并在第二年逐渐达到中等程度;移情的动机成分即亲社会行为等则发展相对较晚,在第一年末开始,第二年内迅速增长。这些研究结论与霍夫曼关于婴儿移情发展理论的阶段性论述并不一一对应。霍夫曼认为第一阶段(0—1岁)的婴儿是自我中心移情,但研究者发现第一年中婴儿能够产生他人定向的反应,如注视、简单安慰痛苦中的他人[18]126-131。霍夫曼认为第二阶段(1—2岁)的婴儿是准自我中心移情,但目前研究证明第二年的婴儿已经能够对痛苦中的他人进行语言和行为上相对复杂的移情反应[11]447-458。霍夫曼认为婴儿移情悲伤是因为婴儿分不清自我和他人,混淆了谁在悲伤,但是并没有考虑情绪调节在情绪唤醒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低估了婴儿移情的能力。对于这些不一致,还需后继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此外,研究所发现的不同移情成分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研究结论也进一步证明了,Decety等人强调的在研究婴儿移情时区分不同移情子成分的观点是非常必要的。
三、婴儿移情的影响因素
目前,婴儿移情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个体因素(性别、气质以及遗传)和社会因素(移情对象的熟悉性、母亲抚养方式以及依恋)两方面进行考察。
(一)个体因素
1.性别
目前,关于婴儿移情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仍有争论。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移情存在性别差异,并且从出生到整个生命进程中移情的这种性别差异始终保持一致和稳定,即女性的移情能力始终高于男性[23]604-627[3]126-136[21]737-752[22]126-136;但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婴儿移情不存在性别差异,尽管有研究者发现女婴的移情能力略高于男婴,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24]70-97[25],因此,仍认为婴儿移情不存在性别差异。可见,性别是否影响婴儿移情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探讨。
2.气质
个体气质拥有许多不同的属性。大量研究发现气质特征能够影响婴儿的移情,但不同的气质属性与婴儿移情的关系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气质的特定属性如学步期婴儿的抑制性、恐惧和悲伤倾向与移情以及安慰行为负相关[26]111-134[27]125-146。个体发育早期,婴儿的抑制性气质虽不影响婴儿对母亲的移情,但影响婴儿对不熟悉成人的移情[28]1189-1197。研究者还发现,在生命的第一年婴儿善于社交的气质与情感移情以及工具性帮助呈正相关[29]367-383。近期有研究发现,婴儿消极情绪性与婴儿对母亲的移情呈显著负相关,婴儿的情绪性能够对婴儿对母亲的移情做出显著地负向预测,但婴儿消极情绪性与婴儿对陌生人移情相关不显著[30]97-121[25]。相对于非易怒的婴儿,情绪易怒的婴儿对他人通常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但是,如果易怒婴儿的母亲在日常母婴互动活动中对婴儿是高反应性的,那么这些易怒婴儿则会比非易怒婴儿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30]97-121。Schuhmacher等人研究发现18个月婴儿的恐惧气质与婴儿安慰行为相关[31]124-134。而Gross等人在18至30个月的婴儿中没有发现婴儿气质(恐惧、羞怯和社交恐惧倾向)与亲社会行为(帮助、安慰或分享)的关系[32]600。可见,婴儿气质对婴儿移情的关系并不遵循简单的模式,具体的关系还需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3.遗传
移情具有遗传效应,如Zahn-Waxler等人以双生子为研究对象,发现移情具有中等强度的可遗传性[3]126-136。不同的均以双生子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移情能力的遗传影响力从20%[33]369-391至69%[34]112有所不同。近期,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的Simon Baron-Cohen与著名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合作,采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对46 861名被试的共9 955 952个遗传位点(SNPs)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移情能力的影响因素中,在测定的SNP范围内的遗传因素占比达到11%±1.4%。考虑到研究并未对全基因组数据进行分析,联系其他研究结果,遗传在移情中的影响可能会高达30%以上。可见,无论是在双生子研究还是非双生子研究中,移情的遗传性是相一致的,表明移情的遗传效应是明确的。
(二)社会因素
1.移情对象熟悉性
移情对象的熟悉性会影响婴儿的移情,表现为婴儿对熟悉的对象更容易产生移情。对于大多数婴儿来说,母亲是其主要看护者,所以目前,在有关移情对象熟悉性对婴儿移情影响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设置的移情对象通常是婴儿母亲与陌生的成人(主要是研究者)或陌生婴儿同伴。研究发现,与陌生的研究者相比,婴儿对自己母亲的移情反应最为强烈,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也最多[35]1081-1092[36]249-265[37]613-637[38]319-330。有些研究同时设计了母亲、陌生成人和陌生婴儿痛苦情境,结果表明,婴儿对自己母亲比对陌生成人以及对同龄人都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以及安慰行为[3]126-136[11]447-458。
2.抚养方式
父母抚养方式被定义为父母典型的育儿策略、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的整体的、一致的模式。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与婴儿互动质量对婴儿社会能力的发展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化角度来看,婴儿的移情可以被看作是特定养育行为的产物[38]319-330[39]3263-3277[40]17-25。Robinson等人发现,母亲温暖的抚养方式与14至20个月婴儿的安慰行为变化模式显著相关:母亲高温暖的抚养方式能够预测女婴20个月时的安慰行为;母亲高控制的抚养方式会导致婴儿安慰行为的减少,母亲低控制的抚养方式能够显著提高婴儿的安慰行为[27]125-146。有学者发现母亲对婴儿的移情看护(empathic caregiving)(当婴儿给他人造成痛苦时,母亲向婴儿富有情感地解释他或她自己的行为带给他人的痛苦情绪)与婴儿的补偿行为及利他行为呈显著正相关[38]319-330。Schuhmacher等人发现父母养护的日常出席能够显著地解释18个月婴儿安慰行为的个体差异[31]124-134。研究者还发现早期父母的敏感性与学步期婴儿对他人(看护者和陌生的研究者)悲伤的移情行为反应有积极的横向以及纵向联系[30]97-121[35]1081-1092[37]613-637。为探讨母亲积极温暖的抚养方式对婴儿移情的真实效应,研究者控制了儿童困难气质、性别和年龄变量,研究结果同样证明母亲对婴儿悲伤做出积极温暖的反应性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婴儿对他人(自己的母亲和陌生实验者)痛苦的移情以及亲社会表现[41]44-58。Massoff指出积极敏感的反应性的抚养方式对儿童心理理论和移情都有促进作用[42]。
3.依恋
依恋是个体在婴儿期与主要抚养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结,对个体个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至今有关婴儿期依恋和移情关系的研究不多,但这些研究仍为早期个体的安全依恋与移情的关系提供了初步的证据。Mark与其同事使用自然观察方法评估了16至22个月婴儿在母亲痛苦及陌生成人痛苦两种情境下的移情反应,实验控制了婴儿的气质变量,研究结果仍发现婴儿的不安全依恋能够负向预测婴儿会对陌生人的移情[43]451-468。相似地,Bischof-Köhler的研究发现,婴儿的安全依恋可以预测婴儿对悲伤的实验者有着更多移情关注和亲社会反应[44]142-158。采用母亲报告的婴儿移情评估方式,研究也发现移情得分最高的是在陌生情境程序中被分类为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其次是回避型依恋和矛盾型依恋婴儿,移情得分最低的是混乱型依恋的婴儿[45]375-392。
四、反思与展望
尽管目前婴儿移情研究已积累一定的成果,但该研究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探讨、改进和加强。
第一,婴儿移情研究需要更可靠、稳定的婴儿移情评估程序,并保证这些评估程序的可操作性。由于婴儿的语言能力比较低,在研究范式方面研究者必须考虑实验刺激的类型和水平设置是否合适;目前婴儿移情的行为研究绝大多数使用的是Zahn-Waxler等人设计的婴儿移情评估程序,但是该评估程序在实际操作使用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每位婴儿母亲在实验中表现的痛苦程度无法统一严格控制,加上现场的拍摄者也会影响婴儿的情绪和行为,所以这些均可能不同程度影响实验评估结果。因此,在未来研究中,为保证实验中的刺激适用于婴儿,实验情境不能超出婴儿期个体的社会知识范围,并且尽量减少实验中对婴儿被试的无关干扰。因此,研究者需尽可能做到在自然状态下诱发并记录婴儿的移情反应[25]。
第二,为了更好地了解个体早期的移情发展与个体社会化的关系,研究者应该结合社会依恋、道德和公平等社会心理学相关因素,探讨人类早期的移情发展与社会性发展的关系。因为人类的高级移情是建立在基本的移情形式之上,并且与一些核心神经机制相联结,而这些核心机制与情感交流、社会依恋以及亲代抚育相关,是影响婴儿移情潜在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探究婴儿移情的社会功能方面,个体早期的移情能力很可能是个体社会性和道德敏感性发展的基础。所以,婴儿移情的未来研究应重视与社会依恋、道德和公平等社会心理学因素的结合。
第三,神经功能成像、病变研究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据都表明,移情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认知能力,成人移情的生理基础涉及大脑的多个脑区。成人移情过程涉及包括原始脑区,如杏仁核(amygdala)、下丘脑(hypothalamus)以及海马(hippocampus)等;进化而来的新脑区皮层相关额叶皮层区域,如腹内侧和内侧前额叶(vmPFC和mPFC,在自我意识方面有重要作用,涉及意图理解)以及后颞上沟(pSTS,涉及意图理解)等区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HPA)系统和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SAM)系统[4]1-24。目前没有关于婴儿移情生理机制的研究,婴儿与成人移情的生理机制的区别和联系仍不清楚。因此,结合脑成像以及fMRI技术对婴儿移情的脑机制进行研究,将是未来婴儿移情的重要研究取向。
第四,目前对于婴儿移情的个体差异情况以及影响婴儿移情的潜在变量研究仍不够深入。婴儿移情影响因素比如抚养方式和依恋影响婴儿移情的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证实;婴儿气质与婴儿移情的关系并不遵循简单的模式,具体的关系仍需深入探讨;性别对婴儿移情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仍不一致。可见,对于婴儿期个体移情能力的影响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
最后,当前婴儿移情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婴儿对痛苦这一较为笼统的情绪的移情,婴儿移情发展特点也是基于婴儿对他人痛苦情绪的移情结果得到的,而很少有研究涉及婴儿对他人的具体情绪类别的移情。因此,目前仍不清楚婴儿对他人的高兴、愤怒、伤心和害怕这四种不同的基本情绪的移情是否存在不同的发展特点,这也是未来婴儿移情研究的一个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