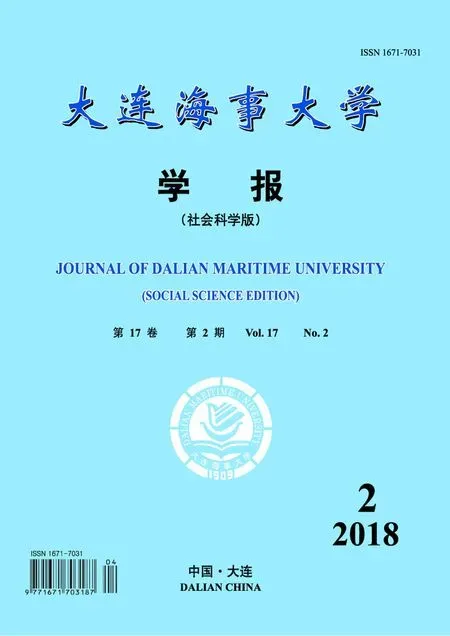“一带一路”倡议下黑龙江-阿穆尔河货物运输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周 新
(安徽师范大学 a.法学院; b.法治中国建设研究院,安徽 芜湖 241003)
黑龙江上中游是中俄界河,下游阿穆尔河在俄罗斯境内。随着两国相互开放界河口岸,俄方向中方开放阿穆尔河及出海口,中俄界河运输以及中方组织的黑龙江-阿穆尔河外贸与内贸江海联运开始起步。2015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实质性启动,*见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并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见2015年5月中俄发表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给黑龙江-阿穆尔河航运*黑龙江上中游总体处于自然状态,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的三级以上航道1924 km;下游阿穆尔河为俄O级航区,可航行3000吨级船舶,通航里程1000 km。由于水系处于高纬度寒温带,每年10月下旬开始结冰,第二年4月下旬结束冰期。带来重要发展契机;而如何构建中俄界河运输以及“中俄外”、“中俄中”江海联运跨法域*法域是法律有效管辖或适用的范围,这个特定的范围可能是空间范围、人员范围或时间范围。正是基于此,法域有属地性法域、属人性法域和属时性法域之分。参见文献[1]。运输模式下“兼容规范统一的运输规则”,促进“运输便利化”,相关法治建设议题亦已同步提上日程。*《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中俄联合声明亦提出,“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可见,包括运输规则构建在内的法治建设,是相关战略举措推进、落实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此项工作的基础,实有必要就现阶段黑龙江-阿穆尔河货运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问题展开研究。
一、黑龙江-阿穆尔河货物运输
黑龙江-阿穆尔河货物运输,涉及中国的,大体可分为黑龙江内河运输、中俄界河运输、中方通过俄阿穆尔出海口进行的外贸与内贸江海联运等几种类型。
(一)黑龙江内河运输
黑龙江内河运输,如果扩及水系而不仅仅在干流,是指中国籍船舶在黑龙江支流嫩江、松花江组成的松花江流域航运网*松花江流域航运网的构成大致如下:源于长白山天池的第二松花江是松花江干流的上游段,主要港口有丰满港、白山港、桦树林子港;嫩江是松花江最大支流,在三岔河口与第二松花江汇合,此段内主要港口有大安港、齐齐哈尔港、嫩江港、富拉尔基港、尼尔基港;松花江干流上的港口主要有肇源港、哈尔滨港、依兰港、佳木斯港、桦川港、绥滨港、富锦港与同江港。整个松花江沿江港站中,哈尔滨港、佳木斯港、富锦港、桦川港和同江港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吞吐量在百万吨以上的港口有哈尔滨港和佳木斯港。松干港口总体格局是以哈尔滨、佳木斯两个港口为依托,向沿江港站吞吐货物,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运输体系。内,黑龙江界河国界线本方一侧以及界河主航道水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国函〔2006〕133号)规定,“边界水”是国界线所通过的河流、湖泊或其他水域(第1条),双方国家船舶在边界水航行时,可在国界线本方一侧和沿通航界河的主航道航行(第9条)。范围内从事的本国港口间内贸货物运输。多年来,黑龙江沿线分布的森林、煤炭、粮食资源是水系内船舶运输、港口装卸的市场基础。但随着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水运木材数量锐减;国家取消粮食计划性调拨,水运内贸粮食货源减少。[2]这种水运货源结构的变化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更为明显。以往以哈尔滨、佳木斯中心城市为主的航运中心逐渐下移,转为以同江、黑河等中俄对应口岸为主,内贸货源逐渐减少,外贸货源相对增加。[3]
(二)中俄界河运输
1992年1月,中国交通部和俄罗斯联邦运输部签署《关于在黑龙江和松花江利用中俄两国船舶组织外贸货物运输的协议》(下称“中俄92协议”),中方为俄方船舶开放黑河、奇克*奇克镇隶属逊克县管辖,位于县境北部边缘地带,濒黑龙江畔,北与俄罗斯阿穆尔州波亚尔科沃隔江相望。、同江、富锦、佳木斯、哈尔滨港口,俄方为中方船舶开放布拉戈维申斯克、波亚尔科沃、下列宁斯阔耶、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共青城、马戈港口以及共青城港至河口的阿穆尔河段。协议的签署在一定意义上为中俄界河运输以及中方经由阿穆尔河出海口组织的内外贸江海联运奠定了国际法基础*政府间协议分为条约式政府间协议和非条约式政府间协议。条约式政府间协议由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发起和谈判,条约草案形成后分别报两国的立法部门批准,批准后由两国元首签发,因此它构成两国间国际法;非条约式政府间协议是指双方政府就特定事项达成协议后,由各自政府主管部门行政首长签字并在各自政府机构内部或相互之间履行会签手续后即生效,此类政府间协议在效力上没有条约式政府间协议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法。参见文献[4]。。
本文所称的黑龙江水系中俄界河运输,系指中俄两国航运从业者利用各自船舶或租借对方船舶在黑龙江界河段以及下游阿穆尔河水域从事的中俄国际运输。中俄界河运输主要在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逊克—波亚尔科沃、同江—下列宁斯阔耶、抚远—哈巴罗夫斯克等对应开放口岸间进行。明水期有散货船运输、集装箱航线、滚装船运输、飞翼艇运输,流冰期有气垫船运输,冬季冰封则铺设浮箱固冰通道。“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后,黑龙江省规划进一步畅通非对应口岸间的松花江—黑龙江—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水运通道。*见黑龙江省《推进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工作方案》(黑政办发〔2014〕58号)。
中俄界河运力中,顶推化作业的干散货驳船曾占绝对优势,[5]近年来随着集装箱船[6]、装载液化石油气罐的渡船[7]等相继投入运营,运输船型已趋多样化。
在运输组织上,除直达对方口岸的界河运输外,由中方黑龙江航运集团与俄方阿穆尔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黑龙江界河以及下游阿穆尔河进行的以互换推船和过驳减载为主要方式的“联合运输”,[8]是中俄界河运输的一大特色。
(三)外贸江海联运
受自然条件尤其是政治历史原因的限制,一个多世纪以来黑龙江水运不能穿过俄境内河段而通江达海,形成封闭式内河。[9]由于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重大装备制造和原材料基地,近年来对俄罗斯等区域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升级,江海联运已势在必行。
黑龙江-阿穆尔河江海联运,指货物在黑龙江水系内河港口装船,经江运运到下游阿穆尔河的庙街或附近其他港口、码头,再换装海船经海运运到目的港,或者通过江海两用船、江海直达船实现河港与海港之间的货物直接运送。根据目的港所在地的不同,分为外贸江海联运和内贸江海联运。*回程则反之。
中俄92协议的签署,为黑龙江-阿穆尔河江海联运去除了法律障碍。当年7月,江船“龙推609”船队在松花江上游三家子港装载2000 t玉米,在距庙街60 km的马戈港进行江船海船换装,完成了到日本酒田港的运输任务。[10]
总体来看,过去二十余年,受承运船型老旧、航道维护不足、港口设施陈旧、腹地外贸货源生成缓慢、回程货源难觅等多重因素影响,[11]这条通往俄远东、日、韩的“东方水上丝绸之路”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12]
(四)内贸江海联运
继中俄92协议之后,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又于1998年12月签署《关于中国船舶经黑龙江俄罗斯河段从事中国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之间货物运输的议定书》(下称“中俄98议定书”)。2004年6月,由黑龙江运往浙江的2700 t水稻,经同江驳运至庙街后,换装“黑河”号江海直达货船运抵温州港,[13]内贸江海联运启幕。2008年9月4日,江海两用船“木兰”号装载438 t 1000 kW定子由抚远起航,经庙街驶入鞑靼海峡,21日顺利抵达汕头,黑龙江重大装备国内江海联运开通。[14]
目前,这条出江入海、江海联运内贸航线,主要将黑龙江水系港口装船的粮食、煤炭、非金属矿石等大宗散货和大型机电设备、大件货物,经俄罗斯港口换装或直接运抵中国东南沿海港口。[15]
与外贸类似,内贸航线也存在货源不足、返程空载、成本难以降低等问题。迟至2009年11月,黑龙江内贸江海联运方迎来首次往返运输。[16]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涵盖俄罗斯远东和中国东北的欧亚地区必将迸发出更大的经济发展活力,黑龙江江海联运、陆海联运等物流通道建设提速,[17]“中俄外”、“中俄中”等跨境联运通道开始获得南方企业、相关部门[18]以及周边国家物流企业的关注[19],黑龙江内外贸江海联运航线有望焕发应有的生机。
二、黑龙江-阿穆尔河货物运输法律适用
航运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这是对市场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厘清并完善航运法律适用,促进运输便利化,是包括黑龙江-阿穆尔河货运在内的航运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法律适用,即依法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20]它既可以发生在特定法域内部,也存在于跨法域场合。对后者而言,在法律存在歧义而又没有统一实体法的情况下,将“确定的法律应用于实际案件”,通常还需要借助“冲突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21]以下重点探讨黑龙江-阿穆尔河界河货运、内外贸江海联运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问题,兼及内河货运法律适用。
(一)黑龙江内河货物运输的法律适用
黑龙江内河货物运输,是国内通航水域内的营业性运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2〕28号文《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在“双轨制”*中国海事法律(这里的“海”取广义,含与海相通的内河水域)对“双轨制”做出实质规定的,首推《海商法》第2条第2款,“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指导意见》也承认,与法律体系相对完善的国际海运相比,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内河航运的立法,国内水路运输法律规范的滞后越来越突出。下,法院审理国内水路货运纠纷案件,确定货方、承运方权利义务,不适用《海商法》第四章,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一般民事法律,并可参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下称“《货规》”)。
应该说,《货规》关于国内水路货运主体民事权利义务的96条针对性规定,有助于缓解一般民事法律“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问题,有益于水运法治建设,但由于《货规》上位法依据缺失,*根据《立法法》,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货规》就水运主体民事权利义务的规定并无上位法律或法规作为依据。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的立法体制建设要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其合法性也受到一定质疑。2016年5月30日《货规》废止*根据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57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废止20件交通运输规章的决定》,自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货规》废止,但该文没有附具废止原因。。
《货规》废止后,《指导意见》第1、2、6条等援引《货规》相关条款的准用性规范落空,包括黑龙江内河货物运输在内的国内水运特色问题,如实际承运人、管货环节、合理绕航、危险货物、舱面货、运输单证,在法律适用上将回到一般民事规定的老路,这引发理论与实务界的担忧与思考*理论与实务界曾就“双轨制”下《货规》废止后的应对提出若干建议,包括:借《民法典》编纂之际增订相关合同法规则;修订《海商法》并将其第四章适用范围扩及国内水路货运;在《海商法》框架下以《货规》特别规定为底本另行增补“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一章,现第四章改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又或是行业协会等组织推出针对国内水路货运的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等等。这些建议均有一个基本预设,即我国海事法律要么维持“分轨”,要么“并轨”统一。该等建议是否可行与必要,有待日后甄别。。
就目前而言,由《合同法》《民法总则》*《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后,《民法通则》与其相异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一般民事法律完成国内水路货运关系调整,在法律适用上确实存在一定不足[22],但尚不至于出现业界担忧的“许多具体问题欠缺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局面”[23]。
首先,原《货规》众多规定,与《合同法》完全一致或出入不大,该等规定的废止并不实质影响法律适用。比如,迟延履行问题,《货规》第34条第1款、第2款确立了“约定期间”与“合理期间”两个判断标准并做出损失赔偿规定;《合同法》分则第290条同样确定有上述两个判断标准,而赔偿问题则可诉诸总则第107条。再如,货物留置,《合同法》第315条赋予承运人得对运输的相应货物行使留置权以担保运费、保管费、其他运输费用的权利;《货规》第40条同样确立了承运人对相应运输货物的留置权,唯所担保的费用包括了“滞期费、共同海损分摊等其他运输费用”,与《合同法》“其他运输费用”并无实质不同,且二者均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又如,承运人责任基础。原《货规》第48条实质沿袭了《合同法》第311条,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承运人对于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的是“严格责任”,[24]这两条规定中的“除外”情形,要么不归咎于任何一方,如“不可抗力”、“货物自然属性和潜在缺陷”,要么属于托运人、收货人等其他当事人的过错所致,《货规》第48条只是将《合同法》第311条的三项免责事由细化为十项,其中第(四)项至第(九)项是托运人、收货人过错的细化,并未超出《合同法》的规定[25]。
其次,原《货规》针对国内水运实际做出的若干特色规定废止后,航运从业者、律师、法官们需要做的是从先前经常参照的《货规》特别规定中回到《合同法》等一般规定中来。限于篇幅,现以实际承运人为例。包括黑龙江内河货运在内的国内水运实践中,承运人在运输合同项下接受托运人托运的货物,又通过租船合同、运输合同或委托(代理)合同将其承揽的货物“委托或转委托”给他人实际运输,这种情况甚为普遍。如何规制这类运输安排下货损、货差、迟延交付所致赔偿关系,运费、滞期费等货方应付而未付费用的追索、担保(相应货物留置)关系,又或是承运货物(如危险货物)导致实际承运方利益损失时的赔偿关系?《货规》借鉴《汉堡规则》《海商法》相关规定,引入了“实际承运人”制度,在未直接缔结合同的实际承运人与货方(托运人、收货人)之间确立起合同关系*有学者称之为“承运人主体的扩张”、“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参见文献[26]第96~108页;另有学者认为对于航空、海上客货运输中的承运人,以最高院“指导案例51号”为代表的我国法院相关判决意见,多肯认实际承运人对旅客/托运人承担法定合同责任或一定情势下的约定合同责任,参见文献[27]。。据此,货方(时常是收货人)可就其遭受的货损、货差或迟延交货损失,直接向实际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下的赔偿,或者在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追究二者的连带责任,而不必绕经承运人,通过两次违约之诉,追究实际承运人的责任,徒增讼累,[28]也不必以侵权为诉由追究实际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因为侵权之诉会施加给货方过重的举证责任,并很可能招致败诉[26]97。同样,实际承运人未获偿付的运输费用以及因承运货物所致自身损失,也可以在合同之诉下向货方主张。《货规》废止后,“实际承运人”制度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法律制度体系中被移除,但实务中实际承运方在承运人委托或转委托下具体承运货物的业务安排并未受到实质影响。根据一般民事法律,由实际承运方造成的货损、货差、迟延交付,可以由承运人在《合同法》第311条、第290条、第107条等条款下向货方承担违约责任,承运人再基于同实际承运方的合同在《合同法》第64条*《合同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下追究其违约责任。实际承运方运输费用未获偿付的,可以基于其与承运人的合同安排*承运人与托运人签署运输合同后,通常会背对背地与实际承运方另签订运输合同或租船合同,偶尔也会出现代理或委托合同,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在合同中披露实际货方。如披露了货方及其支付费用义务(如运费到付),实际承运方运输费用请求除了依据其与承运人的合同约定,还可以依据《合同法》第65条的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向后者主张,在二者签订了运输合同的情况下,实际承运方并可依据《合同法》第315条对相应的运输货物行使留置权,承运人此后再依合同向货方追索。当然,对于货方货损、货差,或者承运货物给实际承运方造成的损害,双方可以在《侵权责任法》下向对方直接主张,*单纯的迟延交货所致“纯经济损失”,在中国目前的侵权法下尚难获得周全的救济,参见文献[26]第97页。但在举证责任与诉讼时效等方面与违约之诉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原《货规》中未做规定者,废止前后均适用一般民事法律规范。以诉讼时效为例。《货规》未有时效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18号),托运人、收货人就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者承运人在此合同项下向托运人、收货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另根据《指导意见》,上述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适用《民法通则》。在《民法总则》施行后,新法中止、中断的规定优先于《民法通则》相关规定而适用,如在新法下中断事由增加了“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这就涵盖了实务中申请支付令、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破产、申报债权、在诉讼或仲裁中主张抵销等情形。上述批复及《指导意见》是就违约之诉诉讼时效期间所做规定。由于目前调整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一般民事法律中未见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1号)第14条*该条规定:“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为由提起的诉讼,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与无正本提单提取货物的人共同实施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行为为由提起的侵权诉讼,诉讼时效适用本条前款规定。”这样的类似规定,无法得出国内水运侵权之诉与违约之诉适用同一诉讼时效期间的结论,这样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侵权之诉诉讼时效期间应为《民法总则》第188条下的三年而不是上述批复下的一年。这种规定的歧异,尤其是三年长时时效与水路运输市场快节奏流转的不合拍问题,期待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二)黑龙江中俄界河货物运输的法律适用
从法律角度看,中俄界河货物运输,在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起运港、目的港、航行水域等方面均具有国际性,涉及中俄两国不同的法域,在因货损、货差、延迟交货等方面产生法律纠纷时,两国法律均有适用的可能,因此,法律歧异带来的法律冲突不可回避。
1.中俄界河货运法律冲突
对于中俄黑龙江-阿穆尔河界河运输,俄方的适用法律为《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TheMerchantShippingCodeoftheRussianFederation, MSC)(下称“《俄商船航运法》”)。该法典第3条称,本法适用于海上以及内河水道(internal waterways)航行的海船(除非联邦加入的条约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在内河航行之内河船(inland ships)、在内河海上航线间航行并经停外国港口之江海两用船(mixed(river-sea)ships),据此,在俄罗斯法律为准据法的情况下,该法典第8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f Cargo by Sea, CCCS)”*《俄商船航运法》第115~176条。可适用于黑龙江-阿穆尔河界河货物运输。对中方而言,《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在国际运输方面无适用障碍,但在适用船舶上却存在一定问题。该法主要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或海江、江海直达运输*《海商法》第2条。,适用于黑龙江-阿穆尔河内部界河运输多少有些牵强;在运输船舶上,《海商法》适用对象为20总吨以上的海船,*《海商法》第3条。这对于界河运输中的河船、江船、飞翼艇、气垫船等各型船舶来说,适用《海商法》是有疑问的。因此,对于界河运输,在中国法律为准据法的情况下,目前可适用法律主要为《合同法》*原《货规》即便不废止也不能适用于涉外运输,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江河、湖泊以及其它通航水域中从事的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适用本规则”。,其第十七章“运输合同”适用于水路、公路等单式运输以及多式联运。
为对中俄水运法律有稍显全面的认识,界河运输适用法中亦将中国《海商法》相关条款纳入比较。对照《俄商船航运法》与中国《海商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两国法律有相同或相近之处。比如,《俄商船航运法》下,船长、船员、引水员管船过失(“航海过失”,navigational error)致损免责,就货物毁损灭失、迟延交付承运人享受单位赔偿责任限制,以及承运人受雇人、代理人在受托范围内致货损或迟延得援引承运人抗辩的权利(“喜马拉雅条款”)等三项规定,不适用于沿海运输以及涉边境的界河运输(coastal cargo carriage, cabotage)*见《俄商船航运法》第122、167、170、171(2)条。,这与中国《海商法》、废止前的《货规》的“双轨制”安排是接近的*见《海商法》第2条第2款、第51条第1款第1项、第56~59条。。中国《合同法》下,承运人代理人、受雇人过失(含航海过失)致损,承运人不得免责;承运人无责任限制的权利;该法亦未规定“喜马拉雅条款”。再如,《俄商船航运法》规定了承运人开航前、开航当时保持船舶适航的义务*这项义务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是不可通过合同当事人间的协议加以变更的(见《俄商船航运法》第124条第3款)。,这与中国《海商法》第47条的规定相一致。
两国法律亦存差别突出的规定。比如:《俄商船航运法》CCCS的规定除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外,也适用于国内沿海、内河以及边界水运输*上文提到的航海过失免责、海事赔偿单位责任限制与“喜马拉雅条款”(即承运人受雇人、代理人援引承运人抗辩理由的条款)除外,不适用于沿海运输(见《俄商船航运法》第122条)。,而中国则将沿海、内河运输与国际运输分轨,国际运输适用《海商法》,国内沿海、内河运输适用《合同法》等一般民事法律。《俄商船航运法》详细规定了托运人、收货人、第三人的“货物控制权”,中国《海商法》没有对此做出规定,《合同法》第308条尽管有补缺式的规定,*中国《合同法》第308条规定:“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但相对于复杂的水路运输,该条规定尚显不足。如在货物控制权主体方面,《俄商船航运法》下包括货物(含代表货物的单证)转让前以及船舶离港前的托运人以及货物转让后的收货人与第三人,*《俄商船航运法》第149条。而中国《合同法》下仅为托运人。《俄商船航运法》下承运人的责任基础均为附列明例外的过失责任制,除上文提及的航海过失免责不适用于cabotage以外,在责任基础上国际、沿海、内河运输统一;*《俄商船航运法》第3、166、167条。而中国沿海、内河运输下为严格责任制*见废止前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48条、《合同法》第311条。,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海商法》第四章则为附列明例外的过失责任制或称“不完全过失责任制”[29]。
《俄商船航运法》亦有诸多中国法下所未见的特色规定。比如:港口当局有权以命令(order)形式暂时停止或限制单式或(涉水)多式联运下的货物接收;*《俄商船航运法》第123条。租船运输下,当承租人未指定或未在适当时间内指定装货港或者所指定的港口并不安全时,承运人(出租人)有权拒绝履行运输合同并要求赔偿,该条规定不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俄商船航运法》第126条。中国《合同法》“租赁合同”章及一般民法并无船舶租赁的针对性规定。《海商法》第四章下的“航次租船合同”仅规定了出租人两项强制性义务*即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的义务,以及按照约定的或者习惯的或者地理上的航线将货物运往卸货港的不得绕航的义务(《海商法》第94、47、49条)。,至于船舶提供、货物提供、受载期限、滞期速遣、卸货港口、合同解除等项规定,仅在航次租船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海商法》第94条。更多体现出对运输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此外,《俄商船航运法》下尚有诸如甲板货、危险货物、提单海运单等运输单证、拒运权以及实际承运人责任*见《俄商船航运法》第138、151、142、143、155、156、173条。等详尽规定,而中国《合同法》等一般民事法律规定则显得颇为单薄。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实与推进,中俄界河货运常态化往来,两国界河货运相关的海商海事纠纷势必由偶发转为多发或频繁,如求诸诉讼或仲裁等法律程序,上述两国法律歧异便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法律冲突,需要务实应对。
2.中俄界河货运纠纷法律冲突的冲突法应对
对于中俄黑龙江-阿穆尔河海事海商纠纷,中方的专门法院是大连海事法院及其哈尔滨派出庭,俄方没有专门的海事法院,海上、通海水域货运合同等商事纠纷,由俄罗斯联邦商事法院审理。[30]
在中俄两国法院适用的冲突规范上,有必要讨论中俄92协议第3条:“协议双方船舶在对方水域和港口,应遵守该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规则。”
对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从狭义角度看,鉴于这份协议系两国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代表本国签署,本条“法律、规定和规则”应主要指称两国海事行政管理方面的规定*比如协议其他条款涉及的“引航”、“货运量”、“运输保证”、“船员/船舶证书”等方面的管理规定,以及协议项下边防、海关、卫生检疫等他项管理规定。。其二,两国船舶界河运输所生民商事关系(如货运合同、船舶碰撞等海商海事关系)适用法律是否包括在本条的“法律、规定和规则”当中,不够明确。如结合中俄98议定书第11条*该条规定,“中国船舶通过黑龙江俄罗斯河段时如出现争议问题应由海事仲裁委员会解决(莫斯科)”,结合该仲裁委的受案范围(下文论述),该条的争议仅包括民商法领域的海事海商争议。,这里的“法律、规定和规则”似应取广义而包括水路货运合同法等民商事法律。如果这一理解成立,本条应兼作中俄界河运输海事海商争议解决的冲突规范。船舶所在的“水域和港口”系该冲突规范下确定准据法的“客观联结点”,“现行”二字从时际法角度对新旧法律予以限定。这样,一旦中俄界河货运产生法律纠纷,无论诉请中国或俄罗斯的法院,均应遵照协议第3条,适用船舶所处水域或港口所在地的中国或俄罗斯当时有效之实体法律*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俄罗斯《民法典》第1190条规定,除非涉及自然人法律地位,根据俄罗斯冲突法所指引的外国法律仅仅为其实体法而不含其冲突规范。。
上述广义理解只是探讨,未见权威解释,也难查证相关司法实践*目前以中国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和俄罗斯阿穆尔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双边涉航主体,基本以双边内部协商方式解决包括运输争议在内的诸多议题。大连海事法院及哈尔滨派出法庭尚无中俄界河货运所涉海商海事纠纷成案审理实践。俄罗斯方面也未见以英文公开发布的相关案例。个中原因涉及诉讼成本、诉讼便利化、法律文化交流以及海事司法国际公信力等诸多方面。以供鉴别。
如果上述第3条应作为两国界河运输的统一冲突规范予以适用,那么时至今日,这条制定于1992年的冲突规范看似简明,但以一条基于船舶所在地为客观联结点的双边冲突规范去应对国际航运所涉货运合同关系、船舶碰撞侵权关系、船舶物权关系、船员劳动合同关系等多重关系类型,实则“简单粗暴”,既不便利法律选择,更无法保证公正的实体结果。以界河国际货运合同关系为例。合同准据法选择晚近的趋势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互补,主观联结点与客观联结点结合。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便顺应了该立法趋势。俄罗斯《民法典》第1210、1211条在此基础上甚至兼采“特征履行说”,详列包括运输合同在内的众多有名合同的特征履行方,以指导法院合理判定“最密切联系地”。如以广义理解并适用上述协议第3条,在界河运输合同争议中无视当事人通常的选法合意,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在中俄两国界河运输尚未订立统一实体法*1951年中苏签订《黑龙江、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松阿察河及兴凯湖之国境河流航行及建设协定》,并据此成立“中俄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简称“中俄航联委”)。相关资料显示,60余年来,中俄在中俄航联委平台上议定了6000多项涉及界河航运管理的协议,其中包括2009年达成的《中俄国境河流航行规则》,但尚未涉及私法领域的国境河流货运规则。的情况下,上述92协议第3条宜做狭义理解,在两国法院具体审理界河运输案件时可直接适用其本国冲突规范,这样更能达致案件的公正合理解决。
3.中俄界河货运纠纷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应对
从长远角度看,对于中俄常态化、规模化的界河货物运输,两国宜商讨缔结“关于中俄界河货物运输合同统一规则”方面的协定,具体内容可以借鉴《关于内河货运合同的布达佩斯国际公约》(TheBudapestConventionontheContractfortheCarriageofGoodsbyInlandWaterways, CMNI)*CMNI公约在统一内河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方面卓有成效。公约由欧洲经委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ssion for the Navigation of the Rhine, CCNR)和多瑙河委员会(Danube Commission)于2000年10月联合制定,于2005年4月1日生效。截至目前,共有18个参加国(participants),除摩尔多瓦外,全部为欧洲经委会成员国。参见文献[31]。。
首先,公约诸多规定体现了海上、内河水上运输(waterborne transport)规则逐渐融合的趋势,相关条款在中俄水运立法中亦多有体现,移植、整合的难度并不大。比如,CMNI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制度之设及其对内对外关系规定,与《俄商船航运法》第173条基本相同。中国原《货规》“实际承运人”制度尽管废除,但考虑到该制度在航运与司法实务中的重要性,修法重建的呼声很高。[32]
其次,在运输单证签发、承托双方权利义务配置、交货与收货等货运各主要阶段,公约制定了符合内河货运实际的合理规则,值得黑龙江-阿穆尔河货运借鉴。比如,公约下的运输单证系运输合同与承运人接管货物的证明,包括提单、货运单或其他商业单证等形式,而其“书面”亦含电报、电传、电邮、传真等诸多形式。*CMNI第1条第6、8款。又如,承托双方约定货物由特定(类型)船舶承运的,承运人应依照约定;但在低水位或碰撞等其他有碍航行的情事下或因遵照船舶所在地港口之通行惯例,承运人有权将全部或部分货物转船而无须事先征得托运人同意。*CMNI第3条第4款。交货时间方面,承运人应在约定时间内交付货物;若无此约定,则在虑及航次情况与航行阻碍因素对勤勉的承运人所能要求的合理时间内交付货物。*CMNI第5条。再如,根据运输合同或行业习惯或卸货港法律规定将货物交与收货人处置,视为“交货”;遵照法定要求将货物交与当局或第三方,亦构成公约项下之“交货”。*CMNI第10条。
再次,公约总体上的实体法规定与个别情形下的准用性规定相结合,体现了推动特定领域国际法治统一的灵活务实态度,契合中俄实际。如对于装前卸后货损的赔偿责任,公约规定受可适用于运输合同的国内法支配。*CMNI第16条。在时效方面,公约规定了一年的诉讼时效,被诉方可以书面声明予以延长;时效中断与中止,受可适用于运输合同的国内法支配。*CMNI第24条。
如果中俄能借鉴CMNI具体规定,结合各自相关立法,借助并充实中俄92协议第7条机制,在“中俄政府间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运输常设工作小组例会”现有平台上充实法治议题,或者借助“中俄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这一平台,商讨制定相关统一实体法规则,必将有力地促进中俄界河货运便利化。
(三)黑龙江-阿穆尔河江海联运的法律适用
黑龙江-阿穆尔河“中俄中”、“中俄外”江海联运途经不同法域管辖下的内河与海洋水域,其货运关系法律适用之核心在于完善冲突规范以协调法律冲突。
35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linical medicine: application and thinking
1.外贸江海联运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目前,黑龙江沿岸中方进出口货物多采取江船与海船在俄罗斯阿穆尔河出海口的庙街或附近海港换装的方式进行,在性质上属于多式联运[33]。以出口为例,多式联运经营人接受托运人一次托运,经过至少三段不同方式的运输方能抵达目的港,即黑龙江内河段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前段运输)、阿穆尔河段的俄罗斯国内水道货物运输(中段运输),以及海上货物运输(末段运输)。*在中国,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和国内水路(沿海和内河)货物运输适用不同的法律,承运人的权利义务不同,因而视为两种运输方式,符合《海商法》第四章第102条关于“多式联运”的定义。参见文献[34]。这三段运输,涉及多个法域:托运人、多式联运经营人以及前段运输所在的中国法域,中段运输所在的俄罗斯法域,*租用俄罗斯海船出海运输,亦即俄罗斯船舶所有人作为区段承运人时,俄罗斯法域在整个多式联运中的法律管辖利益不能忽略。相关争议如在俄罗斯涉诉,根据《俄商船航运法》第173条、《俄罗斯民法典》第1211条,俄罗斯船舶所有人作为船舶出租人或代理人受中方承运人之委托(entrust),实际履行区段运输,应被视为“特征履行方”,其所属的俄罗斯法律为“最密切联系地法律”而得到优先适用。以及海上运输区段相关联的法域;如考虑到收货人所在的其他法域,那么一宗江海联运,涉及多个法域的不同实体规定。在不同法域海事法律管辖权条款下,不同的权利人*如向托运人索偿运费的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了货方货损后向区段承运人追偿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向多式联运经营人或区段承运人索偿货损的托运人或收货人。起诉的法院地不同,各法域实体规定不同,这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法律冲突问题。
对于外贸江海联运法律冲突,在中国内地为法院地的情况下,应适用《海商法》第269条*见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条。:“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该条沿袭了当今主客观结合的“合同自体法”(proper law of the contract)基本趋势,但如何将当事人自主“选法”落到实处?如何在“最密切联系原则”下既赋予法官适当的裁量空间又给予其必要的适法指引?唯此粗线条原则,并不能给予包括江海联运在内的合同关系以足够的适法指导。
笔者尝试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框架下*根据《海商法》第102条,包括本文黑龙江-阿穆尔河外贸江海联运在内的多式联运合同规定在“海上运输合同”框架下。对多式联运法律适用提出法条完善建议。黑龙江外贸江海联运经识别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多式联运合同,直接适用这一条。
第N条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
1.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时或者订立合同后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并得在不损及合同效力以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至迟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前述选择。
2.除本款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应明示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
(1)合同载有当事人同意将合同项下争议交由某国(地区)法院审理或仲裁机构仲裁的,视为当事人同意该国(地区)法律适用于合同项下争议。
(2)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地区)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视为当事人同意该国(地区)法律适用于合同项下争议。
3.除当事人另有不同约定外,当事人选择的法律适用于合同是否成立、成立的时间、效力、内容的解释、履行、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的解除、变更、中止、转让、终止等争议。
4.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可以是有关国家(地区)法律、第三国法律或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唯所选择的法律须为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规范;当事人选择法律意在规避法院地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或者所选法律有悖于法院地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和/或善良风俗者,视为当事人没有做出法律选择。
5.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适用与合同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地区法律。如有疑义,则视以下地点所在国家或地区为最密切联系者,但合同明显与另一国家或地区有更密切联系者,不在此限:
(1)件杂货运输合同,承运人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或地区;
(2)航次租船合同,出租人或承租人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或地区;
(3)多式联运合同,多式联运经营人或区段承运人所在地国家或地区。
6.尽管有上述各款规定:
(1)合同履行方法符合履行地之法律规范者,亦为有效;
(2)在货物留置事项上应同时符合货物交付地当时有效的相应规定;
(3)法院地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强制性规定者,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
说明:
第一款涉及选法及变更选择的时间,借鉴了2005年《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6、47条,以及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第1款。
第二款涉及法律选择的明示或默示方式。我国以明示选法为原则*见《纪要》第46条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以“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见《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这种默示选法为有限例外;在海运实践中,如果没有明示的法律选择条款,管辖权条款和仲裁条款也可以成为确定默示选法的重要线索。[35]
第三款采用冲突法上的“分割”方法,规定了合同实质事项的准据法,这也符合当今国内外相关立法的基本趋势[36]。
第四款涉及选法的关联性以及“法”的范围界定问题。传统上,多数立法要求当事人选择法律需与合同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但晚近以来,尤其是海上货物运输领域,立法*中国《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7条即顺应了该趋势。与司法实践对此限制已经放松,盖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善意的意思自治以及因应国际贸易与海运业的发展趋势。作为必要的制衡,要求当事人选法不得恶意规避法律,不得损及至少是法院地的公序良俗。海上货物运输领域,出于对货主利益的维护,对限制或减轻承运人责任的法律选择,则多被视为违背法院地的强制性规定。至于将“法”扩及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也被视为更契合航运实际。[37]
第五款是“合同自体法”的“客观”板块,以“特征履行说”为基础,指导并适度约束裁判者自由裁量权,但为防止矫枉过正,另附“例外条款”做适度平衡。中国法律没有细化规定运输合同的特征履行方,对于本文讨论的外贸江海联运,联运经营人或区段承运人作为“特征履行”一方,其所在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通常应得到关注,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只有当承运人主营业机构所在地与货物装载地或卸载地同处一国时,推定承运人为特征履行方才是合适的”[38],所以此处设立“例外条款”很有必要。
第六款其实是本条的杂项条款,第1项合同履行的方式不必完全适用其自体法,可以在“分割法”下适用履行地法;第2项是“重叠适用”的法律选择规范,突出了海运留置权行使过程中货物交付地利益的维护;第3项是“直接适用法”在合同关系的径行适用,以维护法院地在个别特定事项上的核心利益[39]。
2.内贸江海联运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以下分两种情况探讨:
其一,纯国轮实施的“中俄中”内贸江海联运。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相关公告规定*根据交通部《关于开展黑龙江省内贸货物经俄罗斯港口运至我国东南沿海港口试点工作的公告》(2007年第11号)、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完善黑龙江省内贸货物经俄罗斯港口运至我国东南沿海港口试点工作相关政策的公告》(2013年第65号)以及海关总署相应公告安排,内贸陆海联运通道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出境(陆),借道俄海参崴港、东方港、纳霍德卡港(海),运抵上海、宁波、黄埔、泉州、汕头、洋浦、天津、大连等沿海港口。,借道俄罗斯海参崴港、东方港、纳霍德卡港的内贸陆海联运海上区段,在无“中国籍国际海运船舶”满足运输需求的情况下,经报备交通运输部,可由外籍船舶承运,但内贸江海联运未见官方相关授权与安排。这样,黑龙江沿岸港口经阿穆尔出海口与国内东南沿海港口间的内贸江海联运,除航经区段含阿穆尔河、鞑靼海峡、朝鲜海峡等国际水域外,承运人(联运经营人、区段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实际上均为国内主体,所涉法律冲突为国内法范畴,其核心在于中国水上货物运输法律“双轨制”下承担江海联运的承运人在法律上的身份定位,不同的身份定位会对应不同的“属人法域”及其下不同权利、义务配置,从而形成不同属人法域间的海事人际法律冲突。[40]
交通部《关于黑龙江过境俄罗斯至我国东南沿海港口江海联运有关问题的批复》(“交水发〔2004〕287号”),从海事行政管理角度将“经俄罗斯换装至我国东南沿海港口的黑龙江江海联运比照国内航线运输进行管理”。如果按此思路在私法层面将“中俄中”内贸江海联运定性为国内水路货物多式联运,那么适用法律为《合同法》第十七章下的“多式联运合同”及合同法下其他相关规定。
从船舶营运的角度看,黑龙江内河段属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无疑义;黄海及东海段运输视为沿海水路货物运输,亦可接受;但俄罗斯阿穆尔河段尤其是鞑靼海峡与朝鲜海峡段的运输,本质上与国际运输段无异。因此在私法层面将“中俄中”内贸江海联运比照国际运输似更合理,相应的,中国法下适用法应为《海商法》第四章“多式联运合同的特别规定”及该章其他相关规定。
《合同法》与《海商法》意义上的内贸江海联运经营人、区段承运人身份定位,会对应不同的权利义务。比较《合同法》第321条*《合同法》第321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和《海商法》第105、106条*《海商法》第105条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第106条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依照本章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规定负赔偿责任”。,二者均为“网状责任制”,但具体适用过程中有同,更有异。第一,在货损明确发生于黑龙江内河区段或中国沿海区段的情况下,两种身份定位均适用调整该区段的《合同法》,没有法律适用差异。第二,在货损明确发生于阿穆尔河段或鞑靼海峡、朝鲜海峡区段时,国内江海联运定位下,只能将该等域外区段比照域内水运区段从而适用《合同法》方合理;而在比照国际多式联运的定位下,该等域外区段为国际运输区段从而适用《海商法》。第三,在货损发生区段不明时,国内联运定位下应适用《合同法》;比照国际联运的定位下,应适用《海商法》第四章。
比较《海商法》《合同法》相关规定:责任基础上,《海商法》下的承运人对货损与迟延的责任基础为“不完全过失责任制”,承运人对“船长、船员、引航员或者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驾驶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过失”以及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火灾”所致货损与迟延,得免除赔偿责任;《合同法》下的承运人对货损、迟延,承担的是“严格责任”,上述航海过失与火灾过失致损不得免责。责任限额上,《海商法》第56条、第57条、第59条规定了海上承运人享受单位责任限制的权利、额度及丧失责任限制的事由;而《合同法》第311条以及《民法通则》第112条下的水路承运人应对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货物的损坏、灭失或迟延交付向托运人、收货人承担完全赔偿责任,除非承托双方对货物价值量事先商定,再依“合理预见规则”对完全赔偿原则加以限制。可见,国内联运与国际联运承运人的身份定位对应的权利义务差异明显,在具体争议当中,定位不同,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实体结果不仅仅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有无责任限制),甚至是赔与不赔的问题(如是否免责)。这对于黑龙江-阿穆尔河内贸江海联运船货各方来说,绝对不是可以忽略的小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鉴于上述“中俄中”内贸江海联运与包含海上运输区段的国际多式联运更为趋近,为培育联运线路,增强承运人抵御风险能力,降低营运成本,避免联运经营人、区段承运人身份定位上的模糊给争议结果带来不确定性与不公正性,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或完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司法解释时,就此设置单边冲突规范,以指导法律适用与航运实践。建议条款如下:
第N条 黑龙江沿线港口绕经俄罗斯出海口至东南沿海港口的内贸货物运输,参照适用《海商法》第四章第八节的相关规定。
其二,有外轮参与的“中俄中”内贸江海联运。
实务中若租用了外轮(如俄罗斯江海两用船或海船)参与内贸江海联运,并产生法律争议(比如承担区段或全程运输的外轮致损或运费未获支付),如何适用法律?
如诉诸中国法院,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国际多式联运制度进行识别,进而在前述单边冲突规范指引下适用《海商法》第四章第八节。
特定情形下,相关外国法律对联运争议也会有管辖利益。现以俄罗斯法律为例。根据俄《民事诉讼法典》第五编“涉外案件的诉讼程序”第398条,外国自然人或组织有权诉请俄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且与俄自然人、组织一样享有所有程序权利并履行相应程序义务。在管辖方面,根据法典第29条第1款,如果俄方区段承运人致损,作为被告,其财产所在地、现居所地或原告知悉的被告最后居所地法院均可以受理案件;而根据该条第9款,在合同载明履行地的情况下(如合同订明俄方船舶自庙街转船后承运海运区段),则履行地法院可就合同各项争议行使管辖权。如果相关争议在俄商事法院涉诉,依据法院地冲突法(俄《民法典》第1210、1211条),如确定俄法律为准据法(如基于合同约定或俄区段承运人是“特征履行方”),则应适用《俄商船航运法》第174条“货物联运”及相关法律规定;如经法院地冲突法指引应适用中国法(如基于合同明确约定),而中国法律就此存在“双轨制”规定(也就是存在国内属人法冲突),俄法院需要进一步就此做出选择以最终适用相关实体规范。
行文至此,有必要讨论一下中俄98议定书第11条,“中国船舶通过黑龙江俄罗斯河段时如出现争议问题应由海事仲裁委员会解决(莫斯科)”。
对于本条“争议问题”,结合俄罗斯联邦工商会海事仲裁委员会(The 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MAC)的受案范围*MAC初始组建旨在解决海上运输过程中船货海难救助所生争议,如今其受案范围已涵盖海上货运合同、租船、海上保险、船舶碰撞、捕鱼作业等传统海商海事纠纷,以及经纪、代理、船舶维修、船舶管理、贸易实现和其他海上运输领域出现的诸多海商争议。参见文献[41]。,应理解为江海联运合同项下及相关之海商海事纠纷。对于“应”,从作准的中文字面理解,系指从事“中俄中”内贸江海联运的中国船舶(含当然解释下租用之俄罗斯船舶)在俄水域发生前述争议问题,(如不能自主协商解决),需在议定书指定的MAC通过仲裁解决。
但这似乎有些问题。首先,根据中俄《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1条以及中俄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根据俄《民事诉讼法》第403条第1款第2项,对于涉外船舶运输(托运)合同纠纷,如托运人(不论国籍)位于俄联邦境内,即便是中方当事人(如承运人、实际承运人)也可直接向俄法院起诉;而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俄方当事人就相关争议在中国法院起诉也有多种管辖权联结点供选择。,两国当事人在对方法院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并无法律障碍;议定书第11条以特别法规定将国际民事诉讼排除,可能意在发挥国际商事仲裁的比较优势,但也欠妥当。其次,仲裁程序以当事人仲裁合意为基石,而不能受制于强制性管辖,MAC在其最新仲裁规则(2017年1月27日)第3条亦强调提交其仲裁的争议需基于当事人之合意,因此本条绕开当事人合意而径行指定MAC仲裁,同样欠妥当。另外,如果原被告均为中国主体,双方可供执行的财产也位于中国境内,仅仅因为途经俄水域发生争议(如承运货物落水或湿损),就排除中国法院的管辖,指定到莫斯科MAC仲裁,则有武断之嫌。诚然,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对其境内涉外货运等经济活动行使(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协议中应予尊重;但对于其间发生的国际民商事争议,可否适当淡化国家主权色彩,更多彰显法院、仲裁机构在(准)司法供给侧对国际民商事主体的服务功能?在两国元首力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的背景下,这一点值得关注。
为此,笔者建议:两国相关部门洽商该议定书项下议题时,可以考虑删除该条款,而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争议解决方式,并注重发挥两国现有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作用,更多彰显两国(准)司法机构的服务功能。
三、结 语
在中俄政治互信、战略互信牢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中俄及周边经贸合作不断提升层次的大势下,包括黑龙江-阿穆尔河货运在内的物流通道建设日显重要。通道法治建设作为其中有机组成部分,需深入研究、同步落实。本文就黑龙江-阿穆尔河内河货运、界河货运、内外贸江海联运法律适用问题的点滴思考,是通道法治建设题下的粗浅尝试,期待业界专家斧正并引领相关领域研究,以助益中俄友好及区域合作大局。
[1]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2.
[2]仲维庆,王红,苑维忠,等.黑龙江水运港口发展分析[J].北方经贸,2011(8):21.
[3]朱晓峰.黑龙江水系港口布局规划战略思考[J].中国港口,2008(7):23.
[4]赵要德,冯洁.浅议与我国能源项目有关的政府间协议[J].国际石油经济,2014,22(5):91.
[5]邹伟宏,李大海.中俄界河航运安全监管现状及建议[J].珠江水运,2014(11):64.
[6]张玉芬.黑航集团开通中俄首条内河国际集装箱航线[J].交通企业管理,2006(11):44.
[7]李会.中俄界河首次液化石油气水路运输正式开通[J].中国海事,2014(7):81.
[8]潘世常.黑龙江水系中俄船舶联合运输改进对策[J].水运管理,2005,27(7):7.
[9]张国良.试论黑龙江水运走向海洋战略[J].龙江社会科学,1994(2):28.
[10]曹宇,汤震宇.浅析黑龙江省粮食水上跨境运输发展对策[J].黑龙江交通科技,2012(4):103.
[11]朱晓峰.黑龙江水系江海联运发展策略[J].水运管理,2008,30(2):2.
[12]孙浩进,周薇.黑龙江省构建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瓶颈”与对策[J].西伯利亚研究,2015,42(4):21-23.
[13]师伟.大力推进黑龙江江海联运[J].中国水运,2008(4):15.
[14]倪伟龄.黑龙江开通重大装备江海联运[N].经济日报,2008-09-03(9).
[15]张俊澎,陈渌.江海联运大件运输新航线开通 黄金水道开辟“掘金”新路线[N].黑龙江日报,2009-02-26(3).
[16]李勇.黑龙江江海联运首次实现往返运输[EB/OL].(2009-11-04)[2017-09-22].http://www.jjckb.cn/cjxw/2009-11/04/content_189027.htm.
[17]吴刚.对接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给力[N].国际商报,2015-07-06(A07).
[18]李民峰,刘亿服,孙昊,等.口岸通道建设提速 区域物流中心崛起[N].黑龙江日报,2015-05-11(1).
[19]陈秋杰.黑龙江省开展对俄物流合作研究[J].西伯利亚研究,2015,42(2):18-20.
[20]彭凤莲.中国自贸区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3(2):141.
[21]黄进.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制定与完善[J].政法论坛,2011,29(3):3.
[22]金鑫哲.《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止后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7:6-12.
[23]孙思琪,陈博雅.《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止的影响与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2):8.
[24]南风艳.我国水路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的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3:22-24.
[25]黄毅.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适用[J].世界海运,2013,36(1):53.
[26]郑晓哲.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的突破[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1.
[27]刘胜军.论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从“指导案例51号”切入[J].法商研究,2017(5):133.
[28]张国军.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实际承运人责任探析[J].世界海运,2014,37(11):46.
[29]李天生.国际海上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反思与重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27(7):59.
[30]KRASNOUTSKIY K. Shipping Law 2017, Russia[EB/OL].[2017-10-08].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shipping-law/shipping-2017/russia#chaptercontent2.
[31]Budapest Convention on the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Inland Waterway (CMNI)[EB/OL].[2017-09-17].http://www.unece.org/trans/main/sc3/sc3_cmni_legalinst.html.
[32]侯伟.关于将内河货物运输纳入《海商法》调整范围的立法建议[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28(3):16.
[33]胡正良,赵阳.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6.
[34]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12.
[35]王国华.海事国际私法专题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188-189.
[36]CHAN F W H, NG J J M, WONG B K Y. Shipping and logistics law: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149.
[37]余妙宏.论海商法中国际惯例的性质与地位——兼论对《海商法》第268条和269条的修改[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7,17:136-137.
[38]BLOM J. Choice of law methods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tract[J].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1980, 18: 187.
[39]屈广清.屈广清新论文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25.
[40]周新.“双轨制”与海事人际法律冲突[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25(1):110-120.
[41]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at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EB/OL].[2017-10-14].http://mac.tpprf.ru/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