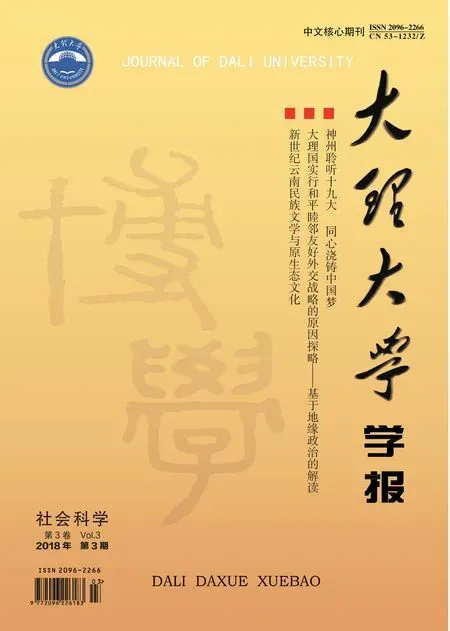凯鲁亚克的信仰嬗变历程探析
祝 昊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 450000)
“若试图了解凯鲁亚克的写作方式,必不可少地要考虑到他深刻的宗教情结”〔1〕。一直以来,宗教的维度对凯鲁亚克有着深远的影响,佛教与天主教两种信仰交错混杂,或隐或显、或主或次地影响到他的人生,同时这种矛盾的宗教情结也始终贯穿在其文学创作中,为其作品平添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凯鲁亚克早年经历了天主教信仰的失落,选取了来自于东方文明的佛教思想为其“第二次宗教信仰”,他一再地宣称“在佛中,我找到了我的庇护,在佛法中,我找到了我的庇护”〔2〕。然而,佛教的庇护还是未能让凯鲁亚克远离充满苦难、瞬息万变的残酷现实,使得他无论是在精神信仰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最终都回转到原初的天主教信仰的轨道,完成了从佛教信仰向天主教信仰的迂回复归。
一、向“垮掉禅”告别
在现代社会中宗教日益世俗化的大趋势之下,宗教已由以教会为制度基础的信仰转化为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信仰。凯鲁亚克也与普罗大众一般,在个体灵魂沉陷于消费社会的深渊里始终无法得到解救之时,冀望于借助原始的东方宗教的力量使自我灵魂得以解脱,藉以抵抗林林总总的现代性危机。然而,由于凯鲁亚克对佛教的消费者取向,使得他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理解,既有忠实的传递,又有创造性的叛逆,同时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谬误。于是,凯鲁亚克的佛禅信仰以及其作品中所体现的佛禅思想,就被学者形象地称为“垮掉禅”。所谓的“垮掉禅”是由著名的比较宗教学家阿伦·瓦茨在《垮掉禅、传统禅和禅》中提出,主要指出了垮掉派的佛禅思想所具有的格外关切自身,较为主观随性,以禅味视之颇感突兀等特点。虽然凯鲁亚克“通过直觉和研习般若波罗密多的经文,在其作品里深切体会到‘最高的完满智慧’”〔3〕,从而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形成独特的文学风格,但同时也使得他对佛教元典无意的误读和有意的曲解变得不可避免。例如《达摩流浪者》中所提及的《金刚经》原文就颇有杜撰之嫌,而《孤独天使》中甚至无法将佛教和道教的概念明确区分,以至出现了“客人须是佛教徒,能够理解‘道可道,非常道’”〔4〕159之类的谬误。其实对凯鲁亚克而言,经义上的差别无关宏旨,他所需要的只是在作品中有着与众不同的佛教的思想,正如他写作《达摩流浪者》的目的一样,作为《在路上》的续集,这部小说主要的卖点,即其佛教主题——只不过是作家作为自主的消费者,从可以获得的聚积中遴选出的宗教主题,并将它注入私人“终极”意义系统之中,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
众所周知,佛教和禅宗的思想与天主教迥异,它的教义支持将许多放浪行为视作追求解脱和自由的手段。一旦将佛陀的形象摆到台前,诸如吸食毒品、饮酒狂欢等行为在佛陀的荫庇之下都能获得合理的解释,乃至种种腐化堕落、疯狂叛逆的行为皆可被当作超凡入圣的举动。如《达摩流浪者》中,贾菲等人的性行为仅因采用了佛教中结跏趺坐的姿势,便被贴上了“雅雍”的标签,从而被描写成为神圣的仪式。不难看出,他们所喜爱的也仅仅是禅宗的自在自为能为他们的荒唐淫乱提供冠冕堂皇的说辞。垮掉禅虽扭曲了禅宗本身,却恰好成为成功地冲击了主流价值观,动摇了清教传统之后,凯鲁亚克反抗世俗成规,向传统价值标准进行挑战的有力武器。他将佛陀推向台前,主张将佛禅思想确立为社会的主流,藉以填补信仰的真空。凯鲁亚克借用佛禅思想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并将其无限放大,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例如在《达摩流浪者》中,凯鲁亚克就通过对禅僧寒山形象的塑造,不遗余力地去凸显自己的意图。在小说中,寒山并非作为人物出场,而是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出场,他象征着绝对的自由,代表着主人公希冀达到的大彻大悟的境界。对凯鲁亚克而言,寒山只是众多文学意象之一,是所要表达的思想具象化的体现。寒山及其所代表的佛教思想,也只是作家反抗世俗权威的干扰和制约,标榜自我的价值和追求的有力武器而已。
在垮掉禅里,礼佛参禅只是解脱灵魂的手段,与吸毒纵欲等极端行径别无二致,然而在与世俗狂欢交融的表象之下,在这“台前的佛陀”身后却一直隐藏着一位“幕后的上帝”。霍姆斯在为《垮掉的一代》作序时说:“我们看到了对神的热爱和对神的敬畏——虽然凯鲁亚克耽溺于佛禅和东方哲学,但是他始终无法摆脱天主教的涵濡。”〔5〕诚如斯言,在凯鲁亚克文学生涯后期的所有作品中,在“佛陀”的身后都能看到“上帝”的身影,其作品中将基督与佛祖等量齐观的例子比比皆是,无论是《孤独天使》中的杰克,还是《达摩流浪者》中的雷,与其所信仰的佛教禅宗之间都绝非虔诚的信靠关系。他们对于佛教禅宗的信仰,本身就和对上帝的信仰是紧密相连的:“‘今天晚上,我要在星空下祈求上帝,让我可以完成我的佛工和获得我的佛性。阿门’……‘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佛’”〔6〕。宗教的终极目的是寻得解脱,无论是基督教的来世还是禅宗的今世,真正的宗教信仰要求更加地投入、无私和超然,也要更加地盲目和无我,要融升华、献身、神圣、忠诚于一体。但凯鲁亚克却无法做到,正如雷所说,他无法“忘记自己”、无法摆脱天主教信仰对他的濡染。所以,当在佛教之中始终无法获得心灵的依靠之后,他不得不抛弃“台前的佛陀”,重新皈依“幕后的上帝”。
其实,在《达摩流浪者》中已能初步看到凯鲁亚克对其佛教信仰的背弃。在小说开端,尽管雷屡次标榜自己是严肃的佛教徒,但天主教传统的影响依然作用于他的身上,使其难以解脱,对现代社会中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迷恋也让其无法专注于佛教信仰,获得灵魂的解救。所以在小说尾声,凯鲁亚克通过摩西在西奈山上的典故,向读者暗喻出雷的最终抉择。而在之后的创作中,凯鲁亚克展现自我选择的方式更为直白。例如在《孤独天使》中,他不仅直接地否定了自己的佛教徒身份,更是直接地否定了自己的佛教信仰,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母亲一样与上帝保持联系”。在凯鲁亚克的垮掉禅里,佛教和天主教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在所难免。然而一旦当“台前的佛陀”退场,“幕后的上帝”重新走上前台的时候,他便开始向垮掉禅告别,正式踏上了向天主教传统回归的道路。
二、向“十字架”回归
事实上,佛教对于凯鲁亚克而言仅具有观念上的性质,无论是在思维模式上,抑或是在心理需求上他都更倾向于天主教,因为凯鲁亚克始终都只是将佛禅思想视作抗拒传统生活方式,回归存在本真的有效模式。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向天主教传统回归,并在文学创作中以向“母亲的身边”“永恒的牧歌”以及“十字架”的回归表现出来。
告别在路上的生活,回到母亲身边正是凯鲁亚克向天主教传统回归,完成信仰归正的第一步。对凯鲁亚克而言,身为天主教徒的母亲便象征着天主教信仰,母亲的存在便意味着天主教传统的存在,“母亲的身边”是他最后的避难所。故而“母亲”一直是其文学创作中重要的意象,无论作家在作品中是以萨尔、杰克,抑或是别的身份出现,在每次浪迹天涯后,他都是回归母亲身侧。如在早期的《在路上》中,萨尔徘徊于以迪安为代表的放浪形骸的世界和由母亲所构成的安稳宁静的世界间,一次次地回到母亲的身边,又一次次地选择了再次上路。随着凯鲁亚克在宗教信仰上的变迁,在中晚期的创作中,回到“母亲的身边”的愿望表现得十分强烈。在《孤独天使》的结尾,当杰克以疯狂的方式去逃避恐惧与绝望的努力失败之后,当无法再在充满新鲜感的佛教信仰中寻得灵魂的安宁之后,他最终选择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天主教传统当中,因为每当回到母亲身边时,他都能看到“母亲正低着那安静而永远弯曲的头颈,为他们缝补着染血衬衫上的裂口——母亲从来不会摆出一副殉道者的姿态,也不会说出任何抱怨,她似乎正沉迷于某种高于缝补的境界,似乎她正缝补痛苦、荒唐和所有失去的一切,以决然的快乐和沉重缝补你每天的生活”〔4〕380。虽然在一开始,杰克觉得重新回到原初的信仰十分荒谬,可他却无可奈何,“我向早已在坟墓中化成粪土的父亲祈祷——我知道这很荒谬,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向他祈祷……这正是我继续生活的原因,也正是我母亲继续生活的原因”〔4〕385。坟墓里已经化为粪土的父亲,象征着已经失落的天主教信仰,而这却又是一直支撑杰克和他的母亲继续生活的原因,无论是在路上疯狂的漫游,还是对达摩禅理苦苦的追寻,都不能使杰克摆脱苦难,他所能做的只有重拾原初的信仰,回到“母亲的身边”。
在“父亲的世界”失落之后,幕后父亲的形象还是时隐时现,便已暗示着凯鲁亚克对失落的人类伊甸园的无限眷念,他开始了对“永远牧歌般的乡村生活”的追寻。对宗教徒来说,他们可以觉察到空间的非均质状态,而这种空间的非均质状态,正是在神圣空间与非神圣空间的对立中体现出来的。在《科迪的幻念》中,当科迪跨过墨西哥的边界之时,他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我能看见上帝之手。未来属于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在阿克多班,出现了如同《圣经》里才有的高原——只有怀着大山般崇高的信仰才能到达。我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会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7〕当科迪刚一跨过美墨边境,他立即发现了那里有着不为人知的乡村意识,立即识别出了墨西哥教会神父所体现出的圣经式父权形式。他立即识别出了非神圣的美国和神圣的墨西哥之间的差别,于是他渴望生活在这样充满神圣性的地方。而他希望在其中安置住所的渴望,正是他对生活在神圣中的渴望,是对自己不被纯粹主观体验的相对性所困惑的渴望。然而渴望回归永远牧歌般的乡村生活,并不仅是对存在于纯净和神圣的空间中的渴望,还包含着对身处于纯净和神圣的时间中的渴望。在凯鲁亚克看来,曾经的在路上生活、对异教的皈依等行为都象征着从有序向无序倒退。所以他希望在时间上回到母亲的子宫、回到婴孩的样式、回到起源的时刻,只有如此,他才能与曾经的“创世记”时间结合,将自我从罪恶和失败的桎梏下解放。其实,不论是对失落的人类伊甸园的眷恋,还是对永远牧歌般的乡村生活的追寻,凯鲁亚克所表达的都是对恢复到诸神生机盎然的存在状态的渴望,他希望能够重回天主教传统中,让生活像刚从造物主手中诞生出来时那样崭新和纯净。
在最后的小说《大瑟尔》中,凯鲁亚克则不采用任何的象征或隐喻,直截了当地描绘了对“主的十字架”的回归:“我看到十字架,它没有声音,我的心为它出窍,我整个身体向着它消退,我展开双臂让它将我带走……然我又看见十字架,我冲破那些喧闹的声音说‘我和你在一起,耶稣,永远,谢谢’——我一身冷汗躺在那里想知道这么多年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什么,我学佛和抽烟确保了在‘空’的状态中冥想可十字架突然出现‘我们都将获得拯救’。”〔8〕在凯鲁亚克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创作都是为了完成向“十字架”回归这一最终的目的。他希望通过写作进行忏悔,而最终,凯鲁亚克以标准的天主教葬礼结束了对佛教的信仰,在主的十字架下得到救赎,完成了对天主教信仰的最终回归。虽然从表面看来,凯鲁亚克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从天主教到佛教再到天主教这样一个从反叛到回归的过程,但从深层来说,他对上帝的信仰却从未停止,他对上帝裸露灵魂、与上帝直接对话、期待圣灵的充满的渴望也从未中断。正如阿伦·瓦茨在论及西方人对佛禅信仰的接受时所言:“对禅充满兴致且有透辟见解的西方人士务必具有某种至关重要的禀赋,他须对所处的文化系统有着透彻的了解,从而才能在潜意识中规避此种背景所带来的熏陶濡染;他须真正地同上帝以及自我的希伯来—基督教意识达成契约,从而才能无所畏惧以及背叛地接纳与拒斥”〔9〕。作为反例,他特地举出了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禅”,认为这一群体在本质上与基督徒别无二致,只不过是以佛教禅宗之名,行求索基督圣迹之实。
三、结语
尽管凯鲁亚克在佛禅思想中寻觅到诸多与自身观念相投契之处,但他对佛禅的体验依然停留在癫狂放纵的层面,对佛禅的研读也更多地停留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他始终秉持的都是源自于天主教的一神论思想,并最终在禅宗的开悟和上帝的赐福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佛教所谓的自我拯救仅仅是要把自己从一切此在,包括社会此在和自然此在中抽身出来:这种获救,追求者只要依靠其独自愿望和思考就可以获得。如果追求者满足了完全扎根在其灵魂观念中的条件,获救也就得到了。佛教的惟一内容就是要把个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且不需要任何超验的力量”〔10〕。加之凯鲁亚克的佛教信仰只是一种表层化寄托,这就决定了作为宗教信仰,佛教始终无法像天主教那样为凯鲁亚克提供终极的信靠或依托,而只能行使临时的“非宗教”的精神寄托功能。因此,在佛教这种显性的反叛之下,凯鲁亚克因袭的还是天主教这种隐性的传统,这就决定了即便是在对佛教兴味盎然之时,他亦冀望于能够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主宰一切,冀望于借助这种超越俗世却为俗世所期望的“设定的存在”来弥合灵与肉的裂痕,从而告别“无神的黑暗”。
〔1〕NICOSIA G.Memory babe:a critical biography of Jack Ker⁃ouac〔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3:326.
〔2〕比尔·摩根.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M〕.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386.
〔3〕JOHNSON K,PAULENICH C.Beneath a single moon: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M〕.Boston and London:Shambhala,1991:95.
〔4〕杰克·凯鲁亚克.孤独天使〔M〕.娅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5〕杰克·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M〕.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6〕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M〕.梁永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35.
〔7〕KEROUAC J.Vision of Cody〔M〕.New York:McGraw Hill,1972:221.
〔8〕KEROUAC J.Big Sur〔M〕.New York:Viking Penguin,1992:206.
〔9〕WATTS A.Beat Zen,Square Zen,and Zen〔J〕.Chicago Review,1996,42(3∕4):48-55.
〔10〕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