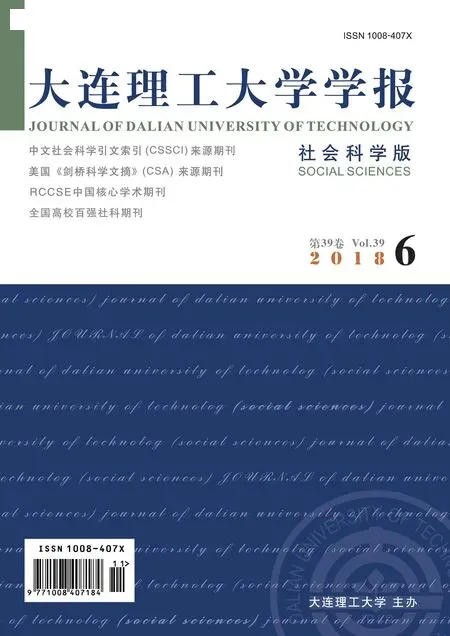庄子哲学中的“真人”与“真知”及其关系探微
杨 锋 刚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真人”与“真知”是庄子哲学的基本观念,对“真人”与“真知”的揭示和彰扬,庄子不仅向我们提示了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境界,而且促发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存在境况与知识追求。这一独特的思想方式无论对于理解庄子哲学本身,还是对于我们今天的生存方式和知识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真 人
人何以为人或曰人的自我理解,是先秦诸子人文致思的核心主题。庄子的“真人”,正是这一思想语境中出现的对于人之“应然”的诉求和理想。因此,要理解庄子“真人”及其独特意义,有必要回顾一下庄子之前及其同时代的哲学思想对人的理解和规定。
大致说来,在庄子之前,中国哲学思想对人的理解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思路。在孔门儒学那里,人的规定性是在人文化成的向度上,围绕德性伦理而展开。这样一种思想传统,由孔子所开启,经过孔门后学的承续并在不同层面上的彰扬,长期以来弥贯和流淌在儒家思想的精神血脉中,成为儒学的思想内核和价值追求。《吕氏春秋·不二》曰:“孔子贵仁”[1]。在孔子那里,“仁”并非某种抽象的道德法则,也不是某种具体的特定形态,而是在一个人的现实生命活动中,通过他的立身行事而表现出来的“成人”之道。总体而言,孔子之“仁”开启的是一个人之为人的意义境域和价值方向。诗、礼、乐的修习和陶养是“成人”的基本要素,而贯穿于这些基本要素之灵魂的,乃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真诚无伪。孔子之后,《中庸》进一步从天人之际的向度显微阐幽,高扬“性与天道”的贯通,明确提出“仁者,人也”,并以“诚”作为天道与人道相贯通的内在依据,奠定了儒家心性论的形上基础。孟子远淑孔子之“仁”,近承《中庸》之“诚”,进一步将“仁”与人合而为一,统一于道。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又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又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在孟子看来,此仁义之道,即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性。孟子指出,仁、义、礼、智四端,乃是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本性,就如同人生而具有四肢一般。由此四端之心,奠定了儒学人道与人伦的根基。在现实文化的层面上,礼义就成为仁、义、礼、智所表征的人道价值的承担者,从而凝定为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正如《礼记》中反复申述的:“凡人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曲礼》)
与孔门儒学在人文化成的向度上成就人之德性生命的思路不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在天道自然的维度上开显人的自然本性。在老子看来,儒家所倡导并高扬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并非道德本身,相反,恰恰是大道消隐的产物,是对人之源初道德本性的背离和遮蔽。它非但不能成就人之道德生命,反而使人日益远离道德本身,生存于非道的状态之中。在老子那里,道最根本的命意乃在于自然,而自然则意味着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真实本性。在老子看来,人的自然本性不断地陷溺于耳目鼻口等感性欲望,以及巧伪诈利、仁义圣智等世俗价值之中,真实的生命被湮没。因此,老子主张“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通过“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等“日损”的“为道”方式;“致虚”、“守静”(《十六章》)、“知足”、“知止”(《四十四章》)等心性修养工夫返朴归真,回复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老子笔下的“为道者”就鲜明体现了人的天真自然的生命情状和真朴博大的生命境界。这一思路在庄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在先秦思想史上,庄子首次提出“真人”,来寄寓和表达他的人性和文化理想。在庄子那里,“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庄子哲学的标志性范畴和核心价值。在庄子之前的文献中,除了《老子·二十一章》中的“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一语外,其他地方尚未见到。“真”的明确并大量使用,始于庄子。粗略统计,《庄子》全书共有60多个“真”字,主要关涉于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如“真人”“真性”“真君”“真宰”“真知”等。在《庄子》文本中,对于“真”的最为集中的描述,大概要数如下文字: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
尽管《渔夫》不一定就是庄子本人所作,但上述关于“真”的描述却非常契合庄子思想的精义。一方面,“真”意味着“精诚之至”,与伪相对。伪表现为人的行为的虚假造做,如“强哭”“强怒”“强亲”等,它因缺乏内在生命的真诚而沦为虚假的表演,从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另一方面,“真”意味着“天”,是天真自然的内在本性,与俗相对。俗既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世俗欲望的奔逐,也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世俗文化价值。伪与俗虽然在不同层面上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但在根本上都是人为的、非自然的,因此是非真的,是对“真”的背离、扭曲和遮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之“真”被各种各样的“伪”和“俗”所遮蔽,由此导致人的现实生存的颠倒,庄子称之为“倒置之民”(《缮性》)。
此外,庄子还通过“天”与“人”的区分来突显自然之真与人为之伪的对立,彰显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性。在《秋水》篇,河伯问北海若:“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回答:“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牛马四足,这是牛马天生自然的本性,而用辔头络马首,用缰绳穿牛鼻,却是人为对自然的强加和伤害。“反其真”就是返回到其天生自然的本然状态。而要回到其天生自然的本然状态,就要层层抖落人为之“伪”与“俗”对自然之“真”的遮蔽。成为“真人”,就是人的心灵和精神不断突破现实流俗层面的欲望、知识、名利、观念、价值等等的“伪”与“俗”的桎梏和枷锁,让真实的性命之情层层超拔透显出来,回归自己天生自然的内在本性,从而获得无往而不在的自在与自由。“自由而自在是人之自然本性,在自然状态,人之本性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2]
在《大宗师》篇,庄子集中刻画了“真人”形象: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如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
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颒。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此外,在其他篇章,庄子对“真人”的生命情状也多有揭示。在庄子看来,“真人”超越了世俗经验世界的欲望、利害、得失、计较、毁誉、分别、生死等的桎梏和枷锁,他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律动完全顺应和体现着道。因此,“真人”并非某种抽象的人的观念,也非某种特殊的人的形态,更不是某些特异之士,而是在根本上回到了人的天真自然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开显出的一种与道同在、与天为一的生命境界。
二、真 知
正如以“真人”作为人性的理想,在知性领域,庄子提出“真知”作为人类知识探求的目标和价值方向。在一般意义上,知被看作是人对世界的认识、经验、理解和判断。但在庄子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知,遗忘了人的生命存在本身,不断滋长着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分裂和疏离。在此意义上,我们所知愈多,反倒离真实的存在愈远。因此,庄子对“知”的关注和思考,并非出于纯粹的知识或理论兴趣,而首先源于对人的存在境况的反思与洞察。严格说来,在庄子的思想世界中,“知”并不是指知识,而是“知”本身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揭示“知”与人的生命存在的关联。
在庄子那里,“知”在根本上表现为对人的存在境况的揭示,不同层次的“知”始终与不同层次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境界相关联[3]。在庄子看来,一般人沉溺于日常世俗经验世界的奔逐,他们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外部世界的种种经验性认知。这些经验性知识,直接与“欲”和“技”相关联。一方面,作为欲望性的存在,一般人求知无非就是追求口腹耳目之欲的满足。感性欲望的不断膨胀牵引着人殚尽思虑、劳形怵神、身为物役、心为形役,最终“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另一方面,这种知作用于对象世界,就产生了“技”。《天地》篇那位抱甕取水灌园而不愿使用省力机械的汉阴丈人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定不生,神定不生者,道之所不载也。”由“技”衍生的“机械”“机事”,不断激荡和滋长着人的“机心”。“机心”的蔓延,侵蚀着人的淳朴自然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层层遮蔽了“真心”的光明,破坏了人原初的生命感知能力,使人无法真实地去感知、体验和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同时,“机心”又会进一步催生“巧”“伪”“诈”等功利机巧性活动。这样的知不仅助长着人的利欲之心,而且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纷争的工具和手段,如《人间世》所谓:“知也者,争之器也。”如此一来,人被各种各样的欲望以及由之而来的虚妄价值所迷惑,而日渐丧失了原初真实的性命之情。
除了与“欲”和“技”相关的“知”,人类的经验习性和文化观念等也构成了“知”的各种不同形态。在庄子看来,人在获得一定的知识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滋长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学一先生之言则暧暧姝姝而私自悦也,自以为足矣。”(《徐无鬼》)由此“自以为足”的心态,逐步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思考方式,庄子称之为“成心”。他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齐物论》)成玄英疏曰:“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4]29林云铭亦曰:“成心,谓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见在胸中,牢不可破,无知愚皆然。”[5]可见,“成心”就是偏见以及对于偏见的执著。“成心”在不同程度上限定着人看待世界的基本视域,并成为人评价世界的基本尺度。“成心”不断固化着人的封闭、狭隘的心态,造成心智的封囿和枯竭。就如《秋水》篇的河伯,拘限在自己的狭小天地,却“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已。”如此一来,人便无法感知到世界的真相。“当世界被成心,因此被不同的‘我’所包围,被意见和偏见所包围的时候,一切都笼罩在假象中。与此同时,真实的世界却隐藏起来。”[6]不仅如此,大多数人却认认真真地生活在假象中,在偏见和是非的漩涡中扩散和膨胀着各自的欲望。徐复观曾深刻指出:“在中国缺乏纯知识活动的自觉中,由知识而来的是非常与欲望而来的利害纠结在一起。”[7]
庄子指出,人总是生存于特定的时空境域之中,不同的境域决定了人“能知”和“所知”的限度,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游》)同时,世俗文化价值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并内在制约着他的思维方式和生命境界。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庄子》文本中从许多不同层面揭示了这一点,如《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辨、有用无用之辨;《齐物论》中关于“觉”与“梦”“正处”“正味”“正色”的拷问;《秋水》篇濠梁鱼乐之辩等都深刻揭示了由不同的存在境况和生命境界而来的“知”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与上述之“知”直接相关于感性欲望和现实功利不同,以惠施、公孙龙等为代表的名辩学派的知性探求似乎具有某种超功利性,成为“知”的另一种形态。《天下》篇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并说“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可见惠施对此类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天下》篇还详细列举以桓团、公孙龙为代表的辩者们的理论,他们的说法尽管讨论的具体问题不同,所指对象各异,但在理论性质和意义指向上与惠施是完全一致的。
在庄子看来,惠施及名辩者们一味沉溺于这类“逐物”之知,徒逞口舌之能,玩弄概念游戏,以奇谈怪论相与争胜,哗众取宠,惑乱人心,封囿在语言名相的牢笼中,而不关注人的生命存在,这样的知识探求在根本上是毫无意义的。一方面,从天地万物本身来看,人的所知是极其有限的。妄图以狭隘的知见,穷天地万物之奥秘,不但无法认识万物的真相,反而带来精神的纷扰和迷乱。《天下》篇批评惠施:“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秋水》篇魏牟嘲笑“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的公孙龙如“坎井之龟”,其知犹如“蚊虻负山,商蚷驰河”,其辩无异于“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另一方面,从人的生命存在来看,人生是有限的,而“知”是无限的,惠施及辩者们“相与乐之”的“极物之知”,只是在“物”的世界里纠缠,而忘记了生命本身,因此在根本上是对生命的浪费。《徳充符》篇批评惠施“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梧而瞑。”驰散心神、耗费精力、忘失本性,把有限而短暂的人生耗费在虚妄的坚白之论,且自鸣得意。《天下》篇又批评他“弱于德,强于物,其途隩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返,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天地》篇批评辩者之流乃“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
上述种种“知”的形态,尽管有层次高低之不同、求知方式之差异,但在根本上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对人的存在本性的背离和遮蔽。《徐无鬼》篇指出:“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淩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囿于物”的“知”是与生命无关的,因而并不是真正的“知”、理想的“知”。而真正的“知”必然是关涉生命本身的,是从“物”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返回,是对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生命存在本性的揭示。那么,真正的“知”如何可能?《大宗师》篇南伯子葵问闻道者女偊:“道可得学邪?”女偊回答他:“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即是说,要通达“圣人之道”,首先有赖于与之相应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境界。
由此可见,在庄子那里,“知”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人”的问题。一种真正的“知”、理想的“知”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乃在于一种真正的“人”、理想的“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境界的开显。这真正的“人”、理想的“人”,就是庄子所谓的“真人”。
三、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真人”对“真知”的这种先在性关系,在“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一观念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大宗师》开篇即曰:“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矣。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就是说,领悟到什么是天之所为,什么是人之所为,这是知所能达到的最终可能性及其限度。在此基础上,以天之所为来规定、引导人之所为,实现生命的圆满,这是知的盛大完美的状态。尽管如此,仍需分辨的是,这种说法很容易导致一般流俗意义上的“天”与“人”的相分而相对。因此,根本说来,只有“真人”才可能开显出“真知”。
在庄子看来,“真人”与道同在,他回到了人的天真自然的心灵和精神状态,实现了人天生自然的内在本性。因此,他能够在道的不断敞开中揭示天地万物的本然状态。一方面,只有天真自然的心灵和精神状态,才能敞开道、经验道并接纳道,从而获得对天地万物的真实洞见;另一方面,正是在道的自身显现中,才不断开显和揭示着人的存在本性。通过体道的心性修养,人的本心本性得以逐步抖落覆盖其上并胶固其中的欲望、知识、观念的染污和枷锁,而不断地超拔和透显出来。因此,庄子认为,首先要通过“外”“忘”“丧”“心斋”等心性修养方式层层剥落现实经验世界的习性和观念对道的遮蔽以及对人的存在本性的扭曲和背离,实现对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彻底净化,从而能够以“目击而道存”(《田子方》)、“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养生主》)、“以天合天”(《达生》)等体道的方式,不断敞开世界的本然状态,实现向人的存在本性的复归。
庄子指出,道无所不在,但在现实世界中,人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背离着道、遮蔽着道。因此,要回到道,回到人的存在本性,首先就要从根本上彻底瓦解和净除现实世界各种各样的背离并遮蔽道的经验习性和生存方式,把人的心灵和精神从现实世界的欲望、利害、计较、思虑、毁誉、荣辱、是非、分别、物我、死生等层层枷锁和重重遮蔽中超拔出来,所谓“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庚桑楚》)庄子指出:“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同上)在庄子看来,只有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正”“静”“明”“虚”才能与道相应,从而感应道、融入道的自身显现当中。这种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净化是通过“外”“忘”“丧”“心斋”等方式来实现的。《大宗师》篇的闻道者女偊谈自己体道的经验,即是一个层层而“外”的过程:
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郭象注曰:“外犹遗也”,成玄英疏曰:“外,遗忘也。”[4]114清人刘凤苞亦曰:“外者遗也,忘世忘物忘我,脱然无累于中,所谓与物皆冥也。”[8]通过“外天下”“外物”“外生”的过程,层层剥落粘附在心镜上的污垢,人的心灵便如“朝阳初启”般豁然朗显。
在涤除欲望、知识、观念等对心灵的染污,回复心之虚静灵明的同时,还要忘掉“我”。《逍遥游》篇指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三者既相互区分,又彼此交迭。有功、有名,根源都在于有己,无己则无功、无名。“无己”意味着对功、名的否定,但更根本的在于对自身的否定。《天地》篇说:“忘乎我,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忘己”即《齐物论》中的“丧我”,因为这个“我”总是粘滞在“我—对象”的关系之中,永远纠缠于物我、是非、彼此等的对象性关系之中,陷溺于各种现实的困境,无法透显一个真正的“吾”。“吾丧我”就是要丧掉那个作为物而存在的“形态之我”与作为角色而存在的“情态之我”,以此透显本真的“吾”[9]。而只有这个能够丧我之“吾”,才是一个能够聆听“天籁”的与道同体的存在。《大宗师》篇颜回通过“坐忘”而“同于大通”的过程,就是一个由忘物而忘己的过程。颜回由忘仁义、礼乐等世俗世界的文化观念,到忘去自己的形骸智识,而达到无思无虑、内外俱泯、“同于大通”之境实现与道同在的本性。
除了“忘”,庄子还特别强调“心斋”对于经验道的意义。《人间世》篇颜回将适卫,向仲尼请教化卫君之法,仲尼告之以“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就是心的斋戒,它意味着心的专一虚寂。耳目之知乃是最粗浅的,而心知虽较耳目为深入,但尚“止于符”,仍属知之粗者,而气则纯任空灵虚寂,如此空灵虚寂之气,方能直接感应道,所以说“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由耳、而心、而气,心达到了虚的极致,虚而待物则能感通,感通则能应物应人。就此而言,所谓“心斋”,就是心灵的自我净化,去蔽显真,此即《知北游》篇所谓“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这样的心灵是“虚”而“静”的,唯其虚,才能敞开并接纳道;唯其静,才能感应并通向道。“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心”若明镜般莹澈虚朗,方能显现天地万物之本然状态,获得对天地万物的真实鉴照。
当人的心灵和精神不断回归其自身的本然状态的时候,人便能够不断获得对世界的原发性经验。《田子方》篇温伯雪子“目击而道存,亦不可以容声矣!”《则阳》篇“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缘其所起,此议之所止。”这都表明庄子对以语言、思虑、知识等求道方式的弃绝和否定,而彰显一种原发性、直觉性的体道方式。“击”意味着瞬间性、迅捷性、当下性、直接性。所谓“目击”,就是以“心”之“目”去“观”道,而放弃任何关于道的言说、思虑和计议的企图和妄想。在庄子看来,道无所不在,但是“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这是因为“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天道》)人的耳目见闻,乃至思虑语言,都拘限于经验世界的表象,并且因其本身的有限性,只能经验道之“粗”、道之“迹”,而无法经验道之“精”、乃至道本身。因此,只有消解了语言、知识、思虑对道的遮蔽,道的光芒才会显露,所谓“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识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笔下的体道者都处于一种无知无欲、无思无虑的状态,形如槁木,而心若死灰。
《养生主》篇庖丁解牛的故事还展现了一种“技进于道”的方式:“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说明经过长期的“技”的修炼,“神”已经突破并超越了形体官能的拘限而与“道”合一。《达生》篇那个津人之所以能够操舟若神,就是因为他神志专一、神定于内,故外患不足以相撄。那个道行高深的承蜩者痀偻丈人讲自己的承蜩之术,就是因为他能够做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以神遇”、“神定于内”、“凝于神”等,都表明只有心神专一,方能回到心之本然状态,从而与道合一。正是在此意义上,《庄子》强调“修心反真”、“体性抱神”(《天地》)等心性修养方式的重要意义。“修心反真”意味着抖落外在经验世界和内在观念世界的污垢,回归心的虚灵明觉的本性,与道合一。“体性抱神”意味着回归并涵养心、性、神的虚寂恬淡、精纯不杂的状态。“修心”与“养神”亦即庄子所谓“知与恬交相养”(《缮性》,在“交相养”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耳、目、鼻、口、心的通彻澄明。《外物》篇指出:“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彻”者,“通也”[4]404。只有耳、目、鼻、口、心的通彻,才能感知到世界的真相,获得对世界的真实性洞见。
综上所述,庄子通过对“真人”与“真知”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揭示,开放出一条不断通达“真人”与“真知”的思想道路,不断实现向天地之道亦即人的存在本性的回归。在此回归的道路上,天地万物以及人类自身不断敞开其自然而本然的状态,显示其自在而自由的本性。惟其如此,人的存在才得以告别“伪”和“俗”,而“游”于“至美”与“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