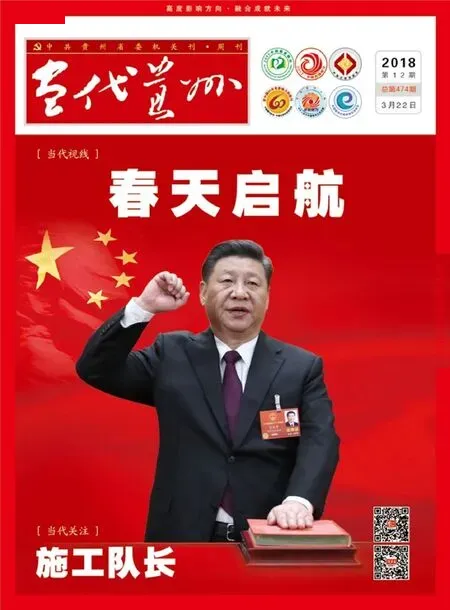儒家身份伦理中的权利和义务观
文_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 汪枭枭
伸张权利也不能忽视道义
周萌:儒家的理论起点是血缘伦理,即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爱不断递减。推广到社会伦理,便是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大概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儒家已与现代社会脱节,甚至格格不入。我们不妨先回到孔子的源初阐述,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着眼于什么。
《论语·颜渊》中,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方法,这八个字也成为儒家强调等级的基本证据。诚然,当今社会,父母并不因年龄和辈分而有优先决定权,子女也不必唯父母意志是从,而是大家均应服从于“理”。实际上,问题不在于等级本身,而在于承认等级仍无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之下,是否还有更合乎人性的追求。
周萌:若是联系有关“正名”的说法,则能更好地体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背后的深层意蕴。《论语·子路》中,孔子对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正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另一种表述,而这段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当时卫国发生了父子争国的事情。卫灵公的儿子蒯聩与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关系不好,刺杀南子失败后出逃晋国。卫灵公去世后,蒯聩的儿子辄被立为国君,而蒯聩借重晋国返回卫国与自己的儿子辄争位。
站在辄的角度,蒯聩是父亲,从道义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应当主动让位给父亲;站在蒯聩的角度,辄是遵从卫灵公的遗命继位的,等于秉承了父亲的意愿,从法理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理应遵守本分,不应与辄争位。孔子提倡“君臣父子”,意在强调每个人在申张各自的合法性的时候,不能完全忽视了彼此的道义和法律义务。
文明的建立需要秩序感
周萌: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均有不同的身份规定,只有各自尽到身份义务,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才有章可循。换句话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视野,也不是强调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儿子对父亲的服从,而是等级之下的个体视野,亦即每个人都有应尽的本分。孔子把父子争国视为恶行,因为他的着眼点在于义务而非权力,但这在后代逐渐跑偏了,尤其是“三纲五常”的提法,使得义务本位朝着权利本位转变。
“三纲”一词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即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原先并没有“三纲五常”的说法,孔子只是讲根据社会站位的不同,每个人有相应的身份义务,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突出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的主导性,这不是义务本位,而是权利本位了。这样一来,尊君抑臣的观念得到了有效发挥。董仲舒的阐述有那个时代的特色,那就是专制帝国在秦始皇时代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在形态,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思想文化等内在形态。
周萌:墨家主张兼爱,即平等无差别的爱。《墨子·兼爱上》中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墨子的基本推论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视同自己,把别的家庭视同自己的家庭,把别的国家视同自己的国家,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其实,这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不符合人之常情,注定只能是乌托邦。相反,儒家讲血缘伦理,是基于自然而然的情感,是用常人的标准要求常人。
不顾现实地抹平一切差异性,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孟子在《滕文公下》中批评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意思是说,文明是需要某种秩序感的,杨朱放大个体的独立性,墨子抹煞个体的差异性,推而广之,会使国家的层级管理丧失合法性,这是开倒车的行为。
拥有权力就应该接受约束
周萌:“尚同”也是墨子的核心观点之一,实际上,每个人爱的心灵与爱的能力也是不同的,那么应当以谁作为标杆呢?墨子的答案是君主。《墨子·尚同》中说,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周萌认为,儒家提倡的“差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双重平等。也就是说,拥有这份权利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图为周萌在录制优课联盟网络课程《资治通鉴与传统政治文化》。(田余/摄)
不难看出,所谓尚同,实则是下层同于上层,所有人同于天子,亦即以君主的意志为终极归宿。这似乎是个悖论,初看起来墨子追求平等,为普罗大众说话,但他的理论落脚点竟然是君主,而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现实地来看,兼爱往往流于乌托邦,而尚同不仅容易实现,而且很有诱惑力,历代统治者都在尽力做到这一点。相对而言,原始儒家反而是在努力限制君权。
周萌:是的,时至今日,无论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实践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顾一切地抹煞所有差异性,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换句话说,绝对平等是乌托邦,等级依然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相对平等。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双重平等。也就是说,拥有这份权利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
其实在儒家的理想世界里,那就是希望天子修身立德,影响身边的大臣,然后在首都建立首善之区,用以引导全国人民。儒家的“差等”观念中,所处的位置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也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而君主的样子不同于大臣,因为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更高。正因如此,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对政府和公众人物要求越严越好。
当然,儒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身份义务,而现代社会更注重权利平等。或者可以说,在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平等方面,儒家是缺位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正是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时尤应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