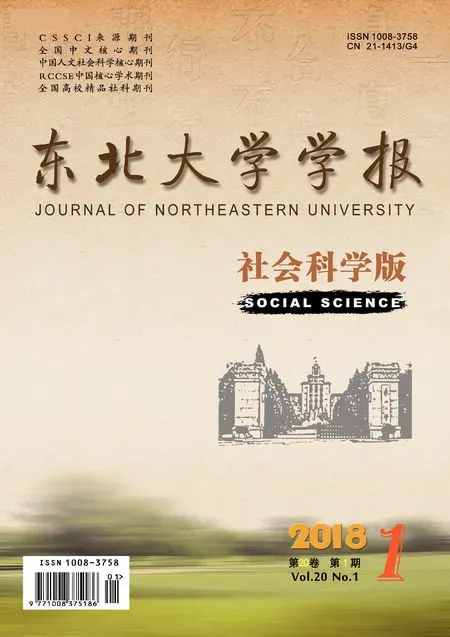从抽象的异化到异化的抽象:符号消费背后的异化逻辑及其本质
田 芯, 徐绍元, 徐桂娣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得符号消费愈演愈烈,符号消费表面上看是为了获得商品背后所蕴藏的价值和意义,而其实质仍然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一种手段,是资本通过符号对人控制的一种途径。所谓符号消费就是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除了消费商品本身以外,同时也消费着这些商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或“内涵”。当符号独立于物而存在,符号商品或商品上所附着的符号价值在大众传媒的夸饰下开始不断地被制造、销售,人们偏执地追求符号所带来的意义,在这种消费欲望的驱动下,人不但成了商品的奴隶而且也变成了符号的奴隶。在商品消费中,人还多少保持着相对于商品而言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但在符号消费中,人们逐渐丧失了主体的独立个性,主体被异化、符号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不但能够全面物化,而且在这种物化的基础上还可以全面抽象化、符号化。人在进行符号消费时只不过享受着符号消费所带来的虚假满足感与快乐,人已然屈服于符号的统治。这种符号消费背后有着深刻的异化逻辑,本文将以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异化理论为基础,揭示这种异化是如何产生的、异化逻辑是如何展开的及这种异化的本质,从而使我们了解符号消费背后人的符号化生存状况,为消解这种异化提供理论依据。
一、抽象的异化:商品生产和消费中人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劳动对象中,但这个劳动对象一旦“获得”人的本质,就成为和人相对立的异己化存在,反过来而控制人。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论述时曾明确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52在商品消费中,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需要进行交换才能够重新回到生产者身边,但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已经随着劳动产品进入到了商品交换领域中,回到生产者身边的消费不再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手段,消费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与自身相背离,消费也发生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发生在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是一种抽象的异化,集中体现了抽象的物对人的控制。
我们首先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来考察。“异化”一词是指人创造了物,但物却反过来制约着人,使劳动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使人从动物中脱离出来成为人,人类的本质属性是劳动,而劳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对象化的产物,劳动者在对劳动产品的创造中实现自我,所以劳动产品理所当然属于通过劳动将其创造出来的劳动者。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下,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已成为了外在主体的力量,主体的劳动行为不是由劳动者自身自由支配,劳动对劳动者而言,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最终后果就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1]51因此,在异化劳动下,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成为异己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能动地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整个自然界,使之成为适合人本身生存的世界,这一活动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这种将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象化的生命活动将人类从动物中脱离而出,并与动物直接区分开来,并通过这种生产,使人的劳动产品和人的自由得以实现。异化劳动使人的类生活转化为动物式的,劳动者的劳动就仅仅成为维持生存的手段,将人的一切都围绕在生存问题上,主观能动性的意识对异化劳动中的人而言,成为了附属之物,人类的类生活失去了意义。异化劳动将人的类本质转化为了异己的力量,人成为丧失了类本质物化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资本家是相对立的,也正因为私有制的存在使劳动和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剥削掉,再也不属于劳动者并站到了劳动者的对立面,并异化为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就表现为资本家对劳动者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异化的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发生了异化,且人与所属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人的类本质与他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异化了。
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条件下,人通过劳动不但没有获得自己的本质,反而创造出一种异己的力量成为控制自己的对象,这就是商品生产。人通过劳动而创造出的产品成为异己之物反过来和人相对立。在一般人看来,物作为人的产品说到底是人劳动的结果,因此,物对人的控制不过是人的“杞人忧天”。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看到作为实物形态的物和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伟大和深刻在于,揭示了这种实物形态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在人类劳动中必然产生的结果,表面上是人的劳动生产出某物,而实际上是人通过劳动生产出物和人的关系,也即这种物和人的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生产的”。人通过劳动,生产出异己之物,甚至是对立之物、控制之物,进而生产出使这种对立、控制“合理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从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中来考察。消费领域中出现的异化现象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之为三大拜物教。三大拜物教表面上也是物对人的控制,但究其实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起来的关系对人的控制,是物以更抽象的形式对人的控制。生产的异化或劳动的异化相对而言好理解一些,因为异化就发生在生产或劳动的过程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劳动者直接感受到。但是,消费中的异化相对隐秘得多,而且这种异化往往隐藏在主体选择或主体满足的背后,甚至不被当作异化而是当作主体性的某种表现而被人感受到,因此揭示这种异化如何从直接性而转化为间接性甚至到符号消费中的抽象性的异化逻辑显得尤为必要。
商品是通过自身的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东西,具有有用性,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商品具有了交换价值这一属性。“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3]商品的价值作为商品的本质属性,凝聚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上。任何商品都是具有价值的属性,但是,商品的价值唯有进入消费领域经过等价交换,并且是由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才能得以实现。在其商品成功交换后,带给劳动者经济利益,更是人类维持劳动的唯一途径。而不受商品生产者控制的市场经济,却对商品交换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人类产生对商品的畏惧,失去了对创造商品的愉悦感,将其视为决定生死存亡的“神”。在这种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下,人和社会的力量体现为商品的力量。商品在这一交换活动中具有了某种神秘色彩,仿佛拥有了自我的意识,能够自己主动与他物产生关系,并成为能够决定生产者命运的主导者,生产者受到了来自于自己创造出来的商品的束缚,商品站到了创造了它的劳动者的对立面,成为劳动者异己的力量。劳动者与其劳动潜能相分离,主客体关系相颠倒,异化的范围从生产过程发展到了消费过程中,异化由直接性转化为间接性。货币作为表现和衡量其他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出现在商品交换活动中,使得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有了一种统一的标准。在等价交换原则下,人与物都成了可以进行抽象交换的物品,成了定量的符号。人不能通过劳动直接享有商品的使用价值,人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金钱,才能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所有的需求都转换为对货币的需求,真正的需求被消解了。只有拥有货币才能交换,货币成为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货币被人们赋予了某种神秘力量,能够购买一切,征服一切,人们迷恋货币的力量就像迷恋造物神一般,彻底地臣服于货币,因此,商品拜物教走向了货币拜物教。货币的存在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从而占有更多货币,货币成为资本,而不仅仅是等价交换物。在这个过程当中,货币最后产出的量大于投入的货币量,于是产生了剩余价值,完成了资本的自我增值。当货币转化为资本时,一种最彻底形态的拜物教诞生了,即资本拜物教。
三大拜物教使得人在商品消费中彻底异化了。首先,商品消费使得人和商品之间的主客关系颠倒了。商品的价值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但是商品的价值需要进入消费领域后通过劳动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交换,转让商品的使用价值来实现。这一过程表现为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因这种商品交换不仅能够给劳动者带来经济利益,且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商品被赋予神秘色彩,使人对物产生了畏惧感,商品成为独立于人存在的物,站到人的对立面,成为人被自己创造出的物所支配,主客体颠倒了。其次,商品消费是使人进一步物化,进一步量化,进一步抽象化。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建立在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创造出商品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中。商品价值的大小也就是指商品的价值量,所以衡量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商品所消耗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劳动量来决定。这种量化的衡量标准,将人等同于劳动工具,使人物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也随之异化为数值大小的交换关系。最后,商品的消费使人的存在进一步抽象化,人是什么是由他能消费得起什么来决定,不但主客关系颠倒了,而且“物我”价值也颠倒了。
二、异化的抽象:符号消费中人的异化
相对于商品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异化而言,在符号消费中的异化更具有间接性的特征,而这种间接性是异化逻辑的内在需要。这种间接性的异化掩盖了直接性的异化对人的伤害,在商品生产和消费中人对人的这种控制直接的结果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这种控制的反抗,这种控制和反抗都具有直接性的特点。但是,在符号消费领域中的这种异化使得人的反抗失去了现实的对象,而且通过符号消费,使得异化(不断实现着的异化)变成了主体的内在(超出基本生理)需求。在商品消费过程中,异化也稍稍具有间接性的特征,人对人的控制也隐藏在消费过程当中,但是商品、货币和资本本身仍然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异化仍然会或多或少地被感受到,因此,需要更加隐蔽的形式来掩盖这种异化。异化需要进一步被抽象化,而这种异化的抽象,就是符号消费中人的异化。符号消费使得人和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隐藏到符号背后,使得这种异化更加隐蔽但也更强烈。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物质资料达到空前的丰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从以生产为中心的模式走向了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这种模式也标志着消费社会的形成。异化的范围由劳动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人完全处于一种物的异化状态,人即使逃离了劳动,仍然逃不开被束缚,成为被强制消费的动物[4]。而且这种强制消费,不再仅仅表现为物对人的控制和人对人的控制,而转化为消费符号对人的控制。所谓的强制消费,实际上指的是不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消费,这种消费的强制并不是真的有人强制去消费,而是把“消费”转化成某种“价值”或“意义”,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对消费者构成某种“吸引”,而这种吸引并不是从主体生发出来的需要,而是由这些“价值”或“意义”构建出来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主体具有强制性。
在消费社会,人们购买商品所看重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所谓的符号消费,是指人们的消费目的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购买物品,而是为了通过消费这一行为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及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在今天的消费社会中,我们的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对自我进行识别和归属的行为,并通过消费的物品对他人进行识别和归属,人们自我建构行为在消费活动中完成。但人们更是在琳琅满目的广告教唆中失去了自身的判断力,偏执地追求符号而丧失了主体的独立个性,丧失了真实的自我本性。这个过程中,人被符号统治着,成为符号的奴隶,主体被异化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了。
鲍德里亚指出:“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纵行为。”[5]不同的符号表现出不同的含义,影响并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和群体认同。人们对物品的占有或交换的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为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或交换,而是为了对商品所具有的符号意义的占有和交换,同时也是在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符号的消费中形成自我的界定和自我认同。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符号作为一切的主宰者,主宰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消费过程中,符号之间的关系最终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消费所宣称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化理念,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广告的诉求,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向消费者展示商品,并在传播过程中使消费者根据媒介的诱导信息重新进行统一编码,最后是消费者自动依附于广告的编码规则并与其达到一致,适应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从而成为消费者行为的基本价值观。广告成为驯化消费者的手段,广告刺激消费欲求,并通过各种甜蜜的话语来掩盖实际的交换逻辑,使工人们被资本家的剥削更加隐秘化,使人处于广告营造的幻影中,在满足自己需求的消费中悄无声息地被剥削,并被符号所支配着,迷失了自我价值,在媒体给予的幻影中寻求幸福。
在消费活动中,人们希望通过消费不仅能够获得集体归属感,更想通过消费来建构自我,实现自我的自主性。人们试图在消费商品中寻求差异,想要以此来界定自我、获得身份认同。人们对差异的需求使以差异为目的的生产出现。例如各种限量版的商品、特制的商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种以差异为目的的生产,也使人们的需求不再是对某一物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寻求陷入无止境。符号的差异总是在不断地被缩小,不停息地进行着更新替代,差异的更新犹如无理数般没有尽头,使得人们对消费的欲望成为永无止境的追求,消费被彻底异化了。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6]最终,人失去了真正的自主性,在异化的消费中成为全面异化的人。
三、异化的符号化: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
从抽象的异化到异化的抽象,人的异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展开,在于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的商品化,异化本身已经符号化了,最终导致人的符号化生存。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符号化和符号商品化产生了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本来就是属于物的属性,依附于物而存在。但是,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于符号化的商品所具有的文化意象更为看重,甚至超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是否被符号化决定了是否能被消费。符号操纵着物,并将物的存在价值完全被符号所制造的幻象所掩盖。消费主义是符号异化的极端形态。消费主义鼓励消费,提倡象征性的消费、炫耀性的消费、奢侈消费,鼓励人们追求个性化消费,物质享乐主义盛行,消费成为了当今人们的人生目标[7]。人们在大众媒体的“劝导和驯化”下,发疯一般追逐各种商品,失去了自主性,只知道物质享受和自以为是的“自由性”购买商品,忘记了对精神世界的反思追问,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可见,符号消费不但使人失去了反抗的对象,也使人失去反抗的能力。异化本身已经符号化了,并成为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商品作为人的劳动产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商品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有用,而在于能否被售卖出去。因此,商品会被进一步“塑造”,在其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被进一步符号化。商品符号化的实质就是对商品的有用性的“篡改”,符号化了的商品更容易被控制和推广。这个进程同时也是符号的商品化。所谓的符号商品化就是符号成为了一种商品,成为了以商品形态存在的消费品。符号成为商品的“附加值”,甚至成为商品“价值”本身。人们消费商品,更多的是对商品附加的“符号”的消费,这是符号消费的本质,也是商品消费最极端的消费形式。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物品只有化身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对象。这正是对当今消费社会消费活动的真实写照[8]。在马克思那里,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是与问题无关的[9]。也就是说,商品的有用性绝不仅仅局限于使人获得自然生理的需求,而且要满足人的虚荣心、炫耀目的、地位渴望等等。在物质资料丰富的消费社会,人们对商品的依赖性已经不仅仅在其使用价值上,而在商品所蕴含的意义上,即商品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成为了商品的第三属性,并在商品交换中取代了使用价值的主导地位,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动机。
在消费社会中,物自身已经消解了,符号消费使消费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人们在这种脱离了客观世界基础的符号消费中,渐渐迷失了自我。人们在制造符号、追逐符号中,在受符号主宰的游戏中丧失了理性,被无限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充斥着头脑,使真实的需求被虚幻的欲望统治并控制着,通过符号的刺激人们自发地条件反射一般产生消费的欲望,在对符号的追逐中,人逐渐变成一具主体意识完全被消解的抽象的空有欲望的躯壳。在这种符号统治下,人的身体成为了“最美的消费品”[10],符号消费使得异化更加抽象化,更加隐蔽。符号消费的抽象化直接结果就是异化似乎消失了,人在消费中实现了某种解放,而且随着这种消费的发展似乎人会越来越解放,这种错觉使得人完全放弃了对异化的反抗,即使想反抗也找不到反抗的对象。因此,符号消费使得人把自己无法解放的罪责重新归咎到自身上来。符号消费首先让人们消费商品所象征的符号,其次让人们消费符号所象征的“商品”,最后让人们接受“符号商品”所象征的意义或价值。正是这种层层深入,使得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人越来越抽象化而无法获得自己的现实性,也就失去了反抗现实的力量,人的存在本身被符号化了,
综上所述,从人的物化到物的符号化再到人的符号化,异化层层深入。符号消费是这种异化得以完成的手段,而资本推动符号生产是这种异化得以实现的本质。从商品生产过程到商品消费过程,再到符号消费过程,资本对人的控制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人的异化不是消失了而是严重了。异化在这一过程中由直接性转变为间接性和抽象性,而这种转变正是符号消费背后的异化逻辑和本质。只有把握了这种异化逻辑及其在各个阶段的特征,才有可能为消解这种异化提供某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中,异化虽然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特征,但是人们还是能切实地感受到这种异化对人的影响和束缚,马克思提出以消灭私有制来消解这种异化。在符号消费中,异化表现出了人的更多的主动性和自由性,甚至表现出某种异化消解的特征。但这种主动性和自由性仍然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仍然消解不掉异化本身。符号消费只不过是人在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之后的暂时的迷茫状态,这种迷茫状态所遮蔽的仍然是资本对人的控制关系,只不过是控制手段的转换而已,这种控制手段的背后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正义。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消费社会由消费引领着人们寻求幸福的这条道路,使人们将其价值观、幸福观及自我建构、自我认定全部建立在畸形的符号消费下,成为完全异化的人及社会关系,这种现象让人堪忧。这种异化的符号消费使人性逐渐泯灭,成为符号的信徒,人不再是真正的人,人对所谓符号消费象征的“自由”追逐,不过是追寻了更多的束缚,并在“自由”的虚假符号下沦丧为被奴化的人。
符号消费背后异化的演变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异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全面异化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从物对人的控制到符号对人的统治,每一次异化的进程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地位。今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出发,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消费行为显得尤为必要。只有那些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才是值得提倡的。正常的消费是人的基本需求,而符号消费不仅仅是物满足人的过程,也会导致异化,通过物控制人的过程,成为人控制人的工具,导致符号对人的统治。因此应客观对待、正确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人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消费过程中,真正成为物的主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2] 夏莹.拜物教的幽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71-87.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54.
[4] 刘同舫.象征交换:鲍德里亚超越符号消费社会的解放策略[J].广东社会科学, 2016(4):57-63.
[5] 张劲松.重释与批判——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39.
[6]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2.
[7] 刘飏.中国消费主义发展的伦理思考[J].学术探索, 2016(11):15-19.
[8] 刘维兰.试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推向符号[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0,27(4):35-39.
[9]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23.
[10] 王中忱.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M]∥罗刚,王中忱.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