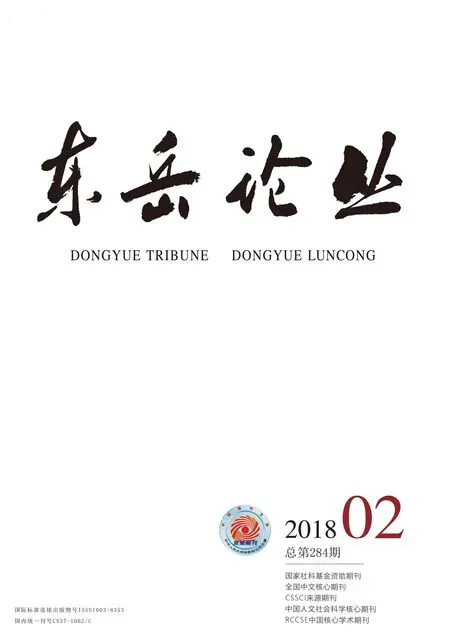《醒世姻缘传》中的命运反讽
——叙事语义学的阐释
[加拿大]傅礼军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绪 论
《醒世姻缘传》是长达一百回的白话长篇小说,作于明末清初①《醒世姻缘传》的写作年代是一个仍然有争议的问题,此处采用邹宗良的观点。见邹宗良:《〈醒世姻缘传〉前言》,载袁世硕、邹宗良校注,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8页。。作者署名“西周生辑著”,其真实身份有待考证。从全书采用大量山东方言的情况来看,作者无疑是一个山东人②参见邹宗良前引文,第22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这部长篇小说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学术界对于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也有了日益明确的认识。如徐朔方和徐复岭都提出,《醒世姻缘传》是一部堪与《金瓶梅》和《红楼梦》相提并论的描写现实社会日常生活的“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③徐朔方:《论〈醒世姻缘传〉以及它与〈金瓶梅〉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页。。最近,黄云凯更提出,《醒世姻缘传》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金瓶梅》和《红楼梦》。黄云凯指出,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生活现实之一,但“《红楼梦》写的是爱情,而《金瓶梅》写的则是欲望”,只有在《醒世姻缘传》这里“婚姻才第一次成为小说的中心”;《醒世姻缘传》“所反映的现实的广阔与细腻程度,在古典小说里,是无出其右的”,换句话说,“仅就现实性而言,《醒世姻缘传》在古典小说里是空前绝后的”④黄云凯:《前尘事,岁无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虽然《醒世姻缘传》受到高度推崇,但就学术界的现状来看,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研究相比,关于《醒世姻缘传》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为了准确评价《醒世姻缘传》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我们亟需对这部长篇小说做出细致的分析、阐释和评价。
本论文将通过对女主人公薛素姐故事的分析,对《醒世姻缘传》的文本意义做出新的阐释。薛素姐和狄希陈的婚姻故事在小说中占据核心位置,薛素姐也是全书中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因此,在《醒世姻缘传》的研究中,分析薛素姐形象的论文占有不小的比例。这些论文大多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素姐予以肯定和赞扬,对小说作者西周生对待素姐的态度加以批判。如发表较早的王良惠的论文,称素姐“是西周生笔下唯一追求自主意识的形象,力求成为自己的主人,她从内心到动作都是指向以尊临卑的传统文化……。她虽被吞灭,但精灵永存!”*王良惠:《一位追求自主意识的女性——〈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楚爱华说“素姐手拿大棒,威风凛凛地站在女性群体的前沿阵地,在男性闻风丧胆、鬼哭狼嚎的狼狈中体验着女性站立的喜悦,给女性做出了表率,也给了她们斗争的勇气和争取自由的信心。”*楚爱华:《〈醒世姻缘传〉中素姐等悍妇形象出现的原因及其时代意义》,《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杨江平、李新灿认为,“素姐的妒悍并不是她天性如此,而是由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等社会制度所造成”,然而,“封建宗法社会的作家西周生不了解女性妒悍的社会根源,将女性妒悍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女性身上。”*杨江平,李新灿:《薛素姐性格言行的还原批评》,《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傅丽提出,“薛素姐作为明清叙事文学中的悍妇形象,集中体现了另类女性与正统妇道的对立关系。”*傅丽:《背叛妇道的悍妇人格——二论〈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付丽指出,“男权压抑与薛素姐悍妇心理生成密切相关。”*付丽:《男权压抑下的悍妇心理——略论〈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付丽又认为,“在新旧文化冲突的意义上,悍妇薛素姐对进步的人本思潮,也算发出了一声尽管微弱却不失可贵的回应”*付丽:《悍妇人格的个性解读——略论〈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王英提出,素姐的“抗争,是对整个男权社会的抗争,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坚持和抗争,是难能可贵的。”*王英:《悍妇薛素姐及其文化意蕴》,《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卢卓元认为,“薛素姐却勇敢地跳出了千百年来女性卑微的生存地位,打破了套在女性身上的重重枷锁,……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书写了另外一种生存范式。”*卢卓元:《凶狠和残忍之下——薛素姐悍恶个性解读》,《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9年第4期。牛景丽、阮丽萌认为,小说作者之所以把女性描写为“恶魔”,是“妄图达到教育闺阁女子以净化世风、重新树立男性权威的目的;另一方面便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在口诛笔伐中寻找泄愤的快感。”*牛景丽,阮丽萌:《〈醒世姻缘传〉薛素姐形象之女性主义解读——兼谈明清家族小说中悍妇形象的话语模式》,《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以上对于素姐形象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拓展我们对素姐这个人物的理解,但是,正如刘洪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素姐的发火是对夫权的反抗,因而得出素姐虐待丈夫是合理的,但这实在不符合小说的实际。”*刘洪强:《薛素姐的谱系分析——兼论作为“贞妇”的薛素姐》,《济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在有关素姐的研究中,有些论述不是严谨地依据细致的文本分析来做出阐释,而是从某种既定的立场出发对人物进行评点,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对素姐形象做了过分的拔高,或者对作者的写作意图做了过分的贬低,总之,属于“过度阐释”,很难说符合小说文本所表达的意义。
本论文将依据叙事语义学的方法进行文本阐释。叙事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把一个叙事文本划分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两个层次。经典叙事学重点研究的是话语层次。经典叙事学把故事看作是既定的材料,集中探讨叙述者如何通过特定的叙述方式把故事转化为一个叙事文本。叙事语义学虽然是由经典叙事学发展而来,但与经典叙事学不同的是,叙事语义学重点研究故事层次,把故事视为一个“虚构世界”(fictional world),集中探讨虚构世界中人物的行动、冲突和情节。根据叙事语义学理论,虚构世界中人物的行动,受到价值系统、道义系统、认知系统、意图系统等系统的制约。价值系统关系到人物的欲望,道义系统界定了人物的义务,认知系统涉及人物对虚构世界中的现实的知识,意图系统描绘的是人物围绕制定行动计划而采取的一系列心理运作*关于叙事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可以参见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p.111-122.傅礼军:《状元弃妻:中国戏剧典范情节的叙事语义学》,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28-35页。。对于叙事文本中人物的行动,需要从欲望、义务、知识和意图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才能够理解人物行动、冲突和情节的意义,最终把握叙事文本的意义。
以往对《醒世姻缘传》女主人公的研究,通常分析的是薛素姐这个人物形象,而本论文分析的则是“素姐故事”。传统的人物形象分析着重分析人物的特征、品德、个性或性格,本论文则重点分析素姐的行动并阐释其行动的意义。素姐的行动是“素姐故事”的基本分析单位。素姐的行动在小说世界中构成一个单独的人物领域(domain),即“素姐领域”。如果她的行动涉及其他人,引起了冲突,这样的冲突就构成了小说世界中的一个事件。一个对素姐领域和小说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可以称为一个重大事件。就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而言,素姐领域中一系列重大事件之间的前后时间关系和相互因果关系,构成了素姐故事的情节。由此可见,本论文是从人物的行动出发,通过考察引起行动的欲望、对行动起着制约作用的义务和知识、负责制定行动方案的意图等各个系统在故事中的作用,对人物的行动、冲突、事件和情节的性质、结构和意义做出阐释。通过这样从行动到事件再到故事整体情节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对素姐故事的结构和意义有着更准确的把握,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写作意图有着更充分的理解。
在对素姐故事的分析中,我们将集中关注反讽的运用。反讽与人物的意图系统有着特别的关系。意图系统涉及人物的一系列心理运作,包括评估事态、设立目标、完善计划、对计划实施后会产生的结果做出预测。当行动的实际结果与目标、预测完全相反时,反讽就出现了。例如,如果一个人物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计划实施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却产生了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如俗话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行动便产生了反讽效果,而这个人物则成为反讽的对象。
对于素姐故事的分析,可以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进行。对单独一个事件的分析,属于微观层次的分析,而对素姐故事整体情节的分析,则属于宏观层次的分析。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首先在微观层次上分析欲望与义务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事件,其次分析由于人物的知识与小说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事件结果。最后,我们对素姐故事的整体情节进行宏观层次的分析。
二、欲望与义务的冲突
在素姐故事中,绝大多数事件是由欲望与义务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在《醒世姻缘传》的小说世界中,义务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社会规范,这些规范界定了一个人的义务和职责。违反社会规范的行动有时会招致惩罚,这时事件呈现为违规-惩罚的情节。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按照素姐欲望的目标对素姐故事中的事件进行分类。总体上看,素姐的欲望主要有三个目标,即外出游逛、控制家产和控制丈夫。下面我们分别考察素姐在这三类事件中是否达到了她的欲望目标以及是否因为违背社会规范而遭到惩罚。
属于“外出游逛”欲望目标的事件有:游三官庙会(第56回)、去泰山进香(第68-69回)、游玉皇庙会(第73回)、游北京皇姑寺(第77-78回)、游成都府城(第97-98回)。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游三官庙会”和“游玉皇庙会”两个事件。
在“游三官庙会”(第56回)事件中,狄希陈去北京国子监注册读书,父亲狄员外陪同前往,在家乡的素姐执意不听父亲薛教授和婆婆狄婆子的劝阻,出外到三官庙会看打醮,把薛教授和狄婆婆气得中风偏瘫。当时的社会习俗不允许女性随意游街串巷、抛头露面,尤其禁止年轻女性和出身于所谓诗礼之家的女性去庙会这类男女混杂、不分良贱的场所*参见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袁世硕、邹宗良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7页。。素姐为了满足自己外出游逛的欲望,违背当时社会的礼俗规矩,却没有受到惩罚。在与父亲和婆婆的冲突中,素姐取得了胜利。不过,从宏观层次来看,这个事件的后果中隐藏着对素姐不利的因素:她把狄婆子和薛教授气得中风偏瘫,消弱了夫家和娘家的力量,也消弱了夫家和娘家对她的支持。
在“游玉皇庙会”(第73回)事件中,素姐随两个道婆参加玉皇庙会,与娼妇程大姐并肩同行。因为程大姐与一群光棍吵嘴,光棍们痛打这群妇女,把她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狄希陈送衣裳给素姐,素姐怨他不陪伴自己来庙会,抓住他的胳膊咬了一口。素姐到济南府控告那些光棍,遭到太守训斥。太守贴出告示,引素姐之遭遇为例,严令禁止妇女入庙烧香。因为两个秀才弟弟和狄希陈都不肯替她出头告状,素姐假说他们已死,在尼姑庵挂幡念经超度他们。这个事件说明了当时社会禁止妇女游逛庙会的原因,即她们离开家庭的保护,在家门之外容易遭受流氓的欺侮。这个事件中,素姐虽然实现了她外出游逛的欲望,她的违规行为却招致惩罚,先是遭到光棍们的羞辱,随后又受到太守的训诫。
总体上看,在属于“外出游逛”的事件中,除了“游成都府城”(第97-98回)之外,素姐在其他事件中都达成了自己的欲望目标。除了在“游玉皇庙会” (第73回)中遭受惩罚之外,在其他事件中都没有受到惩罚。值得注意的是,素姐外出游逛,在当时社会里被视为“不守妇道”的行为,因此把父亲和婆婆气得偏瘫,但她在家里却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而只是在缺少家庭保护的庙会上和衙门里受到惩戒。
属于“控制家产”欲望目标的事件有:公公娶妾(第56回)、小姑出嫁(第56回)、气死婆婆(第59-60回)、气死公公(第76回)、道婆事件(第95-96回)。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气死婆婆”和“气死公公”两个事件。
“气死婆婆”(第59-60回)事件是“公公娶妾”(第56回)事件的延续。在“公公娶妾”事件中,素姐的公公狄员外从北京聘来一个厨娘调羹,后来娶她做妾。素姐担心调羹生出儿子来分了她的家产,计划阉割公公不让他再生儿子,又宣称要害死调羹。按照当时社会的习俗和法律,作为家长的父亲在世时,儿子是无权占有和处分家庭财产的,儿媳更没有权利过问家庭财政问题*参见魏道明:《古代社会家庭财产关系略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素姐想独占家产的欲望十分强烈,所以违背社会规范干涉家庭财政问题。在“气死婆婆”事件中,素姐先是造谣说调羹串通家里的仆妇狄周媳妇抵盗家产,后来又污蔑她们二人与狄希陈有奸情,意图把调羹赶出家门,以便杜绝调羹为狄家再添一个儿子的可能。素姐拷打狄希陈,气死了狄婆子。薛教授听说素姐毒打丈夫、气死婆婆,自己也气死了。狄婆子的弟媳相大妗子为了惩罚素姐气死婆婆,打了素姐二百棒槌。按照当时的法律,素姐拷打丈夫、气死婆婆,是犯了重罪,要遭受“凌迟”的极刑*参见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袁世硕、邹宗良校注,第794页。。在这次冲突中,素姐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遭到婆婆的娘家人的报复,受到了惩罚。
在“气死公公”(第76回)事件中,调羹生了一个儿子小翅膀,素姐想方设法要吓死小翅膀,气得狄员外病势加重。狄希陈从北京赶回家乡。因为怀疑狄员外私下向狄希陈交代家事,素姐痛殴狄希陈,结果气死了狄员外。素姐逼着调羹改嫁,狄希陈派人把调羹母子送到北京。在这个事件中,素姐达到了自己独占家产的目的,而且她的违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
总体上看,在属于“控制家产”的事件中,素姐除了在“气死婆婆”事件中遭到婆婆的娘家人惩罚之外,在其他几个事件中都没有受到惩罚。在早期的几个因为“控制家产”欲望而造成的事件中,她没有实现欲望目标,但是在“气死公公”事件中,她达到了目的,独自占有了全部家产(下一节中,我们将指出她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属于“控制丈夫”欲望目标的事件有:眠鞋事件(第52回)、裙衫事件(第62-64回)、北京之行(第77回)、淮安之行(第86-88回)、告夫谋反(第89回)和妻妾之争(第94-95回)。所谓“控制丈夫”的欲望,指的是素姐反对和制止狄希陈嫖妓、偷情和娶妾的欲望。下面我们重点分析“告夫谋反”事件。
“告夫谋反”(第89回)事件是“北京之行”(第77回)和“淮安之行” (第86-88回)两个事件的延续。在“北京之行”事件中,素姐听说狄希陈在北京娶了童寄姐为妾并且与调羹母子一起居住,于是赶往北京,打算逼着狄希陈把寄姐和调羹一起卖掉。按照当时社会的习俗和法律,男性有纳妾的权利,特别是在素姐没生儿子的情况下,狄希陈有充足的理由纳妾,而素姐想要逼狄希陈卖掉素姐和调羹的欲望,则不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在这个事件中,素姐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淮安之行”事件中,狄希陈的厨子吕祥告诉素姐,狄希陈带着寄姐和调羹去成都赴任了,素姐要吕祥陪她一起追赶狄希陈。在这个事件中,素姐的愿望没有实现。在“告夫谋反”事件中,素姐从淮安回到家乡后,到绣江县衙门控告狄希陈去四川调兵谋反,企图让县官用公文把狄希陈提回家乡审问。县官审出素姐是诬告,判素姐受了肉体刑罚。在这个事件中,素姐的欲望没有实现,她的违规行为则受到严重的惩罚。
总体上看,在属于“控制丈夫”的事件中,素姐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属于“控制丈夫”的六个事件中,她在四个事件中遭到惩罚。在“裙衫事件”中受到弟弟惩罚,在“淮安之行”中遭到厨子拐骗,在“告夫谋反”中受到县官刑罚,在“妻妾之争”中遭到寄姐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出手惩罚她的都不是狄希陈或她的婆婆、公公。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与“外出游逛”和“控制家产”有关的事件中,素姐在大多数事件中达到了她的目的,而在与“控制丈夫”有关的事件中,她一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她很少在家里受到惩罚,多数惩罚发生在她走出家门之后。出手惩罚她的人,除了少数是亲戚,绝大多数都是家庭之外的陌生人。
三、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
在素姐故事中,她的认知与小说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有时造成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在小说中,一个人物对小说现实的无知和误解可能会引导这个人物对事态做出不准确的评估,从而采取错误的行动,引起冲突,导致事件产生不利于自己的结果。一个人物也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物的有意欺瞒,从而产生错误的信念。人物的无知和其他人物的欺瞒经常导致事件产生对人物自己不利的结果,使人物成为反讽的对象。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分析“裙衫事件”(第62-64回)和“气死公公”(第76回)两个事件。
在“裙衫事件”中,素姐从智姐那里得知狄希陈买了裙衫送给别的女人,但智姐的话却是为了报复狄希陈而撒的一个谎。事实上,狄希陈这时候并没有与哪个女人有婚外性关系。素姐相信了智姐的谎话,拿狄希陈没有犯下的过错去惩罚他。为了把狄希陈从素姐的囚禁中解救出来,素姐的弟弟薛如卞在素姐房里偷放了一只鹞鹰恐吓素姐,并谎说鹞鹰入房是死亡的预兆。素姐为了活命而请尼姑白姑子为她建醮忏罪,并让狄希陈住在尼姑庵为她念经忏悔,结果狄希陈与尼姑们趁机奸宿。在这个事件中,素姐因为狄希陈本来没有的婚外性关系而惩罚他,其目的是为了阻止他有婚外性活动,但在一系列错误信念的指引下,她的行动最终导致狄希陈有了婚外性活动。事件的结果走向了素姐意图的反面,从而形成了对素姐行动的反讽。
在“气死公公”事件中,素姐把狄员外气死后,逼着调羹改嫁。调羹要求回北京,于是狄希陈派人把调羹母子送到北京,使得素姐相信自己独占家产的计划获得了完全成功。但实际上,狄希陈瞒着素姐,把素姐知道的田产房屋留到自己名下,而把素姐不知道的田产房屋分给了调羹生的儿子小翅膀。狄希陈拿银子让寄姐的母亲童奶奶在北京买了房子,派人把调羹母子送到北京与童奶奶、寄姐同住。在这个事件中,素姐为了独占家产而千方百计要除掉调羹母子,但由于大家合起伙来欺瞒她,她自认为获得的全面成功只是部分的成功。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素姐对小说现实中某些事态的认知不足会产生出乎她本人预料的结果。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素姐对现实的认知不足也明显地表现在她的整个人生故事上面。
四、命运的反讽
最后,我们对素姐故事的整体情节进行宏观层次的分析。一个事件的起因在微观层次上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一个事件的结果,它对人物命运的长远影响,有时在微观层次上却显示不出来,而只有在宏观层次上才能看得清楚。人物在一个事件中可能得到了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可能对这个人物的命运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时就会出现对这个人物的命运的反讽。
素姐故事的整体情节的意义,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分析。
在第一个层次上,素姐故事是一个女性打破各种社会规范的故事。根据前面第二节“欲望与义务的冲突”的分析,可以说在每一个事件中,素姐的行动都违背了一项或者几项当时社会的习俗、道德或法律规范。她的违规行动有时达到了目的,有时却没有达到目的;有时受到惩罚,有时却没有受到惩罚。但是,不管素姐在行动过程中是否遇到了挫折,也不管素姐行动的结果是否对她有利,如果说素姐的行动中有什么是前后如一、始终不变的话,那就是她一直致力于冲破社会规范对她行动的约束,坚持按照自己的欲望行动。因此,素姐故事首先是一个女性为了实现自己欲望而不断违背社会规范的故事。
在第二个层次上,素姐故事是一个女性亲手拆毁了自己生存保障系统的故事。素姐一直坚持与社会规范对抗,从而引起她与周围人物的冲突。这些冲突产生了严重后果,摧毁了她自己的生存保障系统。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个人的生存都有赖于一个保障系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女性的生存保障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丈夫、夫家和娘家。在素姐与社会规范的冲突中,她以严酷的虐待逼得丈夫离开她娶妾另外建立家庭,通过气死婆婆、公公而使夫家名存实亡,又因为一系列事件疏远了娘家人。她的行为不仅伤害了丈夫、夫家和娘家,而且也创造了使自己受伤害的条件,因为她逐渐地拆毁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保障系统。
第二个层次的故事,对第一个层次的故事构成了反讽。第一个层次的故事,描述了冲突发生的原因。第二个层次的故事,描述的则是冲突发生的结果。在第一个层次的故事中,素姐坚持按照自己的欲望行动,从而引起了与社会规范的冲突。代表这些社会规范的是素姐的家人,包括丈夫、婆婆、公公、父亲、弟弟等人。因此,与素姐直接发生冲突的,并不是抽象的社会规范,而是代表这些社会规范的人。素姐与自己的家人发生冲突,其结果是削弱了家庭的力量(如气死了婆婆和公公),或者减少了家庭对自己的支持力度(如疏远了丈夫和弟弟)。拆毁自己的生存保障,这并不是素姐行动的目标。素姐行动的目标,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满足自己欲望的过程中,素姐无意之中拆毁了自己的生存保障。素姐的为了满足自己欲望而采取的违规行动,最终使自己陷入生存困境。这就是对素姐命运的反讽。
以素姐控制家产的欲望为例。为了实现这个欲望,素姐气死了婆婆和公公,逼走了调羹母子,她对狄希陈的虐待逼得狄希陈到北京娶妾另外建立家庭。到了这个时候,素姐独自一人占有了狄家的财产,可以说心愿完成,应该感到满足了。素姐的确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她不懂得农田经营,也不会管理家政。周围的人不再像往日那样看在狄员外、狄希陈的面子上照顾狄家,而是开始派她与其他家庭一样平摊杂役差徭,而她又要供养她所敬仰的两个道婆的家庭生活费用。于是,她感到经济上支持不住了,算计着要到四川去投奔狄希陈。“如欲不去,家中渐渐的不能度日。”*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袁世硕、邹宗良校注,第1249页。素姐的欲望目标是独自占有家产,但她独自占有家产的结果,却是落得自己无法度日。她的欲望目标的实现,最终反过来伤害了自己。这无疑是对素姐命运的反讽。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素姐的命运遭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反讽,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欲望不符合当时社会为女性所设立的各种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对现实缺乏认知。素姐不懂得,在她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她的生存有赖于丈夫、夫家和娘家的支持。素姐的无知使得她无所顾忌地拆毁了自己的生存保障。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素姐对现实的无知导致了命运的反讽。
五、结 语
素姐故事叙述了素姐的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冲突的起因和结果。素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地打破社会规范,而这样做的后果,则是无意之中拆毁了自己的生存保障系统。素姐实现了自己的欲望目标,但目标的实现反过来伤害了自己。因此,素姐故事的结构是一个命运反转的情节结构,而故事情节所传达的意义,便是命运对素姐的欲望和无知的反讽。
从《醒世姻缘传》所运用的命运反讽中,可以归纳出作者西周生对于现实和人生所持有的如下见解。其一,个人的欲望和行动受到社会制度的约束。其二,个人命运受到自己认知能力的限制。其三,个人命运是由自己的行动造就的,但是由于个人是在对现实缺乏认知的情况下行动的,因此不受社会制度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欲望去行动不一定对自己的命运有利,反而有可能遭到命运的嘲弄。《醒世姻缘传》所表达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清醒地看待现实的理性人生观。
《醒世姻缘传》对素姐故事的叙述,从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不同角度考察了女性与家庭的依存关系,表达了对女性凌虐丈夫、忤逆公婆、不守妇道等行为的否定,指出了这样做的后果等于毁掉了女性自己生存的基础。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素姐的行动表明她所信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而《醒世姻缘传》作者所表达的则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占据主流地位的家族主义。如果说小说作者对素姐的个人主义行动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作者并不单纯是从维护男权的角度,而是同时从维护女性生存的角度来表现这个问题的。通过素姐故事,《醒世姻缘传》从十分现实的角度考察了个人命运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密切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