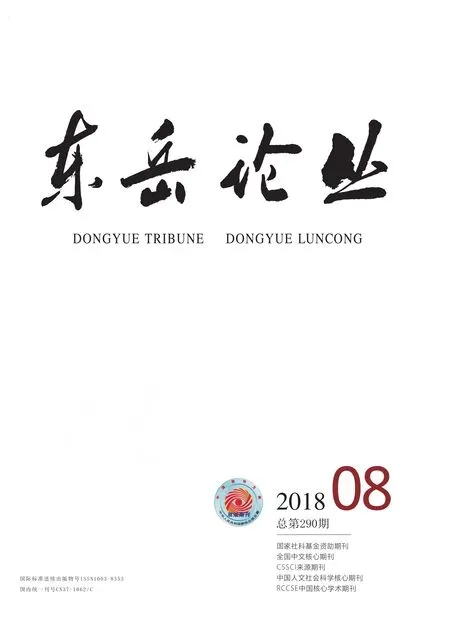“邓丽君热”文化研究:私人经验与现代听觉变革
刘欣玥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交接的年代”:从王蒙笔下的“邓丽君热”说起
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Andrew F.Jones)曾提出,考察现代中国的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文化史,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与政治变迁及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纠缠。“在长达七十年的历史话语中,中国的流行音乐始终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牵制,既为后者服务,也与之斗争。在20世纪中国复杂的政治角力之下,流行音乐的发展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投影。”①F.Jones,Andrew.Like a Knife: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1992,p.10.笔者注:安德鲁·琼斯写作本书的时间是1990年前后,引文中的“七十年”,指的是始于1920至1930年代上海的中国流行音乐史,至九十年代大约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琼斯对中国革命和音乐意识形态性的理解,及其对“历史的投影”的基本判断仍然有效,或可与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所提出的“声音政治”形成更复杂的对话。所谓“声音政治”,即是关于声音的生产、控制、传输、接受等诸环节的政治,而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即为“声音”与“政治”、“音乐”与“权力”的缠绕和互动②具体可以参考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2期。。在1977年出版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里,阿达利首次提出了“音乐”与“噪音”这对辩证概念,并为声音如何参与政治秩序的塑造和维护提供了一套解释性的理论逻辑。“是声音和对它们的编排塑成了社会。与噪音同生的是混乱和与之相对的世界。与音乐同生的是权力以及对它相对的颠覆。”③[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通过差别化的方式,权力让人们把一种声音视为颠覆性的“噪音”,而把另一种声音视为有秩序的“音乐”,从而对“噪音”进行压抑和控制。在阿达利看来,由于音乐本质上具有隐喻的向度(dimension métaphorique)和预言性(prophetic),“倾听”音乐,就不仅是在倾听现实中意识形态的流转与对峙,也是在倾听超越日常生活层面的未来①Attali,Jaques.Nois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11.。
从阿达利到琼斯,无论是权力秩序更替的“预言”,还是政治角力的“投影”,都揭示出现代声音与社会历史变迁深刻的同构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及现代性的“问题与方法”。具体而言,随着“声音政治”或“听觉现代性”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历史被添上了“音轨”,尚未被学界有效开发、整理、讨论的“有声的现代中国”已经浮现。包含音乐在内的“声音”的百年嬗变,富有文化意义的听觉空间的错动,听觉感官的规训,到听觉行为习惯的变迁等等,都需要得到更为具体的梳理和探讨②在文化研究领域曾长期重视“视觉”而忽“听觉”,在欧美学界前沿方兴未艾的声音研究(sound studies)近年来也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注意,并开启了理论引介、话语范式建构及本土实践尝试的一系列学术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开大学的周志强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敦副教授。具体可参考王敦:《流动在文化空间里的听觉:历史性和社会性》,《文艺研究》,2011年第5期;王敦:《听觉文化研究:为文化研究添加“音轨”》,《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王敦:《“声音”和“听觉”孰为重——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港台流行音乐传入大陆的邓丽君歌曲走红,作为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出现的“听觉文化事件”,成为萦绕在一代人耳畔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邓丽君低吟浅唱,温软甜美的歌声,对于习惯了革命音乐“高、强、响、硬”的大陆听众的冲击,在于率先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让人知道“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唱”③李治建:《启蒙与流行:中国大陆20世纪70、80年代邓丽君歌曲》,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作家王朔曾用“先声夺人”形容初次聆听邓丽君的“动情”体验:“台湾人是后来的。他们人进大陆前,已经先声夺人。我指的是邓丽君的歌。……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④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天涯》,2000年第1期。用乐评人金兆钧的话说,“邓丽君是一座桥,沟通和启发了大陆一代青年人的情感和耳朵”⑤金兆钧:《来也匆匆,风雨兼程——通俗歌曲十年观》,《人民音乐》,1990年第1期。。回顾20世纪非均质的历史进程,剧烈错动的转折时刻,也往往是声音表现最为活跃、混乱的时期,亦即阿达利所说的“交接的年代”(intervening period)。稳定的“音乐”符码所对应的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被打破,伴随着“噪音”涌入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转轨的征兆,“交接的年代”成为“声音政治”释放出丰富信号的关键时刻。“邓丽君热”之于听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其不仅是历史转轨时期的一面镜子,更以“噪音”之姿,直接参与乃至推动了一场深刻的“现代听觉变革”⑥不无遗憾的是,不仅目前两岸三地对“邓丽君现象”的研究兴趣寥寥,仅有的学术讨论成果也大多局限于流行音乐史研究,从音乐成就、演唱风格、审美特色与流行成因分析等角度展开。参见祝欣:《邓丽君研究综述》(《东方艺术》2014年第A2期)一文,确如祝欣所言,“有关邓丽君的研究,成果不少,但相对于邓丽君所承载的大众文化的丰富和复杂而言,仍然留有不少新的研究空间。”赵勇、祝欣的《邓丽君、流行音乐与 20 世纪80 年代的批判话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生成语境分析之一》一文,从大众文化价值的角度对“邓丽君热”展开了较为有效的分析。。
而在回忆录、音乐界争鸣、媒介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变迁史等资料之外,作家王蒙在新时期“复出”之后的一系列小说,也为“邓丽君热”探究提供了一份非常独特的参考样本。1979年末到1980年初夏,重返北京的王蒙在短短数月中接连发表了短篇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和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在这些文本中,可以发现大量“声音”元素的积极参与。与同时代作家相比,王蒙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些“有声”的文本,勾勒出历史现场“众声喧哗”的声音风景⑦这些“声音元素”具体表征为对语音、音乐、歌声、以及声音的传播媒介的文学修辞与文学叙事。对于王蒙这一时期创作中的声音政治分析,可参见刘欣玥,赵天成:《从“革命凯歌”到“改革新声”:“新时期”与王蒙小说中的声音政治》,《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1期。。与大量传记和回忆资料不同,王蒙的小说作为一份特殊的“社会档案”,不是经过沉淀与过滤的“后见”,而是一种与历史进程共时空的书写,因而既记录了“声音”本身,又同时呈现了使“声音”获得意义的具体语境与参照体系,避免了因为语境变换而产生的“失真”。在王蒙笔下的声音风景中,“邓丽君”恰恰是多重话语汇聚、交锋的焦点。在中篇小说《蝴蝶》里,官复原职的老干部张思远,从录音机里听到了邓丽君的名曲《千言万语》: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常围绕着我,
每天我都在祈祷,
快驱散爱的寂寞……
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风靡全国。原来他并不太知道。他只是恍惚听说许多青年在录制香港的歌曲。那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对于香港的文化,他从来没有放在眼里。……一首矫揉造作的歌。一首虚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
歌词中对爱情的祈盼和邓丽君缱绻的唱腔,都是具有“异质性”的元素,立刻引起了老干部的强烈不适。但张思远继之而来的一连串自反性的疑问,又让我们看见了这位听着军歌与革命进行曲长大的老人的游移态度。其微妙处,正在老人对“爱的寂寞”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的思考,言语之中,似又通过对文革时期“大喊大叫”的声音情状的否认,透出些许肯定:
这首歌打败了众多的对手,即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甚至是一首昏昏欲睡的歌。也许在大喊大叫所招致的疲劳和麻木后面,昏昏欲睡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必然?①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
王蒙本人曾在自传中谈及1979年春在新疆初次聆听《千言万语》的回忆,当时作家刚刚从北京“平反”归来,而邓氏歌曲已经在遥远的新疆文联四处流传。“我听了两次,觉得不错,调调记了个八九不离十。但我只是莞尔一笑,没有说一句邓丽君歌曲的好话,说明其时我对意识形态问题仍抱有极其警惕与慎重的态度。从此我知道了个词叫‘爱的寂寞’,这个词是否通顺,是否无病呻吟,我一直抱着疑问,但它带来了另类的感受,另类的信息。”②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作家所说的“另类的信息”,一方面来自闻所未闻的甜美歌喉本身,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禁止”与“禁止不住”之间政治气候“回暖”的信号。王蒙“不敢说好话”的谨慎,或张思远对其存在合理性的思考,都是厌倦了文革“大喊大叫”“大鸣大放”的一代人,猛然在新时期之初在听觉中与邓丽君相遇的真实反应——这种面对邓丽君既“不适”又“游移”,即抵抗又吸引的矛盾,作为改革初期的某种历史“投影”,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颇具意味的是,在对“爱的寂寞”进行冷嘲热讽时,张思远直接将它放置在“左翼音乐传统”的对立面,视作与“音乐”相抵牾的“噪音”:“现在是怎么回事?三十年的教育,三十年的训练,唱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好’、‘年青人,火热的心’,甚至还唱了几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之后,一首‘爱的寂寞’征服了全国!”③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曾经热火朝天、朝气蓬勃的集体合唱与无病呻吟、谈情说爱的“靡靡之音”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道德与趣味双层意义上的“低俗”和“不健康”仿佛不言自喻。王蒙下意识的对比思考本身,也通向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被邓丽君的歌声所冲击和撼动的,不仅是收音机、录音机前一个个聆听的个人,更是曾经由抗日救亡音乐、“进步群众歌曲”乃至“语录歌”筑成的左翼激进革命音乐秩序。这一秩序的正统地位正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战。七八十年代之交,“靡靡之音”与“革命歌曲”表面上只是人们不同的听觉好恶与选择,但从演唱到传播,二者对主导地位与合法性的争夺,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与政治意识形态深度纠缠的“听觉变革”——之所以称之为“变革”,是因为无论是歌曲内容、演唱方式还是传播途径、收听方式,每个环节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而最终作用于新时期人的听觉与情感。兼具“聆听者”与“写作者”双重身份的王蒙,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声音历史变迁,其小心翼翼的构思与商榷,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极具症候性的在场心态。但彼时的王蒙,也许能够认识到邓丽君歌曲的政治意味“是一种宽松与和谐的符号,而不是动辄一脸悲情的阶级斗争硝烟”④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却未能说清,“谈情说爱”的歌曲为何引起其本能的不安?邓丽君“矫揉造作”的嗓音又是如何打败众多歌手,征服了青年一代的耳朵?究其根本,其“另类的感受”,究竟是何种“感受”,又为何“另类”?
二、“爱情的位置”:情歌回归与感官革命
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很快引起了大陆音乐界的剧烈震动,尚未摆脱阶级斗争思维的主流乐评家与学者,将之扫入为“腐朽”“萎靡”的资产阶级艺术阵营而大加批判。1980年2月,《人民音乐》编辑部在北京西山举办会议,重点讨论当时的流行音乐问题。在这次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的座谈会上,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而由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同样因为模仿邓丽君的“气声”唱法而受到了批判。直至1982年,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邓丽君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却仍是多篇批评“不健康”的港台流行歌曲的文章的实际攻讦对象。虽然复杂的、半地下的传播生态,让我们无法确切获知邓丽君传入大陆的详细歌曲名单,但根据当时的报刊文章及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何日君再来》《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美酒加咖啡》《香港之夜》等等,是最常被提及的曲目。不难看出,“爱情”是这批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共同的题材。在建国以来长期警惕“爱情”,往往将情歌粗暴地等同于“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乃至“黄色音乐”进行消灭的语境里,“邓氏情歌”招致猛烈攻击,无疑是新中国既有的革命音乐秩序的惯性所致。无论是歌词里缠绵悱恻的情感表达,还是柔声细诉的吟唱方式,对大陆这个唱惯了“战斗进行曲”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来说,已经太过久违以至于陌生了①将“战斗的进行曲”与“抒情歌曲”对立的思路在七八十年代的音乐界讨论中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譬如在1979年发表于《人民音乐》的《抒情歌曲杂谈》中,乐评人施光南就将当代中国的音乐传统分为“轻、软”的“抒情歌曲”和“高、快、硬、响”的“战斗性的进行曲”,反对音乐界一直以来用后者压抑前者的做法,更明确提出反对“爱情歌曲即黄色音乐”的“清规戒律”。见施光南:《抒情歌曲杂谈》,《人民音乐》,1979年第6期。。
在笔者看来,时人围绕邓丽君的“人性复苏”“热爱生活”“普通情感”“撩动情欲”等纷繁、直观、感性的表述,其实都内嵌于音乐世界呼唤“抒情”与“爱情”的共识与共鸣之中②“它(邓丽君的歌)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十分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唤醒了人性,告诉我们日常生活是如此值得珍爱、……人们把它当做了人性复苏的先声。”见陶东风:《邓丽君:歌声依旧在人间》,《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那时你听那种歌,简直是天籁!……那时刚开始发育,身边又没有任何爱情歌曲,你一听到邓丽君这种甜蜜的、异性的声音,真的是……音乐的震撼力,那个时候是最强的。”见周云蓬:《春天责备》,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经由音乐语言的转译,这一共识,同样在声音的层面上触及到了八十年代复苏的人文精神中一个关于“情”的核心命题。可以说,重新肯定“爱情”与“个人”的情感价值,是文革后大陆文艺界“拨乱发正”的普遍潮流,在冠以“伤痕”之名的文学和电影创作中,都有过人们更为熟知的表达。在这里,有必要注意到的是,由于音乐创作自身的特殊性,加之建国以来流行音乐产业的先天不足与多年荒芜,大陆音乐界的复苏与本土创作“突围”的进程,实则比文学、电影等领域要缓慢和谨慎,“禁区”迟迟没有突破也曾引发一些不满③见广源:《禁区为什么还未能突破?》,《人民音乐》,1979年第6期。。在大陆的创作界还小心翼翼地在“禁区”的边缘摸索时,脱胎自港台成熟的流行音乐产业、漂洋过海而至的邓丽君带来的听觉经验,从内容到形式,从歌词主题到感官体验,都是前所未闻的。其“超前性”的冲击与示范可想而知,也率先让音乐世界找回了失却已久的“爱情的位置”。
回顾“爱情”与“情歌归来”引起的骚动,无论是民间的心驰神往,还是官方的口诛笔伐,都指向了同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人们通过音乐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的需求,而另一方则是中国当代音乐长期压抑个人情感的生产机制所留下的情感空洞,尚不能填补大众“解禁”以后的心灵需求——这一矛盾,自然激发了对本土情歌创作的呼唤。1978年9月,中国音协在武昌召开声乐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声乐作品的现状,与会专家一致注意到“题材不广泛;表现形式不多样;音乐语言比较贫乏。体裁、形式上,战斗进行曲多,抒情曲少,爱情歌曲几乎绝迹”等问题。“抒情歌曲和爱情歌曲是非要不可”成为本次讨论的共识,虽然这一肯定,携带着明显的左翼文艺话语限定④“写抒情歌曲,应遵照周总理关于音乐‘三化’的教导,创造出具有无产阶级的健康情感、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符合广大群众审美要求的抒情歌曲。”见王思琦:《当代语境中的“时代曲”、“抒情歌曲”、“轻音乐”概念的使用与分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而面对作为反面教材的“不健康”港台歌曲的风靡,也有国内的乐评家大胆呼吁不以阶级性划定主题,拓宽抒情歌曲的题材,并单独强调了创作爱情歌曲的重要。“不能一接触生活,甚至表现个人感情,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创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某些外来歌曲却在这些方面填补了人们对歌曲题材多方面的需要这个空白。……必须写出更多样化的抒情歌曲,包括爱情歌曲。”⑤施光南:《抒情歌曲杂谈》,《人民音乐》,1979年第6期。将“爱情”从阶级斗争的“禁区”中解放出来,创作出“自己的”爱情歌曲,成为了一种比“一面倒”的讨伐更为冷静的回应态度。有趣的是,邓丽君作为“文化他者”,实际上是在被官方否定的基础上,发挥了一种“反向的启蒙效应”。
正如开篇所提到的,邓丽君对于“爱情表达”的“启蒙”与“示范”,一方面是其歌曲在内容与题材上的拓展,即“唱什么”;另一方面则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听觉乃至身体,即“怎么唱”。邓丽君带来了一种陌生的,绵软而迷人的听觉感受,被人们纷纷形容为“没有听过的声音”⑥王彬彬曾著文表达相似的感受,“听了十年‘样板戏’,听了十年‘语录歌’,初听邓丽君,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我们谈到‘八十年代’的‘启蒙’时,邓丽君的歌似乎也不妨谈一谈。邓丽君也以自己的方式,对一代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这是审美意义上的启蒙,也是情感和人性意义上的启蒙。”王彬彬:《诗忆》,《黄河文学》,2010年第12期。。其令听者感到或愉悦,或不安的秘密之一,正在独特的扁韵咬字和以气裹声的、“柔声低吟”(crooning)唱法。对于这种唱腔的直观体会,王蒙在短篇小说《夜的眼》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①值得一提的是,王蒙的发声也提醒着我们,对于邓丽君歌曲的“抵触”其实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除了其所“代言”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个层面指向文化受众的代际变化。拒绝或抵触邓丽君,可能不仅仅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危险”自觉,还可能与一代人特殊的情感记忆、听觉训练与审美习惯有关。邓丽君将大量气声的运用与自己温软的音色结合,发展成为极具个人特色的唱嗓。这种唱法,“几乎让邓丽君的听众有一种耳朵被吹气的错觉;独特的软语呢喃,使得邓丽君的歌声仿佛是一封封悄声说着体己话的私密情书。加上录音技术的进步,她清晰又不失真的声线带给听众的浓烈亲密感,是当时或先前的国语歌手都无人可及的。”②洪芳怡:《邓丽君、国语流行音乐史与历史记忆》,《歌唱世界》,2013年第3期。对刚刚从极权年代与政治压抑中走出来的大陆听众而言,这种柔软的、甜美的声音带来的情感启蒙和身体暗示,不仅满足了时人对抚平创伤、宣泄深藏已久的情绪的需求,也直接经由声音启迪了另一种生活想象:不同于充斥着刺耳的高音喇叭与锣鼓喧天的政治运动的“公共空间”的生活,而是隶属于亲密的“私人空间”,能够自由表达细腻、普通却真挚的“人情”的日常生活。
在教会了人们“用嗓子的另一个部位唱歌”的同时,邓丽君唱腔中蕴含的“情欲”意味,早在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这种“性别化”(sexualized)或“情欲化”(eroticized)的声音,招致了对邓丽君,以及最早一批模仿邓丽君的大陆歌手的猛烈批评③这批歌手包括李谷一、陈明、程琳,甚至更晚的田震、王菲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80年前后批李谷一的“《乡恋》”风波。对于80年代批判邓丽君、李谷一等人的文化事件梳理,可参考赵勇,祝欣:《邓丽君、流行音乐与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话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生成语境分析之一》,《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1期。。曾有研究者如此分析:“当歌唱者用自然的发声(即本嗓)来歌唱时,如果模仿(不论自觉与否)了生活中表现情欲的人声效果,就一定使听众在生理上或心理上下意识地‘回忆’或感受到某种情欲。”④蒋一民:《论音乐审美的低级趣味》、《论音乐审美的低级趣味》(续),《人民音乐》,1985年第1期、第2期。虽然论者的本意是批判“低级趣味”和无节制的感官沉湎,但对“发声方式”与“情歌的‘意味’”的关系,对于气声唱法造成的听觉快感分析,实已为我们打开了在“感官革命”层次一探究竟的入口。如果说“情歌归来”承载着“爱情”在音乐叙事层面从合理到合法的步步争取,那么耳语般的气声唱法与及其对情欲的鼓励性暗示,则恰恰是在生理层面实现了一次感官的“解放”和苏醒。如学者周志强所言,邓丽君这种缠绵悱恻的唱法,直接开启了声音“性别化”的潮流,用有“性”的声音代替了曾经“无性”的声音,构造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⑤周志强:《“唯美主义的耳朵”:“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与声音的政治》,《文艺研究》,2013年第6期。。
最后值得补充一提的是,“柔声低吟”唱法的首创者不是别人,正是三四十年代风靡上海滩的歌星周璇。邓丽君无论是在演唱方式,还是翻唱曲目上(如周璇名曲《何日君再来》)都能看到“继承”周璇的痕迹。因此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当时批评者用以攻击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黄色音乐”乃至“时代曲”的话语,都有着切实可寻的历史渊源和依据。这些“标签”源自于二三十年代以黎锦晖、陈歌辛等人为代表的上海都市流行音乐创作,而引领上海滩歌舞厅与唱片业摩登的“时代曲”,正是中国流行音乐史话的起始点⑥关于上海的都市流行曲与中国流行音乐史的论述,可参考居其宏:《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屠锦英编著:《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代表作品评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从上海、武汉到延安,以抗日救亡与政治动员为主导的左翼音乐运动在逐步扩大自己的版图,包括“时代曲”在内的不少市民阶层通俗歌曲,被定性为格调庸俗,魅惑人心,消弭战斗意志的“黄色音乐”而饱受挤压——这一切,几乎是大陆音乐界批判邓丽君的历史预演。随着左翼文艺的逐步政治化与极端化,服务于意识形态灌输的“齐声合唱”成为革命音乐秩序的象征物与集大成者,而表达个人心迹的“独唱情歌”,只能随着“时代曲”的噤声流入海外与港澳台等地,在大陆版图之外落地开花。在20世纪大众音乐秩序的光谱上,如果说“民族/国家/集体”与“个体”话语对合法地位的争夺,曾经以“集体”战胜“个体”而告终,那么这一次则是“个人”的反败为胜——由邓丽君的歌声重新构建的个人本位的世界里,爱情话语穿透了曾经看似坚固的集体抒情范式,也辗转带回了一个沉寂多年的音乐传统。
三、“流动的禁区”:盒式录音机与“私人听觉空间”的雏形
面对同样陌生的邓丽君,有人听到了“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的“危险”,有人听到了“痛楚的启蒙”,有人听到了“人性的苏醒”。这些截然不同的听觉感受与心灵反馈,彰示出“声音”与“耳朵”之间的复杂张力,绝不单纯是个人趣味的好恶之别。因为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声音”与“耳朵”本身都是被社会、经济、政治所形塑的产物:“声音”本身无所谓意义,只有经过听觉感知和解释群体的界定与评价,才能被赋予好恶美丑等不同的价值①更为详细的相关讨论可参考王敦:《“声音”和“听觉”孰为重》,《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而“耳朵”也并非纯粹天然的身体器官——“耳朵”能够听到什么、如何聆听,同样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合力而为的“规训”机制。就像安德鲁·琼斯提醒我们的,“技术”(technology)同样是我们在探讨中国流行音乐现象时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②F.Jones,Andrew.Like a Knife: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1992,p.8.——在“邓丽君热”的文化现象背后,除了上文提及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意识形态变迁,在媒介技术层面,盒式录音机与磁带文化的出现,同样构成这场“听觉变革”的重要面向。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贸易政策松动,盒式录音机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开始渐次流入内地,形形色色正版走私、盗版刻录、听众自行翻录的音乐磁带,也同步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其引发的七八十年代音乐传播媒介、播放-收听空间的变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音乐的性质与功能,更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一代人与“声音”的关系。如果说上文讨论的大众情感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解释,那么盒式录音机与磁带则开启了从物质技术层面认识“邓丽君热”的可能。
虽然在1978年之前,不少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短波收音机“听敌台”,偷偷收听来自台湾、香港乃至澳洲国际广播电台中的邓丽君歌曲,台湾中央台甚至专门开设了针对大陆听众的广播节目“邓丽君时间”作为实施“心战”的手段③有关当时“偷听”邓丽君的情况,可参考马多思:《偷听邓丽君的日子》,《文史博览》,2103年第11期,高小康:《从“偷听”到“催眠”》,《歌海》,2001年第1期。。在政治空气依然紧张的年代,这些仅限于小范围的、不稳定、带有鲜明“禁忌”意味的“偷听”,显然无法与日后邓丽君大规模的传播相提并论——情势大约在1978年左右发生了改变。“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重获生机,进而席卷各地,实在是很短时日内的事情,它始自1978年底政府宣布收音机与录音机被允许放宽自港澳带返国内之时,港澳、台湾等的流行曲,便通过卡式录音带、收音机、经由回乡探亲的港澳侨胞带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④毕小舟:《从闭塞到交流的中国大陆歌坛——1979年国内乐坛的一个剖面》,《国外音乐资料》,1980年第五辑。转引自李治建:《启蒙与流行:中国大陆20世纪70、80年代邓丽君歌曲》,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音乐史研究者居其宏则将流行音乐的“复苏”直接归功于盒式录音机:“对流行音乐在大陆重新出现影响最大的是卡式录音机,卡式录音机在城市青年中的渐渐普及为港台流行音乐的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⑤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录音机或收录机成为紧跟时代潮流的新事物,这其中邓丽君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磁带和录音机成为普及邓丽君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尽管具体的走私途径与内地的销售渠道至今仍然隐秘不明⑥徐敏:《消费、电子媒介与文化变迁——1980年前后中国内地走私录音机与日常生活》,《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
相比于欣赏方式上带有单向性、被动性与强制性的广播(更不用说更早的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全面覆盖的“高音喇叭”了),磁带技术挑战了从前由唱片和广播所构筑的媒介公有制体系⑦张谦:《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转型脉络中的中国音像业与通俗音乐传播——以“中唱”为研究个案》,《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3期。,从文化产品上带给了听众的“耳朵”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播放媒介从“公共”走向“私人”,解放大众的双耳,音乐文化产品自主选择权的出现,都可谓是革命性的。作为受欢迎程度遥遥领先的港台歌星,邓丽君的歌曲传入最多,流传最广,以至于在一代人的回忆里,“盒式录音机”几乎成为与“邓丽君”形象共生的文化符码。就像一位亲身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学者所说的:“邓丽君刚进入大陆的时候,我们是用双卡录音机听的。邓丽君的声音弥漫在胡同和街道上。等到双卡录音机的时代过时以后,当80后、90后开始习惯插上耳机听音乐以后,他们对邓丽君魅力的认同已经就缩水了。对我来说,不用双卡录音机听的邓丽君就不是邓丽君。”①王敦语,见王敦、周志强2016年9月2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对谈整理:《寂寥的“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李泽坤整理,《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3日。
值得一提的是,王蒙也在本时期的创作中频频提及“进口录音机”,且凡出现“录音机”之处,往往伴随着邓丽君或其所指代的“港台歌曲”。王蒙有意识地将其放置在时代与代际的“新-旧”矛盾之中,可以作为一份特殊的“亲耳所闻”(earwitness)的现场实录。虽然在小说家用文学书写捕捉这一“新媒介”的1979年前后,方兴未艾的录音机文化,尚未释放出它对于后来八十年代文化变革的全部能量,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蒙对“进口录音机”蕴含的时代寓言性和文化预言性是高度自觉的②最典型的表现,当属以一台“闷罐子火车”上的录音机为“文眼”的《春之声》。王蒙多次谈到过这一场景的象征意义。“在落后的、破旧的、令人不适的闷罐子车里,却有先进的、精巧的进口录音机在放音乐歌曲,这本身就够‘典型’的了。这种事大概只能发生于一九八〇年的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既有时代特点也有象征意义。这怎么能不令我神思,令我激动,令我反复咀嚼呢?”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譬如在《蝴蝶》中,张思远起初只是“恍惚听说许多青年在录制香港的歌曲”,终于“从一个贸易公司采购员所携带的录音机”那儿听到了“爱的寂寞”(盛怒之下,张思远的第一反应是“想砸掉这个采购员的录音机”)。在《夜的眼》中,因为小伙子不肯把那台“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的声音调小,“香港‘歌星’的声音”不断干扰着主人公的发言,让他变得结结巴巴,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录音机里发出的电磁声响干扰着老一辈人的政治敏感的神经,也撩拨着文革后一代年轻人面对新生事物蠢蠢欲动的心灵。可听而不可见的歌声,经由引领潮流的磁带和录音机而被实体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复苏的自由市场中,成为引领时尚的文化消费品——与录音机浑融一体的邓丽君的歌声,既是特定年代的文化产物,更是充满了魅力的商品,深深烙进一代人的文化记忆里。
与此同时,同样不可忽略的是王蒙笔下“许多青年在录制香港的歌曲”的情节,这一现象确有史证可考:在那个版权意识薄弱,相关法规尚未到位的年代,年轻人竞相翻录、流传邓丽君的磁带的朴素、高涨的热情,即使官方三令五申也无法扑灭③雷颐的论述也可供参考:“1979年随着国门初启,中国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暌违已久的流行音乐。‘流行’的再次流行,当然得益于‘初春’的政治气候,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盒式录音机这种‘新技术’的引进,大量‘水货’录音机和港台流行音乐磁带如潮水般涌入,进入千家万户,翻录成为家常便饭,实难禁止。”见雷颐:《三十年前这样“批邓”》,《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这提示着我们,录音机带来的文化变革,不仅发生在自由选择及消费的层面,更落实在自主储存、制作、编排声音等主体色彩更为强烈的行动及其象征意味上。这场以年轻人为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声音复制运动”,首先与大陆获得了大量生产空白录音带的技术条件密不可分,“这些空白带为流行音乐的私人化保存和私人化传播提供了极大方便”④1979年1月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出版了新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第一张CD、第一套中国录音影集,开创了新中国音像事业先河。但它对流行音乐最重大的贡献应是它出产的空白带,这些空白带为流行音乐的私人化保存和私人化传播提供了极大方便。见张燚:《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人文解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其次,“翻录”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推动了大陆音像产业初步的商品化,“当时,在大多数甚至的音像商店里,都可以为顾客转录港台流行歌曲,这样人们就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得到港台歌星的演唱录音”⑤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总而言之,在这里,“翻录”触及到了录音机媒介文化的另一重意义,即在民间与官方之间对“声音制作权”的争夺。因为录音机不同于收音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具有自主灌制、转录、擦洗磁带的功能。在这个“声音走私时代”,通过“声音复制”而“自主制造声音”的意义,是令公众的角色从被动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变成了声音的生产者⑥张闳《现代国家的声音神话及其没落》,朱大可,张闳主编《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 2005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因此在一代人与“声音”的关系上,如果说听众获得了多元、个性化的“聆听自由”是第一个改变的面向,那么首次取得了自主“发声”的能动手段则是第二个面向。而在笔者看来,盒式录音机因其便携性(因此亦会被称为“便携式录音机”),带来的播放-聆听经验的流动性,并因此推动听觉空间的移动与私人听觉空间雏形的出现,则可看作是变化的第三个面向。
海克·韦伯(Heike Weber)曾在一篇讨论“移动收听”行为(mobile music listening)的文章中谈及,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便携式音频技术(portable audio technology)塑造了西方一代年轻人的听觉记忆,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20世纪下半叶电子设计与消费中最重要的特点。便携式技术和听觉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塑造了革命性的当代听觉文化,便携式录音机就是这一文化脉络中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移动听觉装置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可移动的聆听方式,直接挑战了之从前固定在特定空间内(如音乐厅、剧院、节日现场、沙龙客厅等)的音乐演奏与欣赏习惯。由于这种“突破”常常率先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似乎天然地容易引来“传统/老派人士”侧目。但对于年青一代来说,这种新的音乐欣赏形式不仅有效地培养了个体身份认同和消费群体归属感,更开启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听觉模式变革①Weber,Heike.“Taking Your Favorite Sound Along:Portable Audio Technologies for Mobile Music Listening”,Bijsterveld,Karin & van Dijck,José eds.,Sound Souvenirs:Audio Technologies,Memory and Cultural Practices.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pp.69-70.。七十年代末,便携式音频技术甫一传入中国,首先吸引的也是大批城市青年。以至于带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留长发、肩上扛着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已经成为八十年代颇具争议的“时髦青年”的典型形象,在今天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时代符号②参见金兆钧:《三十年流行音乐的变迁》,收入吴忠义主编:《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8年讲座精选》(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又如王蒙在《布礼》中也描绘过这种符号化的“时髦青年”(《布礼》,《当代》1979年第4期)。贾樟柯导演的电影《站台》(2000年),也曾对这样的“时髦青年”形象做了视觉-听觉双重性的还原与再现。。作为张扬时尚的象征,个性解放的代言者,便携录音机里的邓丽君,随着年轻一代(当然,不仅止于青年)移动的身体,将歌声的触角伸向了各个角落:学生宿舍、舞厅、大街上、汽车与火车车厢、公园……原来只能通过“偷听”才能触碰的“禁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借助便携技术进入了从前的通俗歌曲难以企及的空间。可以说,虽然那时候尚未出现耳机这种完全将私人听觉行为与外界区隔开来的设备,但在笔者看来,录音机形成的私人自主空间或小范围内“内部的公共空间”,已经可以被视为后来私人听觉空间的雏形。而在这场混杂着幻想与行动、叛逆与疗愈、跟风与标新立异的,复杂的聆听-共振里,“流动的禁区”逐渐为自己收获了更多的认同,并逐渐为其自身的“解禁”,为其后来从暧昧到公认的存在合法性争取到了更大的话语权力。
结语:邓丽君与“现代听觉变革”中的私人经验
在讨论完个人情感与情欲化的听觉感官革命,录音机文化所孕育的私人听觉空间的雏形之后,如果我们重新回头去理解金兆钧所说的“邓丽君启发了大陆一代青年人的情感和耳朵”,或许就能够看到,一场以“私人经验”为核心的“现代听觉变革”的不同面向已渐次浮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从“偷听”到“偷渡”,正是邓丽君的情歌漂洋过海而来,唤醒了一次大众从“耳朵”到“情感”的革命性共鸣。首先,在歌唱-聆听的内容中,曾经沦为边缘的个人化的抒情主体,终于从多年被“充公”的集体主义表征中脱落、回归,尤其以爱情为代表的私密经验,正在深情、缠绵的旋律中成为新的日常经验——虽然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对“后革命文化”孕育、熏染的新的历史主体而言,此处的“私人/个人”想象或许只是另一次集体性的幻觉。其次,是一种情欲化的、亲密私语化的演唱方式对于感官的唤醒,在经历了以邓丽君为发端的争议之后,终于因为“通俗唱法”的正式命名而在声乐界获得一席之地。最后,在传播媒介的层面,录音机和磁带技术为人们带来了音乐产品的聆听选择权、自主制作权,以及聆听行为与聆听空间的私人化、可移动化,深刻地改变了听众与声音的关系,也召唤出新一代聆听主体的身份认同。
这一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个历史转轨的特殊时期,与“邓丽君热”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了深刻的纠缠,并揭示出一种根植于当代中国本土经验中的“听觉现代性”。伴随着个人话语与告别革命的情绪愈演愈烈,曾经以政治性,集体性和公共性为导向的新中国音乐秩序出现裂痕,继而走向塌陷。随之而起的,是商业化、私人化、娱乐与审美化,甚至是视觉化的声音新潮——而邓丽君只是它的序章,或一个非常特殊的过渡性的产物。此后,以崔健为代表的中国摇滚乐将登上历史舞台,九十年代音乐产业市场化景观逐步酝酿成型,被“随声听”和耳机征服的更年轻的音乐消费者,也将重新改写公共与私人的声音秩序。但是,如果我们将大陆的一代人尚震惊与沉醉在邓丽君歌声中的历史时刻定格,侧耳细听——就像阿达利在谈论音乐的“预言性”时所说的那样,在邓丽君所构筑的声音风景里,我们已经听见了一种超前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想象的,截然不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