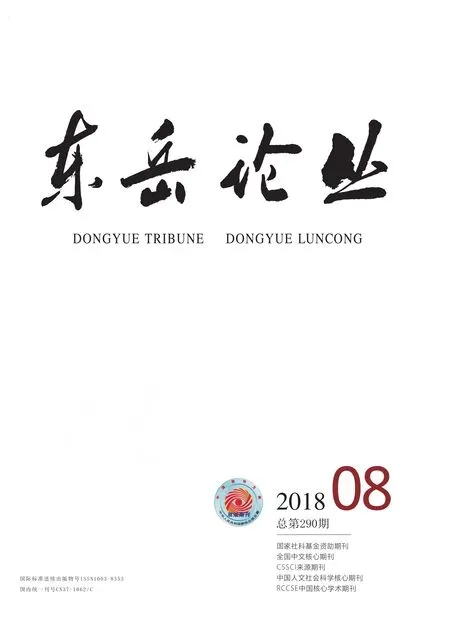乡村振兴战略下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文化理路
张海荣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序 言
近代以降,中国乡土社会固有的生态系统被迅速打破。裹挟于现代化洪流中的广大农村,如同叶叶扁舟,寓时势风浪里摇摆不定,日渐失去自己的底色与主体性,并不断遭遇困难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出于资源提取与社会治理、维系底层社会稳定和民族复兴等目的,各种建设力量,或党派、或团体与个人,前赴后继地努力至今,希冀找到同期困扰乡村发展之结,以便给出治本方案。
以20世纪初中期为例,官方的、民间的以及学院中的内外人士,大力开展农村调查,旨在发现摆脱乡村困境的“密钥”。尽管立场、出发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倚重翔实的实地调查,探索者们提出了颇为多元的观点和改造方案,并诉诸实践。若作些归纳,大体上可分为:(1)卜凯为代表的“技术学派”,认为中国农村落后是技术问题,改良技术即可;(2)乡村建设者所形成的“文化学派”,认为中国农村问题主要是“文化失调”和农民愚昧;(3)费孝通为代表的“产业学派”,认为中国农村落后在于单一的农业,土地改革只能解决生存不能解决富裕问题;(4)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是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制度造成农村落后,改变农村当从改变制度入手①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再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
中国乡域广袤且发展不平衡,这些解决农村问题的理路和方案,迄今仍不算过时。百年来,因社会变迁急速,农村问题事实上带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就新时代农村发展状况而言,成绩的背后依然潜藏着诸多羁绊。用历史眼光加以审视,不难发现:当下中国农村的发展困境,上述方案中所触及的问题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主要是缺失和谐自洽、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也就是文化价值的有力支撑。一如乡村建设者曾经的研判,在于“文化失调”。转型期,乡村文化失调导致农民“精神贫困”,严重制约着富有建设意义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致难以应对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不当趋利”“信仰滑坡”“风气不端”等种种颇为棘手的挑战。乡土文化要延续,就要进入到乡土文化的内部,深刻了解乡土公共文化价值内部的逻辑和关联,深入村民的精神世界,抓住乡土文化的意义之魂*李方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力转型与村治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藉此,重塑兼具传统与现代的适洽的乡村文化伦理及价值认同,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着重从农民的精神层面探寻破解农村问题的“柔性之道”,可谓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特别是,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样态最终取决于农民的精神高度。
一、精神贫困:转型期掣肘乡村发展之根本所在
转型期意味着整个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发生显著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分配形式等都有着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囿于传统和现代的制度交织、变与不变的观念共生、公与私的利益纠葛等,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的软实力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的精神世界比较贫瘠,此种状况被学界称之为农民的“精神贫困”。
从理论上讲,精神贫困可谓多层次、多内涵,相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及其要求而言,这是一个属于动态范畴的概念。本文特指转型期囿于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农民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是一个主要反映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畴*余德华:《论精神贫困》,《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深入分析农民的“精神贫困”,可结合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如学者所言:精神贫困是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理性的行为表现,其本质为个体失灵,是志向失灵和行为失灵的结果*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毫无疑义,农民的经济贫困乃至权利贫困较大程度上源于其“精神贫困”。在“双重失灵”的非理性观念支配下,农民不仅难以适应竞争激烈、复杂多变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且自身素质不断下滑,严重制约着乡村的发展。
(一)“德性失守”销蚀村庄的凝聚与和谐
个体失德与个体失灵如同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没有志存高远的目标,做事不理性、不守底线,自然谈不上有德;反之,缺失公德与私德,就不会有通力协作,所谓美好家园建设,“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如此类的抱负也就成为空话。转型期乡村虽不乏“德性之美”,越来越渗透了“失德之恶”。
具体地讲,邻里关系日渐冷漠,尊老爱幼美德受到冲击,传统的温情被磨蚀。令人忧思的是,人情冷漠不仅体现在邻里间,还弥漫于亲人中。有些乡域,老人得不到儿女善待是常有的事。有人在过年时节因病、饿、冻而去世;有的老人死在条件欠佳的私人养老院,子女竟迟迟不肯问津*近年来笔者在河北省若干乡村社会调查情况。。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变得“七零八落”,甚至伦理“倒置”。在许多农村,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赤裸,孝道日益衰落;年轻一代的兄弟关系也越来越离散*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老人无奈自杀现象时有发生,相关研究不乏其例*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与此同时,留守儿童被双亲忽略乃至遗弃伤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农村社区道德生活的退化*吴理财:《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变迁》,《人民论坛》,2011年第24期。,或曰伦理与德性危机。
孝经有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圣治章第九》)。现今的诸多农民,其亲与他人通通被抛诸脑后,自私自利,公德与私德大为缺失。随着村庄日益变成半熟人社会,村民流动频繁,“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态也难以维系。仗义执言、扬善抑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村庄无论大小,难有凝聚与共同奋斗的精神面貌。
(二)“心理失衡”削弱村庄建设的内外动力
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对广大农村农民而言,意味着同样要走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既然这一进程不可逆,需要农民积极主动地融入,尤其要打破传统中的封闭思维,秉持开放包容、通力协作、积极进取的良好心理状态。现实诉求与实际状况却相去甚远。
转型期受社会贫富差距大、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村庄治理不善等内外因素影响,乡村民众的心理日益变得多元复杂,落差与不平衡感逐渐加强。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少人会怨气十足,有着浓浓的受剥夺感*即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最早由美国学者斯托弗(Stouffer,1962)提出,其后经默顿(Merton,1968)的发展,成为了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它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Stouffer S A.Social Research to Test Ideas:Selected Writings.Free Press of Glencoe,1962.转引自:王浦劬,龚宏龄:《行政信访的公共政策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随之产生了外部归因情结。所谓外部归因,是从自身以外的原因寻找解释自身失败的理由。哪怕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个性、外貌或健康等个人因素造成,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美]埃里克·霍弗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在不平衡感的支配下,久而久之,他们的内心被羡慕嫉妒恨所占据,做人本该有的“公道”“诚实”与“感念他人之好”逐渐被忽视和漠视。
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以及“等、靠、要”心理的支配下,村民的政治信仰已无从谈起。与之相伴的,是闹访、缠访事件不断。有理闹,无理也闹。若到县乡镇走动,不难发现举着条幅或抬着棺材堵路堵门的事,对此,媒体也多有报道*《荆门7村民信访不信法多次缠访闹访企事业单位均被拘》,人民网:http://hb.people.com.cn/n/2014/0803/c194063-21859366.html。。心灵缺乏安顿,心理失衡,乡村中违背良俗、残害亲人等“伤天害理”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刘洋:《致六死12伤怀柔杀人案被告人判死刑》,《新京报》,2015年12月26日。徐海涛:《灭门案背后的乡村伦理之痛》,《半月谈》,2013年第8期。。
心理失衡带来的是言行举止失范,使得乡村生产生活所倚重的人文生态变得日渐单薄和脆弱。结果,在困扰农民自身健康和谐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内外力量积极参与建设新农村的步伐。诸如,本该投入的建设项目和资金“畏难而撤”;怀有为民做事的“有德有能有识”之人“望而却步”,本着“宁统千军、不领一民”的看法不再参选村干部,不少村庄因之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而难以自拔。
(三)“认同失灵”抬升村庄的治理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尤其是市场经济与信息科技引发城乡生产生活方式骤变,农民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多元,价值认同愈加分散。有些村民既不守传统的“礼”又不遵现代的“法”,而是唯利是图,变得极为自私与狡黠。无理性无底线的人多了,乡村便难有浩然正气。
风气不正,使得一些村庄选不出“两委的主职干部”(即村书记和村主任),即便乡镇政府强力推动选举,当选者在分崩离析的内讧环境中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最终都会“撂挑而去”,村庄陷入行政“荒漠化”的困境,治安状况不断恶化。在光天化日下,劫掠盗窃问题时有发生。有人在去往农贸市场的路上被捋破耳垂、抢走耳环;有人作短暂的小憩,身边的手机已不翼而飞。对此,受害人无力又无奈,慨叹“世风日下”。
村庄共同体价值认同与凝聚力的缺失,为乡村边缘人*所谓边缘人,是指不被乡村主流文化价值规范所认同、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游离于乡村主流社会且有着自身独特亚文化的群体。在农村,其典型代表为混混、地痞流氓、黑恶势力、钉子户、无赖等。参见田先红,高万芹:《发现边缘人——近年来华中村治研究的转向与拓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的沉渣泛起特别是混混治村提供了便利土壤。混混受时代的文化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边缘人的思维观念异于村民常态的价值取向,缺乏操守,有的仅是破坏性。混混不带一丝一毫德性赤裸裸地恐吓盘剥村民,令不少村庄堕入如同解放前那种被“土豪劣绅”肆意欺凌之境。乡村“灰恶势力”的形成与为所欲为,表面看来是组织失灵,深层次却是文化认同缺失所致。于村民而言,缺乏挺身而出与恶势力斗争的“公心和正义感”;于灰恶势力而言,内心毫无底线,没有规矩意识与起码的为人处世之“道”。
市场经济时代,农村社区文化在经验层面、话语层面和规范层面几乎同步发生不可逆转的激变,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吴理财:《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变迁》,《人民论坛》,2011年第24期。。在这种深刻变迁中,乡村文化呈现出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对象也呈现出空置与虚化状态*赵霞,杨筱柏:《当代中国乡村文化认同的理论外延与路径依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如相关调研所关注,“乡风文明与乡土文化,是中华文明与社会文化的正宗源头所在,是我们文化的根基”,“要一定警惕一些乡村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影响,趋利主义泛滥;警惕传统价值观被逐渐颠覆,是非观念模糊、价值判断标准失范”*王海磬,于溯:《完善乡村治理,突破人才瓶颈,重塑文明乡风——民进中央“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研综述”》,《光明日报》,2018年5月12日。。
当下,不解决农民的精神贫困与权利贫困的问题,农民自己没有成为农村变革的主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彻底的持续的农村变革*钱理群:《老石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读〈刘老石纪念文集〉》,《信睿》,2012年第8期。;振兴乡村的战略,就会因行为主体缺乏精神之魂而大打折扣。
二、价值认同重构:破解乡村发展困境之文化理路
历史地看,乡村社会传统的生活与治理,乡村秩序建构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从来都是强化礼教对人的教化作用,并不存在那种特意要改造农民成为新人的现代观念及意识形态;其更多的在于树立礼教的榜样,通过有形可视可触摸的“艺”的感化,令人慢慢领悟无形秩序之“道”,进而实现乡土社会尊礼合规的低成本自治。有学者称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为“不成问题的乡村”*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民国以来,随着国家政权的下沉,乡村传统自治体系被打破,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价值观念渐渐渗入乡土社会,如乡村建设运动中倡导的“民主”“法治”“再造新民”等。外部植入的思想观念几经变化流转,在丰富涵养农民身心的同时,始终存在新旧交替中的不协调问题。传统乡村孕育的仁爱、奉献、克己、守序、谦让、自足的价值观念,因生产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改变逐渐被磨蚀,广大乡村人的文化认同没有找到动态平衡。
自20世纪90年代起,乡村社会加速变迁,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宣告农民“离土”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急剧转型,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即“乡土之神”)迅速瓦解*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传统时代与集体化时期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信仰被迅速地解构、新的颇具正能量的价值体系尚未被有效地建构起来,文化价值认同的缺失使得当下乡村发展举步维艰,上述问题便是其显症。重构乡村和谐的文化价值认同或曰伦理价值体系,着重提升农民的精神境界,实乃振兴乡村的当务之急。
(一)重塑守序与遵道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为规矩,也代表着秩序。在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礼乐制度与礼乐观念。有学者研究,除了礼,孔子对乐也非常重视,他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诗、礼、乐的学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学习诗歌,可以启发人产生做君子的志向,学习礼可以使人在家在国不失规矩,学习乐则可以教人在内心培养起和乐崇高的境界,最终成为真正的君子*阎韬:《孔子与儒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乐记》载:“礼辨异,乐统同”(《礼记·乐记》),蕴含着规约行为、涵养心灵的共同道理。
在这样的文化理路下,统治阶级用“礼制”进行王朝治理,广大乡土社会相应形成了一套礼教文化。仁者,人也。礼失求诸野,便是“礼治”的佐证。顺着这一逻辑,中国人不管是士人、农人还是工商之人,均讲究“人品”。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两种,一是空间之俗,一是时间之俗。人品受时空局限之人,故谓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第244页。。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庸·第二十九章》)君子之道,本质上是存于个体身上的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的大雅德行。所以,中国传统教育,亦可谓只要教人为君子不为小人,教人为雅人不为俗人。说来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则不易到达其最高境界④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第244页。。
正因为境界高和难以企及,做君子、拥有好人品就成为传统社会为人所追求的至尊之“道”。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轴,“礼治”与“为君子之道”的追求,二者不仅相辅相成,重要的是,以绵柔却不失刚性之力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二千余年。期间,尽管民变、匪乱、王朝更迭的“戏码”不断上演,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此种状况被学界称为“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斗转星移,在现代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传统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渐崩塌,追求做君子、拥有好人品的文化土壤受到冲击。相比于城市文化建设的资源条件及其因应状态,乡村文化状况不容乐观。正如楼宇烈教授所概括:中国乡村传统文化正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境地,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意识(也就是魂),礼仪之邦现在一举手一投足一言谈都不知道什么才是规矩*楼宇烈:《离开“道”,中国文化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中山国学堂(公众号),2018年5月14日。。
俗话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缺乏秩序规约及濡养心灵的“道”,乡村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谈到:“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德]盖奥尔格·齐美尔著:《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振兴农村,必须着眼于农民的心灵观照,重塑守序与遵道的乡村文化价值,将传统“礼”的约束与追求做君子之“道”进行创造性转换,使其与现代公民之责及其文明教养相契合。守序与遵道的文化价值观不仅决定着如何做人,还会影响到择业观、消费观、婚育观等方方面面,是解决农民精神贫困的重点所在。
(二)“敬法”与“修儒”相连接
百年变迁,无论城市与乡村,已经在现代化征途中驰骋了一个世纪。在这一征途中,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都必须锐意向前,遇水架桥、逢山开路,因为没有回头路可走。从思想文化角度看,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需要人在经济活动及社会治理方面有理性契约精神,即现代工业文明孕育而生的“法”“理”等价值观念。
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广大农村实现现代化。作为建设主体,农民自身在思想观念方面能否有现代建树则至关重要。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的书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时下,当各方力量在千方百计地助推新农村文化建设之际,并不意味着应该忽略或无视乡村传统的价值观念。如史学家钱穆所言:纵谓中国旧有,已不切时代,亦当识其来历,善为变通,斟酌改进,以求愜适。万不当于自己固有,懵焉不知。谓可一刀两断,崭地更新*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251页。。笔者以为,现今的乡村文化建设,尤其是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若将“敬法”与“修儒”相连接,不失为有效抓手。
敬法作为现代公民的修为,属于外在约束;修儒代表传统个体德性的濡养,属于内在约束。简言之,“法的意识”属于公德层面,“儒的观念”当属私德层面。两相对照,在培育现代人的过程中,理应把现代的“法”置于传统的“儒”之前。内在的约束尽管很有效力,“儒”毕竟带有比较明显的传统特征,且存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比如,重义可以是凛然的有情有义,同时也会夹杂着非理性、比较偏狭的江湖之气,这就需要颇具理性的“法”等现代观念来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意义。
举一例,广东省普宁市的果陇村与北山村,比邻而居,相隔不过六公里。因祖辈之间的世仇(即历史恩怨),百年来两村一直恪守祖训——“互不通婚”*许佳鸣,张初瞳:《化解“世仇”——两古村相距六公里,百年互不通婚》,《南方周末》,2018年5月17日。。子孙后代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交往中却一直受困于这一规训。以传统眼光打量,两村对祖宗之训的维护,体现了守义有规的“儒”的坚守。用现代思维审视,时过境迁后沿用狭隘的“成规”办事,事实上是对当代人的束缚,影响了两村的睦邻友好与合作共赢。现实诉求终于打破传统的狭隘观念,2018年5月11日,果陇村与北山村各派代表,握手言和,步入和睦共处的新时代。
案例表明,儒者的价值观念应与时俱进,要借助理性、包容的现代思维完成自身的转型,以便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形成“公序”与“良俗”竞相辉映的合力局面。乡风文明的实质当为优良传统和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先做公民、再做儒者*林安梧:《先做公民,再做儒者——一位台湾教授的“公民儒学”与社会实践》,《南方周末》,2012年4月5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三)培育弘扬新时代人文精神
在探讨乡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寻求破解农民精神贫困的方案时,不着意于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弘扬,不注重人文关怀,研究极有可能陷入浅表化之境,进而抓不到问题的实质,即:“如果不研究文化主体的人的内在的心灵,我们似乎是没有资格来谈论文化问题的”*胡军:《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解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4页。。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谈及,“人的活动大概有三个来源……。我所指的三个来源是本能、思想和精神。这三者之中精神的生活造成了宗教”*[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张师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0页。。人的观念世界可分为多个层次,精神层次位于纵深处,当属最高境界。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在于人有本能的意欲或欲望,而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更在于人是有精神的;由此,也就理解罗素为何言“精神的生活造成了宗教”。
众所周知,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其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也可以说是人文精神的助推。对人文精神作些概括,主要是指在整个人类文化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它倡导要重视人类文化的积累,尊重人自身的价值;它追求真善美,重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它强调依靠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秦钠:《人文精神:高等教育的重要内涵》,《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若沿着时空脉络作些梳理,人文精神的蕴含与呈现并非源自近代,也不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专利。就中国而言,传统的乡土文化已饱含着这样的精神。因着人文精神的存在,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先民们创造出勤劳果敢、刚正不阿、崇德向善、节俭循环、取之有道等生存智慧,形成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刘忱:《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2期。。
人文精神本不分国家和民族,不局限于时间与空间,有敬畏、有限度、不疯狂,对真善美即人性之美的保有和坚守,应是其永恒的原则及追求。需要指出的是,在寻求摆脱当下农村建设的困境时,之所以强调培育弘扬新时代的人文精神,是因为无论中国传统时代还是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化时期,人文精神常被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缠绕、遮蔽乃至偏离其本来的面目与方向。单就现代化分析,这一过程事实上是把“双刃剑”。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异化着人;在激发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同时,也将人的非理性一面释放出来。这便是当下人们反思现代性的根源所在。
解决问题需要先从认识问题入手。放眼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今无论哪一个国家,要想摆脱现代性困境,必须着眼于“人的建设”,重中之重是人文精神的回归。剥离掉过于受权势、利益等欲望驱动而不计后果的狭隘思想,让真正的“人”的精神高度体现出来。结果,每位个体(小我)的价值和尊严能够得到实质保障,人类“大我”的精神关怀也尽显其中,最终建立起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社会乃至文明世界。
置身于如此背景下的中国乡村,破解农民精神贫困问题,这种治本之策自然不该被疏忽,应竭尽全力地培育和弘扬。新时代有了人文精神的统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守序与遵道、“敬法”与“修儒”的有效连接,均不会落空。
三、无用之用: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建设问题的深入反思
文化有诸多层面,是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由外而内可分为“‘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心态层处于至深处,为内核,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谈之“精神”。对“精气神”这一核心部分,俗称“人心”。
人心是个大课题。研究者所提出的“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是人心管理”*李强,胡宝荣:《人心管理: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河北学刊》,2012年第5期。,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中对“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很难扶起来”的观照,以及一百年前梁济自杀时所纠结的“科学或许可以救世救国,断不可以救人救心”*周宁:《人间草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8页。的问题,事实上殊途同归,共同指向看不见摸不着而又至关重要的“柔性内核——人之精神、人之心”。
无论时空如何变幻,破解人的精神贫困问题,“养心”与“正心”理应是“不二法则”。转型期关于农民的“心灵”建设与“性灵”的濡养,固然有不少有利条件可资“挖掘与依托”,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多种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改善了乡村文化过于“贫瘠”的现状。不管哪种探索,囿于大环境的影响,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格局有限的问题。最大的困扰在于,现实中似乎“凡事”都带着“功用”的考量,若没有深层反思和坚定意志,很难从过于功利化与世俗化的“名利泥淖”中跋涉而出。
被传统功利思维与现代商业文化桎梏的人们,不分地域及男女老少,做人做事不那么纯粹,附着了过多的欲望。心不纯则行不端。即便到寺庙参拜,所秉持的通常为求功名与利禄的“执念”,而非真正虔诚的信仰。如学者所概括,对于许多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体现得很精彩,坏处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鉴之,若要将功利化的“小聪明”提升为修身养性的“大智慧”,实非易事,必须回到“人之为人”的这一根本命题,在精神层面“筑长城”。
梁漱溟先生言:“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清明,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梁漱溟:《吾人的自觉力》,见《我的人生哲学》一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1页。
“自觉”、“清明”与人格的表述,正是“人之为人”该追求与达致的精神高度。对中国文化哲学有所了解的人士,大都明白梁先生佛学造诣深,谈人的修为渗透了大量佛学思想。与之相比照,诞生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也非一般人能迅速领悟,但同样指向“人”之精神及其作为。道家思想体系中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等,能为人类文明提供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的哲学基础*刘涛:《汤因比的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社会观察》,2013年第3期。。“无为而治”与“无用之用”(《庄子·人间世》)等经典思想,昭示着做人做事不能局限于狭隘的格局里;不狭隘、不功利,“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些蕴含着辩证法的深邃思考,从另一角度诠释了“为人”应达致的“自觉”与“清明”,也是有人格的表征。
攀登精神高峰、富有精神气概,不仅仅是中国优良传统文化讲究的品格和“要义”,在西方文明的孕育与文化精神的追求中,事实上蕴含着相同的逻辑。我们时常所谈论的西方现代化的典型代表——英美,两国的强大与稳固无不源自其国民极力守护的“不谈条件”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规则等价值理念,绝不是“形而下”的气势汹汹的开拓市场与疯狂逐利。作为主导者——精英阶层,他们的思想与精神气质,恰是来自一套“无用”的修身养性的教育。在英国,“越‘精英’的私校,就会花越多的金钱和时间,学习越多只能修身养性、不能养家糊口的‘没用’的东西”*姜丰:《在英国贵族学校,都学些什么》,《南方周末》,2018年5月17日。。
细细品味上述报道并加以延伸,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精神境界的提升,虽然在钱财、教育等方面与英国贵族阶层的生活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但富有人文情怀、伦理价值的精神需求及其培育路数本该无异。进言之,在市场经济时代,当人们迷失于“贸利的闹市”而难以自拔的时候,看似“无用之用”,实则是摆脱困境的“旨归”。
综上,乡村文化建设,如果能使农民怀有一颗“不功利”“不浮躁”之心,在精神上真正富裕起来,才称得上为“建设”。任何带着功利思维的“举动”,实质是打着“文化建设”的旗帜进行反文化的“行为”。欲速则不达。文化不能“打造”,文化建设之路应是一个慢慢浸润的过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梁漱溟先生曾提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借此理作进一步的反思,精神贫困的问题不单是当下乡村治理中需要破解的难题,也是转型期中国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棘手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