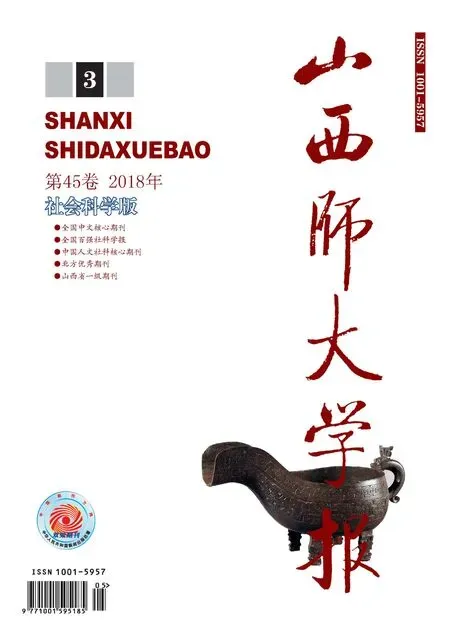农村女性的城市伤痛和返乡之困
----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为例
薛 月 兵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孙惠芬的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并非讲述乡村女性进入城市并遭遇沦落的老套故事,也与同时期作品中关于女性进城苦难的外在描绘抑或在消费主义文化中欲望奔突的简单刻写不同,而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两个农村女性欲望城市而又无法进入城市、返回乡村而又无法承受乡村之实在和命运之悲剧的尴尬。在此心路历程中,作家精微深刻地展演了她们在城乡之间从想象城市的激情到遭遇城市的伤痛,从农村年节仪式中的暂时满足到面对农村实在的茫然和恐惧,从彼此情谊和爱恋的建立再到最终的无地彷徨。由此,小说彰显了城市话语体系在与农村话语体系的博弈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如何渗入农村女性的欲望层面,成为她们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支撑物,以及该支撑物丧失之后她们又不得不面临的精神性眩晕、主体性虚空的僵局。
一、城市幻象:农村女性的欲望框架
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真正的主角是那个并未加以正面表现而又无所不在的城市。齐泽克指出:“如拉康所言,幻象充当的是‘绝对意涵’,它构成了框架,我们透过这个框架体验世界,并把世界体验为具有一致性和意义的事物。幻象是先验空间,特定的意涵效应在那里生成。”[1]150如其所述,主导性的城市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幻象框架,构建着农村的“现实”。这首先表现在农村青壮劳力向城市的流动。如成子、玉柱以及他们的父亲在城乡之间候鸟般的迁徙。他们的离去不仅使山庄变成了一个由婆婆和媳妇组成的女性世界,而且也抽空了她们情感的依凭和精神的寄托。其次表现在歇马山庄房屋中的空间布局和器物的摆设中。如宽大的灶台、宽大的餐桌,炕与柜之间的“客厅”;如李平家中餐桌上的米色台布,柜子上灰蓬蓬的干草,炕上雪白色的床单。此种空间布局悬置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形式感,寄托着农村人对城市无尽的向往与慕效。同时日常生活中的器物摆设只有被组织进城市的意义体系之中,才能获得她们的认同。此外,城市话语体系对农村现实的建构还表现在服饰、化妆等外在形象方面。如李平的“淡妆”和那件“锈红色毛线外套”,潘桃的烫发和走路的姿势,等等。在小说中“镜子”的意象多次出现。“镜子”隐喻着城市大他者的凝视以及农村女性在城市大他者的欲望空间中理想自我的构建。由此,农村日益成为城市话语体系的建构物抑或复制品,而原本的农村渐趋消逝在历史的时空之中。
城市话语体系不仅建构着农村的“现实”,而且也成为农村女性欲望的框架。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幻象为我们的欲望提供了坐标,即建构了能使我们欲求某物的框架。”[1]144透过城市幻象的框架,她们建构起自身的意义世界和精神支撑。无论是李平还是潘桃,她们尽管置身于农村之中,但却生活在城市。她们都曾怀揣着城市的梦想与激情。如小说所叙述的:“潘桃说,刚下学那会儿,一听到电视播音员在电视里讲话,就浑身打战,就以为那正在讲话的人是自个儿。李平说,我和你不一样,光听,对我不起作用,我得看,一看见有汽车在乡道上跑,最后消失到远处,就激动得心跳加速,就以为那离开地平线的车上正载着自个儿。”[2]在对城市的梦想与激情中,潘桃并未真正走入城市。她“心比天大胆子却比耗子还小”,对城市充满着惊惧和恐慌。但正是因为从未走入,所以潘桃始终保持着浪漫的生活姿态,沉浸于对城市的幻象之中。那是一个由大学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电视主持人的优美身姿和甜美声音构成的假想场景。在此场景中,潘桃因为能够将农村之实在纳入到城市的意义网络之中,使其可以躲避这一实在的尖锐和沉重:“在她心里,浪漫是一份最安全的东西,它装在人的思想里,是一份轻盈的感觉,有了它,会让你看到乌云想到彩虹,看到鸡鸭想到飞翔,看到庄稼的叶子想到风,它能把重的东西变轻,它是要多轻就有多轻的物体,它怎会伤人?”[2]也可将潘桃的浪漫视为神经质疾病的症状。在《心理功能两项原则的表述》一文中,弗洛伊德认为神经质疾病症状源自于心理活动中趋乐避苦的根本原则。心理主体一旦在真实世界遭遇痛苦,就会把关注力投射到幻想的世界,而与此同时主体也并不否认现实世界的实在性。潘桃尽管认识到:“而结了婚,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结了婚,附了体的鬼魂一程一程散去,潘桃的灵魂从遥远的别处回到歇马山庄,屋子里的被窝、院子里的鸡鸭、野地里长长的地垄,与她全都缔结了一种关系。”[2]然而,她始终“拒绝与光景中的情景沟通和共鸣”,始终彰显着那个“心中的自己”。尽管置身于农村之中,但潘桃却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另外的“现实”之中。简单的婚礼就是其对宿命抗拒的典型表现。
潘桃生活在城市的幻象之中却并不自知。潘桃的“知”始自小说伊始对婚礼场景中李平的观看。最初潘桃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观看李平的。之所以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看,乃是因为潘桃的想象性凝视。也就是说,潘桃是在农村大他者亦即农村话语体系的想象性凝视中确立起自我认同的:她是歇马山庄中最漂亮的女性。这一认同使潘桃在观看李平之前有着足够的自信和优越感。与潘桃相区别,李平是在城市话语体系的想象性凝视中确立自我认同的,不同于乡村女性之“漂亮”的“城市”和“洋气”是其典型的表现。“漂亮”与“城市”和“洋气”的区别本质上是农村话语体系和城市话语体系对不同主体塑造以及构建方式的区别。因而,在李平走近潘桃的时刻,她的观看发生了逆转,其主体性观看在此时逆转为“被看”的位置。李平在婚礼场景中过度的“城市”和“洋气”正是潘桃所匮乏和欠缺的。匮乏和欠缺使潘桃此前居高临下的姿态瞬间破碎、坍塌,由一个被他者(农村)所欲望的主体转变为欲望他者(城市)的主体:“潘桃成为真正的女人,其实是从成子媳妇从门口走过的那一刻开始的。那一刻,她懂得了什么叫嫉妒,还懂得了什么叫复杂的情绪。”[2]
与潘桃不同,李平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城市的想象性认同之中,她试图通过自己的美丽以及“真情和善良”的乡村伦理获得城市的接纳。“她怀着满脑子的梦想离家来到城里,她穿着紧身小衫,穿着牛仔裤,把自己打扮得很酷,以为这么一打扮自己就是城里的一分子了。”[2]然而在来到城市后,她所珍视的美丽、真情和善良反而成为城市欲望的对象。在资本逻辑对其身体和乡村伦理无餍足的捕捉与消费之后,最终将其推入无底的深渊。李平终于弄清了一样东西:城里男人不喜欢真情,城里男人没有真情。城市的伤痛使李平最终失去了欲望城市的能力,丧失了城市幻象的框架,遭遇了自身的第一次死亡。此后的李平必须面对和承受农村的实在,接受农村话语体系的规训。因而,不论是李平还是潘桃,她们表征着普通的农村女性在面对城市时的两种姿态:惊惧恐惧和无所顾忌。她们向往城市,却又被城市排斥,从而不得不处在对城市妄想式的痴迷抑或被城市排斥的无望之中。她们成了蔓延在歇马山庄贫瘠土地上的瓜蔓,欲望的茎叶在向四周伸展、攀爬的同时,根却深深地扎在农村的土地上,使其伸展和攀爬的努力幻化为一个空洞的姿势。
二、返乡之困:实在的呈现和意义的匮乏
在遭遇城市的伤痛之后,李平决定返回农村。小说伊始潘桃和李平的婚礼场景是非常典型且颇具意味的。对于潘桃而言,她对婚礼场景中的“高潮”时刻充满恐惧并尽量逃避。因为婚礼仪式意味着主体在农村话语体系中位置的锚定以及“浪漫”的丧失。潘桃选择了旅行结婚的方式,意欲逃避农村女性的宿命,避免在“一时的火爆过去之后,用她的一生,来走她心情的下坡路”[2]。如果说潘桃是一种强迫症的症兆,她意欲在不断的延宕中避免与“高潮”时刻的相遇,那么李平落幕前的高潮则是一种癔症的症兆。李平在婚礼场景中向城市的告别仅仅是外在的、仪式化的。在意识层面,她要忘却城市,表现出对农村话语体系的屈从;而在潜意识层面,恰恰是被压抑的城市欲望的过度实现,是落幕前的高潮,是在有意制造的“隆重和热闹”中实现真正的“飘一次,仙一次”的渴望。然而,这场婚礼仪式使李平获得了农村话语体系的符号性委任,凝定了李平在农村话语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因而婚礼仪式对于李平而言是承前启后的,是“城市李平”的结束和“成子媳妇”的开始。它包含着城市幻象破碎之后李平对农村女性命运的接受以及在农村话语体系中的自我救赎。正是因为具有救赎的性质,所以李平不仅对农村真实日子的到来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在农村话语体系的规训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屈从,“叫她吃葱就吃葱,叫她坐斧就坐斧,叫她点烟就点烟”。
孙惠芬的小说总是在类似“农村的红火日子”抑或“年节仪式”中书写由农村话语体系建构起来的“现实”。在此“现实”之中,是久别重逢之后亲人的团聚、长期劳作之后的身心休整、沉浸于民间习俗之中的仪式感与文化认同。婚礼仪式结束后,“农村的红火日子”抑或“年节仪式”为李平提供着意义的支撑以及欲望得以暂时满足的形式。然而,在农村的红火日子抑或“年节仪式”结束的时刻,她们与隐匿在幻象帷幕之后的农村实在相遇。所谓农村实在是指农村中的事物由于无法被组织进城市的幻象空间,成为一种客体性残余,呈现为无意义和惰性的特征。如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雾气里的机密其实是一种潮湿的机密,是快乐和伤感交融的多滋多味的机密,那个机密一旦随雾气散去,日子会像一只正在野地奔跑的马驹突然闯进一个悬崖,万丈无底的深渊尽收眼底。”[2]“悬崖”“深渊”无疑是符号意义网络消逝后农村实在的隐喻。此种实在对李平而言,是“样样器具都裸露着,现出清冷和寂寞”,是“锅、碗、瓢、盆、立柜、炕沿神态各异的样子”,是“眼前的一片空落”,是“光秃裸露的地、沟和树”,是“没有蒸汽的清澈见底”,是“清冷和寂寞”。对潘桃而言,则是“她一下子就傻了,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她好长时间神情恍惚,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干什么,搞不清楚自己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剩下的日子还该干什么”[2]。
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农村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的祛魅。“幻象着重于对主体的诱惑和控制,着重于为大他者服务的诱导性功能”[3],由于农村女性的欲望是由城市建构的,农村话语体系已无法为主体提供框架及其欲望的内容与形式。因而,曾经在农村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的父亲角色在小说中表现出女性化和喜剧化的特征。成子的父亲早年丧父,他的母亲又死于脑溢血。他独自一人生活在孤苦之中,自怨自艾、无暇他顾,完全丧失了父亲的权威。而玉柱的父亲忙于打工,早已将父权转交给了玉柱的母亲。小说中真正代表农村话语体系对主体进行询唤与规训的是李平的姑婆婆和潘桃的婆婆。两位婆婆尽管都是农村话语体系的执行者、父权的代理者,但又有所不同。李平的姑婆在对成子媳妇的询唤中表现出矫情的仪式感和造作的权威性,她要求侄子媳妇对自己无条件的服从,哪怕仅仅是外在的服从。潘桃的婆婆则由于一直生活在失去儿子的焦虑中,因而在潘桃面前表现出“小辈人”式的谦卑。无尽的唠叨与诉说是其规训媳妇仅有的方式,然而此种唠叨与诉说对于潘桃而言仅仅是一堆声音的残迹而已。父权位置的女性化、喜剧化体现了农村话语体系在现代化、城市化价值体系中的去势与尴尬。
实在呈现及其意义的匮乏,引发了李平和潘桃与农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婆婆面前,潘桃在微笑中有着“彻头彻尾的严肃”,在羞怯中有着“理直气壮的命令”。不同于潘桃一贯的抗争姿态,李平对农村话语体系的屈从尽管有着因城市伤痛带来的主体重建和精神救赎的意味,然而,冒犯的征兆却渐趋显露。它出现在李平与姑婆之间“就不兴为女人洗?”的玩笑中,出现在李平对潘桃婆婆礼节性的敷衍中,出现在面对山庄女人们不中听的议论时不向其就范的快感里。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最终选择了精神性的背叛与逃离:城市李平再次取代了“成子媳妇”,城市的潘桃再次从“玉柱媳妇”的身体中跃出。唯有如此,她们才能在城市的幻象空间中躲避“实在界荒漠”的侵袭。当然,我们不能在存在主义的层面去品评歇马山庄中的这两个女人。事实也证明她们没有直面存在困境的勇气和担当。她们仅仅是两个普通的、欲望着的农村女性,有着“常人”的弱点。事实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采取一种“横站”的姿态,试图在无路之路中探求一条道路来,恰恰是鲁迅努力的方向。精神性的背叛与逃离使李平一改此前“一件衣服只要穿就穿旧穿脏的原则”,“她非常想在某一时辰,换上一身好衣服,大摇大摆地走在她们(屯子女人)面前,像她结婚那天那样,让她们看看她还是原来那个样子”。[2]同样,如果说屯子女人的欲望已被城市所构建,那么李平的此种行动意欲在屯子女人的欲望剧场中,展演其“城市”与“洋气”的剧情,再次完成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三、无地彷徨:农村女性的欲望僵局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原初的题目为《两个人》。之所以命名为《两个人》,按照孙惠芬本人的说法,这一题目包含着自身的生活哲理。即女人的世界其实很小,她们的一生其实只是和一个人的斗争。如其所述:“他们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是不同的人,但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人,或男人、或女人。他,她,通着女人的精神,占据着女人的世界,所谓‘两个人’的世界。”[4]56“两个人”可以说是孙惠芬对女性与世界相处方式的概括,也是分析和解剖女性精神心理和欲望层面的密码。在丧失了农村的“红火日子”和“年节仪式”这一屏障之后,面对农村的实在、欲望的僵局和女性的宿命,李平和潘桃开始构筑她们之间的情谊—爱恋。之所以说她们的情谊具有爱恋的性质,是因为在城市的幻象框架中,彼此作为对方的欲望对象而存在。李平在潘桃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那个无所顾忌地欲望着城市的自己。同样,潘桃在李平身上看到了城市化的理想自我。在彼此的情谊—爱恋中,她们再次拉开城市幻象的帷幕,标出了她们自身世界的边界,筑起了抵御实在的精神城堡。可以说,李平和潘桃之间的情谊—爱恋具有着摆脱农村实在、欲望僵局、女性宿命并重建意义世界的维度。
正是因为她们之间的情谊—爱恋包含对存在丧失的焦虑以及生命意义的维度,所以无论是李平还是潘桃,都必须承担破坏这份情谊—爱恋所引发的僵局和罪责,否则使她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坐标系将再次分崩离析。这在她们的第二次会面中有着明显的体现,此次会面的失败使她们再次陷入了一直以来想要躲避的世界。此后,她们清楚地意识到彼此间的情谊—爱恋是需要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持的,“因为第一次的任性导致了不该有的煎熬,友谊伊始,两个人都小心翼翼,仿佛那友谊是只鸡蛋,不能碰,一碰就会碎掉”[2]。甚至她们之间的情谊—爱恋一度呈现为债务与奖赏的关系:“但有时,却是需要交换的,是需要你一段我一段的,比如潘桃讲了自己的恋爱,李平就必须讲她的恋爱。这种时候,不用潘桃逼,一个静场,李平就知道该自投罗网了。”[2]在此种债务与奖赏的反复中,李平和潘桃的情谊—爱恋在一步步推进、加深,甚至在反对婆婆们的围剿中达到了至高点。
尽管农村话语体系处于去势与尴尬的位置,然而规训的力量却无处不在。此种规训在小说中表现为道德楷模的树立。潘桃的母亲无疑是村庄女人们的理想典范。她曾是歇马山庄的大嫂队长,不仅美,受到村庄男女的高度评价,更为重要的还有德,是乡村道德伦理的楷模。此种规训还表现为山庄女人的议论和婆婆们的教谕。在她们的议论与教谕中凸显的是农村女性的本分和节俭。此外,作品还通过李平母亲的告诫显示了此种规训的残酷性:“必须放下为姑娘时的架子,尤其在村里的女人面前,她们的嘴要是没遮拦就能一口一口吃了你。”[2]在此情境中,对李平而言,城市伤痛是其纳入农村话语体系必须加以隐藏的创伤性内核,因为这个创伤性内核有着将其在农村话语体系中所拥有的一切彻底摧毁的力量。李平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她必须隐瞒自身的创伤性内核,唯有如此才不至于丧失自己得以存身的现实。然而,在情谊—爱恋的移情中,在债务与奖赏的反复中,她必须偿还自己的债务,向潘桃交付自己的过去。在必须隐瞒和全盘交付的两难中,李平最终选择了后者。
年节再近,李平再次融入农村生活中并不常有的“红火”之中。而玉柱返乡的延迟和李平的“背叛”则使潘桃陷入面对农村实在时的冰冷与恐惧之中。此前在彼此爱的移情中“城市”和“洋气”、真情与善良的李平,在恨的移情中被改写为放荡、张狂的李平。移情的逆转使此前爱的喜剧迅速转向恨的悲剧:“李平被成子拥在怀中,被一些城里男人拥在怀中,并不是在歇马山庄与自己厮守了大半年的那个李平,而正如婆婆说的,是风流的,是从眼睛到眉梢,从脖子到腰身,通通张狂得的不行的李平。”[2]这样的李平在潘桃恨的移情中显影,使其站在农村话语体系至高无上的道德位置上对李平发出了最终的审判。在潘桃移情逆转的那一刻,李平已处于被审判的位置而面临自己的第二次死亡。小说中的李平死了两次,第一次是城市话语体系中的李平的死亡,第二次是农村话语体系中的“成子媳妇”的死亡。李平面临的僵局是:自己本想通过真情和善良获得城市话语体系的接纳与认同,然而真情和善良恰恰是无法被城市话语体系接纳的剩余;自己本想通过顺应和屈从获得农村话语体系的接纳与救赎,然而城市伤痛又使其顺应和屈从的努力被彻底击碎。在经历了“成子媳妇”的死亡之后,李平遭遇了拉康所谓的“焦虑”时刻:“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拉康的‘焦虑’概念所包含的特质。焦虑之所以为焦虑,并不是因为缺乏欲望的客体—成因。导致焦虑的,并非客体的匮乏。导致焦虑的,却是这样的危险:我们过于接近那个客体,并会失去匮乏本身。焦虑是由欲望的消失带来的。”[1]11—12在此“焦虑”时刻,李平能否再次激荡起欲望的勇气,那一抹孤傲的姿态能否继续下去,抑或因终生处于那个屈辱的被审判的位置彷徨于无地?同样,潘桃在怀孕之后,“每天握着婆婆的手,大口大口呕吐”,这既是新的生命孕育之时的妊娠反应,又是城市理想终结之后面对农村实在的心理反应,也是因对情谊—爱恋的背叛而产生的精神反应。类似于萨特在《恶心》中所表达的主题,此时的潘桃清醒地感知到自身与其所处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清醒地感知到自身存在的现实以及生命的无意义,并在此无意义的存在中产生“恶心”的感觉。
四、穿越幻象:两种话语体系的审思
孙惠芬在延续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作家于荒凉、虚无的现实的境遇中书写女性生命体验和悲剧命运的基础上,写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女性在城乡二元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向往与排斥、对抗与规训的心理悲剧。作家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切近人物的精神心理和欲望层面,在叙述农村女性在城乡之间现实遭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精神心理和欲望层面窥探和发掘她们内心隐秘的风景。在城与乡之间,她们向往城市却又被城市排斥,返回农村却又不愿面对农村之实在。在向往与排斥、返回与不愿面对之间显现出她们欲望的僵局、精神的困境。如宋晓萍所指出的:“她所渴望的,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是她曾坚决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纠缠着她;她勇往直前,却只为落叶归根。她离开时,没想到要回来。她回来时,却是永远离开。”[5]从想象城市的激情到遭遇城市的伤痛,从农村年节仪式中的暂时满足到面对农村实在的茫然和恐惧,从彼此情谊和爱恋的建立再到最终的无地彷徨,孙惠芬在对农村女性精神心理和欲望层面抽丝剥茧般的精神分析中,揭示出歇马山庄中两个女人的存在困境、欲望僵局和悲剧命运,揭示了她们在进城/返乡的历程中意义世界的不断重建而又不断失败的焦灼、恐惧和无奈,揭示了她们的幻象空间在坍塌破碎后所引发的愤懑、耻辱和恶心。
究其实质,小说中人物所有的努力与失败、困境与僵局都源自于那个无所不在的城市。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历史现实当然总在被符号化;我们对历史现实的体验总是以不同的符号化模式来调停的。”[1]120城市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是由一套作为叙事的符号网络支撑着的。而话语体系的运作与实施则完全依赖于对该话语体系的相信。相信在一开始就加入到了意识形态的运作与实施中,并成为其必不可少的构成性要素。我们相信农村必将为城市所取代,相信当前农村/城市的二元格局必将湮灭在城市最终的胜利与辉煌之中,相信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性工程将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的最终目标。此种相信一旦将自身设定为人类状况的真理,其可怕之处在于,它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文化,包括人与世界、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以及人的精神、灵魂、信仰、善良等,视为现代性的障碍一并祛除。当所有的人接受此种偏见的时候,其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和漠视就具有了合理性,农村人将不得不处在现实虚空和传统祛魅的焦虑之中。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我一直都在论证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它篡改了我们祖先的形象,扭曲了从我们的祖先到我们发生的变化。尤其严重的是,它将变化解读为特定信念的衰落,这样一来就遮蔽了不同时代在背景性理解与社会想象上的巨大差异。”[6]究其实质,此种相信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非文化认知,是一种未经反思的妄断。
其实,无论是城市话语体系还是农村话语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匮乏和不一致性。也就是说,作为不同的话语体系,它们在建构历史现实的过程中,总会有无法被结构进话语网络中的剩余、残迹。农村话语体系在为人们提供民俗仪式、宗法血缘、价值信仰的同时,却导致了个体生命活力的匮乏;城市话语体系在为人们带来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理想、价值信仰的缺失。这也正是为什么处在前现代社会阶段,我们梦想与渴望城市,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又想象和返归农村的原因。因而,城市同样并非人类最终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建立在资本运作之上的话语体系,在城市之中事物自身只有纳入到商品—资本的意义体系中,成为商品—资本意义体系中结构性的要素,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此种通过抹除事物自身的本质属性,凸显其作为商品的交换特征,本质上也仅仅是一种“物”的意识形态而已。同时,就市场个体而言,城市话语体系隐含着一个撕裂自身的内在矛盾:主体性的匮乏。围绕着商品—资本的逻辑运作,市场竞争、自由主义、工具理性、世俗化等都以激发人对金钱和财富的攫取和累积为主要动机。当对金钱的追求成为唯一的价值和意义时,个体往往陷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淖。
当社会从“生产之镜”步入到“消费之镜”的时刻,海量差异化、多色彩的符号增生与繁殖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拟像”的和“超真实”的时空之中。城市话语体系的幻象特征在“拟像”及“超真实”的社会中被充分彰显。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价值早已超过了其使用价值。人们在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中,凸显的是符号背后身份、地位、权力等象征性差异。符号的能指愈亦脱离其所指涉的客体和对象,使得整个社会日益成为由符号主导、控制的拟像社会。拟像社会不仅遮蔽了社会现实的真相,而且在拟像的背后空无一物。它之所以得以存在,恰恰在于对人们欲望的不断刺激。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或者现实“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下存在”。这种丰盛的匮乏最终导致了人们“心理的贫困化”。人们的欲望需求在海量的商品刺激下无限地增长,满足感和幸福感却在不断递减,无法规避的差异和分化逻辑使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愈发强烈,紧张、不安、焦虑充斥着当代人的心灵,持续不断的竞争压力使当代人患上了各种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由此,从农村到城市抑或从城市到农村并非进化论式的因果、线性的发展,而是不同话语体系在建构历史与现实过程中被压抑之物的返回。本雅明指出:“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救赎。”[7]13在此,本雅明意指曾经在先前的话语体系和历史肌理中空洞的、无意义的踪迹都会在当下的历史肌理中回溯性地得到补偿。这提示我们不论是农村话语体系还是城市话语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郁滞时刻”,在此时刻要么是城市话语体系的活力再次彰显,要么是农村话语体系在重返中渴望获得自身的意涵。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生命活力在现代想象中的激发与显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以及新世纪在返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集体乡愁,等等。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化解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对立隔阂,在去除现代性非文化认知偏见的同时,转向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认知。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存在永远不能不与我已经提到的重要参照系产生关系:世界、他人、时间、善。这种关系在我们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时能够并且事实上也已经被改造,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全然消失。我们不能没有某种关于我们道德处境的意识——某种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意识。”[6]在这一转向中,首要的问题是基于人与世界、自我与他人,以及人的精神、灵魂、信仰、善良等农村话语体系在与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有效对话中展开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5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2]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J].人民文学,2002,(1).
[3] 范燕宁,赵伟.从“人之征兆”到“社会征兆”——齐泽克“征兆”理论的社会学意义及其警示[J].社会科学研究,2011,(1).
[4] 孙惠芬.城乡之间[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
[5] 宋晓萍.萧红的地:封锁与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J].天津社会科学,1999,(4).
[6] (加)查尔斯·泰勒.两种现代性理论[J].陈造通译.哲学分析,2016,(4).
[7] (法)让5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