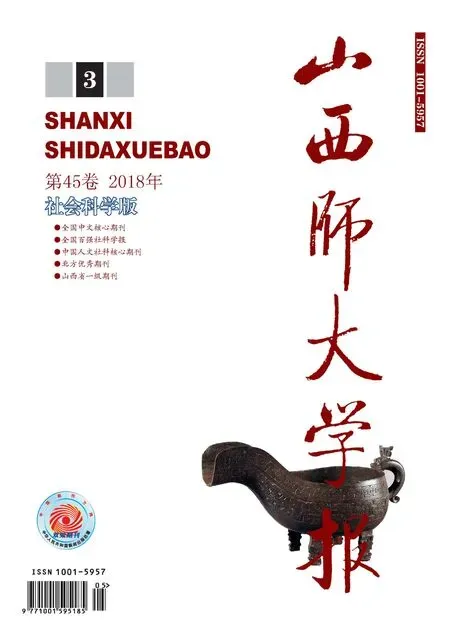传统、革命与性别:20世纪40年代华北乡村女性婚姻探析
王 微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515)
关于革命根据地婚姻的研究,学界主要从“婚姻与立法实践”“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性婚姻家庭地位”“婚姻制度与家庭变革”以及“女性婚姻观念与婚俗”等四个维度展开。*岳谦厚、王亚莉在梳理1980年以来国内外有关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研究成果时的分类。随着性别理论在多学科广泛运用以及新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兴起,女性逐渐成为婚姻问题研究的聚焦点。 然而,从女性角度切入探讨婚姻政策颁布后乡村女性的切身体悟与应对的文章数量较少,本文以档案资料为依托,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以女性视角为探讨问题的基点。第一,考察20世纪40年代婚姻政策颁布后,在革命、战争、传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华北乡村女性的婚姻观念、对婚姻政策的掌握和利用以及婚姻生活状态、两性地位等。以期从宏大叙事中剥离她们的生命体验,还原历史场景中真实的妇女形象。第二,通过对乡村女性婚姻生活、思维惯性的关注,窥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探讨传统、革命与性别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第三,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华北中共控制区女性婚姻实态的爬梳,体悟妇女解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一、婚姻观念:多元下的迷茫
为践行妇女解放精神和满足让女性走出家庭支援战争的需要,中共华北控制区各根据地自1940年初相继颁布了新婚姻条例。*如《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4月1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2月4日),《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3月16日),《修正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9年7月19日)等。新婚姻条例的出台,无疑是一场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从法律上直接赋予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权利,给女性婚姻家庭生活和男女性别关系带来了变迁与重塑的机会。然而在战乱、灾荒以及乡土社会经济基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形下,乡村女性婚姻观念与变革程度却未像想象的那般理想。
(一)对婚姻政策的多元认知
华北乡村女性对中共婚姻改造的认知与反馈是多样的。一般而言,青年妇女普遍要求婚姻自主,较开放的中老年妇女能接受新婚姻政策,曾遭受过包办婚姻的妇女也赞成自由婚。但新婚姻政策亦招来些许非议:“自由结婚可是好,但是谁长得难看了永也说不上一个老婆了,谁自由给他一个呢?”[1]赞成买卖婚的女性大有人在,甚至部分妇女存在着卖钱越多越体面的思想,以财礼多少来估量自己的身份价值。面对再嫁,寡妇也有着不同的考量。她们最大的顾虑是孩子和财产,对未来生活的担心更是很多丧偶妇女拒绝再嫁的重要原因。对处于生存底线边缘且受传统惯习长期浸染的乡村女性而言,在革命中尚未形成追求自由之思想。
尽管婚姻条例已普遍推广,制度规范以外的畸形两性关系仍大量存在。如“带夫改嫁”“两头跑”等。还有的女性以“家庭生活困难,可以暂糊口”为借口,在丈夫外出当兵失联后,未办理离婚手续便与他人同居。[2]61对传统乡村大多数女性而言,谋生手段较少,已婚女子改善生活境遇的方式除了改嫁和重婚再无其他。可见,乡村女性对新婚姻政策的理解与认知未超出“过日子”的考量。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在她们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完全受新式思潮的左右,支配她们思想的恐怕更多的还是旧式观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新旧杂糅的矛盾的婚姻观念结构。”[3]300因此,婚姻自由带来的“解放”,她们尚未体认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女性乃至中国女性都处于性别解放意识缺失状态。
(二)对婚姻自由的“误解”
各根据地婚姻条例的颁布、民众运动的进行以及社会教育的开展,使不少女性逐步意识到传统旧婚俗的不合理性,认同婚姻自主与男女平等理念。但限于知识与眼界的制约,她们并不能准确理解新婚姻政策。 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妇女解放了,地位提高了,就要离婚,甚至在外乱搞。左权县桐峪镇的常成娥出嫁不久,就和外人“相好”。面对他人规劝,常氏以“女人家要自由”[4]相驳。有些媳妇们稍感不如意就要求离婚,甚至将离婚作为威胁家人的手段。有的离婚仅是“人云亦云”。 更有些女性并未理解婚姻法的具体条款,没有考虑到婚姻缔结对家庭与社会的重要意义,以自我利益诉求为主导。如北岳区康庄一妇女离婚用完赡养费后要求复婚。[1]沁源县第一川村纪某为了读书与他人结婚,待达目的后便提出离婚。[5]鉴于妇女对自由婚的误解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抗战日报》曾载文予以批评:
妇女的解放,不是从贫穷的家庭中脱离出来,嫁一个有钱的就算解放了,妇女的真正解放,应该是在经济上起的作用日有增加……好穿好吃,好舒服的虚荣心,与依赖男子寄生的心理与习惯,是应加以教育与纠正的。[6]
“解放”对处在生存边缘的女性而言并非生活必需品,为了活下去,新婚姻法成了她们改善物质环境的可凭之据,因此她们对婚姻法的“误解”也就不难理解了。上述案例,与其说是女性因传统束缚而产生的迷茫,不如说是她们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她们对利益衡量的标准中尚未出现中共在乡村社会倡导的新道德与新观念。
二、婚姻困境:强迫与不公
婚姻政策颁布后,华北乡村女性的婚姻掀起了些许涟漪,性别秩序也获得了重建的契机。然而婚姻不自由现象仍普遍存在,且出现了新形式。
(一)传统语境下的婚姻困境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嫁汉、穿衣吃饭,是中国传统婚姻观念。虽至近代,西式婚姻理念逐渐在大城市悄然兴起,但在较偏僻的华北乡村,传统依旧根深蒂固,父权文化并未日渐“式微”。因此,当妇女反对买卖婚时,常遭到父母责骂。对中共提倡的离婚自由,父母出于经济、社会舆论等原因多持反对态度。相较于婆家给女性施加的压力,娘家应承担起“补偿性亲属关系”的角色,但娘家人碍于传统、经济、姻亲关系等因素多将嫁出的女儿弃置不顾,甚至直接出面阻挠。正如阎云翔所言,公众领域发生的变化往往不会立即反映到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具有排外与封闭的性质。[7]60所以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婚姻自主在华北乡村仍难以见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再婚是男女都面临的问题。不过,女性再婚的情况较为复杂。正如杨懋春所言:“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没有比在再婚上的歧视表现得更明显了。”[8]115—116民众多认为“穷得不能过的、名誉不好的,倒不如再正式嫁了好”。[9]但对正派的寡妇再嫁、特别是带产再嫁,他们则极为反对。长治二区信义村的李巧长带房带地改嫁,此种情形在这个小山村还是第一例,群众反应激烈:“这媳妇才坏良心啦,……带人的东西找找汉子,什么有出息,还得倒贴哩。”[10]当革命来临时,华北乡村女性仍生活在被婚姻礼仪习俗裹挟的封建社会中,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文化心里结构一直是制约女性解放的桎梏,且暴力革命摧残的是旧政权秩序,并没有摧毁家庭内部乃至社会的父权制思想体系。
(二)革命哲学中的工具婚姻
中共颁布婚姻政策、赋予女性婚姻自主权利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动员广大妇女、充分挖掘妇女的人力资源,以弥补战争与革命所致的人力短缺。然而她们在稍许挣脱传统婚姻枷锁的同时,又不得不服从革命整体利益。美国历史学家L.S.斯诺夫里阿诺斯曾指出:“争取妇女权利这项事业在妇女自身中间没有得到优先考虑。在革命期间,她们主要适应本阶级的需要而没有适应她们作为女性的需要。”[11]199比如,女性的身体在战争中变成了攫取更多兵源的工具,但她们的利益诉求和切身感受却被搁置了。榆次县某村村干为了完成扩军任务让3个新战士选妻,被选的女子都不情愿。村干部就威胁说:“你们不拥护新战士,就别结婚了。”[12]岳北李方村村干的做法更加荒唐,他们让即将参军的农民随便挑结婚对象。若挑选出的是已婚妇女,便动员该女子与丈夫离婚,若其夫不从,就命令该男人去服兵役。另一个村动员新战士时,把轿子抬到哪家门口,哪家的妇女就被抬走。若哪个被“相中”的女子不从,遂派民兵去抢。[13]太岳区四地委统计称:“动员给新战士的女人是村村都有,有的还进行闺女村与村之间的互换。”[14]平顺五区不完全统计,有70个妇女被迫嫁给新战士。[15]在新丈夫离家上前线后,很多妇女因对解决婚姻问题感到无望暗自啜泣,那些一夜怀孕的则更是不幸。
抗战伊始,为保证军人无后顾之忧,各地政权对军婚实行特殊保护。一些地方干部在军婚条例的指导下,对军婚的处理较保守。山西某地,丈夫五到十年无音讯的军属根据婚姻条例纷纷提出离婚或退婚,虽然条例明确规定三年以上无信者可请求离婚,但政府多采取拖延的政策,主要担心批准离婚后,革命军人回来向政府要媳妇。当时地方政府的做法并非杞人忧天,因之前有些荣军回来要他已另嫁的老婆,态度极其恶劣,有的甚至辱骂政府,“在后方吃饭专给人离婚,革命十几年没了老婆”。政府若不管,有的荣军就“脱下军衣拿不革命来威胁”。鉴于此,地方政府一般不敢“轻举妄动”。[16]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伴随民族救亡运动与阶级革命而兴起,由此也决定了妇女解放依赖于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从苏区时期开始直至国共内战结束,中共控制区女性婚姻让位于阶级、战争、革命的情形是形势所需,彼时她们婚姻利益的被搁置现象亦可看成是一种为了革命的奉献与牺牲。
三、弱者的“武器”:维权的合法与违规
“五四”以来,学术界长期将女性勾勒成被动、受压迫、生活在暗无天日中、无反抗能力的形象。然而,本文认为不能将女性看成铁板一块,更不能忽视她们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传统女性在某些层面会利用各种方式反抗传统父系社会秩序和革命所带来的不平等、规避利益受损,但她们采用的方式与达到的目的却难与“妇女解放”直接勾连。
(一)依法维权
随着革命与战争的进行,乡村妇女逐渐有了利用组织与政策维权的意识。从当时各地的档案中我们均能觅得一鳞半爪。如临县张家寨王子华去娶刘家庄刘姓女子时,该女子跑到区政府告发家里包办婚姻,后经政府判决解除婚约。[17]阜平县一50余岁的豪绅买得不到20岁的女子为妾,临娶前该女子向妇救会求助,妇救会依据边区禁止买卖人口纳妾之法令力争。[18]
婚前利用政策求得结婚自由的女性已为数不少,婚后依托法令获得离婚自由的更是不胜枚举。一些女性充分利用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使用“感情不合”“虐打”等词汇与家庭、政府抗争。如潞城县申海棠与丈夫感情一直不佳,申常因对婚姻不满故意生事,男人愤而出手,她即借故提出离婚。[19]对女性提出离婚的审讯记录中有大量的她们用官方词汇回应离婚理由的案例。
女性与组织、政策结盟有效地达成自我婚姻诉求。一方面,妇救会、政府成了她们解决自我问题的场域;另一方面,在这些法律条例的明文规定中寻找到了可凭之据,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弱者的形象,进而诉说符合政策的“不幸”与“痛苦”,她们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
(二)违规诉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传统婚姻仍占主导地位,女性多无法自主选择结婚对象,婚后对丈夫又有诸多不满,长此以往造成夫妻感情不和。在较闭塞的环境中,发生婚外性关系成了她们排解对婚姻不满之感的主要途径。武乡五区树早村的田成家与丈夫感情不好,嫌丈夫外貌不佳,再加之贪图小利与别的男人苟合。[20]和顺东关的李改梅对自家男人样样不满,婚后夫妻关系不睦,该女子常与他人通奸。[21]
此时的华北乡村,女性离婚亦不为乡土大众及干部接受与认可,离婚的艰难性就可想而知了。面对遥遥无期的婚姻关系解除,有些妇女便通过“乱搞”表达自己的不满或以此挑战男权的尊严。四区一妇女干部,丈夫智商有问题。女方提出离婚,政府为迁就男方,同时也担心由此会引发更多的离婚案件,一直未准,以致女方后来有了婚外性关系。[22]151虽然乡土社会的男女性关系并不像士大夫阶层那般严防死守,但“性乱”“破鞋”对一个女人来说也并不光彩。当她们生活缺少必要的更新途径时,性成了她们诉说的主要方式。
面对无法解脱的不幸婚姻,其中一些女性选择不同居、破坏财产甚至杀害丈夫和孩子等多种报复行为,挑战旧有的婚姻与伦理体系。
首先,一些妇女因不满婚姻而浪费粮食和生活物资。新绛县义泉村,金某婚前因丈夫长相不佳,遂心生厌恶。婚后此种态度依旧未变,但又不敢提出离婚。后得知即便提出也未必能如愿,索性断了离婚的念想。为发泄不满,丈夫每天打多少柴她就烧多少,做饭也很浪费。[16]不与丈夫发生性关系是第二种报复方式。介休一区一父母主婚的女子为了不和丈夫同房,“晚上睡觉裤子还结上疙瘩”。[13]磁县义张庄村妇女柴茂青被前夫抛弃后,被迫嫁与支书的弟弟为妻。因被迫成婚,婚后20天她一直和衣而睡。[23]伤害孩子和丈夫是第三种方式,也最为极端。沁源一区垣上村村干强迫郭春梅嫁给她的大伯子,结果该女子将她与大伯子生的4个孩子都害死了。[24]汾城南杨耕地村刘风英多次提出离婚,男方都不同意。后来区上接受了她的离婚请求,但到县上又未得到准许。她悲愤难耐,遂将男人砍了几刀,后去自首。[25]
女性在史学家的书写中常默默无闻地存在,她们的反抗史亦很少被提及,然而现实中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建构反抗武器。高彦颐认为:中国女人的历史有两种律动,“一种是私下的、个人的,另一种则是公众的、国族的”。在理解“真实的”女声后,让这些“微型化”或“被封装”的历史重建光明。[26]7—9当然我们不可能获得太多那个时代的“女声”,本文希冀通过对档案资料的爬梳,间接聆听她们的声音。
四、无声的反抗:沉默中的灭亡
在新婚姻政策的洗礼下,乡村女性婚姻观念已有所改变,但敢于通过抗争来解决自己婚姻问题的农妇毕竟是少数,面对不理想的婚姻状况,她们多表现出无可奈何与不知所措。
(一)忍受痛苦
在这些无奈的妇女群体中,“听天由命”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很多妇女认为自己“命该如此”。如栗城县某村一高姓妇女在谈到自己不幸婚姻时,此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男人很小,不懂什么,性欲上达不到我的满足。因而爱情很差,于是向别人发生性交。但现在男人反不喜爱我,……成年半个不和我谈两句正当话,到现在二十多岁了,还没有生一个小孩,我很想离了婚,但是我娘家说:离了婚就不让我住家了,以后永不理我了。只能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慢慢的吧。[27]
试问:离婚后或逃离原生活圈后,若娘家回不去或娘家无力供养她们,她们的出路在哪儿?命运如何?民国时期,尽管男性们大声疾呼“娜拉”的觉醒,很多妇女也产生了自立的渴求,但能够真正赢得经济独立的女性是极少数。[3]437女性若想真正使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经济独立是根本。杨懋春的社会调查中提到:“被遗弃的妻子不知道任何法律程序,害怕陌生人,她们确实伤透了心,但认为抗争没有用——她们已经失去丈夫了。她们认命了,不作太多的反抗,因为她们还有孩子可依靠,有公婆供养她们。”[8]115由此可见,很多妇女的“认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她们无力养活自己,与其漂泊在外,不如继续忍耐下去。传统乡村妇女扮演的角色有限,她们对“母亲”的角色看得尤为重要。对孩子的情感和自我未来生活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以至于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们认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自戕生命
革命战争时期,一些乡村女性苦于婚姻家庭生活无出路自杀。自戕生命一方面是她们悲观失望的具体表现,即农民日常概念中的“想不开”;另一方面是她们将性命作为话语与利益争夺以及道德资本积累的筹码,也就是“赌气”。1943年后为了稳定抗战大局,妇女解放方向逐渐由“婚姻自由”转向了“和睦家庭”。华北抗日根据地亦通过“立典推英”鼓励女性参加生产,塑造“新女性”群体。然而政策调整后,一些地区对婚姻案件仅以家庭和睦劝解,本处弱势的妇女因申诉无门只能以死抗争。涉县1946年曾有37个妇女因婚姻不自由自杀。[28]据涞源四个区1947年9个月的统计,因婚姻不自由自杀的妇女有13名。[29]北岳区1948年11、12两个月内,6个县13起妇女自杀案件,对婚姻不满的10件。[30]晋城1949年春夏以来因村干不给开具离婚证明上吊、跳井死了两个。[14]从当时女性自杀记录中,我们已很难明确多少人将“自杀”作为诉说自我委屈、从道义上谴责家庭不公的手段;又有多少人真的是无路可走,未来的日子只能以死相对。
就长期受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挟制的妇女而言,为逃离苦难生活采取较为激进手段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仍采用最传统的“听天由命”“自杀”等形式无声地反抗社会的不公及家庭的虐待。婚姻政策颁布后仍存在的消极现象是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反复。
五、结语
新婚姻政策下沉到乡村社会过程中,不断与基层磨合,其间充溢着法律与习俗、两性关系、新旧婚姻观念等多方的冲突与博弈。女性婚姻实态折射出乡村社会中旧有习俗势力根深蒂固,维系家庭与农业生产的传统父权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40年代华北乡村并不具备实行婚姻充分自由的经济与观念条件,加之婚姻变革的复杂性,致使新婚姻政策推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矛盾与问题。
婚姻政策的颁布给乡村女性带来了获得新生的希望与解放的机会,但总体来看,在经济与政治地位上都处于劣势的乡村女性对婚姻尚无太多选择的主动性。当传统尚未洗涤殆尽时,她们一方面要继续被“父权”压迫,两性平等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另一方面当女性被革命亟需之际,她们的婚姻与身体又成了动员男性、完成战争与革命任务的主要媒介,她们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在近代中国挽救国家危亡的过程中,女性身体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具。而且“革命中国”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在阶级革命框架中推进的,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形影不离”。
由于眼界、学识等多方因素的限制,“革命启蒙”后的乡村女性对新婚姻政策的理解并非完全到位,且她们多是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是否遵循新婚姻政策。面对传统与革命带来的婚姻压力,她们的反映多元,结局亦不同。既有利用政策、政治话语和传统抗争,展现了女性为争取婚姻权利积极抗争的鲜活场景;也有认命、在困顿中结束生命或继续无可奈何地度过余生的悲惨处境。女性深处革命、民族、阶级、性别等多重视域之中,婚姻自由、现代婚姻制度真正建立的道路仍荆棘密布。
参考文献:
[1] 北岳三地委.关于婚姻政策执行的检查(1943年)[B].山西省档案馆,A44-7-2-1.
[2] 白潮.乡村法案——1940年代太行地区政府断案63例[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3] 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闺女接客娘不恼”常成娥母女太“自由”[N].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8-8(4).
[5] 沁源县关于妇女运动的简结(1949年1月21日)[B].山西省档案馆, A12-8-6-4.
[6] 婚姻案件与妇女解放[N].抗战日报,1943-3-13(4).
[7]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2006.
[8]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9] 冀南区党委妇总会.1942年妇女工作总结(1942年12月22日)[B].河北省档案馆,25-1-317-1.
[10] 长治二区信义妇女工作调查材料(1948年8月2日)[B].山西省档案馆, A1-7-8-2.
[11] (美)L.S.斯诺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 晋中区妇委.晋中区妇女工作总结报告[B].山西省档案馆,A47-1-113-2.
[13] 岳北妇联.岳北妇女运动开展情况的总结(1949年)[B].山西省档案馆,A13-8-3-1.
[14] 太岳区四地委.关于妇女工作材料之一节(1949年7月4日)[B].山西省档案馆,A12-8-6-9.
[15] 如何贯彻中央关于农村妇女工作决定(1949年)[B].山西省档案馆,A1-7-12-5.
[16] 婚姻问题宣传教育材料(1949年)[B].山西省档案馆,A37-5-1-8.
[17] 临县一年来实行婚姻自由的概况[N].晋绥日报,1949-2-28(2).
[18] 亚苏.三三妇女工作意见谈[N].中国妇女,1940-8-10.
[19] 潞城县一年来婚姻问题和解决情况(1949年1月12日)[B].山西省档案馆,A1-7-13-3.
[20] 晋冀豫区妇总会.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8月—1942年5月(1942年7月15日)[B].山西省档案馆,A1-7-4-13.
[21] 和顺东关妇女典型材料调查(1948年月15日)[B].山西省档案馆,A1-7-8-5.
[22]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河北省妇女运动资料选辑(第3辑)[Z].内部发行,1983.
[23] 磁县不少村庄妇女 严重受虐待杀害 磁县政府应彻底检查迅作处理[N].新华日报,1949-3-8(2).
[24] 沁源一区垣上村妇女运动简结(1949年2月13日)[B].山西省档案馆,A13-8-3-9.
[25] 晋绥十地委妇委.十分区婚姻问题材料(1949年2月1日)[B].山西省档案馆,A35-1-9-10.
[26] (美)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7] 第五区妇救会关于口则村妇救工作的总结(1943年1月)[B].山西省档案馆,A166-1-137-3.
[28] 北岳区妇联.妇女工作研究报告(1948年12月4日)[B].山西省档案馆,A43-7-5-1.
[29] 五专署妇联会.关于执行婚姻政策的检查与今后的意见(1947年12月14日)[B].河北省档案馆,33-1-7-4.
[30] 涞源县委检讨妇运工作.北岳日报[N].1948-1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