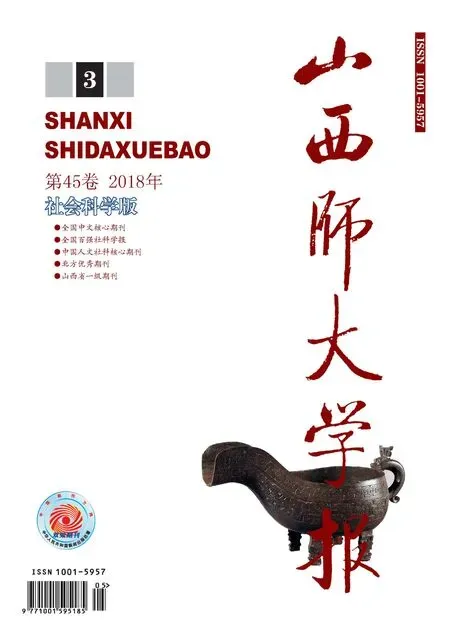两 汉 谶 纬 堪 舆 考
张 耀 天
(武昌理工学院 通话素质教育学院,武汉 430200)
中国思想史研究涉及两汉历史部分,对有关彼时形成的谶纬研究,一般言之甚少。原因有三:一是留存文献较少,谶纬涉及国家政治生活成分较多,为两汉之后历代统治者所焚禁,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方向的建立;二是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讲“子不语”的理想主义倾向有关,谶纬多有封建迷信成分,而后世哲学体系或思想史体系建立,多以秉持纯粹理性之立场,故谶纬多不察;三是谶纬实际囊括的学科颇为繁杂,不仅不易于操作,且难以寻觅切口。谶纬按顾颉刚的说法,包括上古神话、释经、天文、历法、神灵、地理、史事、文字等领域。颇类似今天所讲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又任继愈先生、冯友兰先生,在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内,认为谶纬为两汉神学或两汉经学庸俗化的呈现,此后中国思想史对谶纬之考察,多持回避态度。但哲学的童年,除了愚昧与迷信,对谶纬的考察,不仅是研究中国哲学形成时期的“歧路”的重要素材,也是研究两汉政治生活、民俗生活的主要样本。
两汉谶纬体系非常复杂。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谶纬可能杂糅了诸如三代神学、儒家经学、老庄道家思想、阴阳家及易学家的占卜、相数学等知识体系,也可能受到了外来宗教诸如佛教生命循环、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影响。从其思想发生的角度出发,可以远溯至传说中河图洛书、先天八卦等中华文明的图腾时期,及周代之前的连山易、归藏易等与周易不同的生命体认知方式,另外与秦汉之际的阴阳灾异说、道家神仙说和当时在世界领域内较为先进的天文学有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讲,两汉谶纬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进程重要的一环,一方面它可能继承了先秦乃至于先周的神学思想,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神话世界”的相关史料,同时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性主义思潮,尝试用经学的理性诠释对“神话世界”的合理性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它之后的中国文化开始新的征程,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体系开始历时长达千年的对谶纬因素的“正本清源”和恢复理性的工作。但不可否认,谶纬作为两汉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的史实, 首先,它已经渗入到两汉的政治生活,谶纬成为西汉的宫廷政治的主要内容,及王莽新朝和东汉立国的基础;其次,它成为后世中国宗教世界构成的一个重要时代,中国本土道教的神仙体系和后世道教发展的诸如丹学、符咒等,均以为基础。更重要的是,剔除其封建迷信的成分,谶纬也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如天文历法、人居地理、地理数学算数、建筑科学等学科,在这一时期都被充满想象力的谶纬体系所刺激,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1]
彼时谶纬体系的思考,依然是建立在以天人关系为目的,杂以天文、地理、占卜、星相、算数、方术等具体方法,进而构建起一个涵盖对宇宙天文、地理人文及历史人事规律探索的思想体系。两汉时期也是中国堪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秦代焚书而占卜类图书不焚,为堪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线索;“堪舆”首次在中国历史史料中出现,也是在汉代,《史记》《汉书》中均有对堪舆家或堪舆史实的描述。如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中有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皇家婚嫁礼仪都把堪舆家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可见两汉时期堪舆已经融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体系中。更重要的是,后世的堪舆学体系的建立,在这一个时期也逐渐形成雏形,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望气堪地的方法论和和谐人居的价值论,包括堪舆的相关图符、厌胜等方术,都受到了彼时谶纬学说的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讲,后世堪舆学可能脱胎于谶纬,或者说至少堪舆学在谶纬的影响下得到了重大发展。[2]
一、 谶纬源考
谶纬起源于占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儒者多称谶纬, 其实谶自谶, 纬自纬, 非一类。谶者,诡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支流,衍旁义”。在清代学者看来,“谶”多诡隐语,为占卜预测;纬则是经学的旁支与演绎,而事实上谶纬语境中的纬书,也多以神秘主义去阐释经典,也是古人附会经学、预决吉凶的一种文化现象。
谶纬有别。中国文字的象形初意,都和夏商时期的占卜有关,谶纬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谶”大体源头有三:一是中国古代的图腾,如今天考古发现的许多原始壁画,既有图腾记录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历史;后世对这些图腾的引申和阐释,都是建立在这些图腾语焉不详的基础上,这些图腾因描述历史不及文字清晰,故解释空间很大。
二是专指“河图洛书”并以此为蓝本的后世的附会。河图洛书的传说,一直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全程。目前可见的先秦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河图洛书于《尚书》,《尚书·顾命》中讲:“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再如《易传》中讲:“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中也有对河图洛书的文字记载,如《论语5子罕》有记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见,河图洛书不管是事实还是传说,先秦时期确已深入知识分子的考察。两汉时期,几乎所有学者都有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如西汉孔安国说:“河图,八卦是也。”孔安国作为孔门传人,在注《论语·子罕》时,首次提出“河图,八卦是也”。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这一点也是秉持了《周易》对河图洛书的认知立场。扬雄则称:“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扬雄是结合了历史传说,也认为龙马神龟贡献的河图洛书,是伏羲画卦的基础。班固在著《汉书·五行志》时,直接引用了刘歆观点:“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确定了河图洛书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也明确了两汉时期河图洛书与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
三是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专业”的术士以阴阳学说为宗旨,所建立一个整套有借以判断吉凶、具有神秘性的符号,这些图谶内容十分丰富,大体有符命、图谶及书谶等,并在两汉时期蔚为大观。如《后汉书5张衡传》中有详细记载的“谶书”大体有八十种, 如《春秋谶》《诗谶》《春秋元命包》等,这些“谶书”多假托圣人、或附会经典,富含封建迷信的色彩,是两汉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纬书较之经典而言,是对圣人经典的旁支解释。两汉时期纬书颇盛,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为代表和底色,涌现出一大批以神秘主义解释儒家经典的纬书体系。特别是东汉以来,儒生对儒家传统经典诠释比较经典的,有《书纬》《易纬》《诗纬》《礼纬》《春秋纬》《乐纬》《孝经纬》,被后世统称为“七经纬”或“七纬”。这“七经纬”中,除了传统的“六经”外,还有对《孝经》的解读。这些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既非训诂,也非大义,而是关注于宇宙生成的形上学讨论、《易经》传统的象数讨论、伦理与天道相符的合法性讨论。
纬书系统的发展,事实上得到了皇家政治的大力支持。从陈胜吴广起义中的“大楚兴,陈胜王”,到汉高祖刘邦反秦立汉,都有借助谶纬民谣的舆论力量。另,秦朝末年也有谶语“亡秦者胡也”,后来果然秦二世胡亥死而秦亡。新朝的王莽、东汉立国的刘秀,也都是个中高手,均利用谶纬进行政治舆论的宣传。光武帝刘秀在对谶纬的推广上,走得更远,如早年刘秀起兵是利用了当时流传的《赤伏符》上的谶语,而取得天下后,更是“宣布图谶于天下”,由此流行于秦汉之际的谶纬文献体系,正式建立,共计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还有儒生假托为伏羲到孔子演绎的三十篇,加上“七经纬”三十六篇,共八十一篇。借助于国家政治的力量,实现了谶纬之学的神圣地位。
两汉的这种谶纬文化氛围,实现了神秘主义诠释经典的三个方向:一是实现了神秘主义解经的体系化。中国历史上,如此庞大的学术力量,四百年历史从今文儒生,到董仲舒《春秋繁露》,再到扬雄、刘歆解经,王莽新朝建立,东汉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最终以《白虎通义》为总结。整个中国的文化,陷入了一种“理性的愚昧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用理性来遮蔽文化的非理性,用理性塑造一个愚昧的时代。图谶、纬书,成为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二是神秘主义解经的合法化。《史记》中记载西汉王朝早期有关国家祭祀、五岳封禅,有关后宫政治中的巫祝政变,这些都证明汉朝早期的最高统治者事实上默认了这种神秘主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东汉的五经博士,皆通晓谶纬,如同明朝万历皇帝以道教的“青词”来确定内阁首辅一样,知识分子反而把谶纬作为“内学”,把儒家传统经典视为“外学”。至于到班固所著的《白虎通义》,更是糅合了谶纬与传统经学,成为谶纬合法化的证明。三是神秘主义解经的职业化。尽管两汉时期,谶纬的迷信和荒谬,遭到了张衡和王充等人的坚决反对,但此时神秘主义解经建立一个庞大职业社会人群。上到经学博士、国家官吏、皇室成员,再有阴阳家、堪舆家、占卜师等,都以这种“神秘主义”为职业。这是中国历朝所不曾有的、空前绝后的一个迷信王朝。[3]
谶纬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是经学庞流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在西方的这个时期,也有对《圣经》所构建的神学体系进行过度解读、曲解误读的时期。如《尚书中候考河命》:“舜乃设坛于河,如尧所行,至于下稷,容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置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曰:‘禅于夏后,天下康昌’。”此时的知识分子,附会了河图洛书,认为这是中国禅让的信物,同时把当时的具体场景以栩栩如生的写实主义描述出来,指出黄龙所负的河图,“赤文绿错”,长达“三十二尺”。《圣经》之后的时代,学界对《圣经》也确实存在过过度解读的漫长时期,如有教士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宇宙诞生的时间,及世界万物诞生的时间表等。这种争论一直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尼西亚公会。这个会议,和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通过《白虎通义》一样,也通过了《尼西亚信经》,结束了这场论战,《尼西亚信经》由此成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由此可见,“神俗互证”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二、 谶纬诠释体系与堪舆学基本学科建设
借助谶纬的合法性地位,堪舆学在两汉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堪舆”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在《史记》《淮南子》《汉书》《吴越春秋》及扬雄《甘泉赋》中频频出现,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或是一种天文地理的研究学科。其中《汉书·艺文志》就其目录而言,有“堪舆金匮”十四卷,从卜筮择吉的角度论述风水,成为后世理法派专著;而《宫宅地形》是从环境地理与建筑布局来论述堪舆理论的,成为后世形法派专著。此外,后世多为托古所著的《青囊经》《青乌经》《搜山记》等堪舆学的“开山之作”,也多相传为此时所著。同时,出土的该时期文献,如北大整理的“北大汉简”有关堪舆的记录等,也可以印证这个时代是堪舆理论辈出的时代。与儒家经典神学化的谶纬相比,堪舆反倒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如《汉书·艺文志》所讲:“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形,壬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堪舆以人地关系为核心考察对象,囊括有关中国传统天人关系认知基础上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展示出两汉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而彼时的谶纬学说,对堪舆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关学科依据、研究切口和基本研究方法的“道—学—术”一体化的依据。
谶纬的诠释方法,为堪舆学附会于儒家经典、构建学科体系,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先秦至两汉,基于皇家政权的迷信,及谶纬的流行,加之天文学、地理学的逐渐成熟,各种方术、神仙术极为风行,并且深入到民俗生活中。如王充在《论衡·四讳》中批判道:“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王充在当时即批判当时社会忌讳“西益宅”的迷信现象,而在今天的农村建筑中,也屡见成俗。另,《史记·樗里子列传》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樗里子在生前即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并且预言死后一百年天子的宫室和墓地会在自己墓地的左右。至汉代,果然“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这些文字记载,都说明对于居住环境(后世所谓的“阳宅”)、墓地选择(后世所谓的“阴宅”)在秦汉之际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表述”背后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应该如何构建?或者讲,如何借助寻找一个“元理论”来构建整个堪舆学的“道学”体系?这成为两汉之际堪舆学发展的一个瓶颈。西周初年,以周公为首的知识分子对西周之前的巫祝文化进行了改造,通过“敬德保民”剔除了原始神学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堪舆学的神秘体验,如何在理性主义之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获得合法性来源,成为堪舆学发展的重点。而此时的谶纬流行,以神学精神解读儒家经典的方式,恰好为堪舆学的发展瓶颈提供了破局之法。
堪舆学开始模仿谶纬对经典的解读方式,构建起一个建立在“天人合一”且为儒家思想所承认的经典解读方式,把人类“趋吉避凶”的本能,提升到“人文化成”的高度。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讲,“凡民函五常之性,而且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上之风气。”认为人的性格乃至于人的声音、方言,都是受“风气”、风水的影响。这个解释体系的路径建设,以及附会经典、附会元典的思想,也是当时谶纬思想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结果。[4]
三、谶纬“天人感应”思想与堪舆学人地关系
两汉谶纬的底子就是天人感应。这个“天”,是被人格化的天,既是儒家传统中的自然之天、道德之天、规律之天,也是神学中的意志之天、生杀之天、赏罚之天。这个“天”已经脱离了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讲的“天何言哉”的自然主义倾向,成为一个赏罚、生杀的人格神。具备了人格意义的“天”,自然有它的情感、它的思想、它的感受,所以智者如果能够借助一系列的灾变、符瑞、异相去管窥天意、探知天意,那么就可以趋吉避凶,实现个人意志了。
如果说谶纬是两汉的一种文化现象,那么董仲舒的思想则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代表。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写道: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
董仲舒以“帝王师”自居,借助灾变说告诫帝王,如果王道能够正行,那么天地当代元气就能和顺,风调雨顺,景星出现,黄龙下降;如果王道不能正行,那么天则有变,天地的乖戾之气就会呈现,灾难就会降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时候,仁民亲物,赋税合理,家家和睦,道德立国,甘露、朱草、醴泉、凤凰、麒麟等这些祥瑞就会出现。在这段文字中,看到的董仲舒不再是一个儒家先贤至圣的形象,而更类似于一个江湖术士。
东汉光武帝刘秀,本人不仅笃信谶纬,更是借助谶纬实现政治抱负的获益者。如当时流行的《赤伏符》,其中有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再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这些谶纬之说,不仅在今天看来荒谬,时人也认为荒诞不经。早在西汉,王充即对当时流行的许多谶纬迷信,进行了批判,如儒家所歌颂的古代帝王“天人感应”祥瑞事件,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在王充看来,或为荒谬,或为偶然:“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谶纬有关“天人感应”的应用,仅具有思想史的研究价值,其中富含封建迷信和神秘主义。但这“天人感应”学说却对堪舆学构建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关系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堪舆学是对人趋吉避凶居住取向的思考,但是整体的哲学观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思考基础上。
两汉时期整个阴阳学说和“天人感应”学说,渗透在对儒家学者对传统经典的解释体系中。此时的堪舆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阴阳、五行、八卦等堪舆的主要元素,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认,同时堪舆中“望气”实践的方法,也在“天人感应”的解经体系中得到了论证。堪舆学在弥漫着浓郁神学气息的两汉谶纬现象中,迅速成长。如《淮南子·地形》即以“天人感应”说,对人类所居住的地理环境进行分析:
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豁谷为牧。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怄;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 皆应其类。
《淮南子·地形》杂糅了先秦以来人们对地理构造形成的猜想,高山、河流、丘陵、峡谷,都具有人格特点;矿产资源,是因水而生;人口生育的性别比例,是感气而生;人的性格特征,也与各地气象、水土有关,所以说中土出圣人。由此可见,有关天人感应、风水气象等要素,已经富含堪舆的基本思想。在这个阶段,谶纬的“天人感应”说启发了堪舆学建立的世界观基础,并开始以人地关系的考察作为学科研究的中心。可以讲,谶纬突破对天道人事的神秘主义解释,为堪舆学构建人地关系为核心的研究切口,提供了关键性思路。
四、谶纬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与堪舆学时空观
两汉时期谶纬脱胎于阴阳五行,这种对宇宙结构和生命生成特有的哲学观,自春秋战国缘起之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于哲学领域均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彼时,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代表的史学,董仲舒、桑弘羊为代表的儒学,张衡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等,在其相关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对阴阳学说的认可。如司马迁父子认为:“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也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阴阳学说并非完全出于一种迷信的考虑,相反司马迁父子认为阴阳学说有以迷信裹挟民众的嫌疑,但同时认为阴阳学说中对顺应天时的启发是可取的: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作为对世界基本认知的阴阳假说,加之五行说,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现象划分、总结的成果,具有极强的普适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认知成果,可以“套用”于任何现象观察且可言之成理。两汉的谶纬,秉持阴阳五行的宇宙生成论,用阴阳相化、五行生克作为解释世界变化的基本原理。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算数,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表示空间与时间的方位、天干、地支等范畴也逐渐成熟,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特有宇宙观。同时,在谶纬“天人感应”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堪舆充分吸收了谶纬中的阴阳五行说,把对人地关系的探索,放置到天人感应的语境内,同时把人类“趋吉避凶”的本能提升到智慧把握的层面,由此在两汉谶纬神学的土壤内,诞生了较为完备的堪舆学体系。
如后世保留比较好的、已经公认为两汉时期的纬书文献《乾凿度》,此文假托为孔子所著。东汉《白虎通义·天地》已引用《乾凿度》,可以推测该文大体出现的时间应该不晚于东汉。《乾凿度》对后世道家、儒家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一个宇宙生成体系,认为宇宙生成是一个由“寂然无物”的“太易”到“太始”,这过程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乾凿度》把易道、太初、天地、阴阳、气化等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都纳入到研究体系中,对后世堪舆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根本性的关键作用。如《乾凿度》中假托孔子之口,把阴阳、八卦、地支、天干、四时都囊括到一个庞大的宇宙生成体系,堪舆学中有关时空的思考,皆脱胎于此:
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万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剥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依其类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乾凿度》把易与太极、分生阴阳,作为天地之始;春夏秋冬,四时为四象;四象分阴阳,故为八卦。八卦与方位相匹配,象征四正四维,成为堪舆学方位和时空观察的出发点。而这些都是“易德”的象征,又归于“天人感应”的主流思想。堪舆学在谶纬宇宙观的观照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空方位认识论,并成为堪舆实践中对人居地理考察的基本原则。
两汉谶纬对中国哲学或历史之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近代谶纬研究者刘师培认为,谶纬有五个方面的价值: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两汉谶纬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同时两汉谶纬的出现,也是对先秦巫祝文化、天文地理知识、阴阳五行学说等文化源流的一次总结。两汉谶纬所形成的中国古代特有的“天人感应”世界观,及浓郁的神秘主义文化氛围,都催生了或促成了堪舆学体系的形成。堪舆学中有关天人关系的认知、有关人地关系的考察、有关时间空间的认知,也都源于两汉谶纬。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讲,两汉谶纬是后世堪舆学之母。[5]
纵观世界各个文明古国的发展历史,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一直充斥在文明历程的道路上。从本质上讲,谶纬或堪舆,与其他人类科学一样,都是人类通过自己的立场认知世界、理解世界,并尝试通过智慧实现趋吉避凶本能的一种方式。谶纬或堪舆之类的富含封建迷信的知识体系,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科学,究其原因在于基本认知立场的错误:谶纬和堪舆,均是建立在“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的基本认知立场上,这种神秘的、体验式的认知逻辑,形成了一个个不可验证的、认知逻辑不可逆的因果链条。即按照谶纬或堪舆产生的认知结果,只在“天人感应”的认知环境中成立,脱离了这个环境,很难寻觅其成立的合理成分。以“风水”为极端化表征的堪舆学,在今天成为一个经济现象乃至于“显学”,捆绑到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的快车,今天的“风水”让历代学者力图剔除的堪舆学中迷信要素死灰复燃,并且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的行业。究其原因就在于,“天人感应”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从古至今每个中国人的认知世界中。也唯有以科学精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参考文献:
[1]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2] 杨庆中.论孔子仁学的内在逻辑[J].齐鲁学刊,1997,(1).
[3] 张耀天.试论周易历史哲学的天命观[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3,(6).
[4] 张耀天.堪舆名考及理论溯源初探[J].常州大学学报,2012,(4).
[5] 张耀天.《禹贡》堪舆考[J].船山学刊,2013,(4).
——以王嘉《拾遗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