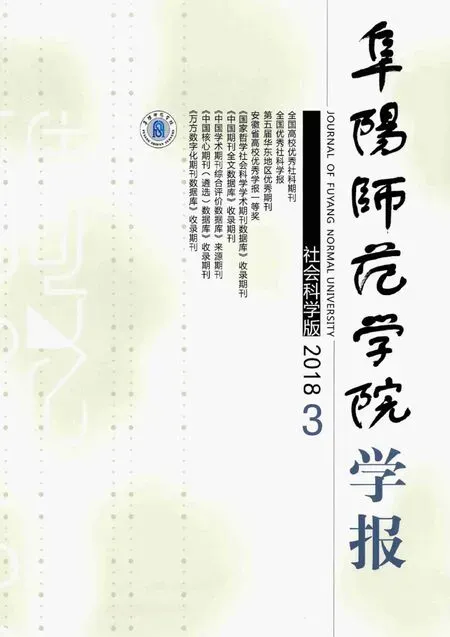诠释学视域下的朱熹与戴震孟学比较
余亚斐
诠释学视域下的朱熹与戴震孟学比较
余亚斐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朱熹和戴震是宋代至清代孟学系谱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对《孟子》的注释和疏证,表现了不同的诠释理路。以诠释学为视域,分别从历史性、问题意识、诠释方法和视域融合四个角度对朱熹和戴震的《孟子》诠释现象进行分析,阐明两人在孟学研究上的差异和在孟学上的贡献。
朱熹;戴震;孟子;诠释学
学界对朱熹与戴震的研究由来已久,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张立文、陈来、汤一介、余英时、吴根友、黄俊杰等学者都有诸多成果问世。近十多年来,以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研究逐渐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诠释学也已初具规模,其中以汤一介创建的“中国解释学”和台湾黄俊杰的孟学诠释史研究为代表。虽然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化,做具体的研究。从现代诠释学的视野展开对朱熹和戴震注孟比较研究,整合传统与当代,既援“西”释“中”,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有助于彰显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特点,推动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发展。
一、朱熹与戴震的历史性比较
朱熹与戴震作为《孟子》的诠释者,他们都生活在不同于《孟子》成书的战国中期的另一个时空条件之中,他们对《孟子》的诠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以及自己经验的影响,这些构成了诠释者的历史性。在哲学诠释学看来,历史性是一切理解活动的前提,“我们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1]387,历史性本然地包含在了理解活动之中,构成了理解的“前见解”。历史性的存在,使得诠释者所理解的经典内涵与经典的原意产生差距,并构成诠释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孟子以及《孟子》成书存在于大一统形成之前的战国中期,当时的政治与文化处在多元开放的状态,孟子以“游士”自居,无恒产、无定主,入世而不仕,不隶属于某一政治势力,不服务于某一政治理念,正如孟子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2]96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造就了孟子的独立思想与批判意识。孟子所处的时代,功利主义盛行,墨家与杨朱学派占据主流,儒家式微,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2]155所以孟子写作《孟子》一书,着重于批判杨朱与墨家学派,阐明仁义的社会意义,重振儒家。与孟子不同,朱熹与戴震都生活在大一统形成已久的封建社会,他们所面临的思想挑战也完全不同,他们不同的历史性,是造成其思想差异的原因之一。
朱熹处于中国封建制度危机四伏的南宋时期,他所面对的是由唐末以来长期混战所带来的社会纲常伦理秩序的破坏,从思想上来看,这些动荡是儒学衰落和佛学冲击的结果。在宋代新儒家产生之前,儒家着力于社会形下层面的伦理和政治实践,在社会政治领域和人伦生活方面发挥作用,在哲学思想方面则鲜有建树。佛教与道教在魏晋之后得到长足发展,与儒家不同,释、老两家集中于玄之又玄的心性、天道等思辨哲学,逐步占据了思想领域,并由思想领域渗透到社会政治与生活各个方面,层层瓦解儒家的社会根基。作为宋代思想领袖的朱熹,他自觉地承担起应战佛教思辨哲学、建构儒家形而上学的历史任务。在朱熹之前,中唐大儒韩愈首倡儒家“道统”,以区别道、释之传承,实现儒家自觉。正如韩愈在《原道》中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韩愈认为,儒家正统传至孟子中断,后儒理应承接孟子而传,所以,孟子成为原儒与新儒的连接点。宋代理学家接受了韩愈的这一主张,自觉继承儒家道统,《孟子》也因此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正如朱熹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他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4]2 596朱熹如此重视《孟子》,正是要通过集注诠释活动,在理学义理中开辟儒家形而上学,回应佛教挑战,重振儒学,完成历史任务。
与朱熹不同,戴震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乾隆年间,一方面是文字狱政治文化的高压,另一方面是天道性理的道德理学沦为官衙统治者的杀人工具。戴震的家乡在号称“程朱阙里”的徽州,明清之时,那里的理学积淀非常深厚,理学的盛行,既为古徽州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息,又使得那里的人民深受封建礼法制度的束缚。如休宁吴氏条约规定:以幼犯长、以卑抗尊者“酌其情之轻重以示罚,自一钱起至二两止,仍责令陪礼服罪”[5]。而且,戴震及其家人也深受礼法制度的迫害。当时,有本地豪绅侵占戴震家的祖坟,戴震前往县衙控告,结果县令非但不体察民情,反而认为戴震以卑抗尊,欲致其罪,使得戴震被迫避仇入京。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和个人遭遇之下,戴震对理学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正如他说:“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虽得,谓之逆。”[6]275戴震通过分析理学的理论缺陷与社会后果,反对理学化的儒学,通过重释《孟子》,恢复原始儒学的本来面貌。戴震对《孟子》的诠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历史性的影响,他的那些诠释《孟子》的著作,其矛头皆指向理学及封建等级制度,也在其中表达了对民主与人道的向往。
二、朱熹与戴震的问题意识比较
在理解与诠释文本的过程中,问题意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意识不仅是构成读者“前见解”的重要部分,而且还使读者与文本共同处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之中,正如伽达默尔说:“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了某种特定的背景中。”[1]466正是在不同的问题意识之中,文本的开放性才能得以展现,文本的意义才能在诠释中得到延伸和创生。《孟子》作为儒学经典,提出了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仁政、心性、利义等,成为后世儒家学者讨论的核心问题,但是,哪些问题首先被历史重新倡导和追问,这便取决于读者的问题意识。朱熹与戴震在诠释《孟子》的过程中,既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它们为戴震与朱熹的跨时空对话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同时又存在着差异,正是在不同问题意识下的理解,两人才展现出不同的理论旨趣,并创造了“孟学”的新意。
朱熹诠释《孟子》,主要的问题意识是在《孟子》中寻求儒家的心性论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儒家的形而上学,为理学提供合理的本体论依据。在先秦儒家中,孟子是涉及心性问题最多的思想家,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301意思是:扩充先天之心,可知人性本善。知人性本善,则知善自天出。在孟子的哲学中,“心”自天出,先天本有,“心”中蕴含着一切善的种子和根源;由“心”至“性”,是后天修养的过程,是“心”的扩充,由己达人,由人及物;由“性”知“天”,是在返归先天中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是对天人合一的实证。朱熹在对这一段话的诠释中,充分展现了他在《孟子集注》中所灌注的问题意识。朱熹解释道:“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7]349朱熹认为,“理”在“心”中,“性”即是“理”,“理”自“天”出,三者结合起来,“理”便是出自于“天”、存于人“心”、同于人性的东西。这样,朱熹既为“理”寻求到了先天的根源,“理”上升为“天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又为“理”奠定了人性的基础,天理即是人性,只有符合天理的“性”才是人性,否则就是人欲,人欲非天理、非人性。
与朱熹不同,戴震诠释《孟子》的问题意识是检视理学流于玄虚蹈空之弊端,扭转儒学经典沦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命运,批判官僚化的理学,返归被理学遮蔽的人性中的现实层面,以此实现人性的解放。朱熹通过对《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诠释为理学构建了一套精致的形而上学体系,戴震亦要通过《孟子》的诠释实现对理学体系的解构。正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补正》中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抉摘宋明理学之蔽,卓然自成一家言,其意不在专释《孟子》。”[8]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阐释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理”,显示出他强烈的批判、解构理学的问题意识。在戴震的诠释之下,“天理”不外乎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事物的道理,既不是什么超越性、神圣性的至高标准,也不是代表尊者、贵者的个人意志。戴震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6]266这段话的大义是:天理是关于自然万事的具体道理,即事理;事理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达成的共识。所以,天理是事理与人情的统一,是情理的交融。这样,戴震便通过对“理”的重释,使高高在上的“天理”重新返回生活,容纳情欲,实现了对理学的批判与对人性的关怀。
三、朱熹与戴震的诠释方法比较
中国经典诠释历来存在着两大方法的对立与交织:一是追求原意,表现出对经典的尊重;一是注重义理,体现对时代的呼应。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这两大方法又有不同的表现,如经学今古文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训诂与义理之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争等。在中国经典诠释实践中,这两大方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时常地相互交织。朱熹与戴震在注“孟”、解“孟”的过程中,自觉地反思了这两大方法的利弊,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各有侧重。
朱熹立基于宋代视域,扬弃汉学旧例,继承宋学新风,通过疑经、改经,阐发义理,直探圣人本意,趋向直抒胸臆。宋明理学肩负着应对佛老、重振儒学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在经典诠释方法上,主张打破经典原意的束缚,不拘束于文字,看重义理的贯通与高明。正如二程所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9]朱熹也继承了宋学的这一诠释方法,认为经典的精髓在于它承载的圣人之意,而圣人之意虽然通过文字来表现,但又隐含于文字之中,所以,经典的诠释必须要通过阐发,其义理才能昌明,正如他说:“大抵圣贤之言多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触而长之,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圣贤本意,则从那处推得出来?”[4]1 586不过,朱熹主张创造性的诠释,是以圣人本意为前提的,而不是读者的任意附会,不能以读者的主观理解违背作者的语意,正如他说:“大抵某之解经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不敢自以己意说道理也。”[4]1326例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解释“齐宣王好色”一段时,先对文本字词进行详细的训诂,然后立即用理学的思想体系加以诠释,朱熹在注文中说:“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7]219由此可见,朱熹又力图超越汉、宋两学的对立,主张训诂与义理相结合。但在两者的主次关系上,主张治经首在义理,根据义理来辨明字义。
与宋学诠释方法不同,清代学者将毕生精力投注朴学,从事古籍辑佚校勘、考证音韵字义、名物训诂等工作。戴震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力量,继承了文字考据与概念分析这一“汉学”诠释方法的传统,力主通过训诂达证经典义理,如戴震说:“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6]187另一方面,戴震又分析了“汉学”与“宋学”两种解经方法的弊端,认为“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6]189,力图综合两者,以字义解为方法,以义理通为目的。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正是要通过对“理”“性”“才”“道”“仁”“义”“诚”等诸多概念的分析,来揭示被宋儒遮蔽和曲解了的孟子原意,还原孟子思想的本意。如戴震分析了“性”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演变,认为在先秦儒家的《论语》《易传》和《孟子》诸书里面,人性是气化流行的产物,是感官与知觉的统一体,“性者,血气心智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6]295。随着道、佛两教的兴起,“性”成为人之感知、情欲之外的“他物”,宋儒于是仿效之,另立天理之性,实则“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终昧于六经、孔、孟之言”[6]296。由此可见,戴震诠释《孟子》,是通过文字考据与概念辨析来达到义理阐述,以此来批判宋儒。
四、朱熹与戴震的视域融合比较
读者与作者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性视域,正是因为视域的不同,造成了原意与理解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但是在现代诠释学看来,这些矛盾与差异并非是消极的,而是展现了文本意义的创生;而且,文本的意义还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去影响、被创生,和理解者一同处在不断形成和交互影响的过程之中,由此形成经典诠释的“效果历史”。因此,经典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完成的,而是一个开放的、无尽的过程,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经验和思想的综合,来实现视域的融合,形成文本更为广阔的意义。由此可见,朱熹与戴震对《孟子》的诠释,既不是回到原意的复现,也不是单纯地托物言志、阐明己意,而是彼此视域之间的融合,是对《孟子》意义的再创造。
朱熹对《孟子》的诠释,不仅奠基在传统汉唐经传笺注的基础上,更是融合了儒学与佛学,以理学思维对《孟子》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是原始儒学、佛学与理学三者的视域融合,形成了新的孟学。宋明理学无不受到佛学的影响,这是理学家无法摆脱的历史性先见,甚至可以说,没有佛学,便没有理学。在朱熹《孟子集注》中也无不渗透着佛学义理,朱熹之所以要注释《孟子》,正是因为他在《孟子》中看到了一些与佛学相近的心性理论,可以借此来建构新儒学的形而上学。如朱熹在解释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时说:“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知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7]349朱熹的解释与慧能禅师“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10]是何其相似,同时又蕴含着理学的思想宗旨。由此可见,朱熹是在综合了佛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先秦儒学进行开拓创新,佛学既是朱熹思想与原始儒学的不同之处,也是朱熹对孟学发展的最大契机。正是在朱熹的努力之下,《孟子》在儒学经典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孟子》也成为了儒学形上学的重要代表著作。
戴震一方面反思汉、宋两代儒学,认为对圣人之意的理解,必须以训诂为门径,以义理为归宿;另一方面又受到明清之际反礼教思潮的影响,将其与朴学和《孟子》思想结合起来,实现了三者的视域融合,在推动孟学的发展上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戴震扬弃了传统章句式的解经方式,如赵岐的《孟子章句》、朱熹的《孟子集注》,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体例,在孟学史上第一次对《孟子》中的重要范畴进行选取,并进行集中疏证,以范畴的方式彰显了孟子哲学的逻辑体系;其次,通过对《孟子》的诠释,戴震复兴了原始儒家的人道精神,重新将儒家的形上道德领域转向形下经验世界,回归生活儒学传统。正如戴震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6]275戴震思想中的人道精神与向生活儒学的回归,既接续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孟子倡导“与民同乐”“省刑罚,薄赋敛”“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等;又使孟学向生活世界与民主思想伸展,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接轨,发扬了孟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孟子》作为儒学经典虽然具有“原意”的存在,但是它的生命通过解经、注经的历史长河所繁衍出来的意义,既超越了经典的原意,也同样超越了诠释者主观性而成为永恒的客观存在。《孟子》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它随着每个时代的理解而推陈出新。作为宋代至清代孟学系谱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朱熹与戴震的《孟子》诠释丰富了孟学的内涵,推动了孟学研究的发展。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韩愈.韩愈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91.
[4]黄士毅.朱子语类汇校[M].徐时仪,杨艳,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高寿仙.徽州文化[M].沈阳:辽阳教育出版社,1995:45.
[6]戴震.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8.
[9]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378.
[10]坛经[M].尚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3.
Comparison between Zhu Xi and Dai Zhen’s Mencius under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YU Ya-fei
(School of Politic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Zhu Xi and Dai Zhen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s in the Family Tree of Menciu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ir commentary and sub-commentary to “Mencius” reflect different explanatory approach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this article well clarifies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study of Mencius and contribution to Mencius from the analysis of Zhu Xi and Dai Zhen’s “Mencius” explanation phenomenon respectively from historicity, consciousness of questioning, explanation approach and perspective combination.
Zhu Xi; Dai Zhen; Mencius; Hermeneutics
2018-04-09
2014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诠释学视域下的朱熹与戴震孟学比较研究”(AHSKQ2014D131)。
余亚斐(1980- ),男,安徽淮南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19
B21
A
1004-4310(2018)03-01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