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语境中皖南贵池傩面具的艺术设计研究
张成勇
(怀远县茆塘学校,安徽 蚌埠 233000)
一、傩及贵池傩面具概述
傩,是以驱鬼愈、祈吉祥为目的,以戴面具手持砌末道具为表演特征的民间祭祀性活动,导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和巫觋宗教,世界各国均广泛存在。而有关中国傩的历史,饶宗颐先生曾考证为殷王的八世孙甲微创制,即“上甲微作傩”。周代将其纳入国家祭祀之“礼”,据《周礼·夏官》所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而司傩,以索室逐疫”;孔子亦说:“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1](P226)刘宝楠注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2](P226);较晚的《吕氏春秋·季春纪》则从傩与农耕文化的内在关联得出:“国人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3](P25);东汉高诱在综合孔子的言论后注解道:“傩,读论语乡人傩,同命国人傩,索宫中区隅幽阁之处,击鼓大呼驱逐不详。”[4](P25)可见,这时期的傩已经以“礼”的形式走出了宫廷,伴随仪、舞、戏等曲艺类型涌入田间地头、宗族祠堂,成为乡民生活须臾不可分割的整体部分;尔后,历代均有官方及民间自发组织较大规模的傩事活动,尤降宋至明较为兴盛。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可见当时傩事备受统治者重视。析言之,“傩”外化语言的扩张形式,使得“傩”本身的价值取向不断向“神”靠拢。实际上,向“神”靠拢,就是“人”的设计操控,反哺民众娱神娱人的视觉审美体验,克服自然灾难的良方药剂;从历时与共时角度看,傩的类型分化已具明细(官傩—军傩—乡傩);再者,从字源学的角度亦看到,傩,为“人”、“难”,人遇灾祸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义为:“行人節也,从人難聲”[5](P372),段玉裁注:“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6](P372)傩之功能即是驱逐祸害,保护自身不受伤害。从造物设计角度考量,无论是许慎的“象形”或是“傩面具”的模仿,皆是古人关照、整合一切自然现象并以此解构、归纳客观事物相似性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仿生学意义。“象形”作为艺术手法同构自然万物的共同点和异质性,将其融入客观现实的改造当中。因此,研究一切傩文化艺术的同时,要从“傩”的“基点”开始,这个“基点”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造物设计意识,实用功能与民俗审美的表征使然。从非遗角度看傩的生成与变化,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最深的根源,一个民族或群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性隐寓其中”[7](P49-50),成为流传弥久的远古音符和图腾。
地处皖南腹地的池州至今仍然保存并延续着上古时期的傩事活动,主要流布在九华山麓东南方位的贵池、青阳、东至等县区。其中,以贵池的梅街、姚街、茅坦、墩上及周边乡镇一带最为典型。每到正月初七至正月十六,乡民以各自宗族为实体,以“社”为单位展开祭祀祖宗、驱逐邪恶的宗族性仪式活动(包括傩仪、傩舞、傩舞),故而贵池有“无傩不成村”的说法,傩的普遍和兴盛投射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裙带的宗法制和农耕文化在造物活动当中的浸染。“从现存的傩事活动看,它的积淀是层累的,既表现出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内涵,也表现出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它的深厚影响。”[8](P9)优越的“吴头楚尾”地理条件,荆楚、吴越文化与祭祀昭明太子(即萧统,501―531)的土著文化及九华山地藏王菩萨文化有机交融并在此潴留,形成区别于其他诸地不同的特色内涵;其次,扫射其他省份来看,傩文化中的仪—舞—戏三段皆已断层,唯贵池傩相对较为完整,依然流露出商周的遗风,为世人展示了精湛的原始造物设计观念,而傩戏至今演绎戏曲史上早已逝去的孤本,成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由此可见,以贵池傩展开定向的艺术设计研究契合当前的非遗语境。
傩面具,贵池当地人俗称“脸子”,它是傩事的灵魂载体,亦是其核心的符码元素,具有表号和识别双重视觉价值。笔者在贵池傩文化的调研中发现:傩面具似乎顺应着“面具在则家族在,面具亡则家族亡”的历史轨迹。这种以家族为纽带的宗法祭祀制度维系着、扣结着傩面具的存在,使得面具从制作、开光、使用等一整套程序附有神的特征,以致每道工序都要虔诚膜拜,焚香祈祷,这种原始的宗教造物意识不仅流淌在乡民的心间,还浸入并控制人的生理层面。诚如傩文化学者何根海教授所写道:“傩面具是古代巫文化傩祭的表现特征,也是傩事活动的核心,更是一种象征,经过初步的艺术加工,以其古朴的线条、色彩、图案,震撼人心。”[9](P48)从目前贵池傩来看,一整套完整地规范的傩事活动,傩面具即是当然核心,一切皆围绕面具来诉诸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官能感受的原始艺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既是宗教意识的凝聚产物,又是担当人、神的使者,沟通人际与神的对话,并请神附身驱逐鬼魅;其二,从迎神下架—社坛启圣—请阳神—移驾这一轮流程亦能看到面具在傩事活动中的地位;其三,在角色扮演上,“戴面具是神,脱面具是人”,傩面具的指向性和目的性十分明确。 “它不仅作为一种道具和形式表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观念,成为民俗活动和民间文化的载体,”[10](P61)同时作为造物设计的客观形态,贵池傩面具较为完整地保存“原始产品”的雏形,蕴含诸多造物设计方面的思维意识、色彩观念以及文化内涵。(图1)

图1 贵池秋浦河畔的傩面具雕塑及祭祀昭明太子浮雕
二、造型与装饰
贵池傩面具是造型的艺术、设计的艺术。作为造物的普遍方式,具有原始初态的设计痕迹,并以实用为前提、感化为先导的精神基础;而占卜祭祀、驱逐鬼瘟的功能随着漫长地历史文化的交融渗透到贵池当地的土著文化,形成鲜明地围绕祭祀昭明太子为心理机制的文化特点。唐代罗隐《文庙诗》曰:“秋浦昭明庙,乾坤一白眉。神通高学识,天下神鬼师。”*参见《杏花村志》卷八,清代郎遂撰。可见,贵池傩在唐代已十分盛行。面具造型也有所变化,但是,其功能并未因造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是由它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稽诸文献,贵池傩面具造型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兽面纹的孕育期。主要以自然界的动物为刻画对象,如鸟、蛇、虎、鱼等。它既是氏族的图腾信仰,亦是繁衍后代的无声表露。刘街姚姓、清溪程姓、棠溪吴姓、徐村柯姓家族傩舞《打赤鸟》中,龙亭均摆放一只木制鸟形面具,造型单纯,刀法自然娴熟,较为准确地刻画出鸟的大概形象。从构成角度看,点与线的有机穿插,使其组成完整地面的统一。其他还有太和章姓的彩色虎头面具亦十分独特。

图2 招魂使者面具
第二阶段,是兽人合形的充实期。以动物和人主观臆造的鬼神相结合,在融入早期原始动物的特征后注入自身对神鬼的认知。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人总“是嫌自己的力量微薄不能判定一件行事的吉凶,要仰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一种力量来做顾问”[11](P2),用“礼器”敬天,用“面具”请神驱逐鬼魅。池州市博物馆馆藏珍品“招魂使者”面具(图2),以虎形作基础,将眼睛圆形化,眉目及嘴用力上翘,整体造型体现“黄金四目”、“狰狞凶怒”的特点。以点及面,构成合理精到,尤其是线的反复运用十分讲究,既增加了视觉的效果,又巧妙地将虎形和想象之物结合起来,单纯自然之物已不见踪迹,栩栩如生的“招魂使者”成为守护乡民生产的精神支柱。

图3 关羽面具
第三阶段,是神人同形的成熟期。由于战乱和政治权利的迁徙,东晋(317-420)、南北朝(420-589)的官宦避难贵池,将宫廷乐舞带到此地,并与当地土著的“乡人傩”合为一流,改变傩由早期巫觋方术演变成为娱神娱人的祭祀活动。“宋南渡之后,杭州成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类地方戏也随之向杭州发展”[12](P103)并辐射皖南地区的贵池。昭明太子作为“土主”及南戏传奇的融合及九华山佛教的渗透,使得傩的形式愈加丰满,常佩戴民俗戏曲的人物面具表演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剧目。如殷村姚姓家族《关公斩妖》(又名《圣帝登殿》)中的关羽(图3),其面为枣红脸,眉毛竖立,眉锁呈向上趋势,丹凤眼微睁微闭,耳垂大且竖直,头戴官帽,具有浓郁的戏曲味道和民间传说的威慑特点。这时面具已从蒙昧脱胎,大量戏曲剧目、民间传说、佛教真经的汇集,促使面具朝着程式的方向发展,以便有更多神力为乡民驱灾纳福,求得“土主”和祖宗的庇佑。
由此可见,贵池傩面具的造型变化不仅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碰撞的结晶,亦是乡民对傩的认知使然;而从造物设计角度看,傩面具造型的变化有着显著地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傩面具的写实性

图4 蛙纹彩陶
从造物属性及功能来说,傩面具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驱逐鬼疫的核心工具,虔诚地刻画面具与乡民渴望神灵的庇佑有着天然地联系;另一方面,傩面具的写实性亦是人类认知事物的把握方式,它是基于实用为目的的设计思维,而不是单纯从精神上愉悦视觉的感官,反映人类发展初期对造型艺术再现的认知心理。马家窑晚期的几何形蛙纹彩陶(图4),其最初功能与傩面具几乎等同,即用来占卜或祭祀。但是,“在人类社会文字记事不发达或巫术、宗教极为盛行之时”[13](P151),诸多实用器物便充当沟通天际的角色,被赋予神的能力。后期造物设计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活之物不能尽情地满足人对天神的崇拜,继而以具体、写实的造型代替平常所需之物,使得傩的语言更加丰富多元,而造物设计的初衷并没有因造型的写实而发生变化,只不过扩大其实用的功能;从傩面具的纹样演变历程亦可看到,傩面具与蛙纹彩陶的根本区别在于抽象的蛙纹朝着类似几何风格方向发展,而写实的面具则继续沿着“纹化”的轨迹一直前进。“纹样的图像学研究与肖像画之类的图像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抽象符号性。”[14](P151)愈加写实的造型就愈吻合设计之初的信仰,那是因为只有“像”才能表达乡民对神的敬重,而写实就是“像”的诱因,充斥着朴素的巫觋文化心理色彩。
(二)傩面具的“纹化”性
纵观整个傩面具的造型变化,其实质就是不断“纹化”地过程。《广韵》有云“纹,绫也”,为丝织或皱纹、纹路、纹样等自然肌理,延通“文化”之本义。古汉语中“文”与“纹”皆可转换用之,可见“文化”与“纹化”存在着某种发生学的关系。推察贵池傩面具的造型演变亦可看到,“纹化”不仅使其造型样式得到增益,还投射出每个时段乡民对傩的整体认知。人类最初的设计心理机制,在丰汇的视觉语言中得到反馈,继而“纹化”乡民的日常生活。
浑言之,视觉化的设计既是“纹化”的重要手段,又是承载召唤傩神灵魂使然。从整个面具造型的发展进程来看,以“纹化”为中心并向外弥散的方式十分鲜明,它囊括了视觉的两个层面:其一是造型的“纹化”。诸如傩面具初期造型多摹仿自然界的鸟、虫、燕、虎、蛇等动物形象;中期出现动物形象与臆造的鬼神结合;后期戏曲人物造型受贵池当地土著文化及九华山佛教影响,傩面具的“纹化”呈现世俗化倾向。从设计角度亦可看到,“艺术设计主要任务是造型,是利用一定材料使用一定的工具和技术为一定目的而创制的结构”[15](P55)。这种结构既是材料肌理的“纹化”变革和支撑造物设计的前提,又是工艺技术上的日臻完善,充分体现贵池乡民对生活的挚爱,对生命的讴歌,对傩神的敬重使然;其二是面具内涵的“纹化”。由单纯驱鬼瘟、祈吉祥“纹化”成娱神娱人、祭祀祖先及昭明太子为目的核心道具。制作工艺上的伐木、雕凿、制胚、煮胚、髹漆上彩、定色调整、完具成型等步骤均能体现内涵“纹化”的形式张力,可见制作愈深入,视觉“纹化”就愈加丰富,隐喻乡民以德报德、以恶制恶朴素地宗教心理和“观物取象”的设计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傩面具的造型“纹化”既是装饰语言最为本质的特征,又是人类在造物设计中用“美”的形式、“艺术”的思维改造材质的手段。因而,装饰不仅反映人类造物设计初期的心理“纹化”,亦是傩面具上最为普遍地设计符码。
三、色彩与寓意
贵池傩面具是视觉的艺术、心境的艺术。因此,“在诸多的设计语言中,色彩语言最容易传达心情,最容易与人沟通”[16](P3),最容易驱逐鬼疫、护佑乡民。诚如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所写,说道表情作用,色彩却胜过形状一筹,它比任何造型更直接地刺激视觉感官,进而使形象语义更加丰满充盈。站在文化学的立场看,人类使用色彩美化生活由来已久,例如阿尔塔米拉洞窟中受伤野牛的红色岩画、云南沧源阿佤山区红色涂绘岩画中使用赤铁矿粉杂糅牛血,无不体现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对形象的探寻、视觉的追求,除开造型写实而外,似乎唯有色彩才能表达巫觋所不能言。现代色彩学理论也表明,西方主要以自然科学的眼光解读色彩文化,多以矿物质原料的名称来命名,如淡黄、深红、湖兰、普兰等。而中国古代,由于五行学说的植入,其色彩理念则注重精神层面的象征释义,东西方对色彩的认知偏差是由民族地域文化所导致的,它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对色彩的认知及把握规律,贵池傩面具正是这种色彩观念的产物。
关于五行学说,最早见于战国后期的《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后,《吕氏春秋》在具体阐述阴阳相生相克观念的基础上强化与政治的合融,形成独具特色的色彩模式:“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17](P127)这种学说“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其物性分配了世上的万事万物”[18](P17),并集结这五种事物象征的色彩及相生相克之理。于是,“计划政治制度时就要使用这原理,编排历史系统时又要使用这个原理。”[19](P17)五行学说弥散着类似宗教信仰般的意味,包涵先民对色彩的归纳能力及数理的认知,据此“说明自然界的状态,更进而说明社会的状态”[20](P17),形成深层的心理导向机制,浸染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戏曲小说等方方面面。
(一)五行色彩观念的浸润
就贵池傩面具而言,它完整地反映五行学说在面具施色中的理念。通察面具发展历史,它是由感性走向理性,由稚拙走向成熟的运动过程。早期的巫觋面具,以自然材质为本色,没有表现色彩寓意化、装饰化和工艺化的特点;后期,面具色彩受使用功能、地域文化等复杂的因素影响,隐含宗教、道德、人性的寓意。尤其是象征五行的赤、黄、青、白、黑搭配并用,使其形象更加鲜明、指向更为明确。
如五行中象征火的赤色在缟溪曹姓、邱村柯姓、张村汪姓及茅坦山湖唐王二姓演出的《关公斩妖》剧目,时常可见关公脚踩竹马手舞大刀,捉拿东、南、西、北、中五方鬼怪。殷村姚姓的《圣帝登殿》则是关羽身着绿袍,率关平、周仓登临巡视,目扫周围鬼魅。虽有各异,但所配面具皆为赤色,象征武圣关羽忠肝义胆、勇猛无比的英雄形象。
而象征土的黄色在梅街太和章氏宗族所演的《刘文龙赶考》等剧目中均有体现。《刘文龙赶考》,以刘文龙祖先积有阴德,被玉帝所知,派文曲星君下凡将其心换为文曲之心,指点考取功名,又派九天玄女教其武功,平定和番以及求取功名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烽火刘姓家族所演《和番记》与上述村落虽有情节不同,但玉帝所戴面具通为黄色,象征功德广大、忠实权威之意。
五行属木的青色,主要依存山湖村王、唐、项三姓及潘桥邱村柯多姓演绎的《钟馗捉小鬼》戏文里。钟馗头戴青色面具,驼背鸡胸,手持神剑,身披“彩钱”,以剑指小鬼,小鬼跪地求饶。其后,小鬼夺钟馗剑,钟馗反向小鬼卑躬屈膝。最后,钟馗生智,夺其剑继而斩杀小鬼。钟馗是阴间神力,故而以青色释义阴森可怖,表现钟馗桀骜不驯的性格。
白色为五行金性,如土地公、仙人、和尚等其它形象。山湖新唐屋、老唐屋、阳春王姓的《和尚采花》,有和尚、童子、姑娘、嫂嫂。乡民戴白色和尚面具,手拿宫扇,作一定动作,旁蹲一童子,持小旗在地上回扫,三个妇女手叉腰,围圈扭动唱“十二月采花”。白色象征善良、纯洁,在其他民俗戏曲表意反派奸诈,如京剧中的曹操。
黑色为五行水性,棠溪魁山吴、双龙汪等家族演出的《陈州放粮》剧目清晰地体现这一特点。《陈州放粮》又为《陈州粜米记》,讲述包拯接宋仁宗御旨开关放粮之事。所佩包拯面具,除帽沿镶黄和上额绘有红色月亮,通体施黑色,以此表达人物形象的率真质朴、刚正不阿。
五行色彩理念的分类、渗透,就是将神的功能、等级、善恶逐一排序,强化“傩神”对“人”的引导,“人”对“傩神”的敬重,具有鲜明地指向性和象征意义。
(二)相生相克的色彩规律
中国古代色彩由于五行学说的浸入,形成相生相克的色彩原理体系。
所谓相生相克,即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色轮回周而复始,内在规律的运作体现五行色彩的变衍、派生。如相生即为木生火,为青交赤,交集为深紫色;火生土,为赤交黄,交集为橙色;土生金,为黄交白,交集为淡黄色;金生水,为白交黑,交集为灰色;水生木,为黑交青,交集为深青色。(图5)从色彩学上说,相克是叠色方法的表现,如金克木,为白与青,叠色为浅蓝色;木克土,为青与黄,叠色为绿色;土克水,为黄与黑,叠色为黑绿色;水克火,为黑与赤,叠色为深红色;火克金,为赤与白,叠色为粉色。(图6)
相生相克的理念既是色相的剥离与聚集,又是阐明事物普遍联系的哲学观念,反映五行学说对傩面具的视觉心理机制的内在作用。另外,贵池傩面具由于制作后期掺杂大量的当地土漆和桐油的使用,色彩纯度、明度降低,呈现出原始、率真的视觉意象和精神状态。

图5 五行相生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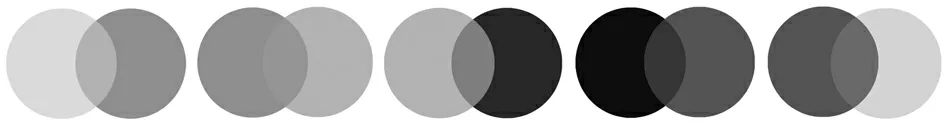
图6 五行相克色彩
另一方面,五行色彩亦是贵池乡民以傩的方式祭祀昭明太子金神属性。昭明太子即萧统(501-531),南梁萧衍之子,编撰过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明嘉靖《池州府志》记载,萧统食用过当地鲫鱼而恋其味,遂将池阳命为贵池。贵池为萧统封邑,外祖父丁道迁又为宣州太守,管辖贵池,加受九华山佛教熏染,自然说明贵池傩与萧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萧统被奉为贵池土主或“文案菩萨”、“文孝昭明帝”,乡民亦称“萧九郎”供奉堂屋案桌,成为官乡傩事祭祀的精神中心。
据《梁书》记载,萧统生于“齐中兴元年九月辛巳”,死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易学上,辛是金,辛巳、辛亥纳音皆是金,说明昭明太子的诞辰与忌日都与五行金有关。”[21](P161)贵池东南九华山脚下的荡里姚姓搬演的《打赤鸟》,一人戴黑色面具,头裹红布,持弓箭;一人戴白色面具,头裹红布,守持飞鸟。戴黑色面具的人向戴白色面具人手中的鸟作射击状。二人共舞四段,先打后又放走。白色为五行金色,和红布合为火克金。黑、红、白象征金生水克火,白为昭明金神,自然不敢冒犯,又为农事而要除害鸟,所以先打而后放;再者,《易经》所载“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暗示傩舞四段与昭明太子(九郎)的关联。相生相克的五行色彩规律对贵池傩面具的演义,亦是官民祭祀昭明太子金神的敬畏使然。
诚如上述,贵池傩面具对五色的吸纳,充分体现在造型以外利用色彩语言祭祀祈福、驱逐鬼魅的心理,充溢着宗教和礼仪文化,生活方式的伦理型、依附型与五色互为吸引、互为交融,成为“解读”贵池傩面具视觉色彩内涵的重要符码和关键因素。
四、文化与内涵
作为“傩文化”群体的典型,贵池傩详尽地、完整地反映诸多文化因素在面具中的交融,它适应巫觋的需要而不断拓展自身造型、色彩语汇,承载通神、请神、祭神的主要功能和美化面具的心理动机,成为乡民理解傩、进入傩的一种普及化方式。以造物设计眼光看,“设计文化是造物的文化,是人类用艺术的方式造物的文化。”[22](P113)傩面具包罗“艺术”的一切品格,以此处理宗族与族人之间复杂的文化抵牾心理,“它提出问题,运用叙事造成悬念和神秘,然后随着故事的发展再来解决悬念和神秘带来的问题”[23](P39),共同演绎人神共傩的交织状态。表面上看,面具是祈福禳灾的表征符号,是整个傩事活动最为显著的特征;而从深层的角度亦可觉察,面具不仅是征服乡民内在心理的主导机制,而且还是联结家族情感的精神纽带,维持族人之间互相认同、互相归属的“胶合剂”,诉诸贵池乡民对傩的文化认知。
一般说来,家族傩事的兴旺即是以宗教为媒介的渗透,且宗教与宗族本质上存在诸多交汇的地方。宗教利用宗族灌输祭祀傩神的思想,宗族利用宗教维护家族的内部繁衍。因而,傩面具是融化、凝聚本族以外血系的“融合剂”,是维系一个庞大家族或几个联姻家族稳定的文化信仰、审美旨趣。可见,傩面具的背后存在多重文化上的释义,充满鲜明的地方宗族文化内涵。
(一)维系宗族裙带的心理机制
贵池傩面具是宗教与宗族浑合的产物。它维系一个宗族的兴衰荣辱,关乎宗族子孙绵延的头等大事,乡民自然竭力构筑“神”的代表体系,织造超自然神力的用具。查阅家谱文献,贵池当地傩事活动较为频繁的宗族以外来迁徙者居多。如姚姓家族从山东迁至江西,再以江西迁入贵池;章姓家族从福建迁至泾县,再以泾县迁入贵池;而刘姓家族则是从相邻的江西直接迁入贵池。
由于宗族的迁移,致使迁居于此的人口减少,加上改造自然环境效率低下,无法取得当地的话语权和共享当地的物质财富,扩大人口再生产成为主要途径,祈求傩神护佑人丁兴旺成为必然。茅坦乡山湖村杜姓搬演的“献马杯”充分体现上述的心理机制。“献马杯”又名“舞踩马”,以碗盛红鸡蛋,摆在祭祀的社坛,石板放贡品三件,族人焚香叩拜;后由本族四童子扮“关索、鲍龙、鲍虎、鲍三娘”,身穿战袍,扎竹马,舞马交战;待事毕,再回宗祠或神堂踩“落圣马”,此时,族人上年有生育婴孩的人家逐续贡上红鸡蛋,供奉案头,执长者取红鸡蛋放于木盘,托给戴红色面具者;而后,戴红色面具者将鸡蛋从扎竹马的腹部绕过,再传给其他三个童子作同样动作;最后,放入长者木盘,供于祠堂。族中青年男女希望来年早生贵子,便可取之并向龙床中的面具作揖跪拜,四位踩马者共同还礼。礼毕归家食用,据传有得子添金功效。
这种具有儒家宗族意味的傩事活动,随着傩面具神化功能的感召,既增加族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又消解生活琐事的矛盾,使傩面具代言“神化族长”的身份,寄托乡民祈祷子孙满堂的朴素心理。换言之,乡民的需要决定傩面具的文化功能及内涵,它是维系一个家族长久不衰的精神纽带,负载联姻家族日常交往的关系裙带,使之成为乡民内心机制的心理标识和文化符码。
(二)造物设计文化的本质需要
傩面具的本质是造物文化的设计符号。它以傩的“神化”方式联结宗族群体的共同认知,具体的则反映面具的造型形象、色彩指向、文化含义以及约定成俗的观念。所以傩面具设计文化是由具象到抽象,由抽象再到具象的对流整合过程,它是乡民对造物设计的认知体验。
从造物方面来看,设计与傩面具存在互为影响的实质。傩面具再现设计的目的,设计表现傩面具所有的语素结构,影响当地的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析言之,设计借助傩面具体现制作工艺上的进步,傩面具需要设计为其“傩场”构建一个等级森严的图式,以便傩文化得到稳定、有效的传播。
诸如傩事中面具的摆放,按家族和演出剧目不同,傩面具有13枚、18枚、19枚,等等。数目虽不尽相同,但摆放形式却是严格按照傩神等级高低、功能大小设计的。以东山乡韩村的13枚面具为例:第一层摆有玉帝、圣帝、状元、文曲;第二层摆有武曲、土地;第三层摆有刘公、大娘、小娘;第四层摆有社公、土地母、回子、童子。(图7—图8)由于戏文的渗透,面具的角色可以互换,但摆式依旧要恪守祖制。如殷村姚姓中“皇帝”面具,在《刘文龙》中代表汉灵帝,在《陈州放粮》代表宋仁宗,在《孟姜女》中则代表秦始皇。因地位、功能等同,角色相互转换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乡民心理需求,体现傩面具设计的灵活性和前瞻性,避免了傩事活动中因面具过多而发生识别错误的现象,使其傩文化的内涵更加鲜明真实。

图7 山湖村傩面具摆设

图8 山湖村宗族傩事
综上所述,傩面具是人进入“傩场”驱灾纳福的主要工具,类似巫觋“借助酒精力量达到昏迷状态以与神界交往”[24](P39)。因此,艺术成为傩面具从功利性走向伦理性的特殊符码。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所写:“艺术不仅提供打开外部世界的锁钥,也提供打开心灵的锁钥。”[25](P437)艺术化的傩面具设计即是以艺术设计的手段,解读傩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宗族文化的双重解码机制,亦是人之尺度、文化之尺度在面具上的集中显现,凝聚乡民在漫长的造物岁月中对设计文化的体认和追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傩面具是傩文化的核心载体,它传承和保护了傩的发展,蕴含诸多乡傩田野文本的文化审美价值;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傩面具融合绘画、戏剧、舞蹈、音乐、仪式等多种元素,保留了大量、有效的宗教文化信息和原始造物理念,对于深入破解傩面具的设计文化符码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2]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一[M].(清)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十三·乡党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54.
[3][4]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六[M].(汉)高诱撰.吕氏春秋·卷第三·季春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 .
[5][6](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
[8]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的背后: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9]何根海编著.池州傩仪:人神到场的村落祭仪[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10]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1.
[11]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2]聂石樵:古代戏曲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14]李砚祖:装饰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5]李砚祖: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6]李莉婷编著:色彩构成[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5.
[17]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六[M].(汉)高诱撰.吕氏春秋·应同·卷第十三·有始览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
[18][19][20]顾颉刚,等:古史辨[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21]何根海编著.池州傩仪:人神到场的村落祭仪[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22]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23]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4][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M]. 北京:三联书店,2010.
[25][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M]. 林夕,李本正,范景中.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