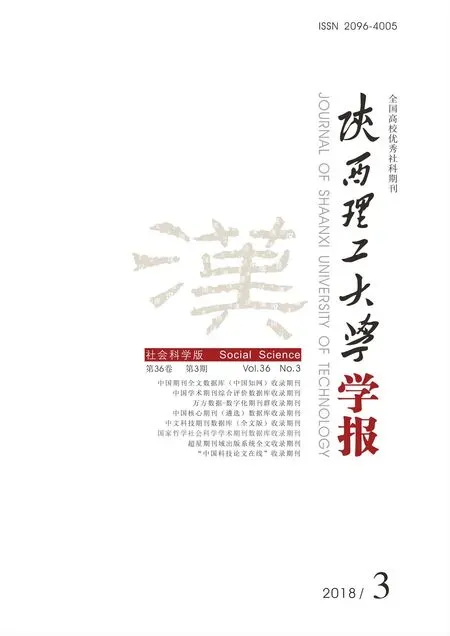晚清地方军事化中的节义塑造
——以汉江上游为例
赵 永 翔
(陕西理工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作为地方舆情载体的府县志书是官方政治理念下的史学书写,其中的人物志则是最能彰显地方风貌的史志篇章。事实上,方志人物形象受社会大背景影响而往往会具有鲜明的时段性特征,节义人物即是其中具备典型性的一类。明人王圻《节义考》,将节义人物分为忠臣、义徒、节妇等多种类型。由于“节义”是与“忠孝”同等重要的儒家伦德观念,故“忠孝、节义同为国典所褒,志乘所录”[1]卷五七,158,一直被视为地方风教之引领。在晚清汉江上游地方军事化①清中期之后,持续的战乱使官方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明显削弱,民间士绅及其领导的团练等军事力量成为地方秩序重要维护者的趋势加强。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据此以“地方军事化”概念指代这一历史状况,目前,已在国内史学界获得广泛认可。进程中,官员、绅民、烈女等不同类型的殉难人物,其个体身份作为潜在的教化资源,而被纳入地方秩序的重建中,其本然形象亦随之被进行了符合政教需求的完美化再造。
一、 彰国宪以慰“忠魂”:殉难的官员
汉江上游自嘉庆初就长期陷于地方军事化状态之中,是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彼时整体局势直接相关的。汉江上游地处秦岭南麓与巴山北麓之间的狭窄走廊之中,山谷阻绝,汉江深险,南北栈道绵亘千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清代乾隆朝以后,南方诸省人多地少的“狭乡”移民大量迁入,使该地五方杂处,民情复杂,各类社会问题巨繁难治,虽地处国家地理版图之中心,而仍成为腹地之边缘。自嘉庆初至同治末,该地先后因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西征、川滇农民起义的迭连冲击,以及匪盗等治安问题叠加,“湟池不靖,妖氛四起,汉中实当其冲,屡被锋镝”[2]序,1,社会秩序陷于混乱。这一屡治不靖之地遂成清代腹地治理的难题,清中叶以来的府县各志均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剧变。
清中叶以降,随着各类反清起义在汉江上游地区的广泛蔓延,代朝廷牧守,负有守土之责的州县官长,因抵御各方反清势力而殉难者甚多。尤其是同治二年(1863),各州县遭川滇反清义军冲击,文武官弁死事者甚多,最著名者莫如宁羌知州金玉麟、西乡知县巴彦善、南郑知县周蕃寿。金玉麟在“发逆窜扰”时,与同城文武分门守御,城陷,死于南门。事后陕西巡抚刘蓉在上清廷的奏折中称,金玉麟自牧守宁羌以来循声卓著,城破殒身报国之时志节凛然,“死后贼将其尸特为具棺以殓,且张伪檄于榇上,大书‘此系陕西好官’”[3]118。在刘蓉看来,金玉麟秉懿好德,即使人伦泯灭的“逆匪”亦对其表达了尊敬与褒赞。周蕃寿则在汉中城被团团围困,救援无望的情况下,先于衙署后穿凿一井,城破之日,尽驱妻妾子女投入井中,自具衣冠出堂,被刳肠决脰而死。而巴彦善在反清武装到达城下时,慷慨登陴,率吏民死守孤城,援绝力竭被执,大骂不屈而死。刘蓉认为三人既有临难不苟之心,则推其平日修己立身与居官行政亦必有异于俗吏之处,故奏请皇帝准采撰三人生平事迹而表彰之。此外,他还认为汉中自军兴以来,地方官撄城罹祸以归忠义之林者不可胜道,若能以合理的方式对其皎然志节进行表彰,不仅可表忠荩而励操节,亦且有俾于世教。清廷亦认为三人均志节凛然,堪悯恻,不仅允准将其载入府县志书,且令官方于府城建祠,接受民间祭祀。
但是相比于官方文献“我者”口吻的撰写,民间人士以“他者”眼光注视而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光绪年间,亲历咸同乱局的褒城县乡居士绅周炳垣,撰写了纪实诗文《纪乱词》,借此书披露了反清义军围攻汉中时的惨烈过程,展现了与官方文献记载截然不同的战时社情民意。该书记载当同治间川滇反清义军初起川东时,道府大员对即将而至的危机麻木不知,而义军由阳平关进攻汉中时,上下一片混乱。在此危急情形下,清廷命四川按察使毛震寿为陕西布政使,带勇急赴汉中防剿。毛氏初至汉中时,地方民众目之为救星,焚香跪迎,竭力奉养。然其驻扎月余,并不接仗,治军又不严,所属兵勇四处劫掠,民不堪其苦,甚至称之为“毛贼”。彼时义军已占据汉中北部门户洋县,对汉南各县构成直接威胁。地方民众在官方忠君保家口号鼓动下,倾尽所有,为毛震寿提供兵饷,然其兵勇食尽民粮,却不用命,惟知掘长壕限对方戎马,实际却发挥了自固而不能制人的反作用。此种消极策略导致佛坪、褒城依次失守,全局遂不可顾。更令乡民不解的是,毛氏所统蜀军竟半与“贼党”相识,每临阵,彼此相互招呼,其又勒饷不发,导致枵腹作战的兵勇哗溃成匪。地方官绅不得已与毛军约定战胜有赏,然其兵勇竟“嘱贼通融让阵”,官军在后假追以示为胜,“每一战胜,必向局绅索银数千,作犒赏之资”[4]785。
周炳垣《纪乱词》还记载蜀乱漫及汉中时,汉中道宪所请历办城守诸务的公绅、耆老、主事们,惟知侵渔粮饷。南郑知县周寿藩勾通劣绅,诬陷良绅,道府亦为所愚,于是,群小得志,权柄下逮,上宪形同木偶。迨至捻军大举围攻汉中城时,上下一片混乱,周寿藩退居城中,惟令枯守,每月消耗民间口粮无算,却“并未闻得一胜仗,灭一股贼,为民除害”。及至坐食山空,“官为倡议就民食,勇遂借端以搜民财,精华既竭,救援无望,遂四门放火,大肆掳掠而去”。周炳垣以“可怜万户千门盛,祗供周郎一火焚”来讽刺周寿藩的懦弱无能。汉中知府李定南则滥招数百乡勇而不知合理遣用,反因乡勇军粮追缴而屡屡勒捐民间,“其劝捐也,设万岁牌于二堂,日中令捐户跪之,汗流浃背,民不堪其虐”[4]784。周、李二员养勇三年,一战即溃,以纸上谈兵的低级应对能力致府城被攻陷,不但自己性命未保,数万百姓亦惨遭屠戮。按理而言他们是这一旷世惨剧的罪魁祸首,然在官修志书中他们竟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仗节死义的英雄官长。清廷居然也认为这些官员深知大义,实可嘉悯,除加恩照例咨部赐恤外,还令其载入祀典,岁时致祭,庶使地方绅民及守土之兵共知朝廷褒奖忠烈之至意,成为一时笑谈。
但实际上,官方此举自有其深层用意。在儒文化的纲常礼教体系中,节义为天地之栋梁,天常人纪赖兹弗坠,作为教化权力主导者的官员们,其形象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永作人臣之则的目的,以体现节义的引导性。尽管一些遇难官员或并不值得嘉悯,但出于维护官方权威,府县志书不惜罔顾事实,以符合朝廷教化旨意的政治语言,对殉难官员的形象予以完美化重塑,极力使他们以忠君庇民的形象得广泛宣扬,并缠绵固结于民心,成为其百世不泯,血食兹土的民意基础。地方军事化时期的社会失序,在治理层面上也直观地表现为,官方自身的科层性政治威慑力,及其在地方教化资源征调方面的能力显著下降。地方志对遇难各员的褒赞,并非是在封闭叙述空间中对公众情感与意见的真实呈现,但身处其间的民众耳目所闻自有公论。
二、 励风教以正人心:取义的绅民
励风教以正人心为施政之先,相比于平常时期志书人物传以扶弱济贫、修桥铺路等,作为传主生平主要功绩,战乱年代则独以取义成仁为首选。地方军事化对社会的深远影响,使志书人物渲染了义勇色彩,如宁羌州从乾隆十三年(1748)征讨大小金川,至嘉庆元年抗击“发逆”,以地近川界而被朝廷征发战场的县民实在众多,以致于光绪间该州纂乡土志时,对忠义人物进行了等次之分,“奋身杀贼至死不却者为上,慷慨捐躯以身报国者次之,随众赴斗转战而殁者又次之,至邂逅遇难求生不得,或为贼羁绊而死,虽或忠义之名,原无忠义之实,旧志一概收入,兹从略焉”[5]49。对节义人物分等而记的做法,固因忠义人物太多,更与官方借节义人物生前影响和贡献而鼓动民心有关。阖家几代聚居并在抗击“贼匪”过程中从军死战的义门之家,忠孝节义备于一家,尤属志书编者们所可书的乡里教化资源,汉江上游的府县各志收录了很多这样的义门之家。义门本指儒家伦德推崇的累世同居的大族,地方志为出自同一家族的人集中写传,具有将以孝亲为核心的宗族教化,和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教化结合起来的用意。
府县儒学知识精英们作为响应官方教化的民间代言者,是志书节义人物的主要撰写者。文人学士以其所撰述而承担劝忠孝、褒节义之职责,他们以精心构思的文辞鼓动人心,即使鄙薄顽懦之夫,亦不能不有所感奋而兴起抗争。在志书中,生员们一改往昔彬彬文质之象,践行杀身成仁,尽其道而死的道德职责,成为具有胆魄敢蹈白刃而不辞的义士。在地方官员看来,“士大夫宜砥名砺节,备千城腹心之用,及变起仓卒,毅然以气节相引重,庶足折乱萌而张国势”[6]卷四,乡曲诸生荷戈登陴,倡义为桑梓,战死为家国,乃国家养士之泽至矣的结果。这显然是将个人行为由保家而升至报国,由惨烈败死而美饰为养士之成功。
相对于少数记载翔实的节义人物,大多数人则只记姓名而缺乏细节,对他们的记述无论在语言修辞上,还是事迹描述上带有明显模式化痕迹。为了避免情节类同,志书的撰者还特别选辑了一些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生员死事。如嘉庆二年(1797),“楚贼入境”,窜至生员马呈瑞家,呈瑞为之讲忠孝节义,贼云“‘这人不合时’,遂攒刺之”。生员张瑄被执胁以降,不从,“贼问:‘尔是生员,必不怕考!’遂用柴火烤死”[2]594。选辑此类事件,一方面凸显匪盗之野蛮,以激起民间愤恨舆情,另一方面借殉难生员倡导知识阶层坚守儒家义利观,节义文章并重。
基层士绅群体作为清代地方军事化过程中,官方实施民间动员的主要依赖对象,他们以平素居乡所积的威望,而在民众抗击外来侵扰中扮演领导者角色,但事实上,他们本身也是节义人物的主要来源。频繁的战乱使民众喜节义而尚任侠,除了作为首领角色的士绅群体,普通乡民也以抗击匪盗的主体见诸志书。嘉庆白莲教起义与同治发捻起义都赖民团堵御,然民团在待遇上与正规军队不同,不独体现在他们同为战斗人员却享受不到对等的物质奖赏上,也体现在精神荣誉上。在带兵大员的奏报中,阵亡义勇寥寥无几,推原其故,总由地方官藉乡勇之力御敌,战胜则冒为己功,幕友亲丁皆得滥膺保荐,战败阵亡被害者,以其非在伍之兵,匿不呈报。清仁宗痛斥此类情况,云:“是乡勇人等,杀贼既不能叙功,徒死亦毫无赠恤,何以慰忠魂而励士气?岂不思乡勇皆朕之赤子,为国出力力战被戕,焉有父视子亡不加怜悯乎?”[7]29715要求嗣后各路乡勇有打仗阵亡者,俱一体议恤。湖北、陕西因而设立节义局,寻访阵亡殉难文武员弁及绅民妇女,以倡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
节义之士在平世似无所用,但变故之时却求而不得,原因是节义于世教本非小补,实乃救人心、振世风之急务,民意因此观感而兴起。在清代政治文化的顶层设计中,节义为天地之栋梁,天常人纪赖兹而弗坠。这种道德要求绅民以朝闻夕死,辞爵禄蹈白刃为忠义,而将其写入志乘则代表义烈人物于天地间百世不泯。尽管绅民们处在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之中,却有着具体不同的遇难情节。在地方志书中,他们成就节义的过程多样,有力战而死者,有骂贼被害而死者,有城陷自缢而死者,有仰药而死者等。这类情节多在嘉庆前后,值汉江上游陷入混乱之时,被裹入反清义军中的普通民众极多,强者操戈以从,弱者伏首就胁,鱼贯累累,官军一至则先试锋镝。这种情形使清军在所谓剿贼战争中陷入越剿越多的怪圈中,官方逐渐意识到:“岂尽民之无良歟?抑平日礼义不讲,激劝不行,以致昧昧焉从贼而死,官斯土者可不怵然心动乎!”[8]189他们迫切希望把裹挟其中,可以教化的普通民众从不可教化的匪盗中剥离出来,故特别重视忠义观念的宣扬,借议恤旌表风世励俗,使兵勇以临敌退避为羞,田夫樵竖以从贼苟活为耻,并痛斥那些愧世偷生流为匪者。
在嘉庆初至同治末的六十余年战乱期间,汉江上游各山区州县近山已无完村,既有社会秩序全面崩坏,大量无辜百姓枉丢性命。嘉庆以来的府县各志认为,汉江上游虽处僻隅,平日揖让雍容不及都邑人士,然嘉庆及咸同年间勤劳王事遇难不屈者却不乏其人,良由国家二百余年间,深仁厚绎涵濡化导至深且久之故,故弁兵、乡勇皆知临敌以退避为羞,即深山穷谷之中的田夫樵竖亦以从贼苟活为耻。然节义之载于志书者毕竟是其中少数,其中,不少具体细节还非撰写者所亲见,其事或访诸父老,或竟无所传闻,不免有挂漏之伤。乐安恶危、趋生而避死乃人之常情,然在清代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圣天子表章节义,赠官赐荫赐祠,德洋恩溥,万世无极,诸君子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其皆可以无憾哉”[2]序,1。朝廷对子民的元身份设计,使他们将忠孝节义的教化观念上升为自觉遵行的价值观念,并为此甘赴刀兵水火。从社会治理层面上讲,这不仅起到了对个体的社会归属和情感归宿的统领功用,而且还与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等伦德说教,共同构筑了社会秩序的民意基础。
三、 励贞节以昭潜德:守节的烈女
女性之中有高行足尚,淑范可传者,官府当按例为之请帑建坊表闾题额,以昭明潜德而砥砺世风。一般来说,其程序先由士绅采访事实,举报妇人节孝,开具事实,再由县、府加结转详,至省抚题准后,给银建坊。汉中府自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九年(1829),不断增加节义人物,续得节孝、贞烈妇女二百五十口。因间隔较短,未修新志,知府杨名飙刊刻旧志时将节孝名册附于编末,以备汇篡,同时,另印一册传布基层,俾乡里咸知观感。如此,村社妇女有贞心苦节而被湮没不彰者,可得续节旌扬,并有机会补刊府志,以垂不朽。
在晚清地方军事化过程中,很多随家人死于战乱的烈女节妇大量涌现,像同治二年兴安府徐氏家族为避匪乱,老幼男妇共计四十一人匿于石洞,“贼怒而架木草熏灼洞内人,于是无噍类焉”[9]65。修志者为照顾到尽可能大的社会面,有意促成大量普通民众进入义节传。但在志乘的篇幅限制下,却只能以寥寥简单言语对她们记载,以致传主缺乏个性描述,人物形象千人一面。此外,更有众多节烈之事只有结果而无过程,成就节烈的细节阙如。相比于大部分语焉不详的普通义烈人物,那些被收入艺文志得以表而题咏的士绅家庭节妇,却能占据较大篇幅而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节义志连接着家史和地方史,其撰写与刊刻实际上是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信息,是经过官方化改造后的公开宣扬。在官员和儒学先生们看来,节义志与祠祀圣母烈女同具风励郡俗之意。地方官皆知致治之要在于风化,移风易俗莫先于鼓励良善和旌表节义,然山村僻壤之地的贫寒耕织之人,纵有善行其乡邻嗟叹为可钦可叹,其姓氏却不传于城邑,如此以致幽光湮郁,潜德销沉者不可胜数。同样,旌表妇德亦是如此,“居下处卑,未尽旌厥闾里。采访非其人,则以爱憎为取,失实者多矣”[2]序,1。旌表节义为彰善大典,这一使教化用意大打折扣的非正常现象,其实很早就引起清廷的注意。早在雍正元年(1723),清廷即着各省学臣遍加采访,避免以富家巨族而滥为表扬,务求苦寒守节家的草野俊彦同霑恩泽,并对守节十五年以上的节妇给予旌表并赏银建坊。尽管朝廷表励贞节之典至优且渥,然地方多视为具文,或未曾建立,或草草应付。清世宗恐日久乃至泯没,不能使民间有所观感,饬令地方于公所设立祠宇,将忠孝节义之人俱标姓氏,设牌位置于祠中祭祀,用以表彰节义,阐幽光而垂永久。迨至同治二年(1863),清廷敕定新章,规定凡贞烈节孝许造具简明事实册,由学官移至州县后,径由督抚题旌,不许留难苛索。如光绪年间,定远厅志的纂修者以该厅苦节能贞者虽不乏人,然因前无志纪述,以致贞烈节孝湮没不彰,而就近今之可纪者近百人汇册上闻,成为千载一时之盛会。那些久被湮没而终被发掘的节义人物,其在志书中的形象经过再加工后,内化为官民共有的集体记忆。
持续的战乱以及由此衍生的后续兵匪扰乱,不惟破碎无数家庭,亦使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遭致毁坏,为地方社会带来灾难之深重,惨不堪闻。民众将亲人伤亡和财物损毁的现状,内化为由愤懑、焦虑、迷茫、绝望等复杂情感杂糅而成的悲情心理基调。官方在维风化正人心,恢复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注意修复民众的心理创伤。此种情景下,宣扬妇女潜德幽光与轶闻往事,就不单单是官方在社会集体心理诉求下,对带有悲壮色彩的节义当事家庭的精神抚慰,同时,也成为地方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重整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量的乡野节妇在志书中的状态,得以由“缺席”而转为“在场”。
传统妇德讲求德、容、言、功,而节义非属其中,大凡妇女不得已而以节义见于书者,其大多有遭遇某种不幸。妇人从夫,以从一而终习为故常之事,即有懿行也按例不必见诸纪录,惟有守贞保节为其特长。自宋儒程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既出,女子咸以改适为羞,以是为先儒立言之效。夫妇关系为五伦之始,朝廷旌门之典扶持妇女之节义亦可影响其家人与乡人,是以达到旌乎者此而劝乎者彼的目的,用意可谓深远。清廷对妇女们的道德期许,使她们面对社会危机乃至性命之忧时,持守贞节而不屈淫威,甘蹈白刃而不辞,以丈夫之行而自视为新妇德。在妇女群体脱离了原先的社会轨道和生活方式背景下,地方志书重塑她们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亟需,是与朝廷教化宣扬和道德规范的最终目的相契合的。
四、 结语
方志人物是官方对地方各类人物,以符合朝廷教化标准而严格遴选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方志节义人物传记作为官方政教宣传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以文字记载为方式的道德旌表,蕴含着扶树人伦端风化之意。晚清汉江上游的地方军事化进程尽管削弱了官府的权威,但并未造成无政府状态,官方仍然是地方事务的主导者,文化士绅们依然是官方支持下的舆论喉舌。在地方不靖的大背景下,官方深以为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则太平之基不固,故纂修人物志的士绅们将自身道德诉求与家国情怀和社会重建结合起来,并以此制造舆论,建构出官方与民间共同应对社会危机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相比于平常时期志书人物志以科举、职官、耆德作为主要篇章的书写对象,地方军事化时期的节义志更能反映特殊时期,官方主导下的悲情书写方式对民间意识形态的引领意愿。殉职的官员、取义的绅民、守节的烈女,虽因身份不同而在文字书写上被赋予不同笔触,但他们的形象同在国家教化理念下进行了再塑造,并通过信息传播、舆论制造、知识传承等方式发挥着民心抚慰的文教善后功用。
[参考文献]
[1]贺长龄,盛康.清经世文正续编[M].扬州:广陵书社,2011.
[2]郭鹏.嘉庆汉中府志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3]宋文富.重修宁羌州志校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4]陈显远,郭鹏.续修南郑县志校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5]宋文富.光绪宁羌州乡土志校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6]孙铭钟.沔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7]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刘德全,郭炎昌.光绪旬阳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9]李启良,李厚之.安康碑版钩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兼及志书、年鉴和史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