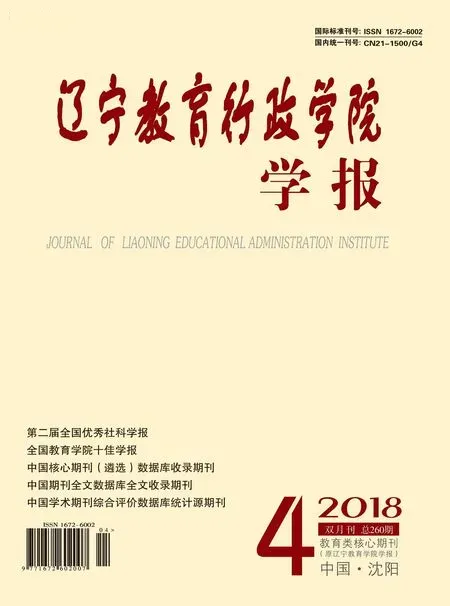儿童文学中“聪明的坏孩子”形象的叙事价值
——由《夏当当响当当》引发的思考
李盛涛,崔晓凤
1.滨州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0;
2.滨城区第八中学,山东 滨州 256600
自2014年始,济南出版社推出“方方蛋原创儿童文学馆”系列,将其定位为我国儿童文学新锐腾飞的一个平台。自成立以来,推出佳作若干,其中刘春玲的儿童小说《夏当当响当当》(以下简称《夏当当》)尤为独特,很能体现出某种“新锐性”。相对于其他虚构性的动物角色或神怪等超现实角色为艺术形象的原创作品而言,刘春玲从现实维度、以简洁明快而富含诗意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聪明的坏孩子”形象夏当当。刘春玲准确地把握了这一艺术形象与当代生活的价值关联,使这一形象体现出重要的叙事价值,而这一叙事价值主要体现在性格的复杂性、身份的当代性和教育价值的契合性三方面,值得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所借鉴。
一、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主人公夏当当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小说以小学校园为故事背景,通过夏当当和老师、同学们的矛盾作为主要故事,写出了主人公夏当当的一段成长历程。夏当当的性格是复杂的:他聪明自负、耍小聪明、有心机,还喜欢嫁祸于人;有时会犯糊涂,穿错鞋子,把自己反锁在学校厕所里;他好胜心强,曾自告奋勇抓班里的“小偷”;他具有叛逆性,故意跟老师捣蛋,还美其名曰“制裁老师”;他具有羞耻感,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又有很强的责任心,曾极力帮助在校园内游荡不上课的“三炮”张乐乐;他有奇思妙想,成功地教育了喜欢在厕所镜子上印口红的女生……在夏当当的复杂性格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就像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其实,这些性格特点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都是聪明孩子的小把戏。夏当当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复杂性可用“聪明的坏孩子”这一形象类型来概括。“聪明”指的是夏当当的学习接受力强,能言善辩,有心机,有奇思妙想;“坏”则是指他的各种自以为是的叛逆性表现。“聪明的坏孩子”这一类型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心理基础。“聪明”并不与智商直接相关,而是凝聚着家长、亲人对儿童的宠溺之情和儿童长期在宠溺环境下形成的自我认知。“坏”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内涵:情感色彩多来自口语的昵称,有喜爱、赞美等意;不具有道德范畴上的负面因素,只是在学校这一特殊环境中的个性表现,与学校的集体性要求发生冲突而已;“坏”甚至成为儿童自己所认可的一种与众不同、个性独立的身份标签。可见,“聪明的坏孩子”使夏当当与其他儿童形象区别开来,内在性地体现了他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
在夏当当复杂的性格当中,作者刘春玲注入了一种变量。当然,刘春玲并没有将这种变量具象化为一个明确的纵向变化过程,而是将好与坏的性格因素作为动态的变量共存于夏当当的性格当中。一次性的过错让夏当当有了悔过之意,但并不意味着他改正了这一缺点,他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夏当当一次次地犯错体现了对儿童教育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对儿童的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通过一次性教育一劳永逸地实现教育目的。这样也写出了夏当当的真实性格。夏当当有悔过之意,也有改过行为,但作为尚未形成认识能力和行为规范的儿童来说,有时夏当当的改过行为变得滑稽可笑,例如夏当当在一次度假中看到村支书建养老院、修路为百姓服务时,夏当当决定要为同学服务。于是,夏当当替卫生委员检查卫生,不让卫生委员检查;他替数学课代表交作业,不让数学课代表交作业;更可笑的是,他和体育委员一起喊操,一个说向右转,一个说向左转;同学们说他“管得太宽,像个太平洋警察”。这种描写既符合儿童身份,也获得了荒诞性的喜剧效果。这里,作者没有刻意拔高夏当当这一人物形象,而是写出了他的天真和可爱之处。同样,作者也写出了夏当当的无力感。当夏当当看到别班的学生“三炮”张乐乐整天游荡在校园内不上课时,决定走进“三炮”的内心世界,帮其重返课堂,然而却无能为力。最终,“三炮”在其爷爷的强制下重返课堂。这些描写,始终确保了夏当当形象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夏当当性格中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羞耻心和责任感。羞耻心使夏当当具有反思性和忏悔意识,例如在“老师有请”一节中,写夏当当嫁祸丁聪聪后被老师教训,遂有了“想找条地缝钻进去,从此再也不见李老师”的羞愧感。这种羞耻心正是他以后性格转变的心理动因。因羞耻心而来的忏悔之意使夏当当这一形象具有了性格的深度模式。而责任感的存在则使夏当当的性格意义指向具有了社会性和宏大性,例如当体育课上丢失铁环、同学丢失零钱时,夏当当挺身而出,虽然没有发现“真凶”,但也体现了他的责任心。当小说最后写夏当当通过奇妙的方法教育了爱往厕所镜子上印口红的女生时,意味着夏当当真正的成熟。羞耻心和责任感确保了夏当当性格变化的道德维度和社会性。
夏当当这类“聪明的坏孩子”形象与传统儿童文学形象有所不同。传统儿童文学形象并不追求性格的复杂性,反而具有纯净化特点,人物形象往往是道德或正义的化身,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道德性符码的人物形象决定了人物性格的纯净化,不可能复杂。而夏当当性格的复杂性恰恰表明它不是一个道德性符码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夏当当既不是英雄的化身,不具有改变历史的英雄般的史诗力量;也不是道德力量的化身,不能成为人类美好精神力量的标签。他只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有着日常生活的情感形式和生命形态,他身上体现着作者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尊重。当然,现有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有类似“聪明的坏孩子”形象,如日本作者臼井仪人的漫画《蜡笔小新》和同名动漫中的形象小新。在一定程度上说,小新可算作“聪明的坏孩子”,但夏当当不同于小新形象:如果说小新的“坏”多由主人公触犯道德的边界所构成,而夏当当的“坏”则由主人公叛逆行为对集体性规范的冲突所造成。正如有学者在论证儿童文学中主人公的“淘气”现象时说:“其共同特点就是不受羁约,有一种突破规约的冲动。正是这种聪明、机灵、智慧是淘气常显出可爱的特征。”[1](P73)小新五岁,没有正确的认知观念和明确的是非观,但他的这种懵懵懂懂的认知行为却无意中触犯了成人世界的道德边界,因而小新的“坏”有点“污”(当代网络用语)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内心纯洁,行动犯禁。这正是《蜡笔小新》的核心矛盾。但夏当当不同,夏当当作为小学生,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能力和是非观念,正是自我意识正在形成却未形成的时期。因而,夏当当认知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恰是作品的核心矛盾。因而夏当当不会像小新那样触犯道德边界,他只是不断地在自我调整和自我纠错,以便达到集体性的规范要求。所以,刘春玲笔下的“聪明的坏孩子”夏当当具有性格的独特性。
“聪明的坏孩子”这类文学形象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学功能。最突出的文学功能是带来了故事的戏剧性和矛盾的冲突性。从性格的构成因素来看,“聪明”的性格因素使主人公同其他人物形象区分开来,易造成个体与群体的对立;而“坏”的性格因素则使主人公同规范、纪律等对立而造成冲突。因而,“聪明的坏孩子”所带来的矛盾冲突,既有他和外在环境的有形冲突,也有他和外在规范的无形冲突。而且,好与坏的性格因素在“聪明的坏孩子”身上是个彼此消长的变量,这种性格本身的不确定性又带来人物形象与环境的关系变化。可以说,“聪明的坏孩子”形象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也是一个矛盾发生体,他的任何行为都能带动矛盾的发生。例如在“制裁老师”一节中,夏当当故意采取叛逆的方式制裁老师,却最终伤及自己,结果带来了同学、老师和妈妈的嘲讽,使自己陷入羞愧自责之中。所有这些矛盾,可以归结为主人公和学校这一集体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是特殊语境中的矛盾冲突,离开了学校环境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因而具有语境性和条件性,不具备普遍性。这种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以个体最终臣服于集体为结局,而是个体依然保持着鲜活的性格特征和生命意识。
除构成矛盾冲突外,“聪明的坏孩子”这一形象还有着喜剧性的美学功能。在很多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都存在一个由悲剧到喜剧转变的故事核心,因而具有一定的悲剧性因素,如格林的《灰姑娘》《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作品。这类作品中的儿童命运往往经历了一个从地狱到天堂的转变过程,实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社会进化论观念构成了同构性的互文关系。其实在夏当当的生命历程中并不明显存在一个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变过程,其生存环境也不像传统儿童文学那样存在一个神魔对立或阶级分野的社会环境,而是当代都市中的日常生活,没有你死我活的对立冲突,只有生活中的磕磕绊绊,这些小矛盾反而增加了生活的快乐和诗意。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代生活是喜剧性的,特别是在儿童的视野当中更是如此。于是,夏当当的喜剧性格和当代温馨和谐的日常生活便构成了某种同构性关系,强化着文本的喜剧性效果。
二、艺术形象的当代性
夏当当的身份定位不同于传统儿童文学。在传统和当下的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的身份定位往往建立在虚构维度之上,形成了诸多虚构性的超现实形象类别,诸如:动植物类形象,有猫(《黑猫警长》)、狮子(《狮子王》)、葫芦(《葫芦兄弟》)、羊(《喜洋洋与灰太狼》)、海绵(《海绵宝宝》)、熊(《熊出没》)等;神魔科幻类形象,如孙悟空(《西游记》)、铁臂阿童木(《铁臂阿童木》)、奥特曼(《奥特曼》)等;被神化的现实人物类型,如阿凡提(《阿凡提故事》)、一休(《聪明的一休》)等。这些儿童形象被高度抽象化、理想化,缺乏现实维度的艺术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儿童形象的文化品格带有斗争性,体现了正义与邪恶、美善与丑陋的冲突,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这种高度虚构和抽象的人物形象塑造与作者道德观念的先验性预设密不可分。而《夏当当》的人物形象身份设置却是现实维度的。首先从夏当当生活的环境看,既不是虚构的神魔世界,也不是瑰丽奇特的童话世界,而是当代都市中的校园生活场景。如果说传统儿童文学中的故事背景具有宏大性和仪式化特征,而《夏当当》中的故事环境则体现出世俗性和碎片化特征。在夏当当的生活中,没有灾难、死亡和阴暗,只有快乐、幸福和光明。主人公夏当当就像一粒种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发芽,茁壮成长。其次从夏当当的性格本身看,他的性格表现就是日常生活里的喜怒哀乐,都是些因生活小得失而产生的情绪波动。而传统儿童文学形象的性格本身具有某种精神性,往往体现了人类的某种精神力量。夏当当这类“聪明的坏孩子”使儿童艺术形象从传统的神坛之上跌落到世俗的生活微澜之中,因而也就获得了一种当代性和真实性,也获得不一样的典型性。
主人公夏当当身份的当代性与当代真实维度的生活环境描写密不可分。《夏当当》的故事背景以当代都市中的校园生活为背景,几个老师和一帮小孩子构成了小说的人物图谱,故事琐碎无序,风趣幽默。在刘春玲笔下,校园生活是喜剧性的。实质上,真实的生活并无喜剧与悲剧之分,只因有了作者观念的投入,才有了对生活不同的审美认识。小说《夏当当》中的生活形态绝非原生态的生活,而是经过了审美关照后的诗意生活。学校的大门、路边的银杏树、窗外的麻雀、梧桐树上的喜鹊、流浪的灰黑猫、能变成蝴蝶的柳蚕……这些生活中习见的事物在刘春玲笔下焕发出绚丽的色彩。如作品写到:
1.路边,高高的银杏树上,翠绿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还摇呀摇的;紫叶李站在灌木丛中,远远看去,深紫色的叶子就像开了一树紫色的花。树下草丛里有一些旋转的水龙头,水龙头像海龙王一样能喷水,喷出的水柱是一道道旋转的银线,不小心还洒下一些碎银。夏当当跑过去,抓了一把那些抛洒的碎银。线断了,银点儿落在手心里,手湿了。一些银点儿钻进夏当当胸膛里,夏当当觉得自己就像一颗被淋浴的小草,凉爽极了。
2.窗外,梧桐树椭圆形的大叶子和柿子树狭长的叶子在枝头招摇。梧桐树上站着一只喜鹊,穿得很讲究,黑色的礼服趁着白色的衬衣,颜色搭配得那么和谐。喜鹊往下俯视着夏当当,它好奇这个男孩子在办公室里做什么。可是,这只喜鹊没有耐心,没有深入探究的兴趣,长尾巴往下一按,又往上一翘,展开翅膀飞走了,留下夏当当一个人孤独地站着。
在上述描写中,作者运用了拟人手法描写事物,让习见的事物具有了陌生化的惊艳之感;并且在轻盈明快的叙述当中,颇有宋词造境达意的笔法。
这种诗意的语言不仅体现在描写当中,还体现在叙述当中,例如:
1.夏当当的英语成绩是这几天班里的笑谈。夏当当郁闷极了,忧郁就像掠过高空的云彩,遮住了夏当当的心。
2.日子像风一样从夏当当的童年里刮过,从同学们的童年里刮过,“偷”走仪器的是校长,还是夏当当——现在,谁也不在意了。
刘春玲的诗意叙述建立在明快、自然的基础之上,而非晦涩难懂,充分照顾到了儿童接受水平和阅读能力。
诗意的校园生活来自作者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审美外化。在生活中,作者刘春玲是一位工作在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师,多年的教学经历让她对儿童世界和学校生活有着丰富的积累和深切的体会,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审美感知和艺术表现,并源源不断地在她笔下极具灵感性地氤氲而出。在某种意义上,诗意的校园生活也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童话世界。原本枯燥的校园生活在刘春玲笔下变得妙趣横生,富含诗意。在小说中,种种矛盾和摩擦不再是社会罪恶和阶级冲突的表现,而是充满趣味和喜剧性。其实,快乐而充满诗意的校园生活也是当代社会生活的表征。悲剧性的故事情节注定与当代的主流观念和社会现象不符,也不符合当代都市儿童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在儿童眼中,生活总是瑰丽无比,充满浪漫色彩的。而刘春玲笔下充满喜剧性的生活碎片恰恰体现了当代生活的某种本质。
三、教育价值的当代契合性
任何儿童文学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教育价值。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是个被建构物,“童年是在儿童观、学校教育、印刷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种合力向前推动下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2](P20)正因为如此,儿童文学中势必被植入了很多教育内容。在《夏当当》中,“聪明的坏孩子”夏当当的教育价值的核心体现为一种生存智慧。从文化层面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体现为一种文化类型或精神力量。由于受现代性视野下的社会进化论观念和长期的斗争文化所影响,历史进程被阐释为文明和野蛮的斗争,从而在人类的精神中产生了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下、美丽与丑陋等对立性的精神质素。这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文学、艺术生产中出现了对这种精神图谱的同构性表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亦如此,于是许多儿童文学形象成为人类精神质素中伟大、崇高和美丽的精神性符码。这是传统儿童文学创作无法割舍的文学使命。但夏当当却不同,作者并没有在他身上安放一种宏大的精神质素,而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情感,况且“聪明的坏孩子”这类形象也根本无法承担这类宏大精神的叙事。而夏当当这种“聪明的坏孩子”所带有的教育价值集中体现为当代都市生存环境中所诉求的生存智慧。当代中国欣欣向荣,在儿童眼中更是温馨和谐,因此在社会层面既没有阶级分野、革命斗争所造成的动荡不安,也没有神魔对立、妖孽横行的混世乱景,有的只是在和谐环境中因认识、观念、性格、喜好、利益等因素产生的误会、摩擦与矛盾。因而,在丛林法则所构成的当代人际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你死我活的矛盾斗争,而是相互依存、趋利避害,需要的是一种生存智慧。而夏当当表现的就是这种生存智慧。当夏当当被反锁在学校厕所里时,是因为他不懂得有个暗锁;当他想抓住偷铁环的小偷时,是想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当他嘲笑别人时,是想表明自己的聪明;当他做好事时,是想更好地融入学校这个集体当中……所有这些背后都体现着一种生存智慧。在很大程度上讲,夏当当是知识型主体,而不是精神型主体;他身上并没有体现出一种精神力量,而是由知识、信息等因素汇聚而成的认识优越感。尼克·史蒂文森认为当代主体式各种话语的创造物,“现代主体性是压制和多种社会话语的各种破裂性效应的结果。”[3](P67~68)也就是说,当代主体不仅是各种话语的创造物,而且本身也保留了各种话语的矛盾和冲突。知识型主体使夏当当获得了一个貌似聪明的形象,但知识的博大也让夏当当不时品尝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奈。知识和主体的这种不确定关系也造成了夏当当性格的不确定性。他的自信和失落都是因为知识而引起,当他掌握知识时便获得了自信;当他没有掌握时,便失落羞愧。英语考试得零分带给他的羞愧便是明证。夏当当从一个自由、任性的生命个体转变为一个符合集体要求的生命个体时,势必有所牺牲和放弃。这也是生存智慧对于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悖论:生存智慧给人以日神精神能使人成熟和冷静,却夺走了人的酒神精神让生命不再丰满和强悍。当然,对于一个人生观、世界观尚未成型的儿童来说,对于规范的正确认识和遵从是必要的!
“聪明的坏孩子”夏当当形象的教育价值主要通过审美期待视野、成长主题和介入性叙述来实现的。
首先,夏当当这类“聪明的坏孩子”形象具有广阔的审美期待视野。如果人物形象具有广阔的审美期待视野,可以被不同的儿童群体所接受。对于“聪明的坏孩子”而言,好孩子能从这类形象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坏孩子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生活中的孩子往往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这类孩子更具有普遍性,因而他们更能从“聪明的坏孩子”身上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聪明的坏孩子身上体现了一种深层次的美学品格,“是儿童要求自由,表达了儿童追求自由的生命哲学。”[4](P41)所以“儿童之所以对顽童形象如此情有独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顽童身上,儿童可以逃脱成人规则的约束,获得主体的自由。儿童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自然能体味到顽童形象给他们带来的自由幸福的审美感受。”[4](P41)所以,“聪明的坏孩子”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能被广大儿童读者所接受。“聪明的坏孩子”与传统儿童形象的审美期待视野不同:如果说传统儿童形象以高大完美的艺术形象给人一种崇高的审美感,而“聪明的坏孩子”则以幽默风趣的喜剧风格给人以亲切感;如果说传统儿童形象震撼小读者的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聪明的坏孩子”主要产生一种价值的认同感。在“聪明的坏孩子”身上,存在一种价值的悖论,但这种悖论更能让儿童产生教育的认同感:你虽聪明但你有缺点,所以你要接受教育;你虽有缺点但你很聪明,所以你更要接受教育。这种悖论性的价值能让生活中的儿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促使他们向好的方面转化。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对自身缺乏准确的认识和定位,性格往往表现出摇摆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夏当当这类“聪明的坏孩子”形象给小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自我教育镜像。
其次,小说所体现出的成长主题也很好地促进了教育价值的实现。尽管小说的纵向故事线索不是很明显,但夏当当有着一个成长的生命历程,遂构成了一个成长主题模式,即夏当当从任性、自负和叛逆的“聪明的坏孩子”到一个知错就改、有责任心和敢于担当的“聪明的好孩子”的转变。在夏当当的成长历程中,老师、同学等他者形象构成了重要的教育因素。作品中,有爱冷嘲学生、批评不留情面却也光明磊落的柳老师,有认真负责的李老师,还有深入了解学生家境的唐老师等,他们在夏当当的成长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其他同学则对夏当当起到了镜像化的教育作用,如敢做敢当、勇于承担责任的姜金池,傻乎乎、有点死心眼的丁聪聪,成熟、善解人意的崔杰,爱推理、动脑筋的姚瑞瑞,在校园游荡不上课的“三炮”张乐乐……作者对这些儿童形象虽用笔不多,却也极具个性。他们作为正面的或反面的艺术形象影响了夏当当的成长。当然,这些他者影响因素不是通过单纯的说教来实现对夏当当的教育功能的,而是通过行动的道德力量施以影响。例如,在“铁环谜案”中,夏当当为了了解铁环失踪一事偷看柳老师的QQ聊天记录,发现里面全是空的,原来平时柳老师根本不闲聊;在“班里转来个小美女”中,写夏当当喜欢上了班里新来的女生崔杰,每天都从路边一户人家偷偷采摘一朵白玉兰给崔杰,后来夏当当才知道那户人家正是崔杰家,但崔杰并没有当众戳穿夏当当;在“春天里的一把火”中,写夏当当怂恿姜金池在滨海学院的操场上纵火,面对老师的调查和询问,姜金池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来表现的,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感化力量。他者形象的教育作用是外在性的,最终要通过夏当当的内在领悟才起作用。因而,夏当当的成长不是骤然转变的,而是渐变式的,体现了一种真实性。夏当当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实际构成了主体和环境的关系,而成长主题最大的叙事价值就是将个体成长和社会语境关联起来,体现了环境对主体的积极影响,从而也就肯定了环境的存在价值。
最后,作者为了突显教育性,有时往往通过介入叙述表现出来。所谓介入叙述,就是“在叙述中插入了很多评论,发出了许多附加的信息。”[5](P327)尽管介入叙述有时让读者反感,但刘春玲的介入叙述并不多,而是少而精辟。例如,当老师、同学们和夏当当对不上课的“三炮”张乐乐无能为力时,张乐乐的爷爷却用严厉的手段将张乐乐弄回教室,使张乐乐发生转变。小说写到:“夏当当心想:大家都喜欢好脾气的唐老师,害怕严厉的张乐乐爷爷,他们俩一个像温暖的春雨,一个像呼啸的寒风,可是呼啸的寒风没有摧折花朵,却唤醒了一朵未开放的花。”在“神探”一节中,当夏当当埋怨老师对班里的小偷保密时,夏当当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小说写到:“夏当当是个天才,天才就是聪明,听别人说话领悟得快。从此以后,夏当当犯错误,柳老师再严厉地训斥,他也没有忧郁过,只是认真改过,让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夏当当记住了:改正错误的孩子,照样是阳光、健康的孩子,应该抬着头长大。”这里,介入叙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叙述的关键节点很好地实现了教育功能。作者在进行介入叙述时,为了避免说教的生硬,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使语言既有美感,又有情感上的亲切感。
总之,小说《夏当当》通过“聪明的坏孩子”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对现实把握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独特的教育功能和接受群体,儿童文学创作往往刻意回避现实,从遥远的国度或虚构的世界中获得一种审美距离。但刘春玲的创作勇敢地近距离去描写儿童的生命形式和生活状态,并达到了一种典型性。作为新锐作品,尽管《夏当当》有不足之处,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对当代生活的准确把握和艺术提炼值得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所借鉴。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