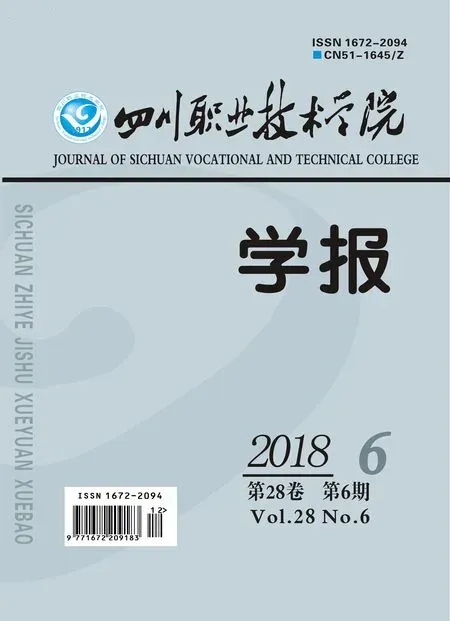《国语·周语》中礼制特点与说理艺术
王立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国语》是先秦史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个国家的历史,时间上起西周时期周穆王十二年征犬戎,下至战国周贞定王时期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约有五百多年。《国语》中八个国别的内容和风格各不相同,更像是是八个国家的史料汇编,学界普遍认为是战国初期左丘明所编而成。
周王朝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分封诸侯。随着各个诸侯国的建立发展、江河山川的阻隔,各个诸侯国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也逐渐凸现出来,正如《礼记·王制》所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所以《国语》有着显著的地域文化差异。在行文风格上,正如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中总评《国语》八“语”时所说:“《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在内容上,《齐语》《晋语》体现的是以法治理国家、以集权政治制霸诸侯的“法治”文化。《周语》《鲁语》主要体现的是以“礼”为中心的礼乐制度。礼制在先秦时期的体现就是将不成文的法律道德化,并将这种道德观念推及到广大诸侯以及平民之间,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在这种意识之下,人们按照礼制行事,符合礼的行为受到称赞褒奖,违反礼的行为则要受到批判甚至是讨伐。统治者便是以这种方式维护自身统治地位。
在《周语》中,记言说理的内容十分丰富,且体现的礼大致有四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特有的、普遍性的说理技巧。
一、温情脉脉的君臣关系
周王朝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维系,君臣多为同一个家族内的成员,君臣关系与后世比起来显得更温和、更有人情味。诸侯在天子面前是臣子,但是在自己的封地上又是君。赵伯雄在他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中提到:“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众多君主。”如此一来作为划分尊卑上下等级的礼乐制度显得格外重要。在君臣关系上,礼制规定了不同国情的封国与周天子的种种从属方式,以及君臣之间应有的权利义务。正是君臣之间有着血缘关系,这一部分中的辞令很多显得那样温情脉脉。
在《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中,穆王出师无名,祭公首先征引《周颂》:“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例举后稷与不窋的事迹,强调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使人民归化,而不是武力,此时的劝谏之辞显得温柔和缓。进而话锋一转,从管理封国的典章制度出发,“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认为在犬戎没有违反礼制的情况下攻击他们是不符合礼制的,况且犬戎“帅旧德而守终纯固”攻打犬戎只会失败。祭公的话可以看作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道德说教,显得很温和,后半部分则是以国家的礼制来劝谏,显得有强制意味。《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中内史过与祭公的话语结构相类似。内史过指出了晋惠公违背礼的做法,“夫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王也”,预测晋惠公“必无后”。然后阐述理由,他的话层层递进,先征引经典《夏书》《汤誓》《盘庚》,借经典之语从道德层面指出问题。接着内史过叙述了君臣百工的尊卑等级:“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纵其身乎。”顺接之前的道德说教,在礼制层面上更加深刻地分析了问题,深化自己说法的合理性。《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中,周襄王想要借助狄人的力量攻打郑国,富辰认为,与郑国的矛盾是兄弟之间的问题,如果请外人插手,只会从中渔利。富辰引用当时的俗语“兄弟谗阋、侮人百里”,以兄弟比喻周与郑,想说明周攻打郑相当于兄弟相残。“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富辰进而从兄弟之情讲到现实利益上,进一步阐述不可以狄伐郑的理由。郑国曾帮助过周,如果攻打郑国,则是忘恩负义并且会失去拥护,“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狄,不祥;以怨报德,不仁。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襄王拒杀卫成公》中,晋文公听信元咺的申辩,劝周襄王杀死卫成公,襄王拒绝。周襄王将君臣比喻成父子,“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显得有亲情味。他进一步阐明理由:“又为臣杀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君不可因臣而死,这又体现了君臣之间严格的尊卑等级关系,显得冷静而又残酷。《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体现臣对君紧密从属的礼制特点,即使是遇到危险也不能有怨恨之心。邵公为了救宣王而使自己儿子被杀,这固然有愚忠的成分在其中,但历史地看,他身处于那种礼乐制度所构建的社会环境之下,在思想中对君主的忠成为一种理所应当遵守的原则。这样来看,他的做法在当时又是积极进步的。
二、以德为兵的征伐原则
在礼制框架下的周王朝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德服天下。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诸侯违背礼的情况下才有名义发动战争,“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礼记·月令》)“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国语·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从礼的立场来看,战争的正义性是最重要的,符合礼便是正义的,不符合礼便是非正义的、得不到诸侯支持的。即便是杀人遍地、流血千里的战争,如果符合礼便会占领道德制高点,从而获得多方支持,最终到达到战胜甚至是不战而胜的效果。在这一类型的辞令之中,都是预测战争失败的内容,但是在说理上没有从敌我态势、兵法等方面论述,也并没有将战争的必然失败作为不可出兵的理由,而是全部以是否符合礼法道德来说理,劝谏之辞显得深刻有说服力。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中,祭公阐述了征伐的原则:“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穆王征犬戎师出无名,已经背离了用兵的原则,但违背礼制并不是祭公劝谏的主要原因,祭公阐述用兵的原则是劝谏的手段:如果这样做不但打不赢犬戎而且会破坏荒服制度,荒服制度的破坏则会造成周天子统治的动摇。与此相类似,《仓葛解阳民之围》也强调武力的威慑作用,故事叙述了晋文公攻打阳樊一事。仓葛劝谏晋文公说:“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武力起威慑的作用,但轻易炫耀武力、不重礼制教化,军队则会失去威慑力。
《王孙满观秦师》中王孙满看到秦军军纪不严明,“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说道:“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秦师无谪,是道废也。”先秦时期对出征之前的礼十分重视,出征前的校阅礼在于检查战备状况、鼓舞士气,所以出征前的礼显得格外重要,由此可见秦军背礼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战败的危险。王孙满不但看到了秦军不合礼的问题,而且看到了军纪涣散的隐患,而军纪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礼记·曲礼》),所以预测秦军必将遭受失败。
三、仁义礼智的个人修养
关于个人修养的礼在《周语》中体现得最多。这些篇目中的言谈辞令或劝谏、或预测可能发生的恶劣后果。在多数情况下,君主违背礼仅仅是导致不良后果的间接原因,然而劝谏或预测的辞令却都以违背礼制为由进行说理。
周天子的权力来源于上天,自己的品德要合于上天才能得到神的庇佑。尊敬天意和建立自身道德是统一的,顺应天意和遵循天道也是统一的,君主必须完善自身的道德,符合天道天意,才会实现其道德理想[2]。《内史过论神》中内史阐述了君主的个人品德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君主的个人品质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君主的品德高尚则可以将福祉惠及到人民,民神无怨,反之民神就会怨恨,神也会降祸。以《周语》的礼制观来看,是否有道德关乎到振兴一个国家,还关系到是否可以取得政权。在《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里,单襄公对儿子预测说晋周必将能继承晋国,因为他品行端正,“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中密康公之母劝其子不可接受三女,要献给天子,认为这不是康公所能承受得起的,“小丑备物,终将亡”,最终密被灭国。值得注意的是周灭掉密一定不是因为密康公接受了三女,而是康公的个人欲望无限膨胀,逾越了礼制,导致密的灭亡。其母劝其献出三女是因为看到了他欲望无限膨胀的倾向,想要遏制其逾越礼制的趋势。
《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与《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叙述了两个品质相反的君主,预测了两种相反的结局。晋惠公“夫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王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结果身死之后,子孙也被杀死。晋文公接待内史兴,一切安排都符合礼,“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果然晋文公在践土之盟后称霸。与这篇相联系,《仓葛解阳民之围》中被劝谏的晋文公接受了仓葛的建议,撤销了对阳樊的包围。臣子进谏而君主纳谏,这在《周语》中仅此一处。《仓葛解阳民之围》呈现了晋文公虚心纳谏的品质,这与他的称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康公论鲁大夫》一篇阐述节俭自律的重要性,刘康公认为季、孟“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二人的家族可以长久地存在于鲁国,而个人品质与二人相反的叔孙、东门则“若家不亡,身必不免”。与此篇中的事例相类似,《晋羊舌肸论单靖公》也是主要讲臣子的,羊舌肸认为单靖公言谈举止都符合礼,“夫宫室不崇,器无彤镂,俭也;身耸除洁,外内齐给,敬也;宴好享赐,不逾其上,让也;宾之礼事,放上而动,咨也。如是而加之以无私,重之以不淆,能避怨矣。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单靖公在席上特别喜欢以《昊天有成命》赋诗言志,羊舌肸从单靖公的言谈举止中看出单靖公完全符合诗中所体现的成就王命的美德,认为单靖公就算不能使周兴旺,也能长久地维持家族的兴旺。
与之相反的例子,在《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中,郤至想要凭借自己的战功超越排在自己前面的七个人,担任正卿之位。单襄公认为晋国的胜利是大势所趋,不是郤至一人的功劳,凭借一人之力与等级排在自己之前的七个人抗衡,将会很危险。况且郤至已经违反了礼,“叛战而擅舍郑君,贼也;弃毅行容,羞也;叛国即雠,佻也”,单襄公评论道:“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同样是反面事例,在《单襄公论晋将有乱》中,单襄公根据三郤的不同举止“其语犯”“其语迂”“其语伐”推测出三人无德,晋国即将有乱。这固然有牵强的成分在其中,单襄公当然不能从简单的举止中看出三人道德品质的全貌,而是根据三人不同的政治立场下的利益原则推测出来的。因此单襄公在分析三人的语言特色时,他所表达的正是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政治利益而考察三人的言语殊异,而他们的命运亦是在政治场合下的语言是否合于所处的环境而推测出的后果,实际上单襄公相当熟知政治环境中的语言形式,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什么时候说不该什么时候说[3]。但是单襄公却从仪态的角度进行说理,在被礼制浸润的文化氛围中,这样说理比直接指出问题显得更委婉也更有说服力。
四、顺德保民的治国方针
《周语》中多处有关治国之道以及君民关系的事例,无不体现了重民思想。农业社会中经济是国家的存亡的根本,国家治理得好坏关系到生死存亡,所以与温和的君臣之礼的说理比起来,关于治国之道的说理显得更加直接而严肃。前者的说理中把严肃的礼制内容以及现实问题放在最后,而将征引《诗》和《尚书》的内容放在前面,显得委婉和缓。而在这部分中,说理的言辞显得激烈,往往率先阐明立场,指出问题,然后从现实利益出发,阐述理由,最后才征引经典深化说理。例如《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叙述的是单穆公劝周景王不要铸大钱废止小钱的事。单穆公一开始便明确表示“不可”,认为废止小钱会让民众失去资材而造成匮乏的情况,从而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又征引经典,“《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诗》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济济。恺悌君子,干禄恺悌。’”最后明确表示景王违背《周礼》,“吾周官之于灾备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芮良夫论荣夷公好专利》中芮良夫劝说周厉王不要任用荣夷公,因为荣夷公好利,垄断国家资源不与国民分享,而这是很危险的。在说理时,芮良夫首先很直白地道出危险:“王室其将卑乎!”然后从现实层面上阐述了垄断资源的种种不利,“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最后引用《诗》,“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从道德层面劝说,深化说理的正确性。
农事也可以归于经济当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主要是虢公劝宣王举行籍田礼的辞令。虢文公也是首先直接表明态度“不可”,然后主要从两个方面劝说:一,农业是国家大事,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举行庄严隆重的籍田礼可以使人民更加辛勤劳作,“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二,只有及时翻种土地、进行农事活动才能不失农时,保证粮食充足,“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关于农业的典章制度就是为了最现实的问题:粮食。这篇当中的说理,前半部分将现实利益与典章制度相互结合进行陈述,中间陈述农祭礼,结尾又回到现实问题上:“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
与经济无关的事例有二,但因为同样是关于生死存亡的治国之事,所以劝谏的言辞与之前的事例一样激烈。《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中,灵王为了阻止谷水破坏王宫想要壅塞谷水,太子晋表示:“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劝他不要这么做,应顺时而动,行动应有所节制。而后又相继例举共工、大禹的事迹,陈述治国之道,得出“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鮌之败焉。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王而饰之,无乃不可乎”的结论。表面来看是阻止他阻塞水流的事情,实际上太子晋是以此为暗示,劝灵王看清目前事实,应率先解决王室内部的诸多问题。“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可见王室有乱的原因不在于壅谷水而在于多宠幸之人。太子晋劝谏不可壅谷水的言辞显得较为直接,但是其中暗示的现实问题委婉曲折,富有深意。《邵公谏厉王弭谤》中,周厉王残暴,杀死有谤议的人。邵公将比喻说理与直接说理结合,循循善诱,阐明不应阻塞人民谤议的理由。首先是比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最后直接说理,阐明防民之口是防不住的道理,“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五、灵活多变的说理技巧
《周语》中也有很多单纯地以合“礼”与否来进行说理的。这些事例中,单纯以“礼”表劝谏的有《谏宣王不可立戏》《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前文中仲山父认为废长立幼有两处不妥,一是不符合礼制,二是废长立幼的话鲁国不会遵从,如此则是触犯王命,如果遵从的话其余诸侯也会效仿,这样立长的制度就会被破坏。后文中单穆公以不合礼制为由阻止景王铸大钟,认为这样做只会徒劳无益,“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还有直接阐述礼制的。例如《襄王拒晋文公请隧》中晋文公请求死后用天子之礼,襄王拒绝,他认为关于显示尊卑差别的各种典章制度是自己统帅百官万民的前提基础,所以不能破例,如果晋文公想要以天子之礼下葬完全可以自己实施,但襄王绝不会冒着破坏礼制的危险赐予他这一权利。《定王论不用全烝》中,定王根据随会的疑问,阐述了宴会之上分享祭祀天地的祭品之礼。《伶州鸠论钟律》讲的是音乐的礼制,阐述钟律的重要性以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礼”不只在人物的对话中体现,直接阐述礼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周语》中的记言,多为政治性的言论,或进谏,或预测人事,或阐述典章制度,但是无论怎样都是围绕着“礼”展开的。说话者往往见微知著,从对象人物的细节中发现背礼之处,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并高度准确地预测到不良后果。同时《周语》中丰富的修辞也十分值得注意。修辞是对语言的修饰和整合,它讲究技巧和方法,是为了表达意思、互相交际服务的。有了语言,就必然要使用修辞技巧[4]。《周语》中的说理有理有据,常常各种技巧结合,它以“礼”为中心,以直接说理、比喻说理以及征引先贤事迹、经典、俗语等为辅助,展现出了高超的说理技巧。说话人根据特定情况采用合理的说理方式,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采取不同的语气,显示出那个时代高度成熟的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