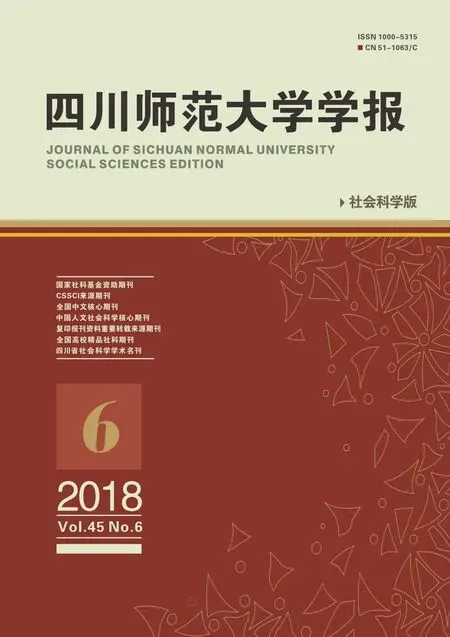论“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及其后果①
(东南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18)
回顾40年间的刑事司法改革,有相当部分制度呈现良性发展态势,刑事诉讼运作的诸多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也必须承认,《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及相关改革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部分改善停留在刑事司法改革目标的浅层;就深层而言,有些制度改善缓慢、有些停滞不前、甚至部分还有所恶化,改革成效外化为鲜明的非均衡性。那么,上述困境的症结究竟何在?笔者将尝试从“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的角度切入并展开相关分析。
一 概念厘定
所谓“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是指在刑事司法体制的整体刚性之下,由局部切入,通过一种科学、合理的甚至是“细枝末节”的技术设计来调适工作机制与改进工作方法,进而逐步解决刑事司法体制不足的问题。此种改革的措施往往呈现出技术性与细节性的特征,期待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注]宋远升《技术主义司法改革与法治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1-2页。。在中短期内,公安司法机关通过优化工作态度、改进工作方法与完善工作机制来提升刑事司法场域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公民权利保障的水平;从长远上看,通过小规模、持续性、技术性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体制与刑事诉讼价值的契合,从而产生刑事司法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二 核心特征
作为长期以来奉行的重要改革路径——“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表现出两大核心特征。
第一,“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并未根本触动中国刑事司法的目标追求[注]刑事诉讼的价值与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密关联的,目标是通过立法在价值中选定的优先顺序,比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同样是刑事诉讼的价值所在,但不同国家通过的立法却可能在两者之间设定不同的优先度。。
“刑事司法制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目标的优先性问题(setting priority)”[注]约书亚·德雷克斯、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一卷·刑事侦查),第4版,吴宏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首先,“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在认识论目的上强调发现客观真实,在价值层面上则倾向于控制犯罪而非保障人权”[注]左卫民《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以证据案卷为重心》,《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其次,由于对实体真实的强调,在公正与效率之间,中国的刑事司法倾向于选择公正而非效率;再次,在公正价值之内,对实体公正的价值强调优于对程序公正的强调;再次,同样在公正价值之内,在避免“错判无辜”与“错放有罪”的价值选择之间,中国刑事司法倾向于后者,缘于“中国的社会舆论除了在发生冤假错案或者严重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情况之外,一般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很少抱有同情的态度”[注]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最后,在效率价值之内,“权力效率”的追求优于“权利效率”。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效率的重视不足,或者说对于诉讼的经济性考量不足。此种观点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严格而言,我国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注重赋予公安司法机关高效行使权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型诉讼经济,即考虑节约国家权力运行的成本而提高权力行使的收益。与之相反,整个刑事诉讼中对于权利经济的关注却十分有限,缺乏从被告人角度充分思考成本收益的问题[注]关于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可参见: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第二,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并未根本触动中国刑事司法的诉讼构造。
在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中,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与诉讼构造是相互区别却又紧密关联的概念。价值选择影响刑事诉讼的目的,目的制约刑事诉讼的构造,构造决定控辩审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关系,关系与地位又决定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行为及其效力。从外部构造来看,在国家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国家本位特色。国家作为唯一的支配性力量,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相对于当事人一方极其显著的支配性地位,从而形成权力与权利悬殊的差序格局。从内部构造来看,我国刑事诉讼呈现出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构造,控辩审三机关依托书面材料按照强势的警察权、尴尬的检察权和弱势的审判权[注]陈兴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考察: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的权力差序格局相互分工、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具体而言,一方面,三机关在各自环节内享有完整的权力,在前一阶段提供书面材料的基础之上展开决策;另一方面,三机关尽管名义上相互配合打击犯罪,但对权力分配是以侦查为中心的。
由于“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未对刑事诉讼的目标与构造产生根本性冲击,这就使得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固化为一种“行政治罪模式”[注]陈瑞华《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以便于以发现实体真实、高效追诉犯罪为主要诉求点,强调秘密治罪、单方决策[注]左卫民《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研究——以证据案卷为重心》,《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和书面审查。在这个过程中,权利对权力以及权力之间制约被小心地控制在最低限度。
三 具体例证
针对刑事诉讼目标与构造固化所形塑的“行政治罪模式”,1996年和2012年在对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时,“司法化”成为一以贯之的理念。“司法化”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着力打破“秘密治罪”,扩大辩护人对审前程序的参与。
在1979年刑诉法中,辩护人只能在审判阶段介入(二十七条),与之相关的阅卷权、会见通信权也仅存于审判环节(二十九条)。换言之,整个审前程序被国家机关垄断,成为公权力对嫌疑人的“秘密治罪”。为此,在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均将辩护阶段前移,并持续强化辩护权利。具体而言,1996年刑诉法将辩护阶段前移至起诉阶段(三十三条),相应地,阅卷权、会见通讯权也一并前移(三十六条),同时还新增调查取证权(三十七条);此外,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有限地介入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帮助(九十六条)[注]但法律明确这一阶段律师的身份只是“法律帮助人”而非“辩护人”。。随后,在2012年刑诉法中又进一步优化辩护权,包括将辩护律师的辩护阶段前移至侦查阶段(三十三条);强化会见通信权,规定“凭三证即可会见”[注]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可以会见。,无需审批且不被监听(三十七条);强化阅卷权,规定审查起诉阶段即享有完整的阅卷权(三十八条)[注]1996年刑诉法第36条规定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权是受限制的,只涉及“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2012年刑诉法第38条则规定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所有的“案卷材料”。;强化调查取证权,新增辩护人向办案机关申请调取证据权(三十九条);新增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四十六条)等。
第二,大力推动“单方决策”向“双方决策”发展。
其核心目标在于打破单方权力构造的恣意性,保障处于弱势被告方的参与机会并对结果形成影响[注]左卫民《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在1979年刑诉法中,逮捕、侦查、起诉等环节的核心事项属于公安检察机关的单方决策,被告方缺乏法定途径影响上述权力的行使过程与结果。以审查逮捕为例,1979年刑诉法确立了纯粹的书面审查模式,检察官只需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做出决策,既不需讯问嫌疑人亦不需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此,2012年刑诉法新增第八十六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应讯问嫌疑人并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同样,1979年刑诉法规定侦查终结之后,侦查机关可以单方做出是否移送审查起诉的决策。对此,2012年刑诉法新增规定在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记录在案(一百五十九条)。类似的情形同样还体现在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程序的修订之中,1996年刑诉法新增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听取嫌疑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一百三十九条),2012年刑诉法则规定不仅要听取意见,还要“记录在案”(一百七十条)。
第三,持续强化证人出庭,提升庭审的对抗性,弱化对书面审的依赖。
面对长期以来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证人普遍不出庭,导致审判程序对抗性不足的弊端,两次刑诉法修订不断完善证人出庭制度,力图通过对证人庭审质证来增强庭审对抗性。1996年刑诉法先是确立了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四十九条),旨在免除证人出庭的后顾之忧。2012年刑诉法在进一步强化证人保护措施(六十二条)[注]增加在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特殊犯罪中,对证人及其亲属的特殊保护以及特殊的作证方式,比如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明确证人出庭补助制度的前提之下(六十三条),首次明确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一百八十七条)[注]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且也是首次立法明确了证人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出庭的训诫、拘留等惩戒措施(一百八十八条)。
总的来说,回顾改革开放之后40年有关刑事诉讼的司法改革,立法者期望通过法律修订,实现对诉讼程序的司法化改造,打破传统“行政治罪”模式所体现的秘密性、单方性与书面性的弊端,向着公开、双方与亲历的司法要素发展。然而,颇为遗憾的是,有相当部分的改革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公检法机关在各自分工的阶段之内对工作方法、工作理念和工程程序的技术化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刑事诉讼既有的目标与构造。具体来看,首先,刑事诉讼在目标上仍然围绕发现实体真实、追求实体公正和避免错放有罪展开。诉讼程序“司法化”改造中,对被告一方权利的打造仍然要在原有刑事诉讼目标的统摄之下。换言之,辩护权利的壮大仍然要服从于追究犯罪的需求,这也使得辩护权利貌似强大,但辩护律师在审前对刑事案件的介入仍然是较为有限的,几乎无法形成对公权力的实质限制。其次,刑事诉讼的构造仍然以单方决策为主。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讯问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更大程度上只是工作态度的转变,并不必然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仍然很难参与到公安司法机关的决策过程中。尤其在审前程序,中立司法机构几乎完全缺位,也就无法形成标准的诉讼三方构造。这就导致了刑事诉讼构造仍然表现为单方、不平衡的双方乃至弱三方的构造。公安司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之内对于涉及当事人根本权利的职权事项都具有单方的决策权[注]左卫民《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再次,刑事诉讼仍然高度依赖于书面材料。法院以公诉方移送的案卷笔录为基础展开法庭审理,而不是在法庭上通过直接接触各种证据的原始形式来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注]陈瑞华《新间接审理主义:“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中外法学》2016年第4期。。“法院对侦控机关提出的证据多采取形式化的审查方式,审查对象也基本上是侦控机关所‘制作’的案卷材料,法官对事实与证据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侦控机关对证据的‘处理’和‘加工’,故而很难摆脱侦控机关的‘信息控制’”[注]左卫民《审判如何成为中心:误区与正道》,《法学》2016年第6期。。由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形成于庭前和庭后的阅卷,那种通过推动证人出庭进而提升庭审抗辩强度的诸多改革收效甚微。
众所周知,对于刑事诉讼而言,主流的改革呼声是“权利保障”与“权力限制”相结合。从表面上看,40年间刑事立法文本中权利保障条款显著增加,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权利水平也有了一定改善。然而,正是因为“技术性刑事司法改革”的存在,与权利运作息息相关的深层次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改变。这使得整个刑事司法改革中,权利保障的内容常常流于形式,而权力保障的内容则立竿见影。这不仅可能影响到改革的实际成效,也大大增加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因此,下一阶段改革应在技术性优化的同时,推动深层结构的变革,避免将改革拖入纯技术化的“表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