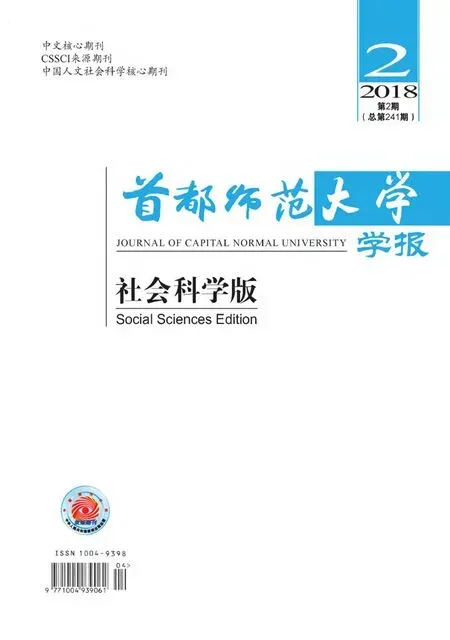叙事视点的异同与互鉴
——对中国现代话剧与电影关系的一种重新考察
计 敏
1980年代初,我国电影界曾经掀起一场关于“电影与戏剧离婚”的论争,有相当多的学者立足于电影的美学特征,对中国电影长期桎梏于戏剧的传统提出一系列的批评,并将“非戏剧化”看作电影本体意识觉醒的标志。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求新求变的冲动掩盖了某些逻辑概念上的含混。这场讨论虽在实践方面推动了中国电影语言的探索更新,却在观念理论领域留下了一定的隐患,或多或少阻塞了电影与戏剧进一步相互对话和借鉴的道路。
本文旨在对中国戏剧与电影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和解读,研究并非侧重于电影接受戏剧的影响,也不是从本体论角度阐释两者的异同,重复前人已大量论述过的话题,而是将论域集中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戏剧(主要是话剧)与电影的关系上,作一番动态的历史性考察。众所周知,在这50多年里,中国现代话剧与电影两种源于西方的不同艺术类型,从引进、发展到走向成熟,都与五四新文艺运动同步。相同的时代语境、文化生态,使得它们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始终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在许多方面互相影响。其中,艺术形式的自觉,叙事方式的变化,同样是现代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因为形式规律及其更新,恰恰是艺术发展过程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叙事形式的突破与创新,也是一个时代观念体系变化的风向标之一。
叙事学作为196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艺术理论,与传统研究方法最大的区别是,不再局限于对作品的题材、内容及其社会意义等外部方面的解读,即“不关心讲什么故事,而关注是什么元素使故事构成”*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叙述角度、叙述结构等如何确定和安排,往往决定了艺术形式、风格的基调。以叙事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话剧与电影的互动关系,会开启一种崭新的视角。
比如,中国早期电影在写实型话剧的影响下,几乎都是采用单一的、客观全知型的视角,这也是和其戏剧性的结构相适应的。所以,当电影编导们逐渐摆脱了“影戏”美学观念之后,利用画面和声音创造多重叙述视点,也就是题中之义了;反过来,这些电影手法又影响了戏剧的叙事角度,话剧舞台上不断出现的多视角交叉的形式,就是这一借鉴的结果。当然,舞台叙事的新技巧又反馈到电影,尤其到了40年代,无论戏剧还是电影,均出现了叙述视点自由转换的方法,标志着它们都已摆脱了早期艺术上比较幼稚,表现手法相对单一的阶段。正是这一系列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了两种艺术的共同发展和成熟。
本文将借助叙事学的方法,通过实例文本的分析,集中在叙述视点问题上,对戏剧与电影的相互关系进行再解读。
一、电影:戏剧影响下的叙事角度及其变化
亚里士多德曾给悲剧下过一个重要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这一理论对西方戏剧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强调“行动的摹仿”,西方传统戏剧没有“显在”的叙事者,作者严格遵循“潜在”的叙事原则,尽力隐蔽叙述行为,让戏剧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行动,演绎情节;而剧作的思想倾向则在酷似生活的场面和细节中自然地流露。简言之,故事是由演员表演出来,而非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写实型的“幻觉主义舞台”原则就是这种叙事角度的完美体现,意在造成高度客观、真实的视听综合效果。这种方法和中国戏曲惯用的“显在”叙事不同,因为戏曲舞台上根本不存在保持生活幻觉的“第四堵墙”*所谓“第四堵墙”即假定镜框式的台口有一堵透明的“墙”,把舞台与观众分割成两个互不干扰的空间,演员被封闭在舞台的小世界里,观众则透过“第四堵墙”窥视这个小世界。“幻觉”的产生主要依靠逼真写实的表演、布景、灯光等,以引起观众审美心理上的 “移情”作用。,经常出现自报家门、背躬、插科打诨等暴露叙述行为的做法,并不恪守单一的客观视角;也有别于布莱希特倡导的“叙事体”戏剧,因为他故意要打破“第四堵墙”,让叙事者出场的目的在于破坏“幻觉”,引导观众进行理性的思考。
五四以后的中国话剧对传统戏曲采取了批判和决裂的态度,形式上也全盘模仿西方写实主义戏剧。因此,幻觉式舞台的写实性叙事开始占据主流地位,适应这种舞台形式的剧作,如《雷雨》(1934年)采取的就是西方经典的写实主义叙事模式。作者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地进行“潜在”叙事,整个故事完全通过剧中八个人物的行动、语言铺陈开来,造成如体验现实生活一般的幻觉效果,“使观众似乎感到自己的确坐在实际生活中发生这些事件的现场并听着和看着这一切”*[英]J.L.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一)》,周诚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的确,从以人物的行动演绎故事的特点来看,戏剧理所当然是电影最接近、最值得学习的艺术。因此,20世纪初期的中国电影无疑是以戏剧化观念为主导的。所谓“影戏”,就是将电影看作银幕上的戏剧,自然地形成戏剧化电影大潮。导演程步高曾如此描述初创时期在亚细亚影戏公司拍片的情况:“一个远景,拍一段戏。一段戏拍完,开麦拉搬个地位,再来一个远景。”*程步高:《影坛忆旧》,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整个拍摄就像舞台演出的影像记录,类似梅里爱时代呆板的“舞台剧影片”,而摄像机始终固定在一个地方,宛如观众在看“戏”,只不过是通过银幕这个媒介。
如果说中国早期电影只是简单地套用戏剧的特性,那么随着写实主义模式在话剧中的确立与成熟,这种客观、写实的叙事方法对电影产业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电影叙事基本仿效传统戏剧的“锁闭式”或“开放式”,一律采用客观视角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叙述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宰了影片创作。情节高于性格这一戏剧最早的原则,也造成了电影“情节至上”的倾向,观众完全被外部情节所吸引。
如舞台剧导演出身的应云卫,在执导影片《桃李劫》(1934年)时就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戏剧的叙述视点。影片虽是大倒叙结构,以校长探望狱中的学生,学生讲述毕业后的一系列遭遇作为开头和结尾,但主体部分还是以情节的因果关系作为叙述动力,层层递进:从男女主人公毕业后踏入社会开始,历经结婚——男主人公两次失业——沦落为苦力——为救产后生病的妻子而偷盗——妻子死去——孩子被送入育婴堂,直到男主人公因失手打死警察被捕入狱而终结。影片似乎是从主角的回忆开始的,却并非采取他的个人视点,做主观的叙述,而仍然采取写实戏剧惯用的客观视角,不动声色地进行“潜在”叙述,顺着情节的推进一步步导向高潮。该片所采取的戏剧化叙事视点,有利于客观真实地再现(摹仿)生活,从而引发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强烈关注与情感共鸣,对银幕上的 “幻觉真实”产生心理认同;但另一方面,拘泥于外部情节的客观叙述,却在挖掘主人公内心活动与主观感受方面受到局限,这是不利于发挥电影的叙事特长的。
30年代曾取得票房佳绩,由马徐维邦拍摄的国内第一部恐怖电影《夜半歌声》(1937年),也完全遵循了戏剧化叙事的原则。虽然影片在镜语组织上有独到之处,出人意料的拍摄机位和镜头运动,辅之以特殊的用光、夸张乃至变形的造型,成功地营造了神秘、恐怖的氛围,但其叙事的视点还是无主体介入的客观展现,甚至在主人公宋丹萍对人诉说自己10年前惨遭残害的一段长达30分钟的回忆中,也见不到个人情感浓烈、交织着恐惧和仇恨的主观镜头。
其中,宋丹萍与恋人李晓霞相会被李父抓住,李父动用私刑逼迫其和晓霞分手这场戏,全是通过旁人晓霞、继母、恶霸汤俊的表情和对话,来展现宋丹萍的痛苦,并未将镜头转向宋的视点,表现他的心理意识;又如夜戏散场后,汤俊指使流氓往宋丹萍脸上泼硫酸这一情节,影片也只是以一个远景,通过同伴惊呼:“硝镪水!”来提示事件的发生,一场混战的群众场面(一方要抓凶手,另一方为其开脱)遮蔽了宋丹萍抑或其他在场人的主观视点。这一叙述视点上的“去个人化”,无疑脱胎于舞台叙事。因为在舞台上类似毁容的情节很难直接呈现,只能将受伤者包围起来,通过众人的语言、行动,引导观众想象所发生的事情。最突出的例子是宋丹萍脸部伤愈拆绷带的场面。观众首先从周围人的惊恐表情里猜测到被撕去纱布的宋丹萍毁容之可怕,待到宋自己在镜子中看见了一张狰狞的面孔时,似乎出现了“我者”的角度,但这个镜像还是为了向观众交代“事实”,而非真正表现他的内心。影片随即通过宋丹萍一系列激烈的外部动作——推翻烛台、打碎花瓶、撕扯桌布等来表现其痛苦,遵循的还是舞台剧的原则,由演员“表演”故事给观众看,而不是个人视点的讲述。也正因如此,该片无需多加改编,便被直接搬上了舞台。*1941年,马徐维邦曾受国联剧团之邀,将其成名作《夜半歌声》搬上舞台;此外,傅梅也曾将影片《夜半歌声》改编成符合“三一律”的话剧《凯歌》,并由文江图书公司于1946年3月出版单行本。
然而,通过镜头来叙事的电影,在叙述视点上理应比由舞台场面构成的戏剧更加多样和复杂。电影可以像戏剧那样,“叙事者努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自身的活动上引开,掩盖并移置这种活动”*[美]尼克·布朗:《本文中的观众:〈关山飞渡〉的修辞法》,戈铧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3期。,甚至可以比戏剧更进一步,“直接利用摄影机作为一个‘窗口’或第二双眼睛,观众借此观察现实——它(影片,引者注)把摄影机抓得牢牢的,只允许‘记录’正在发生的事”*[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做到类似纪录片一般的真实。二次大战后兴起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差不多同时期的中国影片《万家灯火》(1948年)《乌鸦与麻雀》(1949年)等,便突出呈现了这种纪实美学的风格。这些影片的景别以平朴的中、全景为主,追求场景、细节的真实,极少用特写、闪回等渲染情绪的主观镜头。《万家灯火》中大量的长镜头,以及令人难忘的饭桌上的两场戏,不仅保持了空间的完整性,更以一种“生活流”的手法,生动地表现了未死方生年代里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这种淡化情节而强调细节的叙事,使影片具有了某种生活的原质感——战后“年头不对”的混乱局面、物价飞涨的荒诞、小职员失业的痛苦、美满家庭的行将崩溃等等,弥漫着深深的焦虑,这些客观叙事段落的逼真性与感染力是超过写实型戏剧的。
但另一方面,电影毕竟是以连续性的画面与音响组接构成的艺术,这又使它与通过演员表演故事的戏剧相比,在叙事上更加自由灵动,不同的镜语组合可以建构一部影片独特的叙事视点。电影不仅有戏剧那样的外视点(潜在)叙述,即从一个客观的视点进行全知型、全方位的叙事,还可以有并不隐藏视点的第一人称叙事。戏剧舞台上囿于真人表演,观众看到的永远是“他者”,视点被固定于单一、客观的角度上,而电影叙事既能从“他者”出发,又可模仿“我者”的视点。
如吴永刚导演的影片《浪淘沙》(1936年)就突破了客观全知的外部视角,多次出现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主观视点。当主人公阿龙杀人后茫然地在街上踯躅时,耳边不断出现“阿龙杀人了,阿龙杀人了!”一声紧似一声的喊声,这画外音其实只是阿龙紧张恐惧心理的外化。接着镜头切到坐在海边的阿龙,从他的视点看出去,自己的身体仿佛已被眼前垂下的一张巨大渔网网住了,动弹不得,这一主观镜头很好地表现了阿龙此时惶恐、无助的心态。
费穆执导的《春闺断梦》是联华公司1937年出品的短片集锦《联华交响曲》中的一部,该片叙述了两名同床女人所做的三个噩梦。全片利用主观镜头,如大面积若隐若现的阴影、夸张扭曲的构图,以及被嵌入变形画面中的怪异的恶魔,来呈现“梦魇”,渲染一种压抑、逼仄、扑朔迷离、恐惧肃杀的气氛,而这一杂乱无序的梦的流动,却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另外,贺孟斧在联华执导的《话剧团》*贺孟斧导演的 《话剧团》为1937 年联华公司出品的三段式集锦片 《艺海风光》之一,其余两部为朱石麟导演的《电影城》以及司徒慧敏导演的《歌舞班》。(1937年)也突破了“情节至上”和客观叙述的戏剧原则,将人物的心理幻觉作为表现对象,通过剧作家韦杰的主观视点,表现其压抑的内心,实则映照了现实环境的黑暗。这些影片与当时话剧的叙述角度和方法可谓大相径庭。
二、戏剧:从单一视角到多重视角
早期电影受戏剧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现象,戏剧化电影的观念无疑最具代表性。然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相对稳定的叙事体系。中国电影在那个时期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原先完全模仿戏剧叙事的状况而趋于多样化。反过来,电影叙事角度的丰富多样性,又挑战了戏剧的单一性,也对戏剧产生了反哺作用。一些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主观叙事视角引入戏剧中来,打破了写实戏剧纯粹的客观叙述角度,在不断克服原有局限的过程中,发掘出戏剧的艺术表现潜能。
徐訏的四幕剧《军事利器》(1939年)*《徐訏文集·第16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48页。,在人物表中就列出“作者与一个不知国籍的老婆婆,以及一个比利时的中年人”等,表明叙述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在作者与几个旅客的谈话中展开的。但这种剧作实验尚未得到舞台演出效果的证明。而田汉编剧、南国社1929年1月在南京公演的独幕话剧《颤栗》可以说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变体。该剧故事从“子”的主观视角出发,讲述了他由于在家庭中未得到应有的地位,从愤而弑母,到知晓自己的私生子身份,转而理解、同情母亲,直至最后决然离家追求自由的过程。剧中主要人物共四个,分别是子、长子、母亲、警长。虽然该剧不像《军事利器》那样直接出现“作者”(其实还是扮演者)的叙述,但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剧中的“子”替换成“我”,只不过这种第一人称叙述是隐含的。幕启时,“子”就忿忿不平地诉说着自己痛苦屈辱的人生:
她为什么不在刚怀我的时候就把我堕下来呢?一个人生下来就得受人家羞辱,受人家耻笑,他不能得他应得的权利,不能受他想受的教育,别人在太阳底下堂堂皇皇的走着笑着,他却像一颗长在那不见太阳的墙脚下的野草似的,憔悴的活着。啊!这样的生活不比死还痛苦吗?*《田汉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45-59页。以下《颤栗》中的引文均出自此,不再一一标注。
以“子”的主观视角进行第一人称的叙事,使观众对“子”产生认同。接着,继续由“子”当众讲述童年时代所受的折磨。因为想读书,偷了家里的银蜡台换书,被母亲发现后拷问了一天一夜,昏死过去,醒来后除了“贼”的绰号外,还被污名化为神经病。这就是“子”自述弑母的理由,但是当他真正动手时,观众听到了他极为矛盾的内心独白:“啊,我真正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来了,犯出这样的大罪来了……娘啊……这也怪不得我啊。”然而杀母并未成功,他终于从母亲口中知晓自己是母亲冲破专制淫威,与婚外情人的爱情结晶,在母亲的拼死保护下,逃过了父亲的多次仇杀。于是,“子”边坦露心声,边侧面透露“长子”为争夺财产不顾手足之情,置兄弟于死地的实情,剧情由此反转:
我第一次看见那遗嘱上没有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真是何等的失望,何等的羞愤,可是我现在倒觉得很可感谢了,感谢我没有资格得那遗产,我才不像哥哥们一样……财产是那么一种罪恶的东西,又多么能使人犯罪啊!有资格得到遗产的哥哥们,不是有三个吗?到现在为什么只剩了二哥一个呢?大哥怎么死的,三哥怎么入狱的,我虽然是神经病,可是也知道得很清楚,感谢我没有资格分到爸爸那样巨大的遗产,感谢我是神经病,要不然我恐怕连生命也早没有了。生命!啊!生命!可以破坏一切的生命!可以建设一切的生命!无论生命是怎么来的,让它是善美的果子也好,罪恶的结晶也好,它的本身总是可赞美的!可宝贵的!
这番话并非对着剧中其他人物,而是直接对着观众诉说的。该剧借助“子”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实现了在现时情节、“子”的心理状态述说与“母”插入叙事三个层面之间的切换,不仅扩大了独幕剧的容量,而且为观众提供了思辨的空间。因此,剧中“子”的直抒胸臆,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尤其是接近剧终时的一段独白,更是将剧情推向了高潮:
无论我是娘同谁生的,我总是感谢娘给了我的生命!而且我知道我不是那样专制、那样淫恶的爸爸的儿子,我是多么荣幸啊!在那样专制,那样淫恶的威权之下,母亲居然有那种勇气,自由地、大胆地和别的生命结合,娘,你也是多么伟大啊!
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焦点已经由外部情节转移到内心世界,特别适宜主观情绪的抒发。一段段内心独白仿佛是主人公凌乱而跳跃思维的组接,其间对生命、爱情的礼赞,对自由、光明的追寻,又极其契合五四精神,所以演出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据田汉描述,南京“中大”的学生看过演出后,也在日常生活中“神经病”似地念起了剧中的台词。*《〈田汉戏曲集〉第五集自序》,《田汉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页。这与该剧第一人称视角的选择是不可分的,而这一类似小说常用的叙事角度在电影中早就出现了。
在民国的舞台上,以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叙事的话剧毕竟还不多见,更多的是在外视点客观叙述的整体框架中,嵌入部分的内视点叙述,主观叙述还是被封闭在“第四堵墙”内。如田汉《获虎之夜》(1922年)的主调是现实主义的,整出剧表面看来完全是外视点叙述:山区富裕猎户魏福生的女儿莲姑与表哥黄大傻自幼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是随着黄家破落,大傻也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看重门第的魏福生准备把女儿嫁到城里的“高门大户”。幕启时,众人在魏家客堂里围着火炉谈笑风生,魏福生早已在山上布置妥抬枪,期盼今夜能捕获一只大虎,好给女儿莲姑置办嫁妆。观众透过“第四堵墙”看着并听着这一切。很快,幕后山中抬枪一响,被抬上来的“虎”却是身受重伤的黄大傻,莲姑请求留在他的身边照料,也不被允许。随着剧情走向高潮,叙事也渐渐由外视点转为第一人称的内视点,奄奄一息的黄大傻以抒情诗般的语言,诉说着自己的凄凉与寂寞:
一个没有爹妈、没有兄弟、没有亲戚朋友的小孩子,白天里还不怎样,到了晚上独自一个人睡在庙前的戏台底下,真是凄凉得可怕呀!烧起火来,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唱歌,哭,只听得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我才晓得世间上顶可怕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鬼,是寂寞!*《田汉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241页。以下《获虎之夜》中的引文均出自此,不再一一标注。
黄大傻讲述了自己每晚上后山深情遥望莲姑窗口的灯光,回忆小时候与莲姑一起玩耍的情景,直至莲姑熄灯安寝,他才落寞地回到破庙栖身。这一悲剧性的处境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更加重了全剧怨愤、悲凉的情调。最终,绝望的黄大傻带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自杀而亡,一对年轻人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不同视角的选择,其实反映了作者的意图和风格,决定着故事的重心与指向。田汉称《获虎之夜》是“以长沙东乡仙姑殿夜猎为背景写贫儿之殉情的惨史”*《在戏剧上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田汉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无疑重点落在贫儿黄大傻身上,但是,由于上述的舞台表演艺术与生俱来的客观性,剧中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总是做不到像电影那样的彻底。多数情况下,主人公的叙述视点往往是隐含的,只能在整体客观视角中夹杂着局部但又相当强烈的主观视角。尽管这样的舞台处理看上去没有电影画外音来得直接和贯穿,主要还是依靠角色的行动和话语进行“呈现”,但这种叙述方法已经区别于传统写实戏剧的纯客观全知视角,让叙述者直接面向观众,必然大大增强情感的浓度和力度。这固然是田汉一贯的哀婉伤感的浪漫主义风格所致,其实也是作者受了电影叙事方法的影响。虽然写此剧时田汉刚从日本回国,还未动手拍摄电影,但他曾表示:“我是非常喜欢电影的。我在东京读书的时候,正是欧美电影发达的初期,当时日本正在努力学步。我有许多时间是在神田、浅草一带电影馆里消磨的。我的眼睛因此而变成近视。”*田汉:《影事追怀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可见《获虎之夜》《颤栗》采取这种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了电影的主观叙述方法,直接引领观众抵达人物的心灵深处,体味诗一般的意蕴。过去有人批评黄大傻眺望灯光的一段诉说,不符合人物身份与性格,“与其说是一个农村青年,不如说是一个感伤主义诗人”*陈瘦竹:《田汉的剧作》,《陈瘦竹戏剧论集·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3页。。其实仔细剖析,黄大傻正是由作者蜕变而成的“隐含的叙述者”,剧本突破了全知的客观视点,借黄大傻第一人称视点进行叙事,极力抒发青年人在黑暗现实中的痛苦感受,“在人的生死界上,挖掘出心灵深处那种在‘悲哀的洗礼’中的美”*董健:《田汉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突出当时青年追寻光明而不得的时代性压抑。
如果说写实型戏剧常不得不让叙述者隐藏起来,那么“叙述者在场”却是电影常见的手法。当时中国电影的显性叙事方式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叙述者形式多样,剧中人、画外音、字幕等,都可以参与叙述。如沈西苓执导的《船家女》(1935年),以两位老人在西湖旁,边对弈边讲述摇船姑娘阿玲的悲惨故事开始,进入影片的主体部分,而后又再次回到湖边对弈的老人,以他们的评述收尾。蔡楚生、郑君里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以字幕替代叙述者:“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民国二十八年”等一系列字幕,提示着时间的流动;片头片尾字幕“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进一步浓缩了影片的情绪,增强离愁别绪、世事无常之感。
袁牧之作品《马路天使》(1937年)除了客观视角以外,还以音乐承担起叙述者的任务,随着《四季歌》响起,影片的情节就会自然停顿下来,银幕上出现士兵冲锋陷阵,炮火猛烈;百姓扶老携幼,四散逃命等画面。由于跳出了小红卖唱的既定情境,歌曲在此时破坏了故事的幻觉认同,却强化了叙述者的主观表达——日寇的侵略、家乡的沦陷,这是底层百姓悲剧命运的根源。另外,“在电影中,总有一个片头字幕以外的角色,这就是摄影机。在摄影机表现得无所不在的时候,它的行为很像一个无所不在的作者”*[美]贝·迪克:《电影的叙事手段——戏剧化的序幕、倒叙、预叙和视点》,华钧译,齐洪校,《世界电影》,1985年第3期。。《马路天使》开场那段脍炙人口的78个镜头的短切,在表现霓虹灯、车水马龙般的街道、摩天大楼、咖啡馆、舞厅、石狮子等十里洋场的标志性影像后,摄影机便从华懋饭店的最高屋顶一直摇到最肮脏的地下水沟,随即引出游行队伍、看热闹的市民,而且这组镜头多为倾斜的构图;在影片结尾时,镜头又向上停在摩天大楼的顶层,一切华丽依旧,然而不远处的天空却乌云密布,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一面是耀眼的繁华,另一面却是阴影浓重。这一组镜头的自主运动,充分暴露了叙述者(编导)的存在,展示异化了的都市图景下,底层百姓如蝼蚁般的生存状态。
在戏剧舞台上,第一次有明确的叙述者在场的演出,当属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丽人行》(1946年)。该剧多达21场,时空跳跃多变,由于完全突破了传统话剧的叙事模式,作品问世时竟无人敢接手导演,最后还是由富于电影拍摄经验的洪深把它搬上舞台。《丽人行》的编导明显借鉴了电影叙事手法,由一报告人直接登台讲述三位不同女性的故事,并让其“常常以‘作者’的身份出现,跟台下观众做朋友,也跟台上演员打交道,成为剧中人的心绪和意见的代言人,也常常是他们的尖锐的直接的批评者”*田汉:《〈丽人行〉的重演》,见《田汉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402页。。如此之广的叙述功能,使该剧得以顺利展开故事的多个层面,并较好地呈现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与活动场景。
叙述者的在场颠覆了幻觉主义舞台尽力隐藏叙述行为、抹去叙述痕迹的叙事方式,从故事背景的交代、剧情的连接到表现人物的心理情感、发表议论等,显示出更多的主体介入,虽然还只是局限在外部功能上——将观众拉入故事的叙述网络之中,未将叙述本身作为叙事的重点,并强调观众的参与性与自主性,但当时戏剧舞台上的这种变化,还是在时空、结构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自由,从而革新了话剧的演出形式。
三、 独创性的视点转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话剧与电影在各自发展中发生了越来越多的相互接触和影响。随着创作人员的双栖构成和日益频繁的双向交流,话剧(也包括一部分戏曲)与电影的叙事观念相互植入几乎不可避免。在这一背景下,到40年代后半期,戏剧与电影在叙事方法上双双趋于成熟,就叙事的角度而言,两者几乎都出现了主客观多重视点的交叉叠合,而且人称和视点的转换十分自由灵活。这种频繁又自如的视点转换,也反映了戏剧与电影叙事手段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如在本阶段创作的话剧《丽人行》《升官图》《群猴》《李国瑞》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视点转换,尤其在胡可的《喜相逢》(1947年)里,这种灵活的转换几乎贯穿在整个叙述之中,可以说是话剧叙事的一个可喜的创新。
如果说《丽人行》中的叙述者属于故事外叙述者,犹如电影中的画外叙述者,那么《喜相逢》就是让剧中人——刘喜,担任故事内叙述者了。战士刘喜作为主人公,不时地在戏中“跳进跳出”,既表演故事,又从头至尾充当叙述者。大幕拉开,他便向观众说:“我叫刘喜,也不用多介绍,谁都认识我,是个八路军战士”;“我原先有点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啥的。为搜了俘虏腰包,犯过一回错误,这场戏就是编的这桩事儿”;“少说废话,我一见了他(指俘虏王相,引者注),这场戏就算开了幕啦”。随即一阵枪炮声中王相上场,刘喜也瞬间“跳进”剧中表演故事。当然,中间刘喜还不断“跳出”角色交代剧情的进展,或将自己的心理活动讲述出来。譬如当王相交出身上的五万块钱给刘喜后:
刘(开始犹豫)草!……我也拣点洋落儿!……可是,这纪律……哎,管他哩!(四顾无人,放进自己腰包)你看我干什么?
王 老乡你带着吧!(略停)对,你花就带着吧!……
刘(耳根子发热)草!不带着还能怎么着?用你嘱咐?废话!(扛起机关
枪)走!跟我走!
王 老乡,这前……这前……
刘(立住,绷起脸)这钱怎么样?你还想要?
王 这前……这前边是咱们八路军的地方了吧?
刘 嗯。——废话!(自语)草!没干过这一手!乍一干还有点儿拉不下脸
来哩!……唉!这有什么问题。先解决解决困难再说。再说,他这钱怎
么来的?还不是剥削老百姓的?有什么问题!(对王)走啊你倒是?
王 我不跟你走呢吗?
刘(心乱)弄的我心里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胡可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132页。
这一段戏的外部动作很简单,但重点叙述的却是“我”的细微心里活动,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受到戏曲乃至电影的影响。但作为话剧,如何在舞台上自如地驾驭叙述者与角色扮演之间的瞬间转换,在当时还是个棘手的问题,为此,胡可专门在剧本后面附上了“排演注意”:“这剧中有几段独白实际起了报幕作用,表演时希注意与角色身份调和,以免转到戏里去时感到突然。在结尾时倒不妨以演员身份来向观众说话。”*《胡可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可见当时的话剧演员普遍对舞台上叙事视点的转换是不习惯的,直到1980年代,布莱希特的叙事体戏剧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和效仿之后,这种演员“跳进跳出”的叙述体表演方法才成为一种重要的舞台形式。
融电影与戏剧(戏曲)的叙事方法于一体的做法,在抗战后的电影创作中同样不乏其例。就叙述视点的自由转换而言,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是一个优秀的案例,也是把叙述角度的“我”“你”“他”三者切换得天衣无缝的典范。影片以女主人公玉纹充当第一人称叙述者,多达二十四段的旁白,将一个原本“单薄简单”的故事编织得异常丰厚、令人回味无穷。正如一位影评人所指出的:“《小城之春》的伟大,更在于它在叙事方面的独创。旁白的加插本来在中国电影并不罕见,但从没一部暧昧能够胜过《小城之春》的。”*李焯桃:《宜乎中国·超乎传统——试析〈小城之春〉》,黄爱玲编:《诗人导演费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此中的“暧昧”无非包含了三个层面。
首先,影片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视角,却突破了玉纹自身的视野所限。按叙事学常理,第一人称叙事者一般无法叙述自己未曾经历、未曾听闻的事情,属于限知叙事。而该片中不少场景的画外音,叙述的是玉纹不可能了解的事件,却沿用了“我(玉纹)说”。如志忱夜晚进入礼言的房间偷换安眠药的情节,玉纹不仅当时无从知晓,即使事后也不可能知道,但她的画外音还是:“他把礼言的安眠药倒出来,把维他命药片换进安眠药片瓶子里。”*文中所引《小城之春》中的画外音是笔者观摩影片时的记录。下同,不再一一标注。又如,礼言痛定思痛,决计成全妻子玉纹与好友志忱。在此之前,他偷偷走进玉纹的房间,心绪难平地坐在妻子的床头,眼中满是爱恋与不舍,却又在玉纹回屋前悄无声息地退了出来,这时玉纹的画外音又响起:“三年来,他第一次走进我的房间。”其间既透露了他们夫妻疏离隔膜的现状,又将女主人公内心的幽怨准确地传达出来。无疑,此时此刻的玉纹无所不知,是以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在进行叙事,而第一人称与全知视角这种有悖逻辑的搭配,却达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使得客观叙述和主观抒情浑然天成。就像玉纹反复描述初恋情人志忱到来的情景(她并不在场),那种循环往复、一唱三叹、前后矛盾,实际上是她内心情绪的外化,也许潜意识里她早就期盼着这一天,盼着志忱的到来能够打破她如死水般沉寂的生活。
其次,表面看来,“叙述者”玉纹的受述者是观众,但纵观全片也有例外之处,听者有时又会转换成剧中其他人物。影片开头女主人公以平静克制的语气,交代人物、背景、日常生活状态,在内心苦闷的些许透露中,分明能感受到潜在听众的存在,即所有的观影者。但是,她的画外音中竟然出现了“你”,当玉纹被唤出来与客人见面,终于知道客人竟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志忱时,小鹿撞胸的她叙述道:
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他从火车站来。他完全认识礼言的家。我不知道礼言也是他的朋友。我心里有点慌,我保持着镇静,我想不会是他。他毫不知道我跟礼言结了婚。你为什么来?你何必来?叫我怎么见你?
这里,从“他”到“你”,叙述的视点进行了无缝转接。开始时玉纹的叙述还较平稳,对着观众袒露心声,并让自己“保持着镇静”。但随着日思夜想的昔日情人忽然出现在眼前,女主人公的内心波澜陡起,多年积聚的情感一下子喷薄而出,叙述也即刻跳转到“你为什么来?你何必来?叫我怎么见你?”此时的受述者变成了志忱,中间的转换没有任何过渡,但观众丝毫不感到突兀,反而能身临其境地体会女主人公玉纹此刻急迫又复杂的心理活动。
再次,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事与拍摄视点的差异。从影片第一人称的画外音来看,玉纹的叙述是其内心的写照:“人在城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什么”,“我没有勇气去死,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在一个破落的、了无生趣的家里,守着一个病怏怏的丈夫,除了死寂还是死寂。那种幽怨落寞之情一层层晕染开来,而摄影机的视点却并不完全配合叙述者,如香港影评人李焯桃所说,镜头的视角低于站立者的视平线,而接近一个人坐下后的目光高度,这分明是丈夫礼言的视线。因为身体原因,礼言不是坐在床上就是躺在椅子上,镜头对他是平视的,而对玉纹、志忱,则多用微仰的角度,无形中给礼言造成一种压力。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也将礼言的自卑刻写出来。可见,“虽然故事由玉纹做第一身叙述,但镜头的高度却暗示了礼言的视点”*李焯桃:《宜乎中国·超乎传统——试析〈小城之春〉》,黄爱玲编:《诗人导演费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这种有意而为的第一人称叙事与拍摄视点的不和谐对列,不仅与影片抑郁苦闷的氛围极其相符,而且也折射出创作者的叙事意图,是激进求变,还是固守传统,这正是处在动荡时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
很显然,《小城之春》中这些叙述视点的运用,已不光是二三十年代电影中主客观角度的兼用,而是更为巧妙、丰富和圆润的内在转换。应当指出的是,费穆之所以能极其出色地创造出这种叙事技巧,一方面在于他充分发挥了电影声画艺术的特长,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多年来对话剧、戏曲叙事的研究。费穆在抗战前后的上海不仅拍摄了几部有影响的戏曲片,还曾“转行”做过话剧导演,他领导上海艺术剧团排演了《秋海棠》《孤岛男女》《浮生六记》等脍炙人口的剧目,一度被誉为沪上话剧界“四大导演”之一;由于经历了戏剧(包括戏曲)的熏陶和创作实践,费穆战后重回电影界后,在电影的叙事手段上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以上事实都说明,中国的话剧与电影在开始产生和成长的阶段里,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所想象的那种分裂和对抗,或者电影始终被戏剧牵着走的局面。恰恰相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共生和互动,现代话剧在电影和戏曲的双重影响下,对写实主义的基本叙事格局有所突破;同时,现代电影在话剧、戏曲变革过程中也受到一定的启发,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叙述方法,尝试主客观叙事的交叉变换等新形式。艺术家们认识到,无论在舞台还是银幕上,灵活多变的叙述视点和方法,不仅不破坏真实感,反而能够通过视角转换,将艺术笔触伸入人物的内心,从而呈现一种比外部真实更加动人的心理真实。
也许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戏剧、影视作品中叙事方法的多样性,叙述视点的多重交叠、自由转换等早就习以为常,随着当代文化的空前多元化发展,各种跨界融合的艺术现象也已层出不穷。但作为一种历史研究,通过重新解读我国早期电影与戏剧在叙事性方面的相互影响,恢复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真实面貌,并且充分肯定这一历史经验,即在坚持与发挥各自艺术特性的同时,不断地借鉴其他艺术的长处,保持各类艺术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有学术价值的;也相信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对当今的戏剧与电影的创作,都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