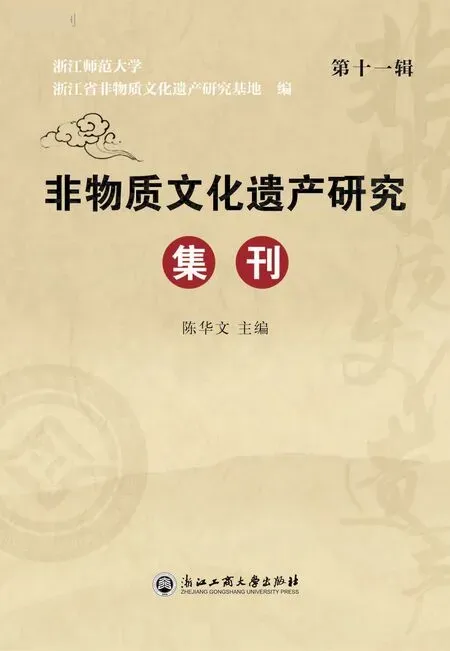博物馆与社区的互动
——基于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考察
王巨山 关晓函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博物馆的发展与实践一再证明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能够促进社区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同时也能促进社区凝聚力(community cohesion)、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再生。[注]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进化中,早期对社区观照较少,随着保护理念的发展,“在公约缔结35周年之际,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世界遗产战略’增加了‘社区’(Community)概念,强调当地民众对世界遗产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世界遗产战略从4C提升到5C,即可信度(Credibility)、有效地维护(Conservation)世界遗产、提升缔约国相关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凭借良好的宣传(Communication)和社区参与(community)。参见岳桦:《1972—2012:世界遗产40周年大事记》,《世界遗产》2012年4期,第14页。然而,博物馆如何与社区建立长期、有效的互动?事实也一再证明缺乏长久、有效的机制,博物馆与社区的互动很难深入,也很难维持。[注]段阳萍:《西南民族生态博物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方李莉:《梭嘎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笔者2014年6月至12月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在合作导师文德安(UNDERHILL, ANNE P.)的推荐下,2次专程考察了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重点探讨分析博物馆与印第安人社区的互动及对印第安人社区文化的展示与传播。
一、博物馆学视域中的社区
社区是英文community的翻译,commun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mmunis,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关系。community可以对应翻译为共同体与社区,有社区与共同体两个含义。社区一词最初在1871年英国学者H.S.梅因(Herry Maine)《东西方村落社区》作品中使用。后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于1887年将社区(Gemeinschaft)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并被认为是社区理论的创始人,其经典著作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有学者翻译为《共同体与社会》,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社区与社会》,还有翻译为《公社与社会》。由此可见,Gemeinschaft翻译为社区还是共同体在学界是有分歧的。虽然社区出现在滕尼斯的著作中,但其并没有给社区一个标准定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在发展上呈现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人的和最高形式的”精神共同体。[注][德]费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4、65页。
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Charles Roomies)翻译滕尼斯的著作时,将德文的社区gemeinschaft一词翻译为community。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进一步发展社区理论,并形成了社区的核心要素:特定区域、共同关系、人及社会互动。
国内社区的概念最初是燕京大学一些大学生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文 Community一词的。它的含义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庭,逐步推广成氏族以至民族(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人群。邻里在农业区发展成村和乡,在城市则发展成胡同、弄堂等等。
目前,关于社区的不同定义超过140种,但从定义的出发点看,不外有两大类:一类是功能主义观点,认为社区是由有共同目标、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另一类是地域性观点,认为社区是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尽管人们对社区的定义不同,但社区的基本含义包括了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并有一定数量规模的进行共同生活的人口。2.有一定的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地域条件,即一定的地理位置、地势、资源、气候、交通条件等。3.有一整套相对完备的,可以满足社区成员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社会生活服务设施。如商业、服务业、文化、教育等设施。4.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5.社区居民在情感、心理上具有共同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认同感、归属感。6.有一套相互配合的适合社区生活的制度与相应的管理机构。”[注]费孝通:《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些思考》,《群言》2000年第8期,第13—15页。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此后2005年民政部在长春的会议、2009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中所讨论和表述的社区也是以地域为主的表述。
20世纪70年代后,博物馆在不断发展中也不再仅仅关注物,而是逐渐关注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1972年5月20日至31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圆桌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博物馆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强调博物馆应与社区加强协作。此后,1984年的《魁北克宣言》和1992年的《加拉加斯宣言》都再次强调博物馆服务社区的职责。1995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挪威斯塔万格举行的大会,讨论主题是博物馆与社区(Museums and Communities ),通过一项有关博物馆与社区的决议(Museums and Communities)[注]Resolution no. 1: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Considering that museums are fundamental tools for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minds, of self-awareness, of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and of community’s identity;Noting that some local museums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are undertaking innovative activities focusing on everyday topics of community life, trying to challenge traditional models and reaching beyond the limits of exhibition spaces, are facing threats of closure and lack of support from their governing bodies;Convinced of the necessity of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of programs and action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s and museology in the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local cultural, social,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The 18th General Assembly of ICOM, held in Stavanger, Norway, on 7 July 1995;Urges local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recognize and support museums as cultural mechanisms in the service of communities, in the valorization of their particular identities, and as unique tools for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Recommends that in the adaptation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and sites as museum spaces, particular care be taken to preserve the visible and informative record of people, events and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is heritage and for the recognition of communities’ struggles,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represented in these three-dimensional documents.Encourages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of ICOM’s National Committee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will consider the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weaknesses and needs of their area of activity in the human, technical, economic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leading to coordinated action for the benefit of museums, of museology and the communities which they serve.。1997年,菲律宾举办的国际博协亚太地区第六届大会的主题是“走向21世纪——博物馆与建设社区”。200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建设社区”。在博物馆学家的视野中,社区又有了与社会学者不同的“含义”。20世纪70年代,英国博物馆学家肯尼斯·赫德森就认为,从博物馆的角度谈社区,社区可以分为四类:“(1)当地的社区——博物馆周围约五里;(2)地区的社区——距离博物馆两小时的旅程;(3)国家的社区——不论国家的大小如何;(4)国际的社区——在某一年内能够向博物馆提供观众的这样一些国家。”[注]吕建昌:《博物馆社区概念及社区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学会:《回顾与瞻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国内博物馆学者也持有类似意见,“从博物馆角度考虑社区这一概念时,不必拘泥于社会学家们的一些观点,既不必像社会学家那么复杂地来划分社区,也不必局限于国家民政部的划分概念,应当结合博物馆的实际情况,以一定的地域或规模以及有利于人际交往、建立共同情感纽带的因素为基本”。[注]吕建昌:《博物馆社区概念及社区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学会:《回顾与瞻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苏东海认为社区的含义比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宽泛得多,它不仅指地域,而且可以指文化群、政治群、商业群,甚至一个单体、一个自然与人文的整体社会。[注]苏东海:《博物馆服务社区的思想由来》,《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25日第6版。由此可见,博物馆学者关注的社区更注重以博物馆为核心的辐射区,并非通常行政管理维度的社区。
二、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建立
(一)北美印第安人概况
在考察美国历史和文化时,不可回避部落族群就是印第安人部落。印第安人是美国的土著居民,1492年,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时,误把美洲当地居民当作“印第安人”。[注]刘明翰、张志宏:《美洲印第安人史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有欧洲来源说、亚洲来源说和非洲来源说等。随着考古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发展,学术界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欧亚大陆。[注]宋瑞芝:《走进印第安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在印第安人的历史中,15世纪到19世纪,美洲印第安人锐减,主要原因是流行病,同时,殖民者和美国西进运动都对印第安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屠杀。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正式承认562个印第安人部落,其中约300处印第安人保留地(reservations)处于偏远地带,78%的美国印第安人生活在保留区之外,其中纯正血统的印第安人比混血印第安人更愿意生活在保留区内。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11年统计,美国登记在册的纯血统印第安人为2,932,248人,约占全国人口比例的0.9%,有着两种血统以上的印第安人为2,288,331人,合计5,220,579人,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1.7%。[注]人民网:《人民网记者走进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2013年8月2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827/c1002-22714681.html。印第安人在美国分布比较分散,在美国五十个州都有分布,其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地方为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在阿拉斯加州人口中,印第安人所占比例最高,超过15%。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和现代生活的挤压,美国印第安人保留的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宗教等传统慢慢消逝,一些印第安人群体呼吁建立印第安文化机构以保护印第安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建立背景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的建立是基于1989年国会通过的《美国国立印第安博物馆法案》(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该法案注意到国立博物馆中没有关于印第安历史与文化博物馆,而当时史密森尼博物馆协会和纽约海伊博物馆(Heye Museum,)均有大量土著居民的收藏,而海伊博物馆也存在展示不充分和藏品过于“拥挤”现象,通过国家行为将二者合并建立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有利于促进印第安人文化的展示、研究和传播。该法案进一步明确鼓励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创建宗旨、法律依据、集资分配和分工管理等内容,基于该法案,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成为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体系的第十六个博物馆。在定位上,基于1989年的法案,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是印第安文化与传统的活态记忆(living memory)。[注]根据法案表述:There is established, withi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 living memorial to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ir traditions which shall be known a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建立有四重目的:一是推进美国印第安人研究;二是收集、保存和展示具有艺术、历史、文学、人类学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印第安人实物;三是为印第安人研究提供支持;四是为哥伦比亚、纽约州及其他合适地区开展上述活动提供支持。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分为三个主要展示地(three sites),分别是纽约海伊中心(Heye Center, New York)、华盛顿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The Mall Museum, Washington)和马里兰的文化资源中心(Cultural Resources Center, Maryland)。《美国国立印第安博物馆法案》通过后,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开始兴建,前后历时15年,2004年建成,总投资2.19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出资1.19亿美元,民间募资1亿美元,其中超过1/3的民间募资来自各印第安部落的捐赠。很多美洲各地的印第安人参与博物馆的设计和修建,其建筑风貌充分体现了印第安文化及传统特色。马里兰文化资源中心开馆时间较早,1999年对外开放。而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海伊中心最初缘于1916年,1922年建成开放,在整合后于1994年对外开放,主要负责拍摄、播出由印第安人创作的,或者是展现印第安文化的影视作品,并且还通过专门性的网站“Native Networks” 举办以印第安文明为题材的影像节(Native American Film, Video Festival)。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是美国印第安人长期争取权利斗争和生存空间的结果,是后殖民语境下印第安人与国家的“妥协”与“合作”,无论是对美国博物馆发展、博物馆学发展还是对印第安人的文化认同、社会认同与自我表达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与印第安人社区文化的展示
(一)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藏品与展览概况
对于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三个地点来说,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是其中最重要的展示馆。该馆位于国家广场的黄金地段,紧邻美国国会山,与国家广场对面的国家艺术馆相对。博物馆外层建筑是由产于美国中北部城市明尼苏达州的浅黄色石灰岩(kasota limestone)构成,造型呈波浪状。博物馆分为5层,建筑面积约23000平方米,馆内大约收藏和展示了四类藏品:实物、图片、多媒体文件和报刊文献。其中实物82万件,图像档案32.4万件(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影像文件1.2万件(包括电影和音频文件),来自西半球的1200个不同土著文化的展品展示了12000年的印第安人发展史,这些藏品涉及美国、加拿大、中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博物馆藏品中,大约68%来自美国,3.5%来自加拿大,10%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11%来自南美洲,6%来自加勒比地区。55%的藏品来自考古发现,43%来自民族学调查,2%是现当代艺术品。[注]Smithsonian: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http://www.nmai.si.edu/explore/collections/。馆内还有影像室,同时常年开展面向学生和公众的项目。
2014年,笔者对华盛顿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进行了两次调查,根据当时调查了解的情况,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展览展示主要分布在博物馆的一至四层,第五层为博物馆管理机构办公室。当时博物馆的布置和展览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博物馆第一层主要分布为印第安人部落提供文化展演的空间(Potomac Atrium)、提供印第安人事物的餐厅(Mitsitam Native Foods Cafe)和提供影视放映的剧场(Rasmuson Theater)。平时没有印第安人部落展演的时候,表演空间摆放展品。在博物馆的第二层主要分布博物馆商店(Roanoke Museum Store)和回归原住地展览(Return to a Native Place Exhibition)。博物馆第三层主要分布“我们的生活”(Our Lives)永久展览、一个临时展厅(Changing Exhibition)和儿童活动中心(Activity Center)。博物馆第四层分布两个展览:我们的宇宙(Our Univer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Shapes Our World)和部落与国家(Nation to Nation: Trea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 Indian Nations Exhibition),还有一个会议中心(Conference Center)。同时,在第三层、第四层展厅外的橱窗里还有印第安人的藏品展示(Window on Collections Exhibitions)。
(二)博物馆空间与印第安人社区文化的展示
1.“三个空间”与印第安人文化展示
(1)文化展演空间(Potomac Atrium)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主入口在馆的东部,进入博物馆走过走廊就可以看到位于博物馆第一层的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文化表演空间,笔者第一次去调查时,印第安人部落正在进行文化表演,圆形广场的四周和走廊里则有其他印第安人在展示和出售文化产品。第二次去调查时,该空间被利用起来进行印第安人实物展示,可见该文化空间的用途是多样的。根据1989年《美国国立印第安博物馆法案》对博物馆的定位要求,该文化空间也是体现活态记忆(living memorial)的重要场所,是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心脏”。同时,在设计时,该文化空间也被赋予了重要的象征意义,反映印第安人的文化:圆形、面向东方的设计来源于印第安人建筑形式,而地面上的黑色与红色圆圈上也代表印第安人的至日和分日。
(2)餐厅(Mitsitam Native Foods Cafe)
博物馆餐厅也是活态展示印第安人文化的重要场所。食物制作是一个族群或部落文化的重要体现。餐厅提供了美洲各地印第安人的传统餐食,博物馆参观者可随时进入餐厅就餐,体验用传统方法制作的印第安人食物。
(3)博物馆商店(Roanoke Museum Store)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第二层是博物馆商店,商店中主要出售印第安人的当代艺术作品和手工制品,如首饰、陶器、服饰、手工艺品、现代艺术品、音像制品、书籍以及一些当代商品。在出售的印第安人手工艺品上都有制作者的头像、艺术家编号、作品信息介绍等内容。
有声音批评博物馆的第一、二层过于商品化,在笔者看来,第二层的博物馆商店不仅仅是商店,也是现代印第安人文化的一种展示,在出售现代印第安人文化制品的同时,也在博物馆内将印第安人的过去与现在,甚至印第安人个体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2.三个展览与印第安人文化展示
笔者2014年11月去参观调查时,博物馆的长期陈列有三个:
(1)我们的生活(Our Lives)
展览主要聚焦于印第安人在21世纪的认同问题,展厅门口的一块展板明确写道:这个展览关注的是当下我们是谁。在这里你可以直面感受美洲地区印第安人身份认同的动力。展示主要涉及八个印第安人部落。在展览的入口,矗立两个大屏幕,屏幕上不同的、行走的印第安人形象呈现在大屏幕中,而对应的话语是:“美洲的任何地方,您可能正在和一个21世纪的印第安人同行。”
展板中的文字进一步解释道:展厅的中央地区可以看到影响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例如定义、社会和政治意识、语言、空间和民族自决。这些揭示的认同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生活体验。[注]展厅展板原文:The central areas of the gallery look at key elements that have affected native identity, such as defini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language, pla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se areas reveal that identity is not a thing but a lived experience.展览对身份认同提出很多思考,围绕身体与灵魂、生活在本土空间、艰难的选择、身陷现代化等主题,提出很多问题,如:谁是原住民?谁决定?我的样子体现我的认同?我的血缘体现身份认同?我的认同体现在科学图表里吗?我的认同体现在文件里?我的认同来自过去冰冷的艺术品吗?数字是我的身份认同吗?我的认同来自政府吗?
整个展览大部分以文字和图片形式呈现八个印第安人部落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同时辅以多媒体展示和景观陈列方式展示一定的场景,使观众能产生比图片和文字更直观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文字在展览中扮演重要角色,展览需要突出的主题则以较大的字体进行凸出,以实现主题表达的目的。
透过各个部落的文化展示,展览透过上述身份认同和面临问题聚焦到印第安人的生存焦虑。如何在当下环境中摆脱(breaking out)生存焦虑,展览中间的展板给出了进一步解释:生存不仅仅是存活,生存意味着尽你可能保持你的文化,从自我的创造到政治行动的一切事物中寻找生存意义。[注]原文:Survivance is more than survival. Survivance means doing what you can to keep your culture alive. Survivance is found in everything made by Native hands, form beadwork to political action.
(2)我们的宇宙(Our Univer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Shapes Our World)
展览主要关注印第安部落的宇宙观(包括世界观和生物与宇宙的哲学思考)以及关于人类与自然世界的精神联系。展览结合印第安人的太阳历,向观众展示了西半球印第安土著居民祖先在节庆、语言、艺术、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的聪明智慧。展览序言写道:
在这个展厅,你将了解印第安人如何理解他们与宇宙的关系和如何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印第安人)的生活哲学来自我们的祖先。他们教会我们与动物、植物、精神世界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在我们的宇宙观中,你将邂逅来自西半球的印第安人继续在仪式、节庆、语言、艺术宗教和日常生活中表达这种智慧。将这种学说传递给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那是保持我们传统存续的方式。[注]博物馆展厅门口的展板原文:In this gallery, you’ll discover how native people understand their place in the universe and order their daily lives. Our philosophies of life come from our ancestors. They taught us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animals, plants, spirit world and the people around us. In our universes, you’ll encounter Native people from western Hemisphere who continue to express this wisdom in ceremonies, celebrations, languages, arts, religions, and daily lives. It is our duty to pass these teachings on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or that is the way to keep our relations alive.
展览按不同部落分为不同小区域展示其宇宙观。在表达印第安人对自然、植物、动物的生活知识和生存观念时,展览图片、文字和实物相结合,并借助多媒体展示技术提供更多与展览相关的内容。
在展示印第安人部落对宇宙的认识时,展览采用了景观陈列的方式,以昏暗、神秘的方式进行呈现。
(3)部落与国家(Nation to Nation: Trea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 Indian Nations Exhibition)
这一展览以时间为经线,以重大事件和协议为纬线,编织了从殖民史到现在印第安人部落与部落、部落与政府、部落与其他殖民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所以将“条约”(treaties)作为整个展览的主题词,是因为双方所达成的“条约”在协调双方关系上扮演核心角色,尤其是现今,一些协议仍在规定美国政府和印第安部落的责任与义务。如今,这些历史和故事已经成为美国和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展厅内,很多的醒目文字表达了印第安人的主张:我们永不放弃(we never gave up)。
展览展示了1682年、1790年、1794年、1851年、1838年、1851年、1868年、1945年、1975年、1978年、1988年、1990年等各个关键时间点上,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政府以及其他部落达成的“条约”,1945年之前的“条约”展示内容较为丰富,包括《条约》缔约双方的观点争议(Viewpoint)、《条约》简要内容、余波(Aftermath)以及《条约》的照片。历史上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各部落签订的《条约》超过300项,正是用这些《条约》,美国印第安人逐渐丧失了大量的土地、地位和权利[注]李剑鸣:《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美国研究》1994年2期。,各部落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越来越小。因此,在展览中,展板上不时会出现印第安人发出的抗议声音,如对美国政府废弃1800年达成《条约》(The Two-Row wampum)的理念,《条约》在印第安人眼里成为“糟糕的废纸”(bad papers),其成为征用和掠夺其土地的工具。展览不断有这样的文字出现。如:
伟大的国家信守诺言。(Great nations keep their word.)
我们绝不会放弃。(We never gave up.)
我们不会搬迁到别的地方……我们会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造物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希望这些《条约》受到保护……我们将会和太阳一样永恒。(We are not going to move any place... My people will live there until the creator change the world and we would like to have our treaty protected... My people are still growing as long as the sun going.)
伟大的国家要像伟人一样,应该信守诺言。(Great nations, like great men, should keep their word.)
前面两个展览是基于印第安人的文化展示、发展思考和自我认同,而《部落与国家》的展览则将印第安人的思考和斗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即作为弱势群体如何在当下国内环境中争取生存空间。这种生存包括原住空间的保留、文化的存续、族群内部的认同、社会的认同,更包括国家的认同。
除三个固定陈列外,在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中,也有小型临时展览。如在三楼走廊的展览《返回原住地》(Return to a Native Place: Algonquian People of Chesapeake Bay),展示了曾经住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印第安人部落的阿尔冈昆人(Algonquian)生活情况。整个展览分为返回原住地(Return to a Native Place)、切萨皮克的黑暗时代(Dark Days in the Chesapeake)、复兴(Revival)、认识世界(Knowing Earth: Chesapeake Native Identities)、坚持到底(Holding on: Strategies to Stay Native)、永远记得(Forever Remembered: The Native Chesapeake)6个板块,展览只是利用博物馆楼层的走廊进行展示,因场地较小,所以展示内容以文字和图片为主,简介了切萨皮克湾地区原住民部落的历史、曾经的生活与现状。展览最打动人的一句话是:这个展览需要你用当地人的眼光看待切萨皮克。[注]原文:This exhibition asks you to look at the Chesapeake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ingenious peoples.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是印第安人展示原住民文化和自我表达的重要文化空间。这种展示和表达在完成展示任务的同时,已经超越了博物馆的一贯保有的认同作用,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将印第安人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将印第安人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将印第安人的文化主权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作为“接触地带”的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是印第安人文化自我展示的“场域”,也是印第安人的“自我言说”、表达理解、需求、关注和认同的“舞台”。
四、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与社区互动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工作范畴超越了传统博物馆收集、展示与研究的功能,成为印第安人部落与其他族群、社会和国家对话的重要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后,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对印第安人文化的保存、保护和展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活态记忆”(Living Memory)理念的生动实践
19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立印第安博物馆法案》已经对博物馆的定位进行了明确要求,要求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成为印第安人文化的“活态记忆”。在纽约的海伊中心也曾在外部有一个匾额: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不是只关注过去,当然也不是关注死去的或正在死去的文化,它关注活着的文化。[注]原文:NMAI is not just about the past and certainly not about the dead or dying. It is about living.参见Marilena Alivizatou,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he museum:new perspectives on culctural preservation, Abingdon: Left Coast Press, Inc, 2012,pp.105.
活态记忆理念的确立影响了博物馆展览和实践。印第安人的活态文化在馆内和馆外都有体现:馆内提供了印第安人基本的文化陈列和提供了印第安人文化活态展示的空间,馆外印第安人社区广泛参与和策展、互动,建立于此的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活动内容和陈列内容更新较快。
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对于印第安人文化的活态展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即多媒体展示,多媒体展示的影片不限于过去的影像资料,其影像资料主要通过自制和面向社会征集有关印第安人新拍摄的影像资料,不断有更新的影视作品能够展示不同时期印第安人与时俱进的状态,这些影像资料不仅供博物馆内多媒体播放,同时也可以借给研究者使用。博物馆还有一个隆重的盛会,1979年到2011年,由纽约影视制作中心主办印第安人影视节(Native American Film + Video Festival),为西半球印第安人媒体和影视制作人媒体讨论和研究印第安人文化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也为博物馆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考察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基本理念后,我们发现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是相吻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什么,而是为了保持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这就要求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正在传承着的文化。在理念上的契合使得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学者认为博物馆正在做的事情很好地保护了印第安人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了印第安人文化的连续性,而重要的是在历史发展中保持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是极其一致的。
(二)社区的自我表述
在与社区的互动上,在笔者观察到的与非遗保存有关的博物馆中,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做的内容相对较多,且效果最为明显。通过前面的介绍,不难发现博物馆的文化展演空间和餐厅是博物馆与部落、社区互动最为明显和紧密的地方,此外,稍有留意,我们就会在博物馆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博物馆的展览基本是以印第安人为第一人称进行展示的,三个主要展览都是如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宇宙》《部落与民族》都是以我们(our)作为“故事”的讲述者,而来自社区的“主张”也在博物馆中得到展示和传播。
博物馆从建筑外观的设计、建筑到展览的设计与展品的诠释都离不开西半球印第安人部落和社区的合作和帮助,虽然有时这些来自部落或社区的策展人(curator)并不理解博物馆和展览是什么,但与博物馆的合作和自身的学习,担任策展人的印第安人出色完成了部落文化的“自我展示”。博物馆的展板上,非常明确标示出展览的策展人,这是博物馆对策展者的尊重,也是博物馆与社区互动的内容与成果。同时,展品的文化解释权也归属印第安人部落(社区),这种紧密互动避免了展品与社区文化和语境失去联系而停留在“文物”层面,与社区和印第安人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展品能够为观众构建是超越文化层面的意义。博物馆的活态展示理念和社区互动紧密观照的是印第安人的认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与其说是纪念印第安人经历的暴力、文化的湮灭和消逝,不如说是印第安人表达身份认同的场所。[注]Marilena Alivizatou: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he museum:new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bingdon: Left Coast Press, Inc, 2012,pp.128.
当然,印第安人或相关社区的过度参与也易让人忧虑,如不懂传统博物馆概念和展示技术和方法的原住民会在展示和策划中让步吗?来自社区的策展人和博物馆、博物馆专家的关系如何协调?来自社区的策展人虽然会与社区反复沟通,但策划展览对社区反映的真实度有多少?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特别强调社区的作用,如社区在项目确认、申报、保护、管理和其他决策中要发挥相应的作用。博物馆作为专业文化展示机构,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回避社区的作用,博物馆不能代替社区去解释社区的文化,不能将自己的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强加给参与展示活动的策划人,同时还要协调好策划人与社区的关系,能把握好其对社区文化的代表性和解释的权威性。
(三)社区文化的研究与阐释
开展研究是博物馆基本功能。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开展印第安人部落相关问题研究,如藏品研究(Collections Research)、历史与文化研究(History and Culture)、艺术研究(Native Arts)以及相关文物返还问题(Repatriation)[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0年,美国通过了《印第安人墓葬保护与返还法》(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Repatriation Act,NAGPRA),该法案适用美国国内印第安人的遗物、丧葬物品、艺术品和其他文化财产。1990年以前,已有博物馆返还印第安人文化遗产的案例,1990年之后,随着相关内容写入宪法以及美国印第安人在学界和其他社会领域地位提高,返还越来越多。参见杜辉:《帝国主义与文物返还叙事》,《东南文化》2013年4期。。在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中,既有馆内专家,也有来自印第安人社区的印第安裔学者。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经常举办讲座、研讨会,同时有馆刊《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s)的出版,纽约馆内的影像、音频等资源也向研究者开放。面向大众的公共教育也是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经常开展的活动,具体的活动会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进行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