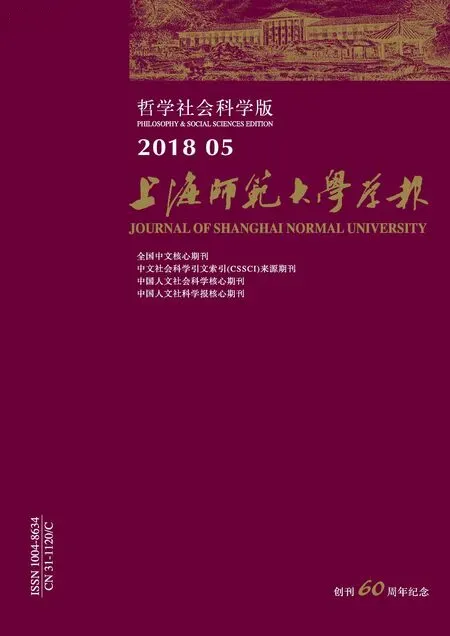文献、口述与研究:重建日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自1991年8月14日韩国金学顺女士指证日军性奴隶暴行以来,已过去27年,日军“慰安妇”——性奴隶的反人类罪行,日益被人们知晓。各国的史学界、法学界等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国际社会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要真正弄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并解决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遗留问题,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就世界史学界的关注程度而言,笔者以为“慰安妇”问题在二战历史研究、教学中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拟总结回顾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过程与成果,并就几个重要问题进行阐述。
一、重建日军“慰安妇”的历史
尽管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中稍微涉及“慰安妇”这个概念,“在占领桂林时期中,日军犯下了强奸和抢劫之类的一切种类的暴行,他们以设立工厂为口实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的妇女,被强迫为日军作娼妓……”,①但由于时间仓促、取证困难,加之日本当局刻意隐瞒等原因,因此“慰安妇”没能被列为专门的犯罪类型,并予以追究和判决。
1991年以来,日军“慰安妇”历史的调查研究经历了非常艰难而曲折的复原历程。复原的困难在于:其一,战败时日本销毁了大量的文献。其二,在受害者和受害国方面,性伤害的事情难以启齿,且大部分受害者已离开人世了。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菲律宾、东帝汶、印度尼西亚、荷兰等地“慰安妇”幸存者勇敢作证的引导下,在各地人权组织的推动下,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旗帜鲜明的决议下,同时也得益于历史学家、法学家等深入、艰难的田野调查取证,以及各类历史文献的搜集与公布,从而逐渐揭露出战时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秘幕。
在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的团队寻找档案文献,出版资料集,推进学术研究。②松冈环、西野瑠美子等对日本老兵进行访问和日记的搜集评估。③川田文子等对日本“慰安妇”进行调查。此外,千田夏光、松井耶依、金一勉、铃木裕子、金富子、中原道子等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日本政府方面,则于1993年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政府与此有关联,并进行反省。但日本政府又企图依靠建立女性亚洲国民基金的办法来避开国家责任问题,从而遭到了亚洲各国的抵制。2015年12月,日本政府与韩国政府迅速达成“不可逆”的“慰安妇”协议,但由于缺少诚意,遭到幸存者和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加之韩国政府的更迭,现在已处于搁置状态。
在韩国,民间社会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调查幸存者并进行援助,建立了“分享之家”的养老公寓。④民众自1992年1月8日以来,每个星期三都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已坚持26年。该周三集会全名是“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每周三定期和平集会”,目的是要求日本就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强制动员“慰安妇”等问题进行真相究明、对受害者正式道歉以及进行法律赔偿。在2011年12月14日第1000次周三集会时,民众将日本大使馆前的周三集会场所所在道路命名为“和平路”,并在此设立了和平少女像,此后又在韩国国内和国外推广建立“慰安妇”和平少女像,已卓有成效。⑤
中国方面也做了多方努力。如寻找幸存者,确认事实,查询历史资料,尤其是日本占领军的文献、战时报刊等。已出版120册《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⑥其中有日军官兵供认在亚洲各地抢掠妇女、设立慰安所的大量事实。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了关东军的资料,⑦有不少与“慰安妇”相关。前后出版的著作还有《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慰安妇”与性暴力》《证据:上海172个日军慰安所揭秘》《南京日军慰安所实录》以及ChineseComfortWomen:TestimoniesfromImperialJapan’sSexualSlaves等。⑧
二、日军“慰安妇”历史的几个关键点
1.时间与空间
日军“慰安妇”历史的起始时间和地点是1932年1月的上海。当时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指定一批日侨开设的风俗店为海军指定慰安所,包括“大一沙龙”、三好馆、小松亭和永乐馆4个。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海军慰安所,持续时间从1932年1月到1945年8月,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目前有5幢房屋完好保存下来。⑨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发动侵华的“一·二八”事变。此后,战事扩大,日本政府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由于发生多起日军官兵强奸战地妇女的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为此征募日本妇女建立一些专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具体操办者是该派遣军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冈部在同年3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这时,传来士兵们千方百计搜索女人、道德败坏的各种传闻,为了解决士兵的性问题,就着手积极建立这种设施。”⑩于是,冈部与永见俊德中佐论证了“慰安妇”问题后,向冈村宁次递交了实施报告。冈村宁次立即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女性组织“慰安妇团”,运至上海的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高层也迅速推广慰安所。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辽宁到云南,日军在中国占领地广泛设立慰安所,范围涉及吉林、山西、湖北、广东、湖南、广西等22个省。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慰安所遍及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各占领地,冲绳、朝鲜半岛和台湾殖民地也均设有慰安所。
概而言之,日军“慰安妇”存在的时间是从1932年1月到1945年8月。从空间上看,几乎所有日军的占领地、驻屯地均设有慰安所或变相的慰安所。
2.日本政府与军队的关联
为日军部队配备“慰安妇”、设立慰安所,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项基本制度。因此,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口号下,日本政府的外务省、法务省、内务省、警察系统、各都道府县与陆军省、海军省积极合作,均为慰安所的设置、管理提供便利条件和许可。所以,日本政府和日军与慰安所之间不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这一性奴隶制度的“助产婆”。
以日本外务省系统为例,其开具了派遣日本、朝鲜“慰安妇”前往中国等地的证明。1938年秋,当武汉会战还在进行时,日本外交部门与军方已在合谋设立武汉慰安所的事宜了。9月2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藤味在致外务大臣宇垣一成的《对于汉口占领后邦人进出的应急处理要纲》中已提出:“居留民以外的人来汉口,将根据输送能力和申请人的开业情况来考虑,但建立军队慰安所没有限制。”可见日本政府派出领事馆关注慰安所的建立和管理。又如1939年2月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花轮义敬在致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关于管理去汉口渡航者的文件》中称:“军队慰安所已有20家(包括兵站、宪兵队和本馆批准的慰安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开始介入慰安所的调查。在南京,1938年4月16日,日本总领事馆与日本陆军、海军举行联席会议,协商对南京慰安所的管理,会议规定:“军队开设慰安所时,需将慰安妇的原籍、住所、姓名、年龄、出生及死亡等变动情况及时通报给领事馆。”
毫无疑问,日军则是推行“慰安妇”制度的主体,其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参与设立慰安所。
1938年3月4日,日本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发送“陆支密745号”秘密文件,内容就是募集“慰安妇”、建立慰安所。文件规定“慰安妇”的征募工作一律由派遣军一级进行“统制”;各军要选派合适的专门人选来担任此事;征募女性时要与当地警宪取得联络。这一文件得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批准。这一正式文件还明白无误地揭示了,除军方之外,日本政府的警宪系统也加入“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中。它集中体现了日本陆军省作为政府军事最高领导机构在推行军事“慰安妇”制度中的领导者角色。1940年9月19日,日本陆军省颁发给各部队的教育参考资料《从中国事变的经验来看振作军纪的对策》,针对日军出现的“掠夺、强奸、放火、杀戮俘虏等”行为,认为“性的慰安所给予事变精神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要求“对慰安设施有周到的考虑”。在日本政府和军队高层看来,慰安所承担了振奋士气、维持军纪、预防强奸等多项功能。这一记录进一步表明,日本政府、军方设立慰安所系统,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1940年,视察中国东北后日本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所见》中记载道:“在中国部队前线生活普遍不太好。接下来要考虑官兵的精神慰安以及给养。听部队长说,不明原因的逃亡、暴行接二连三发生,需要给他们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尤其是国境守备队3年都没外出过。督促恤兵部尽快采取有效措施。”1942年9月3日,在日本陆军省科长会议上,恩赏课长指出要在现有慰安所的基础上,追加“将校军官以下的慰安设施,拟按以下规模:华北100所,华中140所,华南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库页岛10所,共400所”。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枢机构直接指挥了建立慰安所。当时的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是松井石根,参谋长是塚田攻。上述命令的下达,至迟在1937年12月1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该日的日记里写道:“从(华中)方面军那里收到关于建立慰安设施的文件。”由此可知,在占领南京前,日本华中方面军就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设立慰安所的命令。另外,在上海金山卫登陆的日军第10军,随后也收到了同样的命令。该军参谋寺田雅雄中佐在湖州指挥宪兵队秘密征集当地女性,并于12月18日设立了日军慰安所。为了保证在上海地区尽快开设日军慰安所,上海派遣军参谋部要求该参谋部第二课课长长勇中佐专门负责此事。12月19日,饭沼守写道:“委托长中佐迅速开设‘女郎屋’。”同月28日他又记载了“日本军的违法行为愈演愈烈,由第二课召集各部队负责人,传达参谋长的训诫令”。
在吉林省发现的两份历史文件表明,日军为建立“慰安妇”制度支付的费用非常巨大。其中一份伪满洲中央银行的档案,是该行资金部外资科的电话记录,时间是康德十二年(1945)三月三十日,内容是在徐州的日军第7990部队,经关东军第四科批准,通过伪满洲中央银行淮海省联络部向该行鞍山支行经理汇款252000日元,用于采购“慰安妇”。这笔款项的受领人写着“鞍山圣理司令部”,估计应是伪满洲中央银行鞍山支行的经理,而“司令部”三字推测应是衍文。该文件明确记载,“实际受领人是在鞍山的米山鹤”,“上述金额表面是公款形式”,“需要用大额汇款的形式存入支店的定期户头,虽然有这种存款限制,但推测可以免除其限制,允许其以军用公款的科目处理”。文件最后附加了“本件需持关东军第四科证明办理”表述,下面还记载了3笔已经汇送的经费:1944年11月17日,50000日元;12月16日,150000日元;1945年1月24日,80000日元。这4笔汇款相加达532000日元。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第7990部队为“采购慰安妇”汇付了如此大笔的钱款。这表明,日军用军费来推行“慰安妇”制度是当时日军内合法的事情,也就表明了日本政府和军队是建立性奴隶制度的推手。这些钱款,主要用于日本在华、在韩的警察系统征用和运输“慰安妇”,日本工兵部队修建慰安所建筑,以及建立军医体检体系、慰安所警戒等用途。所谓的“采购慰安妇”的资金并不是支付给“慰安妇”的,在中国、韩国、朝鲜的调查中,这些国家的“慰安妇”受害者连生命也没有任何保障,根本就没有报酬。
从史料中可见,日军基本在军一级机构设置管理慰安所的机构或军官(岗职)。通常由参谋部、军医部、管理部共同负责慰安所事宜,也有在酒保部或兵站下面设立专门管理慰安所的机构,有的称为“某某科”,有的则直接命名为“慰安所科”“慰安妇股”。如在关东军里,由司令部参谋第三课负责慰安所事宜。日军驻屯上海的第7331部队,则专门设有慰安所科。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兵站也设有慰安所科,由军官2人、下士官2人、士兵4人共8人组成,其职责是管理“慰安妇”、监督慰安所运营。史料记载,每逢“慰安妇”到达民营慰安所时,兵站慰安所科即协同慰安所的老板一起,查验“慰安妇”的照片、户籍抄写本、警察的许可书、地方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书、病历等。
3.慰安所的类型
通常有军队自己设立的慰安所、日侨经营的慰安所、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以及傀儡政权日军合作者设立的慰安所几种类型,其中日军直营的慰安所最能体现日本国家实施性奴隶制度的本质,其中既有自上而下有计划设立的,也有中队、大队等部队自行设置的。
还有一些原本是妓院,但被日军和傀儡政权指定接待日军官兵,往往不挂慰安所的牌子,却是变相的日军专用慰安所。
也有不少受害者并不是在正式的慰安所中受害的,在中国这一现象较为普遍。日本战犯秋田松吉供认,自1940年2月至1941年5月,第43大队第3中队山东省章丘县南曹范分遣队长山根信次伍长以下15人在南曹范盘踞。他任该队一等兵步哨。山根伍长通过伪村公所强制带来5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这15人对该5名中国妇女进行了一年零五个月时间的淫污。山西省有约70位幸存者作证,她们大多是被抓到炮楼受害的。
4.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规模
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事实表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规模远远超过我们此前的估计和想象。例如在上海可以确定至少存在过172个日军慰安所,南京至少有70个日军慰安所,海南岛的慰安所有67个,武汉也有数十个慰安所。当然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浙江省金华市档案馆藏有日文版《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这本完成于1944年4月的朝鲜人同乡会名簿,是中国情报人员获得的。在这份短短的两百余人的名单中,隐藏着不少日军在金华地区建立“慰安妇”——性奴隶制度的信息。经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确认,名簿记有11个慰安所,慰安所老板8人,管理人员7人,而“慰安妇”竟高达126人,占金华鸡林会朝鲜人总数的60%,最年轻的只有17岁;慰安所相关人员共计141名,占金华鸡林会朝鲜人总数的67.19%;比例之大是非常惊人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日军推行性奴隶制度的普遍性。
5.“慰安妇”是被强迫的还是生意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似乎正在进行一场“谁比谁更右”的荒唐游戏,以吸引日本民众的眼球来谋求各种政治利益。2007年3月5日,针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日本战时推行性奴隶制度的决议,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竟说,“美国议会的决议案不基于事实。虽然得到通过,但我不会谢罪。从狭义看,没有证明强制性的根据。也没有能证明那些的证词。也许不会有从军‘慰安妇’自己愿意走那条路,的确有业者在中间强征的情况。可是,没有官员冲进屋子里、把人带走的那种强征性”。2013年5月,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公然声称,在战时的情况下,“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存在”;他甚至建议,驻日美军官兵可充分利用日本的色情场所。2014年1月,新上任的日本放送协会(NHK)新任会长籾井胜人竟然胡说,慰安妇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
当日本政府和军部为确保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实施“慰安妇”制度后,大量的外国女性和殖民地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主要是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妇女。在亚洲各地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和证言,证明这些女性是被强征或诱骗,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她们失去人身自由,苦不堪言,生不如死。
在山西盂县、武乡等地,日军在与八路军对峙的艰苦环境中,时常将抓到的农村妇女控制在炮楼里,那里就成为“合法的强奸中心”。经过长期的调查所知,当地愿意站出来指证日军性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至少有70人。在海南许多地方,日军也是任意将女性抓入军队据点作为性奴隶使用。如在澄迈,“一发现稍有姿色的女青年都抓到军部里充当‘慰安妇’,专供其玩乐。日军每个中队都设有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今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家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石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2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强制征用和随意抓捕中国女性作为日军的性奴隶使用,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些“慰安妇”被凌辱而亡,甚至被日军杀死吃掉。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下士官绘鸠毅(原名石渡毅)供认,在山东省的索格庄,日军强逼一名女战俘做一下士官的“慰安妇”。因在索格庄长期驻扎,食物供给越来越困难,下士官竟把她杀了,然后吃了她的肉。而且他不仅自己吃,还对中队的人谎称大队本部送来了肉,让全中队的人都吃了。
日本宪兵参与了对日军慰安所的管理,例如统计进出慰安所官兵的人数,并进行管理。在吉林省档案馆发现了两份日军档案,是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给该军参谋部的报告,其中统计了南京、下关、镇江、句容、金坛、常州、丹阳、芜湖和宁国9个地区的慰安所情况,除了宁国因交通断绝情况不明外,其他8地均已设立慰安所。档案记载,在芜湖,“慰安妇”比上一旬增加了84人;在该地的109名“慰安妇”中,日本女性48人,朝鲜女性36人,中国女性25人。在镇江的109名“慰安妇”,要面对15000名士兵,平均1名女性要面对137名士兵。报告明确记载:在2月中旬的10天内,有8929名日军官兵进入了镇江的日军慰安所,竟比前一旬增加了3195人次;在该地,平均1名“慰安妇”10天“接待”了82名官兵。在丹阳,因为“慰安妇”暂时只有6人,严重不足,因此报告中明确写上要“就地征募当地慰安妇”。在大木繁的另一份报告中记载:湖州的慰安所里,有中国女性11人,朝鲜女性29人;当桑名旅团开到湖州时,日军数量已有所减少,但仍增开了一家“特种慰安所”。无锡“最近也要增加20名‘慰安妇’”。
三、“慰安妇”历史如何记忆
2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漫长而艰难的受害者调查,包括韩国、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菲律宾、东帝汶、荷兰、印度尼西亚。能确认的受害幸存者情况为:韩国239人,朝鲜209人,中国大陆250人,中国台湾50人左右,印度尼西亚发现数百人,菲律宾100多人,东帝汶数十人,日本10人以内,荷兰也有多名受害者。
中国大陆发现“慰安妇”幸存者的省市,涉及黑龙江、吉林、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海南等。广西荔浦的韦绍兰战时被日军抓到马岭慰安所,被迫怀孕,逃回家后,生下“日本仔”罗善学。近年来,他们曾到上海、南京、东京、大阪等地作证,至今母子俩仍生活在大山脚下。
岁月流逝,幸存者日益凋零,目前中国大陆有14位,中国台湾只剩下2位,韩国还有30位,荷兰只有1位(拉芙女士生活在澳大利亚),菲律宾有数十人,印度尼西亚还有上百人。
1.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在日军“慰安妇”问题上,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共识。早在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专门就“慰安妇”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了报告。是年4月1日,联合国法律专家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报告认定日本政府需要负起相关责任,并建议日本政府:(1)应当对违背国际法设立慰安所的行为负法律责任;(2)应当对被作为性奴隶受害的每个人予以赔偿;(3)应当公布一切有关资料;(4)正式向被害者谢罪;(5)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一历史事实;(6)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
同样,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法学会等均做出了谴责日本实施性奴隶制度的报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于1993年调查后发布报告,提出道歉、赔偿、国际法院立案等7条建议。2007年以来,美国、加拿大、荷兰、欧盟、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国会(议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政府否认历史责任。
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决定将这段反人道的历史写入教科书,在课堂上讲述,如中国、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日本的高中历史中保留了一些内容,但比20世纪90年代已有明显的倒退。
2.悲惨的历史如何记忆
金学顺揭发日军暴行的8月14日,正在成为“慰安妇纪念日”,每年的“八一四”,各国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慰安妇”的活动。各国或地区的新闻工作者和电影人纷纷参与拍摄“慰安妇”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如韩国的故事片《鬼乡》,中国大陆的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等,中国台湾的《阿妈的秘密》《芦苇之歌》。通过观看《二十二》等纪录片,既引发了中国公民的议论和关注,也完成了“慰安妇”问题的知识启蒙。
设立历史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延续记忆。2017年4月,在东京举行了第一届日军“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会议,“慰安妇”博物馆已出现在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菲律宾、荷兰等地。在中国大陆,有黑龙江孙吴关东军“军人会馆”陈列馆(2009)、云南龙陵董家沟慰安所旧址陈列馆(2010)、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2015)、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2016)等。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是在日军慰安所旧址上建立的,有8幢旧房,朝鲜“慰安妇”朴永心于2003年亲临作证。美国、加拿大也在建立“慰安妇”博物馆。
3.申请世界记忆名录的较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名录活动,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绝好方式。2014年中国向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南京大屠杀资料”和“慰安妇资料”两个项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慰安妇资料”申遗未能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见是:考虑到“慰安妇”关联的还有其他国家,建议联合申请。于是2016年5月31日,中国与韩国、菲律宾、印尼、东帝汶、日本、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民间团体或机构一起,递交加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名称为“‘慰安妇’的声音”。这次联合申遗的资料非常丰富,共计2744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慰安妇”历史资料和“慰安妇”调查及抗争活动的文献。这些文献尽管存在残缺性、破损性等缺陷,但确实是真实的、唯一的,恰恰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记忆名录的要求。
但日本右翼势力等也申报了“日军的纪律”的项目,宣称日军的军纪非常严明,企图混淆视听。在审核之时,日本政府甚至扬言,“‘慰安妇’的声音”如获通过,日本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压力之下,201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定结论是,建议两个“慰安妇”相关项目展开对话。目前,我们的国际申遗委员会已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愿意对话。事实表明,关于战争暴行如何评价和如何记忆,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历史学者的研究需要价值中立,冷静评判,谨慎落笔。但历史学家也承担着判断善恶,鞭挞罪行,指引人们向善的责任和使命。日军“慰安妇”——军事性奴隶的战争罪行,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日军南京大屠杀等一道,是20世纪反人道的严重战争暴行,人类应该深刻记忆并吸取教训,以防止类似暴行的重演。
注释:
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90页。
②吉见义明关于“慰安妇”的主要作品有《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年版)、《從軍慰安婦》(岩波書店1995年版)、《共同研究 日本軍慰安婦》(与林博史合编,大月書店1995年版)等。
③松冈环搜集了百余种日军老兵的日记等,以南京为中心,展示了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建立慰安所的部分事实,其主要著作有《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新内如、全美英、李建云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沈维藩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西野瑠美子曾在中国海南、云南、南京、上海等地调查,主要著作有《從军慰安婦》(明石書店1992年版)、《從軍慰安婦と十五年戦爭》(明石書店1993年版)、《女性国際戦犯法廷全記録》(合编,绿風出版社2002年版)、《戦場の“慰安婦”——拉孟全滅戦を生き延びた朴永心の軌跡》(明石書店2003年版)。
④“分享之家”是通过韩国的慈善家捐赠土地、民间募集资金以及韩国佛教曹溪宗等参与的方式,于1995年12月定居在京畿道广州市郊,它既是“慰安妇”幸存者的养老院,也是一个“慰安妇”历史博物馆。
⑤树立“慰安妇”雕像的有加拿大、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德国等。菲律宾的“慰安妇”像2018年被移除。可参见[日]日本軍“慰安婦”問題webサイト制作委員会编:《〈平和少女像〉はなぜ座り續けるのか》,世織書房2016年版。
⑥《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华书局2015—2016年版。
⑦吉林省档案馆:《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军侵华档案研究》,第1册,吉林省出版集团2014年版。
⑧主要著作有,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1999年版);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双兵:《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苏智良、陈丽菲:《“慰安妇”与性暴力》(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苏智良、陈丽菲、姚霏:《证据:上海172个日军慰安所揭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苏智良、张建军主编:《南京日军慰安所实录》(南京出版社2018年版);丘培培、苏智良、陈丽菲:ChineseComfortWomen:TestimoniesfromImperialJapan’sSexualSlaves(加拿大UBC出版社2013年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⑨“大一沙龙”最早称“大一”,是上海日侨较早建立的日本式“贷座敷”。所谓的“贷座敷”,是一种日本式的风俗营业店,除了向客人提供餐饮外,也提供女子供客人玩乐。其接待的客人,虽然说不分国籍,但实际上以日本人为主,有日本士兵,也有日本普通侨民。“大一”的名字在1920年的《上海日侨人名录》上已有记载,初由日本侨民白川经营,设立于宝山路,后迁至东宝兴路。
⑩[日]岡部直三郎:《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1932年3月14日,芙蓉書房1982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