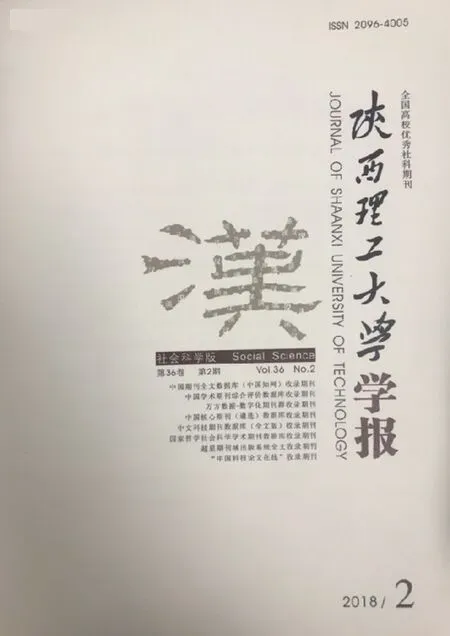多元文化视野下回族语言中的借词溯源
——以西安回族方言为例
马元丽,马新芳
(1.陕西师范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2.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陕西 西安 710002)
民族间的交流离不了语言的交流,语言的交流离不了相互借鉴。所谓借词,是指人类在语言交流过程中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来的词,是民族间交流的产物。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1]173当某种事物的名称在交流一方使用的语言中并不存在,或其中一方特别强大时,借词因此就产生了。王力先生认为,借词是外来词的一种,“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意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2]587客观上讲,适度借用其它民族语言词汇对于自身民族语言可以起到丰富与补充的作用,词汇交流借用过程实际上是文化交流的过程,是汲取其它文化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尤其是借用那些文化意义丰富的词汇,对于不同民族间的学习借鉴尤为重要。各民族间的开放程度越高,交融程度越深,民族间语言交流借用就愈多,这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
汉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很多外来词汇,这其中主要包括一些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一些在本民族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像“葡萄”“石榴”“苜蓿”等词汇是汉代从西域借入的词;“世界”“因果”“圆满”“塔”等词语是汉代以后从印度借入的佛教用词;“琵琶”“骆驼”“胭脂”等借自匈奴;“沙发”“披萨”等借自欧美。[3]这些吸收自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流传千年至今,已经和汉语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汉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语外,各少数民族语言种类非常丰富,因此不同地区汉语方言也从相关兄弟民族语言中吸纳了一部分借词。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西安回族方言中的借词来源。
一、陕西回族形成的历史源流
陕西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的交融之地,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关中、陕北在历史上曾是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满族等民族长期活动和杂居的区域,曾拥有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内迁的少数民族政权,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在内)建都于西安,陕西方言在各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受到一些外来语汇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在汉代,丝绸之路将西域各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相互交融逐渐扩大,汉末至魏晋之际,原居西北至东北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居内地,历史上称为“五胡”内迁。实际上,内迁关中的少数民族并不仅仅限于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等五族,还有乌桓、柔然、高车、稽胡等,族类及人口众多。据西晋江统所著《徙戎论》记载,仅关中一地百万余口居民中,“戎狄居半”[4]1533。
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曾先后建都长安。《晋书·江统传》记载,南匈奴归附东汉时在关中仅有五千余户,到西晋时已增至三万余户。[4]1533原籍中亚、“高鼻多须”的羯族曾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在长安建立后赵政权(319年-351年),他们虽说是入主中原,但处于非主流文化,因此竭力保持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前秦(350年-394年)是氐族政权,建都长安,秦军曾押送二十万鲜卑俘虏迁往长安,大部分被安置于关中一带军马场牧马;后秦是(384年-417年)羌族政权,也建都长安。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对各族人民的融合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北魏后期鲜卑族将军宇文泰迎魏孝武帝于长安城建立西魏政权,重新推动鲜卑化政策。匈奴铁弗部人赫连勃勃于407年在今陕北一带曾建立“大夏”政权,后挥师南下,一举拿下长安,在长安称帝,从此,大批的匈奴人定居关中,在陕北及关中等地留下了本民族的文化印迹。
隋唐时期,各民族交流融合又得到新的发展。唐都城长安是当时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城中居住来自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三万人。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世就是那个时代民族交融的典型。隋代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鲜卑族名为那罗延,鲜卑姓氏为普六茹,杨坚掌权后改为汉姓“杨”,并让已改鲜卑姓氏的汉人恢复汉姓,结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形成了汉化的主流文化社会。唐太宗李世民家族有着胡人的血统。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唐太宗的祖母是北周鲜卑大将独孤信的女儿,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是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5]55。元稹《法曲篇》中的诗句:“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唐传奇《东城老父传》中记载的:“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从不同侧面都印证了隋唐以来多民族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呈现出空前的盛况。正是这种多民族融合的背景,造就了开放、自由、包容的大唐盛世文化。
先民来自西域的中国回族的产生更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鲜明例证。公元七世纪中叶,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军队西征,先后征调了大量的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入伍,这批西域人后迁入中国,吸收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这其中有一支天宝年间应唐王朝邀请前来大唐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军队,他们在帮助唐王朝平定战乱后留在大唐,驻扎在陕西渭南沙宛一带开垦屯田,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成为陕西回族先民的一部分。
二、西安回族方言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中国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做母语的初期,到群体性使用汉语做通用语的漫长历程。长期与当地民族通婚及经贸往来,加速了回族先民掌握汉语的进程。十三、十四世纪,回族的语言已经从最初的多母语时期,经过母语加汉语的双重语言时期,最后过渡到汉语取代其他各种母语而成为回族的统一语言。来源不同的回族先民共同使用汉语,这标志着回族作为中国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的形成,正如李树江先生在《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序中所言,“没有汉语作为各个不同来源的回族的共同语,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形成的。”[6]2
我国回族自公元十三世纪左右就开始将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但由于宗教纽带和民族情结,回族在普遍使用汉语的同时,也在本民族之间的交流中,刻意保留了一些方便宗教生活和联络民族感情的先民母语语汇,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方言。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借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语,这些词语大多与回族群众所信奉的伊斯兰教相关。回族群众保留这部分先民语汇借以方便宗教生活,联络族群感情,强化民族认同感。
所谓西安回族方言就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主体,吸收、借用了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词汇而形成的一种带有回族特色的西安方言。回族同胞在与汉族同胞交往时不会使用外来词语,而在回坊人之间的日常生活语言中,经常会夹杂部分外来语词汇,如:
阿拉伯语音译借词:赛俩目(平安、和平)、兑亚(今世)、给亚麦提(后世)、尔德(节日)、伊玛目(领袖)、塞拜不(缘由)、都阿(祈祷)、乜提(举意)、讨白(忏悔)、克尔白(天房)、哈俩里(合法的)、哈拉目(非法的)、拜俩(灾难)、以扎布(证婚词)、法依代(好处)、乃随卜(福分)、尼尔埋低(恩典、食物)、卧尔兹(劝诫)、乌巴里(可怜)、者麻力(俊美、好)、耶提目(孤儿)、引撒尼(人)、萨瓦布(回赐、感谢)、付迷(倒霉)、尔麦里(功修和善行)等等。
波斯语音译借词:胡大(真主)、阿訇(教师、学者)、邦克(召唤)、乃玛子(礼拜)、邦不达(晨礼)、撇什(晌礼)、底格儿(晡礼)、沙目(昏礼)、胡夫达(霄礼)、阿不戴斯(小净)、兀苏里(大净)、杜闪比(星期一)、歇闪比(星期二)、查尔闪比(星期三)、派闪比(星期四)、主麻(星期五)、别麻儿(疾病)、巴巴(长者)、板代(奴仆)、杜失曼(仇人)、多斯提(朋友)、多灾海(火狱)、古拿哈(罪过)、赶逮(臭)、喔也(脸)等等。
西安回坊较年长的坊民间见面时打招呼的常用语是“按赛俩目而来以库恩”(大意即“愿真主赐你平安”),表示感谢时多会说“萨瓦布(感谢)你咧!”在表示同情时常用“乌巴里”(即可怜)一词,如在遇到乞讨的孩子时回坊人常会说:“看这要乜提(施舍)的娃乌巴里的,来把这些尼尔埋低(食物)给娃”,这一句话里就夹杂着三个阿语借词:乜提、乌巴里、尼尔埋低,这种夹杂着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汉语表达方式,很久以来已成为回族坊上人之间所习有的一种语言交流方式。但近年来随着回族年轻人就学及就业环境的改变,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会说这种有特色的“坊上话”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少。
三、西安回族方言中的佛教用语借词
汉语中有许多词语都源自佛教用语,如“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大千世界”“天花乱坠”“三生有幸”“现身说法”等等。为了适应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需要,以汉语为民族母语的回族,自然无法完全回避汉语中庞大的佛教词汇,为了沟通的需要,回族用语中不可避免也借用过少量佛教用语。对这些词汇,回族人在使用过程中采用了化用的方式,使原本属于表达佛教理念和佛教文化的词汇用来表达回族的宗教理念和宗教文化。
如“寺”本为佛教宗教场所之名,回族借其意将穆斯林礼拜场所称为“清真寺”;再比如西安回族在遇穆斯林亡故时一定不能说“死”而要说“无常”或“归真”以表避讳与庄重。“无常”原本是佛教用语,来源于梵文意译,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生起、变异、坏灭之中,迁流不息,绝无常在,谓之无常,回族人借用过来用以表示“死亡”意义。回族人还借用佛家“归真”一词表示死亡。《释氏要览》下《送终·初亡》:“释氏死谓涅盘、圆寂、归真、归寂、天度、迁化、顺世,皆一义也”,可知“归真”本是佛家对人死的别称,进入穆斯林经堂语后,“归真”意思虽仍然表示“死亡”,但却将其巧妙从字面上化解成“从真主那儿来,仍回到真主那儿去”的意思,使其完全融入回族文化当中,成为回族日常语言。
包括“知感”“皈依”等原出自佛家用语的词语,现今都已完全融入回族语言当中,为回族群众所接受。而相比来说有些宗教借词接受度就较差,如回族经堂语中的“参悟”一词本出自佛家语汇“参禅悟道”,因其仍明显带有佛教色彩,在回族口语中接受度不高,这反映了回族民众对其他宗教因素渗入的戒备和提防。
但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语言的借入与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语言本质上就是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不同种类、形式的语言可以表达相同的思想。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早就指出,在通行汉语文的地区日常生活中就应以通用的汉语文来表达伊斯兰教思想。在以汉语为学术话语的语言环境中,这种表达方式是回族伊斯兰教在以儒、佛、道为中国思想文化核心的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适应,反映了回族在文化学习上的一种开放心态。
四、西安回族方言中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借词
我国各民族同胞之间在往来接触过程中,语言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各自吸收某些对自己有用的语言成分,当某种事物的名称在交流一方使用的语言中并不存在,或其中一方特别强大时,借词就产生了,如十三世纪蒙古族和十七世纪满族入主中原,就为汉语带来一定的蒙古语和满语词汇。西安回族方言中也有借用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语言词汇的现象。
(一)维吾尔语借词
西安回族方言中有不少维语借词,如西安回族称爷爷为“巴巴”、奶奶为“拿拿”、母亲为“拿儿”、姨妈为“娅娅”等,与维语中同类称谓发音一致。陕西方言中常见的形容词“尕达马西(杂七杂八)”也是借自维吾尔语,指“琐碎的、杂乱的、乱七八糟的”意思,维语读音为“尕德儿马西”(gadirmax),陕西方言借入后仍是杂七杂八的意思,如“你这屋里尕达马西摆了一河滩,也不拾掇拾掇?”“最近尕达马西的事情太多了”。
再比如“安珍尔”是西安回族对无花果的俗称,西安回坊人把无花果树称为“安珍尔树”,这一词汇也是来自维语。无花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分布于土耳其至阿富汗,唐代即从波斯传入新疆,然后从新疆传入中原。无花果在维吾尔语称为“安居尔”,与波斯语音近,波斯语称为“anjir”。唐代《酉阳杂俎》的记载中无花果被称为“阿驵”,与波斯语的“anjir”、维语的“安居尔”以及西安回族方言中的“安珍尔”发音对应,三者应同源。
“艾来百来”在西安回族方言中经常用来形容一个人这样又那样、出尔反尔的意思,如“这人不可靠,一天就会艾来百来的”,意思就是这人说话出尔反尔,做事变来变去,不靠谱的样子。“艾来百来”来自维吾尔语,在维语中是“这些那些、这样那样”的意思,引入汉语后引申为与人交往中爱说话但不靠谱、东拉西扯废话多的意思,如“这人艾来百来拉扯个没完”。“艾来百来”在维语中原为副词,在借入西安方言后词义有所发展,既保留了原来的用法,又活用为形容词,多用来形容那些出尔反尔、见风使舵的言行,如“这人艾来百来的事情太多了”。这个维语词汇在音译为汉语词后更像是个合成象声词,读起来就像是翻来覆去、不着调的样子,非常形象。
“胡里麻达”在西安方言里的意思是马马虎虎、凑合的意思,如“大家都集合了,他来不及仔细整理,胡里麻达把东西收拾了一下赶紧往外跑”。“胡里麻达”一词来源于新疆土语,但词源是维吾尔语。
(二)满语借词
回族方言中的满语借词不多,有“嘠什哈(羊拐)”“撒目(到处看)”“沙琪玛”(糕点名称)等。其中“嘠什哈”是最有特色的一个。
“嘠什哈”是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儿童一种传统的游戏玩具,学名“羊髌骨”,西安方言中俗称“羊拐”,回族人习称“嘠什哈”。“嘎什哈”呈六面体,形状圆方相间,小巧玲珑,凹凸分明,是北方妇女儿童所喜爱的一种随身玩具。它玩法多样,可分为弹、抓、搬、撒、赶几种,为了游戏中快速辨别正反侧面,有的还要染上红、绿、蓝、黄四种颜色。“嘠什哈”在满族语言中称之为“嘎拉哈”(galaha),满族儿童有抓“嘠拉哈”的传统,关于它的来历,有这样一个历史传说:相传金代帝王金兀术,在少年时不思进取,金兀术的父母为锻炼他成长,督促其进山打猎,他不负父母的期望,亲手猎杀了四种猛兽,摘取其髌骨而归,最终成长为一名勇敢、强悍的青年猎手,并在以后成就霸业,受到女真人的拥戴。锡伯族人也有玩“嘠什哈”的传统,早在北魏时期锡伯族的先民——鲜卑人就有此项游戏,拓跋鲜卑曾统治中国黄河以北,所以“嘎尔出哈”便成为北方蒙古族、满族、回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朝鲜族、汉族等各族妇女儿童所喜爱的一种游戏玩具。“嘠什哈”在锡伯族语中称为“嘎尔出哈”,与满语音近,锡伯语本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故此推定西安回族方言中的“嘠什哈”一词应属满语借词。
(三)蒙语借词
陕西方言中“旮旯”(拐角的意思),“克里马察”(赶快、雷厉风行的意思),“胡里马叉”(做事不认真、邋遢的意思),“普希来亥”(拖泥带水、不利落),“吉麻眼”(糟糕),“抹脱”(脱落,也指做事过于出格而出事)等词语都来自蒙语,包括西安市内的几个地名如“马呼沱”“沙呼沱”“幹耳垛”等均来自蒙古语。
除借用来自其他民族或宗教的语言之外,回族方言中对汉语儒家思想及其语汇也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逐步与中华文化相融合,把伊斯兰教中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致中和”思想结合起来。正如清初伊斯兰教大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自序中所言,“圣人之教,东西同、古今一”[7]15。明清两代的回族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们既博览诸子百家之学,又钻研伊斯兰教经典,不仅精通伊斯兰教的教理教义,还具有很高的儒学水平,他们“以儒诠经”“借儒以自重”,加速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公元十六世纪,陕西咸阳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胡登洲阿訇发起创办了经堂教育,他在继承前人宗教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把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与儒家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创办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学的伊斯兰教学者。
清初著名学者王岱舆在其汉文译著《正教真诠·开言》中说:“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8]16;清儒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云:“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8]2在学者们如此开阔的视野之下,像“君臣”“父子”“孝道”之类的儒家用语在清至民国时期回族经堂语中俯拾可得。这种语言上的可接受性,一方面是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本土汉文化倾斜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文明只有在不断地吸收其他文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定律。
纵观中国历史,从汉魏两晋到隋唐时期的数百年历史,是民族间相互交融、此消彼长的过程。这种民族的交融与民族文化的交汇,不可避免地存在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语言交流中相互学习与借鉴。这些文化共融现象或已在漫漫岁月中消失、变形,难以一一溯源,但我们可以在方言文化中找到一些可追踪的痕迹。
[参考文献]
[1]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第八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房玄龄.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李树江.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7]刘智.天方典礼[M].马宝光,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8]王岱舆.正教真诠[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