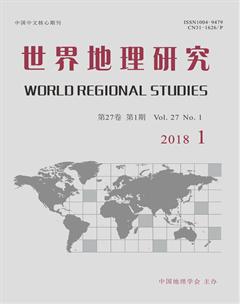滇西北高原山地型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研究
许斌 周智生



摘要:在高海拔、生态环境脆弱、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独特的藏区社会,每所藏传佛教寺院都通过宗教对其周围村落的生产生活空间格局和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村落对寺院的日常运作发展也提供了支持,这是宗教传统浓郁的藏区社会生活的现状。因此,长期以来寺院与村落形成了共生关系,并表现为相应的空间形态和演化机理。以滇西北高原山地环境下的东竹林寺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GIS技术手段,以共生理论为理论工具对东竹林寺与周围村落的共生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寺院与村落的共生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并长期以来形成了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寺院从村落接受金钱、物质等世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村落进行宗教信仰的传播。另一方面,村民在宗教生活中对寺院的高度依赖也使得村落愿意接受来自寺院神圣空间的宗教影响,并且自愿地向寺院输送生活物资等世俗资源,布施和捐赠是主要形式。这种共生关系的地理特征表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计方式、共生要素、虔诚度等会表现出空间分异特征,并根据空间主体所在的自然地形环境、离寺院的距离、村民的职业等条件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圈层与空间密度差异,但是寺院与村落的共生关系格局直至现在都没有动摇过。
关键词:藏区;藏传佛教;寺院;村落;共生;空间;宗教
中图分类号:K927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我国藏区因其高海拔地域环境的多样性、生态环境系统的脆弱性、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独特性、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其范围内的村落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社会表征和空间结构。特别是在藏民族的发展史上,藏传佛教寺院在精神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日常社会生活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村落的形成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造就了藏文化、宗教文化和其他多元文化交融于一体的藏族村落的分布格局、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互动关系是藏区基层社会特殊形态的重要表征,亦是认识和把握藏区社会空间的重要基础。
国外宗教地理学对于宗教与聚落的关系研究开始得较早。拉普特、圭东尼等均认为,在宗教主导的社会中,宗教文化是决定居住形式和格局的主要因子,气候、地理条件只是修正因子。莱格兰指出许多族群住房的形制和格局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还有一些西方人文地理学者注意到宗教对地理环境的改变或形塑,如艾沙克认为,根据宗教教义宣扬的不同,可以直接影响人们居住选择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或改造。
国内学者则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覃江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二元分化和二元性相关联;同时指出寺院依托村落的经济模式是藏传佛教寺院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绒巴扎西认为寺院经济是维系藏区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周智生、王丽萍等人认为在云南藏区,藏传佛教适应并契合了滇西北高原牧区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为当地社会广泛接受,并成为当地的全民信仰,这是寺院与地方社会供施关系的基础。一方面,藏传佛教在滇西北藏区的深入传播与浸润使得村落生产生活空间营造了浓郁的宗教氛围,经幡、小型佛塔、转经轮等宗教设施成为每个藏族村落不可缺少的景观。同时,磕长头、咏六字真言等村民的宗教行为已经生活化和常态化并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惯习。另一方面,村落供施寺院的方式主要依靠藏民的自愿布施以及藏区社会“送子入寺”习俗影响下的僧侣原生家庭对僧侣本人和所在寺院的经济支持。
以往研究多從民族学、宗教学和政治学角度,较少有从地理学视角研究藏区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基于藏区特殊的人地关系和社会环境中,寺院与村落之间社会共生关系的空间形态表现及其演化机理研究,学界未有系统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尚待深入探究的新领域。
1理论基础
1.1共生与共生空间的理论
1.1.1共生的概念
共生(symbiosis)原本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最初起源于1859年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中描述了田间植物、田鼠和猫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共生关系。受达尔文的这一思想的影响,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首次提出共生的概念: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地共同生活,是存在共生方式的不同生物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密切联系。随后的生物学家都是认为共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物体在生理上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了平衡、稳定、持久并且亲密的关系。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尔逊对群体共生做了归纳,把群体共生分为群体寄生、偏利共生、互利共生等三种类型,奠定了后来共生类型模式的研究。
后来共生的概念被引入到社会科学,集中在共生经济、共生产业等问题当中,无论是企业和个人,在其生产、销售甚至消费环节都可以用共生理论进行解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地方政府、银行和社区等已经与企业构成了复杂的共生系统,共同组成共生链,各环节缺一不可。
日本建筑学家黑川纪章结合日本传统文化的唯意志论、大乘佛教与禅宗的“诸行无常”、“万事皆空”等东方的哲理思想,同时又汲取了英国作家阿瑟·凯斯特勒的“子整体结构”思想和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多价哲学,首次提出了“共生空间”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的本质一种共生体系,存在着异质文化的共生、人类与技术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历史与现代的共生、自然与建筑的共生等现象。因此他将其建筑空间设计思想的核心就是共生,将空间研究中的共生思想提升到了哲学高度。
袁纯清在国内较早把共生思想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把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是共生的本质。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诸如民族共生、文化共生、社会共生等学术构想把共生的理念运用到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中。李思强在国内较早阐释共生哲学,他从哲学意义上把“共生”看作是事物之间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命运关系。胡守钧提出了“社会共生论”,认为共生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是社会的普遍发展,并归纳出社会共生关系的基本类型、基本要素、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许宪隆等随后提出了“共生互补论”,认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村落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由于受到生物学和哲学的影响,国内外的前人研究把共生的概念内涵大多定位于共同、包容、整体、互补等范畴,但本研究所要论述的共生关系应主要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即以相互离开都无法独立生存为核心内容对共生关系进行分析。在精神信仰领域,存在着少数民族村落与宗教寺院的分工关系。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许多少数民族特别需要精神的慰藉,他们需要职业化的宗教空间与专职的宗教人员给予他们在精神信仰上的帮助,作为回报,他们会供养资助寺院与专职宗教人员,因为专心研究佛学,僧侣等宗教人员已没有过多精力从事劳动生产,而村落里的农牧民们也不具备专业的宗教职能,所以寺院与村落形成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共生关系,村落负责劳动生产再源源不断地把物资与财务送至寺院,而寺院则向村落传经送教与举办各种法事来给村落提供宗教服务,便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共生关系,两者之间缺少一个都难以生存。所以,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寺院与村落这两种功能不同的空间存在分工的原因。
1.1.2共生空间的界定
因此,根據共生理论,地理学家判断地理单元之间是否在空间上具有共生关系,一般从三个方面判断:①地理单元之间是否具有互补性;②地理单元之间是否具有位置距离或社会关系的邻近性;③地理单元之间是否按某种方式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这三个方面在空间结构和形态上是符合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若干效应的,因此进一步得到共生空间的运行原理:两种生物或社会的个体、群体生活在一起,就必然在空间上形成邻近关系,邻近之后就会产生空间联系,也必然会形成能量的交换与传输,最终形成依赖和互补关系,而且彼此之间是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图1)。
1.2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理论
1.2.1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实质
宗教社会学大师韦伯曾经认为佛教在诞生之日起便和社会经济行为保持着距离,是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迈克尔·卡里瑟斯认为佛教寺院与村落的关系实质是一种建立在寺院“功德施受”(merit)与村落“业报转换”(karma)的互惠共生关系。韦伯与卡里瑟斯的观点是相反的,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佛教文明在认知上的差异性。无论西方话语如何阐述寺院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藏区社会的宗教关系中,寺院、庙宇、教堂等空间单元与周围社区的人、家庭和组织就存在着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台湾学者朱文惠将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关系定义为“互惠共生”,表现在:信众慷慨地供应给僧人食物及生活资料,僧人则以“佛陀的智慧与教诲”为最佳礼物回报施主的“功德施受”,帮助施主“业报转换”,僧人与施主之间存在共生关系。
1.2.2寺院与村落共生空间的界定
把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空间化,便可表现为:以寺院这一宗教空间单元为核心,对周边居民区形成一定半径的信仰辐射区,以各种法事和仪式为内容,以僧人的流动为载体对周围居民区传输宗教信仰。同时,以信徒的流动为载体向寺院输送生存能量,有资金流、物质流等,双向互动的过程形成了寺院与村落之间供施关系的空间过程,这是一种宗教性共生关系空间。还有一种世俗性共生关系空间,即寺院通过对外出租土地、零售、贸易、旅游等经济形式获得维持寺院生存和发展的资本,寺院融入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这自然也离不开寺院周围村落与村民的参与,因此形成的是一种世俗性经济共生空间。对于地理学研究而言,可以从空间视角关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双向互动,从空间形态、空间相互作用、空间要素流动上寻求两者在“功德施受”与“业报转换”之间共生关系的机理(图2),这可以进一步完善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和内容。
2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2.1寺院概况
噶丹·东竹林寺(以下简称“东竹林寺”)坐落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乡书松村南永干顶东坡上,海拔3100米,临近金沙江,是典型的高原山地佛教寺院(图3)。它距所在乡驻地奔子栏23km,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也是德钦县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着“康藏名刹”的美誉。目前该寺在册僧人601人,其中转世活佛9人。
2.2村落概况
东竹林寺所在的奔子栏乡位于滇西北进入藏、川两省的咽喉要地,金沙江河沿岸,地处白马雪山脚,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交通重镇。奔子栏乡管辖奔子栏、达日、叶日、书松、夺通5个行政村,78个自然村,每个村落的海拔均在2500m以上(图4)。村落大多位于山谷、河谷的台地和交通沿线,地势结构陡峭,坡度大多在20°以上。因山地陡峭,平地与耕地面积小,为了合理利用土地,村落和民居多背山而建,集中在台地与河谷等难得的地势平缓地区,分布特征以若干农户组团聚集为主,卫星影像见图5。土地利用形态以低矮高原植被为主,河谷和台地的平地被人工耕作为农田,多为高原梯田,卫星影像见图6。该区域高寒气候特征明显,水资源条件和光热条件不适于农作物生长,只能靠广种薄收来维持一定的产量。畜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例较高,也是高寒山区的气候环境造成的。藏族占当地人口的95%以上,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当地居民生产以农牧业为主,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生计方式趋向多元化发展。
2.3研究方法
基于共生理论,采用田野调查方法,了解藏传佛教寺院与其周边村落的多尺度下的共生空间关系;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寺院僧侣与村民在布施与供养关系中的各项数据以及对寺院与村落关系的各种认知数据;运用3s技术,提取寺院周边村落的空间信息并建立空间数据库,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质性研究。它具有全面和深入的特点,通过收集丰富和生动的资料可以深入地反映事物形成、发展及变化的过程。质性研究方法已逐步为国内外人文地理学者广泛采用。同时还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综合收集、整理和分析民族志、民族史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口述史记录。对50多名访谈对象进行了口述史资料收集,得到大量第一、二手资料。访谈对象涉及村民、村干部、商贩、寺管会主任、喇嘛、主持、活佛等。
问卷法。发放100份问卷,回收率100%,经信效度检验后有效率为95.6%,每份问卷耗时60~90分钟。问卷对象的选择采用分层抽样法,根据不同年龄、民族、职业、收入和教育背景等因素合理分配问卷对象的比例。
3S技术。利用GPS定位测量和记录地理坐标并建立解译地物标志。采用ArcGIS10软件平台提取DEM影像的高程和坡度数据并转换成栅格图像,并根据Google Earth上遥感图像的坐标信息并把德钦县行政地图矢量化后进行配准,把寺院与村落以点状数据的形式叠加至高程影像中。利用ArcGIS10软件平台进行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得出村落对宗教虔诚度的空间集聚图。
2.4数据来源
(1)调查数据。社会经济主要来源于问卷,问卷按户随机发放,由于采用现场指导答疑的方式,问卷有效率为95%以上。辅助结合寺院管理部门与村干部提供的官方资料、新闻报道等其他资料。(2)地图数据。遥感影像来自Google Maps卫星图像、Google Earth截取图像(1:5000衛星图像、UTM投影、WGS84坐标系)等网络地图。矢量数据来自1:400万国家基础信息数据库中的云南省市县级行政区划矢量图,并根据乡级行政区划图进行配准。高程数据(DEM)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的高程数据,并依据乡级行政区划图和卫星影像进行配准和裁剪,最终建立研究区的空间数据库。
3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基础
佛教创立初期在教规上强调布施和化缘的生活原则,禁止从事商业行为和对百姓的贷息行为,不提倡与商贾争利。后来随着佛教群体和寺院空间规模和数量上的不断增大,对财富的观点不断演化,在中央与各级地方政权的支持下,藏区的僧侣逐渐成为社会上层阶层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聚敛财富,单纯的布施生计演化成强大的寺院经济体,其政治经济实力与地方豪强无异,这在佛教起源地的印度和中国的中原地区乃以至西藏地区所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
3.1寺院神圣空间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来自世俗的供养与寺院对功德的维护传播是藏传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基础通过供养制度的确立得到了保障。在原始佛教阶段,佛教成员上至佛陀,下至普通僧侣都恪守不从事生产,托钵乞食的生计方式,得到了统治阶级、贵族、商人、农民和小生产者的信仰并提供供养。他们认为对寺院和僧人提供供养,不仅可以得到福德,而且能得到历经劫难而不坠地域、不遇恶魔和畜生的保佑。因此,便逐渐形成了对寺院的供养制度,并在信教百姓中形成一种惯习。后来,寺院通过供养方式壮大了经济实力后,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并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我国藏区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地方政府的土官与流官为借助藏传佛教在百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巩固地方政权,便给予各级藏传佛教寺院及其僧侣各种神权,将寺院拉入封建农奴制的阵营,以宗教的名义一方面占有土地、林地和牧场等大量空间资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才得到改变,改革开放后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政府鼓励寺院与僧人积极地开展合法自养。
3.2恶劣自然环境使得藏民对宗教信仰产生强烈需求
云南藏区所在的滇西北地区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腹地,是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平均海拔均在2000m以上,生态环境脆弱,广大藏民的生计多以游牧为主,藏民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其对宗教有着强烈的需求。一般而言,农耕社会多处于海拔较低的平原及河谷地带,自然条件相对于牧区优越,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自然风险性小,因此生存的压力较小,人们对宗教的慰藉需求不那么强烈,对宗教的依赖程度不高,对寺院等宗教组织的需求也相对也少。而在青藏高原,游牧作为主要生计方式则很难有效抵抗高原低温多雪的环境,动植物存活率低下。往往一场不期而至的雪灾就有可能吞噬牧民所有的牲畜甚至导致一个家庭的破产,加上牧区低密度的人口分布,使得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比较松散,人际互动不频繁,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的极度缺乏,容易引发藏民孤独感和无助感,使得他们不得不从宗教中寻找心理慰藉。为了满足村落世俗空间保佑人畜两旺及平安和谐的要求,寺院神圣空间就起到了人生指引和心理慰藉的作用,除了固定的宗教祭祀节庆活动,广大信众在处理度过疾病、灾难、变故等人生危机时往往会选择到寺院神圣空间寻求宗教力量的帮助和解决。
3.3供施关系是寺院与村落关系的核心
在青藏高原地区,人们由于受恶劣环境影响所形成的神化价值观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高度依赖。在此基础上,宗教可以重新整合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寺院作为宗教空间对村落世俗空间的吸引力是很强的。村民们愿意承担寺院所有的宗教费用,如僧人的衣食、佛寺的修建、日常开销、宗教活动经费等,并觉得是村落应尽的义务。广大信教群众出于宗教情感和信仰诉求对寺院表现出的物化“奉献”是寺院神圣空间得以生存维系的原初动力和核心基础。寺院周边村落的村民一方面世代沿袭着对寺院供养的传统,寺院在他们心中是一种神圣化意象,即在极乐世界以外之地上的神圣空间。另一方面把希望从寺院这一神圣空间获得福祉与保佑,寺院成为村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一种持久牢固的法缘关系,被称为“供施关系”,在佛经古籍里村民被称为“施主”,寺院被称为“福田”。在“供施关系”里,以俗家信众、家庭或所属的群体为单位,对僧人和寺院施舍以资法缘,而僧人和寺院对信众则施以法利。施主与受施者、供养者与被供养者的相互施予实质上是一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交换活动。这种寺院神圣空间和村落世俗空间的交换活动的背后力量是双方共同对佛教的共同信仰。信仰是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如果离开了共同的信仰,这种交换关系便不复存在。在藏区,寺院与村落由于特殊的供施关系,从历史上就已经联结成稳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并延续到了今天。村落与信众的布施依然是当下寺院生存最稳定的来源。
4寺院与村落共生的衡量指标
处于青藏高原特殊地理条件下,衡量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指标首先存在两种共生方向,第一种方向是村落对寺院的共生,其目的是实现村民们功德施受和业报转换的宗教信仰需求;第二种方向是寺院对村落的共生,其目的是实现获得维持寺院生存发展的世俗利益需求,具体指标见表1。
4.1村落向寺院的布施与捐赠
由于佛教教义强调业报和功德,强调因果报应,号召信众积极为善,这是佛教社会关系的基础,因此藏区的广大信众一直以来从不吝惜向寺院布施,这是寺院生存发展的世俗圆圈。布施为佛教“六度”(一为布施,二为持戒,三为忍辱,四为精进,五为禅定,六为智慧)之首。布施最初是脱离了生产的僧人为生存到村落向百姓化缘和僧人向信众做法师后,信众向僧人提供斋饭,后演化为信众直接向僧人和寺院提供财物。东竹林寺周围藏族村落因地处高原,以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村民多以青稞、苞谷和牛羊输送给寺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信众,他们把以物为主的布施演化为对寺院的货币捐赠。
4.2寺院向村落提供的法事活动
寺院向村落提供的宗教服務分两种,第一种是宗教节日的法事活动。比如在每年的农历正月、五月、六月和腊月间是东竹林寺节日活动比较多的时期。在这个时间段里都会举行各种诵经法会给信众提供信仰支持和心理慰藉,而信众则会都会到寺院来转经和参加节日活动并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布施财物。第二种是日常礼佛活动:东竹林寺作为当地藏民的信仰中心、文化中心,日常对周边村民人流和物质流的集聚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许多村民至今仍保留着每天到寺院转经的习惯,都会顺便到功德箱给予布施。另外,村民信众家里出现葬礼、疾病等人生危机时,都会到寺院烧香布施祈求神灵的保佑。有的家庭则会把僧人请到家里做法事超度,可以在村落里临时搭建场地作为神圣空间。可见,神圣空间是可以移动的,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宗教服务。
5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多尺度特征
社会关系往往镶嵌在地方、区域和景观等空间实体之中并由它们所构建。一定的社会关系对应一定的社会空间,任何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空间基础上的,空间也能决定和重塑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既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空间组织、生长的重要依据,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空间的演化。藏传佛教是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宗教。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体,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宗教的世俗性与经济理性会更多地出现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演化,进而影响到了村落与寺院的社会关系,存在村落、僧人、村民和地方等多尺度的社会空间特征。本研究先对改革开放之前各个时期的东竹林寺与周边村落的共生空间关系进行概括梳理,然后参考共生衡量指标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落实宗教政策后的共生空间的特征进行分析。
5.1寺院与村落社会空间的演化
根据地方史料和对访谈对象的口述史材料的梳理,总结出各时期东竹林寺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表2)。经过历史上数次运动后,东竹林寺的政治地位与功能被降低,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靠政治手段控制村落与村民的生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藏传佛教在广大信众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其神圣空间得到强化,世俗性更强。更多的人,特别是来源多元的信众,从四面八方抱着各种世俗目的走进了寺院。同时,其世俗空间趋于市场化,已经融入当地经济转型和新型城镇化建筑中,以宗教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
5.2僧人的生计来源空间特征和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在落实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以后,“三自方针”得到推行和贯彻,如今的东竹林寺已经完全实现了“白养”,寺院通过群众自愿布施、法事活动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少数政府补贴来“以寺养寺”。在“自养,过程中与周边村落信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寺院与村落之间依然是共生关系。僧人的生计来源包括:家庭支持、念经法事、经堂所得、僧舍转让和社会保障等,在收入的空间来源上存在分异,一是来自寺院空间的收入,二是来自村落空间的收入。通过问卷调查,虽有寺院规定和僧人隐私的顾虑没有得到每位僧人的具体收入,但采用李克特式赋值分析法,通过僧人自己评分,大体上获得了生计来源空间分异的数据(图7)。
随着经济的发展,藏区村落的很多人已不局限于从事传统的农牧业,所从事的职业呈多元化发展,以旅游业、商业和外出务工为主。为了祈求平安和财运,越来越多的信众愿意从寺院把僧人请到家里来念经。另外加上平时农户家有红白喜事,甚至牲畜的出生或死亡都会请僧人来家里念经,给出的布施非常丰厚,少则几十上百,多则几千上万,特别是近几年富裕起来的农户布施的金额往往以万元为单位。由于外出念经得到的收入比在寺院里的经堂高,所以僧人也愿意外出念经,而且级别不同的僧人所得到的布施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年纪越大,也意味着级别越高,得到外出念经的机会就越多。30岁至40岁是僧人能否获得较多寺外村落布施的转折期。另外,由于僧人来源多是来源于附近村落,从小被送进寺院里当喇嘛,按照寺里的规定,寺院不负担僧人开销,各种支出都由其家庭提供。因此僧人家庭有义务提供财物给僧人生活、学习,甚至提供到西藏朝圣的费用。因此僧人家庭经济条件决定了其在寺院里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成年以前。只不过年纪越小需要家庭支持得越多,年纪稍长后,随着级别的升高开始有到寺外念经做法的机会,这才减少对家庭的依赖转型向“自养”。僧人25岁左右是其减少家庭资助的拐点,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需要家庭的资助就越少(图8)。
5.3村落宗教行为的空间特征和结构
东竹林寺周边村落的群众是世俗空间神往神圣空间的主体。居住地与寺院的距离、职业类型、收入水平、年龄等处于不同类型社会结构的信众与寺院的联系构成了村落宗教行为的空间分异特征。以信众去寺院进行转经、烧香和吃斋饭等宗教行为的频率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村落对寺院的共生空间特征和结构。
5.3.1村落对宗教的虔诚度的空间特征
根据地域分异理论,不同村落、不同家庭以及不同的个人对宗教及其寺院的虔诚度是不同的。这种虔诚度具体体现在村落对寺院的参与度上。基于实地入户调查后得到的进一步认识,本研究尝试建立东竹林寺周边藏族村落对东竹林寺宗教活动参与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编制李克特分级赋值量表给村落的各指标打分赋值,最后进行测度和统计。其中把信教人口属性、参加寺院宗教程度、布施程度、对寺院的认同程度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项目,然后再进行多维分类(表3)。不同的村落依据这个指标体系各项指标累加得出对宗教虔诚度的计量值,通过ArcGIS10软件中Spatial Analyst工具集成的Kernel Density工具对村落的寺院虔诚度进行核密度分析,分析村落宗教虔诚度的空间聚集特征。
核密度分析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在空间分析中常用来分析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趋势。其运算原理是以研究区样本的点状要素为圆心,依靠搜索周边半径所产生的圆并计算栅格单元值来分析。圆心处和离圆心近的区域,其栅格单元密度值最高,离开圆心越远,密度值越低,并呈逐步递减趋势,到边界处密度值为0,也就是最不集聚的区域。在本研究中,鉴于滇西北藏区地广人稀,地形复杂,交通不变,村落之间相隔较远的特点,在ArcGIS10中设置搜索半径值为1000m,栅格数据输出像元值为500m。
其公式表示为:
为统一指标,消除量纲,对测度获得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统计各个村落对寺院的虔诚度。经过核密度分析后,根据其地理事件可以发生在任何空间位置上,不同位置上发生的概率不同,同一或相近事件的点越密集,发生地理事件概率越高,反之越低的原理,利用ArcGIS10的空间分析工具模拟生成东竹林寺周边村落对东竹林寺的虔诚度核密度图(图9)。可以发现,东竹林寺周边村落的虔诚度以东竹林寺为核心,由里向外呈圈层式格局。靠近东竹林寺的村落由于地理条件的便利,参加寺院活动次数较多以及布施较多的缘故成为虔诚度最高的区域,成为寺院和村落互动关系的核心区域即宗教吸引力的核心区域,越往外,随着与寺院距离的增加和高程地形的影响,核密度值也逐渐减小,村落对寺院的虔诚度逐渐降低。结合距离测量工具,发现寺院以外3km范围内的东北和正南方向是核密度最高的区域,该区域内的村落对寺院虔诚度最高。寺院以外3~6km范围内的村落为宗教吸引力的次核心区域,而且虔诚度区域不平衡,东竹林寺东面村落的虔诚度要高于西面的村落,这与东面村落海拔相对较低,可达性比西面村落要好有关系。寺院周边6km范围内的村落其核密度值都较高,虔诚度也处于高值发展,这与宗教旅游发展带动周边村落的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产业有密切关系,村民致富收入增加进而向寺院布施的内容与价值相应增加有关系。寺院向外6km以上的区域核密度值不高,村落对寺院的虔诚度维持在一个中低水平,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村落离寺院距离较远,生态环境决定了只能从事传统农牧产业,导致了去寺院的次数和向布施的内容相对较少。但需强调的是,离寺院较远的村落的核密度值低,这里只是根据地理空间的分异做出的一种解释,这不能说明那里的村民对所信仰宗教的忠诚度不高,在藏区社会,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人们对宗教的忠诚度不是单纯依靠与寺院的距离和布施程度来说明的。对很多藏民而言,即便是去寺院的次数不多,布施程度不高,但丝毫不影响其对宗教的忠诚。
5.3.2寺院对村落的吸引力圈层
根据村民居住地离寺院的远近不同调查每月到寺院的频率,得出的村民的宗教行为基本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和邻近效应规律:越是邻近寺院的信众对于参加寺院宗教活动的频率越高,在空间上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到寺院参加宗教行为的频率就会减少:居住在离寺院0.5km半径范围内的村民,参加宗教行为的频率高达95%,然后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一直到距离寺院8km以外的地区到寺院参加宗教行为的频率只有28%,通过距离与频率的关系表现宗教吸引力的圈层。在距离寺院0.5~3.5km之间的范围内村民参加宗教行为的频率都在55%以上,这说明这个范围内是宗教的最大吸引力范围。这不能说明离寺院远的村民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度不高,而是由于距离、地形、交通工具、其他工作忙碌等原因导致了村民随着因居住地离寺院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了到寺院的宗教行为(图10)。
5.3.3不同职业的村民参与宗教行为的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寺院产生的宗教吸引力所表现出的地理学效应和近年来宗教旅游的升温及带来的农牧民生计转型的影响,围绕着东竹林寺衍生了许多新兴职业,形成了新的职业分布格局,见图11:离寺院最近的居民,半径在0.5km范围内的,也就是处于宗教吸引力核心区的居民转型从事与宗教旅游的行业,比如手工艺品销售、佛具销售等;其次处于宗教吸引力也就是离寺院1.5km范围内的村民主要从事与旅行社有关的行业,如餐厅、宾馆等;处于离寺院2.5km左右范围的居民多从事宗教与宗教旅游衍生出来的行业,比如手工业制造、食品加工、运输等。处于离寺院3.5~6km左右范围的居民多从事農业,种植青稞和苞谷,主要供给寺院和周边村落的粮食需求;处于离寺院6~8km及以外地区的村民多从事畜牧业,产品也主要是供给寺院和周边村落。
通过图12可以看到离寺院最近的宗教旅游核心区的村民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还是高达83%,因为在离寺院0.5km左右的范围内参加宗教活动确实很方便。而在离寺院1.5~3.5km的村民参与宗教活动的比例明显下降,这可能是忙于做与旅游有关的生意,无暇从事宗教活动。这时是在许多民族和宗教地区经历现代性转型时常见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少数族群越来越倾向于理性,脱离了传统农牧业生产的农牧民不再受制于恶劣天气、地质灾害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宗教的热衷度有所下降。而离寺院6km以外从事农牧业的村民参加寺院宗教活动的比例比较高,高于从事旅游等第三产业的村民,这说明传统农牧业还是容易受到天气、灾害、疾病疫情的影响,为了祈求生产生活平安,村民们会选择经常到寺院里转经、烧香等,因此该部分村民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比较高。
6结论和讨论
6.1结论
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共生关系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寺院从绝对特权的神圣空间走下神坛,与村落有更多平等的交流互动。村民与村落的宗教行为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与多元性。在提倡寺院积极自养的政策环境下,宗教服务的输出、传播、接受与世俗物资的交换供给是寺院与村落共生关系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在宗教旅游等产业新样态的影响下,村民对寺院的虔诚度在空间上表现出圈层特征与密度差异。具体说来,村落离寺院的远近与生计方式的差异会影响村民的宗教行为,在产业分区结合叠加不同职业的村民可以看到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离寺院较近的村民在对寺院宗教活动的参与性上较高,这体现出了地理邻近性的效应。但距离寺院较远且从事传统农牧业的村民对寺院活动宗教活动的参与性也比较高,这说明对于宗教氛围浓郁的藏区社会,宗教要素的吸引与流动并不一定遵循距离递减规律,藏传佛教寺院的宗教吸引力不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相反是现代性程度越低,地理环境越恶劣,离寺院距离越远的村民的对寺院宗教活动的参与性越高。远离乡镇中心的边缘地区其从事传统农牧业的村民由于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较小,对宗教与寺院的虔诚度反而比处于乡镇中心,从事旅游服务贸易的村民要高,这与他们所在地理环境有关,较远的距离和高山、河流等空间阻隔了现代性的植入,使得当地村民有更强烈的宗教依赖性,进而导致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到寺院参加宗教活动。因此要注意的是,村民到寺院的次数少固然有距离远近、路况等可达性因素有关,但是到寺院的次数少并不意味着没有从事宗教活动,或是对宗教的虔诚度有所下降,换句话说,寺院对村民的吸引力不能以距离和到寺院的次数来简单衡量,这是区别于一般空间主体的特别之处。可见,地理学的邻近效应与距离衰减规律在宗教社会里表现出了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样态。
6.2讨论
空间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先决条件,又是人类行为塑造的社会产物。空间与社会之间是流动的、过程化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些颠覆传统空间观念的思想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寺院作为一种神圣空间似乎不是那么纯粹的,有着深刻的世俗化层面,周围的村落也表现出高度神圣化的场域,这说明村落世俗空间被神圣空间的浸润,也说明了寺院对村落的依赖性,于是寺院与村落便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在实践形态上表现为满足了基本物质和不追求过度的可持续模式。寺院与家庭、个人的共生关系体现着宗教服务与物质供养的交换,抽象的服务与具体物质形态之间的互惠,构成了寺院与村落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主题。互惠交换的要素有物质、资金、宗教仪式、宗教服务等,也有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复合交换,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也包括人与神之间的交换。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在其经典著作《礼物》中所谈到的食物、财物、土地、护符、女人、儿童、劳动、服务、圣职都是可以交换的。从食物到身体的可交互,意味着无论在氏族之间、个体之间,还是在性别之间、代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既关涉物质也关涉精神信仰方面的持续交换。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建立在各种世俗要素与神圣要素流动的基础上的共生关系便是东方宗教社会对礼物交换的写照。被赋予神圣意义的要素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通过仪式(各种仪式和布施活动)这一特殊的礼物形式流动在寺院和村落之间,越过了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界限阻,使以寺院与村落为代表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成为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藏区与寺院之间又原来的单纯香火关系,变成布施关系,再变成世俗关系,再变成经济关系,最后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图13)。因此,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本质是交换与依赖,即存在“精神与精神”、“精神与物质”、“物质与物质”、“物质与精神”这四种形式的交换与依赖。在寺院与村落這两个空间主体上,都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特征,两者不是对立与分离的关系,而是互动与融合,互惠与交换的关系,它们共同适应着社会变革也形塑着社会变革,这构成了藏区社会空间结构的基础,是人一地关系在宗教社会的特殊体现。
在我国地域广阔的藏区社会,宗教稳则社会稳,社会稳则国家稳,也只有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才能有宗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藏传佛教寺院与周边村落的关系已经浸润到藏区社会生活的常态,寺院与村落的共生关系是否和谐关系着藏区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很有必要对这种共生关系进行理性分析并加以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学应该为以藏区为代表的宗教社会的和谐稳定建言发声,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空间治理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