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吹进深谷
张宪光
一
上学路上,有一家兼营五金、文具的书店,位于公社大院前那条乡里唯一的柏油马路北侧。店里仅有两个玻璃书柜,一个摆放小人书,我从这个柜台里陆续淘弄来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另一个摆放其他图书,记忆中我的第一部个人藏书—两册一套的百科读物—就是从这儿买的。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我常在书店里逗留十来分钟,看看是否又来了新的小人书,柜台里有什么新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天巡视那两个柜台,是我的无上快事。多年后返回故乡,发现书店水泥勾缝的石墙坚硬如故,而长长的一排门面已经废弃,木门上红漆斑斑驳驳,弥漫着朽败的气息,几位漂亮的售货员自然也不知去了哪里。

《平原游击队》电影剧照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坐落在小镇西北角,课桌多用土坯垒成,自然也没有电灯。上学第一天的情形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年级班主任和她的女儿。班主任姓胡,是位民办教师,一直未能转正,后来被辞退了。她住在我们村里,每天上班总带着她那个安静的女儿,我们在那里咿咿呀呀地读书或者默默地做算术,她女儿就坐在教室里玩耍。大多数情况下,天还没亮,我们早早地带着煤油灯去上学,与其他同学比着看谁到得早。冬天的早晨,穿过寂静的村庄,偶尔有几声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或是莫名的群吠,心脏也因之而起伏蹦跳。在阒黑的早晨、空旷的校园里,读书的声音传得很远,像气息微弱的戏曲拖腔。煤油灯散着黑烟,等到太阳出来,一个个鼻孔都被熏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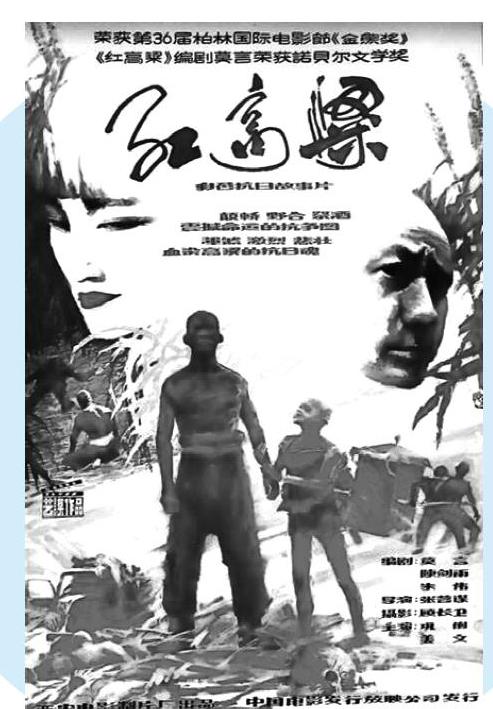
《红高粱》电影海报
那时,学校里有位副校长,每天背着手在校园里威严地转来转去,那严肃的目光与骚动的学童形成有趣的反差。学校里除了本村的同学,还有一些来自邻村的孩子,比如杨楼村的许多女孩,都是茂字辈的,叫杨茂香、杨茂兰、杨茂花什么的,这群“杨门女将”一天到晚叽叽喳喳,搞得教室里乱哄哄的。不知什么原因,学校里竟允许小贩进校卖东西。经常有个老货郎到学校里来,棉衣棉裤,扎着绑腿,那模样就像电影里化装进村的特务。不过他那辆手推车简直就是个万能商店,卖的货多种多样,有哨子、风车、跳绳、橡皮、本子、沙包……凡是你能想到的,他这儿都有。他还卖汽水,用糖精兑上凉开水,几分钱一杯,体育课流了一身臭汗,来上一杯汽水,那时是最爽的事儿。
学校里流行的游戏,有斗杏仁、磕锡块、弹溜溜球、扔沙包、推铁环、搰纸包等。所谓斗杏仁、磕锡块,无非是把东西放在地上几厘米见方的小坑里,谁用杏仁、锡块把坑里的东西投出来就算谁赢,有时候一下子投出,可以把坑里的所有东西都赢下来,甭提多神气了。我当时特别想有一个铁环,可以从家里一直推着去上学,然而始终未能如愿。当时最流行的是打纸包,我们那儿称为“搰纸包”(“搰”方言读作“忽”),即把纸叠成四方的样子,扔在地上,看谁能把对方的纸包翻个个儿。叠纸包,最好用厚实的牛皮纸,不易被掀翻,却不难将对方的纸包给搧飞了。
放学后,便是东家窜西家跑。晚上的游戏,是和村上的孩子去打坷垃仗。小孩子都拉帮结派,以生产队或村子为单位,跟对方互相投射石头土块。那是很危险的游戏,俨然港片中黑社会火拼。一个比我年长的很有名的家伙,被石块打落了两颗牙齿,合了“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意思。还有就是一群孩子分成不同的队伍打仗,一队红军,一队白军,当然通常都是红军取胜。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在一个厕所里站岗,站在那里半个多小时,闻着一阵阵熏来的臭气,现在想来真是有点傻。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位姓李的老师,年轻,热情,课余喜欢给我们讲“一双绣花鞋”,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破案故事,特别过瘾。相反,所读的书都跟高玉宝、刘文学、小英雄雨来、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邱少云等不同年龄的英雄模范有关,那时的书籍除了斗争和献身,没有其他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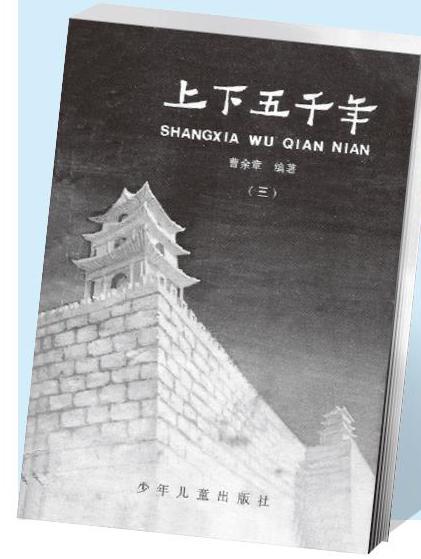
《上下五千年》(第三册)曹余章编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版
二
书店的侧对面,是家铁匠铺,父子兄弟三人浑身黑黝黝的,一天到晚挥舞大锤小锤,铿铿锵锵,火星四溅。后来读到嵇康与向秀“偶锻”的故事,总让我想起那个场景。书店前面有片空场地,是放电影的地方,两根电线杆扯上銀幕就是一个剧场。一听说晚上有电影,村子里的小孩子便开始拿了白粉笔占地盘,下午三四点钟就聚在附近开始等待。傍晚时分,家家拿了小板凳,在自己画的白线内就座。就是在那段马路上,我接受了最早的电影教育,看的是《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节振国》《地道战》《地雷战》《烈火中永生》《黑三角》,等等。还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党》,当时还小,故事情节看也看不懂,只是感觉场面吓人。
小镇的第一座电影院诞生于一九八○年前后,是一座露天影院,有三四百个水泥板做成的简陋座位。记得在那里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冰山上的来客》,虽是老片子,还是吸引了很多的人,几乎场场爆满,是当时小镇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过那种景象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书店东侧建了一个室内电影院,由公社礼堂改造而成。室内的木板座椅要比室外的水泥板舒服多了。我就是在那个电影院看了风靡一时的《少林寺》,那种体验是颠覆性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逃学去看《少林寺弟子》,翻墙回来后不敢进教室,因为里面教导主任正大发雷霆,于是我们几个又偷偷翻墙回家了。农闲时节,那座电影院也经常演戏,鱼台、沛县乃至河南、河北的剧团都来演过,最赞的是《对花枪》里扮演姜桂枝的那个演员,一口气唱上四五十句,字正腔圆,底气浑厚。我之所以对民间戏曲多少有些了解,并不是读书得来的,全是在戏台下蹭戏蹭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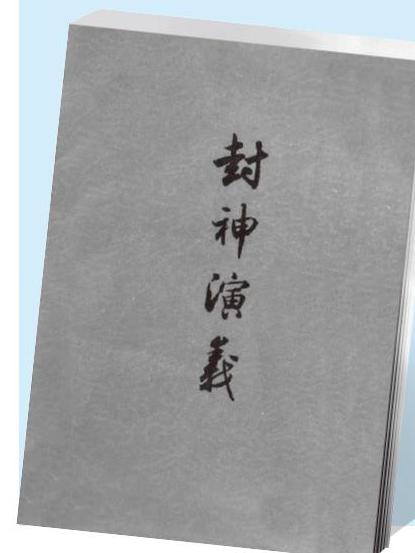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那座电影院热闹了十來年,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在发挥它的余热。每年春节前后,全镇子的青年男女穿着最好的衣服来看电影,是当时乡村男女交往的一个重要方式,其作用大概和少数民族的篝火晚会相似。那时我也曾跟在一帮死党后面,骑着自行车招摇过市,看他们如何泡妞,如何与其他村子里的年轻人斗嘴,那情形跟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里的情景差不多。一个人从小读怎样的书,看怎样的电影,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当时虽然有越剧《红楼梦》这样非主流的片子,但对小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小孩子容易在英雄故事中入戏,敌我对立的认知模式,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种子,直到现在似乎还在我心里生长。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的电影思潮起来了,《人生》出现了,《黄土地》出现了,《红高粱》出现了。
三
一九七四年搬到小镇后,我家又搬了两次。第一个家位于大队部的楼房边上,一排四间北屋。那幢楼房,大概算是镇上最高的建筑,原来是镇子上一个大地主的家产。楼前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株粗大的马缨花—后来我知道那种树也叫合欢树,孤零零地长在沙砾之间,每到六七月间,树冠上满是粉红的花朵。母亲有时候也会到那里去,如今一想起那棵树来,就想起她在树下捡拾石块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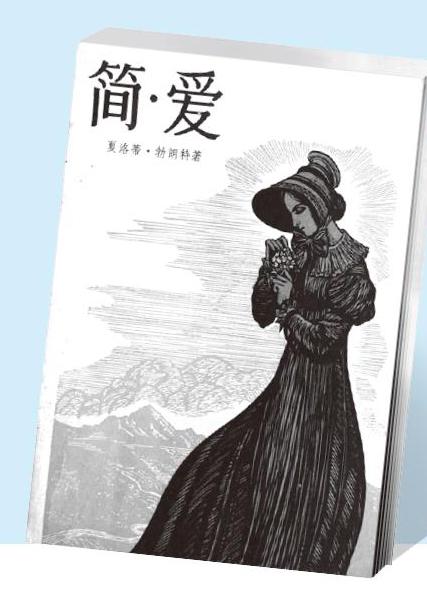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树,各种各样的树,似乎是那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镇最富有诗意的东西。我家的院子也很大,院子里有十来棵粗大的梧桐,高高的树冠有二三十米,每到夏天,枝叶鲜绿,浓阴覆地,蝉声长鸣,雀鸟啁啾。我曾在那棵最大的梧桐树下一口气读完《上下五千年》《朝阳花》,也曾把所有的梧桐树爬了个遍,也曾去掏过树上麻雀的窝……除了梧桐,便是三三两两的柳树,一排一排的杨树,还有在僻静处孤独站立的榆树,挺着尖刺的枣树,它们就是我除了书以外的友人,孤独的友人。
给我带来快乐的,除了树,还有蝉。一个儿时玩伴家里杀树,一棵大柳树,连根刨起,很多人跑去看热闹,只见那硕大浓密的根系之间爬满了蝉的幼虫,在鲜活的泥土中笨拙地爬着,场面非常壮观。在树的根系里,原来有这样一支神秘的军队存在。据古书载,蝉的别名有三十多个,其幼虫却没什么学名。古人不清楚蝉的繁衍过程,故认为蝉是由蛴螬(金龟子的幼虫)或蛣蜣(屎壳郎)蜕变而来,《论衡》称蝉之幼虫为“复育”,或作“腹育”,均不得其要。鲁南一带,把蝉的幼虫叫蛣了龟(此三字向无书面语,姑以己意揣测),大概是蛣蜣和知了的混音,有的地方称为爬叉,自然还有其他的异名。
每年六七月份的傍晚,我们就会拿上一个小铲子,去小树林里挖蝉。时间最宜于雨后,地点最宜于柳树林、榆树林或杨树林。柳树多蝉,古人有“高柳咽鸣蝉”的诗句,早已窥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捉的时候,铲子多数情况用不上,因为它即将出洞时,洞口的土极薄,轻轻一戳,就可以把它拎出来。一晚上,可以捉上一大碗。一是好吃,用盐腌了,洗净,用油炸,皮焦里嫩,最能解馋,亦是大人佐酒佳肴。在物质匮乏年代,是不可多得的营养菜。二是好玩,捉来以后,放在盆子里,看它蜕变。然而它蜕变的速度实在太慢,谁也没有耐心把整个过程看一遍。对于蝉的阳光下的一生,鲁南有句概括的俗谚—喝风倒沫十八天,是不确的,其实际寿命约为一个月。如法布尔《昆虫记》所说,为了这一个月阳光下的生活,它们要在黑暗中作四五年的苦工。最恐怖的是,有些蝉要在地下生活十七年,才有机会爬上地面。
小时候听蝉,从不会把它叫作歌唱,只感觉到烦躁。暑天小睡,蝉声喧扰,常感不耐烦,遗憾自己没有承蜩老人的绝技,不能捕尽那些讨厌的家伙。中年听蝉,不知不觉地和古人有了同感。那蝉声,亢直单调,居高送远,仿佛一篇《感士不遇赋》—它们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才有机会一展歌喉,一纾忧愤。今人听蝉,自然知道蝉声的嘹亮,源于不偶的苦恼,而古代失意的士人,想当然地以为它餐风饮露,五德兼美,并与自己的身世比附。曹植《蝉赋》说它“声嗷嗷而弥厉兮,似贞士而介心”,骆宾王则借蝉来表达“无人信高洁”的苦闷。诸如此类,在在皆是。旅居沪上多年,每次听到蝉声,便想起儿时捉蝉的往事。

王小妮《1966年》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周国强编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我家后来搬到了公社大院东侧,门前是一条宽不足两米的小巷,我就是每天从那里出发,约上一个患有侏儒症的同学一起上学。前面一家人姓闵,宅第高旷,院子也大,人们都说那个院子本属一户大地主,后来被赶走了,于是闵家人就一直住了下去。东边一家也是我的一个同学家,该上学的时候喊一声,于是便一同上学去了。吾乡读书风气不盛,从未见谁家里有个书架,更不用说藏书了。我们能找到的书很少,大概从初中开始读了《封神演义》《七侠五义》那类小说,半懂不懂的,连浅阅读也算不上,只是整天想当侠客。在那个院子里没住几年,父亲退休了,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村子东南角的一个大院子。那一年,我正好上初中,大街小巷都在放《霍元甲》。
搬到这个家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离田野更近了,离大桥、小桥更近了。从小桥到大桥的一段小路,也曾是我的乐土。我曾在那些小河沟里捉过鱼,曾在小桥上把黏土塑成长方块,然后雕刻成手枪,涂上黑漆,也曾在河边垒上土灶烤地瓜。这里,还有我熟悉的蚂蚱们,低吟的蟋蟀,以及秋天的高音歌手蝈蝈。有一年初秋,我回乡省亲,却几乎看不到蟋蟀、蚂蚱们的踪影(大概是农药和除草剂使然),只有那远远近近的蝉声从河沟边的高高的杨树上传出来。那蝉声,开始是独奏,接着是合奏,一阵高过一阵,而后复归于沉寂。另一个变化,也许在我的心里引起了更大的影响—我发现,我们学校的校花就是隔壁家的女孩。她长得瘦高个子,并不是很美,却有着一种天然的风流,像时髦的林黛玉。学校里的混小子们看了《神女峰的迷雾》,便给她取了个“靓猫”的外号。除了歌唱得好,隔三岔五还会穿出一身震撼性的衣服,什么喇叭裤、灯笼裤、牛仔裤,全是她一人独领风骚,其他人只有膜拜、嫉妒的分儿。她是学校男生的公共女神,要说哪个男生没有暗恋过她,没人相信。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家早已搬走,她的消息再未听闻。前一阵回家,发现那女孩曾住过的房间已拆除了,变成了我家的狗窝,旁边荒草萋萋,杂树生花。就是在那个房间里,我和她曾经一起共读过《茵梦湖》,共读过《简·爱》、雪莱的诗,交换过各种各样的文学杂志。

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四
王小妮有一本《1966年》,寫一个小女孩一九六六年冬天的私密记忆。十二岁的女孩,在锅炉房里发现了年轻的锅炉工留下的书包,里面有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抄着这样的诗句:“啊!这就是我曾爱过的人/我火热的心曾为她那么紧张/你的气息有怎么样的火焰/殷殷的目光怀着多少情意……”这些灼热的字眼把小姑娘吓坏了,把全家人都吓坏了,于是那些普希金的诗,那些书,那些照片,全被扔进了最安全的坟墓—火炉。那个锅炉工再来的时候,女孩的爸爸告诉了锅炉工真相,然后把他赶走了。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小女孩的一九六六年记忆,那就是恐惧,那种带着强烈震惊感的恐惧。小女孩如是,大人如是,书包里装着普希金的锅炉工亦如是。那个年代容不下这样的诗句:“我过得孤独而忧郁/我等着,是否已了此一生。”那么,如何来描述我们记忆中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呢?恐怕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词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那儿似乎是由电灯拉开帷幕的,然后是《外婆的澎湖湾》和《霍元甲》。忽然之间,校园里所有的人都在哼唱《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童年》,哼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还有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因此,或许可以说八十年代初期是流行文化开始取代政治文化的时代,也是诗性的年代,特别是后半阶段,几乎是诗人为王。十多年前,查建英编了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的人都是在八十年代特能折腾的主儿,除了阿城、北岛,大都是五○后。他们是城市文化英雄,直接参与创造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历史,相比之下,属于草根一族的乡村孩子的八十年代则“贫寒”得很,偏僻呆滞的小镇,荒芜的文化土壤,既没赶上上山下乡,也没赶上恢复高考,总之是处在历史夹缝里的沉默一代。也几乎没读过什么像样的书,别提什么卡夫卡、博尔赫斯,连《人·岁月·生活》也是后来才晓得。唯一幸运的是家里有不少《诗刊》《收获》《人民文学》《散文》《十月》等文学刊物,全是我那“不务正业”的大哥订的(他现在是盆景名家,创作的水旱盆景曾得过全国金奖)。阿城的《棋王》、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是从那些刊物上看到的,但也只能生吞活剥地读上一些,根本不能消化。记得一九八五年前后,曾印过一种诗歌日历,每页一首诗,全是杨炼、舒婷、北岛、江河、顾城那些人的诗,一边读,一边抄,一边与嗜好这口的人交流,一边开始写,一边开始办校园小报。那时候还不太能体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含义,只是莫名地觉得好。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走吧》:“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那种酷酷的自以为是的腔调,到现在也忘不掉。虽然朦胧诗以及张贤亮等人的小说本身也不富厚,但却够我们这些先天不足、营养贫乏的人啃上好一阵子。
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二十块钱,我是好省歹省,省出六块零五分买了一套《红楼梦》,后来又花几块钱买了两册查良铮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可迷恋的还是朦胧诗。我曾把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抄在一本大笔记本里,留在老家,后来竟丢失了。其实自己的思路是那样艰涩平庸,根本不是写诗的材料,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感觉上像丢了一段青春似的。进了大学以后,对诗的爱好也没有停止,打牌、睡觉之余,便去图书馆读些西方现代派的诗歌,稍稍知道一点波德莱尔、庞德以及弗罗斯特的诗,便是那时胡乱读书得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确立后来精神走向的阅读经验。
我的大学同桌是个才女,也非常喜欢诗,经常交换诗集看。记得那时我买过一本《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和一本学院派诗选,借给她看,她竟然一边读,一边把两本书抄了一遍。那个时代常有这样的事儿。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小气,直接送给她有多好。这些诗集,有一些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弄丢了,没丢的还有三五册,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偶尔看到它们,便让我想起那些和诗有关的记忆。“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我们曾经和诗一起寻找过“生命的湖”,也一起“敲击着暮色的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给我的,除了诗,还有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还有叔本华、尼采,还有《诗人哲学家》和《诗化哲学》。我不喜欢尼采,喜欢叔本华,也许天性如此吧。相比之下,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心理分析一派。这三个人中间,只有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比较好懂,弗洛伊德和荣格都不好读。当年买的那册《精神分析引论》,以及荣格的《人类及其象征》,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架上,从来没读完过—有些书也许是用来缅怀的,不是用来读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出了许多西方哲学名著,不过对我们这些非哲学专业的人来说,和诗联系紧密的《诗化哲学》更受欢迎。除了政治批判,原来还有心理分析、潜意识、本我这些玩意儿,原来还有一种纯粹思辨的、诗意的生活方式存在,这个东西朦朦胧胧中对我们这些人震动特别大。至于是否能够完全吸收那些书的内涵,则是另一码事。虽然八十年代的哲学热,大多是被五四一代嚼剩的东西,在全新的语境里重新被发现、被重述,还是有些横空出世的感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浓缩了诗、小说、哲学的诗意时代,奠定了很多人的精神基调,但它很短暂。收尾的两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电影《红高粱》和贾平凹的《废都》,一个元气淋漓,一个颓废迷惘。八十年代总体上是理想主义的、元气淋漓的,但同时也埋藏着走向迷惘与孤独的种子。毕竟诗与哲学的时代是脆弱的,不是散文时代的对手,更不是技术时代的对手,一遇到商业化、全球化,自然就退败得稀里哗啦。这是必然的,也是悲壮的。我想许多在八十年代度过自己学生时代的人,身上总是有些理想主义的气质,内心总会沾染上忧郁、孤独的东西。里尔克的诗句写得真好:“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阴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热情、理想与迷惘,很多是体现在书信里的,它们就像一枚枚翻飞的落叶,被吹进了记忆的深谷。与八十年代相伴的少年旧事,也如落叶一般,堆积在渐渐模糊的路上。但歌音袅袅,依然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