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塘和《梅塘之夜》
余中先

梅塘的左拉故居
二○一○年秋末的一天,我和三位法国朋友前往向往已久的梅塘(Médan)。
从巴黎的圣拉撒路(Saint Lazare)火车站出发,乘坐前往芒特-拉若丽(Mante-la-Jolis)方向的郊区短途火车,不用半个小时,便到达西郊的维莱纳(Villennes)车站。下车后步行,沿着塞纳河边上的一条公路北行十来分钟,就到了小小的梅塘镇,大文豪左拉(?mile Zola,1840-1902)的一处故居就在那里。
左拉本来在巴黎是有房子的,他为什么要搬到远郊的梅塘来住呢?
左拉少年时,因家境贫穷,不得不早早独立谋生,并在艰辛的生活中坚持阅读和创作。他生活拮据,付不起房费,总是没完没了地搬家,一直到他的经济来源得到保证后才不再频频挪窝。

左拉(1840-1902)
一八七七年,他的小说《小酒店》出版成功,带来的收入使他几乎一夜暴富,终于有能力在巴黎西郊的梅塘买下一幢漂亮的小房子,连带一小块田地。后来,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小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公众欢迎,他也同时不断扩大家产,逐步买下别墅附近的田产。
左拉在梅塘的居所环境清净,楼前是一片花园,花园前不远处便是塞纳河,而火车线也就在花园和河畔之间穿过。这里环境清幽,不像巴黎那样喧闹纷杂,适于左拉安心写作和生活;同时,它距巴黎又不是很远,适于他余暇时接待朋友。
“你们知道这所房子的大门是为你们敞开的。你们什么时候觉得它讨你喜欢了,就过来;或者如果你们闲着的话,每天都可以过来。”左拉给朋友埃尼克的信中这简单的一句话,体现出了梅塘的这所房子的另一项重大功能:接待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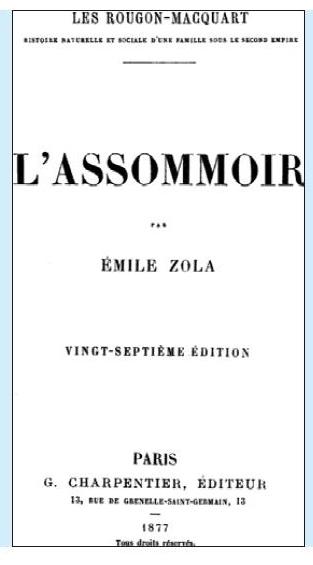
左拉小说《小酒店》1877年初版本扉页
在梅塘这地方,左拉的建造欲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七九年期间,他先是在只有两层高的小屋紧边上,建了一个正方形楼房,有四层楼高。莫泊桑后来提到这幢新房子时,曾不无讥讽地说:“这简直是一个巨人在拉着一个侏儒的手。”这个呈正方形的配楼,被称为“娜娜楼”,里面包括书房、厨房、餐厅、洗澡间。书房位于顶层,除了大橡木的书桌之外,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左拉花一千二百法郎建造的石头壁炉,以及壁炉上方墙上他的座右铭—“无一日不写一行”。
后来,一八八六年,左拉又在老房子的另一边上,造了一栋棱柱形三角顶的房子,起名为“萌芽楼”,因为盖房子的钱来源于小说《萌芽》的稿费收益。里面包括弹子房、卧房等等。
房子的建造和装修自然来自左拉的想象和设计,但平时的监工和此后的维护,则是左拉夫人的功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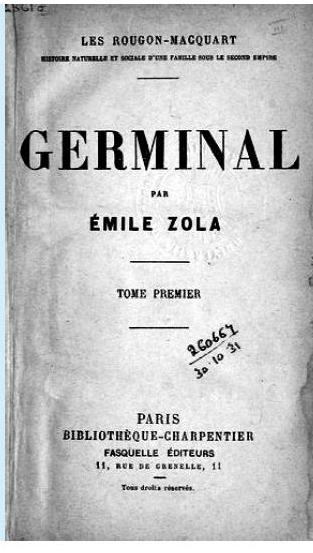
左拉小说《萌芽》1885年初版本扉页
当时,正当一大帮工人在左拉夫人的监督下辛辛苦苦地建造房子时,左拉则跟朋友们在客厅中高谈阔论。当然,对房东左拉先生几近疯狂的建造欲,文人朋友们不免要讽刺一番,他们嘲笑他在建筑中滥用行吟诗人风格,嘲笑那些装饰用的百合花图案、仿古的家具,尤其是浴室中四面墙上从地面一直贴到天花板的花里胡哨的瓷砖。
梅塘,毕竟是左拉文学生活中经济成功的标志,也是他后来安逸的物质生活的象征。左拉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幸福的日子,尤其是,他后來与情人雅娜·罗思罗(Jeanne Rozerot,1867-1914)长年住在这里,保持了一段长久的私情关系。众所周知,左拉夫人不能生育,而雅娜·罗思罗与左拉生下了一女一子,德妮丝和雅克。
不过,到了一八九八年,左拉的安逸日子就到了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一个为正义和自由不懈斗争的人,左拉积极介入了当时震撼了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随着他呼吁正义的战斗檄文《我控诉》的发表,随着法庭对他的审判,随着他不得不流亡英国,左拉远离了梅塘的那种悠闲日子。最后,他的家庭经济也陷入了困难,几乎到了要与梅塘的家产分离的境地。
一九○二年,左拉从梅塘回到巴黎,准备写他“四福音书”中的最后一部,但第二天就被发现死于煤气中毒,年仅六十二岁。不知这所谓的煤气中毒是事故,还是阴谋。
告别了梅塘的同时,左拉也就告别了人生。左拉死后,他的夫人把梅塘的家产捐赠给了公共救济事业局。一九八五年之后,左拉之友协会获得了这些家产的一些股份,在此开辟了左拉博物馆,供人们来这里参观。

1898年1月13日,左拉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发表在《震旦报》上
在法国文学史上,梅塘有着一个十分独特的地位,这一地位是跟一部叫《梅塘之夜》的短篇小说集不可分开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群拥戴“自然主义”的作家聚集在左拉周围,结成了所谓的“梅塘集团”。这些作家是阿莱克西(Paul Alexis,1847-1901)、于斯曼(J. K. Huysmans,1848-1907)、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塞阿尔(Henry Céard,1851-1924)和埃尼克(Léon Hennique,1851-1935)。他们都是文学青年,比左拉年轻十来岁,没什么名气,可说是左拉的“粉丝”。同时,他们气质相近,情趣相投,既有共同的爱国之心,又有相同的哲学倾向。谈到这个小团体时,莫泊桑曾经这样说:“我们并不奢望成为一个流派。我们只是几个好朋友,一种共同的尊敬之情让我们相遇在了左拉的身边,而后,性情方面的一种亲和力,对种种事物的一种相似情感,一种相同的哲学倾向,让我们团结得越来越紧密。”
左拉那时刚在梅塘买下房子,第一栋“娜娜楼”正在建造之中。莫泊桑这样回忆了一八七九年时的情景:
夏天时,我们相聚在左拉位于梅塘的家里……我们全都是馋嘴的饕餮之徒,左拉一个人的食量就抵得上三个普通的小说家,在为长时间的午餐做长时间的消化的过程中,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天。他给我们讲了他未来的小说,他的文学思想,他对各种事情的观点……有些日子里,我们去钓鱼,这时候艾尼克就显示出了才华,同时却让左拉颇感绝望,因为他只会从水里钓上来几只拖鞋……而我,我则躺在“娜娜”号船上,或去水里泡上几个钟头,保尔·阿莱克西在附近溜达,带着一些俏皮的想法,于斯曼则抽着卷烟,而塞阿尔则很不耐烦,觉得乡下太没意思。

左拉小说《娜娜》1880年初版本扉页
这是下午的悠闲光景,而到了晚上,天气温和,风光迤逦,空气中充满了树叶和花的香味,这帮人便坐上“娜娜”号小船,到塞纳河对岸的岛上去散步。谈话中,他们聊到了短篇小说,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当时写短篇写得最好的故事家,是那位法语说得比法国人还更好的俄国人屠格涅夫。阿莱克西说到,短篇小說实在太难写了,而左拉则接过话头,提议不妨各人写一篇关于普法战争的短篇小说。众人一听就乐了,觉得很好玩,为了增加这一游戏的难度,大家商定,第一个写出的作品是什么样的题材范围,其他人必须保留,只能局限在其中,并分别增添各人不同的离奇故事。
莫泊桑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在一片沉睡的茫茫田野中,在明亮的清辉下,左拉开始给我们讲述了那个关于悲惨战争的可怕一页,题目叫《磨坊之战》。
当他讲完后,众人齐声喝彩:“得把它快快写下来。”
他开始笑起来,说:“已经做了。”

《梅塘之夜》1890年版本
翌日,轮到我讲了。
由于左拉的故事以普法战争为大背景,又具体到了法军溃败后的情景,所以其他人也都得讲法国人战败后的故事。莫泊桑在第二天晚上讲的是一个绰号为“羊脂球”的妓女的故事。
第三天是于斯曼讲,接下来的几夜,则分别是塞阿尔、艾尼克、阿莱克西讲。阿莱克西本来想叙述普鲁士士兵糟蹋玷污战场上的尸体的故事,但遭到众人一致反对。结果,他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故事,让众人白等了四天,才勉强挤出了另一个故事。

书房里的左拉
左拉觉得这些故事很有趣,便建议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梅塘之夜》。于是,不久后的一八八○年四月,这部小说集就由出版商Charpentier出版,其中的六篇分别是:左拉的《磨坊之战》(L' Attaque du moulin),莫泊桑的《羊脂球》(Boule de suif),于斯曼的《背包在肩》(Sac au dos),塞阿尔的《放血》(La Saignée),莱翁·艾尼克的《大七之战》(L'Affaire du Grand 7),阿莱克西的《战役之后》(Après la bataille)。
左拉的《磨坊之战》故事发生在乡间一个古老的磨坊里。法军溃败后,剩下一支小分队奉命在此狙击普鲁士军。整整一天,法军士兵寸土不让,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撤退时,只有队长和四名战士幸存。左拉热情讴歌了三个爱国者的英雄形象:镇静沉着的梅尔利埃老村长,他的女儿—美丽而又勇敢的弗朗索娃丝,未来的女婿比利时人多米尼克。普鲁士军官逼迫他们给军队带路,如若违令则就地枪毙。面临生死抉择,他们的回答是:“宁可死,也不能屈服!”最后,在法军胜利反攻的号角声中,梅尔利埃老爹和多米尼克终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莫泊桑的《羊脂球》写了战争中的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从中折射出社会面貌的一个缩影。一辆乘坐十个人的马车获准离开普鲁士军占领区,从大城市鲁昂前往法军防线内的海港城市勒阿弗尔,车上的乘客有工业家、伯爵、商人、修女,还有一个外号“羊脂球”的妓女。众人虽然对她侧目而视,但由于路途长远饥饿难忍,还是厚着脸皮吃光了她随身所带的一篮子食物。马车经过一个村镇时,占领当地的普鲁士军官暗示要求羊脂球陪他睡觉,否则就不放马车通行。这时,同车的旅客本着各自的利益,纷纷劝说羊脂球为他们作一夜的牺牲。一天说不通,第二天接着说,一连好几天,软磨硬泡,终于迫使羊脂球就范。然后,马车获准通行后,众人一上车就顿时换了另一张脸,对可怜的羊脂球不理不睬,任她一路挨饿,在孤独中饱尝众人鄙夷的目光。莫泊桑以逼真可信的情节、精练的语言和娴熟的技巧,揭露了众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彻底暴露的自私、伪善,堪称一部小小的心理分析精品。
于斯曼的《背包在肩》讲的是一个很不情愿入伍的士兵的可怜遭遇的故事。于斯曼生性忧郁,普法战争中上过夏隆战场,后因为生病而亲身经历过一段病院的生活。那种倦怠的混乱无序的病院生活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段可怕回忆,也成了小说《背包在肩》的素材。在这篇小说中,他细致描写了法军溃败前后一个普通士兵那平凡、粗野、充满了兽性的日常生活,他被征入伍,说是开往前线,而一列没头苍蝇似的列车,莫名其妙地把他一会儿拉到东,一会儿又拉到西。在途中,这士兵终于病倒,又被转移来转移去,一会儿到一个病院,一会儿又到一个收容所,整整几个星期,毫无头绪,而那个背包,也是成天打好着,随时准备要背上肩膀。病号士兵最大的乐趣,就是从病院中偷偷溜出来,找个餐馆大吃一通。通过对吃喝玩乐,还有抢劫偷窃的描写,毫无隐晦地揭示出荒唐战争中人性的丑恶一面。
塞阿尔的《放血》以巴黎的围城为故事背景,用漫画的笔触,揭露了战争期间一个负责防务的高级军官因一个风骚女人的诱惑而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劣行。它一方面重复了荷马史诗以来文人墨客一直袭用的红颜祸水的主题—女人永远能让男人犯傻;一方面又在故事中加入了一些新的解释,让它变得既有哲理意义,同时又富有真实可信的细节。交际花出身的德·帕奥昂夫人在战争中摇身一变,成了战地医院的急救医护人员,当然也不免假公济私地在受伤的士兵和军官中寻求一时的爱情和肉欲。因为与巴黎城防守军的法军司令官闹脾气,而去被普鲁士军队占领的凡尔赛小住,但在凡尔赛的苦难经历又激起了她对入侵者的仇恨,便再次返回巴黎,并怂恿那位法军司令老情人突围。然而,她提供的想当然的凡尔赛敌军的“情报”,还有她带着情欲的对司令官的鼓动,导致了突围的失败。
艾尼克的《大七之战》叙述了士兵们包围一个叫“七号”的妓院兼酒馆,并屠杀里面可怜妓女的景象。而他们杀人的理由竟然只是一个战友在那里玩乐时受了伤,回军营之后死去。这个故事让莫泊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玩闹的悲剧更可笑,同时又更可怕的了。貌似荒唐的故事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人在单独一人时,往往聪明而富有理智,但一旦成了群结了伙,则常常不可避免地会变得粗暴野蛮,丧失理性。战争中的人之所以丧失理性,成为野蛮人,也正是因为集体的无意识彻底抹杀了个人的理性。小说结尾处,军队的指挥官这样总结那帮野蛮士兵的行为:“好吧!让我们等一周时间,你们就会看到,究竟谁会对今天夜里的这个事件后悔了……真的比小孩还笨,这些游手好闲的懒鬼!……他们打碎了自己的玩具。”这也算是从反面印证了战争中人性极端愚昧、野蛮的一面。
阿莱克西的作品《战役之后》讲了一个贵妇人的滑稽可笑的逸事。年轻的贵族太太德·普莱莫朗男爵夫人坐着一辆四轮马车,去收殓她那死在战场上的丈夫的尸骨,却对一个陌路邂逅的“可怜的伤兵”动了心,更何况,这两个人还在生活的众多方面有着共同语言:德·普莱莫朗男爵夫人从小到大缺少亲情和爱情,阅读种种书籍让她对真诚的爱情万分地向往;而那伤兵本来是一个教士,教职的清规戒律长年遏制着他内心中充沛的情感冲动。而在战场之间那条公路上,在装载有男爵尸体的棺材的马车上,两个逃亡者之间发生了一段亦喜亦悲的爱情故事。

左拉故居門前的花园,花园过去就是铁道
后人公认,年轻的莫泊桑的《羊脂球》为六篇中的最佳。
以左拉为首的梅塘“小集团”的成立,标志了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正式诞生,而《梅塘之夜》的出版,则被看作是这个集团发起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或者说是自然主义文学流派诞生的标志。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开始不赞成自然主义,或者后来否定了自然主义的理论,但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着自然主义的烙印。
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或曰文学运动第一人,非左拉莫属。左拉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他的自然主义作家,可以算上梅塘小集团的阿莱克西、于斯曼、莫泊桑、塞阿尔、埃尼克,其他的则有龚古尔兄弟爱德蒙和儒勒,还有都德等人。
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泰纳的文艺理论影响下,左拉逐步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即客观地描绘现实,像分析研究生物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来剖析人的生理对性格和行为的影响。他的《实验小说论》和《自然主义小说家》便是阐释这一理论的论著,而他早期的《泰蕾丝·拉甘》和《玛德莱娜·菲拉》两篇小说,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左拉在其自然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来描绘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是为“卢贡-马加尔家族”,为此,他还画出了谱系树,规定了上下五代一共三十多个人物的遗传特征。他用二十五年时间,完成了二十多部小说,构成了这部家族史,以《卢贡家的发迹》为开篇,以《帕斯卡医生》告结束。其中最著名的小说当数《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而左拉梅塘的家的两座楼,也恰恰是以其中的两部小说的篇名命名的:“娜娜楼”和“萌芽楼”。
“梅塘之夜”的故事,我以前早就熟悉,首先,因为那是法国文学史的一段掌故,算是文学常识;其次更因为,我指导的一位硕士生正在做关于《梅塘之夜》的论文,为此,我事先也做了一番功课。但趁着在法国访学,小住巴黎的机会,特地赶来梅塘一游,还是别有一种滋味的。
秋末季节,天气多变,中午十分阴沉沉的天,眼看着就渐渐放晴了。
按规定,梅塘的左拉故居不能自由参观,必须跟随当地的导游一起进去,一起转悠,每一个小时允许一批参观者进入,全程由导游陪同,整个参观过程大约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当地姑娘充当了我们的导游和讲解者。见我们几人总是提一些很“专业”的问题,不仅有些纳闷。我的法国朋友便告诉她,我正在翻译于斯曼的名著《逆流》,对梅塘集团的作家很有兴趣,而且我的一个学生正在撰写关于《梅塘之夜》的学位论文。听闻此讯,那女导游便连连吐舌头,表示惊讶。
左拉故居的整栋房子的外表呈现朴素的浅黄、青灰和砖红三色:浅黄色的墙面,砖红色的房顶、烟囱、边角线、门框和窗沿,青灰色的护窗板和阳台,十分古朴。当年左拉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如今依然保留着原样,许许多多的实物和图片(左拉本人是一个有名的摄影师,当年拍了很多照片),把人们带回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那些“梅塘之夜”,令人重温左拉、莫泊桑、于斯曼等人当年的风采和才華……
在他的书房里,我见到了橡木的大书桌,还有左拉当年花了一千二百法郎建造的石头壁炉,以及壁炉上方墙面上的他的座右铭—“无一日不写一行”。这句话的拉丁语原文为:Nulla die sine linea。法语的直译为:Aucun jour sans ligne,意思当然是:Pas de jour sans écrire une ligne。有人翻译成“生命不息,写作不止”,也很不错,是一种励志名言。
室内的墙上贴着许多海报,大都是后来人们根据左拉的小说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的宣传画,其中尤以《娜娜》和《萌芽》的海报居多。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里的两个楼,不就是“娜娜楼”和“萌芽楼”吗?
“萌芽楼”中还专门有一间房间,用印有《我控诉》文章的布幔做装饰,里面的内容完全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据讲解员说,人们正计划在梅塘再建一个德雷福斯纪念馆,与左拉的故居相映成辉。
铁路线确实非常近,离书房的窗口不到三十米,就在花园的边上。一辆火车刚刚往巴黎方向开去,我们可以从容地赶半小时后的下一趟火车返回。
从中间那栋最老的楼前拾级而下,朝西不远几米开处,便是一个长方形的花园,园子最中央是一个圆坛,种植了一些花卉蔬菜,两边分别是两块不大不小的草坪。南北两侧分别用矮砖墙跟斜坡上公路道和林边的空地隔开……东边上的好大一排矮房子,如今成了故居的博物馆展厅、书店、接待处。而左拉家的整个地产,还包括北头的一片树林。而离花园和树林不远的西边,便是潺潺流动的塞纳河了……
准备坐火车回巴黎时,已是近傍晚时分。天边出现了熊熊烈火一般的火烧云,十分鲜亮。假如,左拉能活到今天,他一定能从朝西的书房大玻璃窗看到这片艳丽的晚霞。
离左拉故居不远的教堂钟楼上的风标鸡,正立在一片橘红的云彩前,那么的高傲,多么像是振臂一呼“我控诉”的左拉。它像是在告诉众人,社会正义之光就在前面,可以用文字来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