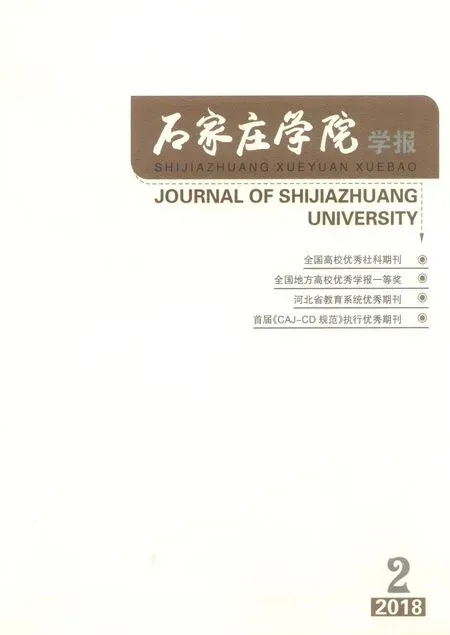质疑破疑 古今通观
——读邵荣芬先生《切韵研究》
宋 峰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自清代陈澧之后,有很多学者都曾对汉语语音史上经典坐标性韵著《切韵》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如王显、陆志韦、周祖谟、王静如、方孝岳、黄典诚、李荣、葛毅卿等。邵荣芬先生的《切韵研究》是文革之后出版的最早研究《切韵》的专著。同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一样,邵荣芬先生在补论前人看法的基础上提出新见,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剖析功底,铸造了《切韵》研究史上的辉煌。该书1963年写成初稿,1964年开始修改,1966年写成二稿,1972年又经修改成了现在的第三稿。《切韵研究》共167页,最早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201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切韵研究》校订本。①下文中未标注的文献均出自于此书。最新校订本仍有几处可校改的地方:(1)p49,第二行“第六章”应为“第五章”;(2)p73,“见唇、牙、喉为下切”中“见”应改为“凡”;(3)p78,“《举要》宵韵系的情况对《重释》的论点说”,“论点”后漏一“来”字;(4)p118,所列举的梵文字母对音材料中,“佛驮跋陀罗 4-8”,其“4-8”当有问题;(5)p149,第四行“萧与宵井”之“井”当为“并”;(6)p171,表右上角,皆二开,ɒi应该为 ɐi。该书共分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切韵》的音系性质;第二章,《切韵》的声母;第三章,《切韵》的韵母;第四章,《切韵》声母的音值;第五章,《切韵》韵母的音值;第六章,《切韵》的声调;第七章,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音节表。其中,第七章的“音节表”包含了该书的全部结论。
《切韵研究》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影响和贡献巨大,值得特别提出的就是它为我们在继续研究和利用《切韵》上提供了一些较为客观、全面和准确的统计材料和相关结论。主要包括:(1)对《切韵》的两个重要传本《王三》和《广韵》的反切上字及下字进行的系联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切韵》声母表和韵母表。(2)邵荣芬先生在制定声母表之前作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参考各家校勘作下列四项校改:甲、该错字(遍布多摄),乙、补漏字(主要在流摄),丙、移小韵,丁、删小韵(包括重出而在韵末的、重出而《切韵》各残卷有未收的、重出而早期韵图不采用的和非《切韵》音系本有的四个方面的内容)。(3)除了声韵表外,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还附录了重要的《广韵》反切上字表及《广韵》中唇音字和开合字互切的切下字表。连同第七章的《王三》音节表,这些表格文献占全文比重的近1/3之多。
邵荣芬先生研究《切韵》,不拘旧说,质疑破疑,立新求解,在掌握大量历史文献和讲求科学论证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新见。概括来讲,《切韵研究》一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不拘成见,对《切韵》的性质作了进一步论证
邵荣芬先生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音系,但也多少吸收了一些别的方音的特点”的观点。这个活方言音系的基础音系是洛阳音系,部分吸收了金陵话的一些语音特点。
第一,邵荣芬先生驳斥了一些人的借助“又音”即所谓的“内部证据”,得出《切韵》是综合古音或方音的观点。综合主要有“改变”和“同时并存”等方式。而《切韵》里的“又音”,只是以一种“综合方音”的“重出”。在论证中,作者利用了与《切韵》相距不远的文献材料,如《经典释文》《字林》等,旁证了《切韵》似乎吸收或综合了以《经典释文》为代表的南方金陵话的观点。对于其中所述及到的“折合”,更能有力说明《切韵》必须有自己的音系作为基础、作为格局的观点。利用“又音”说来断定《切韵》音系的性质为综合说,纯粹属于“无稽”之谈。
第二,纠正了一些人将“杂凑性”和“读书音”联系在一起的看法。读书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读书音对口语音有一种绝对的依赖关系,它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具有完整表达功能的独立音系,只不过是它所在方言音系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已。多数方言读书音的声、韵、调都没有溢出口语语音声、韵、调的范围。《切韵》包含了当时读书音的成分,但所赖以存在的方言基础仍不可没有。
第三,在邵荣芬先生所提到的何超的《晋书音义》、夏侯泳的《韵略》和顾野王的《玉篇》中,与《切韵》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晋书音义》,至于后两部韵书则与之保持了一个较大的差距。邵荣芬先生《〈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论证了《晋书音义》是距《切韵》时间最近的一个反映洛阳音系的系统的材料。《晋书音义》和《切韵》在声母和韵母系统上除保留了少量正常音变现象外,可以说大多一致。邵荣芬先生驳斥了周祖谟先生利用《王三》韵目小注判断《切韵》分韵多从南方人夏侯泳《韵略》的观点。①这里谈到了关于王书小注的问题,邵荣芬先生认为其实质只是表明《切韵》和它所参考的韵书之间分韵精或粗的不同,而非表明它们语音根据上的差异。详参《〈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载《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王书注中的好多情况不能表明《切韵》在语音上从南不从北。为了驳斥周祖谟先生认为《玉篇》反切和《切韵》最为接近,进而认为《切韵》基础音系为金陵音系的观点[1]434-473,邵荣芬先生指出了周祖谟先生在《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研究中的不足[1]270-404,认为在韵母方面《篆隶万象名义》和《玉篇》除了“脂和之、真和臻和殷、尤和幽、严和凡、庚三和清”混淆不分和《切韵》有所差别外,还举到了“山与删、宵与萧”等混并的韵,从而认定《篆隶万象名义》反切的韵母系统和《切韵》的韵母系统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晋书音义》和《切韵》之间的差别。而且,邵荣芬先生指出周祖谟先生在将《篆隶万象名义》和《切韵》进行比较时的不足,认为其忽略了二书在声母方面的异同。邵荣芬先生对周祖谟先生所得出的泥娘部分有所怀疑,认为端、知六母当分,泥娘应合,没有根据可言。邵荣芬先生还从“一字重切”和“系联”现象入手,推断《篆隶万象名义》“泥娘两母已经分化”。由此,邵荣芬先生更加坚定《切韵》的音系大致是一个活语言的音系而不是什么杂凑的体系观点。
二、持论有力,对高本汉学说的进一步修改论证
(一)认为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声母不送气
高本汉将《切韵》中浊塞音並、定、澄、群四母及浊塞擦音从、崇、船三母订为送气音。后来,陆志韦和李荣先生同意高本汉的做法,把这七母订为不送气音。[2]7-9[3]116-124邵荣芬先生同意陆、李所作的修改。指出高本汉用来论证古浊音送气根据的“现代吴方言”并不能作为“古代送气的遗迹”,并充分分析了吴语方言里送气的特点。邵荣芬先生除提及李荣先生所使用的傜歌语音及傜族所说的汉语之音来证明古汉语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不送气外,还补充了以下几个重要证据:
(1)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他们讲的是一种汉语方言;
(2)贵州锦屏县白市一带的苗族也不说苗语,而说一种汉语方言。这两个地区的汉语方言里,古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一概不送气;
(3)汉藏语系里藏缅语族彝语支碧江白语中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这套浊塞音和塞擦音都不送气。包括高本汉在内的研究《切韵》浊塞音和塞擦音送气与否的学者,在结论上的争议,多因材料而引起,材料是否有解释力是论证这一问题的关键。邵荣芬先生总能在材料的分析上独有见解,笔者同意他补充论证的古浊塞音和塞擦音不送气的观点。
(二)批判了高本汉[j]化说和对知组、庄组的构拟
高本汉先生一直坚持其《切韵》声母[j]的学说。邵荣芬先生用客观的事实②包括《阿弥陀经》和《金刚经》中用来对译’d和n的泥母和对译’j的娘母字。肯定《切韵》反切上字一二四等和三等分组的现象毕竟只是一种趋势,不能清楚地表明哪个声母是按这样的方法分为两类。邵荣芬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本汉的[j]化说“不光没有事实根据,而且说法本身也有很多不一致和互相矛盾的地方”。该书紧跟着附录了《广韵》各等反切上字表,罗列全面,对了解各声母反切上字在各等的分布情况有很重要的作用。高本汉对知组、庄组的构拟都是有问题的。邵荣芬先生对高本汉的材料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高氏拟音上的不足,并同意了陆志韦和李荣先生主张将庄组的[■]改为[ʧ]的做法。
(三)否定了高本汉将合口介音分为[u]和[w]的做法
高本汉认为《切韵》的合口介音应分为强[u]和弱[w]。前者适用于开合分韵的合口字,后者适用于开合同韵的合口字。邵荣芬先生认为这样的划分完全没有必要,他同意很多中国学者对高本汉的批驳,假定只有一个合口介音,即[u]。他指出:“唇音字可以做开口字的切下字,也可以做合口字的切下字。反过来,开口字或合口字都也可以做唇音字的切下字。”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中有对此问题的讨论。除此,邵荣芬先生分析,不独《切韵》一书在唇音字上部分开合,认为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反切系统几乎都不分开合。他所列五家音切分别为:顾野王的《玉篇》、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曹宪的《博雅音》、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和何超的《晋书音义》。
此外,邵荣芬先生还进一步引申,用大量的反切材料,如《字林》《易音》等,分析了《切韵》中“咍、灰两个韵系的唇音有些小韵是互相对立”的疑问,得出了它们在反切上的共性,指出“咍、灰两韵系唇音不对立”的事实,由此得出《切韵》中所有唇音字不分开合的结论。
(四)提出纯四等没有i介音等
高本汉假定《切韵》纯四等也有前颚介音-i-。先有陆志韦和李荣先生根据反切上字三等和一二四等有分组的趋势以及四等韵的声韵配合关系和三等不同而和一等韵完全相同的事实,批判了高本汉的说法。李荣先生引梵文对音来证明纯四等没有介音,笔者觉得很有说服力。邵荣芬先生利用佛教密宗翻译陀罗尼的材料,发现四等字不对译i,差不多只用来对译e,得出四等字没有i介音和四等字的主要元音是同于或近于梵文e的音。在四等主要元音上,邵荣芬先生赞同陆志韦先生将其拟为ε的做法,而非李荣先生的e。按照韵图的排列和《切韵》韵母的词序,再加上隋代韵文押韵多有三四等互押的例子,所以三四等在主要元音上是很接近的,若将四等主元音订为ε,则和它相配的三等主元音则拟为æ比较妥当。
(五)一、二等重韵的问题
高本汉先生认为一、二等重韵大多数是音量长短的不同。这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反对,一般都认为是音质的不同所致。邵荣芬先生首先指出了高本汉所依据材料——朝鲜借音的不可靠性。陆志韦《古音说略》根据韵图的排法把一、二等重韵作了不同音质上的构拟,大致可以接受。邵荣芬先生同意陆氏的假定,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三点修改。
此外,关于止摄、遇摄、通摄、流摄和真、蒸、侵韵等主要元音的拟订,邵荣芬先生都有别于高本汉。《切韵研究》一书中第156-157页是邵荣芬先生对《切韵》韵母所作出的音值拟音表。
三、广涉文献,补充并修正前人的论述
(一)泥娘的分立
泥娘的分立,由于在现代方言中一时还找不到区分的证据,多数音韵学家认为《切韵》中此二母不分。邵荣芬先生非常谨慎,他首先从《王三》和《广韵》中反切的系联情形和类隔的多少上推断泥娘和端知一样应该也有分别。①可参考邵荣芬《切韵研究》第36-37页统计表。他还参照了曹宪的《博雅音》、何超的《晋书音义》中反切的系联情形和类隔的多少,同样得出了泥娘当分的结论。他引用大量前后时期的反切材料,比如列举了颜师古《汉书》注中的反切来证实泥和娘上的分化。除此,邵荣芬先生还举到了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的反切,同样得到泥母为一、四等,娘母多为二、三等的结论。其次,他还用到了汉藏对音资料②,较晚的《开蒙要训》证明泥娘自古便来源于不同的“异趣”。《古今韵会举要》同样给泥娘不同的结论提供了一些证据。不过,邵荣芬先生从《切韵》本身存在少量“端和知”“定和澄”的对立,故而推定泥娘似乎也分立,这好像有点说服力不足的味道。
李荣先生不主张分立泥娘。邵荣芬先生反倒其说,对李荣先生所采用的三十字母例进行质疑,毕竟三十字母是后出的,进而对李荣先生的看法进行修正,认为“三十字母只有泥,没有娘,并不一定就能作为《切韵》有泥无娘的直接证据”。邵荣芬先生认为,韵图拿娘母配泥母是按照语音的实际和自己的需要而作出的应有安排,是考虑到声韵搭配的,而且坚信《切韵》韵图区分泥娘母,拿娘配泥是正确反映了《切韵》反切实际情况的。这是邵荣芬先生论证精彩的一节,笔者认为邵荣芬先生的持论有据,但遗珠之憾是还没有在现在方言中找到泥娘分立的证据,我们只能期待未来在方言调查中的发现了。
李荣先生反对将娘母作[ȵ],日母作[nʑ]。邵荣芬先生对李荣先生所使用的梵汉对音的材料提出了异议,又将善无畏以前各家对梵文字母na、n.a、ña的译音列表,认为泥、娘的分别“不容置疑”,同时将日母拟作[nʑ]。面对同样的梵汉对音材料,邵荣芬和李荣先生所持的结论相左,笔者认为,邵荣芬先生的推论是合理的。
(二)“俟”母的独立
关于“俟”母,邵荣芬先生同意李荣先生的做法,将其独立对待,而且一开始便引证了李荣先生所采用的几点理由。①参见李荣《切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93、第127页。但让邵荣芬先生颇感奇怪的是在《切韵》前后的一些反切材料里竟然找不到十分可靠的旁证。他将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反切材料进行总体考察,将“俟”母的音切类型定为三类。第一类是“俟”母不和其他声母系联。俟母独立的材料少见,说明《切韵》俟母的分立并不代表当时的大多数方言。第二类是俟母字用崇母字注音或作切。第三类是俟母字用崇母以外的其他声母字注音或作切。邵荣芬先生推定,俟母原来大概是喉牙音,后来才变为齿音二等的。邵荣芬先生很明了地表明《切韵》时代俟母字是从属于庄组的,驳斥了一些人认为的“俟漦”等字也许就是船母字的看法。
(三)常船韵图的安排错误
对于韵图中船、常两母位置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例如,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认为,切韵系统分床禅是方音的混杂现象,他说:“床禅两母有同一的来源。中古时代切韵系的韵书虽有床禅之分,但是从他分配的情形看来,除去少数例外,大都有床母字的韵就没有禅母字,有禅母字的韵就没有床母字。”他还从方言、守温韵学残卷、《经典释文》等字书证据中推论,认为“切韵系统的分床禅两母似乎有收集方音材料而定为雅言的嫌疑”。陆志韦先生《古音说略》分别从反切上字、谐声通转和梵汉对音三个方面对《切韵》床禅的顺序提出质疑。他认为,韵图中船为塞擦音,常母为擦音是与事实相反的。当然,他还列举到了一些现代方言例证,如东南方言等。邵荣芬先生同意陆志韦先生的做法,而且用一些更加可信的材料进一步论证这个假设。他着重借助梵文字母对音材料,肯定了8世纪以前常母在梵文译音里表现为塞擦音,进而又从常船两母存在区别的前提出发,论断船母表现为擦音。他提出,梵文字母对音和等韵图存在矛盾的原因在于“韵图的安排错了”的假设,并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
首先,他用颜之推的话推断6世纪或6世纪以前的许多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里,常母和船母已经不分了,后《玉篇》《经典释文》里的反切常、船两母也混二为一。总之,以顾野王和陆德明为代表的江南人的反切均已常、船不分了。可是,当时江北的方言大多还是常、船相分的。如曹宪的《博雅音》、颜师古的《汉书注》、李善的《文选注》等书中的反切是严格分开的。到了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何超的《晋书音义》的反切,均又出现相混局面。稍后李贤的《后汉书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的反切常、船两母又相混淆。包括后来的《归三十字母例》、《广韵》中的反切(又音)、《集韵》等都可以看到常、船两母混淆的局面。从这些方面,邵荣芬先生论证了韵图将常、船两母安排错误的可能。接着,邵荣芬先生又从等韵图的奠基人守温的《守温韵学残卷》之“两字同一韵凭切定端的例”中对一系列照二和照三字母的安排上,分析了其排列上的原意,论断了常母是塞擦音而船母是擦音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邵荣芬先生引用了现代方言中一些船母字保留擦音、常母塞擦音的例子②主要是客家话中的梅县话、广东话中的广州话等。。此外,北京话常、船两母常母字的读法也非常具有启发性,用来论证常母古读塞擦音很有说服力。还有,邵荣芬先生同时列举了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金水乡小组所说的汉话来论证常母只有塞擦音、船母只有擦音的读法,也较有说服力。
(四)严凡、真臻互补等问题
现代方言韵母音声调而异读的极其常见。邵荣芬先生认为严韵系和凡韵系、臻韵系和真韵系的区别既然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异调异读,所以认为可以把严韵系并入凡韵系,把臻韵系并入真韵系。
(五)《切韵》的声调
邵荣芬先生提到了陆志韦先生、李荣先生关于《切韵》四声的论断。邵荣芬先生对李荣先生的“四声三调”说提出了质疑。至于《切韵》的调值究竟如何,邵荣芬先生最终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不过文中提及到的“去声是个屈折调”的说法,倒是一个很近情理的推想。
四、小心求证,对一直疑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新解
(一)对重纽字的归类和音值问题的看法
重纽现象在《切韵》和早期等韵图中非常明显。[4]邵荣芬先生用了不少笔墨来讨论中古的重纽问题,他逐条列出董同龢先生《重释》和陆志韦先生《古音说略》中用来证明各自观点的论据,并逐条进行剖析和推导,足见其问题的繁杂及其在音韵学上的重要性。
对重纽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种:
(1)高本汉先生不同意重纽三等乙和重纽四等丙的区别,也就是说不同意重纽的存在。
(2)周法高、董同龢将重纽乙和重纽甲的区别定为主要元音的不同。
(3)王静如、陆志韦、俞敏、李荣、邵荣芬等将重纽乙和重纽甲的区别定为介音的不同。如果按邵荣芬先生将三等喉牙唇称甲,将四等喉牙唇称乙,将舌齿音称丙的做法,那么重纽三等、重纽四等和三等舌齿音的关系可概括如下,见表1。
对于支脂等八韵系里的舌齿音究竟和本韵里所重出的哪类喉牙唇音同类,这个问题虽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邵荣芬先生的重纽三等带-i-介音①即三C介音。、重纽四等带-j-介音②即三D介音,其中[j]不表示颚化。的观点可以说很好地解释了重纽的历史问题。邵荣芬先生在论证重纽问题时,通过寻找新的材料,精密求证,在此基础上驳斥了董同龢先生和陆志韦先生在论证重纽问题上的偏颇与不足。
比如,他结合现代朝鲜语,并借助1747年朴性源、李彦容的《华东正音通释韵考》来论证董同龢《重释》中通过引用朝鲜译音来论证乙、丙同类的不足。他受《韵会举要》的启示,辅以《蒙古字韵》,还得出“以”母不能从甲类里分出来的结论。最后,邵荣芬先生从方言中找材料,得出了如上结论。另外,关于重纽问题,我们还可以参考殷焕先、张玉来先生的相关论述。殷焕先、张玉来先生赞同邵荣芬先生重纽三等加-i-介音,重纽四等加-j-介音的做法,并从重纽上古不同来源的角度分析,同时运用汉藏语系诸语言和汉越语、梵汉对音等材料对见、影、帮三组声母的特殊处理上论证了中古三等重纽中唯独见、影、帮组带-j-介音的合理性。③包括错那门巴话、墨脱门巴话、达让登语中见、影、帮组后存在的复辅音;载瓦语和状语中,独见、影、帮声母所存在的颚化复辅音等。这可以作为邵荣芬先生在论证材料和思路上的一个补充。
(二)庚三知组等
不少学者多将《切韵》庚韵庄组声母字一律归入二等。邵荣芬先生从《切韵》系各韵书庚韵系庄组字用三等切下字的例子证实《切韵》系韵书庚韵系庄组字哪些用二等切下字,哪些用三等切下字,是基本固定、基本一致的,以此来断定知组有三等韵的事实。
五、体现出一种“古今通观”的思路
冯胜利先生在《汉语韵律句法学》中提到了一种“共时和历时相互参证”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同时他还认为,“语言研究应当尽量古今通观,前后关照……科学贵在能分,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通合’的长处,分合都不可缺”[5]16。冯胜利先生的这种学术观念在《切韵研究》这部书中也时有体现,我们可以举例来探讨这种思想。
(一)“庚韵系庄组声母字”
语言的演变是受规律支配的,考察一个时期的音变现象自然离不开释理,能使前后解释得以通透的音变,我们认为才称得上是合理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存在疑问的语言现象的解释尤其离不开对历史上源流的考察。
邵荣芬先生的《切韵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在论述“庚韵系庄组声母字”时,为了证实“用二等切下字的属二等,用三等切下字的属三等”,即庚韵系三等除喉、牙、唇音声母以外,还有舌齿音声母的问题,他不仅举到《切韵》系各韵书庚韵系庄组字用三等切下字的全部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从历史上溯源,见表2。

表1 重纽三等、四等和三等舌齿音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来自于上古铎部的庚韵系入声陌韵的庄组字,虽有二、三等之别,但因为上古来源对象固定,所以看不出其发展上的区别;而庚韵系舒声庄组字因为来源于上古阳部和耕部,又分别对应于二等切下字的庄组字和三等切下字的庄组字,所以从这些字的不同来源上,我们似乎能够证明《切韵》庚韵庄组字有和二等相对应的三等存在。
当然,邵荣芬先生也只是将此溯源考作为判断庚韵系存在三等的一个证据,要给庚韵庄组字判定有三等的证据还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支持,但这个历史溯源的方法对于考究一种语言现象的历史演变无疑是很重要的。
(二)对“影”母字作[ʔ]的拟定
本书对于“影”母字的考察也体现了这种“古今通观”的研究思路。对于“影”母,各家都认为是清喉塞音[ʔ]。陆志韦先生认为汉语的声调变化主要是由声母的清浊决定的,这一点是有道理的。现代平声分阴阳的方言,影母字都读为阴调;但如果影母像现代话那样以元音开头的话,由于元音的浊音性质,影母就应该读阳调,而不可能是阴调。陆志韦认为“影”母如果是零声母,并不妨碍它后来变为阴调,因此他更倾向于把“影”母拟为零声母。不过,这很难解释影母字在平声的变化和在入声的变化两种情况。因为影母字在《中原音韵》里和次浊声母字一同变作去声了,现代北京话影母入声字也基本上都变为去声。按照邵荣芬先生的论述,“这样影母在声调变化方面就存在着平、入不一致的现象:平声和清声母一起变,入声和浊声母一起变”。如果影母果真像陆志韦先生所拟测的零声母那样,那么同一个零声母很难解释影母在平声和入声上所作的两种不同的变化。因此,给影母拟订为[ʔ]的假定是较为合乎事实的。这也是古今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实例。(见表3)
总之,邵荣芬先生的《切韵研究》一书,因其独到的见解和充分详实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古音研究中的不少困难和疑惑,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可。虽然书中的一些结论仍在争议,但其独到的思路已使我们在中古音研究上深受启发。除此,该书还给我们提供了《切韵》研究上的很多重要材料和数据统计①如经作者修订后的《切韵》声母表、韵母表,《广韵》各等反切上字表及第七章“宋濂跋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音节表”等。,对我们研究和解读语音史(方音史)、韵书史等问题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数据。

表2 庚韵系庄组字的上古韵部溯源

表3 《切韵》影母的今音变化
参考文献:
[1]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M]//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
[2]陆志韦.古音说略[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3]李荣.《切韵》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6.
[4]殷焕先,张玉来.重纽的历史研究[J].古汉语研究,1991,(4):7-13.
[5]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