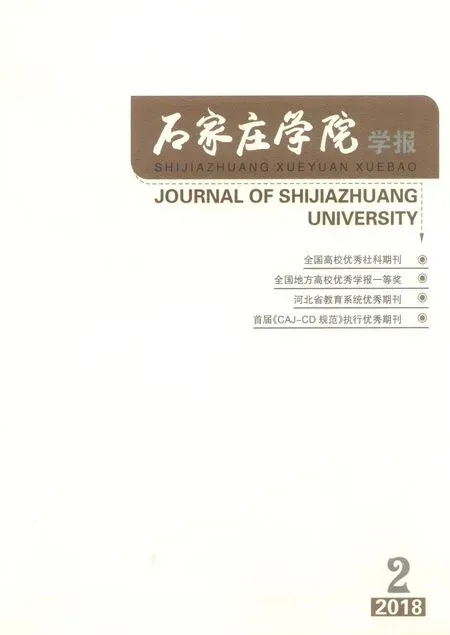南宋“新安学派”的理学追求与诗歌创作
王 昕
(石家庄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新安学派”①周晓光对“新安理学”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作了清晰的阐述,肯定了“新安理学”学派之说。参见周晓光《新安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指宋元明清时期徽州(旧称新安,今安徽黄山)研究和传播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新安学派”兴起于宋室南渡前后,南宋中期之后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南宋“新安学派”成员主要包括徽州先贤、朱熹同道讲友、朱熹弟子及再传弟子等,他们大力弘扬程朱学说,多数学者也进行诗歌创作。据《新安学系录》《紫阳书院志》《新安文献志》和徽州府县志、宗谱、别集等文献,初步统计南宋徽州本籍理学家共86位,其中现有存诗者32位,现存诗歌近3 000首。②统计“新安学派”理学家和理学诗人限于徽州本籍,祖籍徽州、寄籍徽州者未计入。“新安学派”诗人以程朱理学为宗,非常重视提升自身的才学识见、胸襟修养、品行气节等,并“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1]213,他们把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日常践履诉诸于文学创作,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其义理体悟、心性涵养和气格志向。
一、义理体悟与理深其趣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是贯通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宇宙本体与儒家伦理的至高主宰,因此,“理”不仅是自然世界最普遍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伦理法则;理学不仅是形而上的哲学,更是用以指导世人完善自我人格以达到理想境界的哲学。“新安学派”诗人尊崇程朱理学,以研习儒家经典和宋儒学说为本,致力于探究宇宙之道、万物之理,他们不仅善于在静观万物中体悟或探究其理,而且也往往理性地思考自然世界和社会人生。这种重理穷理的追求使理学诗人思维方式、表现手法等发生改变,由此诗歌创作逐渐由传统的感物抒情变为因物悟理,诗歌的情感内容被议论说理所挤兑和削弱,诗歌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也让位于启人心智的理性意蕴。
“新安学派”诗人多与自然山水相亲,在对客体对象的观照和感知中,发现和体悟宇宙自然万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规律。金朋说从春日之物感受到了“天理流行随处见”[2]426;王炎在对梅的欣赏中“细推万物理”[3]29;汪晫的《感兴四章五句》表现了万物不以时间转移而改变的恒定性;詹初的《观春》《新春》等诗旨在说明岁月迅速更迭,然又不断变化、生生不息;汪莘认为“太虚”之中皆有“道”,“是皆诗之散在太虚间者,而人各以其所得咏歌之为诗”[2]282,故其由鸡蛋能见出宇宙天体的构成,在望月时体悟自然运行规律,从“影子”“镜子”“一枝莲花”等物中洞察出人们不易发觉之理。“新安学派”诗人普遍能冷静看待自我与外物,诗中表现出物自有定、胸自有春的理性思索。朱松淹滞宦海多年,深切体会到万物皆有其性,顺应时势、无意而求才是理想的选择,如《侏儒》一诗写侏儒既不能违背其本性妄自续凫增高,也不能怨天尤人;王炎更为乐观地看待世界,如《和至卿叙述三首》其三认为浮名只是外物,摆脱外物羁绊,心无荣辱,当胸有阳春、自然超俗;吴锡畴一生不事科举,贱视功名,甘于隐居生活,如《次韵写兴》认为菘韭自有真味,嘲笑虚名翻误一生。“新安学派”诗人也会对社会历史进行思索,总结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金朋说、詹初等均有咏史诗,通过对各朝史事加以论述,揭示其兴衰之因,强调国家灭亡无不与人事有关,应以史为鉴、不违天理。“新安学派”诗人在诗歌中对自然之理和社会之道的表现,充分显示了其创作时言理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诗人贯通学术与文学的追求。
“新安学派”诗人对自然事物或历史人生所蕴含的“理”的揭示,与其说是受外在之物的启示感兴而发,毋如说是诗人通过语言媒介把对自然和社会的哲学认识以形象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不少诗人通过对具体形象的事物的吟咏描绘或刻画来展示诗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与体悟,从而产生了一些富有哲理和趣味的“理趣诗”。“新安学派”诗人对理的言说既有体道悟理方式的自然而然与有意为之的区别,也有表达方式上是否说理或如何说理的差异,根据诗人对理的感悟和具体表现,可以把理趣诗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即物即理,理趣浑然。即物即理是一种最自在、最活泼的悟理方式,天人之间互相融通,人无须殚精竭虑去穷究万物之理,置身于自然山水中而道机自开,融入春花秋月里而天理自现。即物即理也是一种最自然、最高明的言理方式,诗人无须有意表现其内在之理,更无须以“理语”进行解释说明,而是通过对自然物象或社会事象的生动描述自然传达出其理,物自有理,物理妙合,趣中寓理,理趣浑然。“新安学派”诗人也常常以这种方式体道悟理,并在诗歌创作中表述切身的体验,如李缯《晓步》、汪晫《静观堂十偈》其五、汪莘《春夏之交风雨弥旬耳目所触即事十绝》其九、吴锡畴《洲上》等诗,诗人并不直接言说体悟到的道理,甚至也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感受,而是通过倾心描写或叙述所观所感的自然之境,让人体会其中蕴含的生机与理趣。读者阅读时,在诗中描写对象的审美感染下,如置身于诗人所处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与诗人共同完成对道的体悟,从而领会到造物的生意、生命的自在和自然的永恒。
其二,感物明理,理趣相成。感物明理作为一种悟道方式,既强调外物对人的感发,又突出人对物的感知、思索并发觉其中之理,诗人也往往能通过描写对象而联想引发出与之相关但又超越事物本身的人生哲理。感物明理作为一种言理方式,与即物即理基本不著理语不同,诗人既要写景,又要说理,写景是说理的基础和前提,说理成为其关注的重心和落脚点。感物明理虽著理语,然以物象为本,不劈空言理;虽要明理,然理因感物而得,由状物而现,不干巴巴说理,因此,理与物相随,趣中生理,理中有趣,理趣相成。“新安学派”诗人感物明理诗较多,如詹初的《春日》由白云、绿柳、明花感悟到理学家追求的无心自适、优游无我的生活方式,其理不仅与所描写景物相合,也与诗人的心境相契;汪莘的《秋兴》由杨柳怯秋风反向思考,表达心地不随时节变化之理;许月卿的《雪后》由雪后松树之状体悟到修养之法,说理形象生动;吴锡畴的《舟中》由行程所观美景表达了从容面世的理性思考。
其三,咏物释理,理趣横生。咏物释理通常也是在外物的感发下体悟到其中之理,不过与即物即理、感物明理不同,即物即理之物是诗人所处之“境”,感物明理之物是诗人所观之“景”,无论境或景,都是由不同的物象组成的一个整体环境,而咏物释理之物是诗人专注的某一特定的“物象”;即物即理之理通常是物境“自身之物理”,感物明理之理往往是与景物“相关之事理”,而咏物释理之理可以是所咏之物“自身之物理”,更多的是与所咏之物“相关之事理”。从诗歌表达上,即物即理几乎不著理语,感物明理写景并说理,而咏物释理或通过具体的物象描写寄寓一定的道理,或直接以说理的语言来吟咏某物。咏物释理如果理与物相合,而且表述生动形象,释理常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趣味,呈现出理趣横生的艺术效果。“新安学派”诗人也不乏此类作品,如王炎的《小凫》表达了随从天性、安分知足之理,其理包容在对小凫的行为的生动描写之中,义理与物象不可分离,理因物象而显,物象因理而著,物趣事理,浑融无间;吴锡畴的《笼鹤》以笼中之鹤表达虽享槐阴禄料,毋如云霄万里、宽闲自在之理;吴儆的《说谜三绝》以拟人方式、猜谜的手法咏物说理,理为本心,物为载体,谜为形式,趣理融合,理趣横生。
“理趣诗”基本代表了“新安学派”诗人说理诗的最高成就,但并非表示这些理趣诗就非常成功。陈文忠认为,“理趣是古代哲理诗的最高审美境界”,并归纳了理趣的四个特征:“生趣盎然的形象性”“即物即理的契合性”“审美感悟的直接性”“机趣洋溢的智慧性”[4]。以此标准观“新安学派”诗人的理趣诗,即物即理少了些机趣洋溢的智慧,感物明理在物理契合上稍欠,咏物释理又往往不能让读者直接审美感悟。莫砺锋曾说:“要想写好理趣诗,除了具备长于思辨的睿智心性以外,诗人还必须具备形象思维的高超能力,这样才能把精警、微妙的哲理寓于生动形象之中,实现哲学思考和文学表现的完美结合。”[5]54一方面,“新安学派”诗人说理侧重于理学家追求的义理,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精妙哲理;另一方面,“新安学派”诗人形象思维以及表达能力还未达到成熟,故没有产生较多上乘的理趣诗作。
“新安学派”诗人也会把诗歌作为宣讲其理学观点或阐释其学术理解的讲义,产生了一些为论诗者所诟病的“语录讲义之有韵者”诗歌。金朋说有不少“吟”体诗,以人们喜闻乐见的五绝通俗平易地对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进行解释;詹初的讲义诗涉及范围更广,阐说的义理更精深,如《理气》《中道》《求心斋》《心如谷种》等诗,或探讨理气、仁道等理学根本问题,或示修身为学之道;另外,还有诗人在诗歌中阐说学术义理、宣讲伦理道德,如程洵《荣木和陶靖节韵》、王炎《题刘知宫愚圃三首》其三、汪晫《静观堂十偈》其一等。总体而言,“新安学派”诗人的讲义诗占据的比重不大。从文学角度而言,讲义诗除了遵循诗的格式、韵律之外,完全摒弃了诗歌的基本属性和创作规律,以抽象代形象,以义理代情志,以学术语言取代文学语言,缺乏审美质性和艺术价值。不过,从理学角度来看,“新安学派”诗人不失时机地发现并有效地利用诗歌作为载体来阐述学说,而诗歌形式的要求使理学诗人要考虑如何用精练的语言去更好地说理,这样,讲义诗比起迂腐呆板的说理文章,其接受对象的范围更为广泛,接受也更直接、更快捷,这就大大促进了理学的推广和普及。“新安学派”诗人创作讲义诗,也表明了创作者对其理学家身份的认可和以文学作为说理工具的自觉。
二、心性涵养与以性范情
程朱理学又称“性理之学”或“心性之学”。程颐认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6]292;指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6]577。朱熹进一步解释,“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7]229;并把“正其心,养其性”称之“性其情”[8]201。基于此认识,朱熹不反对诗歌“感物道情,吟咏情性”[7]2748,不过强调诗人吟咏之情应符合“性情之正”,“诗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9]356。因此,理学诗人“吟咏情性”的过程事实上也是自身心性的涵养过程,即“将圣人的德性、情怀、气度等通过诗歌自然地表现出来,体现闲适潇洒的气象”[10]130。“新安学派”诗人普遍重视心性修养,一方面,自觉追求把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自律实践,把内圣作为自己的理想,从而养其性;另一方面,以儒家的礼仪道德来规范和检验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情感,以君子作为自己的参照,从而正其身。诗人在创作中,也往往以理制情、以性范情,把日常情感纳入儒家道德性理的统筹之中。“新安学派”诗人性情涵咏主要表现为“乐”“闲”“静”三方面。
(一)安于山居的乐趣
“乐”是宋代理学家对儒家精神的发掘和传统儒教的发明,也是其追求的具体生活目标和审美理想。邵雍认为“学不至于乐,不可谓学”[11]1088;程颢肯定“学至于乐则成矣”[6]127;罗大经直言“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12]273。“新安学派”诗人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常常在渔樵耕种的生活中充分享受其中的快感。金朋说罢官归隐碧岩山后,吟风咏月,弄花题草,真切体会渔樵之乐,其以乐吟为题的诗歌如《乐渔吟》《乐樵吟》《乐耕吟》《乐牧吟》,充分表达了诗人内在的快活;与金朋说相似,詹初罢官归隐后与妻子开田耕种,并自得其乐,如其《归田》《田居》等诗述其犁黍读书的喜悦心情。理学诗人也善于从日常的生活起居中体会浴沂舞雩的风味,从所居住的环境中发觉让人心爽神怡的乐意。詹初《沐浴》描写自己暮春而浴,乘兴高歌,颇有曾点气象;吴锡畴似乎没有詹初那样兴趣盎然的快乐,然十首次韵方岳的《我爱山居好》组诗,足见其心情的欣悦与舒畅;有“狂士”“铁符”之称的许月卿非常欣赏“安乐先生”邵雍,《春日》等诗表达了其对快乐的追寻。理学诗人呈现的“乐”多是诗人因感物触景引发而起,然其根本在于诗人具有乐者之心,或者说诗人的乐意源于内心深处对乐的认同。“新安学派”诗人以孔、颜、周、程为榜样,不为名利所累,不为欲望所拘,安贫乐道,心中自乐。詹初认为“随地人生俱可乐”[13]377,外在的富贵莫如自身的仁荣;汪楚材欣赏“襟怀无一事,终老乐箪瓢”[14]31834的潇洒自如;吴锡畴认为“箪瓢自钟鼎,风月即勋名”,故能“浩荡一鸥轻”[15]205。只有当人们充分认识到追求目标的价值,排除干扰心理的不适因素,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用心体会,方能寻到孔、颜的乐处,真正实现内心深处的快乐。
(二)优游从容的闲情
理学在本质意义上是引领人追寻“天人合一”的自由之境,“乐”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情感体验和精神面貌,而“闲”既是人自由居住或游走世界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也是人从容面对自然生命与社会人生的修养风度与精神气质。“闲”才会自在,“闲”方能从容。“新安学派”诗人普遍表现对“闲”的钟情与欣赏,他们常以闲居、闲步、闲行、闲思等为诗题,表达自己清闲、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闲、闲雅的气度涵养。诗人们普遍追求身无羁绊的清闲,汪晫终身布衣,以“我无官守无言责,自倚栏干时一拍”[16]771为傲;金朋说退居之后,充分感受“从容泉石无牵绊,不似从前志庙廊”的闲趣[2]427;王炎一生仕宦不顺,终日又为纷扰世事奔波,渴求“归来更倚绳床坐”[3]99的一日之闲;许月卿曾谓“闲中日月诗书府,地上神仙人世间”[17]卷四,把归隐后读书吟诗看作神仙式的清闲生活。诗人不仅渴求身闲体轻,更向往和追求“心闲”。程洵认为“心闲万念寂,枕稳千波妥”[18]卷一,心闲消除万念,方能神定气闲;詹初体会到“水云真自得,吾与尔为群”[13]379,心闲方能自得;汪晫领悟到“心闲世自古,事简日偏长”[16]767,心闲则外在世界也随之改变。在理学诗人看来,心闲实际上意味着平静而无虑,逍遥而自在,从而能够充分感受到真正的快乐,无论是王炎艳羡自由潇洒的闲人,认为心闲能化解忧愁,还是汪莘终身高蹈,在山水自然中尽享自由与闲适,抑或吴锡畴常去做一些俗人难以理解的“闲事”,在闲中感受到至乐,无不体现了理学诗人从容自在的生活态度和理学涵养。
(三)心如止水的静境
“静”是程朱理学的重要范畴,从本体意义上讲“静”与“动”相对,“理属静,气属动”,故“循理为静”[19]499;从伦理学意义上讲,“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7]383。“静”与“闲”“乐”紧密相连,“闲”能生“乐”,“静”亦能生“乐”,而“静”境的实现必须以心“闲”为前提。理学诗人为学上主静持敬,在道德修养上也以“静”为其神往的境界。汪晫取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诗意作“静观堂”,著有《静观常语》三十余卷,正是在对“静”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对“静”境有不同于他人的深刻感受,那种“桑叶一庭深不扫,菊花满院静无言”[16]769的幽静境界,更能衬托出诗人心中的平和淡然;詹初对“静”也有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人们需要荡涤心灵方能至静,“此心欲濯静中去,静定由来物自除”[13]381,因此诗人理想的静境,往往呈现物我两忘、气闲心适的特征;吴锡畴安于闲静的山居生活,喜欢静观自然之物,无论是晚山断云、柳门竹巷,还是雨后草色、矮墙新篁,他常能体会到“静中物物总天机”[15]208,天地万物孕育着生意。当然,并非所有的理学诗人都能保持心如止水。朱松在兵乱四起的时代使他找不到一方静居的环境,而心中的报国之志不得实现更使他不能平静,“我欲安心未有方,至人遗迹已茫茫”[20]卷五,因此迷惘中的朱松徘徊在儒学和释道之间,四处寻求安心之道;隐居山林的汪莘因心存治国之宏愿,故虽高蹈却仍无法平静,他试图摆脱外物的羁缠,以能达到“性静”,《方壶自咏》其三云“谁能一刻静,大胜百年忙”[2]265表达他对“心静”的渴求。主静持敬可以化解、消释诗人用世之志无以实现的痛苦,诗人从不平静逐渐到心如止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理学追求的过程。
三、气格崇尚与诗格提升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内在的刚直不阿、守正不屈与外在的通达洒脱、旷适安乐的结合,可以说“内刚外和”是理学家检验自身道德理想和实践的重要标尺。理想人格除了体现在学识修养和性情气度方面,更突出强调高尚的品德和刚义的气节。“新安学派”诗人以坚贞刚毅的气节著称。庆元党禁,徽州的朱子门生不畏横祸,捍卫朱子之学:程洵被列为“伪学之流”,却慨然致书朱熹曰“滥得美名,恐为师门之辱”[21]135;荐举改官,非“伪学”之党方得擢用,而金朋说上状自陈师从朱熹;汪莘忤韩侂胄,几被所杀;詹初乞辨邪正,毅然罢归。兴亡鼎革之际,徽州士人多能保持一身正气,坚贞不屈:许月卿深居一室,但书“范粲寝所乘车”数字,五年不言而卒;吴浩、吴资深、汪宗臣,义不仕元;孙嵩隐居海宁山中,江恺、汪炎昶,隐于婺源山中;汪梦斗,拒绝受官放还,从事讲学以终。理学诗人对气节的重视也呈现在文学创作中,其诗歌充溢着浩然正气,多有对现实忧患和崇高人格的书写,从而提升了诗歌的精神品质。
(一)高洁品质的自持
高洁品质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道德理想与人格期许,也是自身生活处世的至高坐标。“新安学派”诗人普遍以高洁情操自励自持,其诗歌充分展现了对高逸脱俗、洁身自好的人格的追求和自许。朱松往往能从其观照的草木身上感受到与自己相通的品性,无论是“窈窕云雾窗,参差冰玉肤,绝粒屏香节,仙姿清且腴”[20]卷三的菖蒲,还是“仙姿不受凡眼污,风敛天香瘴烟里”[20]卷二的梅花,都成为其人格理想寄托和追求的对象化实体,诗歌高远而幽洁;王炎称梅、竹为兄弟,“梅兄可纳交,竹弟亦耐久”[3]27,欣赏竹子的直节虚心,赞赏梅花的凌寒傲雪、孤芳清绝;金朋说以植物题吟咏志的诗有二十余首,松的耐寒、竹的不俗、菊的凌霜等,尽见作者的人格追求;吴锡畴以“兰皋”自号,咏兰诗表现了其对兰的品性和精神的欣赏和赞同,“石畔棱棱翠叶长,葳蕤紫蕊吐幽芳。灵均去后无人问,林密山深只自香”[15]205;汪莘常常通过营造超凡出尘的境界,展现其高洁脱俗、清逸特立的精神风貌,在其笔下,常常出现类神仙境界的描写,置身于幽深缥缈、迥异尘世的境地,人也韵高气逸、超凡脱俗。
(二)刚义气节的坚守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刚柔并济,内刚外柔,“仁体柔而用刚,义体刚而用柔”[7]263。柔表现为心态平和、知足旷达的心态和日常行为方式,而刚体现了以道义自守、刚正不屈、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崇高品质。“新安学派”诗人或自述其志,或借物抒怀,或以人为范,表现出对刚义品性的肯定与赞赏,也表示了自己对道的追求的坚定信念。王炎痛心社会士气不振,多次表示其对“刚”与“义”的崇尚,如“白眼看时事,刚肠厌俗流”[3]82“故家乔木高,义气许国坚”[3]35等;汪梦斗坚守气节,拒受元官,羁燕四十余日后口占赋归八首,“身死首阳名不死,家贫陋巷道非贫”[15]66可见其心迹;孙嵩虽无救地扶天、扭转乾坤之力,他以高歌悲吟来表示对社会的抗争,《愍叹》一诗中“救地扶天力不支,犹为落落怪男儿”“可怜傲兀南冠在,吟尽关山恸绝诗”[22]43159等语,表达了国家沦落后作者的兀傲特立与深切悲痛;许月卿诗歌并无过多的志向表白,他以闭门不言的超绝行动书写了真正的气节之歌,不过,从《用名世弟韵》《暮春联句九首》等一些诗歌,不难发现其刚义之气。“新安学派”学者多为朱熹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坚定地信奉朱子之说,以朱熹的品德志节为范,在诗中也多书写对朱熹的崇拜之情和对其“道”的追求与坚守,体现了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坚贞刚毅的气节。程洵曾赴闽问学朱熹,《崇安道中》表达了其不畏险阻、坚定求道的决心;程永奇闻听朱熹去世的消息,虽党禁甚严,仍奋笔题诗,深切痛悼先师;汪莘非常敬仰朱熹,《怀朱晦庵先生》也表示承随朱子之道的由衷心愿;许月卿尊称朱熹“风光月霁足吾师”[17]卷三,朱熹的刚义正气在其身上得到弘扬,“盖朱子平日刚毅之气凛不可犯,则知斯之为嫡传也”[19]2974。
(三)国土丧失的忧痛
理学家的至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实现内圣外王,因此他们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和气质修养;另一方面,他们也以仁者情怀关注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罗大经对此作了精辟的解释:“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12]273“新安学派”学者多远离社会政治,布衣或隐士居多,因此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苦难并非其诗歌的主要内容;然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不能忘却其生活的社会,尤其是外辱侵略、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常会使他们生起故土之失的苦痛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入朝为官的理学家多有中原恢复之志,如吴儆、王炎等都是爱国忧民的理学诗人;而隐居山林的理学家,受理学的追求和隐居环境的限制,使他们趋于内敛,然不乏忧世之作,如汪莘《中原行怀古》表现出强烈的救世情怀、吴锡畴《闻雁》反映了诗人不能忘记中原故土之失这一事实。历史的发展是对南宋社会莫大的讽刺,不仅北宋失去的故土无法收复,最后连自己苟且安居的所有国土都落入蒙元之手。理学诗人难以承受这一丧国之辱,在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遗民意识。汪梦斗被特召进京,自出发到拒不受官而放还归家,舟车万里,客食二百七十日,“悲伤怀感,忧惧愁叹,不能自己,又每见之诗”[15]60,《道过茌平县感马周事》《过御河有感》等诗表示自己忠肝义胆却于国家灭亡无能为力;壮怀激烈的孙嵩,在诗中多抒发亡国之痛,如《秋怀五首》《曲江头》《竹枝歌》《明妃引》等表现了诗人对南国故土的深切思恋与沉重悲哀。
南宋“新安学派”诗人以徽州为程朱阙里,其对程朱理学的尊奉坚定而执着。“新安学派”的理学追求使诗人更为重视自身的学识素养、品行操守的提升,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其生活态度和理想价值,当诗人把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日常践履诉诸于诗歌载体时,与其说是进行艺术创造,毋宁说诗歌创作是“新安学派”诗人理学追求和涵养性情的一种方式,因此,诗歌不仅更多地展示了理学家的学识品行、道德情操和人格追求,而且传统的抒情言志被议论说理所挤兑和削弱,诗歌打动人心的感性形象、情感力量让位于启人心智的理性意蕴、道德价值和精神品格。不可否认,南宋是“新安学派”的形成时期,“新安学派”学者经历了从“共派而分流”到“异出而同归”[23]446、从积极入世向更重养性的发展过程,因此,“新安学派”诗人创作也不尽相同,南宋前期诗人比较外放,诗歌创作多以抒情言志为基本手段;中后期诗人大多内敛,诗歌以涵咏心性、表意明理为主要内容,情感态度平和泰然;宋亡之际,理学家追求的人格意志在国运改变的激召下生发出强烈的民族气节,理学诗人又有悲壮之作。上文主要从义理体悟、心性涵养、气格崇尚三方面,论析“新安学派”学者的人格追求和道德践履在诗歌创作中的艺术呈现,而“新安学派”的理学思想对诗人创作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变化等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1]牟宗三.道德理想的重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2]宋集珍本丛刊:第69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4.
[3]王炎.双溪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4]陈文忠.论理趣——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审美特征[J].文艺研究,1992,(3):59-67.
[5]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朱熹.朱子语类[M]//朱杰人.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朱熹.论孟精义[M]//朱杰人.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朱熹.诗集传[M]//朱杰人.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邵雍.皇极经世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罗大经.鹤林玉露[M].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詹初.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6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1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53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宋集珍本丛刊:第86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4.
[16]汪晫.西园康范存稿[M]//宋集珍本丛刊:第7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17]许月卿.先天集 [M]//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8]程洵.尊德性斋小集[M].上海:民国古书流通处.
[19]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朱松.韦斋集[M]//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1]程曈.新安学系录[M].王国良,张健,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
[2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8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3]程敏政.新安文献志[M].何庆善,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