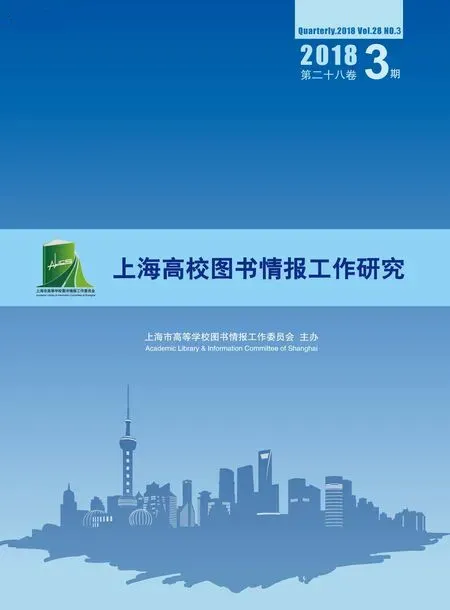浅谈民国藏书家叶启勋、叶启发藏书目录的特点与价值
——以《二叶书录》为中心
张宪荣(山西大学 山西太原 030006)
杨 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1 前言
《二叶书目》是民国时期湖南藏书家叶启勋《拾经楼䌷书录》(以下简称《书录》)、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以下简称《小识》》)两部藏书目录的总称。启勋(1900-1972),字定侯,号石礀后人、更生居士等,藏书楼名拾经楼。启发(1905-1952),字东明,号华鄂主人、朴学庐主等,为启勋之弟,藏书楼名华鄂堂。二人均为长沙著名学者叶德辉之侄,自小在其叔父的指导下精研版本目录之学。叶启发《小识序》云:“仲兄定侯及余方在髫龄,即侍砚侧。先世父时以各书板刻之原委,校勘之异同相示。余兄弟习闻训言,渐知购藏典籍。先世父更以《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一书,命余兄弟分任部居,纂编考核,著之诗歌,以相勉促。牵于人事,仅成十之四五。然定兄及余嗜书之笃,盖胚息于此时矣。”1叶启发撰,李军整理:《华萼堂读书小识序》,载《华萼堂读书小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据此可知,叶氏兄弟无论在藏书的喜好上,还是在版本目录的考订上,均深受叶德辉的影响。这也使二人不仅终其一生嗜书如命,而且即便在避难他乡时还考书如痴,最终成就了《书录》《小识》这两部特点鲜明、价值颇高的目录著作。
从收书数量上看,《书录》收录111部,《小识》107部2按,李军统计为《书录》109种,《小识》106种,实有误。其可能受到了叶启发的误导。《小识》所附的其中一篇题识称,在民国三十四年夏,陆续补入了六篇跋文,“共百零六篇”(第176页)。。除去重复的66部外,两目共收书152部3按,以上包含一书之不同版本,但并不包括合刻、附刻等著作(如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前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三十卷在统计时便算作了1种,因叶氏兄弟并未单列,而是在书中一并加以考证故也)。,虽数量有限,却大多为宋元明善本和名家旧校、旧抄,称得上是两部善本书目。但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叶氏兄弟撰写的题跋内容丰富,考证精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中,除了寻霖《<华萼堂读书小识>浅识》(图书馆,1996年第6期)、《三湘瑰宝 图苑奇葩——湖南图书馆藏宋元刻本掠影》(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5期)、刘雪平《从题跋看湖南近代私家藏书之盛——湖南近代藏书家题跋六种浅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等单篇论文初步对其进行介绍外,李军在整理《二叶书录》时前附的《整理说明》是比较系统的研究性文章。在该文中,李军不仅比较详细地考述了叶氏兄弟的生平经历及两部书目的刊印源流,而且还概括了两书的四个特点:客观记录,博考版本,实事求是,情文并茂。惜限于篇幅,未能展开论述。另外,李冰心硕士论文《长沙叶氏家学传承考辨》一文4李冰心:《长沙叶氏家学传承考辨》,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3-41页。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叶氏兄弟对叶德辉藏书思想和鉴别方法的接受。在思想上分为读书而藏、重小学类藏书、重明代精刻本等三点,在方法上包括辨版本之时代、订抄校之经粗、考卷数之多寡、重藏书印、记先辈佚闻等五点。同时还归纳了叶氏兄弟藏书的三个特点:嗜好宋元旧椠,重毛氏汲古阁本,重旧抄本。以上这些论述皆有夸大之嫌,但对本文的撰写有所启发。笔者拟在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两部书目的具体内容,对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 《二叶书录》的特点
2.1 详于考证,略于对书籍内容的描述和撰者事迹的介绍。
《书录》《小识》这两部书目虽然收书较少,但是对所收的每部著作皆有较为详细的著录。少者几十字,多者则有数千字。从内容看,叶氏兄弟并不是如《四库提要》等大多数叙录体书目那样侧重“考撰人之仕履,释作者之宗旨”1缪荃孙:《善本书室藏书志序》,载《善本书室藏书志》,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57页。,而是将大量的笔墨花在了考证版本相关信息上了。一书之中,举凡撰者、版本、钤印者、题跋者、题跋时间、批校者、作序者等,只要有可疑之处,皆不厌其烦地参照各种资料进行考订,从而使其在著录上较其他书目更加准确清晰。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1 考编撰者
叶氏兄弟两目虽不以叙述撰者事迹为重,但在涉及到撰者的某些问题之时,会参考多种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
如《类编长安志》十卷,琴川张氏影元抄本
此书为元骆天骧所编。叶启勋虽然明确说“天骧始末未详”2《书录》卷上,第51页。,但还是根据书首王利用序、书首题名及其自序推断其字飞卿,号藏斋,长安人,曾官儒学教授,为宋末遗民。
再如《岳麓书院图志》十卷,明嘉靖二十年刊本。
此书为明陈论所撰3《书录》卷上,第53页。。叶启勋云陈氏“始末未详”,但根据此本所附明正德九年陈凤梧序,指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陈氏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记载和《湖南通志·人物志》引《四川通志》陈氏“天顺中官巴州训导”的记载是错误的。最后推测此书是陈氏在此书院求学期间所撰。
统观全书,其实在撰者方面,叶氏并不像《四库提要》那样按部就班地叙述撰者事迹,大多数时候是省略不说的。除非有需要考辨的地方,如上面两例。由此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其书目侧重考证的特点。
2.1.2 考版本
(1)引用诸家书目,考订一书之刊刻时间或底本
如《伊川击壤集》二十卷,明成化庚子毕亨刊本。
此本前后无序跋,无法直接判断其刊刻时代。幸而叶启勋曾见一相同版本,前有成化乙未希古引,后有庚子毕庚跋,故初步推测其所藏之本可能即明成化间所刊。为了证明其推断,叶氏首先翻检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善本书室藏书志》等书目,发现二目所录之本的序跋与其所见之本相同,但未录行款版式,故无法确定具体版本。最后偶然在涵芬楼观书发现了同样的版本,序跋皆全,这才断定其所藏之本确实是成化刻本。
再如《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十五卷,日本翻高丽刊本4《小识》卷四,《二叶书录》第307-308页。。
此本有嘉靖二十三年柳希春跋、江宗白跋等。叶启发根据此两跋所述,认为此本为江宗白据明嘉靖二十三年宋麟寿刻本翻刻者,文内和训亦是江氏所加。由此其版本情况已经明了。但叶氏并不止于此,又参考《仪顾堂续跋》所收宋刻本与之相较,发现二本卷次相当,故又推断其源出宋本。
(2)引用相关资料,梳理一书之版本源流
对于一书的某个版本,叶氏兄弟很多时候不仅会参考多种书目考证其刊刻时间或底本,更会在此基础上进而追溯其源头,缕清其流传过程,从而更加清楚地展现出一书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
如《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旧抄本。
叶启发根据此本卷首钤印,初步断定其为康熙间曹寅旧藏。但此题作“旧抄本”太过笼统,尚不知其底本为何,抄自何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启发检阅了王士禛《居易录》,云:“世无刊本,予家有写本,阙七十余卷,竹垞尝借抄之,又借徐氏藏本补足六十余卷,尚阙第四卷及百十三卷至百十九卷,仅阙八卷。”根据这一线索,继而又检朱彝尊《曝书亭集》,果然有同样的记录,进一步验证了王氏的说法。最后又检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曹寅“交于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楝亭皆抄有副本”,其中便有《太平寰宇记》一书。根据这些材料,此本的版本源流便一目了然了,原来“此本为楝亭抄自竹垞朱氏,竹垞则合王、徐二家藏本凑配递录”5《小识》卷二,《二叶书录》第222页。。
再如《猗觉寮杂记》二卷,林善长抄本,鲍廷博、魏琇批校。
在收藏此本之前,叶氏已得到了叶德辉旧藏明谢肇淛小草斋黑格抄本。经两本互勘,叶启发发现,除了字句偶有遗漏外,此本之行款、每页起讫、字数、误字等皆与后者相合,故其底本显然为后者。但二者又是如何相互传抄的呢?于是叶氏又检阅了黄丕烈《藏书题跋记》和吴寿旸《拜经楼题跋记》,并结合此本中林阮等的题记,推断出谢氏抄本原归龚翔麟所有,继江声据之抄录,后林阮又据江声录本传抄,即此本1《小识》卷三,《二叶书录》第260页。。
2.1.3 考批校者
叶氏兄弟之书目所收书籍虽然不多,但其中名家批校之本却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有些批校审其题记和笔迹可以断定批校者,有些无任何版本信息者则需要进一步考证了。对于后者,叶氏不仅会根据相关资料推断出批校者姓氏,而且还会对之进行反复论述,以确保考证的准确性和正确性。
如《韵补》五卷,元刊本,张穆手校。
此本文内有朱笔校字和朱笔抹字,而无批校者姓氏。叶启发经与家藏多种张穆批校本相比较,推测此本之校语亦“出自石州手笔矣”。但书内既无张氏题记,亦无其钤印,所以尚不敢断定。为了寻求更多的证据,叶启发又取此书的宋本和张穆所校的清道光二十七年杨尚文刻《连筠簃丛书》本与此元刻本比勘,发现杨氏刻本在刊印时,张穆曾据宋本与此本互勘过。三本文字互有异同,而此本校语正与杨刻同,据此可以断定此本批语正是张氏所为。故而叶氏感慨地说“然使非三刻均在余家,则无从订其为石州所校矣”2《小识》卷一,《二叶书录》第204页。。
再如《求古录》一卷,旧抄本3《小识》卷二,《二叶书录》第245页。。
此本文内有朱笔校改,但无题字和收藏图记,故其批校者尚待进一步考证。叶启发首先将此本书根上何绍基的题字与文内校字相校,发现二者笔迹不类,故排除了何氏批校的可能。继检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中对此书的跋文,发现彭氏所云从库本抄出的原抄本中碑刻时代错置情况及避讳字与此本同,故二本实为一本。为了进一步确认,叶氏又家藏古香楼抄本《默记》中彭元瑞的朱笔校字与此本相校,发现二者字迹相同,故可以肯定此本确实为彭氏所校。
2.1.4 考校语时间或版本信息
叶氏书目对批校本校语所录的时间和版本信息非常在意,一般都会根据相关材料对之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
如《瀛涯胜览》一卷,旧抄本4《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55页。。
此本为翁方纲抄自纳兰成德家藏本,并以朱墨笔手校。卷端墨笔题“□□十九年岁在甲戌菊月,□□石墨书楼抄本共五十叶,同日手装并校。”卷末题“甲戌九月既望灯下校”。其中,“十九年”前面有阙,“甲戌九月”不知为何时。叶启勋根据《翁氏家事略记》中有关翁氏生平的记载,发现其所在的时代中,“甲戌”在乾隆、嘉庆两朝皆有,所以此本之“甲戌”尚无法断定。继而又检阅了家藏翁氏于嘉庆二十年所撰稿本《海东金石文字记》,经与此本笔迹相校,发现二本一致,故此本之“甲戌”当为嘉庆十九年甲戌,为翁氏晚年之作。
再如《绛帖平》六卷,大兴翁氏抄本,翁方纲手校5《小识》卷二,《二叶书录》第235-236页。。
此本书面翁氏题字云“乙未七月二十八日灯下识”,又题“辛丑正月六日,以官抄本校勘一遍,止有六卷”。其中,“乙未”“辛丑”不知何年,“官抄本”不知为何本。叶启发根据《翁氏家事略记》的记载,考出“乙未”为乾隆四十年,时翁氏为四十三岁,正供职于《四库全书》馆。辛丑为乾隆四十六年,翁氏四十九岁,仍在馆中,故此“官抄本”即《四库》抄本。
2.1.5 考钤印印主
对版式的描述在叶氏书目中并非每书皆有,但是书中的钤印则是凡有必录,印主亦随时进行考证。这其实跟叶氏兄弟的善本观有关。宋元旧椠或名家抄校如果再加上满书灿然的名家钤印,不亚于锦上添花。故叶启勋在明安氏活字本《初学记》末云:“历为名家藏庋,朱印累累,手迹可珍,又不仅活字本希见之足重矣。”6《小识》卷中,《二叶书录》第93-94页。又在宋刻《韦苏州集》末云:“手迹如新,朱印累累,又不仅以其为天水旧椠为足珍贵也。”7《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07页。由此可见,钤印在叶氏兄弟眼中已经成为评价版本价值的标准之一了。而对之的考证,也自然成为了书目的重点之一。
如《韵补》五卷,宋刊宋印本8《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30页。。
此本徐蕆序及卷二、卷四首钤“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朱文方印,又有“黄琳印”白文方印等,叶启勋分别根据《天禄琳琅前编》和《开有益斋读书志》《式古堂书画考》等的记载,对李廷相和黄琳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述。
其他如叶启勋引《清河书画舫题后》《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对旧抄本《宝晋英光集》“曹琰之印”“彬侯”的印主曹琰的考证,叶启发引《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持静斋书目》对清雍正三年汪亮采刻本《唐眉山诗集》“金元功藏书记”的印主金元功的考证,等等。
叶氏在考证钤印之时,有时会结合作印的时间来推断版本情况。
如《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武英殿聚珍本,翁方纲、何绍基批校。
此本钤有“主考两江”等印,叶启发考证翁方纲曾在“乾隆五十一年以詹事任江西学政”1《小识》卷三,《二叶书录》第257页。,故此印即当时评校诸书时所作,由此也可以知道翁氏批校此本的时间。
再如《张氏藏书五种》六卷,附七种八卷,明万历二十四年张氏刻本2《小识》卷三,《二叶书录》第271页。。
此本《被褐先生传》首钤“翰林院”满汉文大方印和“曾在鲍以文处”朱文方印。叶启发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前附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上谕的记载,认为前一印为进呈后四库馆发还原书时所钤,故此本为返还鲍氏之本。同时还纠正了叶德辉“进呈后钤印发还翰林院”的错误说法。同样,叶启勋所藏明成化十六年毕亨刊本《伊川击壤集》也钤有这两印,叶氏据阮元《知不足斋鲍君传》和王亶望《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记载,得出了与其弟一样的结论。
以上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叶氏书目侧重考证的特点,其实还有考书名(如《书录》所收《风雅翼》《选诗》)、考篇卷分合(如《小识》所收《王临川先生文集》)、考牌记时间(如《书录》所收《八叉集注》)等等多个方面。但无论是哪个方面,都体现出了叶氏兄弟在考证这一点上的痴迷。
2.2 重在辨析诸家藏目、前辈观点之谬误和补充其不足
叶氏兄弟的书目不仅引用诸家藏目和前辈观点进行考证,更在考证的同时指出其谬误,并补其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2.2.1 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之谬
《四库提要》是清代中期以来官方编订的最为权威的书目。自其刊行以来,学者无不奉为圭臬。清代以来藏书家或仿其例编订藏目,或以其论说录于其目,如《爱日经庐藏书志》《皕宋楼藏书志》等,但鲜有订其谬误者3在此之前和同时,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续跋》、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对《四库提要》都有所订补,但条目所占比例在全书中并不是很集中。。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可谓较为集中订正此目的私家目录之一,书中征引公私藏目凡三十多部,其中对《四库提要》凡80次,远远超出其他藏目4陆倩倩:《<郋园读书志>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55-56页。。在如此多次的征引中,叶氏对该目所著的版本、刻者、卷数等多有辨正5罗瑛《叶德辉<郋园读书志>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第47-52页。,体现出叶氏此书鲜明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又被其两个侄儿继承了下来,故在《书录》《小识》中随处可见考辨《四库提要》的条目。今试举几例:
(1)《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旧抄本
此本为曹寅传抄朱彝尊抄本,原阙八卷。《四库》所收来自汪启淑家藏本,云“仅佚七卷”6《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48页。,叶启勋检《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后发现汪氏藏本实为八卷,与其所藏之本卷数正相合,故其云《四库提要》所录卷数“不足信也”7《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49页。。
(2)《瀛涯胜览》一卷,旧抄本
此书撰者为马欢,可是《四库提要》却著录为“马观撰”8《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55页。,实有误。
(3)《六艺纲目》二卷,附一卷,旧抄本,何绍基批校
此书《四库提要》云“刊于至正甲辰”9《小识》卷一,《二叶书录》第207页。。叶启发通过检阅此本卷前所附四序跋年月后发现,最晚作序时间已经到了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了,故馆臣所云的刊刻年月“殆不尽然矣”10《小识》卷一,《二叶书录》第207页。。进而叶氏又据此本末附舒睿跋文,推测出此书虽然有至正诸序,但是刊刻已经到了明初1《小识》卷一,《二叶书录》第208页。。不仅指出了《四库提要》之谬,而且还纠正了其谬。
(4)《宝刻丛编》二十卷,大兴翁氏抄本,翁方纲、丁杰、钱馥批校
此书《四库提要》所据亦为抄本,阙卷已一一列出。叶启勋将此本与之相校,发现馆臣所列诸阙卷尚遗漏了三卷。同时,还将“京西北路”误作了“京东北路”。
以上四例中,第(1)条纠正《四库提要》卷次之谬,第(2《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50页。)条纠正撰者之谬,第(3)条纠正刊刻年月之谬,第(4)条纠正著录内容之谬。此外尚有很多例子。在叶氏兄弟二目中,虽然有一些引《四库提要》考证一书版本的条目,但是很多时候对之持批判态度,或指责为“肊度之辞”(《书录》所收《巽隐先生集》),或称其“考证偶疏,未及详辨”(《小识》所收《求古录》)。甚至对军机处当时所禁毁之书也多方加以维护,如在明张溥《七录斋文集》下云:“盖明末诸公,目睹祖国沦亡,故宫禾黍之思,发为悲愤之语。究之一代易祚,无不有二三死节之臣,亦无不有二三遁迹逃名之臣。后之入主者,既欲我只臣忠于我,而嫉人之臣忠于人,有是理乎?”2《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50页。叶启勋用悲愤的语言不仅斥责了乾隆寓禁于征的行为,还包含了对被禁诸公的同情。
此外,叶氏兄弟对《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也有所订正,如《居士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明天顺六年黑口本,《书录》云:“此本近涵芬楼影入《四部丛刊》,沿《天禄琳琅》之误,定为元板。余取二本对勘,版框、墨线、字体无一不同。所谓字仿欧波,定属元时重刊宋板者,即此本也。苏集取《书影》载本比校,乃知瞿氏所谓元本者,亦即此本。藏书家目往往以元本为宋本,以明初本为元本,自欺欺人。其实此明仿宋之至佳者,固不必强跻于元板方足珍贵也。”3《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18页。不仅纠正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之谬误,而且还指出藏书家鉴定版本之谬误和明代仿刻宋本之珍贵。
2.2.2 正诸私家藏目和前辈之谬,或补其不足
《书录》《小识》考证诸书时引用诸家藏目和诸家之说颇多,如陆、丁、瞿、杨四家书目及前辈黄丕烈、缪荃孙、莫友芝等,皆有所订正。即便是其伯父叶德辉,亦毫不为之隐讳。今试举几例:
(1)《韩诗外传》十卷,明嘉靖十八年薛来芙蓉泉书屋刻本
《书录》引傅增湘之说梳理了该书的版本源流,其中通津草堂本为苏献可所刊,野竹斋本为沈与文据苏本改刻牌记为之,芙蓉泉书屋本为薛来于明嘉靖十八年所刻。可是丁丙《善本书屋藏书志》在著录“通津草堂本”的时候说“弘治后历下薛来、新都唐琳、吴人苏献可及周廷宷先后传刻,此则沈辨之通津草堂原刊初印本也。”叶启勋指出丁氏是“既误以通津草堂为沈辨之,又不知薛本刻于十八年,亦可谓疏漏之甚矣。”4《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17页。
(2)《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明正德十五年刘氏安正堂刻本
此本前后无序跋,惟末卷末牌记题“庚辰岁孟冬月安正书堂新刊”。叶启勋根据诸家藏目的收录状况,首先考出安正堂为书林刘宗器之刻书堂号,其刊刻在明代已逾百年。继而检得家藏与此本合刊者《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一书末牌记题“正德己卯年仲夏月刘氏安正堂刊”,故此“庚辰”乃正德十五年5《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03页。。而《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皕宋楼藏书志》在著录其所藏安正堂本诸书时皆以元刻本视之,实有误。
(3)《小字录》不分卷,《小字录补》六卷,明万历七年沈弘正刻本
此书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和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皆云有两明活字印本,一本卷端次行题“陈思纂次”,另一本于三行另题“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这两本是什么关系呢?瞿、黄以为前一本原为吴郡孙凤所印,后板归吴氏,据之重印,故后者卷端多出一行题字,这样看来二本其实是前后印的关系。叶启发对此则有所怀疑,他反驳道“活字印书随印随散,安有以板归人之理”6《小识》卷三,《二叶书录》第273页。,故推测明代的两个本子其实一个是活字本,另一个是据活字本重刻本,故行款皆同。瞿、黄二人是将两个不同的本子误当作同一本了。
(4)《铁崖古乐府》十卷,《复古诗集》六卷,元至正二十四年刻本
此书在元代刊行之后,明成化间叶盛命广州郡守沈礼亦曾刊行,同时昆山王益又据之重刊。而杨绍和《楹书隅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著录的“明成化己丑沈礼翻元本”前有王益序,后有刘傚跋,显然为王氏重刊明成化间沈礼本。故叶启发云二目皆“误以两刻为一本也”1《小识》卷四,《二叶书录》第316页。。
(5)《论衡》三十卷,明嘉靖十四年通津草堂刊本
此本目录末牌记题“嘉靖乙未春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勘”,版心题“通津草堂”四字,《书录》据此推测云“盖通津草堂为苏献可刻书堂名”,而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和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既著录明通津草堂本,又著录嘉靖乙未苏献可本,是将一刻误作了两刻。而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更将此本误作了袁褧所刻。叶启勋指出这都是“未见原书”之谬2《书录》卷中,《二叶书录》第82页。。
(6)《默记》一册,海昌吴氏抄本
此本校跋朱墨笔灿然,其中墨笔校字,叶德辉不知出自何人。《书录》则根据吴骞跋“癸巳岁,余假得以文本,吾友朱君云达为余手校,且以意改其豕亥”,断定“墨笔为朱云达手校”3《书录》卷中,《二叶书录》第95页。,从而补充了叶德辉考证之不足。
2.2.3 兄弟互订讹误
一般而言,对于同一部书籍,叶氏兄弟所作题跋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题跋内容也尽量会做到互相补充。但有时候,当兄弟一方在考证时出现讹误的时候,另一方会直接提出来,而不会为亲者避讳的。
(1)叶启勋订正其弟之失
如《张右史文集》六十卷,长洲何氏抄本。
此本为叶启发在民国二十年得自何绍基家,其题跋详细考证了书衣所题时间、编订者。同时又考证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宛丘集》七十六卷本的底本和《善本书室藏书志》所录《宛丘先生文集》八十二卷本的编订者等4《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25页,又见《小识》卷四,《二叶书录》第301-302页。。叶启勋通过检阅丁氏所引《文瑞楼书目》《清吟阁书目》,发现两目所录卷数与丁氏所引并不符合。同时又检阅《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载,发现与四库馆臣所录亦有出入。这些都是叶启发所忽略而其重新考证的。所以他说“叔弟东明考之未审,因书此以谂之”5《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24页。。
(2)叶启发订正其兄之误
如《石刻铺叙》二卷,《绛帖平》六卷,旧抄本。
此本文内有朱笔批校,又有何焯、朱筠等跋。叶启勋根据朱跋“中有朱笔校勘,乃何义门之笔”的说法,也认为文内校语来自何焯。但叶启发通过仔细比勘,发现了两点疑惑:第一,此本的批语与家藏何氏批的《才调集》字迹不同;第二,此本书首有朱笔批“卷首皆义门先生跋语,殊不类屺瞻口吻”,而所抄诸条跋语皆用墨笔抄写,如果此本为何焯手自批校,则应皆用朱笔。据此两点,叶启发推断此本为“旧人传录义门批校之本”,故著录上不取其兄“何义门评校”之说6《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60页。,而改为“传录何焯批校”7《小识》卷二,《二叶书录》第232页。。
2.3 意在揭示所藏之书的版本价值
从整体上看,叶氏兄弟所收诸本大多为宋元旧椠、明清佳刻,旧校旧抄,故无论是考证、还是辨误,最后都会落到揭示其所藏之本的价值上来,因此稀见、孤本这些类似的文字常常出现在文内。而在具体的探讨当中,又可分为以下几种不同情况:
2.3.1 引用诸家之说强调一本之价值
如明刻大字本《历代帝王法帖释文考异》十卷,叶启勋首先引《四库提要》之说肯定了此书为“读《阁帖》者不可少之书”,继而引《善本书室藏书志》所录“影抄本”之说,认为“此虽明刻,固当与宋元旧椠同其珍贵”8《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65页。。这样通过引两家之说,不仅强调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更揭示了其所藏本的版本价值。再如明毛晋汲古阁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二卷,叶启发引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之说来强调汲古阁影抄本备受世人推崇,从而说明其所藏之本亦是“纸墨抄写,无不精绝”9《小识》卷一,《二叶书录》第205页。。
2.3.2 通过版本校勘突出一本之价值
列举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其实在叶氏书目中并不多见,但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通过诸家书目所列异文与其藏本进行比较来突出其藏本价值。
如明仿宋本《山海经》下,叶启勋首先引《平津馆藏书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的说法来强调“仿宋精刊,已为藏书家所推重”,继而引尤袤对自己所藏“定本”分卷及卷后题衔等的描述与此本相比较,发现二本一一吻合,故其最后说“此书处宋本外,要当以此本为最善”1《书录》卷中,《二叶书录》第97页。。
(2)通过传世诸本与其藏本进行比较来突出其藏本价值。
如在宋刊本《梦溪笔谈》下,叶启勋通过与《四部丛刊续编》所收的明覆宋本比较,发现后者不仅行款与宋本相异,文中的字句亦有颇多讹脱,故感慨地说“信知宋刻之佳矣”2《书录》卷中,《二叶书录》第83页。。 同样,在毛扆据宋本所校的汲古阁本《春渚纪闻》下,叶启发列举了汲古阁本异于宋本的诸多脱误后,亦云“书贵宋椠,信然”3《小识》卷三,《二叶书录》第264页。。其实他并未收藏宋刻,而是强调在宋刻久佚的情况下其藏本中毛扆校语的可贵。
(3)通过所藏的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来突出其藏本价值。
如《宝刻丛编》一书,叶启发收藏了两个本子,一为旧抄本,一为大兴翁氏抄本。经过相互比勘之后,叶氏发现二本行款、阙卷、避讳等均同,故可断定“其源出一本”4《小识》卷二,《二叶书录》第237页。。但前者诸卷缺文较多,且凡引书相同而前后相续者皆不逐条分注,而于末条总注“以上均见某书”,由此可见其不仅内容不完整,而且不遵从底本旧式,自然在价值上较后者低些。
2.3.3 通过梳理版本源流显示一本之价值。
如宋乾道扬州州学刊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下,叶启发通过翻检《皕宋楼藏书志》《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铁琴铜剑楼书目》等诸家书目后对此书版本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宋时有乾道扬州刻本、元泰定时补板印行,元时有小匡子刻本,明时有两黑口本。“诸本行款相同,避讳空格亦同,则均源出乾道扬州本之故尔。”5《小识》卷三,《二叶书录》第261页。由此再看叶氏藏本,恰为诸本之所自出,故其价值自然在诸本之上了。
以上较为详细地从详于考证、重在辨误、意在揭示版本价值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叶氏兄弟藏书目录的特点。可以看到,虽然二目收书不是很多,但是在具体著录上却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此外,详述一本的递藏源流和收藏经过,介绍与某书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备掌故也是这两目较为突出的特点。因限于篇幅,故不一一列举了。
3 《二叶书录》的价值
叶启发《小识序》云:“仲兄定侯及余方在髫龄,即侍砚侧。先世父时以各书板刻之原委,校勘之异同相示。余兄弟习闻训言,渐知购藏典籍。”又云:“余兄弟每得一书,必互相考审,缀以题跋,或呈先世父加以鉴定,《郋园读书志》中颇多为余兄弟题跋之书也。”6叶启发撰,李军整理:《华萼堂读书小识序》,载《华萼堂读书小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又一题识云:“《(郋园)读书志》《䌷书录》《小识》体裁悉同。”7叶启发撰,李军整理:《华鄂堂读书小识·题识》,载《华萼堂读书小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据此可知,叶氏兄弟不仅自小在叶德辉的指导下学习版本目录之学,渐渐养成了一种每得一书便缀以题跋的习惯,而且《书录》《小识》也是受《郋园读书志》的影响编纂而成的。所以,此二目的编纂思想、体例等无一不与《读书志》相似。但是相似并不等于相同,正如雷恺在叙《小识》时说的“盖本之吏部《郋园读书志》,稍有变更也”一样,其中的“稍有变更”正是体现了叶氏兄弟藏目有别于其伯父《读书志》的独特价值。
那么,其价值到底何在呢?
首先,重视对所藏书籍的考证和诸家书目的辨正使得叶氏书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考订内容的丰富性,还体现在特别注重对考订过程的展现上。
前文已经论及,考证群籍是此二目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种考证并不注重对书籍旨趣的揭示和撰者事迹的介绍,而是将重点放在“辨版刻之时代,订抄校之精粗,考卷数之多寡,别新书之异同”上了8见叶启勋《郋园读书志跋》,载《郋园读书志》末,郋园先生全书本,第211册。,所以举凡撰者、版本、校跋者、校跋时间、钤印者等等,只要有疑的地方,叶氏兄弟都会引用多种资料进行考证。值得一提的是,在考证的过程中,有时为了验证其观点的正确性,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多方引证,反复推求,力求做到言而有徵,如前文提到的对《求古录》批校者的考证等。如果发现其引证材料有失误,甚至还会花费笔墨进行大量的纠谬补缺工作。这使得此二目内容丰富、考订准确,具有了很强的学术性。
从目录学史的角度看,考订并不是叶氏书目的独创,考订版本也不是其独有的。自清代中期以来,对版本的考订其实已经成了诸家编写藏书目录的时尚,所谓“解题内容版本化”1严佐之:《清代私家藏书目录琐论(代前言)》,载《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即指此,这可能是乾嘉考据学向版本目录学渗透的结果。但是从整体上看,即便是再自由灵活的诸家题跋记(如《荛圃藏书题识》《仪顾堂题跋》等),可能会详细考证撰者、版本等某一项,但并不会花费大量笔墨去展现其考证过程(非校勘内容)。即使是叶德辉《读书志》也往往如此2按,《读书志》很多题跋都会略去引证材料的具体内容,考证过程也较为简略。。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叶氏兄弟大量的考订性文字,在清代以来的各类私家藏书目录中都是少见的,这也是笔者在前文中说其“形成自己鲜明特点”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叶氏书目中,并不是篇篇题跋都是如此,但如此特点的题跋并不在少数。叶启发云:“大伯父……尝训启发曰: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何可尠视?昔贤尝以一字聚讼纷纭,故予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3见叶启发《郋园读书志跋》,载《郋园读书志》末,郋园先生全书本,第211册。重视考订的习惯是叶氏兄弟在叶德辉的训导下渐渐养成的。然而从具体书目上看,兄弟二人其实比其伯父考订得更为精细。
其次,注重收录宋元明旧椠、明刻初印、名家批校之本,而以稀见、精刻、旧校(抄)为标准,由此可以体现叶氏兄弟的善本观。
在叶氏兄弟之前,善本的观念和标准早已形成,只不过在具体的收书范围上诸家见仁见智。学者们常常引用叶德崟跋《读书志》时转述叶德辉所说“各家题跋日记于宋元佳处已详尽靡遗,虽有收藏,毋庸置论。惟明刻近刻他人所不措意者,宜亟亟为之表彰”等的言论4见叶启崟《郋园读书志跋》,载《郋园读书志》末,郋园先生全书本,第211册。,认为叶德辉比起宋元旧椠,更重视对明清精刻的收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从《读书志》的收录数量,还是具体评价上,叶德辉都流露出对这些本子的推崇。自然,深受伯父影响的叶氏兄弟,在他们的书目当中,明刻本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5叶启勋在《艺文类聚》下云:“宋元本既不可得,于是藏书家重视明本。”此处虽然说的是《艺文类聚》的版本,但是也可反映出其重视收藏明本的原因。,由此可见他们对叶德辉善本观念的继承。但是从具体的题跋内容上看,叶氏兄弟也有自己对藏书的一些看法,并非盲目遵从其伯父之说,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推崇宋元旧椠和名家抄校之本。
(2) 不太重视时代较近的刻本,除非有名家批校。
(3)明刻本并不一味加以推崇,而更重视其初印和稀见之本。
(4)宋元明佳刻,如果再加上名家批校,或朱印累累则更具值得推崇。
关于第(1)条,叶氏兄弟在多处题跋中均有论述,如在《书录》卷上元刻本《汉雋》下云:“书旧一日好一日,毋怪乎藏书家之佞宋癖元矣。”6《书录》卷上,《二叶书录》第48页。在卷中明仿宋本《山海经》下云:“孰谓书无庸讲本子耶,更毋怪藏书家之佞宋癖元矣。”7《书录》卷中,《二叶书录》第97页。在《小识》卷三明汲古阁刻本《春渚纪闻》下云:“书贵宋椠,信然。”8《小识》卷三,《二叶书录》第264页。可见,宋元旧椠在叶氏心中是具有很高的地位的,因为它们或为后世诸本之祖,可补其讹误阙脱9如宋九行大字本《周书》下,叶启勋经与毛氏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比勘,发现有些条目为后两本所无,且云:“其他正讹补脱者尚不胜缕举。”,或在诸家藏目中鲜有收录,为海内孤本10如宋刊本《宣和图谱》下,叶启勋云:“余后于慎且数百年,得此宋刊秘帙,为历代藏书家所未见,不可谓非至幸。而此书不仅为天水精刊,且系海内孤本。”。同时,名家稿本、抄本和校本与宋元旧椠也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如在此二目中便收录了好几部黄丕烈手跋本,且对之推崇备至11按,叶氏所藏黄跋本有高丽纸印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十五卷,国初抄本《石门集》二册,明嘉靖元年吴氏刊本《巽隐程先生集》四卷,明刊黑口本《东里诗集》三卷,明嘉靖三十七年黄姬水刊本《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三十卷。其中,在《石门集》下,叶启勋云:“荛圃于书目别开一派,既非如《直斋》之解题,又非如《敏求》之骨董,南北藏书家琳琅插架,无非黄氏吉光片羽之留遗,至今旧籍中有士礼居藏印之属,几与宋元旧椠同其珍贵。”。
关于第(2)条,我们可从叶启发的题识中得到验证。叶氏曾说:“《小识》所录应专取宋元明旧椠及批校抄本为主。”由此出发,他还打算将原本收录于《小识》的《来斋金石刻考略》《清异录》等6篇跋语移入附录,因为这几部“刊刻时代太近,亦非旧人批校”1叶启发撰,李军整理:《华鄂堂读书小识·题识》,载《华萼堂读书小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6页。。由此可见,在叶启发眼中,时间太近的书籍如果“非旧人批校”者皆不应收录,这跟叶德辉《读书志》中收录范围是有一定区别的。
关于第(3)条,学者或根据此二目中明刻本的比例来说明叶氏兄弟重视明代精刻本2见李冰心《长沙叶氏家学传承考辨》,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8页。,但其实这只能说明其藏此种版本丰富。如果从题跋内容上看,并不是所有的明刻本都受到推崇,有时反而持有批评态度,如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刊本《旧唐书》下,叶启发开篇便云此本“当时仅据残宋本重刻,又有所窜改,不足贵也。”(按,此本有叶石君批校,故又可见其珍贵。)3《小识》卷二,《二叶书录》第212页。而除名家批校本外,只有那些初印或者稀见的明刻本方才最受叶氏兄弟的推崇。如明嘉靖十九年陈敬学刻本《万首唐人绝句》下,叶启发云:“此书世无宋本全帙流传,此为仿宋精刻,而绵纸初印,触手如新,虎贲之貌,似非其他明刻所可比拟者。”4《小识》卷四,《二叶书录》第344页。又如明项德棻宛委堂刊本《石林避暑录话》下,叶启发云其“源出宋椠,而刻画精美,又流传极稀,存之以备参考,固不必求全责备矣”5《小识》卷二,《二叶书录》第267页。。
关于第(4)条,叶氏书目中随处可见。如叶启勋在明安氏活字本《初学记》末云:“历为名家藏庋,朱印累累,手迹可珍,又不仅活字印本希见之足重矣。”6《书录》卷中,《二叶书录》第93-94页。在宋刊本《韦苏州集》末云:“此书经李中丞收藏,转入郑氏,一再辗转而为余有。手迹如新,朱印累累,又不仅以其为天水旧椠为足珍重也。”7《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07页。在明仿宋本《杜樊川集》末云:“然近来明刻日希,如此仿宋精美,又经何蝯叟逐卷加评,名贤手泽,固当为此书增重矣。”8《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10页。而其在《笠泽丛书》下说得更明确:“善本书而加以名贤手迹,以为镇库物,不亦大快意事乎?”9《书录》卷下,《二叶书录》第112页。
由上四点可知,叶氏兄弟主要是以稀见、精刻、旧校(抄)为标准收录群籍,并且在此标准下对其所收诸本进行褒贬品评的。这种善本观其实与乾嘉以来大多藏书家的观点一脉相承的,但叶氏又将对其善本的态度纳入到了具体的考订过程当中,使人知其为何珍贵,珍贵在何处。在这一点上,应该是较大多数私家藏目详尽和明确得多的。
最后,一些掌故特别是与叶氏家族相关的掌故更具有史学价值。
在藏书目录中载录相关掌故,这是清代以来诸多私人藏书家一直乐此不疲的事。在叶氏兄弟藏目中,掌故的记录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有些为人所熟知,如王延喆刻《史记》等;有些则非由叶氏兄弟揭示则不可知,如叶启勋在宋本《说文解字》和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下讲述了影印《四部丛刊》的编印缘起;在明景泰六年刻本《古廉李先生诗集》下花了大半篇幅介绍了有关方功惠、李亦元的藏书故事;在叶万校明闻人诠刻本《旧唐书》下讲述了其从兄某的种种恶迹10按,“从兄某”一般以为是叶德辉之子,但李冰心《长沙叶氏家学传承考辨》(湘潭大薛硕士论文,2015,第14页)据叶启勋《书录》和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对通知堂本《经典释文》的记载推知为叶德辉之侄叶启崟。。叶启发在宋衢州刻本《古史》下讲述了何诒恺将何绍基书散出的缘由,在稿本《来斋金石刻考略》下考订《四库全书》的书写格式。如此甚多,皆有利于在了解一书版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多的相关文献资料,具有颇高的史学价值。
4 结论
叶氏兄弟《书录》《小识》在具体分类和题跋体制上,基本上是与叶德辉《读书志》一脉相承,所以本质上属于一种题跋记体的藏书目录。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云叶德辉书目是“合考证、校雠、收藏、鉴赏为一家言”,叶氏兄弟二目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只不过较之更加详尽而已,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其目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书录》《小识》虽为二目,实同一目,因为其中所收书籍很多是兄弟俩互相题跋的。而且题跋内容往往会此详彼略,互相补充。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将此二目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