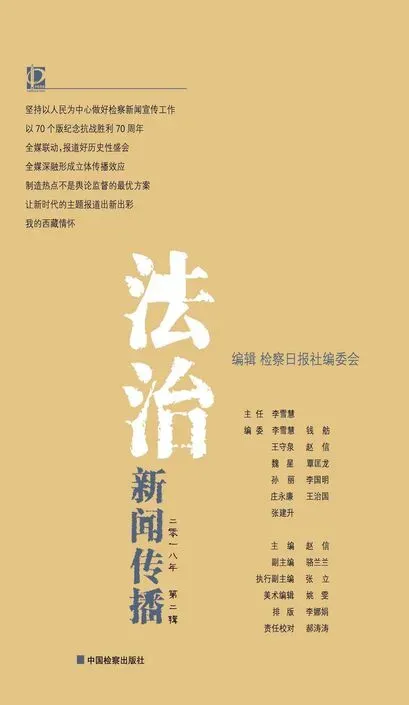制造热点不是舆论监督的最优方案
■孙祥飞
经过主流媒体的报道和社交媒体的议论,在十年前早已经盖棺定论但不为人知的汤兰兰案以全民热议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尘封的历史再度成为热点新闻,司法案件也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媒介事件。在这个案例面前,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媒体在报道汤兰兰案时扮演了何种角色;第二,媒体对汤兰兰案的报道是否有助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传播;第三,在较为敏感的涉法话题面前新闻媒体如何实施舆论监督。
汤兰兰案:媒体制造的新闻热点
2018年1月底至2月中旬,汤兰兰案经由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后,原本发生于十年前的旧闻迅速成为热门网络话题。新闻事件能够成为社会热点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媒体的集中报道,二是公众的集中关注。从数据来看,自2018年1月30日澎湃新闻报道《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之后,截至2018年2月14日23点59分,全网至少有61.53万篇/条与“汤兰兰”相关的新闻报道或网民议论。
媒介中的热点事件是媒体报道和公众议论共同作用的结果。汤兰兰案能够获得如此密集的网络关注度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以澎湃新闻等为代表的媒体从陈年旧事中挖掘出“惊世骇俗”的“猛料”,这些“猛料”涉及大规模的性侵,既能迎合一般受众对猎奇性新闻素材的特殊偏好,也能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宏大社会环境中寻找到某些契合点。
媒介具有制造热点事件的重要功能,这早已在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等关于媒介事件的研究中被证实——它是新闻传播主体梦寐以求的“拳头产品”,意味着在新闻信息严重过载及用户注意力高度稀缺成为信息时代主要矛盾背景下,新闻记者及媒介机构依然拥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价值观建构能力和舆论导向作用。戴扬、卡茨认为,“媒介事件可能通过鼓励或抑制偏爱、价值或信仰的表达而影响大众舆论”。①遗憾的是,此次报道汤兰兰案的媒体没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反而成为热点新闻事件的制造者——媒体除了提供了若干在短期内暂时无解的问题并将舆论的“火力”对准司法机构和案件中的受害者外,我们看不到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也看不到媒体的报道承载了何种积极的法律文化,仅存的只是骇人听闻的案件情节以及纷至沓来的网络争论。在汤兰兰案从幕后走向台前的过程,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法治文化的传播者和司法的舆论监督者,不如说是新闻事件的制造者。
尺度与效果:新闻报道的素材选择
通过对近年来若干新闻事件的观察可以发现,媒体自身被质疑的频率有进一步加大的倾向。尽管这从侧面上反映出网络公众的媒介素养正在不断提升,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媒体的公信力正成为被诟病的对象,例如新近几年来新闻反转、媒介审判、新闻炒作等案例时有发生。在此次汤兰兰案中,舆论界和知识界所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案件本身的若干细节,更包括对媒体的批评和质疑,尽管仍有不少网络观点认为媒体并没有明显瑕疵,但持反对意见的观点也不在少数。有关对汤兰兰案报道的批评性观点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层面:第一,媒体及记者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第二,媒体及记者存在着为罪犯洗脱嫌疑的倾向;第三,媒体在报道时带有较大的主观倾向;第四,媒体提出了若干扑朔迷离的问题但没有提供真相。
笔者认为,汤兰兰案在由陈年旧案转化为热点事件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并非上述提及的四点,而是媒体在面对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时选择了不恰当的处理策略。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具有舆论监督、教育大众、传承文化等若干重要功能,并可在受众的认知、情感、行动三个层面产生或长或短的影响,而最能够承载这些功能并能实现其传播效果的新闻便是那些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有可能引发密集关注的新闻话题都要毫无保留地进行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若干重要场合提及新闻传播要注重“时、度、效”的问题,譬如,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要“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②其中的“度”包含尺度的含义,而“效”也包含了社会影响的范畴。因而,新闻报道要综合考虑其素材性质、社会环境和社会影响等多种因素。从新闻素材的角度看,汤兰兰案因涉及大规模的性侵、未成年人保护、性别领域的争论等若干问题属于较为敏感的议题,从传播效果来看,案件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并没有承载积极的法治意义。
媒体的角色:做法治中国的建设者
在互联网信息严重过载的时代,生产出具有轰动性的新闻是媒体和记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中国的媒体不同于西方纯市场导向的媒体。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新闻不能为了所谓的影响力或点击率来制造轰动效应,而是要平衡群众性和导向性,充分做到既不趋利媚俗又不远离市场,既要舆论监督又要注意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③从法治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助推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并能真正生产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即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个层面的兼顾。
新闻媒体通过新闻素材的选择和新闻事件的报道来反映社会现实、建构舆论话题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不断培养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倾向。涉法案件的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首先,案件报道的理想模式应具有法律导向和群众思维两个基本前提,做到既能获得公众的广泛关注又能承载积极的价值导向;其次,案件报道的理想效果应该是助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入耳入脑入心或者正当地实施了舆论监督的职能。简而言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应该扮演建设者的角色——它不应该止于对社会事实的简单记录,也不能止于提出若干的问题,更不应一味追求点击率而忽视其社会影响。
当然,媒体对汤兰兰案的密集关注有一个看似比较合理的解释:新闻报道通过呈现一起疑似“冤假错案”的若干困惑来实施舆论监督功能,敦促司法机构能够合情合理合法地重新思考其中的若干疑点,进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及确保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显而易见的是,汤兰兰案尽管有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度,但未生产出与之匹配的积极影响力——传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宪法法律尊严的意义,已经被性侵是否属实、媒体是否有错、被告有无串供、司法是否公正等更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稀释、取代。
简单地讲,新闻报道需要实现导向和市场的兼顾,如果两者不能兼顾,新闻媒体所秉持的原则应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汤兰兰案中,媒体的报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超其正面影响,媒体的意图如果是单纯地纠正“冤假错案”,则大可不必采用公开报道的方式向全社会讲述一起扑朔迷离的“法治故事”,完全可以采用内参、专报、要报等方式向有关部门递交。内参也是新闻记者的新闻产品之一,尤其是对这种可能引发高关注度并存在争议的新闻事件而言,通过内参的渠道向有关部门呈送,一方面仍可以实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另一方面更可避免新闻事件进入大众视野后引发不必要的舆论风暴。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凡是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的新闻一定会为新闻的生产者带来超高的流量以及可观的经济收益,相反,内参虽然有助于争议性的问题得到解决且不容易引发舆论风险,但不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媒体不选择内参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注释:
①【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4-02/27/content_2625112.htm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