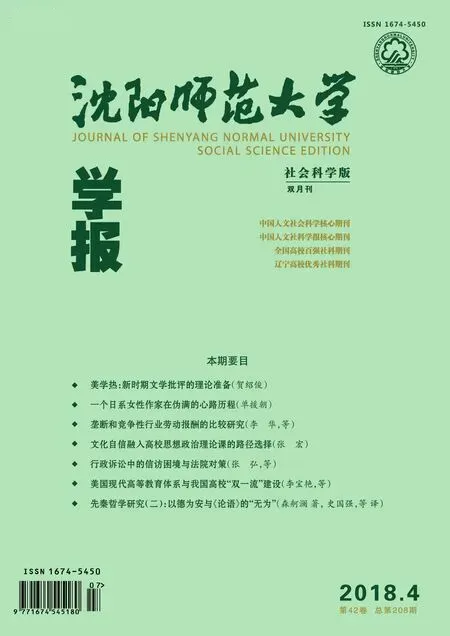战争末期伪满日语杂志《北窗》时评专栏中的作家视角
祝 然
(大连外国语大学 软件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正式向美英宣战。根据同年12月的内阁决议(东条内阁),此次战争被定名为“大东亚战争”。随后,侵华战争、日荷战争及日苏战争也一并被划归大东亚战争范围内。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文艺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积极的响应。在《旧殖民地文学研究》一书中,尾崎秀树曾就该时段日本文艺界的整体动态做出过简练地总结。
自从12月8日对美英宣战,先后召开了文学者爱国大会、创立日本文学报告会、召开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学徒出征、大日本言论报国会起步、召开第二次决战大会、创立日本出版会、整合全国新闻出版业,下调征兵年龄,决定决战非常措施要纲、特工队出阵、第三次南京大会——单从发生于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间的几次重大事件来看,便可以切身领略到其揣步紧随决战体制的情形[1]。
在尾崎秀树所列举的事件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尤其值得注意。作为日本文艺界积极回应“大东亚战争”的产物,“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会议精神无疑成为彼时日本文艺界的主体精神导向。它的主旨精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其一,“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国文化人必须互助协作;其二,促进文化人参战——在其号召之下,处于伪满洲国地区的日本文人、文学团体纷纷做出积极响应,满铁哈尔滨图书馆馆报、日语综合杂志《北窗》也不例外。
杂志《北窗》发行于1939年5月至1944年3月之间,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日语综合杂志,所刊文章文学作品居多,被视为“北满”地区日语文学的主要载体之一。为响应“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号召,《北窗》在对其栏目构成进行调整的同时,还根据时局需要新增了一系列专栏,其中最具时代性的莫过于第四卷第一号至第五卷第四号的“北窗时评”。
“北窗时评”篇幅大约三页稿纸①,占据一页版面。其内容涵盖了伪满洲国文艺界的各个领域,既有“论坛时评”“文艺时评”“歌坛时评”“美术时评”
① 每页稿纸400字。
“音乐时评”等分门别类的栏目,也有针对文艺创作整体状况进行阶段性品评的“创作时评”。这一系列栏目在向读者介绍文艺界诸多动向的同时,还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论。大东亚战争爆发于1941年12月,杂志《北窗》紧随其后在1942年推出“北窗时评”专栏,从其登场的时间点来看,这些专栏无疑都是顺应时局的产物,它们所承载的政治使命、所具备的时代属性不言自明。本文选取“北窗时评”中有关文学方面的文章,就论坛、歌坛、俳坛、文艺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从而以这些日本作家的视角对战争末期的日本殖民文学进行详细解读。
一、战歌嘹亮的诗坛、歌坛、俳坛时评
诗坛时评、歌坛时评及俳坛时评是“北窗时评”栏目中数量最大的一组稿件,这些时评从诗歌的发表状态、主题内容、发展动向、不足之处等多个方面对伪满洲国地区1942、1943年的诗歌文学进行了详细地介绍与评论。其中诗坛时评主要由江畔 担当(仅最后一篇为坂井艳司所写),歌坛时评由三井实雄、高桥正信担当,俳坛时评由高崎草朗、竹崎志水担当。在共计24篇时评中①其中诗坛时评9篇,歌坛时评7篇,俳坛时评8篇。,下述几个关键词尤其引人注目。
(一)“报国”诗歌、“战争”诗歌、“爱国诗”
这类时评中出现的“战争”一词,专指爆发于1941年的“大东亚战争”。这场侵略战争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一如“圣战”般令人敬仰、不容置疑。在《北窗》第四卷第三号的俳坛时评中,作者高崎草朗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了所谓“俳句报国”的正确途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俳句报国之道呢?——(我们应该)基于圣战之下的感激之心,进行振奋国民生活、鼓舞前线官兵士气的创作。”[2]可见,能够报国的俳句首先应该对战争持有“感激之心”,这是一种远高于“支持”的态度,是俳人对于战争问题的诗性解读。其次,这些俳句还要能够在前线与后方两块“战场”产生作用,不但激发作战士兵的昂扬斗志,还要鼓舞普通百姓将战争进行到最后时刻。在第四卷第二号的诗坛时评中,江畔对于战争中日本诗人的具体做法进行了诗人独有的慷慨阐释。
回顾以往,迄今为止每逢大战都会出现很多战争诗、爱国诗,这些诗歌都以军歌的形式渗透给国民,通过朗读、杂志以及报纸等渠道直接深入到战时的国民生活之中,时至今日亦是如此。当然,这些都只是浮于表层的事实,在其内面,诗人们应该脱离长久以来散文主义式的弊端,在大东亚战争的海阔天空之下,转向以诗性抒情为中心。所有的日本诗人都应该把技术上的内容暂且搁置,直接突进所有诗歌的中心思想,磨锐每个人的诗魂[3]。
按照江畔 的评论,诗人在进行创作时最重要的并非徘徊于词句上的斟酌,而是应该直奔主题,因为只有主题突出才能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领悟诗歌所要转达的精神。这种理论强调政治宣传、忽略艺术锻造,因而导致当时出现了很多仅如口号一般的作品,远谈不上诗歌本应具备的艺术性。同期发表的歌坛时评(三井实雄)将上述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作者甚至认为应该将“战争”以及对于战争的“感激”作为诗歌的唯一主题进行创作:“我甚至会觉得,除了战争以外还有能够做歌的事情吗?除了对于战争的感激之外还有值得做歌的事情吗?”[4]随后,作者又在第四卷第三号的歌坛时评中借助读者来信将“歌心”与大东亚战争结合到一处:“最近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我已经停止做歌十年有余,对于大东亚战争的感激之情让我再度寻回歌心。’虽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却可以由此看出,人们对大东亚战争的感激已经反射于做歌之上…(中略)…为完成圣战,‘歌坛’全体业已燃其心魄。”[5]在此,歌人对于大东亚战争的感激之情已经成为他们找到(找回)歌心的主体内容,成为当时的“歌魂”。
诗人、歌人、俳人对于战争的支持并未仅仅停留在创作阶段,时评作品中同样还出现了有关歌人请缨的内容。三井实雄在歌坛时评(第四卷第四号)的开篇写道:
除新闻记者、广播局工作人员等弘报相关人士之外,最近艺文界中的漫画家、摄影师、小说家等也都参加到各种报道队中。我能切身感受到他们愉快的心情,也十分钦佩当局者这一举措的适切性,因为通过指导监督,艺文家一定能够在必要部门中发挥艺文的特色。(中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热切地希望歌人同样能够参加到报道队之中……[6]
从这段时评来看,时至1942年9月,伪满洲国已有大量文学、艺术工作者加入到随军报道的队伍当中。作为一种有感而发的创作模式,和歌自古以来就以浓厚的现场感著称,由于文艺人士加入报道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现场体验战争,这种对于“现场感”的重视便愈加显示出和歌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加之其短小的题材,既能够随感而发,又便于传播,实在是随军文学中十分“符合需求”的文学类型。
俳句报国也好、“爱国诗”也罢、抑或是斗志昂扬的歌人请缨——这些字眼都充分体现出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日本诗人、歌人、俳人对于战争的倾力支持,战争主题已经成为主宰诗歌界的灵魂,进而构成战争末期伪满洲国地区日语诗歌的主题思想与主体内容。
(二)“朗读”
在积极申请亲赴战场的同时,诗歌界的文人们还通过另外一个途径提升诗歌对于战争的宣传作用,那便是经由收音机对诗歌进行广播放送。与小说、散文不同,诗歌凭借其规整的韵律结构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适合朗读的文学形式,加上当时以宣传战争为主题的激情诗作居多,因而便愈加适合用朗读的方式进行推广。张泉曾在研究中指出:“新闻报道、无线电收音机广播稿,是新闻管制的产物。作为知名作家,个人介入还是不介入的选择余地,个人言还是不言的表达空间,极其有限。”[7]另一方面,由于战时物资匮乏,为了节约纸张等资源,通过广播进行诗歌朗读也一并成为“节约援战”的有效途径。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传媒手段,收音机广播成为进行诗歌朗读的主要平台,设立于伪满洲国几大城市中的广播电台均曾开辟专栏进行诗歌朗诵。三井实雄写在第五卷第二号的歌坛时评曾就广播诗歌朗诵的重要意义进行过紧扣时局的阐释:“‘节约,将一切都送往前线’——因此,杂志、报纸开始废刊、减页。也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期待朗咏文学能因此得以博兴。文学的发表形式不能永远只依靠印刷,特别是短歌这种题材简短的文学更是应该转向朗咏的方式。”[8]
然而,与文人们的大力提倡相比,收音机广播所带来的效果却似乎并不如人意。就此,担当诗坛时评的江畔 指出,诗歌广播之所以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担任朗读一职的播音员虽然具有专业的朗读水准,但却并未能够正确地、深层次地理解诗歌内容。因此,这些诗歌所承载的宣传重任便也无法从根本意义上得到完美的实现。
说到朗读诗歌的广播,虽然在各地都已开展进行,但是就我所居住的哈尔滨而言,却远远不能让人满足。这都是由于占据广播局的那一群演员所致。不论哪一位广播员,他们对于诗,至少是对于发展至现代阶段的诗都理解吗?有关这一点着实令人怀疑。他们都只是因循守旧地按照过去的样子依据诗歌格式抑扬顿挫地朗读,并没有多样性的变化。虽然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我想广播局应该更加广泛地招聘朗读者。不知是谁在负责这个栏目,总觉得他对于诗歌的选择也有一些乱来[9]。
作为送给战争中渴求诗歌的国民的作品,诗人必须用自己的声音进行朗诵。声音的美丑居于其次。对于朗读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一定要由能够充分理解诗歌的人声情并茂地进行。但是,朗读者却不能陷入那种由热情所导致的自我陶醉之中,并且必须提高自己的表现技术。广播员在进行朗读时之所以会让人觉得不尽如人意,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关于此,前些日子新京广播局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在节目中邀请逸见吉等数名作者亲自朗读了自己的诗歌[10]。
在江畔 的建议中,作为创作者的诗人也应该参与到诗歌朗诵的活动中,因为他们才是最能够理解作品的人,也最能够表现出诗歌所要渲染的氛围。这样一来,诗人们的工作便从单纯的创作发展到现场朗诵,成为推广诗歌的重要一环。那么,广播局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另一位时评作者坂井艳司在随后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介绍:“三月一日,新京方面为庆祝建国节特别邀请井上鳞二、逸见吉、八木桥雄次郎等人对自己的新诗进行了朗诵。对此,广播局在他们离开时于下楼途中送给每人五元图书券。”[11]五元图书券在当时大约可以订阅一年期的《北窗》杂志,这样的报酬绝对算不上多,加上广播局是在诗人们下楼离开时送的图书券,也就难怪坂井艳司会在文中感慨“诗人不遇”了。但是,这种情形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广播局之所以会支付如此微博的酬劳,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并非一次商业活动,逸见吉等人本来也不是为了报酬而来,电台方面表示的仅为心意而已——然而不论如何解释,广播局的接待方式实在算不上是正式,诗人们亲自参与诗歌广播似乎并未得到电台的足够重视。
(三)“沈潜”
“沈潜”原为日语词汇,意为沉淀心思、深思熟虑①为保持“沈潜”深层含义,本论文中原词使用。。这个关键词之所以会在歌坛、俳坛时评中多次出现,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学形式,“寂び”与“び”一直都是和歌、俳句的灵魂思想,与“物哀”“幽玄”等词汇一同构成日本传统文学的主体意境。这些意境通常生发自作者眼前日常而简单的情形,借由质朴的语句表达出来。当然,所谓“质朴”的语句却并非仅由作者信手拈来,它往往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需要他们字斟句酌——这一过程,便是此处所提之“沈潜”。由此可见,“寂び”也好“び”也罢,传统日本诗歌的主体精神与当时的战争状态之间其实原本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状态,很难实现“报国”诗歌、“爱国诗”的境界。然而,为了迎合时局“需要”,很多诗歌作者却又不得不舍弃传承千年的文学理念,转而投身于慷慨陈词般的和歌、俳句创作。这样一来,他们的作品自然会失去这种文学形式原本应具有的温婉与淡雅,转而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产物。再加上战争期间时间紧迫等特殊因素,很少有作者能够静下心来遣词造句,如此而成的作品难免粗制滥造,如同喊出的口号一般乏味而无余韵。
针对这种现象,担任俳坛时评、歌坛时评的竹崎志水、三井实雄等人均在文章中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指出“沈潜”这一过程对于诗歌创作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对国民诗进行再建的呼声与开战同时而起,这种呼声号称要建设最健全、优秀的国民诗,强调最纯粹的大和民族诗,这是近日俳人必须采取的态度。对于伴随战争而来的各种不便、苦痛,应该暂且甘心情愿地承受,将已沈潜的热情,悠悠地、朗朗地咏出,对于战时下喜好俳句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人士而言,他们的目标恰好应该归置于此[12]。
在竹崎志水的评论中,俳句被视为最纯粹的大和民族诗,俳人吟诵俳句时所具有的情绪应该是经过沉淀的,吟诵的节奏也应该“悠悠地、朗朗地”,而非像高唱口号一般呼喊而至。此处的“沈潜”可以诠释为一种针对过激情绪的沉淀,而非浮在浅层的简单热情。如三井实雄曾在第四卷第一号的歌坛时评中将“沈潜”归结为日本精神的精粹:“自不必说,在日本精神的深邃沈潜之处,蕴含着知性与抒情性。”[13]依照三井实雄的观点,歌人若想创作出既有知性又不乏抒情性的作品,那么他就必须领悟日本精神的“深邃沈潜之处”。另一位歌坛时评负责人高桥正信则将“沈潜”定位为万叶精神,认为当时的短歌只有“沈潜”至万叶精神的境界才能完成自己的时代重任。
由此可见,在“北窗时评”的作者眼中,战争时期的诗歌纵然需要贴合时代,却同样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其作为传统文学的本质,遣词造句上的细细琢磨更是不容缺失。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时评作者们的要求其实是一种“负责任”的创作理念,因为在尊重传统精粹的同时做出顺应时代需求的改进,对于任何时代的文学活动而言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时评作者所提倡的传统诗歌精神与当时的战争氛围却又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沈潜”之下的作品怎么可能营造出斗志昂扬的氛围,以“沉潜”的气质为战争呐喊助威,这种构思原本就是一种悖论。虽然曾有部分作家按照诗歌固有的格式、韵律创作出了一些看似符合要求的“战争”诗歌、“爱国”诗歌,细揣之下这些作品却丝毫无深意可谈,只能算作政治宣传的载体。如此一来,这些作者便成为评论作者们口中仅为敷衍趋势而创作的“轻薄歌人”,这些作品也只能算作“玩弄所谓爱国言辞,并无实际内容”的“拙劣之作”[14],从而遭到世人摒弃。
二、言辞犀利的创作时评
刊载于杂志《北窗》的创作时评普遍通过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的方式,针对刊载于伪满洲国各大报纸杂志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不定时地分析与品评。担当创作时评的几位作家虽然文风不同,但却大都笔调犀利地对于当时文学创作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鲜见溢美之词,这成为创作时评的一大特色。
第一篇创作时评题为《作品四篇》,作者津山谅。该篇时评在对长谷川的作品《宽城子》进行评论时,津山谅写道“:《宽城子》,长谷川所作,对于满洲浪漫精神感悟最深的便是长谷川。贯穿于此人作品中的强烈气魄,的确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将这种精神通过极短的作品展现出来一直都是他的得意之处,他创作出很多超脱的、梦幻般的作品,他将这种精神裹以现实的外衣,于是便成就出《宽城子》这样一部作品。”[15]作为杂志《满洲浪曼》的同人,作为满洲浪漫派的主要作家之一,长谷川的作品一直以浓厚的浪漫主义情绪著称。津山谅称其作品“将这种精神(浪漫主义精神,笔者注)裹以现实的外衣”,足见他对于长谷川的认可,毕竟这部作品没有脱离现实,既有所谓精神上的内核,又有现实做外壳予以支撑。然而,随后一篇来自井上乡的时评却对长谷川 进行了毫不客气地批评“:长谷川的《星云》笔调慌乱,本以为会是颇具思想深度的作品,却实无思想而言,进而言之,恐怕还有堕入庸俗之危险。”[16]由于收集材料所限,笔者未能见到《星云》原文,所以不便评论井上乡的话语是否客观,但若从整篇时评来看,井上乡的这种绝对批判的态度却并非只针对长谷川一个人:对于大内隆雄所译《碱性地带》,他称其“文章粗糙”;对于日向伸夫的《冬夜谈》,他称其“缺少扣人心弦的力量”;对于北村谦次郎的《东北》,他称其“在写实的描写中飘动着浪漫,只是这种浪漫略显低调,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趣味”;对于高木恭造的《在奈良》,他称其“很难让人产生共鸣”……上述几位均是生活在伪满洲国地区的知名日本作家,然而井上乡在对其作品进行评论时却并不顾忌他们的身份与影响力,就事论事,笔致辛辣。由此可见,这一系列时评专栏当时极力希望为作家、评论者营造出的是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氛围,它希望每个投稿人都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地发表个人观点——当然,这种原本值得称赞的办刊宗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恐怕无论如何都难以真正实现。
还有少部分创作时评选择从整体角度出发针对当时的文学状况进行评论,比如安田文雄曾经写道:“……作者们都展示出了相当具有热情的态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我希望他们在选择素材、主题时能够更加深入。相对内地文坛而言,建国十年的满洲文学除了在技巧方面存在劣势之外,作家们的创作意欲也存在欠缺,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17]在此,安田文雄指出伪满日本作家的创作主题明显不够深入,不能对时代素材进行深层次的反映,同时在创作欲求上也远不够积极,还需加倍努力、加倍创作才可以。与安田文雄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井上乡,他用其一如既往的犀利笔调写道:“通过阅读满洲杂志近三四个月间发表的作品,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学创作领域的消极。被创作出来的作品,能给我带来艺术感动的地方自然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创作于满洲的作品,一直都被主张说应该从日本文学中脱离出来,应该形成自己的独自性。然而那些看似具有这种独立性主题的作品,由于缺乏明确的必然性,也就没有办法具有感人心脾的力度。这实在是让人惋叹的情形。如此看来,也就不应该期待在满洲能够盛开出文学之花了。”[18]井上乡指出的弊病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创作领域的低迷,其二是作家在主题把握上的欠缺。在他看来,很多作家都没能真正把握主题,即便找到了貌似具有独立性的主题,也往往因为情节设置上的失真而导致作品在整体上缺乏“必然性”,从而脱离现实、无法令读者感动。
安田文雄与井上乡将“满洲文学”创作低迷、主题不清的状态归咎为作者群体的消极与草率,另一位时评作者铃川洋一则将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杂志及出版社,他在时评中以坂井艳司的一篇作品为例,对作者、刊行杂志《艺文》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铃川洋一指出:“首先,作者的意图是支离破碎的;其次,作者的语言又是虚浮的。(中略) 既然《艺文》是作为全满洲国唯一的综合杂志起步的,那么编辑就必须对于作品的登载负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得而知,只是编辑居然选择刊登此等文章,着实让我怀疑编辑者对于文学的见识。”[19]在此,铃川洋一不客气地指出杂志在进行编辑时对于文章采选的不负责任,并由此质疑编辑的水准,从而将时评的批判视角由作者进一步扩展至出版物的层面。他在文中毫不留情的字句愈加体现出彼时《北窗》所谓“言论自由”的氛围。有趣的是,被铃川洋一批得体无完肤的坂井艳司同样是“北窗时评”的作者,虽供稿于同一本杂志,却又丝毫不为对方留得情面,足见“北窗时评”相对“公正”的评论态度。
从8篇创作时评的主体内容来看,评论人对于当时伪满洲国日本文学所持有的态度在总体上是不满的,他们认为这部分作品的主题不够清晰,作家们的创作意欲不够强烈——如何尽快敲定“满洲文学”的明确主题、彰显出“满洲文学”的独立性,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作家们的创作积极性成为当时“满洲文学”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三、略显寂寥的文艺时评与论坛时评
同诗歌时评及创作时评相比,文艺时评的情形略显落寞,一共只有3篇,其中一篇为论坛时评,另两篇为文艺时评。其实当时的《北窗》杂志已经刊载了很多专门探讨文艺问题的文章,只不过由于这些文章大都篇幅较长,不符合《北窗》时评占据一页版面的要求,因此都被单独刊出。划归文艺时评的仅有井上乡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时评以综述当时文艺界的热门话题为主,并附以简明扼要的评论。在第四卷第四号的文艺时评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满洲文学”其实根本没有实现,并对作家们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理念进行了抨击:“在他们(作家们,笔者注)身上,最初由他们自身决定的满洲文学的概念已经不见踪迹,他们只是凭借意识深信自己还具备这一点。再加上他们一直在‘建国’这一壮大的浪漫主义氛围中尽情呼吸,导致他们仿佛沉醉于过剩的自我意识之中一般,他们一味地将自己毫无依据的感想信念化,并且丝毫感受不到自相矛盾之处。”[20]在另一篇文艺时评中,井上乡对于当时“满洲文学”界热议的“独立性”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当作者)面对特殊的素材时,变化是必须的。应该说此时才初次产生所谓独立性。这就好比是人,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血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拓自己独特的世界。这一点在满洲文学身上亦是相同,它的成立以日本文学为基础,绝对否定它与日本文学之间的绝缘之说。”[21]井上乡的两篇文艺时评恰好勾勒出当时“满洲文学”的两大问题点——对于当时日本作家饱受诟病的“过度浪漫”,井上乡给予了完全的否定,他认为那是由于一些日本作家已经完全陷进过剩的自我意识之中才导致此种现象的产生,这是他们“将自己毫无依据的感想信念化”的产物,必须予以杜绝,因为只有结合实际的浪漫才是正确的浪漫。对于文学界热议的“满洲文学独立性”,井上乡认为“满洲文学”归根结底还是立足于日本文学的,所谓独立性只不过因为作家在伪满洲国遇到的素材与日本国内作家不同而已。也就是说,这种“独立性”其实是建立在素材的独立之上,在属性这一层面,“满洲文学”应该还算是日本文学。
唯一的一篇论坛时评来自中川一夫,他在开篇便感慨道:“满洲国没有职业评论家,也没有论坛,实在是倍觉寂寥。”[22]诚如作者所言,当时的伪满洲国虽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性文章,但是作者却大都并非专业评论人士,只是由作家、诗人等代而为之。出现这一情形的缘由十分简单:彼时所谓的“满洲文学”才刚刚起步不久,不论是基本属性还是主题思想都尚未定性,各个领域的创作也仅在摸索中进行,甚至很多作者也都并非专业人士,因此,没有专职评论家也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这篇时评的结尾尤为引人注目:“为了能将其(评论的作用,笔者注)最高程度地发挥出来,自以为是、偏颇、水平低下都是万万不可的。进一步来讲,这还要求我们具有不被现在的一些计谋所利用的审慎与周全。兴盛论坛的急切之处与困难正在于此。”[22]在此,中川一夫将积极振兴论坛的原因归结为避免文坛被“现在的一些计谋所利用”,希望论坛中提出的观点能够正确引导文坛发展。虽然作者在文中并未点明所谓“谋略”究竟是什么,但若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思考便不难发现,“谋略”一词所指代的应该就是当时日本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支持战争、支持殖民活动的文学策略。加之作者将发展论坛的困难之处也归结于此,上述结论的准确性便愈加可信,因为当时伪满洲国地区的文学活动已经受到了关东军的严格控制,想要建立能够畅所欲言的论坛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从这极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在那个全民向战的年代,在那个战争主题已经充斥文坛的特殊阶段,伪满文坛中依旧能够读到一些有悖“时代动向”的文字,虽然它们语意模糊,虽然它们势单力孤,但却同样凭借自己微弱的声音唱出反对战争、反对殖民的论调。
借由35篇时评文章,杂志《北窗》为读者清晰且详细地勾勒出了战争末期伪满洲国日本文学领域的具体情形。作为“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直接产物,对于战争、侵略、殖民的大力支持成为贯穿该系列时评的主题思想。部分作者对于战争并不十分“配合”的论调同样在时评文章中得到了或多或少地表达。这一系列时评在向读者实时介绍创作动态的同时,还对文坛中比较热门的话题进行了简短精练的评述,其中不乏一些精湛、独到的见解。参与时评的作家虽然大都抱有支持战争的态度,但在对具体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时却丝毫不会趋炎附势,字里行间语调辛辣、直逼问题点,具有很强的阅读性。遗憾的是,一度轰轰烈烈的“北窗时评”最终在第五卷第四号戛然而止,坂井艳司的诗坛时评成为“北窗时评”之绝唱,为这次基于日本作家视角的时评活动草草地拉上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