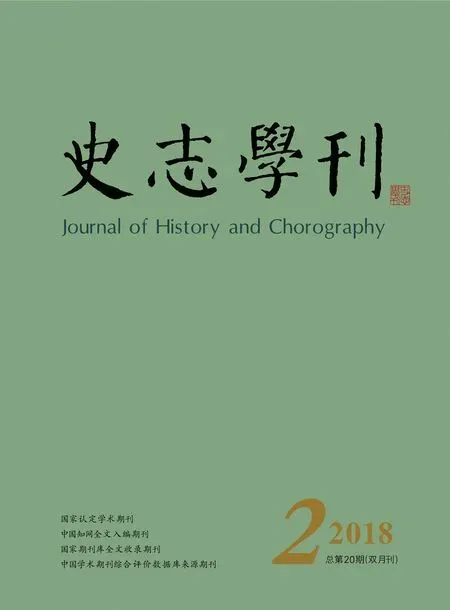明清山西民间信仰与长城记忆
——以崞县扶苏、蒙恬崇拜方志书写为线索
贾亿宝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030006)
明清时期,地方志书修纂活动是由官府知县主持、民间士绅积极参与的地方重点文化工程,对地方文化、历史、社会资料的留存具有积极意义。地方志书往往是通过官方史书及档案相关内容选编、寺庙碑刻誊抄、民间传说整理、特殊专题撰写等方式完成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其中,对民间寺庙、宗教信仰条目的资料撰写,资料普遍搜集整理自当地民间传说记忆,同时配合翻阅前朝史书,搜爬相关史料而成。撰写者水平参差不齐,造成方志编纂书写中的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情况屡见不鲜。固然与编纂者的视野局限性与编纂严谨程度有关,但志书一旦成为定稿,便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成为书面依据,反过来再次影响当地民众对相关内容的认知,对当地的信仰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1]有关清代方志编纂与书写的研究,参见韩章训.谈清代修志作风和经验教训.史志学刊,2017,(2);任柳,陈婷婷.明清与民国时期贵州方志中民俗书写变化研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7,(6);周毅.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看地方志女性历史书写的模式化.史学史研究,2017,(3);徐鹏.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沧桑,2013,(1).。民间信仰作为依赖地方传说记忆最为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色彩[2]王守恩.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山西大学学报,2008,(05).。
山西原平,明清时期称崞县,以扶苏、蒙恬记忆为基础的民间崇拜及传说遗迹的留存丰富。扶苏、蒙恬二人皆为《史记》中记载的历史人物[3]当代对蒙恬相关的研究,重在北征匈奴、长城修筑、秦直道修建、思想意识等方面,另有不少对其籍贯、制毛笔、造筝等事迹的讨论。参见贾衣肯.蒙恬所筑长城位置考.中国史研究,2006,(1);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4).。扶苏,秦太子,世有贤名,被始皇帝派至蒙恬军任监军。蒙恬,原为齐人,祖父蒙骜由齐入秦,祖孙三代皆为秦朝重要将领。蒙恬为将,北击匈奴、攻取匈奴河南地,增修长城,使长城防御体系联成一体,军功卓绝。《史记》明确记载其驻军上郡,负责秦北方边防事宜。此外,蒙恬之弟为上卿蒙毅,为始皇帝倚重,遇害于“代”,也与长城地区有关。崞县、代县相关崇拜起源与流传过程不详,但在明清两代当地志书记载中,证实当地有丰富的祭祀与崇拜活动。谨以原平相关记载为线索,深化对忻州地区的扶苏、蒙恬信仰文化记忆的认识[1]对扶苏的讨论,参见孙文礼.秦始皇“赐公子扶苏书”考.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2004.。
一、扶苏、蒙恬信仰的方志记载情况
崞县县治所辖区域屡经分合变迁[2]蔡顺田.雁门内外两崞县溯源.忻州日报,2012-02-12(003).另有部分相关考述,参见原平史鉴编委会编.原平史鉴.三晋出版社.2009.,但宋元至明清时期,主要以崞县为名。境内有扶苏庙和蒙恬庙各一座,皆在现原平西北部大林乡所辖地区的黄土沟壑丘陵地带与石质山崖接壤处。扶苏庙别称柏枝寺、柏枝神庙、柏枝大王庙或扶苏太子庙,建在西神头村,蒙恬庙别称崞山神庙、崞山大王庙、崞山寺建在南神头村(现名迎新村)[3]刘克敏.原平扶苏庙和蒙恬寺浅谈.忻州日报,2010-08-01(001).。二庙相距约5里左右,周边还有其他相关遗迹传说留存。崞县在明时属太原府、清时属代州管辖,因此在《崞县志》、明清《太原府志》《代州志》中皆有记载。有记载最早的则是现存于《永乐大典》辑佚本中的洪武《太原志》。李裕民编《山西古方志辑佚》,摘出相关条目数条,崞县条存有崞山、阳武谷等相关内容,但崞县柏枝山、扶苏墓[4]对扶苏墓的讨论,主要在秦始皇陵陪葬墓方面,认定陕西绥德地区扶苏墓为纪念遗迹。参见李鼎铉.扶苏墓再探.文博,1999,(05);张文立.此处何来扶苏墓.文博,1999,(02).等内容无载或不存[5]李裕民辑.山西古方志辑佚.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另有所谓永乐《太原府志》的辑本,与《古方志辑佚》所辑洪武《太原志》同出《永乐大典》,应为同一文本的整理本,记载相同,对文本编修时限理解互异,学界说法不一。参见安捷主编.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太原府志集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山西地区扶苏、蒙恬信仰集中区,除崞县外,代县也有相关记载。该版本中收有代县扶苏庙、蒙恬墓简要记载。相关内容另作专文讨论。。万历《太原府志》,崞县仅收录有扶苏太子冢一条相关内容,崞山寺、柏枝神祠等寺庙条目中并无详细展开[6](万历)关延访撰.张慎言修.太原府志.山西人民出版社等,1991.该版府志中有恨斯水与扶苏太子祠、蒙王墓等记载存在。万历《崞县志》据当地文人引用,内容相对丰富,惜早年定为乾隆时早已亡佚,其材料来源不明,无法确引。。明清时期,还有明天顺《一统志》、清嘉庆《一统志》、明清《山西通志》等志书也简要收录相关内容[7]明代天顺《一统志》对该类记载简略。参见(万历)一统志.四库全书景印本.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修《一统志》,嘉庆《一统志》相关内容自康熙时已存在。另外,可以参见(清)雅德修,汪本直纂,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乾隆)山西志辑要.中华书局.2000.该辑要主要辑录雍正《山西通志》,依乾隆《一统志》体例编修,相关记载与通志无异。。
崞县扶苏、蒙恬事迹在明《永乐大典》辑佚文献中仅有“阳武谷”条目明确提及,有“阳武谷,亦云杀子谷,在(崞县)城西南七十里”[8]李裕民辑.山西古方志辑佚.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P223)的说法,补充理由扶苏、蒙恬“军于此”,扶苏死于此,因得名“杀子谷”。万历《太原府志》中无此记载。此处另有太子崖,与杀子谷密切相关。康熙《山西通志》中有关崞县“太子崖”的记载:“在县西南六十里,因扶苏赐死于此,又名杀子谷。”[9](康熙)山西通志(卷 5)·山川.(P129)光绪《崞县志》:“太子崖,相传秦太子扶苏驻军于此,石城故址犹存。”[10](光绪)续修崞县志(卷 1).舆地志·山川.(P333)太子崖处被民间解读为扶苏驻军地,并有石城与太子洞遗址。明清志书记载在这一点上相同,此处“杀子谷”传说在清初应依然活跃[11]太子崖下确为山石峡谷,曾被认为是阳武河源头之一,扶苏墓尚无调查资料证实。。清嘉庆《一统志》中,也有“太子崖”与“杀子谷”在同一地的说法,但代县对“杀子河”传说的记载更为丰富,“杀子谷”内容被移在代县境内[12](嘉庆)一统志(卷 151).代州·祠庙.四部丛刊续编本,1934.(P17)。邻近处还有一处“马头崖”,又称“马投崖”,传说认定是蒙恬战马的殒身地,光绪版《续修崞县志》附图中,崞山位于马头崖以东,两者并非一地。此有“山前三里许,石上马蹄痕”这一遗迹,据称有同治年间蒙恬小庙一座,但不见方志记载。
崞山、柏枝山在当地分别为蒙恬、扶苏神庙所在主山。《永乐大典》所存《太原志》的“崞山”条目中,仅有“崞山神”记载,并无蒙恬事迹相关,记载此地留有宋政和五年高景兆碑,应是其建庙记述的最早依据。嘉靖《崞县志》与此相同[1](嘉靖)尹际可修纂.崞县志(卷2).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本.。万历《太原府志》仅记载“崞山,汉以此名县,上有崞山神庙,庙左有甘露池”[2](万历)太原府志(卷 8)·山川.(P38)等语。康熙《山西通志》中描述与此大致相同。雍正《山西通志》中,收录了崞山上有崞山神庙,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访迹,大段引用了宋代崞县人士张忱撰写的《崞山神庙碑》中的传说记载[3](雍正)山西通志(卷26)·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凤凰出版社等,2011.(P520)。清乾隆《崞县志》载“崞山,西南三十里,……县以此山名,为邑之主山。上建秦将军蒙恬庙,敕封崞山大王,山前三里许,石上马蹄痕传为蒙恬遗迹也。”此处认为“县以山名”,自宋代当地人即有此误会[4](清)邵丰鍭,顾弼修.贾瀛纂.(乾隆)崞县志(卷6)·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 14.凤凰出版社,2011.(P239-241)。其实应是崞县侨置在此后同时出现“崞山”,用以寄托旧崞县民众怀念故乡之意。柏枝山,万历《太原府志》记载:“柏枝山,山石纹类似柏枝”,康熙与雍正《山西通志》皆因袭,雍正版多一句诗文,别无其他。清乾隆《崞县志》记载“柏枝山,正西二十五里,山石貌类柏枝,故名。秦太子扶苏庙在焉。”[5](乾隆)崞县志(卷1)·地理.光绪版续修崞县志中增加“八景之一”记载,按通志内容补充后魏(北魏)高宗兴安年间途经崞山以及行猎事迹.(P181)此时才多了扶苏庙的记载。
蒙恬神庙、扶苏神庙是相关民间信仰祭祀的场所,并非位于崞山与柏枝山顶峰处。嘉靖《崞县志》与万历《太原府志》没有记载扶苏庙,对“崞山神庙”的描述中并无蒙恬事,仅有方位与“宋政和五年建,七月初五祭”等内容。康熙《山西通志》记载为“崞山神庙”与“柏枝山神庙”,内容简略,仅交代方位[6](康熙)山西通志(卷 9)·祠祀.(P231)。崞山寺实际位置在“崞山西南麓”,又称“魁鳌峰”,俗称鬼儿坪、锅坪梁。清乾隆《崞县志》与光绪《续修崞县志》记载大体相同,个别文字有出入:“崞山神庙,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崞山西南麓,地名鬼儿坪。神即秦蒙将军恬也。相传肇邑之初,有神兵出入山麓,以助修筑,因立庙报功焉。齐世祖永明八年暨魏孝文时并遣有司谕祭。宋政和五年重修。(明)弘治壬子、(清)康熙己酉,先后补葺,(康熙)二十二年地震,倾圮。雍正初重修。每岁七月初五日致祭。金安阳王尚书无竞工书,尝题‘崞山神’三字庙额。元好问宝贵之,刻诸石而为之记,今石刻无存。”[7](清)赵冠卿,龙朝言,潘肯堂纂.(光绪)续修崞县志(卷2).建制志·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4.凤凰出版社等,2011.乾隆版中,仅在“秦将军蒙恬”与“因助筑”,“其迹”与“石刻”等词表述上有出入,殊无大异。(P369)两者的记载与雍正《山西通志》中“崞山”与“崞山神庙”的记载大体相同,更为简略,来源应当都是该庙所立碑刻中的史料。《山西寺庙大全》中,对此仅记载其古代修葺经历,未指出其当代被拆毁过程,认定其遗址尚存[8]白清才等编.山西寺庙大全.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P306)。扶苏庙在柏枝山山麓,在明清方志中,记载变化最多。万历《太原府志》记载“柏枝龙神庙,宋时建,七月二日祭”,无扶苏事,偏重龙神[9](万历)太原府志(卷 14)·祀典.(P87)。雍正《山西通志》载:“柏枝神庙,在柏枝山,祀苏鲁都,宋建明时,七月二日有司致祭。”[10](雍正)山西通志(卷 167)·祠庙.(P466)此处“祀苏鲁都,宋建明时”,此处文意不明,并无“苏鲁都”一词相关记载与其他记载印证,疑是笔误。乾隆《崞县志》:“柏枝神庙,在县西二十五里柏枝山。宋建隆中建,元至正二十三年、明正德六年、(清)雍正十一年相继重修,有司岁以七月二日致祭焉。”[1](乾隆)崞县志(卷 4)·坛庙.(P225)仅在重修时间上与之前相比增加两个新的重修时间节点,仅在同一志描述“柏枝山”时才定为扶苏庙。清嘉庆《一统志》同样采用如上记载,并无大异。当地碑刻资料中,扶苏庙与崞山寺均有北魏、唐、宋以来官方祭祀、敕封等传说。扶苏庙还有汉楸唐柏等古树留存,可知其成为地域信仰中心历史悠久[2]唐宋碑刻资料已毁弃殆尽,方志记载模糊,在民间记忆与新修碑记中记载有最迟唐时建寺。。《山西寺庙大全》中将其登记为“柏枝神庙”,记载其古代修葺经历,对其现状记述为“坍塌”[3]白清才主编.山西寺庙大全.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P307)。另有一处位于阳武谷口的“浮图寺”,曾举办有扶苏太子庙会,“浮图”二字显然是佛教用词,但与“扶苏”二字读音接近,讹传可能性极高,惜不见方志收载。
明嘉靖《崞县志》“陵墓”载:“秦太子扶苏冢,县西南四十里,相传扶苏葬于此。”[4](嘉靖)崞县志(卷2)·陵墓.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本.万历《太原府志》则简要记载崞县扶苏太子冢[5](万历)太原府志(卷 14)·祀典.。“扶苏墓”与另一事迹地“太子崖”在同一地点。雍正《山西通志》:“秦太子扶苏墓,相传在县西南四十里,其高若陵,草木旋绕,农不忍耕,樵不忍采,乡人每岁春秋致祭。”[6](雍正)山西通志(卷174)·陵墓.此处与材料来源不明的明万历《崞县志》中记载类似,后者多一句话:“过经于此者,莫不悼太子之不幸,恨赵高之无君,惜秦祚之由短,喜天道之有知也。”(P605)尤其是乾隆《崞县志》记载:“秦太子扶苏冢,在县西南四十里太子崖。”[7](乾隆)崞县志(卷 4)·古迹.(P230)光绪《续修崞县志》则写“秦太子扶苏墓,在县治西南六十里太子崖,其地草木旋绕,农不忍耕,樵不忍采,乡人每岁春秋致祭。”[8](光绪)续修崞县志(卷 1).舆地志·陵墓.(P345)志书中出现了距离变更的问题,有可能是后期重新核实更改。
此外,崞县与秦代历史有关的遗迹,还有红池村附近的石闸口、长城梁两处:“石闸口,壁上刻人,相传秦始皇修边,火头三千人。”“长城梁,县西四十五里,始于赵武灵王,至秦始皇更增筑也,今遗址犹存。”[7](P230)这两处地名与遗迹,是有关秦代长城修筑与增筑事迹的记载,需要结合考古资料进一步证实,但尚无明证。
二、扶苏、蒙恬传说的明清文人考证
按《史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9](汉)司马迁.史记(卷 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82.(P2565-2566)“上郡”一直被认定在现今陕西榆林一带,即现今山西河曲保德西向的黄河西岸以西绥德区域,为史家认同。在清代各个版本志书修纂过程中,以《史记》记载为依据,对崞县扶苏、蒙恬相关事迹的考证就已开始。
崞县方志纂修者主动对扶苏庙与扶苏墓进行考据,存疑但保留相关记载。乾隆《崞县志》“秦太子扶苏冢”一条的按语中,纂修者参阅《史记》,否认了此墓与扶苏有关,认为应为后人附会:“按《史记》,扶苏死于上郡,在今陕西延绥地,非崞境也,此系后人附会。”[10](乾隆)崞县志(卷 4)·陵墓.(P230)光绪《续修崞县志》同样依据《史记》对此提出疑问,差点删去这一记载,但最终保留下来:“前志载此,未知何据,姑仍之,以俟参考。”[8](P345)
围绕神庙祭祀与蒙恬与扶苏相关事迹的记载,碑刻资料与官方文献可为旁证。乾隆《崞县志》卷六《艺文志》中,首先即收录前文提到的张忱撰写的《崞山神庙碑》和金代元好问撰写的《崞山神额刻石记》。张文中只记载了“神兵相助、鬼儿坪”的传说事迹,并未指出蒙恬事迹,马头山也只是山崖形状与马头相似得名,而且当时崞山神灵并未列入地方祀典。元文也无一字提到“崞山神”所指神灵为何人,因此在金代也应尚无相关传说[1](乾隆)崞县志(卷 6)·艺文.(P239~241)。当代人重修扶苏庙,认定有依据可知唐初曾名为圣泉寺,唐初尉迟敬德奉敕扩建,才成为柏枝寺,认为其已为扶苏庙,但依然证据不足[2]重修扶苏庙序.原平扶苏庙碑廊立,2009.。北魏、唐、宋以来官方祭祀、敕封等传说中,扶苏庙敕封“柏枝大王”、崞山寺敕封“崞山大王”皆不以扶苏、蒙恬为正名。从这些碑文资料看来,相关传说与附会不会早于金代。宋金时期,地方杂祀曾有机会纳入国家祀典,但翻检《宋会要辑稿》《元丰九域志》等史籍,此地扶苏庙与蒙恬庙未被宋代典章方志明确收录[3]宋会要辑稿·礼20·诸祠庙.中华书局,1957.辑稿中仅有并州乐平县蒙山神祠为秦蒙恬祠的记载。北宋乐平县为今山西昔阳县,但相关事迹在有关昔阳县志书中无载。。金元史籍中更未见明确资料。明初清理地方杂祠,崞山神庙与扶苏庙也无记载。嘉靖、万历时期的方志纂修中,崞山神庙与柏枝神庙被简要收录,提及蒙恬等语,却无详细说明。崞山寺在明末伴生了盛大的迎神享赛民俗活动,还被知县下令禁止[4](乾隆)崞县志(卷 4)·风俗.(P223)。清初志书搜罗民俗资料,应该立足于在明末就有相关传说流传。
清《山西通志》的纂修者也同样在进行考据工作。“阳武谷”作为“杀子谷”,仅有《永乐大典》孤证。在位于阳武谷顶端“太子崖”又名“杀子谷”的考据中,光绪《山西通志》以崞县相关遗迹作为代州扶苏、蒙恬遗迹的主体,将根源定位为蒙毅:“《史记》:毅祷雨山川,还,系于代。代州扶苏、蒙恬诸迹当改蒙毅,恨斯杀子当入上郡阳周,今延安府。”[5](光绪)山西通志(卷 26)·山川.(P521)对“杀子谷”传说则定位为上郡阳周延安府,排除故事在代州发生的可能性。光绪版《代州志》增加的旧志考证与此相同[6](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当代人也有认同代县蒙恬墓即蒙毅墓的探讨论证,但也属于推测,无法确切证实。参见冯湘.代县“蒙恬墓”真伪考.山西档案,1997(5).此文同样被收雁门关志,见796-797.(P300,304)。有关“杀子谷”的诗文,志书中补充有唐代诗人胡曾、陶翰的诗文,则已是纯粹认定“杀子谷”在代县,崞县与代县在“杀子谷”地名传说上显然发生了文本迁移。
三、蒙恬、扶苏崇拜的长城地域文化认识
崞县的崞山大王庙主传说为“鬼神助力”,扶苏庙则为“柏枝神石崇拜”,分别引入蒙恬、扶苏历史形象,显然是当地神灵不断与特定历史人物融合的体现。扶苏、蒙恬事迹在《史记》中记载明确,相关传说在山西崞县等地的流传显然立足于扶苏、蒙恬统军在长城沿线巡守的基础上。民间信仰引入历史人物传说,意味着民众将相关传说记忆建构成为能够接受和认同的地方文化,成为当地特定记忆的表征,但并非历史真实的演绎、宣传[7]高长江.民间信仰:文化记忆的基石.世界宗教研究,2017,(4);江帆.从神灵“移民”看民间信仰的传承动力与演化逻辑.中原文化研究,2016,(6).。
明清时期,崞县位于雁门关内代州周边地区,长城文化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空叠加中不断累积,形成丰富的“长城记忆”,呈现出丰富的边疆色彩。崞县、代县位于雁门关以南,是古代雁门关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雁门地区便是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峙的前沿阵地,战国时期赵长城便率先建筑于此,李牧在勾注塞关隘屯兵驻守,秦代更是属于蒙恬大军增筑长城的管辖范围内。即便相关故事有可能张冠李戴,尚未证实秦时期此地郡治与属县确切遗址所在,但以崞县、代县为核心区域,拥有丰富的秦文化扶苏、蒙恬传说与景观遗迹,与蒙恬“筑长城”、蒙毅遇害于“代”的文化传说相结合,已然成为该区域“长城记忆”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1]另可参见张玉.神话历史:介于祠堂与神庙之间——秦晋两地扶苏“故事”的人类学考察.百色学院学报,2014(6)。。“长城记忆”在纵向层面为长城地区长期以来口口相传,千百年来逐渐累积的历史记忆写入文本,在横向层面则为同一时代下外来记忆的落户生根,两者都会在流传中产生走形变化。这并不是说当地记忆的虚假,而是其很可能是一种虚化记忆在流传中逐渐实体化过程。
崞县一带,民风彪悍,“地近边塞,亦喜服弓马,捷武关者亦不乏人,即当要害之冲,此亦其要务也。”[2](乾隆)崞县志.卷 4.风俗.(P224)当地社会崇文尚武,民风融入儒家传统的“忠义仁孝”理念。蒙恬、扶苏传说,在当地文化人士眼中,不否认其非本地传说的可能性,但充分肯定并发扬其“忠义仁孝”的象征意义。崞山寺在乾隆六十年失火,嘉庆三年完成重建,本地士绅贾晖应邀撰写的纪事文《重修崞山寺神庙碑记》虽并未被县志收录,但直接反映当时地方士子的认识。其翻阅《史记》认为记载明确,并非死于此地。但其并非考证,重在抒发自己对蒙恬、扶苏多灾多难与“为人御灾”贡献的感慨。贾晖特别强调扶苏“奉诏而死,死孝也”、蒙恬“从太子而死,死忠也”的形象,尤其是蒙恬“无论殁于此或不殁于此,而将军之忠魂冤气,自有不可殁灭于此土之人心者,宜其历千百年而奉祀欤。”[3]原平史鉴,2009.(P291)山西地域的多神崇拜具有鲜明的功利性,是由其当地乡土文化中注重生存的特性决定的[4]赵新平.山西乡土生活研究.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P206)。扶苏庙与蒙恬庙也不例外,两庙位于当地泉口上方,崞山寺处为甘泉池,扶苏庙处为黑龙池,是对当地泉水救旱权利的神灵管控。“蒙恬”“扶苏”形象在当地神灵群体中与其他神灵一同肩负着“降雨禳灾”等实际功能,只在“忠义仁孝”文化上特殊性尤为突出。作为与本就具有男性色彩的“山神”信仰重合的军事历史人物,又与当地处于长城地区这一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间特征结合,已经成为具有阳刚气质、拥有武力的男性神灵“保护一方”的代表,相比女性神灵在信仰民俗中的形象,可谓别具一格。蒙恬“御寇”,扶苏“至孝”,以别样的英雄形象与品德气质影响着当地的人文风气,受到百姓同情。相关诗文中,也留存了大量至少是明清时期文人对此类传说记忆的感怀。清代崞县人冯立《扶苏庙》:“神头分东西,相隔十余里。扶苏与蒙恬,此地同赐死。雄关萦百二,长城绵万里。古殿高巍峨,直矗层峦起。松柏郁苍苍,流泉清澈底。宫门盘磴磴,厥中衣冠伟。貌像尚如生,烈烈忠义鬼。春秋存馨香,千年昭堙祀。为问期高辈?奸魂何依倚。”兰尔潜的《崞县赋》中,也有“秦城嵽嵲,太子留芳”句,就是取材于秦代“长城梁”和扶苏“太子崖”相关记载[5](光绪)续修崞县志.卷 8.艺文.(P582)。都是对蒙恬、扶苏“忠孝”形象的抒情感慨。
明清时期,方志才将某一类民间传说落入文本书写,进行神灵化演绎,那么在这之前的历史遗迹文本中,并无只言片语,那么推定其并非为人熟知的历史传说,应是可接受的一种历史判断。扶苏、蒙恬传说与遗迹以及祭祀活动在山西崞县、代县地区的活跃,无论真假,已经成为当地“长城记忆”文化的一部分。固然不排除为方志收录资料所限,但其作为当地历史记忆的某种表征,已经实现故事的本土化,纪念意味更浓。正如王子今在考察陕西秦直道建设历程中,注意到秦直道周边众多扶苏、蒙恬的相关地名,认为“其不过是民间对扶苏的同情与追忆的产物,而且与扶苏被迁送北上戍边的事迹相关”[1]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4).。崞县、代县相关传说与之同理,加之在明代九边城防修筑的繁荣时期大量的人员往来带来丰富的外地传说落地生根,相关传说进入志书收录范围内,也是该类文化成形土壤之一。在康熙《山西通志》中,蒙恬就已经位列大同府名宦,对其“累土为山,植榆为塞”修筑长城的事迹予以肯定[2](康熙)山西通志(卷 18)·名宦.(P584)。当然,我们绝不排除二人确实身殒这一地区,但一切都需要更扎实的史料来支撑。
结语
目力所及,难以考察现有扶苏、蒙恬信仰在历史时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衰分布全域情况。但崞县、代县蒙恬扶苏文化信仰在方志书写与历史文化流传中的表现,充满了长城地域文化色彩。民间记忆无视真实历史的变迁,直接移植入长城时空下的“当地”信仰,获得地方文化认同,突出其“忠孝仁义”等文化内涵。方志纂修过程中,也运用历史考证与传统认知过滤文本,进行增添取舍。但信仰虚实、传说附会,方志书写往往进行“此厚彼薄”的偏移加工。方志纂修者舍不得轻易删动相关内容,存留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地民众信仰与文化记忆的官方背书,真假已是次要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