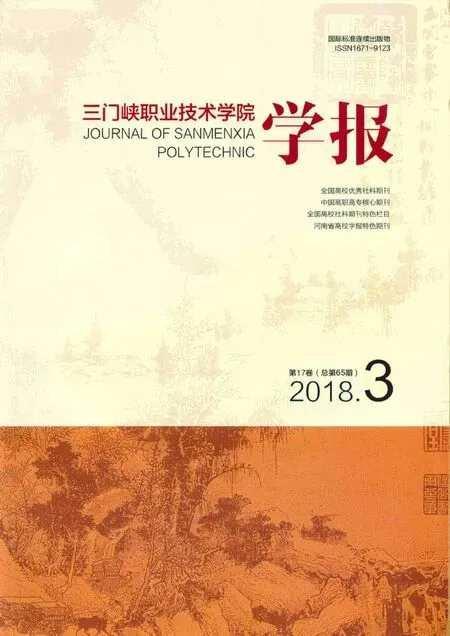《论语》与《孟子》仁义概念考察
◎徐啸雨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2)
“仁”与“义”这两个概念在儒家学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论语》《孟子》这两部儒家著作对此做出了初始设定。为了了解“仁”“义”这两个儒家核心概念在先秦原始儒学原初状态时的意义,需要对《论语》与《孟子》中的“仁”“义”做一番考察与比较。
一、《论语》中的“仁”
在《论语》中,“仁”的出现频率极高,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对于“仁”的解释也是根据语境或对象的不同而变化的。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1]
可以看出,上文中“仲弓问仁”,孔子是从其为人处世的角度来说的;而“司马牛问仁”,孔子则是从其言语行为而言的。因而,“仁”的意义可以因语境而有所不同,难以用一个简单的定义统摄。不仅如此,有时候,在《论语》中,对于“仁”的理解甚至是矛盾的,如: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1]
有子是孔子弟子,他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且很明显对于“犯上作乱”的不忠行为是不齿的,但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却又似乎与此观点相左: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1]
公子纠乃齐桓公之兄,却为齐桓公所杀,按理说,桓公是严重违反了“悌”。而管仲原本是公子纠的老师,与召忽同事于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活了下来,后来居然又辅佐齐桓公,这可以说是严重违反了“忠”(这大概也是后来孟子贬斥管仲的原因)。但孔子却赞许管仲,称其为“仁”,这与“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明显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并非不能理解,正如徐复观所说的那样:一直到现在为止,人与人相互之间,谈到人自身的现实问题时,有的仅是适应现实的环境而说的;有的则是直就应然的道理而说的。同时,一样的话,说的对象不同,表达的方式也常因之而异。有的仅适于某一特殊对象,有的则可代表一般原则。读古人之书,尤其是读《论语》,若不把上面这些分际弄清楚,便会以自己的混乱,看成古人的矛盾。[2]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仁”这个概念在《论语》中的复杂性。但无论怎么复杂,其内涵毕竟是由“仁”这个能指所统摄的,因此其内涵必然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性。
《说文解字》中对“仁”的解释是:“亲也。从人从二。”而段玉裁的注中则说道:“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3]可知“仁”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亲相爱,而在《论语》中,孔子也有过与此相符的表达:“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1]
结合《论语》全书,可知孔子的“仁”就是建立在“爱人”的基础上的,以人性中“爱人”的基本能力为起点而发展出一系列善意与善举。而这种“爱人”又是建立在差等的基础上的,即要先保证对自己亲近的人能有所爱,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地扩充至外,正如在《论语·子路》篇中记载的那样: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1]
在孔子看来,“大义灭亲”并不是他心目中的正直,而父子相互隐瞒才算是。这是因为揭发自己的亲人不符合基本的人性,于“仁”有亏,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怎么能要求他去爱亲人之外的人呢?只有服侍好了自己的亲人之后,才能“泛爱众”,这就是有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的原因。
但在孔子那里,“仁”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修养的境界,故《论语·宪问》云: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
可见,孔子在个人修养之上还包含着一定的政治诉求,即通过“仁”建立起一个和谐安定的大同社会,若是有人能完成这一使命,则其甚至可以超越“仁”,而达到“圣”的境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1]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甚至仅仅是形式上的“爱人”。事实上,孔子十分厌恶那种没有原则但又四处讨好他人的“乡愿”之人,称他们为“德之贼”。在《论语》中,“仁者”不只会爱人,也会厌恶人: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1]
厌恶之情人皆有之,但只有仁者才能真正抛开利益仅从人品出发去喜欢一个人或是厌恶一个人。
而仁者所厌恶的,必然是不仁的恶人,对于这种人,仁者绝不会毫无原则地一并爱之,而是会对其
产生厌恶之情,但若是仅停留在厌恶的程度,则又似乎有些不足,所以紧接着《论语·里仁》又记载道:“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1]
上一章才说了仁者会有厌恶的人,下一章却又说“志于仁”便没有厌恶的人了,此二章看似矛盾,但略微深究便可知其真意,钱穆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解读:仁者必有爱心,故仁者之恶人,其心仍出于爱。恶其人,仍欲其人之能自新以反于善,是仍仁道。故仁者恶不仁,其心仍本于爱人之仁,非真有所恶于其人。若真有恶人之心,又何能好人乎?故上章能好人能恶人,乃指示人类性情之正。此章无恶也,乃指示人心大公之爱。[4]
对于“不仁”的厌恶本身也是一种“仁”,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不仁”的侵袭。到了这一步,“仁”已不再是简单的“爱人”,而已然升华为一种道德原则了,但就如前文所说,“仁”这个概念具有极强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而匡亚明则将这些性质称之为“伸缩性”,即“仁”是分层次的,而孔子在不同的情况下以及面对不同的学生时对于“仁”的各种描述实际上是“仁”在不同层次的表现形态,而这些形态都为最高层次的“仁”所统摄。[5]
正因为“仁”是一种全面性的道德原则,故很难用某个具体的、片面的定义去囊括、描述它,而由此产生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后世宋明理学之滥觞。
“仁”既然是一种“全德”,要达到必然是不易的,需要下一系列的工夫,所以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1],这就颇有《大学》中“格物致知”的意思了,而孔子确实也很重视“学”这一行为,《论语》一上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1],而他也多次推崇和赞美“学”: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1]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公冶长》)[1]
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朱熹注此章时便说六艺“皆至理所寓……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6]由此可知,要在道德上达到高深的修养,不仅要反省内心,还要向外求索,在具体的实践中体会与展现,这就是“学”。而孔子对于自己“好学”的骄傲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忠信”。
综上所述,《论语》中“仁”是一种全面性的道德原则,它以“爱人”为起点,使人将自己的善心由亲及疏地扩充至外,但这种对人的爱并非是泛滥的、无原则的,而是有着特定的标准的,若有人违反此标准,则这种爱会转变为憎恶,而此种“恶不仁”同样也是仁的一种,这也反映出了“仁”的具体形态是多样的。虽然如此,“仁”还是有一定的固定形态的: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1]
孔子一以贯之的“道”自然是仁。忠是尽心尽力,恕是推己及人,二者都是将心比心的结果,也是“爱人”这一情感的先验条件,因为所谓的“爱”或“同情”大多都是人们进行换位思考、想象自己处在他人处境后的产物,是同理心发挥作用的结果。所以“忠恕”是“仁”的基本形态,但即便如此,“仁”在《论语》中始终都还是模糊的,而到了孟子那里,“仁”的内涵才开始由模糊走向明晰。
二、《孟子》中的仁义
“义”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且意义远不如“仁”那样丰富,大多只是表示“正当的原则”这一意思,《礼记·中庸》里说“义者宜也”,朱熹注“君子喻于义”时也说“义者,天理之所宜”[6]。而孟子则将“仁”与“义”并用,构成了“仁义”这个概念,并将其与其他概念结合,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义理体系。对于使儒学体系走向抽象化、概念化来说,孟子实功不可没。
孟子虽并用仁义,但这两个概念在其体系中依旧是各自有着较强的独立性的,这一点从他那经典的“四端”说便能看得出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公孙丑上》)[7]
很明显,此处的仁、义、礼、智四者是并列关系,即各自独立的。而这四者中,又以仁与义为主导,而礼与智只是达到仁义的手段而已,孔子就已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而孟子则直接将礼与智视为巩固仁义的手段:“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离娄上》)[7]
虽然这里的“义”指的是一种孝悌关系,且在《孟子》中“义”字也曾在不同的语境中有过不同的意思,但从四端的角度出发,则可知“义”是一种以羞恶之心为基础的具有道德色彩的本性。之所以说义是本性,是因为在孟子看来“义”不是外界加诸于人的,而是人所固有的,这便是孟子的“仁义内在”说,而与此说相对的,则是告子的“仁内义外”说,二者的分歧在于“义”到底是内在固有的还是外界加诸的。
告子之所以持“义外”的观点,与义的触发条件有关,他说:“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告子上》)[7]
告子认为,爱自己的弟弟,不爱秦人的弟弟,这种孝悌之爱属于“仁”,是因为弟弟与我有血缘关系,即以自己作为判断标准的,所以仁是内在的。而对于年长之人的尊敬则是因为此人的年龄,这种年龄是外在对象的一种客观属性,所以义是外在的。
很明显,在告子看来,“义”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对于老者的尊敬并不是出于人类的本性,而是特定的社会形态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并不是人类本性的延伸与扩充,而是为了满足人与人共存的种种要求,或是为了防止出现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式的社会。总而言之,告子之“义”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并非出自人的本性。
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其实是为其人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服务的,在告子那里,仁是对于亲人的爱护,而这种来自血亲关系的爱是内在的,但未必全是善的。而义则不同,义本身就是正义与善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在告子看来是外界加诸的,并不在人的本性之内,所以人性无所谓善恶可言,只能像湍流的水一样,有什么样的引导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从义并非出自人的本性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推出告子之“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本性有压抑的,而告子自己也说过,把人性纳入仁义,就好像把树木做成杯盘,这一点也为孟子所批判,认为这种理解是对于仁义的祸害,因为这样一来,仁义就失去了自然层面的合理性,而仅仅沦为一种外在的规范了,而这一规范既然是外在的,就有着被破坏、被去除的可能性。因此孟子如果要让仁义长存,则必须论证其自然正当的合理性,所以他才强调仁与义都是内在的。
虽然孟子与告子在“仁是内在固有的”这一点上并无分歧,但在《孟子》中,告子对于“仁”的理解仅限于血亲之爱。而儒家之仁,如前文所说,是人同理心的结果。故告子之仁与孟子之仁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因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孟子既然将仁义连用,就说明仁和义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个问题要先从孟子对于“仁”的分析入手。在《公孙丑上》中,孟子提出了他那段经典的论证:“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7]
人之所以会对落入井中的孩子产生恻隐之心,不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不忍人之心”,而这里的“不忍人之心”很明显是同理心的一种表现,所以恻隐之心就是“仁之端”。需要注意的是,恻隐之心仅仅是“心”而非“行”,仅仅是“仁之端”而非直接就是“仁”。这样一来,孟子不光保证了“仁”的普遍性,同时也回击了那些以恶行来否定性善论的论调,因为虽然人心有着成善的可能性,但若不加以良好的引导,这种“仁之端”就会被埋没,造成“失其本心”的后果,但这一后果是由于引导失误,而非因为人性本恶。而对于“不忍人之心”的演绎,还有一个更经典的案例,那就是孟子见齐宣王: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梁惠王上》)[7]
从常人的角度来看,齐宣王的行为实在是有些荒谬,如果说不忍心一个生命无罪却被杀死,那难道羊不是生命(则牛羊何择焉)?为什么要用羊来代替牛?如果这不是一种拙劣的伪善的话,那大概就只能是吝啬了(百姓皆以王为爱也)。但孟子敏锐地捕捉到了齐宣王的“心”,将其定义为“仁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在于“不忍其觳觫”,而非“无罪而就死地”,对于齐宣王来说,牛那受惊战栗的活生生的形象已经呈现在他的意识中了,而羊则不然,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牛的恻隐之心已发,而为了维护这已发的恻隐之心,齐宣王才要用羊来代替牛去祭祀。也就是说,齐宣王是有着行仁之心,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践了的。而孟子则抓住这不易察觉的“仁之端”来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人对同类的同理心必定远大于对于普通动物的同理心,所以如果一个人都开始对动物产生同情了,那一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能够同情人了。在孟子的学说中,“心”与口耳目等生理感知器官有着同质性,所以孟子将同理(情)心当做一种能力进行了一系列的类比: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梁惠王上》)[7]
孟子在此处的论证逻辑是:如果一个人的某种能力已经能做高要求的事情了,那么他就必然能做同种类的低要求的事情。力气大到能够举起三千斤的东西的人必然能够举起一只羽毛,视力好到能够看到秋天动物的毫毛的人必然能看到一大车柴草。由此便可以推导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仁慈得能够连动物都同情的人,必然是有能力同情人民的。于是孟子尖锐地指出:齐宣王的同情之心之所以没有能够下达到人民那里,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去作为。有能力去关爱人民却没有这样做,因而使得人民陷入悲惨的生活,这就是齐宣王的罪过了,这样一来便可引出齐宣王的羞愧之心,而这种“羞愧”便是羞恶之心中的“羞”。
所谓羞,是对自身过错的一种愧疚之情,换言之,只有当自己有过错的时候才会产生羞愧,而在《梁惠王上》的这段叙述中,齐宣王之罪是他对于人民没有行仁政,是由恻隐之心推出的。有了恻隐之心,知道了善的方向,才有对于“不仁”的羞愧。而羞恶之心是对一个主体行善的警醒与保障。一方面,恻隐之心唤起的是人与人的互相关怀,这是积极的善;另一方面,羞恶之心唤起的是人对于自己“不仁”的怵惕,时刻警醒自己对人要“无伤”,这是消极的善。一是给予关怀,一是不加伤害,由此可见,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是善的两面,这样一来,“仁”与“义”在道德主体中便有了一种内在联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与“仁”在道德主体中构成了内在联系的“义”,只有在主体的过错涉及对他人的伤害时才成立,故这种情况下的“义”仅仅是义的一种形态而非全貌。因为并非所有的羞恶之心都是由恻隐之心引起的,所以并非所有形态的“义”都与“仁”有内在联系。
综之,“仁”与“义”在《论语》和《孟子》中的异同在于:
在两部著作中,“仁”是一种建立在同理心基础上的、以“爱人”为起点的道德原则,这是其相同之处。但“仁”的内涵在《论语》中较为模糊且多变,而在《孟子》中则更加明晰且稳定。
就“仁”的获得来看,《论语》中孔子强调“学”,孔子之仁是与对于外界的求索联系在一起的。孟子将仁跟人的恻隐之心联系起来,即不学而能,不需要向外界求索太多,而是需要反求诸己。即孔子侧重于知识论,而孟子侧重于价值论。
“义”在《论语》中较少被言及,且其内涵较为单薄,但在《孟子》中却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地位也被提到了与“仁”同等的水平。
《论语》中“仁”与“义”是两个分离的概念,而《孟子》中“仁”与“义”这两个概念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并都得到了细致的阐述与发展,而孟子直接将这两个概念并用,发展出了“仁义”这个道德概念,开了儒家义理与心性之学之先河。